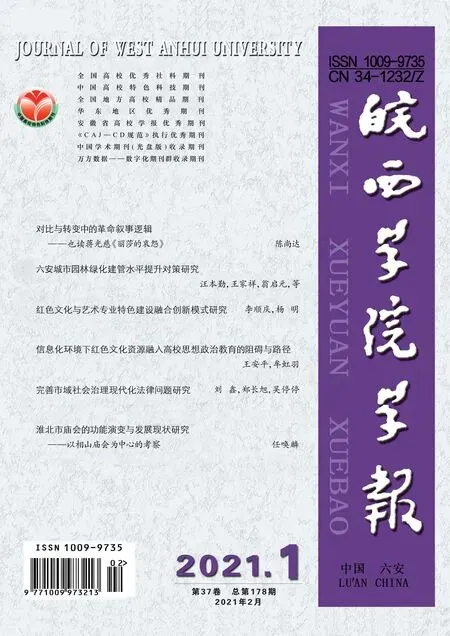“仁”与“敬”
——孔子与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比较及其现代启示
谢狂飞
(枣庄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枣庄 277100)
毋庸置疑,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字“仁”,作为孔子“吾道一以贯之”①(《论语·里仁》)的“仁”字,总共在《论语》中出现了109次,无论在其深刻的德性伦理内涵上还是在其对“仁”的“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强调和提醒上,都体现出“仁”的思想在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重要作用。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孔子是从道德心的意义上树立“仁”在儒家道德哲学中的本体地位的。从德性践履实践的维度来看,孔子强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就突出了德性主体自觉自动自发地行仁践仁中的自主性。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孔子之“仁”作为儒家德性伦理的核心概念,它揭示了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德性之本源和本体。“诚于中,形于外”(《礼记·大学》),所有体现在德性主体之生活世界的德性实践现象的根源都是德性主体的内在之仁。“仁”统摄儒家德性伦理的诸多德性范畴与德性分支。对于儒家德性伦理来说,仁即“一体之仁”,正如王阳明所说:“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夫然后,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P252)
孟子在孔子之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充,得出其性善论。贯穿孔子之仁精神的孟子性善论构成为儒家德性伦理之拱心石。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康德的善良意志论(good will)。康德指出:“在世界之中,一般地,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2](P8)换言之,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可以类比于孔子之仁,康德的善良意志也构成为道德形而上学进一步追问的原初始基。而且,当康德说到善良意志的时候,他用的词是“无条件善”,这就直接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向让人“敬畏”的理性的高度。
康德的道德哲学一般被称为义务论,这本身就传递着一种敬畏和责任。康德道德哲学为了建立道德的纯粹性和神圣感,甚至试图要摒弃感性意义上的德性践履之目的,换言之,按照康德的观点,实践道德不是为了幸福,也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所谓的外在功利,而只是为了道德义务本身。康德认为:“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称为伦理学。前者是自然学说,后者是道德学说。”[2](P35)
从形而上学或所谓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的“道”的高度来说,康德所说的自由就不是一种外在意义上自由,而是“由自”或“由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的生命内在道德学问意义上的道德自由,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德行为自主的自由。这种道德自由超越外在的诸多条件的束缚或限制,这种道德自由使道德主体能够做到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诚如康德所言:“善良意志,并不因它所促成的事物而善,并不因它期望的事物而善,也不因它善于达到预定的目标而善,而仅仅由于意愿而善,他是自在的善。”[2](P43)因此,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与孔子的仁学思想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对提升现代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较大的意义。
一、仁与敬的德性内涵探析
孔子仁学的本质就是儒家的学以成人的立德树人的成德之教,而“持敬”和“诚敬”则是使儒家成德之教成为可能的至关重要的工夫,作为道德实践的深层次的源头活水的精神动力,诚敬绝非无源之水的涵养,而是真实的道德实践之精神动力。康德道德哲学同样非常重视“敬”。尽管康德承认“敬”作为崇高的道德情感是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层面的,但“敬”本身作为一种道德情感的产生又离不开生活世界在经验层面的建构。即使是所谓的先验的概念预设,也是无法摆脱经验层面的道德实践凝聚的。而且,康德本身重视由一种内在诚敬之心所引发的人的类似于孟子所说的“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的知耻和谦卑之心。
康德强调:“但既然这个法则毕竟还是某种就自身而言肯定的东西,也就是一种理智的因果性的形式,亦即自由的形式,所以,由于它与主观上的对立物,亦即我们心中的偏好相反在削弱自大,它同时就是敬重的一个对象,而且由于它甚至击毁自大,亦即使之谦卑,它就是最大的敬重的对象,因而也是一种肯定的情感的根据,这种情感没有经验性的起源,是被先天地认识的。因此,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是一种通过一个理智根据造成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唯一我们能够完全先天地认识的,我们能够看出其必然性的情感。”[3](P70)
“敬”是儒家德性伦理传统的一个重要的德性范畴。从儒家德性伦理的视角来看,“敬”本身就源于其“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伦理之社会属性,并且“敬”本身有着源远流长的德性范畴发展的历史。《尚书·尧典》上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事实上,《尚书》中充满了关于“敬天”和“敬德”的论述,因为只有做到“敬天爱人”才能做到因为敬畏和感恩而带来的“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七十九章)。
《诗经》也强调:“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大雅·民劳》”。《尓雅·释训》上说:“穆穆肃肃,敬也。”《说文·苟部》:“敬,肃也,从攴、苟。”儒家德性伦理中的“敬”包含着“肃穆”的意思,也包含着孟子所说的“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的恭敬之意。之后,“敬”慢慢延伸出“尊敬”的意思,《论语·先进》记载:“门人不敬子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这也体现了一种虔诚恭敬之心在行使儒家之礼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儒家德性伦理在谈论作为一种德性范畴的“敬”的时候,是直接针对德性主体所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的真实的生活经验世界的,这就真正具有一种基于儒家德性伦理实践品格的现实德性人生的指导意义。
正是基于儒家德性伦理的实践品格,儒家在讲“敬”的时候不会走向一种“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的极端,而是遵循一种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孔子还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这就体现了孔子“以仁换仁、以心换心”的从伦理关系的两方面看待伦理实践的中庸之道的原则。“敬”的基础就是“仁”,事实上,“仁”在本体的高度成为所有其他儒家德性伦理德性范畴的共同德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仁”是儒家德性伦理范畴体系的总德或全德。“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经解》)“仁”本身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德性主体要有道德情感意义上的对他者感受的“感觉能力”。没有这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对他者的道德情感的感受能力,就会导致一种“麻木不仁”的德性冷漠状态。针对这种“不仁”的状态,孟子不禁感慨:“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孟子·尽心章句下》)
相比之下,康德是这样来看待“敬”的,他认为:“它们是道德情感、良知、对邻人的爱和对自己的敬重……对它们的意识不具有经验性的起源,而只能是作为道德法则对心灵的作用,在一种道德法则的意识之后发生。”[4](P411)康德否认“敬”作为一种道德情感的经验性的来源,而将其归结于一种预设的抽象的道德法则。这一方面使“敬”有了一种基于纯粹思辨理性的让人敬畏的崇高感,一方面又因为其抽离了生活世界的经验维度而变得让人感到高不可攀,于是使人感到可敬而不可亲。儒家德性伦理的传统是常常将“敬”和“爱”连在一起来用的,正如《战国策·秦策三》所记载:“质仁秉义,行道施德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
要说明“敬”在儒家文化中的特点,就必须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总体注重实践智慧的特点来讲。儒家实践智慧本身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篇》)光有所谓的德性之知,或者说光是在理论理性上知道了什么是一个仁者应该过的生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到“仁守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仁智双彰或知及仁守,还需要做到“庄”和“礼”,才是真正的完整的对儒家实践智慧的理解和运用。相比于思辩理性,儒家显然更加重视道德实践实用理性意义上的实践理性。孔子说“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篇》)孔子所担忧的不是自己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德”或者“什么是仁”,孔子担心的是学生不去实践仁,不去行仁。儒家德性伦理不会抽象的谈论抽象的概念意义上的“敬”,而是结合在中国儒家德性伦理传统中特别重视的“孝”的伦理实践中,“孝”和“敬”连在一起成为孝敬,贯穿于儒家德性伦理德性践履的始终。《诗大序》有云:“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左传》亦云:“孝敬忠信为吉德”。孔子更是将“敬”视为孝的灵魂和核心,孔子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有了孝敬的发自内心真诚的尊敬和敬意作为基础,孝才成为真正的孝,这种敬使得人的孝有了一种让人敬重的德性高度。
二、仁与敬的内在逻辑关联及其伦理意蕴
在儒家德性伦理的视野中,道德情感与实践理性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从儒家德性伦理的观点来看,道德情感就是最高的道德理性。总体来说,在康德道德哲学的视域里,康德是重理性而轻情感的。尽管康德说过“善是被敬重的、被赞叹的东西,换言之,是我们赋予其相当程度上的客观价值的东西。”[5](P52)但康德所说的道德之“敬重”情感更多的还是从纯粹理性的视角来说的,这种崇高到让人战栗的“敬重”情感使人感受到是一种“敬而不亲”的道德敬畏感。
而孔子所说的“敬”是与德性主体所具备之道德心紧密相连的。说到儒家德性伦理视域下的“敬”,我们要一起看到《论语》中的一段经典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针对学生宰我理性到冰冷无情的关于“三年之丧”的提问,孔子并没有用同样的思辨理性意义的逻辑概念来回答,因为孔子非常清楚,宰我这个学生缺乏的不是所谓的思辩理性能力②,而是从人的道德良心出发的德性践履能力。换言之,在孔子的眼中,所谓的“心安理得”,“心安”比“理得”更重要,更具有实践逻辑的优先性。同时孔子强调,“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以爱说仁,由仁讲孝敬。这是典型的情理融合的儒家德性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实践智慧。儒家德性伦理重视的是德性之行,而不是德性之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德性之知意义上的“博学之”最终要落实到“笃行之”的德性践履中去,这才成为知行合一意义上的真正的德性之知。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指出:“义务就是出自对法则的敬重的一个行为的必然性”[6](P407),同时,康德还说:“我直接认作对我是法则的东西,我亦以敬重认识之,敬重仅仅意味着我的意志无须对我的感官的其他影响的中介就服从一个法则的意识。”[6](P408)为了保持敬重的纯粹性,康德一直试图在纯粹理性的意义上来界定何谓敬重,这一方面使人感受到敬重作为一种道德情感的高尚感,另一方面又让人感受到对于敬重这种道德情感的望而生畏的距离感。
从儒家德性伦理的视角来看,当德性主体在遭遇到一种德性考验的现实处境的时候,它首先想到的不是抽象思辨理性意义上的崇高道德法则,而是回归到自己的本心的直觉,换言之,就是看自己是否心安?康德则认为,尽管敬重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是来自于经验层面的生活世界,但产生敬重之道德情感的根源则是在纯粹实践理性中。这种理论建构意义上的曲折和诘屈尽管在表层理论建构的精密性上显得特别严谨,但却缺少一种直指人心的德性践履指导力。
孔子关注的是“于女安乎”,孟子则指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上》),换言之,儒家德性伦理是直接以心说理,心即理,理即心,即心即理,理心合一。这就实现了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的通透圆融,在现实道德生活的实践中也能真正起到对于德性主体的道德生活的实践指导作用。孟子还强调:“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孟子在这里指出了关于儒家德性伦理的重要特色,那就是打通了一般意义上的理智与情感的分隔。这样的话,理义不再只是给人一种可敬而不可亲的敬畏感或神圣感,而是给人一种可敬又可亲的真实感。
作为儒家伦理人格体现的孔子,就以其人格特质体现了这种情感与理性融合的特点。“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尽管“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但孔子给弟子的感觉依然是温润而亲切的,正如孔子弟子子贡所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换言之,孔子身上所体现的君子人格或圣贤人格其实就集中体现了儒家德性伦理所追求的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而非对立。孔子弟子对于老师的情感不仅是基于理性的敬重,更是基于道德情感的敬爱。孔子也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篇》)根据《孟子》的记载:“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从这一段的述说,我们也可以看出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这份至诚感人的敬爱之情。
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的道德自律。道德自律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英文中“self-discipline”的道德律令的含义。这种道德律令是尽可能要排除人之感性或情感的影响的。康德所主张的道德自律就是要求道德主体根据纯粹的思辨理性意义的道德律令来进行相应的道德行为,为了确保这种道德律令让人敬重的神圣性,就必须摒除一切人为的主观情感的影响。即使康德讲幸福,他也不是从儒家所注重的“孔颜乐处”意义上来讲真实的生活世界的幸福的,而是从所谓的幸福律令角度来讲的。
康德认为:“道德律客观地、直接地在理性判断中规定意志;但只有通过法则才能规定其原因性的自由却正在于,它把一切爱好、因而把个人的自尊都限制在对自身纯粹法则的遵守这一条件上。这一限制于是就对情感发生作用,并产生出能够出于道德律先天地认识到的不愉快的感觉。”[7](P107)康德是在所谓的“道德律”意义上来讲作为一种崇高道德情感的敬重的,而相比于康德所说的道德律,儒家德性伦理更多重视的是“道德心”。
儒家道德心熔铸着儒家重要的中庸之道的思想。而遗憾的是,伦理学的发展往往容易在一种对于纯粹理性或纯粹情感的极端追求中摇摆。“对于伦理学来说,由此导致的结果在于:它在其历史上或者被构建为一门绝对先天的伦理学,而后是理性的伦理学,或者被构建为相对经验的和情感的伦理学。几乎没有人问过:是否就不存在一门绝对的并且情感的伦理学。”[8](P308)休谟更是将情感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极端,他说:“理性是,且应当只是情感(passions)的奴隶,而且除了服侍和服从情感,理性不得自称有任何其他的职责”[9](P360),休谟这个论断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说法,为了限制理性的宰制作用,将情感的作用推向了极致。这又导致了另一个维度上的过犹不及。当然,休谟这里用的英文单词是“passions”,这个词本身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讲的道德情感(moral emotions)的情感之意。“passion”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一种极其强烈的情感。孔子强调要对情感进行适度的节制,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孔子从来都主张要节制,因此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篇》)最重要的是内心的真诚的情感,而不是一种过度的表达。“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儒家所追求的情感理性就是追求一种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的符合中庸之道的德性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儒家德性伦理的视角来看,纯粹思辨理性意义上的道德先验和实践理性意义上的道德经验二者是统一的。包括敬重在内的道德先验之崇高律令是来自于真实生活世界之大量道德实践经验的凝聚而道德实践之经验则是道德理性之先验观念在生活世界的具体体现。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孟子·尽心》)
对于孔子来说:“仁”不仅是一种客观的评价人的德性境界的静态的标准,更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篇》)的“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的生命学问的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道德实践。所以孔子也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充分肯定德性主体的自觉对于德性建构的作用。“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无论是自我德性的日臻完善或止于至善,还是外在人生事业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成长,都需要通过从德性主体自身出发的自觉的自强不息的“弘道”的实践才能成为可能。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论语·泰伯》)根据《说文》:弘,弓声也。后人借‘强’为之,用之‘疆’义。此‘弘’字即今之‘强’字。“毅”是坚毅之意。“弘毅”指的就是一种对弘大志向的奋力担当和坚韧践行。
康德是将道德情感意义上的敬重感视为一种所谓的特殊的情感的。尽管这种敬重感是不能离开感性意义上的经验世界的,但其根本动力则是来自于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也就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意义的超越界。
这就造成了人的情感和理性的分隔,也造成了德性践履无法做到孔子所说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的“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的德性伦理意义上的“知情意行”的通透贯穿。从儒家德性伦理的视野来看,德性主体的德性践履动力不是来自于一个所谓超越生活现象界的“物自体领域”内的崇高的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来自于自己的本心和良知。
三、仁与敬的现代德育启示
康德说过:“由德性的法则对意志所作的一切规定的本质在于:意志作为自由意志,因而并非仅仅是没有感性冲动参与的意志,而是甚至拒绝一切感性冲动并在一切爱好有可能违背这法则时终止这些爱好的意志。”[7](P99)在康德看来,敬重感更多的是指一种神圣的对德性主体来说的约束作用。而且康德认为它是一种悬置在感性之上的理性宰制人的道德意志。有了一种崇高的基于道德律令的敬重感,德性主体就能超越一种充满变化的感性现象的干扰进而做到对于崇高道德律令的忠诚。康德认为,只有摒弃充满变化的德性主体情感性的因素,才能保持道德法则的纯粹崇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德是在敬重感的意义上来框定人必须去进行相应道德实践的道德意志。崇高的道德法则激发人对道德律令的敬重之情,这份崇高的敬重之情又使德性主体在面对这些道德律令的时候产生一种澄明诚挚的谦卑,而这份谦卑进而使人去服从这些崇高的道德律令。因此康德说:“其表象作为我们的意志的规定根据而在我们的自我意识中使我们谦卑的东西,就其是肯定的、是规定根据而言,独自就唤起敬重。因此,道德法则即便在主观上也是敬重的一个根据。”[10](P80)这就正如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换言之,在康德的道德世界里,激发德性主体道德实践的动力是来自于神圣的道德律令,这种道德律令因其崇高神圣而让人心生敬重和震撼,进而因为这种敬重和震撼而使德性主体去进行具有真正道德价值的纯粹的道德实践活动。
儒家德性伦理超越了这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书·东方朔传》)的极端化的对于道德实践的理性思考。儒家德性伦理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
针对道德实践之精神动力,孟子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经典论述:“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在孟子举的这个经典例子中,孟子指出:德性主体要救“将入于井”的“孺子”的时候,要自觉排除一切外在的感性考虑,只是去无条件的遵循自己的道德本心和良知。这本身同样体现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境界超越性,但这种超越性是“不离日用伦常”的,是不与真实的生活世界相阻隔的。是从德性主体的本心直接发出来的,是不假思索的。德性主体的本心就蕴含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四端之心”,这种四端之心本身就浸润着康德所说的敬重感。这种敬重感不是基于一种抽象的道德律令,而是基于道德本心对于生命的敬重。
孟子强调:“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道德情感意义上的敬重感同样应该是感知于身,发乎于心而践之于行的。从儒家德性伦理的角度来说,这种道德敬重感是建立在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的敬重的基础之上的。
尽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高度强调“人是目的”的思想,但康德依然认为:“人虽然是够不神圣的了,但在其个人中的人性对人来说却必然是神圣的。在全部造物中,人们所想要的和能够支配的一切也都只能作为手段来运用;只有人及连同人在内所有的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本身。因为他凭借其自由的自律而那本身神圣的道德的主体。”[7](P119)在康德眼中,人的神圣不是因为人之为人的本身,而是因为其被抽象出来的道德自由和自律,而在儒家伦理中,人之为人的可贵是在人之“知情意行”各个维度的全幅呈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篇》)这就直接体现了孔子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的思想。
“仁者,人也。”(《中庸》),人是具备仁德之心的。人是可以通过不断的“止于至善”和自强不息的努力使自己实现人之为人的境界的不断提升的。正如孔子所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人可以在知、勇、礼乐等各个方面实现自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论语·子张》)的生命成长的。孟子也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
作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唯一被强调的道德情感,敬重感遵循的依然不是一种儒家德性伦理意义上的真切真实的道德情感,而是基于纯粹道德律令的设定。换言之,康德注重的不是作为德性主体的人本身,而是德性主体纯粹出于道德义务的道德实践。但是,康德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德性主体要关切而且必须关切在他看来神圣的道德法则本身而不是人本身。而在儒家德性伦理的视角下,不存在抽象的超越于真实人心的所谓的纯粹的道德法则。即使是有这样的先验意义上的道德法则,也是发端于人真实的人心世界和道德情感的。
在儒家德性伦理的视角看来,“敬”作为一种真诚的道德情感,是经过后天的修身养性的德性践履才能达成的。而且,这种“敬重”之道德心是外在德性延伸的基础。根据《论语》的记载: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篇》)《论语》里提到“仁”是109次,提到“礼”是70多次,而提到“敬”是20多次。如“敬事而信”(《论语·学而篇》),“居处恭,执事敬”(《论语·子路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周易·坤》也记载:“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总的来说,从《诗经》雅、颂部分开始,“敬”的含义主要就是严肃、恭敬。有了发自内心的诚敬之心和敬重之意,方才能有足够的面对内在良知的敬畏与戒慎恐惧。这种发自内心的谦卑和诚敬是建构和培养一切其他范畴的基础所在。
“敬”本身是既作为本体又作为工夫而存在的。也就是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相比于康德的道德哲学,具体来说,相比于康德关于敬重感的论述,儒家德性伦理传统注重对生命学问视域下的整体德性观照。它不仅注重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性,也注重内在心性超越性的深层德性架构之建构。正如王阳明所强调的那样:“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卷上)[1](P92)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王阳明非常注重本体和工夫的统合。他强调:“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黄宗羲指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明儒学案序》)这就意味着儒家德性伦理将本体和工夫本身熔铸成了一个整体,而不像康德一般意义上的在本体与工夫之间的隔绝。正因为此,孔子指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后来二程以《周易·坤·文言传》里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为基本的理据,明确将“主敬”作为儒家德性伦理之重要的修养践履路径。
朱熹明确指出:“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到程子始关聚说出一个敬来教人。”[11](P208)朱熹在这里明确指出“敬”是圣人教人的方法。只有通过敬重的道德情感的道德动力凝聚,才能实现孟子所说的“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孟子·告子章句上》)的收摄心性的目标,进而达到孟子所说的“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集义”的目标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的“放心”和“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的修养身心的德性践履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寡欲”,因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章句下》)
总之,儒家“仁”学思想超越了一种思辨理性意义上的逻辑概念分析的理性宰制,直指人之为人的情感理性本质。“仁”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而且体现着“生生之谓仁”的儒家德性伦理之教育精神,即仁者爱人和有教无类。仁是道德敬重的基础。
敬重感是康德道德哲学一个重要概念,它将人的内心之道德律令或道德法则提升到了让人战栗的止于至善的高度,这种道德情感意义上的敬重感推动人的自觉的道德实践并且使道德实践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孔子之仁与康德之敬,分别体现了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二者分别对于德性主体德性践履的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比孔子之仁的思想和康德之敬重感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升现代德育的有效性。
注释:
① 尽管关于曾子所说的“忠恕”是否能够成为孔子所说的一贯之道依然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但毋庸置疑,忠恕是仁的重要内容,根据《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② 事实上,宰我这个学生不仅不缺少所谓的理性意义上的思辨逻辑推理能力,而且应该是孔门弟子中在这方面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根据《论语》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宰我在言语科方面甚至超过了辩才无碍的子贡排名第一。但宰我在《论语》中也是被孔子批评最多的和最严厉的。“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篇》)甚至可以说,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也是针对宰我这样的学生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儒家伦理对实践理性的重视。儒家伦理甚至认为:思辨理性过度的发达会阻碍一个人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