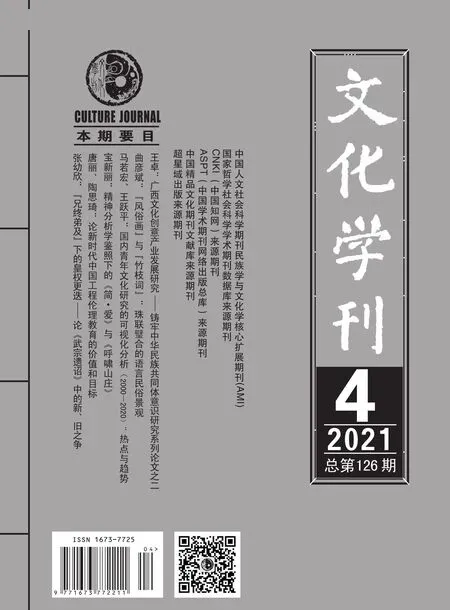论《文心雕龙》中“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
王欢欢
《文心雕龙》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之所以能够辗转承新、影响深远,与其学术态度与研究方法息息相关。刘勰将“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贯穿《文心雕龙》始末。本文旨在分析“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以探究其在文学研究中的意义。
一、“唯务折衷”概念的提出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到:“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者,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1]578可见,刘勰在处理“同”与“异”的关系以及对待“前人”与“今人”的态度上,采取了“唯务折衷”的方法。无论与前人的观点是否相同,均“不屑古今”,要进行有条有理的论述,力求做到“唯务折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止一次提到“折衷”这个概念。例如,《知音》篇有云:“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1]553文学评论者多凭主观好恶,满足于一隅之见,从而得出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见解,若以此衡量千变万化的文章,则无法做到全面、客观,故需采用“折衷”的态度和方法。刘勰论及诗赋用韵时提到:“若乃改韵徙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贸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1]397在这里,刘勰认为诗赋若因两韵一换造成声调和音律生硬、急促,或者因百韵不换导致诵读出现烦劳,均是不可取的。为达到“庶保无咎”的境界,刘勰提出了“唯务折衷”这一解决方法。
据上述可知,“唯务折衷”是公允、恰当之意,即进行文学评论时要透过现象看到评论对象本身的合理性,实事求是地给出全面且公允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折衷”有别于儒家思想中的“折中”概念,儒家的“折中”是指“中庸”。“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且认为“中庸”是“至德”,但他未对“中庸”的具体含义进行明确阐释。《说文解字》:“中,正也;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这也就是说,要妥当地处理事情。笔者认为,“中庸”可理解为强调对立双方的和谐统一,不能缺略一方,亦不能偏胜其中的一方,人们在品评事物、处理问题时采取不左不右的中立态度。如此看来,“中庸”秉持的中立态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公允、恰当,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折衷”的标准是“势”与“理”。“势自不可异也……理自不可同也”[1]578,所谓“势”,是各类文章的基本格调,指客观的自然走势,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2]。“势”既是凭借有利条件而成的一种格调,又是事物自身具有的一种内在客观规律,这符合客观实际。《原道》篇中提及“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1]3。心灵产生从而确立语言,语言确立因而能表现出文采,这是自然之道。自然是文之本原,文之美,并非用辞藻“外饰”于伦理道德思想情感之故,而是“自然”即“道”本身,是“文”及其“美”的内在根据,或云“自然”本身就是“美”的[3]。“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1]10,文辞之所以能够鼓舞天下,就是因为它体现了自然之道。至于“理”,则是指事物内在的客观自然之理。
刘勰把客观的“势”和“理”作为评价的依据,如《奏启》篇中提到:“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专席之雄,直方之举也。”[1]277写作、奏文的文辞要树立规范、标准,使“理”有依据。奏文应兼具法家之长与儒家之礼,将正义之气注于笔墨中,彰显弹劾的声威,如此才称得上“直方之举”,达到“折衷”的标准。
二、“唯务折衷”方法的运用
《文心雕龙》始终贯穿着“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态度。刘勰通过运用“折衷”之法,力求突破各家局限,吸收其合理性论断,摒弃其片面性观点,最终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折衷”体现在刘勰对作家作品的品评上。例如《才略》篇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1]538-539曹植文思敏捷才华超群,其诗作具有清丽飘逸的特点,而曹丕虑周力缓,其乐府诗清丽昂扬。两人的作品各有优点,但人们因世俗之情对二人的评价有失偏颇。刘勰抛弃了“因人废言”的做法,给予二人全新的评价,未因魏文帝的显赫地位而对其文采视而不见,甚至为魏文帝鸣不平;未因陈思王的窘迫处境而提高对他的评价。刘勰对作家作品的客观公允评价,为文学批评树立了典范。
“折衷”体现在刘勰主张的诗歌情志统一方面。比如,《明诗》篇:“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1]57刘勰引用虞舜“诗言志,歌永言”的观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即蕴藏在心里的思想或愿望叫作“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则叫诗。诗的意义就是运用文辞来表达思想或愿望,它可以端正人的思想情感。可见,刘勰在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理论时,并不排斥诗歌抒情的功能,甚至认为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情感是相互联系的,既不可割裂,又不应有所偏废。诗歌创作应当做到情中有志、志中含情。此外,张少康也曾评价刘勰:“在文学创作上的‘言志’与‘缘情’的争论中,他从自己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出发,是主张情志统一的。”[4]《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58人因受外物影响而产生抒情的需要,这种感情是自然而然的。诗歌的抒情性符合“势”与“理”的标准,这是自然之道。又如《情采》:“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368刘勰认为庄子、韩非子之说存在辞采“辩雕”、事物过于浮华的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好清与浊、邪与正之间的关系,便能够在写作中运用文采。文采的作用是修饰语言,而文采本身源于作者的性情。情理与文辞相辅相成,情理明确文辞才能畅朗。刘勰将情放在辞之上,在“诗言志”的基础上肯定诗歌的抒情性,力求情与志的统一。《明诗》曰:“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1]67刘勰认为诗歌有特定的体裁格式,人的思想感情是变化万千的,只能依个人的性情选择合适自己的体裁,故而很少有人能够体悟各种诗歌之美,这也是在强调诗歌抒情性功能。因此,刘勰在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理论时,不排斥诗歌抒情的功能,传达了“折衷”的思想。
“折衷”还体现在刘勰对文体之变的评论上。《通变》有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1]348所谓“设文之体有常”,是指文章的体制安排有一定的常规之法,比如《明诗》《诠赋》《书记》等篇中有数十种体裁,其内容、格式等都有明确的规范和准则,这些是“有常”之体,在写文章之时需要继承其标准和规范,不能师心自用,旨在说明“通”。至于“变文之数无方”,是指写作技巧变化无穷。文章的语言文采、格调气势等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不像“有常”之体那样必须有所皈依[1]346。在这里,“通”是探讨文学的继承性,是刘勰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变”则是探讨文学的革新,但这个变化是以“通”为基础的,因此“通”与“变”不能割裂开。《明诗》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1]65晋代才士的为文有轻浮绮丽的倾向。东晋的诗作有老庄玄学之风,嗤笑入世从政的志向、崇尚远遁世俗的清谈。南朝宋代初年,清谈老庄之学退出文坛,山水诗开始发展起来。山水诗讲究骈俪对仗,每一句诗都有独特的价值,内容上竭力摹写景物之形貌,文辞上力求出新。刘勰能够以“势”与“理”作为标准,对各朝的文体文风进行品评,兼采各家之长,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采用了“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态度。
三、“唯务折衷”存在的意义
作为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自成书至今已有1500余年,影响深远。究其原因则是其以“折衷”的态度看待文学,能够给予历代作家及作品客观、恰当的评价。刘勰不畏惧权贵之言,不轻视位卑之作,不以当世的文学取向为据,不追逐新奇的“流行”文风,将“势”和“理”作为评价的标准。由于这个标准是自然之道,是事物自身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客观规律,所以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批评观点中辨清异同,兼取众长。刘勰的论述是符合客观实际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唯务折衷”的批评方法和学术态度给后世学者提供了标准和借鉴。刘勰把握住了“势”和“理”,使自己的评价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不盲从于“同异”,亦不在“古今”之中迷茫,只忠于事物本身的“势”与“理”,因此能在“同乎旧谈”与“异乎前论”中进退自如,遵从内心的标准,自成一家。刘勰的“折衷”理论对于评论作家及作品有诸多助益。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界追求标新立异,追新逐异的现象屡见不鲜,各类著作也称得上是浩如烟海。如何让作品更有价值,“折衷”这种研究方法和学术态度或许是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