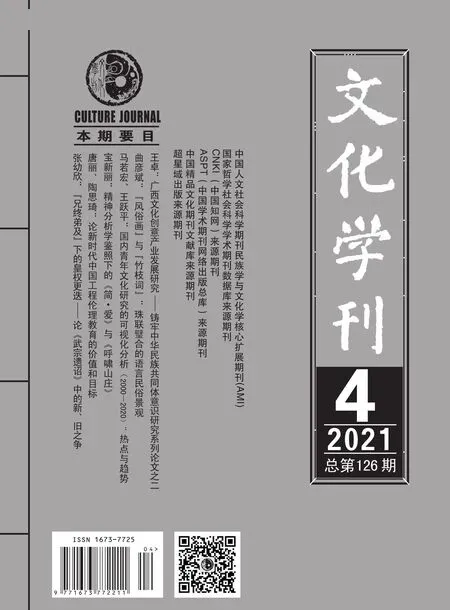开与关 联与隔
——从《雷雨》中的“窗”意象看中国近现代转型
刘 芊 关绮雯
窗作为建筑物的重要部分,在人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对日常生活而言,窗主要起到两个作用,一是与外界沟通、通风透气,二是与外界隔绝、遮风挡雨,简单来说即“联与隔”。所以,窗的本质是房屋与外界环境相通的一个开关[1]。
《雷雨》是曹禺于1934年创作的戏剧作品,那时中国现代文学正处于第二个十年发展阶段。当“窗”作为一个意象进入现代文学作品《雷雨》之中时,作者对“窗”意象的处理方式的背后蕴藏着近现代中国思想转型的特点。
一、叙事结构
窗作为连接室内与户外的物理通道,其基本作用是为窗内人展现外界环境。这种作用不仅仅停留在视觉层面,还沟通了不同的感官,形成一幅完整的图景,作者通过这种图景的构建来更好地发挥环境在文学作品中的叙事作用。这在传统文学和近现代文学中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保留、传承和发展。
(一)传统文学中的窗
对于传统文学中的窗的叙事作用,前人的探究取得了一定成就。“窗”从来不失艺术地表现环境这个叙事作用,“诗人从窗内的个体小空间望到窗外的自然大空间,但是因为诗人之望有所依托,空间形式也有层次感,所以‘窗’就像一个取景框一样。”[2]这是叙事上的联,也就是展现图景的作用。而隔的部分,传统文学更是处理得精妙,运用一扇窗将时空分割,于是有了偷看、偷听等模式,这些模式频繁出现在《红楼梦》《金瓶梅》等传统文学中。罗燕萍认为,关闭了窗,阻隔了视线,却可以让听觉敏锐、感觉澄明,此时的倾听,很多时候成为对自己心灵的倾听[3]。即通过窗表现的环境是丰富的,更有经过一层隔断、过滤后的纯粹,可以使人物的内心声音得以更细腻地表达。
(二)《雷雨》中的窗
窗在叙事上的联与隔的作用在《雷雨》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观众看见的还是四凤的屋子(即鲁贵两间房的内屋),前面的叙述除了声音只能由屋子中间一层木窗户显出来。”[4]38窗外有聒噪的蛙声,沙沙的风声,不安的狗吠;有属于人的臭气,属于夏天的难耐的热气腾腾;有黑压压的乌云和蓝森森的闪电。听觉、触觉、嗅觉、视觉,将窗内和窗外联结起来,归于一幅完完整整的雷雨来临之际的浮躁图景。窗外是暴风雨的前夕,而暴风雨是周家这个封建大家庭矛盾正式爆发的前奏。窗将屋子里的主场景与屋外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浮躁环境联通,使作者精心构建的双线结构实现巧妙的彼此暗示。雷雨,不仅仅是下在窗外,打在草丛中,更是下在窗内,轰击着这座封建大公馆。“一阵风吹开窗户,外面黑黝黝的。忽然一片蓝森森的闪电,照见了繁漪惨白发死青的脸露在窗台上面”[4]128,这句描写暗示了繁漪在向窗外偷看,不仅展示了窗外环境,也为后文揭示繁漪的阴谋埋下伏笔,使作品前后联结,结构更为完整。繁漪的偷看也是对传统文学中偷看模式的延用,窗内外,隔出的是爱情的实现与求而不得。
(三)一脉相承
当窗作为一个物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被叙述时,不论是在传统文学中还是在《雷雨》之中,它起到的都不仅仅是“窗”这个物品的作用。窗作为桥梁沟通内外,使环境更加完整;沟通前后,实现作品的前后呼应与结构完整:这都发挥了其联的作用,让作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而隔的叙事艺术则在“偷看模式”之中得以实现。这种模糊化的艺术效果受到了中国古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的审美标准影响,避免了正面冲突,使矛盾不至于激化,也于无形之中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由《雷雨》对于整体美的追求及对“偷看模式”的再现可见,在近现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人的思维模式依旧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具有独特性的思维模式在近代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仍保持其生命力。
二、主题意蕴
(一)传统文学中的窗:隔
在唐诗中,窗常常与闺怨之情结合在一起,甚至直接用窗来指代身居家中、思念远方情人的女子,“肠断若剪弦,其如愁思何。遥知玉窗里,纤手弄云和。”李郢的《为妻作生日寄意》中“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一句便直接以绿窗代自己的妻子,描绘了由于丈夫没能及时归家而独自一人泪眼汪汪地度过生辰的女子形象,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及无法陪伴妻子过生辰的遗憾。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窗成为女子闺怨之情的一个出口,这展现的其实是封建时期女性的生活模式。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女主内,应当足不出户、远离外界,在这种情况下,窗便成为女子了解外界的重要媒介[5]。唐诗中,多是在外的男子以对写的手法来描写窗,窗与女子相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审美形象。但是在古代,窗是女子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通道,这种通道本质上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束缚,而以唐诗为代表的传统文学通过男性视角给窗蒙上一层美的面纱,反映的却是传统思维对这种束缚模式的肯定,让我们看到男权社会下女性无可奈何的心酸与悲哀。
(二)《雷雨》中的窗:从隔到联
而《雷雨》中的窗的存在却是为了打破,是“联”的意义。周朴园一直想要关上周公馆的那扇窗。他说:“萍儿,花盆叫大风吹倒了,你叫下人快把这窗关上。”“你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这些习惯我都保留着,为的是不忘你,祢补我的罪过。”[4]87他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关上那扇窗,但是根本原因被四凤的一句“老爷说过不叫开,说外面比屋里热”[4]38道出,他认为打破封闭会使外界的危险进入公馆中。周朴园如他的名字一样,就是一座朴质的园子,就是传统文学中女子长居的房子。关上窗,是为了维持他的封建大家族稳定、不受外界的破坏和影响,是为了维护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威严。
但是,繁漪不断地想要推开窗,这座院子的封闭性开始被打破。她“(把窗户打开吸一口气,自语)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4]66,她被周朴园用一座园子、一扇窗和一段婚姻囚禁在封建女性的位置上,苦苦挣扎,以“屋子里的死气”[4]38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作者打破了传统文学中窗与闺怨之情密切相关的形象模式,使其与繁漪的痛苦和窒息感紧密相连。繁漪不断地想要推开窗,有两层意义:一是对周朴园命令的直接违抗,即对男性强权的挑战、对女性权利的呐喊和对民主的追求;二是对于外界的空气,也就是真正的爱情和个性解放的渴望。她想要做她自己,想要爱与被爱,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想要摆脱那座让她感受到死与绝望的房子。这是努力挣脱束缚、改变悲惨命运的叛逆,也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抗争。
还有一扇窗,是一扇爱情的窗。与传统女性面对窗外的虚无独自伤感不同,周萍真的在四凤的窗外等候。在《雷雨》中,男性成为等待的那一方。周萍就守在四凤的窗外,痴痴地盼着她的到来。罗燕萍在评论传统文学中的窗时谈到:“男子和女子一个在窗外,一个在窗内,窗为女子的矜持害羞提供着应有的保护。”[3]但是,《雷雨》中周萍却穿过了窗,真的站到了鲁四凤面前。爱情终于跨出了精神层面的挂念,进入俗世的追求。周萍与鲁四凤之间不被封建家庭所接受的爱情通过窗实现了肉体及心灵上的沟通,是对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反抗,以及对自由恋爱、人性解放的呐喊。
唐诗中的窗多以男子的视角展现,是一扇封建体制下“岁月静好”的窗。《雷雨》中的窗融入了女性视角,并且不是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地开与合的动态之中,是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在封建旧家庭中艰难兴起过程的外化,也与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轨迹相吻合。从唐诗到《雷雨》,从关到开,从隔到联,是对中国不断争取思想解放的过程的拓写。
三、结语
一扇小小的窗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了思想转型的轨迹。窗叙事功能背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与主题意蕴上新思想的萌芽是同时存在、相辅相成的。可见,在近代思想转型的过程中,随着传统体制的瓦解,中国文人身上属于华夏文明的印记并没有消散,思想的萌发和中华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