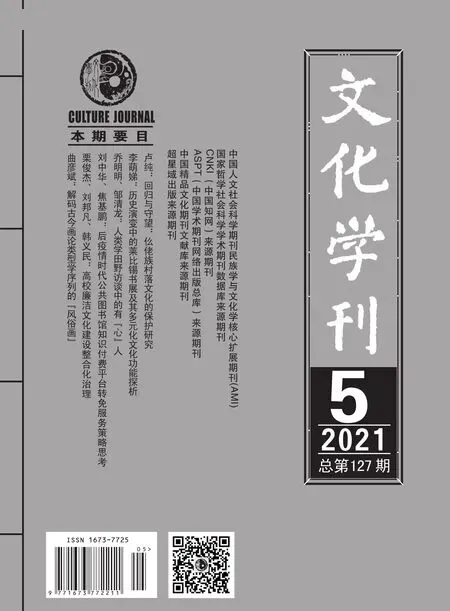异化论视角下《呐喊》中文化负载词的英、日译研究
杨雨时 黄成湘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辛辣讽刺的文笔曾唤醒了部分同时代民众的忧患意识。目前,我国正大力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于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来说,异化翻译策略是让日语读者最大限度了解我国文化的一种策略。而且,日本一流的鲁迅研究专家井上红梅在翻译《呐喊》时使用的异化策略也与鲁迅提倡的“硬译”不谋而合,这种看似“硬”的翻译方法下的“语言产物”或许对于早期目的语读者来说难以理解,但是,随着中日交往的不断深入,这些原本带有浓厚异域色彩的文化负载词会逐步被理解和接纳,甚至成为两国文化的“共识”。
一、异化与归化之争
“异化”与“归化”这对翻译术语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异化翻译是不透明的,它避免流畅,倾向于在译文中融入异质性话语,异化翻译在解释原文时同样具有倾向性,但异化往往是彰显这种倾向,而不是将其藏匿起来。”[1]进而指出异化主要以源语文化为中心,强调译文要有别于目的语;而归化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中心,强调译文要同于目的语。许渊冲是“归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充分发挥汉语优势,扬长避短,重视译文的通顺,还提出了“优势竞赛论”[2]。王育伦赞同鲁迅在翻译中所指的“削鼻剜眼”,指出“翻译作品必须有别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使读者想到这是外国的,而且应该在语言形式的某些方面使读者想到这是‘外国货’”[3]。叶子南指出:“只有当表达同一概念时,原语(如英语)与译入语(汉语)的表达法有差别时,才会出现西化。……极度的归化译法会抹去许多风格、文化、艺术的特征,从而影响译文的真正价值。”[4]总的来说,绝对意义上的归化与异化都是不存在的,两者相辅相成。孙致礼认为:“异化和归化两个相辅相成的翻译方法,任何人想在翻译上取得成功,都应学会熟练地交错使用这两个方法。”[5]孙致礼首先肯定了归化在一定时代条件下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能异化时尽量异化,在难以异化的情况下,应当退而求其次,进行必要的归化处理。也就是说,孙致礼把异化摆在了第一位。进而,孙致礼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谈起,认为原作的“思想”和“风格”都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如果不使用异化的翻译方法,就很难再现原作的思想,而要让原作和译作一样流畅,又必须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
二、《呐喊》英、日译本的先行研究
短篇小说集《呐喊》真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表达了鲁迅强烈的忧患和变革意识,彰显了人道主义精神。时至今日,鲁迅作品英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和日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已基本成熟,但其两种外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如英、日译本的对比研究寥寥无几。本文选用的英译本是199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的美国学者威廉·莱尔的译本(Dairyofamadmanandotherstories),日译本是1932年改造社出版的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井上红梅的版本(收录于《鲁迅全集》)。莱尔是耶鲁大学有名的鲁迅文学作品研究员,他翻译的鲁迅作品具有简洁、流畅的特点;而在日本,井上红梅熟知中国民间风俗,有“中国通”之称,是日本最先翻译鲁迅作品的人。上述两个译本的译者均比较精通鲁迅作品及中国文化,这是本文选择这两个译本的主要原因。
关于《呐喊》的日译研究,冉秀对《呐喊》的井上红梅译本和丸山升的译本进行详细分析得出,两位译者基于各自的时代背景和读者要求,分别采用“鲁迅化”和“本土化”的话语方式进行跨时空翻译对话。20世纪30年代的井上红梅译作满足当时日本读者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民情的愿望。相比而言,丸山升的译作让日本学界更好地理解了鲁迅文学的“神韵”,即与原作极其“神似”[6]。也就是说,井上红梅作为第一个翻译鲁迅作品的人,对中国文学在日传播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相比之下,冉秀对丸山升的译作评价更高。藤井省三在鲁迅文学日语翻译思考中写道:“拙译《故乡/阿Q正传》,并未将鲁迅本土化即现代日语化,而是通过日语译文的‘鲁迅化’来努力传达生存于时代巨大转换时期鲁迅的深层苦恼。……因此,拙译许多文章与明快的格调相去甚远”。[7]藤井省三在翻译鲁迅作品时只是尽可能地还原鲁迅的写作风格,因此存在不少晦涩难懂之处。而本文通过对比威廉·莱尔译本(以下简称“莱尔译本”)和井上红梅译本(以下简称“井上译本”),总结两本译作各自体现的异化或归化倾向,在我国大力倡导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或许能为我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三、《呐喊》中文化负载词的英、日译本比较
文学作品中最关键的就是对文化负载词的解读。准确翻译文化负载词既可以减少文化损失,让外国读者更好地认识中华文化,又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文化负载词能体现出语言包含的文化信息,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现状。美国学者尤金·奈达对文化因素进行了分类,具体为生态、物质、社会、宗教、语言文化五大类。笔者参考尤金·奈达对各类文化负载词的定义,划定了各类文化负载词的具体范围。
(一)生态文化负载词
生态文化负载词包括地理环境、天气、气候、动植物、季风等相关词汇。
例(1):
原文:秋天……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选自《药》)
莱尔译本:The second half of ... leaving nothing butthe dark blue sky.(选自Medicine)[8]49
井上译本:亮るい月は日の出前に落ちて、寝静まった街の上に藍甕のような空が残った。[9]39
此处,莱尔和井上都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乌蓝”这一汉语词汇是“黑里泛蓝”的意思。莱尔根据“乌蓝”的汉语释义,将其译为the dark blue sky(黑蓝的天),而井上选择使用比喻的手法,将其比喻为“藍甕のような空”。“藍(あい)”是“濃く深い青色”(深蓝色)的意思,而“甕(かめ)”指的是“液体などを入れる、底の深い陶器”(盛放液体的深底容器)。经查,日本网站上有很多关于制作“藍甕(あいがめ)”的视频资料,虽然井上没有直接告诉读者,“乌蓝的天”是“黑蓝色的天”,但他引入了“蓝色瓷罐”这一物品,让读者对“乌蓝的天”有了初步认识。
(二)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负载词包括具体的实物、表示货币、时间、重量、距离等度量信息的单位。
例(2):
原文: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选自《药》)
莱尔译本:And right after him comes Third Master Xia. Without spending a single copper, that one ended up pocketing a reward oftwenty-five ounces of snowy white silver.(选自Medicine)[8]54
井上译本:第二は夏三爺から出る二十五両の雪白々々の銀をそっくりおれの巾着の中に納めて一文もつかわねえ算段だ。[9]46
例(3):
原文:温两碗酒。(选自《孔乙己》)
莱尔译本:Warmtwo bowls of wine.(选自KongYiji)[8]43
井上译本:酒を二合燗つけてくれ。[9]34
原文的“雪白的银子”,莱尔译为snowy white silver,而井上译为“雪白々々の銀”,在日语中,这一表述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但这样的用例非常少。原文中的“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雪白的银子”指的是因为夏三爷举报自己的亲侄子夏瑜,官府赏了他二十五两银子,并不像井上理解的,夏三爷赏了“我”(康大叔)二十五两银子。“我”(康大叔)在这段话中阐述的是夏瑜死了,有两个受益者,一是华老栓,他得了夏瑜的血制成了人血馒头,二是夏三爷,而自己却一分好处没捞着。因此,井上的翻译也属于误译。“二十五两”中的“两”这一货币单位被莱尔译为“盎司”,井上则直接译为“两”,并未加特殊说明。中国古代“二十五两”与莱尔翻译的“二十五盎司”并不等值,但考虑到清朝的物价、货币换算,这也是一种翻译的“权宜之计”。此外,书中还有一处孔乙己要温“两碗(酒)”的情景,其中,“两碗”被莱尔译为“two bowls of (wine)”,而井上译为“二合”。“合”是日本特有的计量单位,一合为180毫升。可以看出,井上翻译得更为精确,而莱尔翻译得比较模糊。
(三)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负载词包括历史人物、地名,象征身份地位的头衔,娱乐与礼仪传统,社会机构、娱乐场所等相关词汇。
例(4):
原文:我……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选自《孔乙己》)
莱尔译本:I got a job as a waiter inThe Prosperity For All...(选自KongYiji)[8]42
井上译本:わたしは十二の歳から村の入口の咸亨酒店の小僧になった。[9]32
例(5):
原文: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选自《孔乙己》)
莱尔译本:Went and stole fromDing the Selectman's house!(选自KongYiji)[8]46
井上译本:ところもあろうに丁挙人の家に入ったんだからな。[9]37
“咸亨酒店”创建于1894年,取名“咸亨”寓意为酒店生意兴隆,万事亨通。莱尔译的The Prosperity For All就比井上译的“咸亨酒店(かんこうしゅてん)”更能充分展示其深刻含义。对于文中提到的“秀才”“举人”等头衔称呼,莱尔在注释中有明确解说: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分为秀才、举人、进士三个等级;井上则使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秀才”“举人”是明清科举制度中的称呼,即便日本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为了更准确地传递这类词汇的意义,笔者认为也有解释的必要。
(四)宗教文化负载词
宗教文化负载词包括佛缘词汇、中国古代封建迷信等相关用语。
例(6):
原文: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选自《药》)
莱尔译本:Having done with her weeping and havingburned her paper money, she now sits blankly on the ground.(选自Medicine)[8]56
井上译本:やがて銀紙を焚いてしまうと地べたに坐り込み…[9]49
例(7):
原文:华大妈……化过纸锭。(选自《药》)
莱尔译本:Mother Hua... andburns the paper money.(选自Medicine)[8]55
井上译本:華大媽…泣いて銀紙を焚いた。[9]48
对于“化纸”这一概念,莱尔译本和井上译本都没有格外解释。甚至,莱尔译本将“化纸”和“化纸锭”都翻译成了burn the paper money,井上译本将两者都翻译成了“銀紙を焚く”。其实,“纸钱”和“纸锭”是两个外形完全不同的东西,“纸钱”是供死者享用的冥币,多为钞票或铜钱状;而“纸锭”是用锡箔糊制成银锭状的冥钱。可以看出,两译本在此处均未注意到“纸钱”和“纸锭”的差异。
(五)语言文化负载词
语言文化负载词包括谚语俗语、历史典故、名言、成语,以及方言、脏话等。
例(8):
原文:多乎哉?不多也。(选自《孔乙己》)
莱尔译本:Hath the gentleman many? Nay, he hath hardly any.(选自KongYiji)[8]46
井上译本:多からず、多からず、多乎哉、多からざる也。[9]36
例(9):
原文: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选自《药》)
莱尔译本:Then the Xia kid’s gotta gorub salt in the woundby talking that kinda stuff.(选自Medicine)[8]54
井上译本:あいつが虎の頭を掻いたから堪らない。[9]47
在例(8)中,井上和莱尔都在句式和词汇使用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孔乙己“书呆子”的气质。正如莱尔译本中的Hath、Nay,分别用Has、No的旧体形式来体现孔乙己的说话风格;井上译本则采用了古典日语的表现形式来体现孔乙己“儒雅书生”的形象。在例(9)中,日语中形容“不自量力”的惯用语有“身の程を知らない”等,而井上选择了“虎の頭を掻いた”的表达方式,目的是告诉目标语读者,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不自量力”可以说“在老虎头上搔痒”。但由于该译本是日本第一个《呐喊》日译本,为了便于日本读者理解原文的意思,笔者认为此处应该在译文后用括号加注说明,这是汉语中“不自量力”的比喻。
综上所述,井上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较大程度保留了源语的文化色彩,使读者体会到了中国风情。但他在对原文的理解方面稍有欠缺,对日语中存在但少见的名词没有进行特别的解释说明。莱尔译本较多地站在目标语读者的立场,对文化负载词大多采用注释的翻译方法,甚至用从句来解释、定义文化负载词。两译本对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都存在归化、模糊的翻译倾向,但在文化的解释方面,莱尔译本更胜一筹。
四、结语
近年来,我国大力倡导中华文化“走出去”,日本与中国同为汉字文化圈,在文化方面存在不少相通之处,或许可以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在充分传达原作大意的基础上,让日本读者多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与地道的中文表达。而英语国家与中国存在较少的文化共通点,或许可以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让英语国家的读者在理解译作表达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层面的输出,进一步逆转中国大量输入外国文化的局面。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日益提升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的逐渐扩大,西方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现阶段,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听到,我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也越来越掷地有声,正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好时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论”无疑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这种以源语文化为中心的、彰显“异质性”元素的思想正好符合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需求。在历史的洪流中,“异质”的部分或融入目的语国家文化,被目的语读者接纳,或遭到目的语国家的抵触和排斥,引发“文化冲突”,在“冲突”中实现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