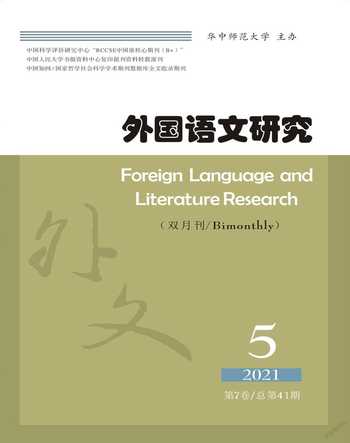悖逆或迎合
内容摘要:20世纪中叶,美国急于塑造其世界霸主的国家形象而极力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即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点被当时的美国荒诞派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捕捉到。他的剧作,以《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微妙的平衡》为例,描绘了怪诞的人物形象与扭曲的人物关系。究其原因,在于该生活方式为人们预设的单一角色规范,以及背后操纵它的价值观念。对此,阿尔比的戏剧人物表现出悖逆或迎合的不同姿态,人物之间由此形成激烈的对峙或微妙的控制局面,构成强大的戏剧张力。当悖逆的一方试图唤醒和抵抗迎合的一方时,阿尔比批判美国生活方式的策略得以显现。
关键词:爱德华·阿尔比;“美国生活方式”;悖逆;迎合;批判
作者简介:雷瑜,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戏剧研究。
Title: Rebelling or Catering: The Dramatic Strategy of Criticizing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in Edward Albee’s Plays
Abstract: In the mid-20th century, America hastened to build its image of global hegemon by promoting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that is,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lifestyle. Correspondingly, Edward Albee who is an American playwright of the absurd observed this predominance. His plays, such as 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and A Delicate Balance, depict absurd suburban characters of American middle class families and their twisted relationships, which are attributed to the single role norms preset by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and the values behind it. Albee’s characters either demonstrate their rebel or conformity, resulting in fierce confrontations or subtle manipulation, and creating powerful dramatic tension. It is when the rebellious attempt to awaken and resist the pandering that Albee’s dramatic strategy of criticizing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is revealed .
Key words: Edward Albee; “American way of Life”; rebelling; conformity; criticize
Author: Lei Yu is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Drama. E-mail: yulei1221@ruc.edu.cn
美國荒诞派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 1928-2006)擅长描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从他的首部剧作《动物园故事》(The Zoo Story, 1959)到他的封笔之作《我,我自己和我》(Me, Myself & I, 2008),阿尔比借助怪诞的人物形象和扭曲的家庭成员关系,揭示了美国中产阶级荒诞的生存现实。事实上,这种怪诞的人物形象和扭曲的人物关系,源于人们对美国生活方式所倡导的一致性的角色规范的悖逆或迎合。追其根由,美国提倡的“美国生活方式”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植入生活的每个毛孔,“由政策的制定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系统地推进”(13),从而催生出单一的生活模式和固化的思想观念。这些导致发达工业社会的美国人因“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受压制而沦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205)。他们的思想也成为“单向度思想”,“充满着自我生效的假设,这些被垄断的假设不断重复,最后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定义和命令”(13)。美国人的内心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自然成为美国政策制定者所宣扬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拥护者。“抗议”剧作家阿尔比聚焦于悖逆美国生活方式的戏剧人物与迎合此种生活方式的戏剧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开对此种生活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价值观念的批判。
一、“美国生活方式”规定的角色规范及其表征
冷战期间,为了争夺世界霸主之位,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处于对峙局面。除却在武器、科技等这些硬核方面提高竞争力,美国政府还注重提升其社会软实力,即通过塑造其世界霸主的国家形象,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着手,以凸显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优势。为此,“美国领导人将美国生活方式宣传为资本主义的胜利,称所有相信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人都能获得这种胜利”(May 8)。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集中体现于物质生活的富裕,如漂亮的别墅、不断换新的车子和各种先进的家用电器等。不过,这种生活方式只面向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有色人种和其它少数族裔群体被排除在外。在政治诱导之余,美国政府还向白人工薪阶层提供住房贷款福利,使他们能够逃离拥挤喧闹的大都市,在广阔的郊区拥有独立式住宅,从而实现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然而,生活在美国郊区的中产阶级在享有政府提供的福利特权时,也得承担政府施加给他们的压力。这种压力在微观层面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思想,让他们一致认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是核心家庭,必须维持其体面和稳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丈夫必须要有稳定、收入可观的工作,健美的身材和阳光俊美的面容这些固定的男性形象特征;而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尽管她们大多拥有知识和学历,其活动范围却受限于家庭空间。主妇们的这种生存境况与当时美国与苏联的一场政治角逐高度相关。为了炫耀生活在各自社会制度下国民的幸福指数,苏联和美国都提出解放女性。不同的是,苏联政府认为的女性解放就是让女性走出厨房到社会施展她们的才能;美国政府则坚持为家庭主妇们提供先进的家用电器,将她们从沉重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可见,无论是单一的男性形象,还是固定的女性角色规范,都表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生存局限。这些都被爱德华·阿尔比捕捉到。
作为美国荒诞派戏剧作家,阿尔比以荒诞的戏剧表现形式呈现了遵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们的生存的荒诞本质。在埃斯林的戏剧论著《荒诞派戏剧》的引论——“荒诞派之荒诞性”中,“荒诞”一词原本指音乐概念中的“不协调音”(Esslin 16)。在阿尔比的剧作中,“荒诞”被用来描绘各种不协调现象。以他的两部剧作为例,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1962)中,被动的乔治与激进的尼克分别代表了悖逆和迎合美国主流社会塑造的男性形象。在《微妙的平衡》中,家庭主妇艾格尼丝精神异常脆弱,时刻担心家庭的不稳定和有失体面,而她的女儿和妹妹却无法像她那样顺从女性角色规范。此外,阿尔比剧中人物的关系也很扭曲。譬如,毫无斗志的乔治遭到妻子玛莎的嘲讽,尼克为了职业晋升与玛莎公然调情。托拜厄斯与妻子艾格尼丝疏远,对女儿漠不关心,而艾格尼丝则对家人实行全面微妙的控制。
这种人物形象与人物关系的荒诞表现贯穿在阿尔比30余部戏剧作品中,揭示了人们对美国生活方式以及其蕴含的美国社会现有价值观念的悖逆或迎合。可以说,阿尔比正是通过剧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人物之间由此展开的对峙和反抗来批判美国生活方式。本文以《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微妙的平衡》(A Delicate Balance, 1966)为例,分析阿尔比戏剧对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展开批判的策略。
二、阿尔比戏剧人物对男性形象的悖逆或迎合
美国生活方式塑造的男性形象仍然在父权制的观念体系中构建而成。这在《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得到了充分诠释。在该剧中,阿尔比勾勒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国中产阶级男性形象,被动的乔治代表了有悖于美国生活方式所虚构的男性形象,激进的尼克则代表符合美国生活方式规范的男性形象。对待乔治与尼克,乔治的妻子玛莎公然嘲笑前者,觊觎后者。玛莎的这种不同反应源于她沉溺在美国生活方式构建的幻象,这也造成她与坚持面对生活现实的乔治之间激烈的对峙局面。
在剧的开篇,玛莎发起“羞辱男主人”(Humiliate the Host)的游戏仪式,在乔治的年轻同事尼克面前嘲笑乔治的无能平庸:“你看,乔治没有太大的……冲劲……他不是特别地……有野心。事实上,他有点……(在乔治背后骂骂咧咧)……他是个败类!”(The Collected Plays of Edward Albee, 1958-1965 210)在夸赞了尼克健硕的身材后,玛莎又回忆起二十年前乔治与父亲的一次拳击比赛。比赛结局令人意外,在乔治久不出手之时,玛莎从后面袭击了他,并将他一拳打倒在地。從拳击赛事件可以看出年轻乔治的肌肉就不发达,中年的乔治身材早已发福。乔治的身材并不符合美国生活方式所期待的身材健硕的中产阶级男性形象。在事业方面,乔治在被评为历史学院副教授后就一直没有如玛莎和岳父所愿,成为历史学院的院长。尽管如此,乔治却不着急扩充自己的人脉,积极为自己的事业铺路。玛莎为此抱怨乔治不上进,埋怨他在父亲举办的教师晚会上“从来什么都不做;你从不和别人交往”(158)。因为乔治不积极拉拢关系、扩大自己的圈子,玛莎斥责他“就是一片空白,一个零”(164)。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依据“人脉”的宽广程度来评判一个人的社交能力的高低。然而,剧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脉”则指资本以特权资源和利益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流动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人际圈,玛莎将人脉视为乔治获得晋升的关键。资本在人际圈的流通和内化导致人与人关系的物化,而乔治的被动则可被视为对这种物化关系的反抗。
在人脉以及身材方面表现得被动、发福的乔治与野心勃勃、身材健美的尼克之间形成巨大的戏剧张力。面对遵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所构想的男性形象的尼克,乔治在接下来的游戏环节中以提问人或旁观者的姿态,撕开冠冕堂皇的尼克的假面具,揭示他的拜金主义、机会主义以及道德的堕落。
在“整蛊客人”(Get the Guests)的游戏环节中,乔治拷问了野心勃勃的尼克与哈妮的婚姻,得知尼克娶哈妮是为了获得她丰厚的财产。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缺乏感情基础,而尼克也承认:“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甚至在我们刚刚结婚时”(224)。拜金主义的尼克虽然获得了财富,但他的婚姻生活却是贫瘠的,阿尔比通过反复强调他与哈妮无法生育孩子暗示他们婚姻的空洞。机会主义者尼克的事业野心使得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参与到乔治设计的“勾搭女主人”(Hump the Hostess)的游戏中,将道德原则抛诸脑后,践踏妻子的尊严,试图与玛莎苟合、抓住玛莎这个难得的机会。而且尼克似乎已经对这种技能驾轻就熟,即“从年长的男人们那里接手一些课程,为自己建立一些特殊小组……征服他们的妻子……”(229)。
在某种程度上,尼克就是阿尔比的剧作《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 1959)中那个被姥姥称为“美国梦”的年轻人。他们面容英俊,身材健美,最为关键的是他们都可以为了利益不折手段。而“美国梦”的孪生兄弟因为反抗遵从美国生活方式的养母的意愿,最终被残忍地杀害和遗弃。运用这种夸张的戏剧手法,阿尔比讽刺了美国社会专断的一致性。这种严密的一致性以美国主流文化为载体,通过塑造统一的男性形象,对人们的生存进行约束。
保持清醒意识的乔治对美国社会专断的一致性了然于心。因此,在撕开尼克的面具的过程中,乔治预测了美国生活方式对男性形象同质化的不堪后果。闲聊中,教授历史的乔治与生物教师尼克针对生物基因工程进行了一场争辩。玛莎对基因工程能够生产一批像尼克一样外表英俊、身材健硕且头脑聪明的男性表示向往,乔治打破了她的幻想。他反对生物基因工程对男性的统一塑造,“我想我们不会有太多的音乐,太多的绘画,但是我们会有一个男人的文明,平滑的,金发碧眼的,中等体重的男人”(198)。这些统一生产出来的男人展现出来的金发碧眼、中等体重,其实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男性形象的特征。乔治在此不仅批判了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科技理性,还借此暗讽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对男性形象的单一塑造。因为无论是科技理性,还是单一的男性形象,都剥夺了美国男性的生存自由,“这个实验一定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但多样化将不再是我们的目标。文化和种族终将消失……蚂蚁将统治世界”(199)。保持清醒的乔治在此警示尼克和玛莎,千人一面的男性形象不仅限制了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的生存自由,使他们成为马尔库塞所提出的“单向度的人”,还终将给美国的文化带来巨大的毁灭性冲击。因此,乔治对尼克说的“我想给你一个救生包”(231),试图以长辈的姿态警醒这位金钱崇拜、道德堕落的年轻人。
与乔治对待尼克的態度不同,玛莎对尼克充满期待,这造成她与乔治的主要冲突。为了引诱尼克,玛莎将自己的裤装换成性感的裙装。乔治深知玛莎此种举动的意图,他暗示尼克:
玛莎在更衣,不过玛莎不会为我而更衣。玛莎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为我更衣过了。如果玛莎在更衣,这意味着我们将在这里呆上数天的时间。你被授予了荣誉,你一定不要忘记玛莎是我们敬爱的上司的女儿。(184)
尼克对乔治的暗示感到震惊。因为他的确有勾引玛莎的念头,只是乔治将他的心思和盘托出反而让他既受鼓励又迟疑不决。乔治的这番暗示让尼克的妻子哈妮深感不安。对此,尼克只能假意拒绝,“你可能搞错了,但我希望你不要在我妻子面前这么说”(184)。玛莎对尼克的引诱归根结底是因为她深谙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女人须取悦男人;只有让男人愉悦,女人就能得到她想要的一切。玛莎从乔治那儿得不到的,就渴望尼克替她实现。玛莎对尼克的渴望反映了她是美国生活方式所规定的男性形象的强力支持者,也是美国现有价值观念的执着拥护者。从裤装到性感裙装的换装行为表明,玛莎和尼克一样具有不顾道德向上攀爬的野心,以及玛莎对乔治的男子气概的否定。在将乔治与尼克进行对比时,玛莎认为乔治不具男子气概,“你不够男子汉,你没有勇气”(261)。讽刺的是,玛莎随后发现尼克虽头脑聪明,脸蛋漂亮,身体强健,极具野心,然而却无性能力。在弗洛伊德看来,性能力是原始的生命动力。因此,尼克的性能力丧失象征了顺从美国生活方式的他的生命受压抑的真实生存状况。
为了唤醒沉迷于美国生活方式的玛莎和尼克,乔治决定直面现实。而这个过程犹如“撕标签”的过程,正如乔治对正在撕酒瓶标签的哈妮说的一番充满哲理的话:
亲爱的,我们都在撕标签;当你穿过皮肤的三层,穿过肌肉,把器官甩到一边……然后到达骨头……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当你埋头苦干的时候,你还没有完全完成。骨头里有东西……骨髓……那就是你要找的东西。(289)
对乔治来说,深入生活的本质“骨髓”才能帮助人们发现存在的意义,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而残忍的。在剧终的“养育婴儿”(Bring Up Baby)游戏中,乔治假想收到儿子死亡的电报,宣布他与玛莎幻想的儿子的死亡消息,以此来唤醒玛莎一同面对惨痛的现实。当玛莎意识到完美丈夫只是虚构的,现实到来的尼克也是不完美的,儿子也是假的时候,终于因自己被生活欺骗而心理崩溃。
借助玛莎和尼克这两位努力迎合美国生活方式的人物形象,以及对这种生活方式保持清醒意识的乔治的警示,阿尔比讽喻了美国政府宣扬的“美国生活方式”如一剂迷幻药,让人们沉湎于虚幻,难以认清现实,并在最终宣布了“人们为了自己的‘幻想’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结构都已经崩溃了”(黄晋凯 106)。对此,乔治也借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衰落》中的一段文字,表明了他对西方文明的担忧,“西方,由于受到联盟的拖累,加上道德观念过于僵化,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最终必将……坍塌”(272)。这可以说是阿尔比对美国生活方式最为有力的批判与预见。
三、阿尔比戏剧人物对女性角色规范的悖逆或迎合
美国生活方式造成《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人物的紧张对峙局面,在《微妙的平衡》中表现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艾格尼丝对家人微妙的全面控制。在剧中,为维持家庭的富裕和体面,托拜厄斯沦为“为钱奔波,直至死亡到来”(The Collected Plays of Edward Albee, 1966-1977 51)的永不停歇的机器,成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马克思 542)。为金钱而忙碌的托拜厄斯在家中沦为非存在的缺席状态。托拜厄斯将家庭事务全推给妻子艾格尼丝,给她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剧的开篇,艾格尼丝向托拜厄斯倾诉自己的苦恼,而后者只在一旁心不在焉地附和着她语无伦次、混乱的情绪表达。托拜厄斯对女儿也漠不关心。女儿茱莉亚已经历四次失败的婚姻,将再次返回父母家中。对此,艾格尼丝坚持要求托拜厄斯出面,尽管她知道无济于事,但“至少,茱莉亚会认为她的父亲关心她,这也许是一种安慰——如果不是帮助的话”。然而,托拜厄斯却犹豫不决,“如果我觉得我可以……与她取得联系,我会说,‘茱莉亚……’,但接着我能说什么呢?‘茱莉亚’。然后,什么话都没有”(37-38)。托拜厄斯这种无可奈何来源于艾格尼丝对这个中产阶级家庭的一切的独自掌控。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与体面,艾格尼丝顺从美国生活方式对家庭主妇的规范。她对家庭实行全面的控制,使得家中其他成员,包括她无法遵守女性角色规范的妹妹和女儿,开始反抗,造成她与家人关系扭曲的僵局。
当艾格尼丝抱怨自己不堪忍受生活的重负时,妹妹克莱尔嘲笑她,“如果你采访一只骆驼,它一定会承认喜欢自己身上的重物”(85)。克莱尔将辛勤付出的姐姐比作甘愿负重的“骆驼”,是因为她认为艾格尼丝虽身心疲乏,却仍迎合社会为她构建的角色规范,即家庭的“统治者,有执照的妻子以及午夜的护士”(108)。表面上,艾格尼丝在这些角色的扮演中被授予控制家庭的权力。但是这些是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的美国社会赋予她的,并非她的自主选择。因此,当艾格尼丝掌握权力时,自身也被权力奴役着。
艾格尼丝对这些角色的被动接受使她自身异化。贾格尔曾指出,这种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具体的、历史的产物”(贾格尔 93)。出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目的的考虑,二战后的美国政府将女性赶回厨房,意在给从战场返回的男性腾挪出更多就业机会。随后,在与苏联的对峙中,美国媒体作为政府的喉舌开始宣扬“美国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主张传统的家庭角色的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操持家庭事务。为迎合这种生活方式,美国家庭女性必须维持家庭的稳定和体面。因此,艾格尼丝规定妹妹必须停止酗酒;女儿必须呆在婚姻的堡垒中;丈夫必须按照她的意愿做决定——为了家庭的安全和稳定,他必须将家庭的“入侵者”,即托拜厄斯的朋友哈里赶出家门,必须帮助她阻止克莱尔酗酒,必须出面将他们的女儿劝回她的丈夫身边。
因此,谈及即将从失败婚姻返回父母身边的茱莉亚,艾格尼丝对托拜厄斯这样说道:
这是她的家,我们是她的父母,我们对她有义务。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托拜厄斯,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单独生活,就你和我,没有……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或是任何人。(36)
由此可见,艾格尼丝并不想收留女儿,也不想自己未婚的妹妹克莱尔或任何其他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她想摆脱女儿和妹妹给她带来的麻烦,即一个失败的已婚女性和一个无法或不愿进入婚姻的未婚女性给这个稳定的家庭带来的威胁。精疲力竭的茱莉亚也察觉到母亲并不欢迎她,对于母亲的责怪,茱莉亚反问道:“是吗!?难道你以为我很享受吗?”(49)被母亲视为安全壁垒的婚姻并没有给茱莉亚带来快乐,也是艾格尼丝极力逃避的现实。
在谈到婚姻时,艾格尼丝与女儿讨论了性别角色这个话题。艾格尼丝坦言若自己为男人会比现在更出色。艾格尼丝的女性意识似乎觉醒了。然而,当她提到一位精神病医生基于医学实践写出的书籍时,艾格尼丝又陷入美国社会为她限定的性别角色的窠臼之中。她评价道:“这本书认为两性正在颠倒,或者至少是变得太相似了。这是一本既可读又不可信的书,因为它扰乱了我们的幸福感”(152)。艾格尼丝认为此书可读又不可信,因为它尽管有些道理,但如果人们都相信的话,会破坏家庭的稳定。
因此,在短暂的犹疑后,艾格尼丝又重新回到她的家庭主妇角色,并表现得义不容辞,“我要让整个家庭保持良好的状态。我要维护它;守护它”(67)。她将维持家庭的稳定作为自己的职责。为了维持家庭的平衡,艾格尼丝指责酗酒和玩世不恭的妹妹克莱尔,“她养你,允许你……宽容你!容忍你的肮脏,你的……‘女性解放’”(107)。克莱尔的放纵行为在她去商店买无上衣的泳衣中也有所体现。她这种放浪的行为受到店员们的鄙视,对她避而远之。克莱尔的这些有失体面的表现,被艾格尼丝归结于克莱尔作为“解放的女性”的行为表现。她们的母亲容忍了克莱尔的放纵行为,然而艾格尼丝却对此深恶痛绝。在保守的艾格尼丝看来,家人的酗酒和放纵会给这个体面的家庭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解放”意味着与保守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意味着克莱尔的这种行为会使得整个家庭成为他人眼中不合格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为此,艾格尼丝曾将终日醉得不省人事的克莱尔送至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因为那里人烟稀少,克莱尔的失态不会被熟人所知。如此,艾格尼丝还能维持家庭的体面。
艾格尼丝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定和体面,不仅斥责、还曾一度抛弃了妹妹克莱尔,并极力劝女儿茱莉亚回到她的丈夫身边。然而,茱莉亚的前夫们,要么是赌徒、酒徒,要么是好色之徒。因此,艾格尼丝执意将女儿逼入婚姻的牢笼,这无疑是在将她推入虎口。不仅如此,艾格尼丝还欲将丈夫的好友哈里及其妻子赶出家门,而其中的原因则是她将这对夫妇视为“瘟疫”。无论“瘟疫”指代什么,它带给艾格尼丝的恐慌根源于它会给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带来威胁。
艾格尼丝以上这些试图保持家庭稳定和体面的努力无疑触怒了家中的每个成员。克莱尔在该剧的开篇就向托拜厄斯扬言要开枪杀了姐姐艾格尼丝,而托拜厄斯对此并不反对和感到震惊。茱莉亚在回家遭遇父母的冷眼后大声指责他们,并在发现自己的房间被父亲好友哈里夫妇夺走后变得歇斯底里。托拜厄斯在儿子去世后开始久不归家,并拒绝与妻子艾格尼丝进行交流。阿尔比还以托拜厄斯与猫的故事来隐射这种扭曲的家庭关系,就如赛科斯认为的,“托拜厄斯和猫之间的关系是该剧中大多数人物关系的范例”(Sykes 452)。托拜厄斯和猫之间的故事是一个惊悚的故事。托拜厄斯对猫的占有不只是从空间层面展开,还包括在情感上对其进行控制。这种双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因“在我与我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没有活的关系……使主体与对象都成为物”(弗洛姆 83)。显然,艾格尼丝对家庭成员的控制将她与被她占有的对象都物化了。这使得为家庭不断付出的艾格尼丝不仅得不到家人的尊重和认可,相反,他们都极力想摆脱她的控制。剧终,埃德娜邀请艾格尼丝走出家门去城里参加活动。艾格尼丝婉拒了这个暂时离开家庭的邀请,“嗯……不,我不这么打算,埃德娜;我已经……我有很多事情要做”(109)。这个如“舒适的集中营”(Friedan 78)的美國中产阶级家庭已成为艾格尼丝的唯一天地,成为她放弃自己的避难所,也成为她剥夺家人的自由的场所。
时隔6年后,阿尔比的另一部剧作《一切结束》(All Over, 1971)在纽约首演。在垂死的著名老者的床榻边,他的妻子与情人为如何处理他的遗体产生了争执。妻子认为自己才是婚姻真正的主人,而情人只不过是避难所。尽管妻子最终获得了料理丈夫后事的权力,但她作为妻子的传统角色显然已被医生和情人以及消费社会的罐头食品替代。在丈夫死后,这位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因为角色的迷失发出痛苦的宣泄。她歇斯底里地喊道:“我不快乐!我……不……快乐!”(366)事实上,妻子的痛苦根植于她的生命被贬低、被功能化。她的一生只是在履行这些角色,如家庭的护士、厨师以及丈夫的性欲对象。她如艾格尼丝一样,被困在家庭的牢笼里,无法成为自己。
女性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迎合所造成的人生困境在剧作《三个高个子女人》(Three Tall Women, 1992)中也得到具现。除却第二幕露面的年輕男子,这部剧作中的其余三位人物都是女性A、B、C。扮演A的著名演员格伦达·杰克逊(Glenda Jackson)本人表示自己很欣赏这部剧作,因为它“完全是以女性角色为中心的,并让我有机会和其他两位女性演员进行深度的合作。大多数剧作对女性角色都不感兴趣,即使有一位女性人物,也只是作为男性角色的陪衬”(Regensdor)。杰克逊的此番言论表明她对当代女性存在境遇的深切关注,也表明阿尔比对美国社会如何看待女性的重视。在该剧的第二幕,A、B、C分别扮演一位女性人生的三个阶段。这三位人物之间的相互否定,更是再现了被物质和性别规范左右的女性的悲剧一生。
在本世纪初,阿尔比的剧作《占据者》(Occupant, 2002)以对20世纪著名女雕塑家路易丝·内维尔森(Louise Nevelson)的一次假想采访而展开。被采访的内威尔森在舞台上回忆了自己的一生,讲述了自己为获得美国绿卡而嫁给家庭背景强大、经济保障充足的前夫的经历,以及她离婚后作为一名艺术家艰辛的成名之路和她遭受的病痛经历。剧终,内威尔森在病房里等待死亡的到来。她在门上写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占据者”三个字。这表明内威尔森始终力图打破美国社会为她设置的重重障碍,她通过艺术为自身的存在占据一席之地,最终完成了她的自我塑造。在最后一部剧作《我,我自己和我》中,阿尔比再次通过描述个体的生命压抑体验,呈现了美国社会刻板的角色规范和价值观念给人们带来的生存局限。
四、结语
无论是单一的男性形象构建,还是固定的女性角色规范,阿尔比的戏剧都意图揭示美国现代社会固步自封的价值观念限制了人们的生存的真相。由于他们对美国生活方式持悖逆或迎合的不同姿态,阿尔比的戏剧人物之间形成或激烈的对峙与或微妙的控制局面。当悖逆美国生活方式的乔治最终打破其他人物的幻想,而迎合美国生活方式的艾格尼丝遭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反抗时,阿尔比对此种生活方式的批判得以彰显。运用此种批判策略,阿尔比撕开了光鲜亮丽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假面具,并表明它使父权制和性别歧视等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得更加尖锐。同时,剧中人物之间的相互对峙与反抗局面还表明,美国社会主流群体的白人中产阶级自身也在拒绝单一的、同质性的美国主流文化。这些都与上世纪兴起的女性运动、男性解放运动等有着共同的政治和文化批判目的,都质疑和谴责了美国白人的“文化恐怖主义”。爱德华·阿尔比深谙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在荒诞派剧作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其在离家出走之前的生活方式。这种时刻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在美国白人保守主义复兴和肆虐的今天仍然十分可贵。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lbee, Edward. The Collected Plays of Edward Albee, 1958-1965. New York: Overlook Duckworth Press, 2005.
---. The Collected Plays of Edward Albee, 1966-1977. New York: Overlook Duckworth Press, 2005.
Esslin, Martin.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艾瑞克·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Fromm, Eric. To Have or to Be. Trans. Guan Sh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London: Norton Press, 2001.
黄晋凯(主编):《荒诞派戏剧》。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Huang, Jinkai, ed.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Beijing: Renmin UP, 1996.]
阿莉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Jagger, Alison M.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rans. Meng Xin.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9.]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Marcuse, Herbert. One-Dimensional Man. Trans. Liu J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Marx, Karl.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2.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9.]
May, Elaine Tyler.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Regensdorf, Laura. “This Tony Winner and Former Politician Has a Lot to Say About Being a Woman Right Now.” Vogue June 10, 2018.
Sykes, Carol A. “Albee’s Beast Fables: The Zoo Story and A Delicate Balance.” Educational Theatre Journal 25.4 (1973): 448-455.
责任编辑: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