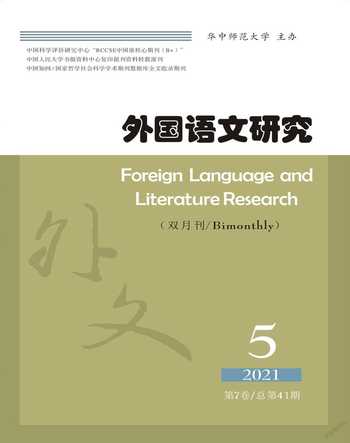“时流的明镜”
张昱 汪希
内容摘要:马洛版《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沿袭了关于人吃禁果而堕落的主题。该剧未及描写弥尔顿式的英雄,也没有像斯宾塞那样刻写一部道德书,更未像莎士比亚那样写实地描写人世一切冷暖情仇,而是人在宇宙中能享有的一切可以享受的世俗内容。基督教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尽善、尽美且无欲,但浮士德这个人物的重心却在于他对世俗物质的渴望,成为了马洛笔下的另一撒旦。浮士德对世俗欲望的追求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免除精神枷锁以后的现世精神和享乐主义态度,这正是人文主义者对人之身份的索求。虽然违背了向上、向善的古典主题要求,本文重在以体会时代精神的角度,以反映论(即镜子说)来参详这部通常认为反伦理的经典剧作,以作为一种新的解说途径。
关键词: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世俗性;文艺复兴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拓扑学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性格理论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运用”(项目编号:CYS2009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昱,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汪希,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The Glass of Fashion”: A Study of the Secularity of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r. Faustus
Abstract: Christopher Marlowe’s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r. Faustus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theme of man’s depravity by eating the forbidden fruit. Marlowe did not describe this play like the Miltonian heroic theme, nor did him write an ethics book like Edmund Spencer, nor did him realistically describe all the cold and warm feelings of human beings like Shakespeare, but his focus is the secular content of all that one can enjoy in the universe.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morality requires that man should be perfect, beautiful and undesirable when they are in the present world. But Dr. Faustus is not like this, his focus is in his desire for the secular materials, so becomes another Satan created by Marlowe. Faustus’ pursuit of secular desire reflects the secular spirit and hedonistic attitude of the Renaissance people after they got rid of the spiritual shackles, which is the humanist’s demand for human identity. Although this play, which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n anti-ethical play, violat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pward and virtuous classical theme, this paper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he Renaissance time through the theory of reflection (the theory of mirrors), which is also a new way to interpret this classic play.
Key words: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r. Faustus; secularity; renaissance
Authors: Zhang Yu is Ph. D. candidate in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E-mail: zhang_yu@sdu.edu.cn. Wang Xi is graduate student at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E-mail: 1031523743@qq.com
英國16世纪的戏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剧作。在该剧中,马洛塑造了浮士德这样一个既具有宗教知识与道德意识又敢于反叛教义、追寻世俗享乐的复杂人物形象,从而在文学批评史上引起了不少的争议。有的批评家认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完全就是一部基督教的道德剧,因为浮士德最终所遭到的惩罚都与基督教教义相符(Cole 121-149)。有的批评家却认为马洛笔下的浮士德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他与马洛一样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致力于颠覆基督教价值观(Levin21)。但无论这部剧究竟是一部基督教的道德剧,还是一部反基督教道德的戏剧,这两派的观点都围绕着神性对浮士德进行评价。事实上,马洛版《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另一个重心是对世俗,即人的非神性因素的追求和享受,此乃文艺复兴人文精神之奥义。
基督教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尽善、尽美且无欲,但浮士德这个人物的重心却不在这个方面,而在于他对世俗欲望,诸如权力、荣誉、美色等的尽力追求。这几个方面却体现了文艺复兴人免除精神枷锁以后的现世精神和享乐主义态度,这正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所在。本文无意于对浮士德的言行进行宗教道德和伦理上的评判,也无意于对基督教教义进行全然否定与批判,而是想从世俗性这一角度切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从对神性的关注转向对人性、人权的追求,重在以体会时代精神的角度,以反映论(即镜子说)来参详这部通常认为反伦理的经典剧作,也算一种新的解说途径。
一、宇宙之镜:马洛笔下的另一撒旦
在《圣经》的开头就提到了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导致了人类的原罪和堕落,之后这一禁果传统对西方文化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说明自基督教以来,教会一直强调神对人的管理与控制,致使人受到很深的桎梏,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教会宣扬的各种清规戒律和禁欲主义达到了顶点,于是基督教成功地颠倒了人们“对现世的爱和现世的至上性,把他们转变为对现世和世俗的恨”(Stumpf & Fieser 365)。在《圣经》中除了人类始祖的堕落外,还有诸如撒旦、七原罪之类与神性相对的兽欲,以此来警示人们放弃世俗的欲望以获得来世的幸福。英国文艺复兴初期的诗人斯宾塞在他的长诗《仙后》中设置了十二种美德,以及与美德相对立的“骄傲之宫”、代表邪恶与虚伪的杜爱莎,来告诫人们要懂得节制、向上向善。且不论斯宾塞的道德书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但其中所展示的内容的确不同于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古往今来,在西方文学的历史中出现了诸多经典的浮士德形象,而这些浮士德的创造者们正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一般,以最初来源于德国民间故事题材的浮士德为原始材料,通过自我对时代、人性的独特体悟雕刻出了一个个个性互异的浮士德。在马洛版浮士德之前,民间流传最为广泛、全面的文字版本为1587年约翰施皮斯编纂的《浮士德故事》。彼时的德国虽正值文艺复兴时期,但天主教会与封建统治仍占据统领地位,因此,编纂者在《浮士德故事》中的浮士德身上重点凸显了强烈的道德说教意味,“通过对浮士德身上人性因素的否定,强化了宗教伦理观念——‘叛教而死’的绝对必然性,力图将现世人生全部纳入这一伦理观的考量中”(李定清78)。因此,在这一版本的开头编纂者便开宗明义,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收到惩前毖后的功效,愿向不信神鬼的大胆的人们献上善意的忠告”(转引自阿尼克斯特55-56)。
取材于英译本《浮士德故事》与早期流传的《约翰·浮士德博士该诅咒的一天和天谴之死》(The History of Damnable Life and Deserved Death of Doctor John Faustus),马洛在沿袭了传统的故事情节外,却赋予了浮士德这个人物另一重与众不同的形象特点与生命色彩。作为英国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剧作家,马洛的笔下的浮士德集乡野骗子、魔法师与悲剧英雄于一体(Womack 141)。马洛通过他对时代的深刻洞察与高超的艺术技巧将浮士德塑造成为了一个反传统式的悲剧人物,在他身上那种离经叛道、欲壑难填的突出演绎显然掩盖了前一版本的道德说教意味,而凸显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世精神与享乐主义。在马洛笔下,浮士德夸张、直率地表达着自己对世俗欲望的追求:“哦,这是怎样一个追名逐利、/争权寻欢、无所不能的世界啊”(陈才宇15)②,“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让我/饱尝一切能愉悦人生的甘甜。/在这自由自在的二十四年中,/我要过得快活,尽情行欢作乐,/只要我堂堂的仪表尚在人世,/普天下人都羡慕浮士德这名字”(95)。这些台词都充分反映了浮士德这个人物追名逐利、争权寻欢、贪得无厌的形象特征,将浮士德的世俗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16世纪的宇宙志学者们常将宇宙与圆镜关联,宇宙志学者威廉·库宁汉就在他的《宇宙之镜》中表示,“宇宙之镜”能反映“天空及行星和其它的星群,大地及其美丽的区域,还有大海及其奇异的扩展”,而人在镜中除了能看到自己外,还能看到“各重天”以及“整个宇宙”(转引自胡家峦221)。类似的圆镜之喻还可以推衍至流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小宇宙、天人对应观念,即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镜子可以再现世界的结构与本质。在文艺界,沿袭自柏拉图以来的“摹仿论”传统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大量艺术家的创作观念。苏格拉底在形容艺术的创作过程时说“只需旋转镜子将四周一照——在镜子里,你会很快得到太阳和天空,大地和你自己,以及其他动物和植物”(转引自Abrams 33)。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则说“举起自然的镜子”(《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场),本·琼森则表示“(喜剧)是生活的摹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转引自Abrams 32)。可以看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此在世界的造物主,以笔为镜将宇宙万物、世间本质映照进他们的艺术小宇宙中。莎士比亚曾借奥菲利亚之口說哈姆雷特是“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对一个全人、完人的规范与要求。而马洛笔下那位撒旦形象的浮士德则同样作为一面“时流的明镜”映照出了人文主义者们在另一方面的追求,即脱离了中世纪的精神束缚,见证了黑死病的疯狂席卷后,开始了对此在世界的珍视、对纵情享乐的肯定以及对世俗欲望的追求。
马洛笔下这个利欲熏心的浮士德毫无疑问是另一撒旦的再现,但正如一直以来被视为邪恶的撒旦形象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转变为了一个敢于举起武器反抗权威的英雄形象一样,浮士德的世俗欲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眼中已经不再是一件理应被禁止、难以启齿的事情,所以这部戏剧才能在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初期频繁上演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利润(Hector 83)。因此,摆脱了中世纪思想束缚的文艺复兴人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将注意力由虚幻的彼世转移到了现世的世俗欲望中。所以彼得拉克热情地书写着爱情的赞歌、莎士比亚激烈地演绎着权力与欲望的故事,但在世俗欲望的表达上,还属马洛版《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最为生动细致、出神入化。
二、镜中之像:浮士德的世俗欲望追求
马洛笔下的浮士德不仅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世俗欲望,还付诸行动通过魔法来换取奴役魔鬼的权力。在浮士德所获得的利益中,知识、权力、财富、能力、爱情、美色皆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在他开头对自己伟大事业的描述中,他说道:“我要派他们飞往印度采金,/到海底为我搜寻晶莹的珍珠,/到新大陆去,踏遍海角天涯,/搜集各味仙果和山珍海味。/我要让他们为我诵读海外奇文,/向我通报异域君主的深宫秘事……”(21-23),他所追求的这些世俗欲望体充分现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大发现、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给英国人的思想所带来的变化,代表了当时的英国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正常需求。
作为一个学识渊博、学富五车的博士,浮士德首先最为突出的欲望追求就是知识,他对知识的渴求代表了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深刻描绘了当时教会与封建统治对科学研究者的控制乃至迫害:“当时自然研究方面也有许多人成了宗教裁判庭的火刑场和牢狱中的殉难者”(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62)。在英国,“教会控制教育是英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Aldrich 40),在过去,教育以及知识属于上层阶级的专属利益,但随着中世纪商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兴起,普通群众也开始接触到教育所带来的丰厚果实,知识分子便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在那之前,根据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可知,社会大致被分为了三个阶层,即贵族、教士以及农奴(勒戈夫1)。但是知识分子的出现则打破了社会结构原有的格局,知识分子这一特殊阶层汇聚了过往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成为了底层人民跨越社会阶层的跳板。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出身低微、贫寒,但最终通过知识脱离了原生阶级的困境。另一方面,浮士德也是在知识的引导下走出了神学对个人思想、行动的束缚,正如他在临死前说道:“哎,如果我从没来过维滕堡,从未读过书,那该多好”(205),这句话虽然是悲惨无奈的,但也侧面反映了正是知识给予了浮士德掌握人权的动力与选择命运的眼界。
浮士德对财富的追求也充分体现了金钱于英国文艺复兴人的特殊意义。在中世纪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逐渐从统治阶层流向了商人手中。财富的积累导致英国的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传统贵族阶级衰落,而许多商人却跻身进入了贵族阶层。例如爱德华三世在1357年,就曾在同一天册封了六个伯爵,而这几个人的出身地位都不高,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靠财富的积累而成为了贵族的(马克垚307-308)。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人来说,商人靠财富取得的成功让他们看到了金钱这种世俗物质的积极面,所以马洛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对财欲的大胆描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内心欲望的揭示与显现,也是对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财富来获得世俗权力的激励。在基督教教义中对财富的贪欲被列为七原罪之一,而浮士德对于财富这种世俗欲望的直白追求在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之下却具有特殊的进步性。
浮士德对权力与名誉的追求也反映了他对人的看重、对自我的确信。他求助于魔法以获得奴役魔鬼的权力,从而能够呼风唤雨,满足自己的任何欲求,使他既能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在空中架起一座大桥,/率领一大班人穿越海洋”(37)、“念念书中的句子就能获得金子,/在地上画个圈,天空就会出现闪电,/雷电交加,刮起大风,暴雨倾盆”(63),也能拥有世俗意义上无上的权力“让两地都朝拜我的王冠。/没我的思维,帝王不得施政,/德意志的君主将由我钦定”(37)。前者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思维,即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无限的能力,这也就充分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后者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所在,即人们对世俗权力的向往皆是正当的欲望。
另外,浮士德在对世俗爱情与美色的追求中也远离了天国虚无缥缈的幸福,收获了尘世的快乐,预见了人的自由。正如法國哲学家福柯所说:“如果性受到压抑,也就是说性是被禁止的、性是虚无的、对性要保持缄默,那么谈论性及其压抑的唯一事实就是一种故意犯禁行为。谁这样谈性,他就站到了权力之外的某一位置上了。他搅乱了法律,预见到了一点未来的自由”(Foucault 6)。当浮士德在与魔鬼靡菲斯特签订完协议后,他立即说道:“闲话少说,给我找个妻子来,必须是全德国最美的女子,我天生放荡好色,没有女人可活不下去”(61)。在此,浮士德这种故意的犯禁言语正是忽视了基督教教义所代表的神权,表达了一种享乐主义的态度,爱情与美色的甜蜜果实是人之本性所需要的快乐。弗洛伊德在他的心理结构理论中谈到了“性力”即“力比多”(Libido)作为一种原始欲望与驱动力在人的心理空间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浮士德对美色的大胆表白便是解开了过往神学对人性的压抑,将人的欲望释放出来,获得了心灵的自由。浮士德在与海伦结合时,他说道:“亲爱的海伦,赐我永恒的一吻”(197),这句话不禁让人想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那句:“只要人眼能看见,人口能呼吸,/我诗必长存,使你万世流芳”(辜正坤译),以及斯宾塞笔下的那句:“虽然死亡让世间一切臣服屈从,/而我们的爱永在,生命重燃”(胡家峦译),这都充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对情欲的渴求,认为世俗的爱可以使人战胜一切,走向永恒。
浮士德在这部剧中所展现的各种世俗欲望追求在人文主义者们的思想中皆可以听到回响。浮士德对传统学科的厌倦、对新奇知识的渴求充分展现了时代的变迁对人们思想的转变,正如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曾指责经院哲学总是准备告诉我们那些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贡献的东西,即使他们是正确的’,而对‘人的本性,我们生命的目的,以及我们走向哪里去’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不加理会”(董乐山14)。作为一个世俗生活中的人,浮士德对名誉的追逐正如人文主义者亚尔培蒂所说:“我相信,人不是生来虚度岁月的,而是要活跃地从事丰功伟绩”(董乐山32)、“只要不是完全懒惰成性和头脑迟钝的人,大自然都给他们注入了迫切想要得到赞美和光荣的愿望”(董乐山32-33)。浮士德对爱情和美的追求同样符合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他将彼世中虚无缥缈的幸福转换为了现世的欢愉,世俗的爱才是真真切切可以感受到,并给人带来幸福的。总之,在这部剧中浮士德对金银财宝、无限能力、寻欢作乐等世俗欲望的追求皆如同镜子般映照出文艺复兴人的现世精神与享乐主义态度。
三、世俗之理:浮士德的身份(人)索求
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浮士德世俗欲望的追求即是对人权的崇拜,这也就意味着人有权力去追逐那些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世俗物质,有权力在现世的生活中寻欢作乐。中世纪大学所开设的七艺课程,本意是自由人应学习的基本知识,所以被称作“liberal arts”,这种思想实际上渐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核心思想观念。人权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也有权力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他可以选择节制、向上向善,也可以顺应欲望拥抱满足和快乐,人文主义最活跃的代表人物皮科在他的《论人的尊严》中借上帝之口对亚当说:“我们使你既不属于天也不属于地,既非可朽亦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你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你任何偏爱的形式。你能堕落成更低级的野兽,也能照你灵魂的决断,在神圣的高级中重生”(顾超一、樊虹谷25)。在《圣经》中,人类始祖的堕落既是神性的消失,也是人性的显现,这样的人性在古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人是理性与欲望的结合物,缺任何一件都不能算作人。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存在之链宇宙观同样也提高了人的地位和尊严,处于中心位置的人既连接了兽的物质性,也连接了天使的精神性,“人不仅超过自然中较低的等级,在某种意义上也超过天使。天使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只能通过人在物质领域发生作用”(胡家峦111)。同样的,尼采在他的哲学中也肯定了欲望的合理性,他认为人性的最高成就是代表黑暗的汹涌和强烈的情欲力量的狄俄尼索斯精神与代表理性与秩序的阿波罗精神的协调(Stumpf & Fieser 362)。总之,人不应把自己束缚在原先被定义的存在概念之中,而应该明白自己才有选择自己身份的权力。
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劇》第二幕第一场浮士德与魔鬼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当浮士德与魔鬼签订协议时,他的血液突然凝固,一切仿佛被一种神的力量掌控着,阻止着他继续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浮士德却并没有就此回头,反而说道:“我的血凝固了,这是什么兆头?/难道神明不愿我签署这份契约?/血为何不流?为何不让我写下去?/‘浮士德将灵魂交出’——就停在这里!/怎么不能交?难道灵魂不属于我自己?/再试试:‘浮士德将灵魂交出’”(55)。在此,尽管有一种神力在阻止浮士德与魔鬼进行交易,但浮士德却依旧一再尝试并最终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从神的手中夺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如此抬高世俗人权的做法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也同样有所体现,剧中鲍西亚说道:“执法的人尚能把仁慈调剂着正义,人间的权力就和上帝的神力没有差别”(《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马洛在《帖木儿大帝》中更是表示:一个国王就好比半个上帝,甚至身为国王比上帝更加光荣,幸福要超过天上的神明,拥有权力去控制、命令别人,获得人们的恐惧和爱,可以为所欲为(Marlowe 101)。
同样,在这部剧的第三幕和第四幕中,罗马教皇以神授权力的名义要将被世俗王权授予教皇称号的布鲁诺处死,而浮士德却用魔法愚弄代表着神权的罗马教皇与他的教士们,并把布鲁诺救回德国,公然支持德国皇帝的世俗权力。在这里,浮士德站到了与罗马教皇所代表的神权的对立面,而与德国皇帝所代表的世俗人权站到了一起,正如德国皇帝所说:“你把布鲁诺从/我们共同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135)。可以看出在教会所代表的神权与德国皇帝所代表的世俗人权中,浮士德更看重人权的力量。
阿伦·布洛克表示,在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所绘的图象里,人是堕落的生物,没有上帝的协助无法有所作为;而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却是,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最高的优越境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人自己的成熟赢得名声(董乐山36)。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跨越了中世纪所宣扬的神权,与古希腊人所提倡的人权遥相呼应,正如古希腊智者安提丰在《论真理》(On Truth)中所说:“实际上按照physis(自然),不论是哪里的人,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自然给予一切人应有的补偿,这是人人都看得到的;所有人也都有能力获得这种补偿”(转引自叶秀山、王树人442),即自然赋予人应有的能力和自由的意志,使人既是万物的中心,也是“万物的尺度”。因此,浮士德大胆地表达并追求自己的欲望其实就是对世俗中人权的崇拜与追求,他公然表达了自己对世俗权力的支持,这一切都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人自身能力的自信、自由意志的肯定,以及人权的强调和重视。
在浮士德追求人权的过程中,他一步步地实践着对人之为人的身份索求。作为一个人,就理应有欲,这一点无论是在斯芬克斯身上、存在之链的宇宙观中,还是尼采的悲剧哲学,亦或是弗洛伊德的意识分区理论中都从未遭到过否认。古希腊智者安提丰认为,人为制定的“法律所确认的利益是自然的桎梏,自然所确定的利益却是自由的”。只有“按照自然”才能得到“有益的东西”,避免“有害的东西”(转引自叶秀山、王树人442)。因此,浮士德身上所体现出的世俗性在英国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之下具有特殊的进步意义,他鼓励人们从思想上脱离中世纪基督教严苛教条的束缚,着眼于尘世的幸福,按照自然的本性去生活,在人权的追逐中获取自由人的身份。这一点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现世精神和享乐主义态度,也正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所在。
结语
马洛版《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以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作为主线,在其间穿插了很多与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大背景相关的因素。结合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来看,剧中浮士德的世俗性欲望显然代表了当时的人渴望从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享乐主义态度和现世主义精神。这种大胆的描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好奇心的满足,马洛通过浮士德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的世俗欲望,虽然他的在追求欲望的过程中造成了诸多“恶”的产生,但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恶”的效应给予了一定肯定,恩格斯也同样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33),因此,马洛对浮士德世俗欲望的极尽描写在当时必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积极意义。但很明显作家更想为现世的人们提供一面映射文艺复兴时代的镜子,让人们看到浮士德的世俗欲望虽然是文艺复兴的一大精神,但也不能忽视他因欲望过盛,未把相应的权(才能)、利(收获)投入正确的使用,最后导致了下地狱的悲剧。这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虽自由,但不能自我膨胀。所以《哈姆雷特》里说得很辩证:“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人虽是万物的灵长,但算不了什么,不应自我膨胀,而且还要懂得克制。
注释【Notes】
①引用自英国著名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所写的《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中奥菲利亚对哈姆雷特的评价。中文参见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英文参见William Shakespeare, The Oxford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本文將在正文中以剧本名以及幕次、场次做注。
②本文所引用马洛版《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中译本来自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陈才宇译(浙江: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英文版参看Christopher Marlowe,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r. Faustu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下文中将仅用页码标注。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Abrams, M. H.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xford: Oxford UP, 2010.
Aldrich, Robe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Toronto: Hodder & Stoughton, 1982.
阿尼克斯特:《歌德与浮士德》。北京:三联书店,1986。
[Anikst. Goethe and Faus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Bullock, Alan. 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Trans. Dong Lesh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Cole, Douglas. Christopher Marlowe and the Renaissance of Tragedy. Westport: Praeger, 1995.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Hector, Helen.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London: I. B. Tauris, 2013.
胡家峦:《历史的星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西方传统宇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Hu, Jialuan. The Starry Heaven: English Renaissance Poetry and Traditional Cosmology. Beijing: Peking UP, 2001.]
Jump, John D., ed. Doctor Faustu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Le Goff, Jacques. 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 Trans. Zhang Ho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6.]
Levin, Harry. The Overreacher: A Study of Christopher Marlowe. London: Faber & Faber, 1964.
李定清:新历史主义视域下浮士德形象的时代转换与伦理变迁。《外国文学研究》6(2009):76-83。
[Li, Dingqing. “The Temporal and Ethical Evaluation of the Image of Faust form the Perspective of Neo-historicist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09):76-83.]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Ma, Keyao. A Study of Feudal Society in England. Beijing: Peking UP, 2005.]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陈才宇译。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
[Marlowe, Christophe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octor Faustus. Trans. Chen Caiyu. Hangzhou: Zhejiang Gongshang UP, 20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 and Engels. Vol. 20.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The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皮科·米兰多拉:《论人的尊严》。顾超一、樊虹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Mirandola, Pico. Oratiode hominis dignitate. Trans. Gu Chaoyi and Fan Honggu. Beijing: Peking UP, 2010.]
Peter, Womack.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Stumpf, Samuel Enoch and James Fieser. 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MacGraw-Hill Companies, 2007.
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二卷。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Ye, Xiushan and Wang Shuren. The Hi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Vol. 2. Nanjing: Phoenix Press,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