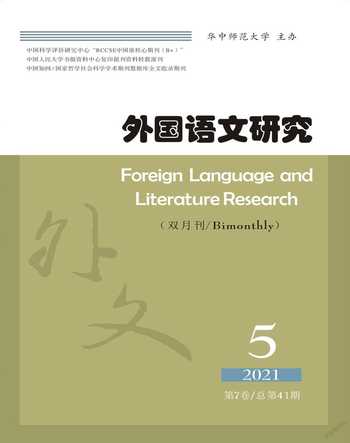语/象统觉与生命变构:论小说《金翅雀》中的语象叙事
李志峰 林茜
内容摘要:美国女作家唐娜·塔特的成长小说《金翅雀》于2014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小说中以名画“金翅雀”与主人公的纠缠为主线,主人公通过对视觉艺术品的认知,在不同阶段用不同的眼光来观察、感知和言说再现,形成不同的统觉,并经由语象叙事呈现出主人公成长中内心的不同阶段,其中“解剖课”成为了主人公习得创伤和陷入困境的现实具象,静物画成为定格自己内心创伤的休憩之所,“金翅雀”完成了主人公对人生和存在的顿悟,从而构造出主人公在经历爆炸之后创伤-成长的完整过程。名画与主人公在这一成长过程中的产生的张力也显示了视觉艺术品在治愈创伤和青少年成长中的美育作用,以及由此揭示出语象叙事的跨媒介性和隐喻性。
关键词:《金翅雀》;唐娜·塔特;语象叙事
作者简介:李志峰,文学博士,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林茜,广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Title: Language/Image Apperception and Life Transformation: On Ekphrasis in the Novel The Goldfinch
Abstract: American author Donna Tartts initiation novel The Goldfinch won the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in 2014. This novel focuses on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famous painting “Goldfinch” and a growing boy named Theo. Through the perception of visual artworks, Theo observes, perceives and verbally reproduces with different eyes at different stages, forming various apperception, and presenting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os inner growth through ekphrasis, in which “The Anatomy Lesson” of Rembrandt becomes a realistic image of Theos trauma and predicament, the Natura Mortes materializes a resting place to freeze his inner trauma, and “the Goldfinch” of Fabritius completes the Theos epiphany on life and existence, thus constructing a complete process of trauma-growth after the growing characters experience of the explosio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painting and the boy in this growth process also shows the aesthetic role of visual artworks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 and the growth of youth, as well as the cross-media and metaphorical nature of ekphrasis.
Key words: The Goldfinch; Donna Tartt; ekphrasis
Author: Li Zhif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Lin Qian is graduate student at Chin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E-mail: lin3qian@163.com
美國女作家唐娜·塔特(Donna Tartt,1963-)的第三部小说《金翅雀》(The Goldfinch)于2014年获得普利策小说奖(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小说以主人公西奥自十三岁经历大都会博物馆爆炸的恐怖袭击后的成长过程和心理转变为主线,用第一人称描绘了西奥在成长中心理活动的创伤和挣扎、对自我的追寻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主人公的成长,是其在经验、知识和心理活动等内容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反映现实的结果,是一个“统觉”①的过程。
除了与小说同名的、法布迪乌斯的名画“金翅雀(The Goldfinch)”之外,小说中还涉及了“解剖课(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NicolaesTulp)”“三个欧楂和一只蝴蝶(Three Medlars with a Butterfly)”等多幅艺术作品,并且这些关于艺术作品的情节设置和文字描述与主人公的成长息息相关。正如潘蜜拉·雷德(Pamela Rader)指出的那样,小说《金翅雀》使用了“语象叙事(ekphrasis)的创新,使人联想到受绘画启发的现代诗歌”,主人公“运用绘画中的美与不朽的比喻来渲染自己”(307)。语象叙事(ekphrasis)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指“运用栩栩如生的语言对事物进行描述”(王安 3),用以描述人物、战争、绘画与雕塑等等。到了当代,语象叙事基于赫夫南(James Heffernan)“视觉再现的文字再现(the verbal representation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的基础定义,成为沟通文字和物象之间的桥梁。语象叙事在新的读图时代中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叙事,而是一种文学的多形式、多模态表现,是以文学的方式联结两种艺术媒介,使得文字可视化也使艺术作品可读化,从而超越了从视觉到文学的单向度转变,建构出文学、视觉、权力等等多重话语互动的复杂阐释。《金翅雀》作为一部典型的美国成长小说,作者用很多的笔墨重点刻画了与主人公成长有关的众多视觉艺术作品:故事的演绎,伴随着主人公对某一特定的或多个不同的视觉艺术品,在不同阶段用不同的眼光来观察、感知和言说再现,即经由语/象创造出不同的统觉,并经由语象叙事展现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的同时,也以语象叙事这一多模态的叙事方式,增添了小说阅读中可读性和可视性兼具的趣味性。那么,小说中主人公成长的心理和意义即不同时期的统觉,是如何通过对于视觉艺术作品的语象叙事所表征的?小说又是如何通过文学将静止的艺术作品在主人公心灵中动态地呈现的?基于此,本文拟探析小说《金翅雀》的语象叙事,尝试透过对主人公各时期的“统觉”的过程,探究这些艺术作品在青少年成长主题、视觉与文字的多重动态转换之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揭示出小说在语言和图像的复杂关系之中所呈现的超越性和文学的弥漫性。
一、“解剖课”:作为视觉认知的创伤学习
语象叙事是对视觉艺术的文字描述,将视觉艺术作品通过语言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如此,“‘语象叙事是一种心理精神机制,它所模仿的并不一定是真正的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感知。文字所追求的并不是再现,而是为了在读者的脑海中模仿观看的这一行为”(Webb 38),换言之,即使是同一个叙事主体对于同一视觉艺术品的描述,也会随着主体的读图感受或者氛围的变化而前后不同,而这些前后的变化能够将叙事主体在成长过程中混杂模糊的情感通过“视觉化”的叙事具现为直观的视觉描述。小说《金翅雀》中,作者以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不厌其烦地呈现了“我”在经受了爆炸之后“创伤-成长”的过程中对视觉艺术品的读图感受,以此来表现主人公在创伤后成长的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
小说《金翅雀》的主人公西奥在小时候“自认为善于观察的人”(Tartt 10),更是受到从事艺术相关工作母亲的影响,不仅了解艺术绘画的基础知识,还由于儿童的特殊视角对艺术有着不同于大人的别样感受。在小说的第一章的第三小節,母亲带领西奥到大都会博物馆观看大型画展《肖像画与静物画:黄金时代的北方杰作》,这场画展的最主要展品之一是“解剖课”。“解剖课”是伦勃朗于1632年的成名作,描绘的是荷兰的杜普医生和他的七个学生的一堂解剖课。“解剖课”在绘画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在绘画内容上预示着科学的黎明,更是在光影表现上预示着十年之后伦勃朗划时代的作品《夜巡》的出现,由此观之,这幅画更像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从这一点出发,作者有意将现实中馆藏于海牙毛里茨海斯美术馆的“解剖课”移至大都会博物馆,作为主人公命运转折向下的重要画展里最主要呈现的艺术品,正是以这幅画中的多重暗喻预示着主人公在经受创伤之后的最终成长与升华。
“解剖课”的出现便指向了不幸。在母亲向西奥介绍这幅画之前,西奥只能通过视觉上的颜色和描绘的人物来感受这幅画的整体阴郁氛围,他注意到的是“惨白的肉体,深浅不一的黑色。那几名外科医生样子活像酒鬼,眼睛充血,红鼻头”(19),而且西奥总是在迷路时看见这个画着“手臂被剥了皮的尸体”的画,画面下面还被画展加上了“红色箭头:手术室,由此向前”的指示牌。在画展前一系列噩兆般的语象叙事实际上“在文本叙事中可以起到预示的作用”(Bartsch i)。毫无疑问的是,这里西奥在读图时对“解剖课”的感受是指向消极和不幸的,暗示了接下来将要在展会中发生的爆炸事件和人间炼狱般的悲惨场景:惨白的肉体和画面的黑色预示着死亡的发生,而“解剖课”巧合般的重复出现与加上的红色箭头则暗指即将降临的避无可避的悲惨命运。
“解剖课”在小说中不仅是与母亲一起去大都会博物馆观看的伦勃朗的名画,“解剖课”更是作为第一部第二章的标题,统率了本章的全部内容:爆炸发生之后我回家等待母亲而后知晓死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章中没有直接出现“解剖课”这幅画,也没有出现类似教学上“解剖课”的场景,那么本章标题“解剖课”该做何解呢?实际上,仔细考察可以发现,本章中主人公对于时空的语象描绘暗合了“解剖课”中的光影线条,甚至可以说,本章的描写技法上借鉴了“解剖课”空间描绘或者光影,以表现我等待母亲消息的“恐慌状态,并且在这种状态下试图说服自己一切都是正常的”(КОЗ?Й 80)的矛盾,这种矛盾正与母亲对于“解剖课”的点评一致:“觉得确实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但说不清哪里不对劲”(Tartt 21)。
正如“解剖课”的主要空间是一个黑暗的密闭空间一样,西奥略过了“看似漫无尽头”的回家路上所遇见的景象,这些都“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而将本章重点放在了对于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家这一空间的描绘上。在西奥回到家之后,分别在厨房、卧室、卫生间搜寻一切母亲回来的痕迹,最后在起居室等待母亲回家,但是此时的西奥已经隐隐有所预感,却尽量说服自己母亲还活着:“我试着设想耽搁了她的种种事情,结果什么想不出来”“也许她把手机弄丢了?”“她会不会是怕吵醒我,于是去了药店或熟食店?”家中的一切正常反而让西奥感到不安,一如在画展上母亲评价“解剖课”中尸体的手那样:“一眼就能看出来,感觉很不对劲”(Tartt 21)。一切的粉饰太平都在接到母亲死讯的电话之后破碎,此时西奥眼中的起居室彻彻底底变成了“解剖课”中的阴郁教室:
平时母亲在家时,起居室总是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氛围,但是此刻这里变得幽暗阴冷、令人不适,就像冬季里的度假屋:纤薄的织物,质地粗糙的西沙尔麻小地毯,从唐人街买来的纸质灯罩,太小太轻的椅子。所有家具都显得细长纤弱,就像踮脚而立,透出一种紧张。(Tartt 59)
“解剖课”中的空间阴暗而幽冷,隐没在黑暗之中,只有强光照亮了尸体,也照亮了围着尸体的八个人。相同的是,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之后,西奥感到原本温暖的起居室中的一切摆设都变得紧促而纤弱,尽管西奥打开了所有的灯,尤其是起居室顶上最亮的吊灯,但是还是显得“幽暗阴冷”,“一道道光圈闪闪烁烁”(60)。可以说,在得知母亲的死讯之后,西奥跌入了“解剖课”中尽管有强光照射但是阴冷的艺术世界之中,以“解剖课”的绘画空间呼应了刚刚得知母亲死讯的西奥的心理空间。
通过对“解剖课”描绘技巧的借用,西奥的第一人称语象叙事使得他掉入了一个“解剖课”的艺术世界。家中是“具有迟滞的艺术时间的西奥公寓的微观世界”,公寓之外的世界则是“具有正常时间特征的宏观世界(一般的世界)”(КОЗ?Й 82)。西奥多次注意到了窗外世界的正常:“天色已晚,人们纷纷下班归来,丢下公文包”(Tartt 52),这些都与西奥公寓中截然不同。西奥公寓中的艺术世界几近停滞的时空只发生了等待母亲这一件事,而公寓之外的世界还在按照正常的时间运转着,这意味着西奥掉进了由自己构造出的心理时空之中。正如“解剖课”中“走神”的角色通过直视的“眼”穿越画面空间与当下读图的人相交叠从而打破画框限制一样,这两个隔着墙壁的世界界限也是以西奥的“眼”被破坏:“我回到起居室,眺望着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52)。在此之后,现实世界渐渐入侵了西奥的艺术空间:先是声音、气味,之后是电话,最后是社工敲开了联结两个世界之间的门,西奥才意识到“我的生活结束了”(59)。在这个意义上,本章标题“解剖课”的解剖对象的不再是实体的尸体,而是陷入“解剖课”的阴暗空间之中又被强光聚焦的西奥的“正常生活”,又或者说,是和母亲在一起的正常生活,由此西奥完成了从正常世界“下降”至创伤世界的过程,“就像从六楼坠落一般”(59),换言之,西奥在“解剖课”中学会了创伤是什么。
语象叙事是用文字的描绘以“追求复制艺术品的即时视觉美和静止状态的目的”(Scott 64),尽管“解剖课”这幅画是静止的,但是通过成长主体西奥对“解剖课”的描绘和“借用”想象之后,成为了西奥承受创伤的过程中西奥无形的心理变化的现实具象化,从而拥有了动态的隐喻和在场力量。
二、静物画:照见心灵内省的创伤定格
尽管语象叙事狭义上指“用语言文字生动描绘视觉艺术品”,小说对静物画(Natura Mortes)的语象叙事以及对于“静物画”本身概念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视觉再现,而通过展示主人公对静物画视觉感受展现主人公的“心象”。小说中,成长主体西奥通过“内心之眼”观察静物画,特别是爆炸之后对于静物画的关注,折射出主人公的创伤心理。
“静物画”(Natura Mortes),源于法语,字面含义为“没有生命的物品”,静物画所描绘的对象也正是“了无生气的东西(still life)”,因此英文中也称静物画为“still life”。小说中母亲和浪荡商人霍斯特分别对“静物画”为何被称为“没有生命的自然物”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释,横跨主人公从中学时期到青年工作之后的,对于小说结构和主人公成长而言不可谓不重要。
母亲的评论揭示出了静物画的某种“自反性”。母亲在即将爆炸的画展上评论的是17世纪荷兰画家的德里安·科特的静物画《三个欧楂和一只蝴蝶》。17世纪的荷兰也正是静物画作为一种独立的绘画题材发展成型的时期,由于大航海时代生活方式的巨变加深了对生活和生命无常的认识,荷兰静物画中也受此影响诞生了“虚空画”,也即用过分美丽的物品和死亡的隐喻以表现“Vanitas(虚空)”、“memento(勿忘死亡)”和“car pe diem(活在当下)”等意识的静物画。而《三个欧楂和一只蝴蝶》正是“虚空画”中的代表作:“黑色的背景上,一只白色的蝴蝶在某种红色的水果上方飞舞”(Tartt19-20)。母親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幅画)在告诉你,生命只是昙花一现,无法长久。死就寓于生之中。所以静物画才叫Natura Mortes”(20)。显然,母亲看见了这幅静物画中“静与动、生与死”的统一。静物画作为静止的艺术,尽管只定格了物品的一瞬间,但是由于“细枝末节也有意义”,高明的创作者往往以高超的技巧赋予静物画以某种自反性(reflexivity),既描绘物品中“美感和蓬勃的生机”,也描绘了那个腐烂的、预示着死亡的小点,引导观看者走向生气蓬勃的静物画之反面——死亡,这也是母亲理解为何“静物画”被称作“了无生气的物”的原因。母亲对于静物画的评价实际上“隐含着生命决定性的特征——短暂性”(Rader 371),艺术,特别是绘画试图捕捉到瞬时的美并使其不朽,但同时又蕴含着毁灭和死亡,甚至只要经历一场火灾或者爆炸就会消失。
正如瓦萨里(Giorgio Vasari)以“艺格敷词(ekphrasis)”的方式再现图画时,不仅仅关注用语言复刻图像,更是将图像的内在意义和品格进行读解(reading in)(李宏82)一样,《金翅雀》中母亲对虚空画的语象叙事和评价,不仅在故事情节上死亡即将到来的预示功能,实际上还揭示出小说与静物画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于历史上被定格的静物画和当下正在面临创伤-成长的少年的一静一动之间。
这种张力首先产生于西奥在创伤中对静物画的凝视。如果说尚未经历爆炸的西奥对美的短暂性尚且懵懂,那么经历爆炸且失去母亲的西奥则以亲身经历演绎了美的失去,从而深陷于创伤的纠缠和时间的停滞之中。西奥的创伤首先体现在爆炸之后的“双重讲述(double telling)”上,即叙事者作为死亡亲历者和幸存者的双重叙事身份的重叠(Caruth 7),作为死亡亲历者不得不帮助死者做出见证,但是这种见证也蕴含着自己作为幸存者苟活的羞耻,责任感和自责之间的矛盾在生命主体的意识中拉扯撕裂,并且以不断回溯创伤画面的方式将叙事者留在原地。西奥的创伤后“双重讲述”分别表现在他在面对警察的盘问和心理医生的治疗:作为爆炸的亲历者西奥无法说出更多爆炸的细节,作为幸存者深藏着对母亲的内疚怀念又敷衍着心理医生的治疗。实际上,对于西奥而言,爆炸那天“就像一枚生锈的钉子”(Tartt 6)。可见,尽管在治愈创伤的过程中“述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西奥的“双重讲述”却完全是无效的,走向了创伤治愈的反面,从而悲观地显示了以语言进行创伤叙事的和不可描述性。
当语言和言说无效退场时,西奥选择了以图象,特别是静物画作为精神的慰藉。他在面对心理医生的言语治疗时,选择了“盯着他脑后的挂画。那幅画看起来像个用陶珠和绳结做成的挂歪了的算盘,我近期的生活里有一大部分是盯着它看”(128)。西奥也常常盯着巴伯家的艺术品看,“直接走到最棒的那些画前面……菲兹·亨利·莱恩和拉菲艾尔·皮尔”(383),从中可以看出,静物画成为了西奥精神上的逃避之地,这也因为静物画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西奥精神上时间的停滞有关。
西奥精神时间的停滞与创伤理论中的“延后性(belatedness)”密切相关。肯尼斯顿(Ann Keniston)讨论“9·11”诗歌的创伤书写之时指出,“延后性在创伤受害者那里常常体现为重复、闪回、预辩(prolepsis)等不同形式的时间不稳定状态”(661)。具体到小说中的西奥,他经常闪回、梦见且不断重复着回到爆炸的那天。“这种事时有发生,不论我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外面的大街上。我正走着路,这种感觉就会再度袭来,我仿佛又回到了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之前的那个怪异、扭曲的瞬间,再一次跟那个女孩凝眸对视”(Tartt94)。爆炸的视觉记忆对西奥的反复纠缠和折磨实际上就是“延后性”的体现,换言之,这些对于爆炸时刻的语象叙事意味着他的精神时间就像静物画中的物品一样被定格了,并且在不断回溯的反复渲染和描绘下变成了一副“过分精确”的静物画,精神上的定格和静物画的相合也是西奥在爆炸后常常注视静物画的原因之一。
通过建构陷入创伤的西奥与静物画的关系,作者借静物画暗示了西奥静止的精神状态和由此带来的影响。第十章中霍斯特讨论《金翅雀》与静物画的对比中指出 “(静物画)过分精确,那就等于给作品判了死刑。所以法语里才把静物画叫作‘死去的自然,是吧?”(496)与母亲关注静物画的内容不同的是,霍斯特对静物画概念的解释是从静物画的技法出发,指出了静物画对物品的描绘过于精确,压抑了从而抑制了未来阐释的更多空间。考虑到西奥此刻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了西奥与静物画一样,过多细节的创伤记忆和停滞的时间阻止了他走向未来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整部《金翅雀》被看作“西奥所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学自画像”(Rader 320),那么处于后灾难时期的西奥毫无疑问是陷入了“静物”状态——如同了无生气的行尸走肉自我封闭,“就像那些试验中失去了希望、躺在迷宫里挨饿的老鼠”(Tartt 189)。而且,与“静物画”中指向历史和时间流逝的静止不同的是,作为活动着的生命,西奥的精神却是静止的,这种一体两面形成了静物画与西奥之间在创伤状态下的层层张力——静物画不仅作为西奥情感的内心投射,更是作为他创伤中的静止精神的具象化和反身性的具象,从这个角度上看,与其说是创伤促使西奥与静物画产生共鸣,倒不如说是静物画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定格了西奥的创伤。那么,小说中对静物画的讨论实际上是在新的时空背景下重新演绎,将17世纪荷兰静物画中的“虚空”主题立足于主人公成长的转折点,探讨了少年创伤-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生与死、失去和得到等主题。
三、“金翅雀”:从生命体验到顿悟成长
语象叙事是“无可厚非的联系媒介”(龙艳霞15),在小说中通过相同的视觉媒介能够穿越虚·与实,将历史与当代、过去和现在相连接(Lundquist 261)。“小说《金翅雀》以荷兰画家卡尔·法布里蒂乌斯(Carel Fabritius)创作于1654年的画作‘金翅雀为标题”(苗福光62),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更是来自于法布里蒂乌斯死前尚未完成肖像画的主人西蒙·德克尔(Simon Decker)。小说中“金翅雀”这幅画与主人公西奥的纠葛贯穿了整本书,因此小说中不仅充满了对“金翅雀”的语言再现,而且“金翅雀”中被束缚的金色小鸟成为了贯穿整部小说和主人公成长历程中的隐喻。
“金翅雀”首先以两次灾难的在场将历史引入了当下。“金翅雀”完成的同一年,法布里蒂乌斯就丧生于一场“丹麦历史上的著名惨剧”——代尔夫特(Delft)火药库大爆炸之中,“金翅雀”就是那场爆炸的幸存者。而当西奥从母亲口中得知“金翅雀”和火药库爆炸的时候,殊不知另一场大爆炸将会在不久后发生,西奥失去了母亲却得到了这幅画。于是,“金翅雀”成为了两次艺术灾难之中的幸存者,“这个美丽的物体让我们想起了生存的奇迹:它在17世纪的代尔夫特爆炸中幸存下来,这次爆炸在1654年杀死了它的创造者,几个世纪后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通过抢救这幅画,西奥将他的故事与这幅画结合起来”(Rader 316)。实际上在现实中,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并未爆炸过,“金翅雀”被收藏在荷兰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也未失窃,作者于2003年一次阿姆斯特丹的旅行中了解这幅画的灾难背景,从而确定了小说《金翅雀》的方向。在小说中,经历过两次爆炸的“金翅雀”成为了西奥成长期的烦恼和命运相伴的朋友,也作为一个图像符号联结了历史和当下,为西奥的成长冒险增添历史气息和艺术魅力的同时,也为西奥的成长顿悟提供了历史维度的思考。
“金翅雀”还参与了西奥全部的成长历程,见证了西奥的成长。小说中西奥对“金翅雀”的读图叙事位于第1、6、11、12章,分别对应着西奥的成长转折点:第1章是西奥经历爆炸之前,第6章是西奥在拉斯维加斯与父亲住在一起后一切开始变坏之前,第11、12章是西奥在阿姆斯特丹经历了“夺画”之战后,特别是西奥绝望自杀前后精神世界中对“金翅雀”的描绘,说明了“金翅雀”在他成长顿悟时刻的重要作用。正如马苏米(Brian Massumi)所说“每次与艺术品相遇均会发生新的事件”(82),西奥的成长体现在不同的阶段对“金翅雀”的读图感知的不同。当还是孩子的西奥第一次在画展上见到“金翅雀”时,只是单纯的描述:“平淡的浅色背景上,一只黄色小雀脚爪被链子拴在一个栖木上”(Tartt 22-23),最吸引他的就是那只小鸟,“这个小家伙被画得直接而写实,没有什么感情用事的渲染笔触;它好像把某种性情——机灵、警惕的神情——严严实实干脆利落地掩藏在心底”(23)。此时的西奥只能将画中的小鸟与旧照片上的母亲形象联系在一起,因为年幼的他的经验不足以支撑更深层次的思考,在视觉上无法召唤出更多的联想和感知。但是,在经历了母亲死亡、和父亲住在新城市并且交到了新朋友之后的西奥再次见到“金翅雀”时,“它的光芒立刻包裹了我,我感到一股恍若音乐的甜蜜感,那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深层鼓动,让人血液沸腾得和谐而自然,心脏跳得又慢又自信,仿佛面对着让人安心、充满爱意的伴侣”(276)。两者隔着众多章节遥遥呼应,又截然不同,尤其是在情感上。前者的“金翅雀”只是单纯的呈现,总体而言是平凡单调,而在后者西奥则赋予了“金翅雀”以丰沛的情感,拥有了第一次观看时缺失了的生命力。对于西奥而言,两次对“金翅雀”读图的不同来自于经历了伤痛来到拉斯维加斯的西奥感受到了这幅画“来自于不可追的往昔”(276),即“这幅画看到了他的眼泪、愤怒和这个年轻主人公的每一种心灵情感”(Rader 18),也是主人公成长秘密的共享者和见证者。
“金翅雀”对西奥的意义不仅在于成长同伴,更在于它成为了他命运的导师。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是长了翅膀的生命,但是我们也被束缚;我们可以飞,我们又不能飞”(Brown 1)。正如作者所言,“金翅雀”中被束缚的黄色小鸟正是某种人类命运的隐喻:在可以飞但又不能飞,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生存悖论。那么,西奥的成长冒险也正对应着他在第一次见到“金翅雀”时皮帕问出的那句:“这只鸟只能那样过一辈子吗?”(24)如同这只被锁住的小鸟一样,西奥的命运徘徊在幸福与痛苦之前,过往的记忆特别是和和母亲一起生活的记忆就像锁链一样锁住他前行的脚步,之后父亲的不怀好意和死亡,好友鲍里斯和未婚妻的背叛,还有无时无刻害怕被抓捕的恐惧,生活的种种不幸和他对于美好的向往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交织上升,直到阿姆斯特丹的寻画之旅达到了顶峰,也“激发主人公反省和顿悟”(芮渝萍300)。引发成长顿悟的关键正在于对“金翅雀”的再次读图解读,西奥想象着法布里蒂乌斯的作画场景:“强壮结实的翅膀,轻轻抹出的针羽。他画笔的速度跃然纸上:坚决果断的一挥,颜料在那一笔下厚厚堆积”(Tartt 656),也意识到这幅画里“只有微弱的心跳和孤独,灿烂阳光下的墙面和无可逃脱的绝望”,但是“困在光芒中心的那只小囚徒,毫不畏缩”,它的尊严是不可否认的:“顶针大小的勇气,毛茸茸的羽毛,脆弱易碎的骨头。并不胆怯,也不绝望,只是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地盘上,拒绝对世界投降”(657)。西奥在痛苦的成长历程中深切地了解“所有人的人生都只有悲剧的结尾”,但是“金翅雀”中的黄色小鸟形象却给予他一种超越时间的艺术救赎,解救他处于混乱无序和痛苦破碎的心。面对永恒定格的束缚和痛苦,弱小的它不低头屈服。终于,西奥从中意识到生存的关键,即面对永恒痛苦的勇气和尊严,像黄色小鸟一样高傲不低頭的毫不退让,纵情投入人生;同时也找到了艺术事业的真谛:艺术的代际传承能够超越有限的生命,“只要画是不朽的(它是),我在那不朽里就占有小而明亮、不可动摇的一席之地”(661)。
简言之,作者正是以“金翅雀”的语象叙事联结西奥所有的成长阶段,在这幅画在小说中不同阶段的语象叙事中,西奥所经历的人生痛苦、自我挣扎的过程与自我救赎和解就通过这幅画自由穿梭在画里画外的虚与实、画所代表的历史和西奥面临的困境之间。在各种生活的旋涡和矛盾交织上升至最激烈之时,“金翅雀”通过它所承载的图像象征和艺术救赎使他对于生与死、人生和痛苦、有限与不朽等主题有了更加深层次的认知,最终完成了西奥的成长顿悟。
语象叙事是“完全隐喻的表达:它通过文字再现的视觉意象是不可能真实亲见的他者的艺术”,而且“关注图像(意象)与文字(词语)的关系”(王安 82)。于是,语象叙事成为了文字的语言模态和艺术品的视觉模态的叠加,不仅有助于表现成长主人公的成长过程,而且通过视觉艺术品所承载的某种历史和哲思实现了文本叙事的升华。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的视觉化和弥漫至图像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文字在历时性上叙事的自我剖析和成长追问又是强调共时性的图像不可取代的,于是语象叙事成为了文学在图像转向中突破牢笼的弥漫方向之一。正如小说中,“解剖课”成为了主人公习得创伤和陷入困境的现实具象,静物画成为主人公定格自己内心创伤的休憩之所,“金翅雀”完成了主人公对人生和存在的顿悟,这些视觉艺术品对主人公的影响正是通过语象叙事表现,成为了主人公成长历程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更是故事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对于画作的观察-意识-表述(反思)-认知的统觉过程,承载了少年成长过程的视觉认知、心灵内省、生命体验等不断变化的多重意义。
注释【Notes】
①“统觉”这一概念经由莱布尼茨与康德的统觉学说,再到现代心理学家冯特的发展,“统觉”被理解为多元复杂的表象可以经由认识主体的综合活动及其意识,获得对自己的思想或不同表象的认知并辨识同一的自身。这意味着对同一客观对象,不同的个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都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观察、感知和再现,都具有不同的统觉。参见石磊、崔晓天、王忠,《哲学新概念词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268-269。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Brown, Mick. “Donna Tartt: If Im Working, Im Not Happy.” The Telegraph Apr. 17, 2014.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JHU, 1995.
Jerry,Gracia. “Adherence to Adolescence: A Psycho-analytical View on Donna Tartts The Goldfinch.”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ocial Issues 2 (2017): 18-25.
Keniston, Ann. “‘Not Needed, Except as Meaning: Belatedness in Post-9/11 American Poetr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2 (2011):4.
КОЗ?Й, ОльгаБорис?вна. НАУКОВ? ЗАПИСКИ. Костенко Л.Д., 2021.
龙艳霞、唐伟胜:从《秘密金鱼》看“语象叙事”的叙事功能。《外国语文》3(2015):51-56。
[Long, Yanxia and Tang Weisheng. “Narrative Function of Ekphrasis as Represented in The Secret Goldfish.” Foreign Language 3 (2015):51-56.]
Lundquist, Sara. “Reverence and Resistance: Barbara Guest, Ekphrasis, and the Female Gaz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 (1997):15-16.
Massumi, Brian. Semblance and Event: Activist Philosophy and the Occurrent Ar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1.
苗福光:《金翅雀》的金色光芒——评2014年普利策小说奖作品《金翅雀》。《外国文学动态》4(2014):62-64。
[Miao, Fuguang. “The Golden Glow of The Goldfinch—Review of The Goldfinch, 2014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World Literature: Recent Developments 4 (2014): 62-64.]
Rader, Pamela J. “Life Has Got Awfully Dramatic All of a Sudden, Hasnt It? Just Like a Fiction: The Art of Writing Life in Donna Tartts Novels.” The Self (2015): 307-314.
芮渝萍、范誼:《成长的风景:当代美国成长小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Rui,Yupin and Fan Yi. Growing Landscape: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itiation Nove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唐娜·塔特:《金翅雀》。李天奇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Tarrt, Donna. Goldfinch. Trans. Li Tianqi, et al.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6.]
王安:《语象叙事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Wang, An. Study on Ekphrasi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9.]
——、程锡麟:西方文论关键词:语象叙事。《外国文学》4(2016):77-87。
[--- and Cheng Xilin. “Ekphrasis: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6): 77-87.]
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