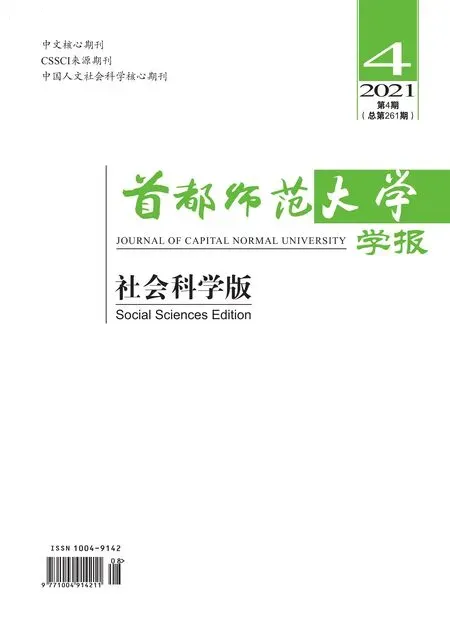美与艺术的范畴
高建平
我们区分美与美感,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能直观地理解成“一个主体遇到一个客体所发生的一个事件”。无论是在主体一边,还是客体一边,都有许多此前的积累。而这些积累,又是主体与客体在漫长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过去的知识积累下来,可成为当下的直接的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美感,而美感的对象就是美。因此,美与美感有着一个共同生长、相互成就的过程。
美有很多种类,需要进行分类研究。当我们说美的时候,还要区分狭义的美和广义的美。狭义的美,是呈现在当下,给人提供直接的愉悦的对象。除了这种狭义的美以外,还有其他各种感受,例如震撼、惊恐、哀怜、发笑、厌恶、恶心,等等,也能给人带来感性的刺激,也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美学”(aesthetics)这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感性学”,研究人对外界的各种感性反应。汉字文化圈将这个词翻译成“美学”这两个字,也常常被人理解成关于美的学问。美学不应只研究狭义的美,而应将广义的各种审美对象都包括在内。
这种感性反应及其相应的对象,可以分成许多的类,但任何分类都不能穷尽无限丰富而细腻的人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感受。这里只是列举几个相对重要和常见的类别,并在列举过程中,说明其中的复杂性。
一、美
当人们说一物是美的,或者说对一物作出美的判断时,有人依据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依据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的原因在于人的心理,客观的原因在于物的形态。我们已经说明了这里的复杂性。任何这方面的研究,都必须结合主体和客体的状况,结合个人与社会的状况。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放弃像柏拉图所做的那样,致力于对“美”和“美的”的区分,从而陷入对“美本身”的寻找之中。有关美的哲学论述,以及在涉及到美的问题时主客间的纠结的情况,我在别的文章中已经作了说明。在这里,我们只是对美的特征作具体的描述。也就是说,当我们谈论美与艺术的范畴时,所涉及到的,是对“美的”事物的分类。
美的特征,依据传统的观点,包括三个方面:
一、平衡或对称,适当的度和比例。这主要指对象中不同要素间的关系构成一种和谐。这里有量的关系:不同音高、音长的声音的结合而成为音乐,而不同的声音的声波波长之间是一种数量关系。同样,颜色的不同也是光波波长不同造成的,其间也是数量的关系。但另一方面,美也可以是不同质的事物间的和谐组合。一片美丽的风景要有山有水,有树有石,和谐搭配。一座美丽的建筑,也是木石铜铁各种建筑材料的组合。古代中国人在讨论音乐美时更重视音的质,他们讲“八音克谐”,是八种不同的乐器发出的不同质的声音的结合。①语出《尚书·尧典》,八音指用八种不同的材料制成的乐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见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二、材质、颜色、光泽。美既存在于不同的事物或事物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之中,也存在于单一事物之中。人们可以谈论黄金白银的美,不是由于它们是贵金属而成为财富的象征,而是由于它们的色彩和光泽。物的材质也能成为美:家具的材质、建筑的用料,都成为美的要素。绿色的大草原、蓝天和大海、法国南部一望无际的薰衣草、荷兰的郁金香、中国江南大片的菜花黄和秧苗绿,都与平衡对称无关,只是一种单纯的颜色,以其巨大的规模而使人感到美。物之美还体现在光之美之上。朝阳有特别的美,夕阳也有自己的美。阳光照在物之上,会产生千奇百变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物的单纯的美,不依赖物的要素间的关系。
三、整体性,成为一个几何的或有机的整体。事物可以有整体的美,这种美只存在于整体之中。按照一些几何图形所建成的房屋、公园、广场,可以有着整体的美,这种整体如果残缺了,就失去了美。文学艺术作品有自己的完整性,长到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短到四句抒情小诗,大到绘画长卷,小到一幅速写,都有自身的完整性,就像一个或者巨大,或者微小的生命体,都有头、身体和肢体、各种器官,有自身的各种内在循环系统。
这是欧洲古典美的三个基本要素。中国人的美,在一些地方有所不同。中国的宫殿或官邸的建筑固然也讲整齐对称,但这种在平面中展开的整齐对称,并不能只是静态地看待其整体性,而要看到其动态的视觉呈现过程。例如北京故宫,宫殿群的排列既是静态的存在,又是从观赏者行进过程中看到的角度变化和感受递进的体现。从前门到午门,直到太和殿走向第一次高潮,再经中和殿、保和殿,再到乾清宫,观赏者的感受也走向起伏深化。中国的园林打破欧洲园林的整齐对称,而将景观动态化,追求观赏山水景观时的随处换景、山重水复、曲径通幽,又豁然开朗。再如,中国绘画受书法影响,克服几何图形的布局,而追求通过绘画的用笔用墨的动作,使画面成为动作的痕迹,画家的气韵风神在画面中得到表现。
在现代艺术中,对这三个要素也多有突破。例如,现代艺术追求的非对称的美,利用非对称造型形成的反差产生美。再如,建筑克服整齐划一和几何型布局,从自然中汲取新的灵感。在光与色方面,更多地利用新的科技,特别新光源的使用,产生过去所没有的奇特效果。在有机整体的追求方面,引入了残缺美概念,让完整的有机整体成为一个隐藏的理解框架,并以此从内在的整体观看这种当下的整体缺失,使欣赏者的心理反应成为可能。
一些美学家还讨论过美与合适的区分。美是由于一物自身而美,在于对象自身的种种要素的使用和实现,而合适是一物适合于他物而美。例如,一物由于自身的形式,包括尺度和比例,可以是美的。一物对于他物的合适,是依据他物来决定它是否美。一件衣服是否美,要看它本身的材质和式样,也要看是谁在穿,是否适合这个人的身材、肤色和气质,是否适合穿衣服人的年龄、身份、穿衣服的场合,等等。离开所穿的人来谈论衣服的美,是空泛的,是使一种本应有所依托的合适变得无所依托。在建筑中,配楼适合主楼;在西方古典油画中,配景适合人物;在中国书画中,题字和印章适合绘画主体;如此等等。
美与媚也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这一对比之中,美倾向于静态的形式,即上面所说的形式的三要素,或者其他一些新的要素;与此相反,媚则倾向于展示生命的活力,展示活动着的身体或景与物所具有的吸引力。
从美的事物的特性看,还有着复杂美与单纯美的区分。在艺术中,有复杂装饰的美,也有单纯无装饰的美。宗白华曾区分错彩镂金、雕绘满眼的美与芙蓉出水、自然可爱的美,就是对这种不同的美的形象描绘。①见《宗白华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50—454页。现代艺术中的极简主义运动,是一种对复杂美的反抗。通过这一运动,改变了艺术中繁复的装饰追求,以简单的形式和线条,呈现出具有现代感的美。
美是多种多样的,人们通过上述一些列举、对举等方式,对各种各样的美加以说明,但这一切都不能穷尽美的无限多样,因为美是不可穷尽的。
二、崇高
崇高是一种重要的美学范畴,它的形成,在美学形成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欧洲,“崇高”概念最早由古罗马时代的一位托名为朗吉弩斯(Longinus)的人提出。这位匿名的作者留下一篇以希腊文写成的文章《论崇高》(Peri Hupsous,即On The Sublime),在这篇文章中,“崇高”主要是指“伟大”“高昂”“高尚”一类的意义,是一个形容词。讲演更雄辩,文章写得更有气势,诗的格调更阳刚,都是“崇高”。1674年,法国新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将这篇文章译成了法文出版,推动了“崇高”概念在法国,以至在整个欧洲的传播和发展。布瓦洛将古典主义对形式的推崇与对艺术中的激情表现结合起来,保持了朗吉弩斯关于用崇高指伟大的风格的修辞学传统。
在17世纪末,有三位著名的英国人,即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夏夫茨伯里和约瑟夫·爱迪生(Joseph Addison),他们分别写文章,用崇高一词描绘他们游历阿尔卑斯山的震撼、恐惧而又转为狂喜的感受。崇高由此与对自然的欣赏联系起来,这是崇高成为独立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契机。1735年,英国人伯克发表了《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SublimeandBeautiful,1757)一书,将美与崇高加以对比,认为:“崇高的事物在尺寸上是巨大的,而美的事物则是娇小的;美的事物应当是平滑、光亮的,而崇高的事物则是粗糙不平的;美的事物应当是避免直线,在偏离的时候,也令人难以察觉,而崇高的事物在很多情况下却以直线条的方式出现,即便存在偏离也是极为明显的;美不应当暧昧不明,而崇高则倾向于黑暗和晦涩;美应当柔和、精细,而崇高则坚固甚至厚重。”①埃德蒙·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这部著作延续了在英国形成的这种以崇高指自然物的传统,但在“崇高”概念史上至少完成了两个飞跃:第一是“崇高”的名词化用法得到固定,即将崇高看成一个独立的美学范畴,而不仅是针对具体事物或艺术性质的描述;第二是将“崇高”与“美”这两个范畴相对举,相互独立,既相反又相联。
在伯克以后,对“崇高”概念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康德。他于1790年发表了《判断力批判》一书,书中延续了美与崇高的对立,并提出了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之分。数学的崇高,是指对象的绝对的巨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审美中试图运用想象力,以一次单一的直觉来把握和包容整个表象,但又无法做到。表象对人的想象力构成一种压力,但理性自身又要求一种完整性。于是,两者之间构成一种冲突。它所带来的不是直接的愉悦,而是首先给予痛感,再克服痛感,通过领会理性的伟大来体验快感。力学的崇高指压倒性的力量形成我们在实际上安全的环境中感到似乎可怕的情景。例如,电闪、雷鸣、旋风、火山,等等。但是,如果这些可怕的对象对人真正构成威胁,那也就不是崇高,也不能构成欣赏了。崇高的对象要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那样,使人“恐而不惧”。对崇高的欣赏,反映出的是一种具有无比力量的自然对我们的威压,并由此激发出我们内心的道德力量。
康德对崇高的论述,充满着强烈的思辨色彩,使直观的感受转化成了真正具有哲学性的论题。至此,美与崇高的两极在理论上被固定下来。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谈论美以及种种对它的偏离,而是将各种各样对不同对象的欣赏,通过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不同模式,分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极,并将各种不同的感受向这两极汇聚。
在崇高对象从自然转向人,再转向艺术的过程中,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浪漫主义者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喜欢自然。他们正是通过诗歌对自然的描写,将崇高观念内化成了一种艺术的风格。
到了20世纪,利奥塔认为,不管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从本质上讲都是在追求崇高。他提出了独特的两种崇高来描绘艺术,提出现代主义的艺术,是一种带着抑郁感的怀旧的崇高(nostalgia sublime),以德国表现主义艺术,马列维奇、普鲁斯特等人为代表,而后现代主义艺术是一种追新的崇高(novatio sublime),以从塞尚,到立体主义,再到抽象艺术为代表。1985年,利奥塔在巴黎的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策划了一个展览,名为《无形物》(Les Immateriau),试图以无形见有形,并将这种观念与康德的崇高,即在理性和道德的帮助下克服当下感观对象的压迫联系起来。
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一些比美更高层次的范畴,并不与美相对立,而是层层递进。例如,孟子曾谈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②《孟子·尽心章句下》,引自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十一·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这些词,都是对一些不同层次的状态的形容。在今天的汉语中,对崇高一词的理解,更偏向于生活和伦理,例如讲人的性格、品德、行为的崇高。作为美学范畴,则比这些要更广泛一些,应该包括自然、社会和艺术等各个领域里的崇高。
三、笑
笑有多种多样:有微笑,内心感到愉快时,或者为了向人表示友好时是如此;也有大笑,内心感到得意时,或者看到什么可笑的事件或场景时是如此。当然,还有更复杂的情感可以通过笑来表达:讽刺地笑、轻蔑地笑、威胁地笑、关爱地笑、无奈地笑、尴尬地笑,等等。美学中所研究的笑,主要在于如何用艺术的手段使人发笑,这涉及对作为艺术手段的笑进行分类,也涉及对笑的心理进行研究。
一般说来,要逗人发笑,有幽默和滑稽两种手段。幽默指利用语言表现引人发笑,而滑稽则指用动作表演使人发笑。例如,一个人讲述某人滑跤的故事,把大家逗乐了,就是幽默,但如果这个人在表演滑跤,那是滑稽。然而,这两者又是不可区分的。《史记》中有《滑稽列传》,但其中所讲的事,多为幽默,即用机智的表达方式,将原本冒犯的意思以不太冒犯的形式表达出来。
关于使人发笑的原因,历史上有一些哲学家做过一些总结。具体说来,有这样几条:
第一,“优越理论”(superiority theories)。这种理论强调笑的人有一种自我优越感。人们笑别人傻、笨拙、吝啬,笑邻居或相邻人群、相邻民族的生活习惯。例如英格兰人笑爱尔兰人或苏格兰人,比利时人笑弗莱芒人或荷兰人,瑞典人笑挪威人或芬兰人。他们说起这些邻近民族的笑话来,似乎有着无穷的乐趣。中国人以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作为笑话的源泉,城里人笑乡下人说话“土气”,没有见识。乡下人也看不惯城里人做派。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城里人将长凳说成条凳、做鱼用葱丝、城里女人的走路姿势,阿Q都觉得可笑。在相声和小品中,喜欢拿方言作为笑料,例如宋丹丹表演东北话、牛群讲河南话、朱时茂教陈佩斯说上海话,都能产生喜剧性效果。对此,“优越理论”可以提供解释。
笑是要笑可笑之人,这种可笑之人的可笑之处,有愚笨却不自觉,还有不聪明还要自作聪明,明眼人一看就觉得可笑。阿Q觉得城里人可笑,而读者却觉得正是由于此,阿Q才可笑,属于“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表现。著名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引用过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说明在人们自作聪明时,对于真正的智者来说,这不过是笑料而已。佛教中的弥勒佛笑口常开,笑世间可笑之人,也是这样一种对世间纷争的超越,显出种种自作聪明的渺小。
在近代,英国人霍布斯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理论,这就是“突然荣耀”(sudden glory)说。体验到自己的胜利和对手的失败滋味,不由得笑了起来。同样,想到自己过去做的某件傻事,也会发笑。无论是笑别人,还是笑自己,都是优越理论。但是,“突然荣耀”理论要强调突然性。“优越理论”可以是比较和反思的结果,体现了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但是,人们的笑是感性的,是对当下的情境的直接反应。引起人们发笑的,不是自己胜利和对手失败的事实本身,而是这一事实在当下意识中的突然出现。同样,人们也不是由于自己比别的某人更聪明这一感觉本身而得意洋洋发笑,而是某一具体事件的突然发生、某一消息的突然获悉或者某一现象的突然呈现,验证人们的这一感觉,使他们忍不住笑出声来。
在人们说笑话、相声或小品以及喜剧表演中,要把握这种“突然”的特点。同样的故事,有的人讲了就能使人发笑,换一个人讲,就使人笑不起来,这是由喜剧表演的才能决定的。这种表演才能体现在多个方面,是一种综合的能力。在其中,讲述时的声音的音调、节奏的把握、讲述者的神态,都决定了故事的“笑点”是否起到了作用,或者用相声术语说,就是“包袱”能否“抖响”。这种“突然”性,就构成一种形象性的片断,它源自“自我的荣耀”却又超越了这种“荣耀”感。某个喜剧表演让人们一想到就笑,与人一谈到就笑,大笑不已。这决不是由于某种荣耀而得意洋洋,反复品味这种胜利的滋味,而是由于某种形象性的表现所具有的“搞笑”的能力,可给人提供的瞬间的感觉,这已经与有关自身的功利性考虑没有直接关系了。
第二,“不连贯理论”(incongruity theories),过去也译成“乖讹理论”,指对象相悖或错乱。走路有脚疾,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平稳走路,一高一低使人感到可笑。说话口吃,不能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也让人感到可笑。这是说,正常不可笑,不正常就可笑。这与“优越理论”有相通之处。
有时,身体的缺陷也被人嘲笑,如阿Q的癞痢头成为村民们嘲笑的对象。长得太胖或者太瘦,太高或者太矮会使人发笑,一些喜剧演员也以此通过自嘲来搞笑。另外,一些表演时的不谐调,也会引发笑声。在舞台上滑倒,表演的道具脱手,讲话时忘了台词,唱歌时走了调,都会使人发笑。人们会理解这些无伤大雅的失误,对此抱以宽容的笑声。在一些表演中,也会故意制造这种错误,造成种种“错误的喜剧”,或者由误会引人发笑的小品,使台下笑声不断。
西赛罗曾说,预想一个结果没有实现,所产生的失望情绪会转为一笑。类似的话其他一些哲学家也说过。例如康德说,如果有一个紧张的预期突然化为乌有,会引发大笑。一群人聚在一起,以为会有大祸临头,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很可能就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原有的预期逻辑断裂,伴随着庆幸与自嘲的感受,引发出大笑。《等待戈多》则反其意用之,等待,却不知道等待什么,从而具有双重效果,表面上是喜剧性的,而实质上是悲剧性的。
柏格森提出笑源于概念化与经验的不一致。他认为,人的生命特征就体现在具有灵活性,以适应当下生活需要之上。“滑稽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活的身体僵化成了机器。”①柏格森:《笑》,徐继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那种机械的、依照概念行事而不具有弹性的行为和动作就是可笑的。例如,搬了家后,不自觉地走到原来住的地方,推门一看,早已是别人的家;幼儿园老师回到家里,对家人或者对朋友,还用对孩子说话的语调;戏剧演员在日常说话中带上戏剧腔;一位老兵退伍后在餐馆端盘子,当有人恶作剧地喊一声“立正”时,老兵会本能地扔掉装满饭菜的盘子做“立正”的姿势。这些过去的习惯动作在新的情况下重复,老习惯难改,从而犯错,发现后自己感到好笑,别人看到后也会忍不住笑起来。人的活动,既有一种惯性,又会展现出生命的活力,对环境有着适应性。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适应性丧失了,或者没有很好地展示,就会出现“机械化”。一些醉酒的笑话也是如此。醉酒使人失去了对外界情况的适应性,只按照意愿来行动,就会闹出笑话。
这种“生命的机械化”,实际上也是“不连贯理论”的一个分支。“不连贯理论”中有些例子用“优越理论”也可解释,但有些则明显不同,用“不连贯”能得到更好的解释。
第三,释放理论(release theories)。紧张后寻求放松,郁闷时需要散心。在压抑的语境中,人们常常借助幽默来排遣苦闷的心情。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一个笑话常常能使情绪得到调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提出了神经系统的压力模式。正像蒸汽机中的蒸汽通过管道释放一样,情感的神经刺激淤积而产生压力,得到释放这种压力就会减轻。斯宾塞认为,笑是一种肌肉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神经的刺激得到了释放。
释放理论的最主要的代表,是弗洛伊德。他把人的心理区分为三层,即“伊德”或“本我”(id)、“自我”(ego)以及“超我”(super-go)。“本我”是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超我”是批评意识,而“自我”在“超我”与“本我”间起协调作用。这种协调需要花费心理能量,如果所动员的能量超过所需要的能量时,这种能量就以各种方式释放,其中一种就是笑。
民间的笑话中,有许多与性有关,而这些故事能够产生笑点,也是利用了这种心理能量寻求释放的要求。笑话使内在的能量释放而轻松,产生爽快的感觉。
第四,游戏理论(play theory),指游戏状态是娱乐或笑的条件。语言的游戏,包括声音的游戏和意义的游戏。绕口令使人感到发笑,是发音能力的展示;饮宴时行酒令带来欢乐,就是才华加巧智能力的展示。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引人发笑的表述来自对既有成语、谚语和名言警句的有意借用或故意错用。例如,批评一个人做事“十拿九不稳”“百发不中”,都是与人们熟悉的成语相对照以形成特定的效果。再如,说一个人“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坐别人的位置,让别人无位可坐”,都是在套用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引发笑的原理有好几种,这几种原理又有着各自的变异的用法,形成丰富多彩的笑的理论。在具体的搞笑的作品中,有这些原理混用的现象,即同一部作品混用了多种笑的原理。例如,“优越理论”可以与“不连贯理论”混用,前面所讲的“生命机械化”,从“优越理论”来讲,也可以讲得通。“释放理论”与“游戏理论”也有相通之处。一些犹太笑话,就既有性的成份,也显出机智性。
198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牛群和李立山合演的反腐相声《巧立名目》,就是混用了几种不同的笑的原理。首先,在相声一开始就说“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就是有意错用常用的格言引发笑声,这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所产生的笑。后面所讲的以纪念外国名人的名义去吃烤鸭,而这些外国名人与他们毫无关系,从而显示其荒谬,是一种典型的“不连贯”的错位所产生的笑。在相声中,多次重复的“领导,冒号”中的“冒号”两个字,用奇特的音调读出,是一种声音的不正常所产生的“不连贯”。声音“不连贯”在重复,会产生一种叠加的效果,经过多次重复,笑声不断增加。相反,巧智所造成的游戏或“不连贯”,则不能重复。笑话第一次听觉得可笑,但重复听就觉得无趣了;而奇特的声音所激发的笑声,却由于多次重复效果越来越强烈。这是一个有趣而值得深入研究的现象。
当然,笑的出现依赖于对度的把握。在幽默与恶俗之间,掌握好度非常重要。恶俗不会引人发笑,而只会令人恶心;可以笑人犯了一次傻,但不能笑真正智障的患者;可以笑人摔了一跤,但不能笑摔伤摔死的人;可以笑人老习惯难改,但不能笑强迫症患者;可以笑人无意中说了一句错话,读错了一个字,但说话阅读水平太差了,就让人笑不起来了。这些都说明,引起笑有各种原因,但这些都是在一定的度的限制之内才起作用。
四、历史感
时间维度能够进入审美,特别是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之中,这是过去的美学范畴研究所没有注意到的。人们研究美、崇高和笑等范畴时,固然考虑到了时间性。但是,对美学范畴的研究,其本身只是对美的种类进行分类,并研究与它们相应的心理机制,以及它们的发生原理。在从事这种研究时,时间性是被悬置的。不同的范畴只是作为美和美感的类而存在,本身的时间性不被关注,更不成为分类的依据。人们所关心的只是美和崇高的永恒性、笑的心理和逻辑特点。然而,历史感这一范畴,却正是把时间性本身当作核心组成部分。
从艺术的开端起,时间性就与审美结下了不解之缘。各原始民族都有史诗,在叙事性的文学中,有许多讲史的故事。产生这些文学作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喜欢故事,将之理解成是对过去事件的陈述。这种陈述本身就能给人们带来愉悦。
孩子缠着大人讲故事,幼儿园孩子爱听老师讲故事,喜欢看故事性强的连环画或电视剧。一些民间的故事,都喜欢用“很久很久以前……”来开头。一些长篇小说常常能够给人提供历史的纵深感。中国的长篇小说,都喜欢作历史溯源。《红楼梦》从女娲补天讲起,说起其中“无材补天”的一块遗石的故事;《水浒传》讲洪太尉放出妖魔,妖魔化身人间、大闹天下的故事;《三国演义》谈到分与合的天下大势,引出思古之幽情,引发“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的感叹。欧洲曾流行长河小说,通过几代人的故事反映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左拉的《卢贡-玛卡尔家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在向读者展现一段历史中众多的人的活动和情感。
在史诗和小说中,故事的叙述方式和技巧、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以及描写、抒情和叙事的语言,本身都能成为美。但是,这些作品还有一种美,这就是历史感。在这些故事的叙述中,历史的纵深感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几十年上百年过去了,在几代人的生活中,有人出生了、成长了,有人衰老了、逝去了,人与人之间发生着种种爱恨情仇,争斗又和解,组织成家庭又分离,种种的交集和纠结,又与社会生活的变迁、时代的变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切人的命运和沧桑兴亡的故事,使人心生感慨。这种感觉本身就成为审美欣赏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感可以增加一物之美,或者使一寻常物成为审美的对象。我们去博物馆欣赏一些古物,赞赏这些古物之美。其实,这种美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本身造型之美,这种美没有时间因素,仅由于其形式本身而被人欣赏;一是物的时间积淀,即因其古而美。当然,两者之间也有联系:正是由于时间积淀,使一物从实用的对象变成被注视的对象,而艺术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被注视物,或要以成为被注视物为前提。
例如,青铜器原本是礼器或日用器皿,但历经几千年,早已成为被欣赏的对象。我们欣赏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如果它们精巧,就称许它们精巧;如果稚拙,就赞美它们稚拙。这时,青铜器成为艺术欣赏对象的原因,就与现代物成为艺术欣赏对象的理由颠倒了过来。今天我们因物的形式美而将它称为艺术品,而对古物,我们由于时间所造成的历史感而形成对它的注视,然后才注意到它的形式。时间本身就使它们成为被欣赏的对象。青铜器自身有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从殷商的早期到中晚期,再到周朝的早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造型有了很大的发展,工艺水平不断提高。但是,我们在欣赏这些青铜器的时候,并不是持一种进化的态度,认为工艺水平越高,就越喜欢。恰恰相反,我们常常持一种崇古的态度,认为商代的青铜器已经达到顶峰,此后的工艺越是精巧,越是被人们认为缺乏内在的精神性,而只注重外在的华美。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形式越精美,越不被重视。原因还是在于,其中有时间性在起作用。
类似的情况,我们在陶器和瓷器的欣赏中也可以看到。陶器本来也只是实用物品,有些陶器同时也是祭祀用具。最初的陶器,很少是纯粹为了观赏的目的制作出来的。陶器的造型、陶器上的纹饰和图样,原本也常具有自己的意味,包括传说的记载和信仰的体现,这些后来都成了欣赏的对象。这种欣赏,并不将原有的传说和信仰排除在外,而只是对它们实现观赏角度的转化。在中国古代,常有“前朝之圣物为后世之赏玩”的现象。信仰的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审美的意味就会凸显出来,但这不等于原有信仰因素消失,只是被当作背景而已。人们把玩古物,将前代视若神圣的器物当作艺术品来欣赏,而这种欣赏是多层次的,有神圣的历史感与对器物制作精美的结合和相互作用。这种多层次,恰恰是由于时间所造成的。
瓷器的情况与陶器相似却有所不同。瓷器出现相对较晚,其中积淀的原始信仰较少,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实用与赏玩相结合的器物。然而,在对瓷器的欣赏中,时间性仍然很重要。一件真正的元青花瓷器可以价值连城,而更精美的清代青花的价值却要低得多。这里面当然有物以稀为贵的因素,但也不仅如此。时间久远的瓷器,本身在瓷器制造史上有价值。这种史的价值也会被纳入欣赏者的考量之中,时间的意识会转化为无意识,影响对物的直接感受。
其实,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即为什么艺术品的真迹有价值而仿制品缺乏价值,也与这里所说的时间性有关。一幅创作于公元10世纪的画有极高的价值,而如果是创作于公元20世纪的仿作,则不管如何精美,也没有多少价值。为了保护敦煌洞窟里的壁画,敦煌研究院做了许多仿真的画作。运用现代技术,可以使这些仿作做得非常逼真。但是,观赏者不远千里想要去看的,还是真迹,尽管这会给文物保护带来极大的困难。意大利佛罗伦萨城有好几个仿真的《大卫像》立在城市不同的广场上,可以很方便地看到,但人们还是要去花钱买票,排队几个小时,去学院博物馆看真迹。面对视觉上完全相同的两个对象,人们要看的还是原作,原因还在于凝聚在原作上的历史感可以增添审美效果。
美学家们很喜欢谈论一个作伪的故事。有一位名叫米格伦(Han van Meegeren)的人伪造了一批画,宣称这是新发现的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Jan Vermeer)的画作,在他设法使评论界相信他的谎言,并使这些画赢得极高的赞誉,使许多博物馆都收藏了他的作品之后,却由于某种原因,申明并证明这是他自己所作。这一故事的结果是,大家都认为米格伦是骗子,法院也要治他的罪。这一故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同样是这些画,如果它们不是维米尔所作,而是一位叫米格伦的现代人所作,为什么就没有意义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历史感。维米尔的创作产生于17世纪,对他的画作的理解应基于当时的艺术水平、图像制作所采用的手法、色彩和造型的技术手段等来理解和欣赏。维米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作品如何继承前人、创造性地发展,又对后人产生影响,成为艺术史发展的重要一环。欣赏者不能抽掉这种历史感,以裸眼面对画作的纯形式。
王国维曾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在其中提出了一种古雅之美。他认为,古雅不像美和崇高那样,既存在于自然,也存在于艺术。这种古雅之美,仅存在于艺术之中。同时,他还认为,古雅之美不像康德所论之美那样是无功利的,古雅之美曾经有功利性,但观赏时不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待。他认为,照康德所讲,美是纯然在于形式的话,那么,古雅是第二种形式。更进一步,他分析道,古雅之美的创造,不像康德所讨论的艺术那样,是天才的作品,古雅之美的创造是经验性的。他的这些论述,均以康德的美学体系为基础,从而指出一种这种体系之外的美。①见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谢维扬、房鑫亮主编,胡逢祥分卷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11页。这是王国维的独创之处,他实际上是用生动的语言和例证,说明了这种累积在审美对象之上的历史感。
物因古而雅,因雅而为人们所欣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文学和其他主要艺术门类中,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复古运动和仿古的文艺实践。诗要学古人,学古人的文风,在诗中用典故,追寻古人的趣味;画要有古意,学前人的笔法和构图。以历史相号召,通过学古来实现文艺的改变或创新。仔细考察文学艺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种种具体的原因,但通过模仿古人,为艺术开辟新的道路,这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排除这些具体的原因,一个共同的根源,就在于人们普遍喜爱文艺作品之中的历史感。
历史感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正如王国维所分析的,它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之上。时间可以使非艺术成为艺术,例如青铜器和陶瓷器皿;可以使艺术品增加其价值,例如古代的书画作品,越古越有价值;可以由此提供艺术真品与仿造品具有不同价值的美学上的依据,肉眼看上去无分别之物,时间可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同样,时间也能使原本的俗变成雅,一首古代民间俗语歌词,时间久了就变得很雅,例如《诗经》中的一些俗艳的词就是如此;古代民间的器物,多年以后也可以变成上流社会的赏玩之物。当然,自然物也可具有历史感,老树的形态美是直观的,但对它的感受则常常来源于老树所见证的故事。大江大河的形态是美的,而江河上发生的历史事件,可加强这种感受。月亮是美的,而想到月亮也曾照耀古人,感受会增强。对自然物有历史感,是一种复杂的感受,是自然中渗透进了人文因素的结果。
五、新异感
与历史感相反,对新异的追求,也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新异是指在文学艺术中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不易见到的人、事、景,它们不是存在于过去的,而是新奇的或假想出来的。如果说,历史感将着眼点放在时间上的话,那么,新异感的着眼点放在空间上。这种空间感,不是指对自身所在空间的感受,而是对另一个空间的想象。
这种新异感,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的神话。希腊的神,居住在各地,或在山里,或在海上,普罗米修斯还被吊在东方高加索的山上。但是,神有一个共同的居所,那就是处于遥远的北方的奥林帕斯山。这对当时的希腊人来说是一个异域,他们将人世间许多不可能的现象,全放在这个遥远的地方。中国神话中的神也是这样。最早神人混杂,神常到下界游玩,也有人爬天梯到达上界。后来绝天地通,神就只是住在天上,或者有说法是住在昆仑山上了。北欧的神话,设想神与冰巨人的斗争。冰巨人在遥远的北极,神从温暖的南方来,神与冰巨人的战斗以神的失败告终,从海上又会出现新一代的神。所有的神话,都在讲神奇的故事,给人制造新异和奇幻感,也使人产生敬畏。这里面有美,有崇高,但是,一种并非来自天然而是制造出来的新异感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后来东西方的交通被打通后,异域就被设定在更加遥远的地方。《西游记》取材于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唐玄奘去印度学习和取经的故事,并将它神魔化。取经人一路向西,离开了大唐的地界后,就到处有妖怪。经过多重磨难,擒妖捉怪之后,才到达佛祖所在的西天。其中所写的西天,并不是真实的印度,而是一个佛教的净土,一个想象中的异域。与此相反,欧洲浪漫主义则以东方作为想象的对象,给作品带来了奇景、奇事、奇人,带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这个东方究竟是哪里,已经不再重要,只要带来奇幻感,可以向它倾注浪漫的激情即可。
艺术中的异域风情,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异域的视觉感受带给艺术创作丰富的源泉。从保罗·高更的塔希提岛,到毕加索笔下的非洲艺术,都带来新异感。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常常受到特别的欢迎。英国人喜欢来自苏格兰的舞蹈,希腊人欣赏马其顿的音乐,美国流行黑人的音乐,都有追求新异的心理在起作用。中国人也是如此,古代的中原人就喜欢胡乐,周边民族的音乐不断引进,成为中华民族音乐的一部分,为人们所习惯。这时,更远更新异的音乐歌舞借助人们对新异感的追求而持续引入,从而使中华民族的音乐越来越丰富。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仍在持续出现。少数民族的歌舞,受到普遍的欢迎。它们借助不断出现的新异感,进入到民族大家庭的艺术主流之中。
在当代文学和艺术中,更为突出地表现出这种新异感的,是童话和科幻文学与艺术。童话创作适应儿童追新的心理,营造另一个空间,讲述在那个空间中发生的神奇的事件。这些空间,可以是爱丽丝所漫游的奇境,是桃乐丝的OZ国,是哈利·波特经9站台到达的魔法学校。只要写得奇幻,营造另一个全新的空间,而又发现那个空间中所通行的逻辑,能为他们所理解,这样的作品就能让儿童喜欢。
科幻似乎是指向未来的,但实际上所有科幻的作品,都是基于现实的关于另一个空间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未来时,其实都是现在时,写的是当下的事。但是,这种对当下的事的叙述和表现,是设定在另一个空间中的。科幻文学和艺术,是成人的童话,并不是科学研究结论的展示。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很神奇,但人绝不可能像书中所写的那样从地球一边钻进去,从另一边出来。《流浪地球》说要许多台发动机让地球流浪,那很好看,但科学家们不要去较这个真,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阿凡达》讲另一个星球的故事,实际上是把在地球上发生的殖民侵略的历史换一个想象的空间再讲一遍。但是,这一切都有效,都能吸引人,原因多样,但关键的一点在于人有着对新异感的追求。这种新异感与其他的感受实现完美的混合,就造就了一部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新异感与历史感一样,主要在艺术中体现出来,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服装和时尚界,中国人用两个词来形容服装的特点,一是“典雅”,一是“洋气”。典雅更倾向于中式的、传统的、贵族趣味的审美,女性的旗袍、男性的中式正装,常常能给人典雅的感觉。王国维说“古雅”仅限于艺术,其实在像服装这样一些一般不被认为是艺术的产品中,也能体现。除此以外,家居设计也是如此,有典雅型的,上追汉唐明清,给人以历史感。与此不同,“洋气”则指西式的、新潮的。不仅服装有“洋气”的,房屋、家具,以及各种装饰,都有“洋气”的。“洋气”本来只是一种中性的描绘,说明一些服装和装饰的特点。但是,它被当成漂亮,受到一些人的热爱和追捧时,就成为一种特别的追求,背后仍是新异感在起作用。
结语:新感性与美
本文论述了关于美和艺术的五个范畴。前三个,即美、崇高和笑,可被称为美和审美的范畴,当然对艺术也适用。后两个,即历史感和新异感,是艺术的范畴,当然也在自然中有所反映和折射。
美与艺术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列举和分析的范畴外,还有许多。例如,许多教材中,都提到“悲剧性”和“喜剧性”。这两者都是复合的范畴,既是范畴,也是艺术样式。“悲剧性”作为美学范畴,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喜剧性”作为美学范畴,可与幽默和滑稽联系在一起。然而,作为艺术样式,它们又自成传统,有着自己的继承性并被赋予其他特点。以时间性来衡量,作为美学范畴,它们具有在时间中而又超越时间性的特点,而作为艺术样式,则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悲剧”和“喜剧”。除此以外,“丑”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一部分可包括进幽默和滑稽之中,例如戏剧中逗笑的丑角;但作为美学范畴的“丑”,则含义不同,成为“美”的反面,不具备逗笑的功能。
艺术的范畴多种多样,我们的列举不能穷尽。这些范畴的逻辑性又与历史性交叉,使我们很难将它们放在同一个逻辑平面上列举。这里所说的“历史感”与“新异感”,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说明两种突出的与艺术有关的范畴。当然,这绝不能包括丰富多彩的艺术审美的特点,而只是努力为艺术审美提供分类的指导原则。
范畴的多样性,实际上还是人的感性丰富性的反映。范畴是将这种丰富的感性进行分类,而感性的感受本身,是很难通过几个范畴而穷尽的。这正像一个连续的光谱具有无限的丰富性,而我们只能列出几种颜色来加以区分。这种区分一方面使这种丰富性得到表述,另一方面也使这种丰富性被粗暴地简化。范畴的研究也是如此,列出几个美学范畴,是对无限丰富的人的感受的表述,同时也是简化。然而,如果我们通过这种简化了的表述,能看到其丰富性,使这种范畴研究成为捕获人的丰富感性的有力工具,那也就起到了它所能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