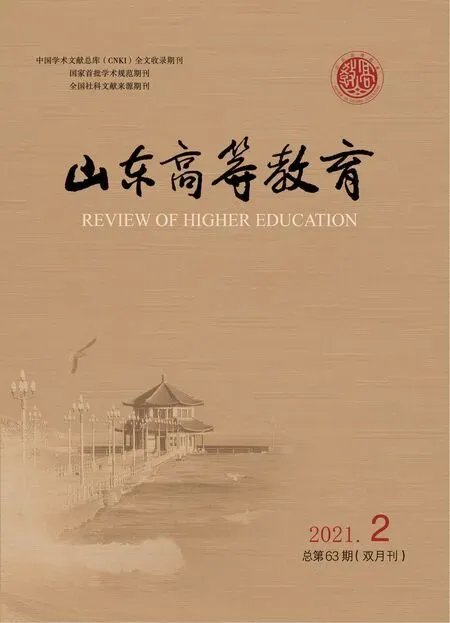罗伯特·赫钦斯与芝加哥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
刘爱生,金明飞
(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金华321000)
罗伯特·M·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家。1929年,他年仅30岁就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直到1945年卸任。作为一个任职16年的校长,赫钦斯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美国大学,建构他心目中完美的大学。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如此盛赞他:“赫钦斯是真正力图从根本上变革他学校和高等教育的最后一位大学校长。”[1]21在此将探讨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
一、赫钦斯上任前的芝加哥大学治理结构
自北美第一所殖民地学院——哈佛学院建立起,就确立起“学术法人—董事会”的基本治理结构。[2]3到1890年芝加哥大学建立时,随着研究理念的确立和办学规模的扩张,美国大学董事会的权力不断下放,董事会直接干预学术事务的事情虽然偶尔还能见到,但越来越引起教师的警觉与抵触;以大学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得到了扩充,表现为行政架构的膨胀;同时,大学教师在学术事务上的权力逐渐得到认可,开始在教师聘任、课程设置、学术标准制定等方面不断诉求权力。
具体到芝加哥大学的治理结构,首先,董事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负责筹集资金、遴选校长及监督大学运作等,并不过多干涉学术事务。其次,学校成立了由校长担任主席,包括院长以及其他行政人员加入的大学理事会(University Council),主要负责学校行政事务。最后,学校还成立了系主任和教授组成的大学评议会(University Senate),负责所有学术事务。而且,为了进一步提升教授在大学治理中的权力,每一个学系都成立了教授委员会。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治理结构,但其背后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底部过于沉重。在这种组织架构下,芝加哥大学的核心单位是系(当时多达26个系),而非学院(当时设有5个学院)。其中,系主任被赋予了很大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作为教师任命和财务的唯一负责人直接与校长沟通;各学系内的教授也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与此对应,院长行政上仅负责学生事务,无权干预学术事务。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院院长昌西·鲍彻(Chauncey Boucher)在1929年抱怨说,作为院长他没有财政预算权、教师任命权和课程管理权,不仅很难更改系主任的课程计划,甚至无权干涉课程安排。[3]121
底部沉重的特征给芝加哥大学遗留了一个传统:为了促进学校整体进步,它需要强硬和固执己见的人来当校长,必要时校长需公然插手学术事务、反抗个别院系的党派主义。否则,学校会因为无序、散乱而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之中。哈珀作为创始校长在管理过程中无疑是强硬、果敢,可以凭借个人巨大的影响力平衡学校顶层与基层的张力。然而,哈珀之后的三位继任者:哈里·贾德森(Harry Pratt Judson)、欧内斯特·伯顿(Ernest Pewitt Burton)以及查尔斯·梅森(Charles Max Mason),或由于公信力不足,或由于年事已高,或由于性情怯懦,都无法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到1929年赫钦斯上任前,芝加哥大学治理结构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效和失衡,表现为校长办公室权力弱化,教师权力过大,学系各自为政、自成一体。
二、赫钦斯上任后芝加哥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
借着20世纪盛行的科学管理理论,赫钦斯上任后委托伦纳德·艾尔斯(Leonard Ayres)组成调查组调查学校治理状况,发现:一是学校机构重叠、臃肿,直接向校长办公室汇报的部门超过50个,但工商管理原则表明,个人有效监管的部门上限是十几个。二是行政效率低下,学系权力缺乏约束。校长办公室因要与各系商议后才能决策,给行政造成了巨大负担,以致无法及时、有效决策。且这种体系下校长办公室经常无暇面面俱到,造成的权力“空档”给予了学系几乎不受约束的自主权。[4]31三是预算体系老化、粗放。预算是由系里一系列临时估算组成,但系主任对财政无精确意识,导致学校既不能自上而下统筹预算,又不能控制财政支出。
(一)调整院系结构,精简行政管理部门
汇总上述意见后,1930年10月22日赫钦斯向评议会提交的大刀阔斧改革计划被迅速通过,并于11月13日获得董事会批准。1930年的改革使赫钦斯赋予了芝加哥大学一个新的章程和治理结构,具体包括:取消单独设立的神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废除唯一一个名为艺术文学与科学的研究院,这个此前几乎容纳所有学系的庞大、混乱的二级组织。将所有学系按照学科逻辑分别纳入新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物理科学四个学部,也就是把之前的研究院一分为四,但新成立的学部对此前拥有自主权的学系有着实质管理权。此外,保留之前的初级学院,不过改变其以往由研究生院中学系各自直接管理的方式,设置成一个独立管辖主体。之后,研究生院中的学系不再是学院的直接管理者,改由院长总辖行政与教育事务,学部仅保留学院的学位授予权,以及提供教育和课程的权力。简而言之,改革是要解决组织无序及治理结构中管理混乱问题,为此新设立五个并行的二级管理主体(学校外的五个专业学院仍保留自治权),由他们对各自所属的基层组织进行管理,从而形成秩序清晰、等级明确的组织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改革并未采取当时美国大学治理中以单一学科门类划分院系的流行做法,这其中有咨询相关意见的成效;也有赫钦斯“芝大的研究和整体规划应该突破单一学科蕃篱的跨学科理念”。[5]92-93
35个学系归入学部后,行政部门和行政方式也随之进行了变革。为提高行政效率,计划改变以往校长直接和系主任商议的方式,学系由各自归属的学部进行统一管理。学部层面,撤消之前学系自立、功能重叠的行政部门,将人事、预算等上移到学部中统一管理。如赫钦斯上任前,学校无财政管理中间结构,无论大小,每笔开支由校长办公室批准,单预算部门校长就要监管73个,改革后则由学部部长统一编制预算。为集中管理、分担校长压力,学校层面新设置教导主任(Dean of Students)和财政审计长两个职位,分别替代之前院系管理学生事务的办公室或个人全面负责学生事务,以及负责学校的财务运营。
经过重构之后,组织结构上改变了以往组织无序、繁杂缺陷,优化了组织设计、分工与协调性,使得学校组织部门得到了有效精简,校长直属的预算和其他事项办公室从80个锐减到14个,其中主要涉及兼管教师事务的副校长、财政审计长、教导主任、学部部长、学院与专业学院及东方研究院院长、图书馆和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社长等。行政管理上,改变了以往制度设计不合理引发的学校无法从整体上统一规划、有效监管、学系各自为政等现象,造成的管理错位、沟通不畅、行政效率低下结果。简而言之,精简部门,对行政事务实施专项负责、分层管理,大大优化了行政系统,提高了行政效率。
(二)削弱学系权力,强化院长和校长权力
组织重构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赫钦斯上任前,芝大底部沉重集中表现在由明星教授管理的学系拥有几乎不受学校控制的独立权。以政治系为例,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自1923年担任系主任起,全国性影响力使他在学校具有很高话语权,1924年他又从劳拉·斯皮尔曼基金会(Laura Spelman Foundation)获得研究基金,所以有梅里亚姆坐镇的政治系基本不受校长及政策影响而实行部门自治。对此结果,赫钦斯批评哈珀给予系主任过多行政权力,首先削弱了学系自治权和系主任的权力。改革纠正以往学系缺乏直接领导的问题,由学部具体管理。取消之前系主任直接与校长商议行政特权,收缩系主任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的行政权力,及部分教育上的学术管理权,由学部部长对其进行直接领导。
针对积蓄已久的院长权力几近断层弊病,改革后作为学部事务总理者,系主任的顶头上司,部长的权力得到了实质性加强,成为自主管理学部的第一负责人。学部部长从资历较深的教师中选择,由校长任命,相较之前仅有管理学生事务的权限,改革后部长负责编制综合预算、教师晋升提名与行政人员任命,享有资源分配和课程监管权力,可自行处理向校长总汇报前的诸项事宜。
1930年的计划没有明确具体变动校长权力,但改革使校长办公室从琐碎事务中解放出来,多数转移到部长与系主任层面,确保校长从总体上对学校实施全面、有效领导。而且部长一众在向下管理具体事务同时需要向上汇报给校长,使校长重新掌握了最高决策权。另外,学部部长由校长任命对校长负责,改革使系主任的多数权力转移到部长这一行政人员手中,实质上与掌握在校长手中并无差异。所以治理结构改革使校长获得了最终控制力,重新收拢了权力,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者。
赫钦斯上任后进行的治理结构改革对芝大的治理和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延续至今。改革使学校形成了校长-部长/院长-系主任的行政管理链条,纠正了之前院长权力断层产生的治理缺陷。从内容上看,改革是以瓜分学系和系主任权力,充实部长和校长权力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试图扭转底部沉重,提高治理效率。从结果上看,改革是使逐渐形成的学者自治向以官僚形式组织起的强有力中央管理体制转变,抑制了权力无序造成的混乱,提高了整体的有序性及行政效率。然而,改革使部长权力得到了空前加强,从整体上强化了学校的行政权力,治理实践中,权力实际上被掌握在校长和部长几个少数人手中,尤其在与教师密切相关的晋升与终身职位聘任方面。此后近十年中,芝大的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与校长制相仿的联合院长制,少数人的集权不免在治理过程中引起不满和摩擦。
三、治理结构改革中的权力博弈
(一)博弈的起因
赫钦斯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拉开序幕的。1929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短短几年,美国的失业率从1929年的3.2%飙升至1933年的25%;[6]98同时,芝加哥大学的捐赠急剧减少,从1929年的1450万陡降至1933年的200万美元。学校一半以上的教师聘期合同只签一年,平均工资和奖金下降了33.3%。[7]41-43大萧条产生的惶恐及生存危机一开始转移了芝加哥大学教师对治理结构改革的注意力。之后,随着美国经济好转,教师一方猛然意识到:赫钦斯的治理结构改革的实质是以牺牲学者自治,教授日渐积累的权力为代价的。
此外,赫钦斯认为,大学校长应是致力解决教育问题的学术型校长,应该有直面学术事务的权力,不只是作为章程赋予的监督者角色。在他看来,做决策只是校长的基本权力和基本职能,根本职能是澄清、定义大学目的,管理权限当包括与达成目的相关的所有事项(如课程一般不由校长负责,但它是实现大学目的手段,应归校长管)。[8]一开始,芝加哥大学教师对刚上任的赫钦斯的管理理念并不了解,但随着了解深入,教师十分抵触赫钦斯的治理结构改革。
(二)博弈的过程
1937年,赫钦斯私下授意阿德勒(Mortimer J.Adler)等人成立自由学科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Liberal Arts)探讨学校的课程,确立自由七艺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但教授代表的反对者认为,赫钦斯的举动表明他想绕开评议会,独自决定课程政策。所以,反对者控诉赫钦斯把个人理念凌驾大学管理之上,对侵犯他们自治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传统抗议。经济学家哈利·D·吉登斯(Harry D.Gideonse)表示:赫钦斯正在实施一种“固定且不可侵犯”的教育项目,且赫钦斯的观点若得以实施,学校将偏离科学研究前沿,走向徒劳的形而上学探索。[9]6-23批评者还认为:“赫钦斯用他本科教育改革上的行为,证明了他喜欢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而且他还乐于抨击唯一有权监管研究生教育的院系。”[10]284言下之意,赫钦斯没有权力管理这些事务。
为了捍卫自身利益,1938年出席评议会的76人以42对34票通过决议,请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针对以赫钦斯为首的行政权力过大、过度控制晋升等问题对芝大展开调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芝加哥分会在在吉登斯主持下展开调查。学术终身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Academic Tenure)调查发现,60%的教职工是一年任期,只有32%的教师拥有终身教职,而10年前这一比例为48%。调查指出,有限合同制比例增加“将会导致大学成为校长政策的工具,不仅会降低教师责任感,还会使言论自由感下降。”[11]178就权力问题,调查表明,校长的最终任命权增强了其控制力,不管他是否选择行使控制权。而校长如果在政策处于商议期间私自展开行动,教育政策的辩论自由也会受到威胁。因此,调查报告建议:增加终身职位比例,确保教育决策权力更加平衡;维护学术人员塑造学术组织的自主权。
赫钦斯于1942年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16页的报告,批评掌握学术权力的教授、评议会组织在对大学实施无效管理。其中特殊利益小团体可以否定任何超越惯例的举措,成员漠不关心只出席威胁自身利益的会议,如近200名正教授的评议会经常只有三四十人出席。[12]177报告指出,评议会宣称必须由其对学术权力负责,但在不违反学术生活这一神圣规矩前提下,教授是一群既不能开除又不能指责的人,谈论这样一群人的责任是很荒谬的。再则,评议会只代表教授,不能完全表达全体教师的想法,况且美国教授的背景和职责,没有训练他们能够管好一所大学事务,为整个学校利益着想,他们被选择是基于成为专业领域的专家,而特殊领域专家的投票不一定意味着是对整个机构政策的最佳判断。大学的巨大规模和日益狭窄的专业分工,使教授几乎不可能知道他所在学部、大学,甚至某些情况下所在系里发生的一切。[13]319赫钦斯建议,应该扩大评议会来源,从全体助理教授至正教授中选出50名成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再选出7名成员组成评议会委员会,要求评议会对所有提交给它的事务都清楚明了的进行处理。[14]119
为了推翻给他造成巨大掣肘的教授寡头统治,赋予校长学术权力,报告提出了两种极端且相左的治理结构设想。一是“放弃责任和效率作为大学的标准”,所有事项将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校长像德国大学校长一样,无权力和教育功能。[15]318二是“巨大权力和平衡权力的重大责任”。据此,校长任期为7年,在学术和行政上有绝对的权力,并直接承担后果,评议会只需选出5名委员充当校长顾问,其余成员仅有对校长是否信任的投票权,当不信任票两次达到三分之二时校长必须辞职,当5%教职工要求罢免校长时,董事会也必须审查。也就是说校长主政期间必须建立在信任投票基础上,而校长及其决策、推行的政策,要么支持,要么推翻。[16]117-118
围绕学术权力博弈的十几年中,反对者抨击赫钦斯强行推行个人教育理念、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扼杀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多。[17]183更有极端者在接受公开采访时谴责赫钦斯的无效领导:学校许多院系在学术知识上停滞不前,就是缺少强有力的校长领导。[18]285对赫钦斯的领导风格和削弱学系权力的行为,以罗纳德·克雷恩(Ronald Crane)教授为首的六人小组先是以信件的形式私下质疑赫钦斯。之后,1944年教授发起了群体反抗运动,评议会以94∶42赞成通过一份《芝加哥大学校情备忘录》,由91位正教授署名提交给董事会(其中不乏赫钦斯之前的支持者),要求捍卫学术权力和学术自由。反对者表示,赫钦斯正在颠覆我们社会借以存在的整个价值尺度,要求继续由学术人员控制、根据学科门类安排学术组织,同时要求董事会向评议会和教师保证大学不会实施任何一种特定的理念。[19]128
为平息纷争,1944年6月8日赫钦斯发表了解释声明,并于1944年7月20日发表《大学的组织和目的》(The Organization and Purpose of the University:An Address by Robert M.Hutchins to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he Summer Quarter)再次调解。即使备忘录事件中教授表示并不是对校长信任产生了问题,董事会也声明肯定赫钦斯校长,但赫钦斯愤愤不平且极度气馁,他不明白为什么在校长任职期间,评议会中反对者日渐增多,指责他的声明令教师沮丧、没有促进科学研究、在任命上与教师的合作度不够。于是1944年秋赫钦斯向董事会提出辞职,虽然被董事会拒绝,但赫钦斯的辞职基本上为芝大十几年的权力博弈画上了终止符。
(三)博弈的结果
在学术权力博弈过程中,教授代表的反对者一方面利用自身影响力“打口水仗”,另一方面积极联合行动,捍卫权力和利益。针对赫钦斯频频表现出的逾权行为,教授通过评议会决议,成立大学政策委员会(The Senate Committee on University Policy),作为评议会辖下日常非正式组织,由各学部选出两名代表,专业学院选出一名代表组成,负责审议学术事务相关的政策,保护教授的学术决策权。正如委员会教授表示,赫钦斯私自授意成立自由学科委员会是属于教育政策上的问题,应由他们而不是校长管理,并且宣示:以后赫钦斯在学术政策方面的提议,教师的推荐任命,都必须要得到相关学部与委员会中的教授同意。[20]162
当然,赫钦斯虽然没有按照自己的理想重构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和治理方式,但是他的努力直接促成了评议会改革,这是赫钦斯担任校长期间为数不多的一次“温和”胜利。1944年学校对评议会的人员构成和运作方式进行了改革。首先,降低评议会的入会等级,期满3年以上的全职教师都可以入选评议会。由评议会选出一个40人理事会,在学术决策中与校长平权制衡。再由理事会选出7人执行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与校长沟通及建议。其次,为修正评议会召开无序,职责不明缺陷,理事会要求至少每个季度举行一次会议,执行委员会每两周定期与行政人员接洽。评议会改革推动了民主治理进程,建立了比之前有效的信息交流手段,但成员的扩大也使治理更加复杂。
四、结语与思考
回顾赫钦斯在芝大的治理结构改革,可以发现,他削弱学系权力、强化学院治理以及巩固校长的最高决策权,符合当下提倡的共同治理理念,具有现代性和前瞻性。但是,他的改革并未得到大学教师的认同与支持。总体上来看,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失败的。现任芝加哥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博耶(John W.Boyer)对此评价道:赫钦斯用他自己的失败生动描绘出,一旦院系和学术人员拥有强大的权力和自豪感,就像芝加哥大学1929年之前一样,现代大学是不能由校长个人完全领导、控制的,即使他才华横溢。[21]
回顾赫钦斯失败的治理结构改革,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以下几点认知:第一,一流大学教师对学术权力的珍视。学术权力一般指学术人员直接管理和控制学术事务、学术活动的权力,从而彰显学术人员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师看来,赫钦斯反复倡导的治理改革违背了他们秉承的信念。正如史密斯(T.V.Smith)代表的反对人员心声:赫钦斯自作主张,试图行使章程规定属于教师的职能,且往往采取高压手段推进。[22]232故以教授为代表的反对者为了保护被他们视为的“天职”权利,不断展开反击。学术人员对学术权力的珍视,还由学术的实践逻辑引起。布鲁贝克(John Seiler Brubacher)认为:“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理解它的复杂性。”[23]31如上述一致,他们批评赫钦斯不了解研究,缺乏教学实践经验,认为在这些领域中赫钦斯没有资格领导他们。而且他们反感赫钦斯把自身放在学术权威中心,定义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命令他们应该如何做,他们认为赫钦斯还侵犯了他们的学术自由。
第二,大学是一个惰性极强的组织。组织惰性(Organizational Inertia)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有维持传统的保守性和抵抗变革的惰性,组织惰性是阻碍组织变革和治理创新不可忽视的对象。[24]在这种组织惰性下,学术人员倾向继续已有的组织生活、治理方式;他们形成的治理信念和对治理传统的维护,在权力博弈中转化为抵抗变革的行动。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对此就指出,高等教育中斗争的结果和变化的范围取决于稳定的代理人和变化的代理人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由于一些专家集团分享着权力,在违背这些专家意愿的情况下改变他们的组织形式是非常困难的。[25]242显然,赫钦斯的治理结构改革的失败跟大学组织的惰性紧密相关。事实上,他在治理结构改革过程中就经常抱怨:“教员的保守惰性使他们对改革怀有一种尽人皆知的敌意,并且只顾自己利益。”[26]220
其三,改革成功与否与大学校长的领导方式有关。科恩(Michael D.Cohen)和马奇(James G.March)指出,在变革和领导过程中,对大学“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校长领导需要审慎对待大学治理的模糊性,更要善于使用说服这项关键的非正式权力。[27]224-228显然,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治理结构改革过程中,缺乏相关的领导技巧。一方面,在改革中,同事评价他发起的改革像“打游击”一样让人摸不着头绪,并且一贯依靠斥责的方式推动进展。[28]489-490这对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尤其是芝大)复杂的管理、官僚权力与社团权力相互交错的现象而言,校长个人片面化主张不但难以推行,甚至让人反感。另一方面,赫钦斯一帆风顺的行政履历增强了他的果敢和自信,但没有让他领悟到说服、战略协商的效用和审时度势的耐心。赫钦斯虽有雄辩的口才,不过实际治校中既难以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善处理小范围的冲突。如克尔(Clark Kerr)所言,为调解现代大学复杂的关系、平衡各方利益,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位坚忍的调解者。之于芝大的改革,游说和耐心恰恰是校长应对这所复杂而保守的庞大机构所必须要的领导策略,因为其中除了根深蒂固的部门利益之外,还聚集着一些自负、任性的著名资深学者,他们唯恐上级要求自己做出改变。故而董事会主席斯威夫特(Harold H.Swift)表示赫钦斯虽然抓住了权力,却没有理解权力的实质。赫钦斯校长表现出的一系列领导缺陷,恰恰与美国学者对大学校长的相关研究结果吻合:校长在致力改革时,其领导方式与改革成败有着直接关系。[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