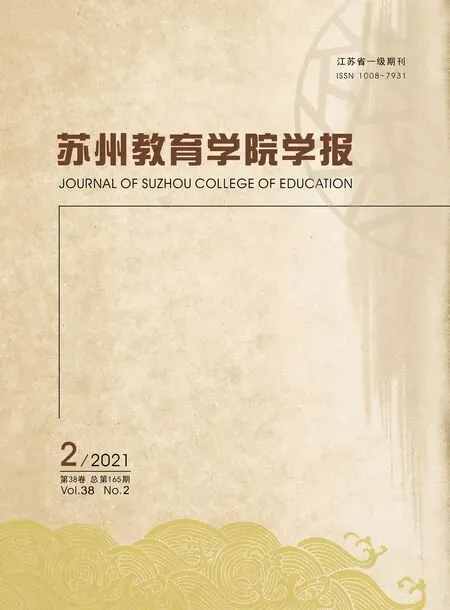余墨:关于汪曾祺小说
陈学勇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我之前写过一篇《一个“汪粉”的姑妄言之》,后在汪曾祺诞生百年之际又作了一篇《年轻小说家汪曾祺》,①以上两文参见陈老萌:《一个“汪粉”的姑妄言之》,《文汇报》2019年3月12日,第10版;陈学勇:《年轻小说家汪曾祺》,《文汇报》2020年12月16日,第11版。仍意犹未尽,不妨再来说说,算是前两篇的余墨。
“四人帮”垮台后,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际,《受戒》悄然面世,反响意外热烈,不啻空谷足音,它为久受压抑的人性奏了一曲甜美颂歌,大家恍然醒悟,原来自己是多么期待久违数十年的人性主题作品,《受戒》作者顿时名满天下。我曾设想,若那时汪曾祺发表在先的小说是“散文化”的《故里杂记》《故里三陈》《故乡人》,而与“故里”写法不同、仍循通常技法路子的《受戒》晚几年才发表—那时人性已然是热门主题,岂不错过了空谷足音的时机,作者还能如今日这般名满天下么?怕不好说,时机错过就错过了。由五个短章组合的《塞下人物记》,写法类似《故里三陈》,正是发表在《受戒》之前,就没有什么反响,似略可反证。
发表《塞下人物记》时,汪曾祺名气还不大,人微作品轻。《受戒》则以主题得风气之先—当时人性题材如初春冻土下的胚芽,欲破土未破土—它率先冒出绿芽,虽为新人新作,毕竟令人眼前一亮,不容忽视。《受戒》理所当然未能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汪曾祺的作品《大淖纪事》在后一年度获奖,则是一个有点“斗争”意味的故事。《受戒》落选,今日读者或非解,放在当年,实意料中事。春暖乍寒,评奖诸公依然心存余悸。汪曾祺追述:“发表这样的作品是需要勇气的。”(《关于〈受戒〉》)[1]147勇气赢来收获,它赢得喜爱的意义远超过一个奖项。汪曾祺由此备受鼓舞,为他放手创作注入了激情和动力。大振的名声,为汪曾祺倡导散文化小说鸣锣开道,他自信地说:“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样子写小说了。”(《谈风格》)[1]312汪曾祺重返了自我,那个数十年前的最后一位京派作家—沈从文—的门生。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他的“得意高足”,汪曾祺一再这么自诩。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八九十年代的汪曾祺,前后各领风骚。汪曾祺享盛誉以来,人们谈了很多他与沈从文的师承,多到连他自己都忍不住私下申辩:“我和沈先生的师承关系是有些被夸大了。”(《致解志熙》)[2]相比之下,师生风姿的差异说得就不够了。不细品汪曾祺对老师的出蓝之处,是不足以见出汪曾祺于文学史的贡献的;当然,看不到汪曾祺有继承又有舍弃,如他舍弃了老师的创作态度,同样不足以理解才情尤甚的汪曾祺何以没能站到巨人的肩上,成就更上一层。
汪曾祺与沈从文原本两种人生。汪曾祺生在儒商士绅家庭,沈从文的父亲则是一介武夫。汪曾祺是家里的“惯宝宝”,享尽宠爱,性情任性而懦弱,生活在水乡却不会游水;沈从文自幼失怙,顽皮不驯,一度投身行伍,亲历杀人如麻的场景。加之苏北之于湘西,乡风悬殊,一处笃实,一处彪悍。步入文坛,汪曾祺所过从者多为基层文化从业者,沈从文则闯入文化精英圈子,圈内不乏政治氛围,两人视野当然大不一样。沈从文满眼人间污浊,笔墨介入社会,以期进步、完善(终不得完善)。他致信徐志摩:“胡先生好像有到南京去做官的意思,那就真糟糕。他是应当来领导一个同国民党那种政策相反的主张,不能受人家的骗局的。你(注:应为许)多对政府行为主张疑惑的人,在某一情形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小兵。”[3]无疑沈从文便是小兵之一员。汪曾祺则坦陈:“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随遇而安》)[4]290汪曾祺与世无争,洁身自好,奉了儒家信条,既然不在“达”位,则退而独善其身,于社会种种,见“怪”不怪,随遇而安。他甚至说,人“要能适应、习惯、凑合”环境。(《牙疼—旧病杂忆之三》)[5]19身为小说家,沈从文不辞责任,直面社会,不平则鸣;汪曾祺则醉心个人情感表达,往往遣兴述怀。人生路上,一位执著进取,一位随遇而安。
就说师承,汪曾祺随性取舍,见仁不见智,不免有所偏向。他眼中的沈从文是“真正淡泊的作家”(《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1]491,许多读者至今仍有此错觉,“淡泊”障目,视一叶不见其余。其实,某个方面,某种程度,作家(非后来的学者)沈从文是好斗的,文坛著名的京派、海派纷争即由沈从文引起。他确有淡泊的一面,晚年不得已耳,属人生的某一阶段、某一侧面。少年汪曾祺是落拓不羁的名士作派,乡下人沈从文永远“名士”不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迫于社会背景,汪曾祺的名士派头不得不收敛,纵然骨子里“名士”气质犹在,反倒轮着沈从文不得不随遇而安了。改革开放后,沈从文无意重返文坛,一头扎进文物研究。汪曾祺梅开二度(其实三度,但第二次开得不算灿烂),为人为文,均不甘随波逐流,加上年岁阅历,人情练达,他渐渐地随心所写,得心应手,绚烂后趋于平淡。
再看小说观念,师生俩“泾是泾,渭是渭”。沈从文藉小说“载道”,汪曾祺用小说来“言志”,都是“抒情的人道主义者”[1]428,实同归而殊途。沈从文愤激社会痼疾,明里叫阵:“作者能于作品中浸透人生崇高理想,与求真的勇敢批评精神,自可望将真正的时代变动与历史得失,好好加以表现,并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迎接五四》)①新发现沈从文佚文《迎接五四》,载《大国民报》1943年5月5日第11期第1版。转引自陈建军:《〈大国民报〉刊沈从文佚文及其它》,《新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第54—59页。汪曾祺像打太极,回避正面交锋,不作拷问,不去讨伐,温暖地陶冶民众。他晚期涉及“文革”的文章,于政治无所深究。关于笔下人物,沈从文写人旨在揭示社会;汪曾祺的兴趣止乎人自身,有些篇章纯粹“寄托个人小小的哀乐”(《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1]244。尤其是短小篇什,难说不带一点自赏、自娱的心态。汪曾祺觉得委屈:“偏偏有人(而且不少人)把我的作品算在悠闲文学一类里。”(《老年的爱憎》)[5]189聪慧的他不应想不到,归类未必准确乃事出有因。略见骨力的几篇算例外,兔子急了还咬人,当然与雄狮张口大不一样。
至于小说艺术,沈从文因循白话小说叙述传统,汪曾祺的散文化作品则逾越传统,“记录”生活,还故事给日常。沈从文近乎说书,把思考放进故事;汪曾祺全然聊天,从生活抽绎感悟。有的小说家思维大于形象,汪曾祺形象大于思维。他不刻意组织情节,而着意体悟生活意蕴,持这样的小说观念,倡导散文化再顺理成章不过。汪曾祺的小说已然以散文化开宗立派,正如他自述的“不开风气不为师”(《七十书怀》)[4]218。汪曾祺之所以名声斐然,正是不囿乃师规范,另辟了蹊径。苛求起来,沈从文的文体特色不及汪曾祺的鲜明,曾多方尝试小说文体,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风貌出现过现代派迹象,然终究未得如愿自成一格。庆幸的是,汪曾祺完成了最为中国化的成熟的“新”小说文体,他不无自得地宣称:“我大概是一个文体家。”(《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1]490他想过“衰年变法”,早在1940年代末,参加“四野”工作团随军南下时,就打算“写一点刚劲的作品”(《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4]108,却没有兑现。幸而衰年也终于未变,读者不要再多出一个巴金、多出一个老舍,只要唯一的汪曾祺。
关于小说散文化的实践,汪曾祺奉献了《故里三陈》等一批“三”题系列小说①此类组合作品有些或不止三篇,有些虽三篇却题目未明标三字。,缺少这批作品,“小说散文化”难免落空。这么说,并非低估《受戒》《大淖纪事》。单个作品来说,这两篇诚然是汪氏最具成就的小说。而论汪曾祺整体创作,论他为“小说散文化”的成功尝试,这两篇毕竟够不上典型、充分。脍炙人口的《陈小手》《李三》《职业》,才是小说文体中的独到建树。难怪汪曾祺自己更看重《职业》,专为它写了不避孤芳的《〈职业〉自赏》。“五四”新文学突破了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沈从文大体仍是沿续“五四”新传统,汪曾祺则又突破了“五四”伊始的小说新传统,借鉴《世说新语》、笔记小说,貌似复古,实为创新,文学史上复古运动从来意在破旧出新。“小说散文化”给中国现代小说注入了新的血液,这是汪曾祺对小说史的独到的贡献。
各类文学体裁中,散文最讲究文字功力,最显示语言魅力。散文化小说自然格外讲究语言,追求语言美感,汪曾祺也比沈从文更加自觉。他甚至偏激地说:“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小说的散文化》)[1]391小说家鲜有他这般用心研究过语言技巧。沈从文的语言清新,汪曾祺在清新里融入文人气和烟火味,两种几乎不相及的气和味复合为别致的语言美。汪曾祺的小说,写的事俗、人俗(偶有雅人),但作者不俗。俗人俗事,写来满纸飘逸、水灵。假如将沈、汪小说混入对方集子,单凭语言,不难一眼认出它姓沈还是姓汪。汪的文字比沈细腻,尤具生活本色,特别是白描,用得出神入化,极其琐屑的景或物和寻常对话,他描写得有情有致。譬如写一块空地:
有时跑过来一条瘦狗,匆匆忙忙,不知道要赶到哪里去干什么。忽然又停下来,竖起耳朵,好像听见了什么。停了一会,又低了脑袋匆匆忙忙地走了。(《辜家豆腐店的女儿》)[6]319-320
什么人都没有出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却不能说它什么意蕴都没有。汪曾祺这等语言功夫,再凭他的才情,汪氏小说的文字魅力堪比当代文学史上若干大家。回眸汪曾祺身处的文学年代,他是一座奇峰。出了个汪曾祺,未必增添当代文学史的壮观伟大,但一定使之丰富多彩。汪曾祺的小说虽无法成为文坛主流,但将是久远的。人性是久远的,艺术美是久远的。
汪曾祺自谦:“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门前流水尚能西—〈晚翠文谈〉自序》)[1]378如此清醒,难能可贵。汪曾祺本不抱登临文学高峰的壮志,也欠大家的气质。他对自己从不设多高的创作目标,犹如跳水运动员,选了一组难度不大、满分不多的竞赛动作。作家应有这自由,评论家不能,也无法强制他。
汪曾祺百年冥寿前后,报刊登出大量关于他和他作品的文章。纪念先贤的日子,偏多溢美为人之常情。只是某大报的溢美有嫌离谱,作者又是知名学者,网络传播很快很广,极易误导读者。譬如,“他(汪曾祺)把文学从虚假的、先验的观念为主的文学回到自身”,还说“他拯救了我们的汉语”。[7]汪曾祺再度创作时,“伤痕文学”不仅揭批政治,也彻底否定了文学的瞒与骗,文学虚假早已被批成过街老鼠,何需汪曾祺来力挽狂澜。至于“拯救”云云,危言耸听。汪曾祺哪里有这巨大能量,更不必说汉语远未到需要拯救的境地。
传闻汪曾祺创作小说一挥而就,无需修改。以汪氏过人才气,有些短小篇幅作品许能如此;略长的,哪怕才气再盛也难做到。中国多有一挥而就的美谈,那是形容,是夸张,和说“倒背如流”一样。至于虚构的小说,总得修改修改。不作修改并不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情,尽管他十分注重腹稿,但落笔后修改也是常有的事。篇末汪氏明确标注修改的就有多篇,取晚年作品为证,如《塞下人物记》《岁寒三友》《日规》《昙花、鹤和鬼火》;更有篇尾注明已改至六稿的,如《寂寞和温暖》。有的干脆重写,最为自赏的《职业》改写了四次。《徙》未标注修改,可是他有文章记述,开篇第一行原先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放下稿纸出去转了转,回家就改成“很多歌消失了”(《说短—与友人书》)[1]193。这句改得好,原先那句像人家笔下的,改了才是汪曾祺的文字。
百密一疏,创作还是要改的。汪曾祺就“疏”过,甚至疏在晚年作品里。《薛大娘》写活了一个不受世俗礼法束缚、敢于主动追求异性的小镇妇女。故事最后写道:“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6]337点题形象而显豁,汪氏小说少有这样显豁的点题。不意后面赘上一小段:“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6]337汪曾祺一贯主张“主题最好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1]271,他小说的主题常常耐人寻味,这一段竟然流于蛇足。一眼看得出其主题,作者自己又出面絮叨,岂不大煞风景。汪曾祺这样的作家,真失误得有点儿低级,难以置信。印象里添了蛇足的不止这一篇,更叫人匪夷所思。这里较真,初衷无非想提醒,切勿由不实传闻误导了年轻作者迷信才气不屑修改,创作正道还是精益求精。拉拉杂杂,最后一小段的吹毛求疵,聊为余墨之余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