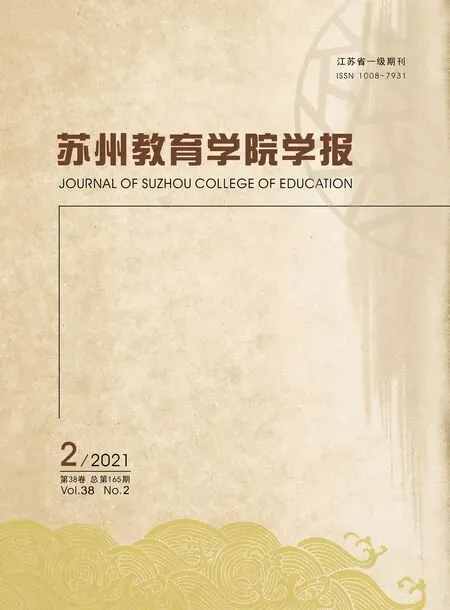非文学的民间文学
陈勤建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以我观之,百余年来学界流行称谓的“民间文学”,是文学,又非文学。 这似乎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论题,而这一矛盾正是民间文学的特质所在。
1906年3月19日,梅光迪先生在给好友胡适先生的回信中,论及新文学、白话文学时说到:“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tc)入手。”[1]1921年1月,胡愈之先生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论民间文学》一文,他认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德文的Volkskund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普通的文学著作,都是从个人创作出来的,每一种著作,都有一个作家。民间文学可是不然,创作绝不是甲,也不是乙,乃是民族的全体……第二民间文学是口述的文学(Oral Literature),不是书本的文学(Book Literature)。书本的文学是固定的,作品完成之后,便难变易。民间文学可是不然;因为故事歌谣的流行,全仗口头的传述,所以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2]
上述学界前辈所阐述的民间文学的学识,是相对于作家的书面文学而作出的区分,对认知文学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具有开创之功绩。我国古代并没有“民间文学”的概念,一百多年前,学界前辈所叙说的民间文学话语,主要是从“大略相同”的英文“Folklore”转译而来的。由于中西方文化、文字的差别,同一个概念往往很难在两方中找到表达对应一致的词语。英汉转译时意思虽有重合,但也有不合,甚至遗漏之处,“Folklore”便是。
Folklore原系撒克逊语中的合成词Folk-lore,Folk为“陋民”“乡民”之意,学界现扩展为“民众”。Lore为“学问”之意。Folklore本意为“the lore of the folk”(民众学问)、“the learning of the people”(民间或人民的知识),其内容包括传袭的信仰、风俗习惯、故事、歌谣、俚语等。在民众中流行的故事、歌谣、俚语等文学艺术因素较强的部分,仅是Folklore的一部分。
阿伦•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自从威廉•汤姆斯(William Thoms)1846年创造了‘民俗学’(Folklore)一词,有关民俗学定义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大多数定义侧重于‘知识’(Lore),也有些定义侧重于‘民众’(Folk)。”[3]显然,和任何学科一样,关于Folklore的学科定义不免有歧义,但总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主要是有关人民知识的内容。可见,以“民间文学”对译“Folklore”,是以小盖大。反之,缺少了Folklore的学科性的全局关照,民间文学中的故事、歌谣、俚语等文学艺术因素较强的部分的特征就不能仅仅是口述的、流动的,还应该有更高的学理层面的意义与固有意蕴的支撑。
意大利民俗学家朱•柯克维拉在《欧洲民俗学史引论》中提及民间文学时指出,假如去掉由特殊的服装、习俗和那种赋予它们以一致性,赋予它们以灵魂—而常常也是意义—的信仰所创造的那种背景,那么,人民口头创作(歌曲、传奇、俗语,等等)的作品就常常完全丧失了生命。①Giuseppe Coechiara trans.from John N.McDaniel:The History of Folklore in Eourope,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81。事实也正是如此,按流行的称呼来说,民间文学中的人民口头创作(歌曲、传奇、俗语,等等)是在一国、一民族或一地域族群特定的生活习俗氛围中存在的。民众的生活习俗发生变化,民间文学的生命力也相应地受到影响。这一切生动地表明,这类文学即使归入文学,仍不能改变它与一般文学不同的、独树一帜的特点—文学,又非文学。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不是单一的纯文学,它与地方方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百多年前,诗界革命的先驱黄遵宪就注意到了歌谣和方言、风土的关系:“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4]他认为要更好地理解和记录民歌,就必须了解当地人民的方言和风土人情等,否则不免会有隔阂,无法很好地保留其本来面目。黄遵宪不仅自己有意辑录民歌,还动员友人共同编辑,并称之为编纂“新国风”。凡是真正的民间文学,其表达必然与相应的地方方言相映辉。正如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5]但是,纵观多年来各地申报的非遗类民间文学,往往在采集的文本中都忽略了这一点。另外,民间歌谣中糅合了音乐、舞蹈的元素,各民族民俗活动中的歌谣展演也往往是文学、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这是无法用文人的诗歌文学标准来类比和衡量的。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承继着世代传袭的心意信仰和精神依托。如千古流传的“梁祝”传说,结尾“合冢化蝶”的情节表现了坚持不懈的韧劲和生生不息的生命观。江南湿润温暖的气候和多丘陵草木的生态环境,适宜蝴蝶的孳生,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生命往往不会死去,而是转化为其他事物继续存在。在这种生命心意信仰下,虽然“梁祝”在生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理想中的民间婚姻模式,但实现这种理想的精神未死。“英台乃造梁墓前,失声恸哭,地忽开裂,坠入茔中,绣裙绮襦化蝶飞去。”[6]“合冢”与“化蝶”,从表面上看是民间“情感动天”、灵魂不死观念的反映,其实质是精神生命对理想境界的继续追求,渊源于江南独特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深层的生命一体化理念。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常用文学的外表传递着地方性的生产知识和生活智慧。比如,2016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与其相关的谚语有:“一月有两节,一节十五天。立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惊蛰快耙地,春分犁不闲。清明多栽树,谷雨要种田,立夏点瓜豆,小满不种棉。芒种收新麦,夏至快种田。小暑不算热,大暑是伏天。立秋种白菜,处暑摘新棉。白露要打枣,秋分种麦田。寒露收割罢,霜降把地翻。立冬收菜完,小雪犁耙闲。大雪天已冷,冬至换长天。小寒快积肥,大寒过新年。”[7]以及“清明早、小满迟,谷雨种棉正当时”,“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等等,以谚语的形式安排一年二十四节律的年中农事,周而复始,清清楚楚。这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农事实践知识体系,展示了劳动人民卓越的生活智慧。这与其说是民间文学,毋宁说是民间知识。
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也是文学表象表达的社会记忆和口传历史。《苗族古歌》《格萨尔》《玛纳斯》《黑暗传》等民族史诗,承担着民族(族群)诞生、发展历史的教科书的职责。我国众多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如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展现了洪荒时代中华先民不畏艰险,与天地奋斗,开创民族历史的丰功伟绩。
总之,Folklore学理框架中的“民间文学”内涵丰富,这是一国、一民族或一族群亘古萌生、世代相传的有关人民知识的传统。内蕴多种混同一体的文化因子,包容在口头文学、音乐舞蹈、心意信仰、历史记忆、生产知识、生活智慧等之中。将Folklore硬译为“民间文学”,或以民间文学等同于Folklore的做法,都是不完整和不合适的。
国际上对于Folklore的认识和研究,往往会根据本国国情、民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倾向。日本民俗学鼻祖柳田国男先生和关敬吾先生合撰的《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指出:“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认识祖国和认识自我,它的意图是站在自然共同体的立场上来研究民众的传承生活样式。但是,各国研究者最初的动机与目的并不一致,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趋势。德国的民俗学始于格林的文献学研究。其后,一方面保持了这种倾向;另一方面,自从黎尔为了社会政策的目的而建立了科学的民俗学以来,受其影响,汲其源流的德国民俗学就带有很浓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的色彩。民俗学是关于特定民族及其民间传承的科学,它的特征取决于该国的文化特点。不消说,民俗学决不是深居书斋、潜心思辩的学问,而是以资料为依据的实证科学,必然要受到各个国家的资料状况即该国文化样式的强烈影响。因此,民俗学往往适应本国情况而独自发展。虽然研究特定民族是民俗学的特征,但是,这并不会动摇反映民俗学一般规律的方法论。相反,这种特征正是本国民俗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终极目的。芬兰民俗学已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如所周知,芬兰曾处于俄国与瑞典的统治之下,长时期内,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却被迫使用外国语,也可以说这是芬兰民俗学兴起的缘由。这个国家的民俗学又是从研究具有丰富传承的民间叙事诗《英雄国》开始的。芬兰是一个民间故事及其他民间文艺资料特别丰富的国家。民间文艺和与之密切有关的民间信仰成为芬兰民俗学的中心问题,在那里,民俗学甚至被认为是研究民间文艺与民间信仰的学问。虽然在我国与欧洲各国,民俗学兴起时,也都有过类似的研究倾向,但芬兰的民俗学却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了方法论。这是和我国民俗学大不相同之点,与德国民俗学的特点也相距甚远。芬兰民俗学在研究民间传承中,特别着重的是文化起源及其传播方向,研究范围限制得甚为狭窄。从上述事例大致可以了解民俗学的研究内容、范围都是由该国资料状况所决定的。”[8]
芬兰将Folklore中的文学艺术因素较强的部分纳入了文学体系的研究,但并没有将其当作纯粹的文学,而是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苏联将Folklore中流行的文学因子另立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学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还没有全面了解苏联学界对源于欧洲的Folklore进行的苏联化解析和学术分工的情况下,一度跟从苏联的“人民的口头文学”研究模式,造成了我国民间文学学术研究对象的认知不清和研究中的被动。
出于苏联国内学科研究的现实,苏联学界一度把国际上Folklore的内容一分为二。在十月革命前,俄国就开展了对Folklore的研究,为此还专门出版了一本杂志《Художист веный фольклор》(《艺术的民俗》),意指民俗中的文艺学,同时,还出版了另一本杂志《Этнаграфия》(《民族学》)。它们虽分属于文艺学和民族学两个领域,却不约而同地介绍、研究民俗学的事象和风俗习惯,界限有些模糊。因此,苏联著名的文艺学家萨哈洛夫认为,既然民俗事项、风俗习惯已有专门的杂志在研究,那外来语фольклор(Folklore)即为民众间流行的语言艺术部分,人民的集体艺术,民俗的艺术。后来,在苏联文学界倡导的“文学的人民性”理念影响下,又另立了“人民的口头文学”(нартрая устная словеснасть)学科。我国的一些学者既不了解苏联学界的这桩历史公案,又不仔细酌定译名与原意的关系,便袭用清末民初以来显示人民艺术创作才华的“民间文学”概念与其相配,真有点“死搬硬套”。一方面,它不能科学地界说这类艺术的范围、特征;另一方面,又生硬地剥离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天然联系,硬把它与独立的作家文学相提并论,结果就是矛盾百出,学术思想也弄得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主流,一会儿说专业作家的文学才是主流。有的强调前者的文学性如何好,有的则一味地吹捧专业作家的文学如何高超。孰是孰非?实际上,这是把虽有联系,但本质上却有很大不同的两种文学形态,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带来的偏差。
百余年过去了,虽有前辈学者把Folklore译为“民风学”“风俗学”“民情学”“民学”“民俗学”“民间智慧”等,但是将Folklore视为与民间文学大略相同的观念却延续至今。这期间,我们学界也有为“民间文学”冠之英语译名“folk literature and art”,以示区分。然而,在改革开放初,一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对我说:“民协对外交流时,国际上一时找不到与‘folk literature and art’同一称谓的学术机构,人家也搞不清你们自己搞的中文化的英文译名究系何意。”呜呼!
对“由人民创造并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流传的文艺作品”,苏联学者倒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它与作家文学不一样的非文学特点。如包加得列夫在《俄罗斯人民口头创作导论》中列专章论述“口头文艺学跟其他科学的联系和它的特点”,强调须注意它“跟文学的区别”,“不能够仅仅局限在文艺学的方法上……例如,仪式歌,就靠近那些作为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材料。许多仪式性的民间文学作品仅仅在把它跟伴随它的仪式同时研究的时候,才能够完全了解”。[9]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所谓的“民间文学”,只有在与仪式信仰或其他文化因子混合在一起的非纯文学的共同体研究中,才能获得真谛。
总而言之,百余年来,我国学界在Folklore学理框架中构建的“民间文学”之文学,内涵与真正意义上的如作家创作的文学,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民间文学”学术称谓已约定俗成,一时难以修正,但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必须对它非文学的广阔内涵有深切的了解,以便更准确地把握、更深入地研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