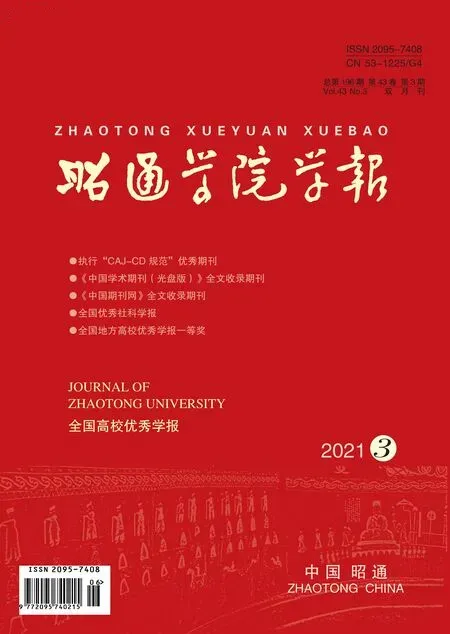论《宠儿》中保罗·D的自我突破之旅
方 伟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以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闻名。其作品《宠儿》(Beloved)的创作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而它的创作灵感却来源于神话、《圣经》和黑人文化中丰富的原型,自发表以来便受到了许多批评家的关注。Nancy Bate认为《圣经》中对古以色列人的奴役是《宠儿》这本关于奴隶制和自由的历史小说有着莫大的关联,并认为《宠儿》和《圣经》的叙事模式都遵循着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勾勒出的“艰难的出生,受难/冒险,牺牲/死亡,复活,仪式化的记忆和集体救赎”神话模式。[1]Sharon Jessee考察了《宠儿》《爵士乐》(Jazz)和《天堂》(Paradise)中的女性启示者,认为莫里森在多重神学和宗教实践的象征下复活了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文化意识。[2]Diane M. Golden继续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启蒙——启程——归来”的理论分析了《宠儿》当中丹芙的回归,她认为丹芙回到了现实世界,是莫里森小说中唯一成功的女主人公。[3]国内也有学者从原型角度研究了《宠儿》,如黄秀敏和王润娟。前者则认为《宠儿》是由圣经文化与非洲文化共同搭建而成,是非裔美国人复杂的种族身份、宗教信仰和文化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4]后者认为莫里森借用了史前文化中的原母神原型刻画人物塞丝,表现了莫里森对非洲民族的热爱与忠诚和对非洲文化的崇拜与眷恋。[5]可以看到,以往的研究对《宠儿》在原型方面基本作了一番包括原型来源、叙事模式和主题在内的全面剖析,但是这些研究都只集中在女性主人公身上,而很少聚焦于一般认为被作为配角出现的保罗·D身上以及其对小说主题的补充。
在《宠儿》中,作为男性的保罗·D和三位女性角色塞丝、宠儿以及丹芙相似,也经历了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提出的英雄“启蒙——启程——归来”的历程。坎贝尔是美国著名的神话研究者。他认为神话的意义是象征性的,而且神话的象征意义是心理上的。在《千面英雄》中,坎贝尔运用心理学的解释方法,从各种不同的文化中选取了大量的神话素材,试图证明世界各地的英雄神话都是类似的,背后有着统一的英雄冒险历程。仔细阅读《宠儿》,可以发现保罗·D在他的英雄历程中突破了冒险和归来的阈限,得到了成长。从男性人物入手发掘小说的主题,能帮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文本的含义。
二、跨越冒险的阈限:追寻自由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对神话中英雄冒险的标准道路作了一番解释,“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种种危险,进入一个超自然的神奇领域;在那神奇的领域中,和各种难以置信的有威力的超自然体相遭遇,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英雄完成那神秘的冒险,带着能够为他的同类造福的力量归来。”[6]24在《宠儿》中,保罗·D的历程也是神话中英雄冒险模式的一种变形。坎贝尔指出,英雄冒险的开端是接受冒险的召唤:
神话中的英雄从他日常住的小屋或城堡出发,被引诱、被带到、要不然就是自愿走到冒险的阈限。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守卫着阈限不让通过的幽灵或神灵。英雄可能打败这位守卫者或博得他的好感而进入幽暗的王国,或被对手杀死而进入死亡之国。越过阈限之后,英雄就在一个陌生而又异常熟悉的充满各种势力的世界中旅行,有些势力严峻地威胁着他(考验),有些势力则给他魔法援助(援助者)。[6]256
保罗·D一开始居住在加纳先生管理下的“甜蜜之家”种植园,在那里加纳先生采取的是一种较“仁慈”的管理制度。加纳先生称自己的黑奴们为真正的男子汉,而加纳太太温和、贤良,从不大骂黑奴,“甜蜜之家”奴隶们基本过着伊甸园式的和谐生活,而加纳夫妇扮演着类似上帝的角色。在加纳先生去世以后,具有施虐倾向的学校老师来管理种植园,使奴隶们的生活不堪重负,使他们决心逃离。使保罗·D开始冒险的可能是一个偶然和一个错误——即加纳先生的意外去世和加纳太太邀请学校先生管理种植园的错误决定——从而揭示出一个英雄从未想到的真正自由的世界,并使英雄和他此时还未能正确理解自由的力量建立起联系。但是又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揭示的,错误并不是纯属偶然的,它们是欲望和冲突受到抑制的结果。[6]47奴隶制度下对人性的压迫和剥削归根结底是不人道的,加纳夫妇家长式的管理作风和对黑奴的善待并不能改变白人和黑人之间对立的种族关系,英雄的冒险是一种必然,从而开拓他新的命运。自学校老师到来以后,这个加纳夫妇为黑奴们创造的伊甸园幻象砰然破裂,保罗·D开始意识到“他们都被隔绝在一个美丽的谎言里,将黑尔和贝比·萨格斯在‘甜蜜之家’以前的生活看成是运气太坏,而置之脑后。无知地把西克索的黑暗故事当作消遣。在保护下相信自己是特殊的。”[7]263首先,保罗·D已经开始把他心灵的重心从“甜蜜之家”转移到未知的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英雄眼里又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保罗·D发现自己“如此热爱这个世界的面貌,什么都能容忍,一切都能容忍,只为了在一个他虽无权享受月亮、而月亮却仍然出现的地方活着。爱的小,偷偷地爱。当然,他小小的爱是一棵树……古老,宽阔,时刻在召唤。”[7]263“树”代表着广阔的自然天地,是自由的象征,这种外在世界的召唤也是英雄内在渴望的一种反映。其次,这一切也显然是受到了作为冒险向导的西克索的影响,是后者邀请保罗·D们一起逃跑,并在逃跑的路途中同保罗·D一起被抓住,然后又揍人,又在全身燃烧的火光中唱歌(因为“30英里女人”怀着他的孩子逃走了),然后悲壮地被枪杀。西克索这个人物具有一种殉道徒式的魅力,如同在梦和神话中出现的向导人物都具有的魅力一样。当这个人物向英雄发出邀请、英雄内心做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原先在“甜蜜之家”的生活便逐渐开始变得毫无价值。“因此,即使英雄短暂地回到他熟悉的日常事务中去,他可能发现那些日常事务徒劳无益。于是他就会看到一连串越来越强烈的征兆,直至号召变得无法抗拒”[6]52保罗·D接受了这种冒险的召唤,和西克索一起出逃,这个召唤使故事便开场,而这种故事又是一种变形的神秘剧,即“一种精神上跨越阈限的仪式或阶段,完成这种仪式就等于经历一次死亡和一次出生。陈旧的观念已经不再适合,跨越阈限的时刻临近了。”[6]48保罗·D必须完成这个跨越阈限的仪式才能获得新生,而学校先生正是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着类似神话中不让英雄通过阈限的幽灵的反面角色。
不幸的是,英雄虽然完成了精神转变,但是他第一次跨越阈限的尝试却以失败而告终。保罗·D在和西克索逃离的过程中被抓住,后者被处死,而保罗·D的嘴则套上了铁嚼子,终日忍受非人的羞辱。后来,学校老师将他卖给了一个正在从肯塔基州前往弗吉尼亚州的奴隶主“白兰地酒”。从在“甜蜜之家”生活到被贩卖,象征着英雄从原本的天堂掉落进了凡间。这一次英雄再次尝试跨越阈限——试图谋杀这位奴隶主(另一位幽灵角色)——从而完成仪式,却再次失败,他因而被送到了乔治亚州的阿尔弗莱德监狱。从被贩卖到被关进监狱,又象征着英雄又从凡间掉落进了地狱。但是,未知的广阔天地对英雄的号召在这次尝试中变得更加急迫。“它发自内部。是一种颤动,先是在胸口,再传递到肩胛。感觉起来像涟漪一样——开始时柔和,然后就转为猛烈。”[7]127英雄内心对自由的渴望达到了极度,这种凡人像神一样使用力量的方式一方面表现了坎贝尔所说的英雄内心凡人成神的理想,另一方面表现了英雄一直在积聚力量,挣扎愈加猛烈。有一天,大雨滂沱,地面变得泥泞不堪,于是犯人们凑在一起用劲儿挣扎着逃出了铁牢笼。暴风雨仿佛是超自然力量的助力,帮助保罗成功逃离了奴役生活。在切诺基人的指引下,保罗·D觅着春天盛开的花向北行进。几年之后,他到达辛辛那提,在塞丝家的门前停下了流浪的脚步,如同神话中的英雄“战胜了所有吃人妖魔之后,最后的冒险通常表现为胜利英雄的灵魂和世界神后的神秘婚姻”,[6]105保罗·D与他一直心念的女神塞丝相会并结合,象征着回归伊甸园式的生活。
三、跨越归来的阈限:重构现实与自我
英雄离开他所熟悉的世界、经历了考验之后,坎贝尔提到英雄在最后归来的途中还必须跨越归来的阈限,“归来的英雄的第一个难题是,在看到使灵魂感到满足的实现了夙愿的景象之后,再去接受现实生活中的转瞬即逝的欢乐和悲伤、平庸陈腐和喧嚣淫秽。”[6]224“归来的英雄,为了完成他的冒险,还必须经受住现实世界对他的冲击。”[6]231保罗·D回到塞丝身边之后,他还面临着两项考验,第一项是归来之后难以适应和经历了一系列创伤的塞丝的生活,保罗·D对现实感到失望;第二项是与宠儿即黑奴集体记忆的代表的抗争,保罗·D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保罗·D的考验在于,他需要重新认识现实,建构起对自我的认同,打开尘封的心灵。
在《宠儿》的前几章里,就在保罗·D初到124号的那段时间里,他仿佛真正回归到了塞丝身边,把自己看作塞丝的伴侣,并坚定信心要和塞丝生活在一起。他向塞丝保证“塞丝,有我在这儿陪着你,陪着丹芙……我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七年了……在哪儿都不久留……可是我到了这儿……我不是奔着这个地方来的,是奔你。我们能创造一种生活,姑娘。一种生活。”[7]55这种生活实际上是加纳先生管理下的“甜蜜之家”那种伊甸园式生活的变体,只不过这次保罗·D想和塞丝一起做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扮演他们自己的上帝。保罗·D还邀请塞丝和丹芙一同去参加镇上的狂欢节,帮助她们又一次融入社区生活,而他自己也交了几个朋友,在镇上显得似乎颇有人缘。三人都玩地很痛快,“在回家的路上,尽管投到了他们前面,三个人的影子依然手牵着手。”[7]59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在手拉手,这是象征幸福未来的一个美好标志。保罗·D在搬进塞丝家之前,还驱走了盘踞在这座房子里的冤魂,这表明了英雄经历了超验归来身上具有一种超自然的非凡力量,更加接近神性。
但是,英雄也面临着归来的阈限,他在归来的阈限前止步不前,而必须跨越这个阈限他才能真正归来。第一个考验就是现实对他的冲击。保罗·D强烈想和塞丝生活在一起的愿望表明了英雄想要归来的意识,但是同时保罗·D也发现,他整整25年都在渴望塞丝,最后他的渴望达到顶峰之后,却坠入了失望的深渊。他发现塞丝背上的“树”实际上只是“一堆令人作呕的伤疤”。[7]26保罗·D突然心中默默地对塞丝的伤疤产生一种厌恶情绪,这表明保罗·D在情感上对塞丝已经产生隔膜,这是英雄在满足他的夙愿之后,第一次面对现实的平庸和陈腐。当保罗·D从斯坦普·沛得那里得知塞丝的残酷选择,即她的杀婴经历后,他指责塞丝“你有两只脚,塞丝,不是四只。”[7]197意即塞丝的行为无异于野兽的行径。“尝了人间的知识之果,就把精神专注从位于中心的永恒转移到位于边缘的突发性事件的瞬间。于是完美的平衡就此失去,精神就此彷徨,英雄就此堕落。”[6]230回到伊甸园式的保罗·D又再次被打回现实,他离开了124号,再次堕落到象征着地狱的当地教堂的地下室里。巧妙的是,象征着救赎的教堂和地下室只有一线之隔,意味着跨过从地下室到教堂的阈限,英雄便能得到救赎的回归。直到保罗·D知晓了124号曾经发生的一切,并在社区为124号驱魂之后再去看望塞丝,想起了西克索说的他所爱的“三十英里女子”——他精神上的朋友——把他的碎片用正确的次序捏拢了,才发现塞丝竟然再次在自己心中掀起了狂澜。“只有这个女人塞丝才会那样,不去碰他的男子气概。他想把自己的故事同她的放在一起。”[7]326保罗·D认为塞丝对他做了同样的事情,让他恢复了作为男子汉的尊严,英雄在此刻才真正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阈限,即在神话中原本是天堂与地狱的阈限,做到成为两个世界的主宰,自由地在两个世界的界线来回跨越。
归来另一道阈限是保罗·D和宠儿之间的对抗。在124号里,宠儿控制保罗·D,任意摆布他,无论保罗·D在哪个房间里,都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和难挨的感觉在纠缠着他,最后他搬到了屋外去住。而宠儿游移不定的身份对我们理解保罗·D的这一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她有可能只是塞丝刚开始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被白人男子囚禁的没有行动自由的普通女子,或者是小说中大多数人物所认为的是塞丝死去女儿的冤魂附在了宠儿身上,也有可能是塞丝过世母亲的象征。但是,“在广泛的层次上,宠儿还可能代表了所有穿越大西洋从非洲被运到美洲的黑奴……宠儿正是代表了这些同处于无意识下的黑奴。”[8]34保罗·D和宠儿之间的对抗,也就是他与自己过去所进行的对抗。为了逃避自己因奴隶身份而注定要忍受的情感痛楚,保罗·D制订了一套压抑式的应付策略。他紧紧地关闭了自己的心扉,把自己过去那些充满创伤的记忆、感情以及爱的能力都锁到了那个生锈的“烟盒”式的心房里。尽管保罗·D与塞丝的结合给了他安全感,令他正视自己的往昔。他却仍然怀疑自己缺乏构建独立人格的一些基本要素,他觉得自己“胸膛里并没有一颗像‘先生’的鸡冠一样鲜红的心在跳荡”[7]92而保罗与宠儿之间所发生的梦魇一般奇特的性关系,标志着他与过去的交锋,开启了他那“烟盒”般的心扉,使他一遍遍地重复着“红心。红心。红心。”[7]140他发现自己还具有欲望,还具有人性。他的盒子豁然开启,他的心再一次变得火热,又可以去感受和爱了。当保罗·D提议塞丝为他生个孩子时,英雄在此时真正地与过去做了和解而步入稳定的生活,开始思考将来。“如今他第二次心怀感激。他觉得自己仿佛被人从一面悬崖峭壁上摘下来,放到安全的地面上。”[7]156
四、最后的归来:雌雄同体的英雄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里指出,“在神话中不乏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神。他们总是带着某种神秘色彩而出现;因为他们使人的思想离开客观经验的世界,进入一个舍弃了二元性的象征领域。”[6]145-146在《圣经》中,当上帝造人时,“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9]11上帝的形象于是在经文中有了明确的答案,“当值得赞美的上帝造第一个人时,他把这人造成两性体。”[11]而上帝在伊甸园里把男女分离,坎贝尔认为则意味这一种堕落:
把女性分离成另一个人,象征着从完美的境界堕落到二元状态的开始;很自然地接下来就发现善与恶的二元性,逐出上帝在其中行走于地上的伊甸园,于是建成的地上乐园之墙……不仅使人(现在是男人和女人)看不到,而又甚至回忆不起上帝的形象……这种说法是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创世奥秘的基本方法之一:即把永恒转移为时间,使一成为二,再成为众多,以及通过二的重新结合而产生新的生命。[6]146
坎贝尔认为英雄的任务就是通过二的重新结合而产生新的生命,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重新找到并回忆起上帝的形象并获得智慧,这也标志着英雄任务的结束。在《宠儿》中,塞丝是一直吸引保罗·D回归的中心,纵使在回归的过程中英雄在跨越阈限上产生了困难,他始终无法摆脱女性主人公的引力,即便前方困难重重,心目中美好的女神形象仍然会激励着他回归,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经历无数艰难险阻也要与妻儿团聚一样。“她是每个英雄所追求的尘世的或超自然能给予至福的目标。”[6]123-125与女神相会对英雄来说是最高的奖赏,即便这个女神已经因为年岁衰老,背上有一颗奴隶生活给她烙印下的苦樱桃树,他也仍能发现她身上存在的美,欣赏“她锻铁一般的后背;还有那张美妙的嘴……那诱人的黑眼睛。在炉火前冒着热气的湿裙子。”[7]326她能“保证灵魂在不如人意的世界中的放逐期结束时,将能再体验到过去曾一度体验到的巨大幸福”[6]108保罗·D正是在塞丝身上找到了极大的安慰,对和塞丝一起稳定生活、生子的向往是他最大的梦想。当他被阻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阈限前时,一度暗淡的前景尽管使他开始怀疑自我,但是最后英雄还是有意无意来到了塞丝身边,意识到女神对他巨大的精神塑造作用,他不可能脱离这个一直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女神而单独存在,因为他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7]326而他们更共同“需要一种明天。”[7]326这样,英雄突破了归来的阈限,与曾经被从他身体里分离出的另一部分又重新结合在了一起,于是英雄既具有了男性又具有了女性的特性,在精神上又回到了类似亚当在夏娃从他身体里分离出来以前的雌雄同体的原初状态。只有这样,英雄才成为一个不仅是男人的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更加具有神性,从而更加贴近上帝,实现一种精神的永恒。这种永恒带来的又是内心的安宁,它能抚平一切创伤,使一切痛苦都化为乌有,正如小说最后所描写的那样,“渐渐地,所有的痕迹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天气。不是那被遗忘的来历不明者的呼吸,而是檐下的熏风,抑或是春天里消融殆尽的冰凌。只有天气。当然再不会有人为一个吻而吵吵闹闹了。”[7]329最后只有宁静的自然事物在英雄心中留存下来,它表征着精神的宁静,而这种宁静又在四季的不停轮换中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五、结语
从单一神话的角度看待《宠儿》中保罗·D这个人物的历程,可以发现作为英雄人物的保罗·D一开始接受了逃离奴役的召唤,艰难地跨越了第一个阈限,在流浪生涯的最后与旧时的梦中女神塞丝相会;在归来的过程中,保罗·D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和对自我的怀疑,重构了现实与自我;最后,通过回到塞丝这个引力中心,保罗·D找到了属于自己身上缺失的一部分,英雄在精神上又回到了类似亚当在夏娃从他身体里分离出来以前的雌雄同体的状态。“神话和童话的职责是揭示在从悲剧到喜剧的隐秘内心道路上旅行的具体危险和技术……它们所表现是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胜利。”[6]23这种以神话模式书写黑人的挣脱奴役追寻自由的历程,使其带有了一种使命感和高尚感,把内心力量和内心考验的至关重要性体现在了在英雄的历程中。只有克服内心的阈限,黑人才有可能真正从过往的痛苦历史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实现内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