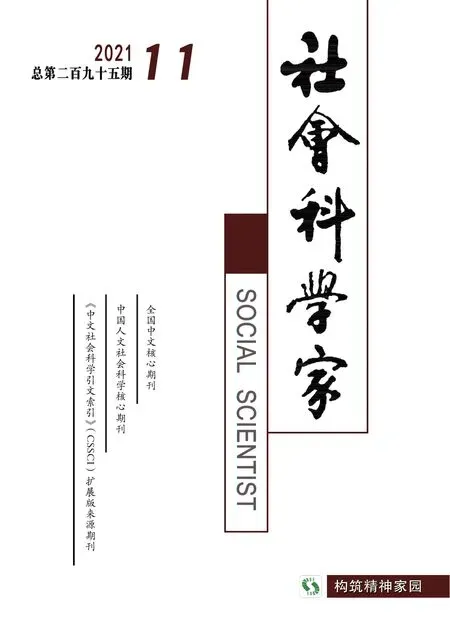玉石信仰与“隐蔽秩序”中的“天下”
李永平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今天的学术研究,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被精英群体、西方话语、架空的理论所裹挟。具体体现在脱离本土传统,缺少人文关怀,远离现实生活。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我们的文学背后的文化文本,须臾离不开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这些基本命题包括生死、疾病、成长与衰老、禳解灾害等等,这一切可称之为隐蔽秩序。哈耶克的社会演化理论有一个核心概念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1],可理解为“自我生成的秩序”(Self-generating Order)、“自我组织的秩序”(Self-organizing Order)或“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之所以说是隐蔽秩序,是因为它是自发演化的产物,却又是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支配秩序。来自自发秩序的文化传统,会集体无意识地呈现为原型情节、原型意象,比如从白壁礼天、黄琮礼地、祭祀用巫玉到通灵玉禳解,就有了小说《石头记》。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还原到文化大传统深层搜寻隐蔽秩序。近年来,除生死、疾病、成长与衰老、禳解灾害等隐蔽秩序之外,重力作为一种隐蔽秩序,参与了人类神话观念的建构过程。对天的象征性表述是这一秩序的言说传统,玉礼器是这一秩序形成的“事物”[2]。
一、玉石神话与华夏资源依赖
在华夏文明诞生之前的兴隆沣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龙山文化、石峡文化和齐家文化中,批量出现玉礼器为社会显要人物随葬的现象,考古学上称之为“唯玉为葬”或“玉殓葬”。通过对《山海经》《淮南子》《史记》等早期文献的梳理,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创世神话研究院首席专家叶舒宪教授把玉石神话历史线索概括归纳为:
黄帝食玉膏和播种玉荣;尧舜时代用赤玉瓮饮甘露;西王母为华夏统治者献上白玉环;大禹获得天赐玉圭建立夏朝王权国家;夏桀远征求取岷山之玉,并建瑶台玉门;商汤问伊尹从何处能运来白玉;商纣王临终用宝玉缠身自焚升天;姜太公钓鱼得玉璜;周公东封其子伯禽以夏后氏之璜;秦昭王以15座城池为条件交换和氏璧;秦始皇打造传国玉玺作为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的标志;刘邦用一双白璧从鸿门宴躲过杀身之祸,建立大汉王朝,真可谓生则守玉玺,死则归玉山。[3]
这些早期历史文献中的神话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种神秘的物质——玉,这种物质有什么功能,它的背后有什么“失落的传统”,玉石神话历史线索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换句话说,国人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背后的玉石神话信仰——玉石为天、玉石为神圣、玉帛为精、玉石不朽(长生不死)等,犹如潜藏在文化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如何奠定、塑造了“以玉为礼”“以玉比德”“以玉喻美”“化干戈为玉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中国礼乐文明核心价值观?
杨伯达、臧振、叶舒宪等著名学者对分布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距今8000至4500年的遗址出土玉器研究表明,墓葬出土的玉礼器背后有一个失落的文化大传统:“玉”曾经是华夏凝聚为文明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同民族认同的标志物。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用“玉魂国魄”来概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中的精神纽带。近二十年,叶舒宪教授通过大量考古实物遗存和15次“玉帛之路”的田野考察材料,进一步指出:以玉为神,传国玉玺代表天(天命)王权,玉象征永生。玉石神话信仰经历数千年传播,最终扎根中原国家,在夏、商、周三代王权建构中,表现出礼仪法器的作用,奠定了数千年代表国家统治阶层的君子佩玉制度和儒家以玉比德的伦理教义。古典小说的巅峰《红楼梦》中,贾宝玉出生时口含的是来自女娲补天遗留的“通灵”宝玉,它的功能首先是延寿保命“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其次是“除邪祟,疗冤疾,知祸福”。正因为是通灵宝玉,宝玉才可以梦游太虚幻境,梦见警幻仙子,未卜先知知道贾家命运。可以说,在古人的信仰中,黜落人间的通灵宝玉几乎解决了西方人在宗教教堂里解决的所有问题。①叶舒宪、古方:《玉成中国》,中华书局,2014年版。在中国,从距今8000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加工生产一种既不是生活资料也不全是玉兵器的器物——玉器。这种生产背后的支配性观念恰恰是萨满的“登天入地,进行宇宙飞行”和“巫觋通天”观念。对具有象征天地沟通的战略性资产“白玉”的掌控的观念和意识,转变为祭政合一的王权神授的神话观念,再转化为文明时代的原始拜物教。
“天”或者“帝”的观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研究表明,玉器可以代表升天的神力,也代表永生不死的能量,这条来自史前玉教神话信仰的基本教义,在古籍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表现。《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4]这里讲述的是礼乐歌舞的由来和掌握者——乘两龙的夏后启。他能够乘龙,为什么还要手操玉环和身佩玉璜呢?参照《山海经》的另一处叙事,可知玉环玉璜皆为沟通天人之际的神圣媒介物,与龙的功能类似,能够助人升天。《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4]把人间的礼乐歌舞之来源,解说成夏启三次上天取来的。其升天工具,照例还是乘龙。将这两个神话文本组合分析,可归纳出天人合一神话观的基本范式,以三个相关母题为表达,即:升天者——乘龙——佩玉璜。玉璜是先秦六种主要玉礼器之一,其形状为半璧形,与璧、琮、圭、璋、琥并称“六器”。华夏历史记忆中最重要的一件玉璜就叫“夏后氏之璜”,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政权更替,一直传承到西周王室的分封诸侯时,使得后代的政治家们对这件象征权力的神圣国宝津津乐道。
玉器能辅助升天,这样的观念与其说是《山海经》作者们发明创造的,毋宁说这是对来自史前文化大传统的深厚信仰观念的一种自觉继承。为什么说仰韶先民就已经具备这样的观念呢?叶舒宪教授认为这类深色蛇纹石玉钺的颜色特征,很容易让人产生有关“玄天”的联想。灵宝西坡大墓M6蛇纹石玉钺在墓主人墓葬仪式中,让玉钺的刃部放在人的头顶上方,指向天宇,类似火箭发射状态的升天的工具。[5]用玄玉制成的斧钺型礼器,是灵魂升天的漫长旅途中引领性的标志物和驱动力。这样的象征效果,正契合了“玄玉与苍天”这一组二元符号,斧钺与星辰的联结构成的象征意义,成为解读升天神话的重要线索。在这个意义上,仰韶先民引魂升天之书的关键——玉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具备“纪念碑性”(Momumentality)[6]的一种特殊的“显圣物”。
在古代墓葬随葬品中,汉代人还习惯让圆形的玉璧代表升天之门,并在玉璧上写出“天门”二字。不过上溯其死后升天的想象之源头,则非灵宝西坡大墓莫属。虽然没有文字,但是玉礼器的出场规则,其结构功能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就因为其被支配的表象背后,有着支配性玉教观念,那就是以玉为天,以玉为神,以玉为精,以玉为永生不死的一整套神话观念。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中讲述古埃及宗教观念的第4章,专列一小节题为“法老的升天”:“死者的居所或是在地下,或是在天上——更确切地说,是在星辰之中。”[7]
中国史前文明中出土的玉璧、玉琮、玉璜、玉璇玑等,是史前巫教祭天、登天的“媒介”,玉璧是巫觋上天的入门券,重庆巫山县出土东汉鎏金铜牌饰标本A3门阙:中央玉璧上书“天门”二字就是最好证明。玉圭是古代巫觋的“量天尺”,可以测日影知四时。河南登封告城镇至今还留存着像玉圭一样的圭表周公测影台。玉璇玑象征宇宙旋转的“天枢”,在神话天文学观念中,围绕北斗星运行的是“天璇”“天玑”二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玉器制作工艺保存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负载了中国人崇高的价值追求。早期社会通过控制玉器的原料开采和加工技术,使之融入到文化大传统的编码系统之中,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
二、玉教、通天祭祀与大传统中的隐蔽秩序——“万有引力”
笔者认为,对向上的空间——“天”的确定性的探索和憧憬深层揭示了远古以来人类被重力束缚,仰望天空的遐想与迷思,由于资源使用的路径依赖,华夏大地上的玉石资源与天之间形成象征性对应关系。关于“天”的神话信仰至少包含了以下内容:1.神灵都在天上,这背后是人类对陌生人-圣王/神“Stranger-king”的认知法则;2.需要献祭天神,后来增加了祖先神;3.死后升天,巫觋可以通天,卜知天意;4.斧钺、玉璧、玉璜、龙、建木、彩虹桥等工具是通天、升天的中介。
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为什么是“玉教”信仰而不是别的物质信仰,玉教信仰揭示了人类文明什么样的隐蔽秩序?
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神话传说的內容就和“天”有关,似乎“天”是最早赋予人类神性概念的对象。人类根本无力撼天:雷鸣、日食、风暴、落日、彩虹和流星——它们在另一个无穷无尽的时空里上演着无休无止的剧情,恣意炫示着自己的生命力。
人类仰望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天空,心里不由怀着恐惧和欢欣,怀着敬畏和惧怕,获得了一种宗教体验。“天”既吸引着他们又压迫着他们。伟大的宗教历史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曾经这样描述,“天”的本性就具有超验性,既可怕又迷人;并没有任何虚拟的神性隐藏在其后,“天”本身就是“令人畏惧的神秘”和“令人向往的敬畏”。地上的人们开始用各种方式试图把“天”人格化。几乎每一个万神殿都供奉着一位“天空之神”。他们开始讲述关于“天空之神”或“至高神”的神话。这种最原始的一神教几乎可以溯源到旧石器时代。在人类进行多神崇拜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公认有一个“至高神”存在,他开天辟地,创造世界,并高高在上地对人类生杀予夺。[8]
古埃及神话里,荷鲁斯是天空的鹰隼,“天空领主”[9]“地平线上的何鲁斯”“东方的主人”,被看作法力无边的大神,甚至被认为居于众神之首。早在纳尔迈(Narmer)调色板上,国王的右上方便有一只鹰。在第19王朝西普塔(Siptah)墓里,太阳神的形象便是羊头鹰身。从很早开始,鹰便被赋予了一种与苍穹相关的神秘力量,它的双眼被认为是太阳和月亮,胸脯上斑斓的羽毛被看作是星星。[10]“荷鲁斯之眼”蕴含着无穷的法力,亡灵经常期待能够获得它,棺椁文中荷鲁斯自己说“我的眼睛是我的庇护所,我的眼睛是我的保护伞,我的眼睛是我的力气,我的眼睛是我的力量”。①这种眼睛与日月昼夜的比附关系也早见于史前,渊源甚古。何蜻考证,甲骨文“日”字乃取象于太阳神眼睛。何蜻:《“日”字构形与商代日神崇拜及人头祭》,载《商文化窥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7、63页。Faulkner,Raymond O.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v012.Warminster:Aris and Phillips,1977.80.
古印度的“吠陀”中,太阳神苏里耶被视为生命的赐予者、万物的起源、宇宙的创造者,地位尊崇。“苏里耶”(及“萨维达”Savitara)是一群神的总称。他们都被认为与太阳的能量相关,属于阿底提亚群体,即阿底提的儿子们。在还没有被人格化之前,太阳神被想象成一只翅膀闪闪发光的大鸟。②后来,太阳神开始有了人的形体,坐在一辆由七匹马或一匹七头马拉的车里。七匹马或七头马象征着一周七天。(德)施勒伯格《印度诸神的世界——印度教图像学手册》,范晶晶译,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117页。中国商周文化传统中,甚至认为听不见鸟的叫声,就失去了请神灵降临(通神)的资格。《尚书·君奭》篇有:“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11]
“至高神”虽然不断被降级,但“天空之神”却从未曾丧失过它的权威,仍然令人们顶礼膜拜。高高的苍穹令它成为神的神秘象征——旧石器时代精神的遗迹。“传统时间体系的建立事实上是通过对空间的测定来完成的”,二者相互渗透,形成神话宇宙观,其精神源泉与太阳及其运行有关。原始初民在对太阳东升西沉的观察中确立了东、西、南、北,且各个方向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如果说鸟象征着太阳而居四方,那么居于四方的鸟表现了古人通过立表测影所懂得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12]
人们热切渴望以天空为代表的超验境界,希望借此脱离人类自身的软弱,抵达彼岸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山在神话中通常被视为神圣之物的原因:它恰好处于天地之间,像摩西这样的人就可以通过登山面见他们的上帝。在各种文明当中,都出现了关于飞行和升天的神话,这表明了人们对超验的普遍性渴望,并期望自身能从人类局限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原始宗教对空间的分割,明显表现出对向上“升天”的执着追求。早期的萨满“通天”活动要依靠动植物及神山,鼎、玉璧、玉琮等礼器,图画、文字等灵媒。龙凤两种神话动物成为早期中国通天的媒介。湖北荆州出土有东周“二龙拱璧载人升天”的白玉佩。玉琮、通天塔、宇宙树是“垂直方向”上的宇宙模式的枢纽,上界是神祇的居所,也是“特选”子民去世后所赴之阃域,[13]下界是死者和冥世魔怪汇集的地方。研究显示,玉琮、通天塔、宇宙树是“垂直方向”上的宇宙模式的枢纽。当萨满人登上世界之轴(Axis Mundi)即宇宙树之后,他们便能知晓生与死、天与地及所有对立面的轴心,那是一个不变的极点。巫师舞蹈中的旋转将法术转化为永恒中心的绝对宁静。正如印第安夸扣特尔部族的圣歌中所吟唱的,“我就是世界的中心。”[14]
早期的玉石神话隐含着远古以来的“通天”代理人“巫觋”对“向上”永恒的空间——“琼楼玉宇”,“向上”觐见的对象——“玉皇”大帝的执着向往。它背后揭橥的隐蔽秩序是:人们难以超越自然秩序重力,向地球引力相反的方向——天空运动(超越)而产生的神话信仰、宗教观念及艺术想象及其表述。由于隐蔽存在而又无孔不入的自然秩序的宿命和困扰,远古以来,玉石神话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与玉石神话光影相随的是对这一隐蔽秩序的言说,这些言说活动以仪式、神话、玉教等形式彰显存在,表述着人对自身的乌托邦设计。所以,作为社会、文化宗教的“天”及其相关的神话观念“天人合一”,才是自然秩序支配中的仪式-神话-伦理-政教多重弥漫式建构的“对象物”。
概言之,重力作为自然秩序的核心,隐秘地参与了中国早期的神话历史的全部表述。套用科幻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的经典台词——“人上不了天”。其背后的自然秩序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万有引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20世纪的头20年发现的相对论证明:引力同样是物质和能量对时空的扭曲,重力的真实根源来自于这种扭曲。[15]由于引力的不可超越,向上的空间因为要消耗人类学进化中的宝贵的能量,就有了极为特殊的宗教、政治、道德内涵:他是正价值所在的空间,成了神明的栖居之所。
三、通天、配天与“天下体系”
玉石神话大传统中,无论你是否聚焦或者思考过,自然秩序——重力“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与各种经济、地理与生活资源等因素机缘巧合地孕育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原始信仰,分蘖出了连续性文明的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通天神话和“建中立制”①早期中国文明中蕴含萨满文化的多种特征不仅为考古材料所支撑,也为人类学田野调查所证实,我们还可以通过神话学进一步探究其对中国文化延续性的阐释意义。美国人类学家佛尔斯脱(Peter T.Furst)归纳“亚美式萨满教的意识形态内容”中包括:宇宙是多层的,诸层之间为一个中央之柱(所谓“世界之轴”)所穿通;地表通常有象征世界中心的圣山,山上有世界之树,上面经常有一只鸟栖息着,这个鸟既可以在天界飞翔又可以超越各界;世界又为平行的南北、东西两轴切分为四个象限,而且不同的方向常与不同的颜色相结合。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135-136页。对天人观念和中国天下政治地理观念的影响。
通过比较神话学的视野可以发现,在世界众多民族与宗教的神话里,都有通天与象征世界中心的圣山(World Mountain)或天柱(The Pole of Heaven)。中国典籍中也存留了很多类似神话: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淮南子·墜形训》)[16]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墜形训》)[16]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大荒西经》)[17]
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山海经·海内经》)[17]
玉石神话信仰背后是关于自然重力的对象——“天”的神话与宗教。中国文化里不存在人与神约定模式的宗教,中国的信仰形式是人道与天道的相配,即所谓以德配天,寻找并占据天人交通的世界中心,掌握天人交流的权力,这就是世界各地初民孜孜求“中”的根本,也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关于古文字“中”字之释义有多种看法[18],归纳起来有两种:一是旂旐召集说[19]。二是立表测影说[20]。通过大量田野作业,笔者倾向同意何驽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即是指立表测量日影的“圭尺”,学者已经通过实地估测,算出传统标准理论地中夏至晷影为1.6尺。太阳为阳,晷影为阴。[21]冯时也认为甲骨文、金文“中”字正是兼得两方面涵义:“‘中’字的字形来源于立表测影定时与聚众建旂旗的特殊活动,而立表与建旗又都体现着四方之中央的空间思想。”[12]
萧兵在其著作里从民俗神话学的视角这样归纳:“‘中’字源起于广义的‘神圣杆柱’,中间的‘|’,无论是旗杆、表杆……都是标志族团所在的‘世界中心’、体现自我中心幻觉的‘神杆’”。所以无论是“旂”还是“表”,都可视为标志“世界中心”的“神杆”,或者说是“神杆”的不同变体,都是为了寻找且占据“地中”,尤其是太阳神崇拜的宗教观念下,太阳及“日影”成为“地中”与“阴阳”的标尺。没有太阳,就无法确定大地之中;没有“日影”,也就无所谓阴阳。[22]
铸鼎象物、传国玉玺都是“建中立制”的一部分,通过纪念碑性的物或者数字象征通天的地理空间秩序。凡是能够达到配天的存在皆为神圣存在,也就成为信仰。中国的“天道”精神信仰是隐蔽的,默认的。换句话说“替天行道”是一种隐蔽的中国文化大传统。赵汀阳先生对此有深入的理解:“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国本身,或者说,中国就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中国就是中国的神圣信念。”[23]
正因为中国的内在结构一直保持着“配天”的天下格局,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个具有神性的存在,成为一个信仰。玉教神话在根本上是玉能通天、配天,因此成为中国信仰的一环。用叶舒宪教授的表述,“升天者——乘龙——佩玉璜(或操玉环)”“商代的王室贵族们还用玉作礼献神明的祭祀。这种玉礼上承史前玉文化礼俗,下启西周至汉代的玉礼制度传统,奠定华夏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天下”观为特征的神话地理观,“玉石神话的传播和认同,如何超越具体的地域界限和民族界限,拓展出一整套以祭祀礼乐为基石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对后来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自夏商周到秦汉的国家统一起到关键的奠基性作用”[24]。秦汉以来,中国作为裂土的时间甚至略长过大一统的时间,“但大一统始终是个政治神学信念。从历史形态上说,中国是一个分与合的动态过程,尽管分合不断循环,但作为大一统的‘合’始终是其存在的本意或曰内在目的”[23]。
从“大历史”的物质演化和结构的形成,宇宙演化的“金凤花条件”的出现,我们对此得到一个精神启示:一个秩序越被广泛使用,越被更多的人分享共用,就会因此凝聚起越多的文化附加值和难以拒绝的政治魔力,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心灵,结果会形成一个无穷增值的循环。中原的特殊地位必定在于中原拥有一个具有最大政治附加值的精神世界,一个人人都可以加以占用而有助于获得、保有和扩展政治权力的精神世界,因而特别值得争相逐鹿,而这个“逐鹿中原”的过程,正是优胜劣汰,秩序奠定的过程。
“最早的中国”是建立在“天命”观念下的“天下之中”,其背后是“天下”观念及其秩序。带有社会范型性质的“天下”关涉个人的人生遭际,即发展为“天命”。西周中期的遂公盨铭文有“天命禹敷土”的记载,说明周人相信早在大禹治水时期就已经有了天命思想。“天命”象征着最高主宰天的命令,同时有人类的使命参与其中。对周人而言,传说中夏的立国者大禹与周的立国者姬昌都曾接受过来自上天的神示。西周取代殷商确立了更高的道德天命信仰。第一,将最高主宰之“帝”逊位于“天”,建立了普遍的天人信仰关系,周人把商人的上帝从一个部族垄断的神明,转变为同天一样可供天下万民共同信仰的对象;第二,天之“命”,定位于“德”,“德”落实于“民”,“敬德保民”成为天命的两大支撑;第三,天命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命令,转变为基于人的“德行”与天命的天人互动互通。①参见2019年4月29日(周一)下午,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讲演:“儒家的俟命境界”。其互动的过程包括“则中”“建中”“日中无影”,即通过测量日影而定方位天下之中的一系列观念和行动。《周礼》所载: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25]
表面上的理由是,夏至时测量日影,表杆投影的长度“恰好”为一尺五,但这尺度的正当性显然是神话。真正的理由是,夏至表杆投影一尺五的那个地域乃是四季分明、雨水均衡、冷暖适中的地方,也就是最适合农业生产而宜居的地方,那里就是中原。《周礼·地官》记载了用圭尺测日影、求地中的逻辑关系:“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并且强调了“地中”交汇天地人神、无可比拟的位置:“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26]可见,地中的理由其实是宜居的“好地方”,倒映为“正中”神话,这个神话引出了地中、四方、六合、天下等神学概念。周朝建立天下体系,按照天下体系的结构需要,地中必须是天下体系的中心。
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国”更有言说“天人合一”的资质。钱穆认为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天人合一”。[27]季羡林晚年对“天人合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8]所谓圣人当仁不让“与天地参”“德配天地”,人类在天地之间是建构价值的主体。“圣人”是这一连续性文明的代理人。其首要职能是执掌通天、通神及交通神灵的祭祀活动的知识。
人间天子能够得到天的庇护,才能奉天时,施仁德,才能完成“行天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的神圣使命。从玉石神话中的天神崇拜到“格于皇天”“降兹珪璧”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圣人获得了以德配天,奉天承运的文明体的神圣身份。进一步说,德原本不是属于人的,而是来自天的。《论语·述而》中有“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①《论语·述而》,载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273页。“《书·昭告》云:‘今天其命哲。’是人之知愚皆天所生,夫子五十知天命,知己有德,为天所命”。只有深入领会到古人讲的天是神话观念,方能举一反三,意识到“天命”“天子”“天德”等,无一不是神话思维传统的派生观念。②对天命、天德和天子的信仰,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一去不返”。如果说,神话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是由于哲学和科学将其作为对立面,才有独立的神话学出现,那么,中国有神话而没有神话学的最好解释,就是中国传统中从来没有哲学和科学的权威。这个事实足以成为“轴心突破”说适合中国文化史的反证。见叶舒宪《“神话中国”VS“轴心时代”:“哲学突破”说及“科学中国”说批判》,谭佳主编《神话中国:中国神话学的反思与开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7页。而以“配天”为存在原则的秩序才是世界秩序。换句话说,正因为有对容纳万物的天的信仰,才使得“最早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其中的“天下”是与天界的“天神”对应的全部人间下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物为抓手的玉教在回答“早期中国”建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他可以理解为“早期中国”的玉成中国,是先于统一中国的“天下之教”。
结论:“天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下为公,天下是公有的,所以作为连续性文明的中国,是文化认同而非武力控制上的文明体国家。因此用今天的话来讲,它的政治设计是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唯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重大。[29]
对“玉教”信仰与文化大传统“神话中国”背后的隐蔽秩序的挖掘,揭橥的价值还表明:没有文化文本的整体观,理性时代学科不断分化的分析研究范式,很难建构元理论,提出元策略,拿出元方案。因此很难改变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缺位、理论被动、故事老套陈旧的被动局面。
作为整体系统的社会自发演化是一个双向过程,既可能由简单到复杂(进化),也可能由复杂到简单(退化)。不一定优(复杂先进的系统)胜劣(简单落后的系统)汰,这是中国的经验。原因是简单系统对抗灾害的生存能力强,复杂系统学习新的事物快,各有各的优势,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补偿关系。[30]可以说,政治就是试图建立某种秩序去占有未来。当一种秩序试图规定未来必须如此发生,秩序就是在创造历史。由此可以理解沃格林所谓“历史的秩序来自秩序的历史”[31]。
中国文明是张光直先生所说的向文明演进的“连续性”主流形态。③《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30-133页。该文另见《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131-142页。古代中华文明的宗教信仰呈现杨庆堃所说的弥漫性、整体性特点:地与天之间的连续,文化与自然的连续,通天与祭祖相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天文、神话、祭祀与圣人相互关联,互为一体。[32]与其他同类型文明的比较,将“中”的观念一以贯之延续下来则是中国文化独特的一面。米恰尔·伊利亚德认为这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宗教来说是根本性的,他将其形象地概括为:至于宇宙的结构和节律,自商朝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各种基本概念之间保持着一种完整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对于宇宙的传统想象是:有个中心,一根垂直的轴贯穿其间,将天地两极连接在一起,并由四极而形成此一中央架构。天圆(状似卵子)地方,苍天覆盖大地,大地描述为一架方形的马车,中央有一根支柱,支撑着像天一样的圆台。五个宇宙之数—四极和一个中央之中的每一格都各有一种颜色、味道、声音和特殊的符号。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央,国都位于中国的中央,王宫位于国都的中央。[33]
从简单社会结构中的玉石神话大传统,我们发现历史的人文特性和观念的力量。人类对自身的乌托邦设计,无论是想象还是具体的实践,都有超越熵增原理自然秩序的愿景。对系统来说,稳定与发展、安全与机会是此消彼长(Trade-off)的关系,有如鱼和熊掌难以兼得。在古今连续的文明体国家——中国[34],这一愿景在玉石时代有“天”“通天”“天道”一系列命题。在这些命题中,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以践行“天道”这一富有使命又合规律的共同意识——“替天行道”之“天下国家”,走出熵增魔咒,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可以理解为今天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资源和精神动力。①在如何表述中国文学、文化上我们出现“失语”状态。身处全球化与后殖民语境之中的学人,后殖民主义在思想方面一定程度上启发着本土的学者以本位立场,消解来自西方话语霸权的阴影,去恢复或者建构自我的话语表述方式,去重启对本土,对“地方”知识与文化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