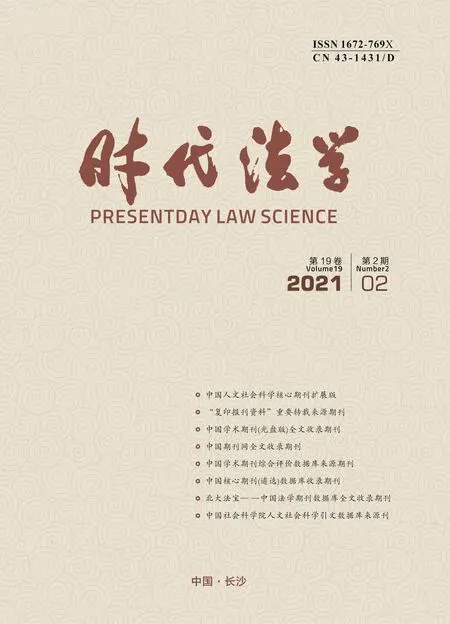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及完善*
凌冰尧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自1959年德国和巴基斯坦缔结了最早的双边投资条约起,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逐渐由依托习惯国际法转向“条约化”,随之而来的是投资条约井喷式的增长。据2019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发布的国际投资报告统计显示,截止2018年底,国际投资条约的总数量已达到3317个,其中双边投资条约(BIT)占据绝对多数,达到了2932个(1)UNCTAD/WIR/2019,p.102.。如此庞大的投资条约体系之下,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数量也节节攀升,通过国际投资仲裁的方式来解决投资争端已成为国际上一种普遍的做法。截止2018年底,全球累计公布的投资仲裁案件942起,而2018年一年的案件就有71起,一共有117个国家成为至少1起案件的被诉方。据UNCTAD估计,至2019年底,投资仲裁案件总数将达到1000起。由于一部分投资仲裁完全保密,因此投资争端的总数应当更多(2)UNCTAD/WIR/2019,p.103.。在投资仲裁案件中,大部分案件被提交至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据ICSID在2018年的年度报告显示,ICSID在2018年中受理了57件新的投资争端案件,为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可以看出投资争端的数量正不断增长(3)ICSID, Annual Report 2018, p.10.。
条约解释是争端解决的重点。不同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双方通常都为国家的情况,国际投资争端的双方通常为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因此投资争端中的条约解释需要平衡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和东道国主权及公共利益。同时,投资争端中解释条约的工作一般由临时组成的仲裁庭承担,意味着有多少投资争端提交仲裁,就存在多少个仲裁庭。随着投资争端案件数量的增长,如果仲裁庭对相同或类似的投资条约条款作出不一致解释的情况得不到缓解,那么势必影响投资条约体系的确定性,也损害了东道国对本国境内的投资行为行使主权的权力。因此,对投资争端中的条约解释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个中缘由并从现行的国际法规则体系中寻找出路是必要之举。
一、投资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的现状
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案件数量的攀升,围绕着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争论也日益激烈。原本由于国际法“碎片化”的特性,对于条约的解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在任何一个国际法领域都不罕见,但是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由于基本不存在常设仲裁庭,又不具有统一且权威的解释机构,经年累月这一问题愈发凸显。这就引发国家和学界都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当性产生担忧。
(一)条约解释缺乏一致性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不同的仲裁庭对相同或相似条款的解释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的情况屡见不鲜,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Frank将这些条约解释不一致的情形分为三种类型:(1)事实、当事方相同,投资权利相似;(2)商业情形和投资权利均相似;(3)不同当事方、不同商业情形,投资权利相同(4)See Susan D. Franck,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Privatizing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Inconsistent Decisions,” (2005) 73 Fordham Law Review1521, pp.1521-1625.。而Schreuer列举了四个容易引发解释冲突的问题,即:(1)“所有与投资有关的争议”或“任何与投资有关的法律争议”;(2)保护伞条款;(3)等待期;(4)最惠国待遇条款(5)Christoph H. Schreuer,Diversity and harmonization of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30 Years on, (Leiden: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 2010), p.145.。从这些学者的研究中不难推断,既然仲裁庭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下对投资条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那么其中必然有一部分解释在一定程度或完全违背了该投资条约文本原本的含义,同时也增加了东道国预期之外的义务。
以最惠国待遇条款为例,有关其适用范围的问题,如是否适用于等待期,众多的仲裁庭尚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在Wintershall v. Argentine案中,仲裁庭认为本案德国与阿根廷的BIT第3条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并没有提到有关投资以及相关活动的待遇,而第4条中列举了最惠国待遇所适用的事项,因此既然第4条已经列举了适用最惠国待遇的事项,那么第10条规定的等待期就不适用最惠国待遇(6)WintershallAktiengesellschaft v. Argentine, ICSID Case No. ARB/04/14, Award (8 December 2008), para.165.。即最惠国待遇只适用于实质性的待遇问题,而不适用于程序性问题。而同样针对德国与阿根廷的BIT中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的解释,Daimler v. Argentine案的仲裁庭给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该仲裁庭认为最惠国待遇也应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7)Daimler Financial Services AG v. Argentine, ICSID Case No. ARB/05/1, Award (22 August 2012), para.213.。针对相同的BIT条款,两个仲裁庭却给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在Gas Natural v. Argentine案中,仲裁庭认为:“除非BIT的缔约国或某一特定BIT的缔约国就可能产生的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否则应将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理解为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8)Gas Natural SDG, S.A. v. 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0,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Preliminary Question on Jurisdiction (17 June 2005), para. 49.。而在Plama v. Bulgaria案中,仲裁庭却认为除非最惠国待遇条款明确表明缔约国有意将其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否则不得引用其他条约中的全部或部分争端解决条款(9)Eg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v. Bulgaria, ICSID Case No. ARB/03/2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8 February 2005), para. 203.。投资仲裁裁决虽无拘束力,仲裁庭也没有依照先例判决的要求,但是实践中,仲裁庭往往会大量援引先例判决中的观点。这就不得不让人担忧,关于某一条款解释的分歧将越来越大。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建立在国家和投资者的信任之上,如果不能保证对相同或类似条约的解释具有相对的一致性,裁决的公正性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此外,东道国承担的条约义务的范围和性质都变得模糊,也就无法准确预测其行使主权时是否会违背在条约下的义务,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使就会受到掣肘。
(二)仲裁庭应用条约解释规则的任意性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的解释规则是目前公认的条约解释规则。早在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院于“领土争端案”中就明确了VCLT所编纂的条约解释规则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10)Territorial Dispute (Libyan Arab Jamahiriya v. Chad), Judgment, ICJ Reports 1994, pp. 20-21, para. 41.。而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ICSID最早于1990年就适用了VCLT第31条的解释规则。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ICSID裁决涉及VCLT解释规则的适用,适用VCLT解释规则已成为主流(11)张乃根.条约解释的国际法(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827.。但是,仲裁庭在具体解释条约时却并非完全依照VCLT的解释规则,有的仲裁庭甚至不适用VCLT解释规则,又或者仅部分采取VCLT的解释方法(12)张乃根.ICSID仲裁的条约解释:规则及其判理[J].经贸法律评论,2018,(6):58.。从一些国际投资争端案件来看,仲裁庭适用VCLT解释规则具有很强的任意性,甚至同一案件中解释某一条款时适用VCLT解释规则,而解释其他条款时又闭口不提VCLT解释规则(13)如Ronald S. Lauder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final award (3 September 2001).。同时,尽管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适用VCLT解释规则占据主流,仍不乏一部分仲裁庭完全不考虑VCLT解释规则,转而参考其他的解释规则,如公平公正、合理性、合法期望等解释原则或规则(14)如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v. Republic of Bulgaria, ICSID Case No. ARB/03/2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8 February 2005). Joseph Charles Lemire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6/18, Award (28 March 2000).。由此可以看出,仲裁庭对于VCLT解释规则的适用不过是浮于表面,每个案件的仲裁庭都有权选择自己认可的解释规则,因而可以认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对于条约解释并没有一个统一而确定的解释规则。由于国际投资条约是国家之间的条约,属于国际公法的范畴,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也应参照国际公法的规则进行。因而,除非双边投资条约另有规定,仲裁庭应当像解释任何国际公法的条约一样,严格按照条约解释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即VCLT规则,来解释国际投资条约(15)UNCTAD. Interpretation of IIAs: What States Can Do. Advance unedited version. No.3 December 2011, p.2.。
仲裁庭在解释条约时任意性的另一大体现就是大量援引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VCLT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第2款规定:“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虽然VCLT未直接将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明确罗列在解释工具之中,但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司法判例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可以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而在裁判时被适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被认为是对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说明(16)王虎华.国际法渊源的定义[J].法学,2017,(1):3.,仲裁庭引用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已有了足够的理由。不过,正如《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规定了法院判决除了对当事国及本案外没有拘束力那样,绝大部分的仲裁庭都否认先例判决的拘束力。然而,仲裁庭在对先例判决在条约解释中的地位大多保持缄默的同时,却又大量援引先例判决佐证其观点,以Daimler v. Argentine案的裁决书为例,仲裁庭意见部分援引的案例来源包括ICSID、国际常设法院、海牙国际法院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庭,可谓无所不包。一些仲裁庭在推导BIT中的法律概念时甚至主要依靠先例判决而非条约文本,形成实质上的“法官造法”(17)李庆灵.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缔约国解释:式微与回归[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5):134-135.。不可否认,由于先例判决对于一些相似或相同的条款作出过解释,为了促进法制的一致性,也因为争端双方意见中就会大量引用先例判决,仲裁庭援引先例判决的做法无可厚非,但是仲裁庭将先例判决中的结论直接作为其解释的正当性依据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援引学者著作时,《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将援引的学者著作限定为“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但显然仲裁庭并不受此限制,仲裁庭不仅将国际公法评论员的报告和法律草案囊括其中,甚至还将一些先例判决中与裁决意见不同的少数派仲裁员意见加以引用(18)如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 v. The Republic of Paraguay, ICSID Case No.ARB/07/29,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2 February 2010),para.181.。一项统计表明,在98项裁决书中,ICSID其他仲裁庭的裁决是援引最多的参考文献,占了全部解释性引用的38%,而援引的学者著作的数量有73项,占到了全部解释性引用中的16%(19)Fauchald Ole Kristian, “The Legal Reasoning of ICSID Tribunals—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8) 19 Europea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01, p.315.。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种观点,即在仲裁范围内投资条约的解释过程主要是仲裁员和学者之间的对话,因为仅这两种引用就占全部解释性引用的一半以上(20)Gordon, K. and J. Pohl, “Investment Treaties over Time—Treaty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2015/02, OECD Publishing, p.14.。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只有在用于确定法律原则时方能适用,也就是说,两者不可单独、直接用于解释条约的条款。而VCLT中虽未将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列入其中,但两者显然也能归于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只是其只能在根据第31条得出的结论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才能被援引。显然,从国际公法的角度,大量仲裁庭将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作为单独的解释工具进行解释的行为是不合理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仲裁庭不仅大量引用先例判决或学者著作,更对其引用的原因不作说明。这样一来,仲裁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向性任意寻找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最终裁决的公正性,即便仲裁庭不存在偏向性,过分依赖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的做法也严重简化了条约解释的过程。
(三)仲裁庭对条约目的的误读
缔结投资条约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于资本输入国(东道国)对于外国资本的需求,因而注重外商投资环境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出于资本输出国对本国海外投资者的保护。然而投资条约通常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很少涉及东道国权益的维护。例如,在中国-孟加拉BIT的序言中就声明“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而对于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并未提及,只在具体条款的第4及第5条才有所规定。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有些仲裁庭会参照投资条约序言来确定条约的目的,并据此推断对投资条约的解释就是要有利于投资者(21)张生.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条约解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70.。如在Siemens A.G v. Argentine案中,仲裁庭认为根据投资条约序言中反映的目的,即保护和促进投资,就可以明确看出缔约国的目的(22)Siemen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3 August 2004),para.81.。在解释条约用语“公平”“公正”时,该案仲裁庭结合词的原意和条约的目的,认为这些用语是指“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对待,有助于促进和保护外国投资和刺激私人积极性”(23)Siemen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Award (6 February 2007),para.290.。这样的解释方式片面强调了投资条约对于投资者的保护,甚至罔顾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和其他的条约义务,歪曲了东道国缔结投资条约的初衷。很难想象,一国会为了保护外国投资而牺牲本国的公共利益。投资条约缔结的目的是复杂的,绝不是条约序言中的寥寥数语就能表达完整。在Saluka v. Czech案中,仲裁庭就指出保护外国投资不是投资条约的唯一目标,而是与鼓励外国投资和扩大和加强各缔约国的经济关系这一总目标下的一个必要因素。通过解释的方式片面夸大保护外国投资可能反而会破坏加强双方经济关系的总目标(24)Saluka Investments B.V. (The Netherlands) v. The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17 May 2006), para.300.。
VCLT第31条第1款规定:“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和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意解释”,而第2款又规定:“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可以看出,VCLT并没有将条约序言部分等同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而是将序言作为上下文的一部分。仲裁庭将序言的内容等同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做法就是将序言作为上下文的全部,这会导致在解释一些模糊的条约用语时,得出过于宽泛的解释。后续的仲裁庭更会通过援引先例判决的形式,将这一不严谨的解释结论变得根深蒂固。如对公平公正条款的解释,在CMS v. Argentine案中,仲裁庭认为一个稳定的法律和商业环境是公平公正条款的重要因素(25)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18, Award (12 May 2005),para.274.。随后的Duke Energy v. Ecuador案中,仲裁庭就参考了CMS v. Argentine案在内的多个涉及公平公正条款的案件,认为“稳定的法律和商业环境是公平公正条款的重要因素”这一解释形成了国际法中公平公正条款的新标准(26)Duke Energy Electroquil Partners &Electroquil S.A. v.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 ARB/04/19, Award, (18 August 2008), para.339。
笔者认为,仲裁庭将投资条约序言中保护投资的表述作为投资条约的全部或部分目的都是不合理的。投资条约序言中对于保护投资的表述一般非常模糊,这是因为保护和促进投资可以通过多种政策形式进行,序言中不可能完整地列举缔约国愿意为保护和促进投资采取何种措施。同样,缔约国在序言中也不可能明确列举自己愿意为了保护和促进投资放弃全部或部分的管理权。一般而言,放弃国家主权权利是需要国家通过明示放弃而非从一些模糊的语句中就简单推理出所谓的“默示放弃”。投资条约序言中“保护和促进投资”这样模糊的表述不能等同于缔约国为了保护和促进投资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也不能推导出缔约国愿意为此放弃自身的主权权利。更何况在投资争端解决的背景下,由临时组成的仲裁庭裁定国家“默示放弃”主权权利的行为更是不合理。正确解读投资条约目的的做法应当是遵循国际公法中关于解释条约的习惯规则,广泛地结合条约文本和其他能够确定条约目的的外部因素,如缔结条约过程中协商的文件,最终谨慎地推导出缔约国的目的和宗旨。
二、投资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不一致的原因
虽然投资条约数量的急剧增加反映了国际投资法的蓬勃发展,但从第一个BIT诞生至今仅仅过了60年的时间,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更是只3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国际投资法仍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最初,由于国际投资大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入资本,出于对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的不信任,为了平衡因国家在司法、行政等方面具有的优势而造成与投资者地位的极度不平衡,才设计出了如今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纵观国际法各个领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争端双方为国家和私人的制度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探究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不一致的成因也应当从国际投资争端的特殊性着手,其中不仅包括投资条约的缺陷,也包括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缺陷。
(一)投资条约条款规定模糊且具有差异性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仲裁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投资条约,不论仲裁庭采取何种的解释规则,也不能脱离投资条约的文本。理论上,只要投资条约的文本措辞足够具体,仲裁庭解释时自由裁量的空间就极小。但自1959年第一个投资条约诞生至今,投资条约在文本上变化并不大,只是从寥寥数条规定增加至十数条规定。相较于其他国际公法领域的条约抑或是WTO的相关条约,如GATT还包括了对条约中的许多条款作了大量说明和补充的附件,在条款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投资条约的规定较为笼统。从投资条约的具体规定来看,一些重要的条款往往都采用了较为模糊的措辞,如“投资待遇条款”,在1982年的中国-瑞典BIT中规定:“缔约各方应始终保证公平合理地对待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27)《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2条第1款。,2001年的中国-荷兰BIT中又规定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享受公正与公平的待遇。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应享受持续的保护和保障”(28)《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荷兰王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3条第1款。,而2014年中国-加拿大BIT中规定为“任一缔约方应按照国际法,赋予涵盖投资公平和公正待遇并提供全面的保护和安全”(29)《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4条第1款。。同一条款采取了“公平合理”“公平公正”和“公平公正并全面”三种措辞,并且对于这三种措辞并没有任何说明。诚然,条约用词的模糊化是一种常见的缔约技巧,国际条约的缔结过程往往十分繁琐,耗时极长,过于具体的用词反而不利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模糊的措辞有助于缔约国求同存异。特别是投资条约,缔约国双方都希望其尽快生效,助力于双方经济的发展。但是,在重要条款上采取模糊措辞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者和国家难以取得一致的理解。事实上,如“公平公正”一词的解释,多次出现在投资争端案件之中,但仍没有一致的意见,甚至在学界也从未取得过共识。不同的仲裁庭基于不同的案件事实,对这些模糊的措辞采取不同的解释,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投资法条约绝大部分都是双边条约,而不同发达国家又推出了各自的投资条约范本,尽管不同范本的内容趋同,但其中措辞的差异性仍可能导致在解释这些条约时理解的不一致(30)刘笋.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问题及其解决[J].法商研究,2009,(6):141.。由于每个国家会签订大量的BIT,其中必然包含了根据不同的范本演变而来的BIT,导致了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变得复杂。以中国为例,中国-瑞典BIT、中国-荷兰BIT和中国-加拿大BIT文本采用的措辞各不相同,目前,中国签订的BIT共有104项(31)参见商务部条法司官网,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访问时间2020年3月30日。,这种BIT文本之间措辞不同的情况绝不在少数。
国际条约在措辞上采取模糊化的处理并非国际投资条约独有的特性,但是由于投资条约双边化严重,条约之间的差异化随着庞大的条约数量剧增,加之仲裁庭往往是临时组成,对条约的解释就更加五花八门。
(二)VCLT条约解释方法的固有缺陷
VCLT中将“条约”定义为“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协定”(32)《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a项。,所有的国际条约都是以文字为载体所呈现,文字在为条约内容提供了确定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如容易产生歧义、涵摄能力有限等。条约中的术语一旦确定之后,其含义就会受限于缔约当时的意义,对于旨在长期合作关系的条约,文字意义的局限无法包容未来的发展。因此,条约的解释需要赋予条约术语新的含义(33)姜世波.条约的动态解释方法研究——兼及法律修辞在法律方法体系中的定位[J].法律方法,2013,(2):320.。VCLT中规定的解释方法着力于追寻文本“通常的含义”,即注重文义解释的方法。然而,面对一些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术语,如“公平”“公正”等,基于文义的解释存在明显的缺陷,容易受到解读方式和立场的影响,特别对于投资条约而言,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会对文本产生歧义化的解读。虽然VCLT解释方法需要考虑“上下文”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但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义解释,如果在解释对象的理解上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即便考察该条约相关的其他条约或法律文书,也只会陷入僵局(34)漆彤,窦云蔚.条约解释的困境与出路——以尤科斯案为视角[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1):66.。
在文义解释困难重重的背景下,目的解释似乎是最可靠的方式。一方面,条约宗旨是缔约时双方就达成的合意,在双边条约只有两个当事方的情况下,分歧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目的解释对文义解释的依赖程度较低。VCLT解释方法需要考虑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也是将目的解释的方法纳入其中。但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目的解释的方法存在很大问题。由于投资条约涉及国际间的投资保护,而世界的经济形势变化极快,缔约的目的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济的变化而改变,一味追求缔约时原始的目的和宗旨并不合理,其显然不符合当下投资者的认知。而目的解释中还有一种动态解释(dynamic interpretation)的方法,即在案件裁决过程中,根据当前的客观情势及未来发展的需要,赋予条约文本中特定概念新的内涵(35)姜世波.条约的动态解释方法研究——兼及法律修辞在法律方法体系中的定位[J].法律方法,2013,(2):315.。通过动态解释的方式,可以确保条约中的权利义务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条约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用动态解释的方法探求投资条约当下的目的和宗旨似乎最为合理,也能平衡投资者和缔约国之间的权益。然而,尽管仲裁庭受到缔约国授权,作为有权解释的解释主体,但显然也不能代替条约的缔约方,对条约的目的作出新的解读。否则,由同一投资条约引发的数个投资争端案件又可能通过动态解释的方法得出数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目的,这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
(三)缔约国制约不足
国际常设法院(PCIJ)曾指出:“对一项法律规则作出权威解释的权利只属于有权修改或废止该规则的人或机构。”(36)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Jaworzina, Advisory Opinion, 1923, P.C.I.J., Series B, No. 8, p. 37.国际投资条约中,缔约国是条约的起草者,拥有修改或废止条约的权力,即便各国都将在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解释任务委托给了仲裁庭,但并不意味着缔约国就失去了解释条约的权力。理论上,缔约国仍可以澄清其真实意图,并就如何正确解读其条约发表权威声明。因此,国际投资条约的解释不是仲裁庭的独角戏,缔约国和仲裁庭在条约解释方面应当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由缔约国为条约解释提供指引,而仲裁庭只在特定情况下获得解释条约的授权,双方共同承担了解释条约的责任(37)Gordon, K. and J. Pohl, “Investment Treaties over Time—Treaty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2015/02, OECD Publishing, p.13.。然而,事实是各国往往忽视了自身在解释国际投资条约方面的作用,将解释投资条约的任务完全交给了仲裁庭(38)UNCTAD. Interpretation of IIAs: What States Can Do. Advance unedited version. No.3 December 2011, p.3.。OECD对一项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对那些影响自身条约义务或争端解决程序的重要问题选择了沉默(39)Gordon, K. and J. Pohl, “Investment Treaties over Time—Treaty Practi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OECD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2015/02, OECD Publishing, p.13.。如果缔约国在关键问题上不提供或不明确地提供指引,那么也很难苛责仲裁庭寻求其他途径解释条约的行为。
理论上,缔约国制约仲裁庭解释权的手段有很多,如监督机制、限定仲裁庭管辖案件的范围、引入岔路口条款、规定仲裁庭适用的法律、构建缔约国共同决策的机制等(40)李庆灵.中国IIA中国际投资仲裁庭的权力约束机制研究[J].西部法学评论,2016,(1):117-121.。一旦发现仲裁庭滥用解释权,全体缔约国可以施加限制甚至撤回授权,但实际上这些制约效果并不理想(41)李庆灵.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缔约国解释:式微与回归[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5):137.。这是由于双边投资条约的数量巨大且使用的版本比较陈旧,要逐一在条款中设置制约机制就需要修改条约,这无疑是个庞大且耗时的工程。另外,当投资争端发生时,缔约国双方的利益很可能产生分歧,此时要双方联合制约仲裁庭的解释权也有些过于理想化。
三、投资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规则的完善
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成因复杂,但最核心的问题绕不开仲裁庭在解释投资条约时解释规则的完善。如果只从外部改变现行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诸如建立上诉机制或是投资争端法庭,而不完善解释规则的运用,届时只会加剧裁决的不一致问题。更何况现行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仍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受投资者信赖的方式,要建立新的替代方案绝非一蹴而就。需要认识到的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将投资条约的解释权授予仲裁庭是缔约国的一种兜底性、妥协性的作法,把原本适用于私主体的仲裁模式套用到具有公法性质的争端中,导致了仲裁庭在行使解释权时虽然具有合法性但却无法解决缺乏合理性的问题(42)姜曦.条约的不当解释——以条约解释主体为视角[J].社会科学战线,2018,(10):266-267.。故而,完善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需要补足仲裁庭行使解释权时的合理性。
(一)恰当运用VCLT第31条
在投资争端解决中,虽然大部分仲裁庭都声称运用VCLT规则,但实际上对于VCLT规则的运用十分随意,往往只通过简单的文本解释方法得出结论,而一旦仲裁员试图超越文本解释方法转而寻求其他解释方法时,常常又容易过于扩大化解释(43)刘笋.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不一致性问题及其解决[J].法商研究,2009,(6):144.。这一方面是因为VCLT规则对于投资争端解决的约束性较低,适用VCLT规则解释条约仅仅是一种习惯国际法。另一方面,VCLT规则比较原则性且内容不具体,对仲裁庭的引导相当有限(44)孙南申.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J].国际商务研究,2019,(2):57.。但是,VCLT规则作为广泛认可的条约解释方法,仍是目前无法替代的。
劳特派特曾言:“法官的责任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探求缔约方的意图。”(45)Hersch Lauterpacht,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nes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YBIL 26, 1949), p.83.条约解释更多时候是一门艺术而非精准的科学,因此,更需要规则的约束。VCLT解释规则将有关条约解释的一般性规则汇编起来,就是为了防止裁判者在解释条约时偏离缔约的目的。正确地运用VCLT规则,可以很大程度上限制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裁决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VCLT第31条项下的解释工具不应被视作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互相作用、有机结合的系统性工具,不存在适用的前后次序。实践中,许多仲裁庭过分依赖于VCLT第31条第1款的规定,按照条约的通常含义直接得出结论(46)Fauchald Ole Kristian, “The Legal Reasoning of ICSID Tribunals—An Empirical Analysis”, (2008) 19 Europea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01, p.314.。如Rompetrol v. Romania案中,仲裁庭在解释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时,就直接根据VCLT第31条第1款,而不顾其他诸如习惯国际法规则等解释工具(47)The Rompetrol Group N. V. v. Romania, ICSID Case No. ARB/06 /3 (6 May 2013), para. 197.。还有部分投资仲裁庭通过VCLT第31条第1款中的“目的和宗旨”,简单地得出应当保护投资者的结论,其本质就是对于VCLT第31条下解释工具的错误运用。此外,需要指出,仲裁庭还错误地将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混同。VCLT第31条第1款原文所指的“目的(object)”和“宗旨(purpose)”应当予以区分,同时纳入解释条约条款时的考量。缔约国签订条约是手段,而需要该条约解决的问题才是缔约国的宗旨。投资条约的目的(object)是保护和促进投资,而其宗旨(purpose)应当是促进缔约国之间的经济发展以及缔约国本国福利的最大化(48)Anne van Aaken. “Interpretational Methods as an Instrument of Control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2014) 108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196, p.197.。根据VCLT第31条的规定,要探求缔约国的宗旨,应当着重考虑与条约有关的任何协定、文书、嗣后实践以及相关国际法规则。因此,仲裁庭应当首先将投资条约与相关的其他任何协定、文书等建立联系,从而组成上下文。
Aguas v. Bolivia案中,仲裁庭将VCLT解释规则概括为三步,首先根据条文文本和一般含义解释,其次根据条约上下文解释,最后根据条约宗旨和目的解释,循环往复直至得到合适的解释(49)Aguas del Tunari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2/3. Decision on Respondent’s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October 21 2005), p. 20.。同时,仲裁庭指出,VCLT解释规则并不侧重以上任何一种解释方法,对于一个条款的解释需要结合其上下文和条约的目的、宗旨,考虑其通常意义。然而,该案仲裁庭归纳的解释方法仍忽视了VCLT第31条第3款的作用。VCLT第31条第3款c项中就要求了条约解释时应将任何有关的国际法规则纳入上下文一并考虑。在条约解释中,“其他国际法规则”的重要功能甚至被学者称为“一栋建筑的万能钥匙”(50)Campbell MacLachlan, The Principle of Systematic Integration and Article 31(3)(c)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2005)54 Int’l & Comp. L.Q. 279, p.281.。但这一如此重要的规则却往往被仲裁庭忽略。国外学者在对229份投资仲裁裁决的统计分析中表明,仅有58个仲裁庭将其他国际法规则作为解释工具,与之相对的是101个仲裁庭引用了学者著作(51)Trinh Hai Y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ies (Brill Nijhoff, Vol.7, 2014) , p.106.。国内学者在对涉及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的投资争端案件的研究中,对28个案件中的解释方法进行了统计,仅有1例案件适用了其他国际法规则(52)朱明新.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表现与实质——基于条约解释的视角[J].法商研究,2015,(3):177-178.。可以说,这一重要的解释工具被严重忽视了。投资条约并不是独立的法律规范,而是属于一般国际法规范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当投资条约约定不明确时,可以使用“其他国际法规则”进行解释。甚至可以说,在解释投资条约时不应当孤立地只考虑投资条约,而是应当结合其他国际法规则加以解释。Philip Morris v. Uruguay案是少有的利用“其他国际法规则”进行解释的案例,仲裁庭在解释间接征收条款时就根据VCLT第31条第3款c项,援引了各种条约、相关文件和判例以证明警察权学说这一习惯国际法的存在,认为东道国在行使警察权时应得到充分的尊重(53)Philip Morris Brands Sàrl, Philip Morris Products S. A. and Abal Hermanos S. A. v. 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 ICSID Case No. ARB/10/7, Award(July 8, 2016), p.65.。在解释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时,该仲裁庭也结合了VCLT第31条第3款c项,考虑习惯国际法的演进。公平公正待遇的概念一直以来都非常模糊,按照字面意思很难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因而需要结合习惯国际法进行解释。但是,学者也指出应当区分两种情况:第一,当条约用语模糊,条约与习惯国际法又不冲突时,适宜引入习惯国际法;第二,当条约与习惯国际法存在争议时,引入习惯国际法反而会引起冲突(54)王彦志.国际投资仲裁中公共健康保护的条约解释进路——以Philip Morris v. Uruguay案中VCLT第31条第3款c项的适用为视角[J].当代法学,2017,(6):156.。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VCLT第31条项下的解释工具不能单独作为解释的依据,否则容易导致有偏颇的结论。
综上,目前投资争端解决中,对于VCLT第31条解释规则的运用过于简单化,其中大量解释工具远远未被仲裁庭用尽。因此,仲裁庭在运用VCLT规则方面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可以预见如果仲裁庭完整地运用VCLT第31条的解释规则,采用多种解释工具进行解释,其裁决一致性一定会有所改善。
(二)运用VCLT第32条进行印证
VCLT第31条和第32条并不是单一的解释方法,而更像是一个方法系统(55)张生.国际投资仲裁中条约解释方面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J].国际经济法学,2014,(1):152.。故而,仲裁庭应当完整地运用VCLT的这两条解释规则,认真探求缔约国的真实缔约目的,综合各种因素,平衡缔约国和投资者的权利义务。VCLT第32条解释之补充资料的作用就是证实适用第31条所得的结论,以及当根据第31条得出的解释意义不明或明显谬误时,确定其意义。这就意味着,第32条和第31条应当是互相印证的,而不是仅仅通过第31条项下的解释工具就能得出合理的结论。试想,如果仲裁庭只依据第31条,根据文本和一般含义进行解释,很可能就先得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结论而不需要再结合其他的解释工具。Aguas v. Bolivia案仲裁庭对于第31条和第32条的适用上,就认为应当先依据第31条考虑文本的通常意义,然后根据第32条进行解释以印证,最后才能将解释应用于本案(56)Aguas del Tunari v.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2/3. Decision on Respondent’s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October 21, 2005), p. 20.。在WTO中的案件也表明,VCLT第32条作为解释之辅助手段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时因其可以证实根据第31条所得的解释结论,也具备证据价值(57)胡建国.安提瓜诉美国赌博案评析[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7,(2):268.。因此,在解释国际投资条约时也应当遵循VCLT第31条和第32条的先后顺序进行印证。
在厘清VCLT第31条和第32条的适用顺序之后,需要明确第32条规定的解释工具在条约解释中的作用,即哪些解释工具是有约束力的以及哪些解释工具仅具有辅助性。例如,仲裁庭在解释投资条约时大量引用的先例判决或学者著作应当被纳入辅助性解释工具,然而仲裁庭的这种作法着眼于学者和仲裁员对条约条款意义的理解而忽视了能够直接反映缔约国缔约目的的文件。先例判决和学者著作并不是探求条约条款意义的独立来源。
VCLT第32条中所明确列举的“条约之准备工作”和“缔约之情况”是能够反映缔约国宗旨的有力证据。虽然有学者指出,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取条约的准备材料,如果片面依赖条约准备材料,对于投资者显然不公平,应当防止缔约国根据准备材料提出一种不同于通常含义的解释规避应当承担的义务(58)张生.国际投资仲裁中条约解释方面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4,(1):154.。对此,VCLT第31条第4款所提出的经确定当事国有某种原意时应具有特殊意义,这里的当事国原意并不是由一国单方面可以提出,而应当是由全体缔约国共同确认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投资者母国。很难想象投资者母国会连同东道国作出明显损害本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解释。在利用VCLT第32条规定的“条约之准备工作”进行解释时,还需注重条约准备工作所涉及资料的范围,由于VCLT第32条同时具有独立价值和证据价值,在独立价值意义上,其范围应当限于具有多边性质的准备资料;在证据价值意义上,其范围则可以包括单边来源的资料(59)胡建国.安提瓜诉美国赌博案评析[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7,(2):269.。而“缔约之情况”包含的内容就更为广泛,包括缔约时的谈判、历史背景等,有学者认为其涵盖了所有与缔结条约有关并影响其内容的因素(60)Richard K. 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43.。显然,条约的缔结情况在理解国家缔约目的,从而解释那些含义模糊的条款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缔约情况推导出缔约国在特定背景下的缔约目的,显然比单纯从条约序言得出结论来得更为严谨。即便这样一来会加大仲裁庭解释工作的负担,但是,仲裁庭所承担的解释工作本质是来源于国家对条约的解释权,这就不得不要求仲裁庭以审慎的态度对待。
(三)适用限制性解释原则兜底
限制性解释原则(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是一项具有争议的条约解释原则,意指当遇到条约用语模糊时,应当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而作出使承担义务的国家负担较轻的解释(61)Thomas W. Walde, Interpreting Investment Treaties: Experiences and Examples, Christina Binder et 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for the 21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34.。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早期就常常使用限制性解释原则,如在“荷花号”案中,常设国际法院认为由于国际法的约束力来源于国家自愿通过条约或惯例的方式接受约束,因此不能假定对国家的主权有所限制(62)S.S. Lotus (France v. Turkey), Judgment (7 September 1927), PCIJ Series A, No 10 (1927), para. 44.。不过,国际法院一方面在判决或咨询意见中承认这一原则,一方面也保持谨慎的态度,常以条约文本明确或需考虑其他条约解释的方法而拒绝适用限制性解释原则。有的裁决甚至直接言明不能在解释条约时适用该原则(63)张生.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条约解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60.。在尼加拉瓜准军事行动案,国际法院认为:“在国际法中,除了有关国家可能通过条约或其他方式接受的规则外,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限制一个主权国家的军备水平,而这一原则对所有国家毫无例外都是有效的。”(64)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6, para. 269.但在2009年的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在对限制性解释原则进行分析时,认为两国的《界限条约》没有规定尼加拉瓜对圣湖安河的主权和哥斯达黎加航行权之间的等级关系,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定应对哥斯达黎加的航行权进行限制性解释(65)ICJ, Disputes Regarding Navigational and Related Rights (Costa Rica v. Nicaragua), Judgement of 13 July 2009, paras. 47-48.。而在2010年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独立声明的咨询意见中又采用了限制性解释原则,国际法院表示:“一般国际法中没有任何对于宣布独立行为的禁止,因此该独立声明不违反任何国际法规则。”(66)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2010, para.84.这一系列判决也说明,限制性解释不是条约解释的一般原则,不能优先适用(67)Richard Gardiner, Treaty Interpretation (paperbac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xvii.。
虽然限制性解释原则在国际法中有一席之地,但仍饱受诟病。一方面是由于限制性解释的基石在于对国家主权的敬意(deference),然而一国行使主权过程中又可能对另一国的主权有所侵犯,这就使得国际法规则更偏向于限制国家主权而非放任。另一方面是由于VCLT关于条约解释的第31条和第32条已经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可,而其中并未规定有关限制性解释原则的内容。在解释条约时,似乎也没有理由不适用VCLT规则,转而优先考虑限制性解释原则。劳特派特认为,即便适用限制性解释原则,也仅在两种情况下:一是主张进行限制性解释的一方需承担举证责任,并且是明确的证据;二是该解释必须是善意的(68)H. Lauterpacht, 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nes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49), p.51.。
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限制性解释原则的运用虽少,但也能寻得踪迹。SGS v. Pakistan案中,仲裁庭在解释“保护伞条款”时,提出要采用存疑从轻(in dubio pars mitiorestsequenda)原则(69)SGS v. Pakistan, ICSID Case No.ARB/01/13,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6 August 2003, para.171.。根据这一原则,如果条约用语意义不清,则应选择对承担义务一方较不繁重的解释,或较不干涉一方领土和主权的解释,或较不涉及对当时各方的一般性限制的解释(70)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ume 1, Peace,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2), p.1278.。有学者就根据限制性解释原则提出了主权主义(sovereigntist),认为对任何限制主权的条款都必须作限制性解释,而且此类限制主权的条款须清晰和直接(71)Van Harte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and Public La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p.132-135.。还有学者依据限制性解释原则提出了无限制推定原则(no-restriction presumption principle),认为可以将无限制推定原则作为VCLT第31条和第32条的补充(72)Trinh Hai Y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ies (Brill Nijhoff, Vol.7,2014), pp.147-153.。然而,实践中大部分的仲裁庭都不认可限制性解释原则,因为这种解释会在条约用语模糊不清时作出有利于东道国的解释,不符合双边投资条约中保护和促进外国投资的目的和宗旨(73)张生.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条约解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62.。许多仲裁庭明确表示对公约中的仲裁条款不能作限制性解释,亦不能作扩张性解释(74)如Mondev International Ltd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CSID Case No. ARB(AF)/99/2,Award (11 October 2002), para.43. Siemens AG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2/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3 August 2004), para.81.。还有如Ethyl v. Canada案的仲裁庭认为限制性解释原则已经被VCLT第31条和第32条所抛弃(75)Ethyl Corporation v. Government of Canada, UNCITRAL, Award on Jurisdiction, 24 June 1998, paras.55-56.。
仲裁庭对于限制性解释原则的采纳各执一词,但需要认识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不同于国际公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涉及的是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并不会侵犯其他国家的利益。再者,投资者的权利是通过投资条约赋予的“特权”,而非基本人权,因此进行限制性解释也不会侵犯投资者的基本人权(76)Trinh Hai Y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vestment Treaties (Brill Nijhoff, Vol.7,2014), p.150.。换言之,国际公法领域运用限制性解释原则的弊端在国际投资法中并不明显。因此,通过限制性解释原则作为VCLT第31条和第32条的补充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仲裁庭必须在用尽VCLT第31条和第32条的解释方法后,得出的结论依然模糊不清。否则,限制性解释原则很可能导致过于强调尊重国家主权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将限制性解释原则作为VCLT第31条和第32条的兜底方式,但由于VCLT中并未纳入该原则,而该原则也存在较大争议,要普遍运用到实践中可能缺乏有力的依据,除非投资条约中明确说明在解释条款时,如无法得出明确合理的解释,需选择东道国负担义务较轻的解释。
四、结语
国际投资争端涉及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对投资条约的解释本质上是在平衡国家维护本国公共利益的权利与保护外国投资的承诺。然而,由于仲裁庭在解释条约时缺乏统一的解释方法以及过于注重保护外国投资,导致了裁决不合理的不一致性。同时,国际投资条约的发展时间较短,文本普遍又以发达国家制定的为主,发展中国家往往出于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而照单全收,导致了缺乏对投资条约解释方面的认识和控制。
为完善投资争端解决中的条约解释问题,不仅需要认识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固有的缺陷,也应当认识到VCLT规则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中的局限性。众多仲裁庭虽然宣称依据VCLT解释规则,实际上却并没有受VCLT规则的约束,对VCLT规则中的解释工具随意挑选,导致了仲裁庭解释条约时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正确的条约解释方法是引导投资争端裁决趋向一致的重要手段,缔约国可以发挥其对投资条约的权利,要求仲裁庭在解释条约时严格按照VCLT第31条和第32条的规定,用尽VCLT第31条项下的所有解释工具,随后再通过第32条的解释方法互相印证。同时,也可以考虑在用尽第31条和第32条仍无法得出明确结论时,引入诸如限制性解释原则填补VCLT解释规则的缺漏。这样不仅使裁决解释结论的说服力更强,也缓和了国家主权和私人权利保护的紧张关系。同时,由于先例判决在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适用正确解释方法的案例将通过被后案援引的方式,逐渐推动投资争端解决裁决的一致性发展,也可为国家在缔结新的投资条约或发布新的国内政策、法律时提供可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