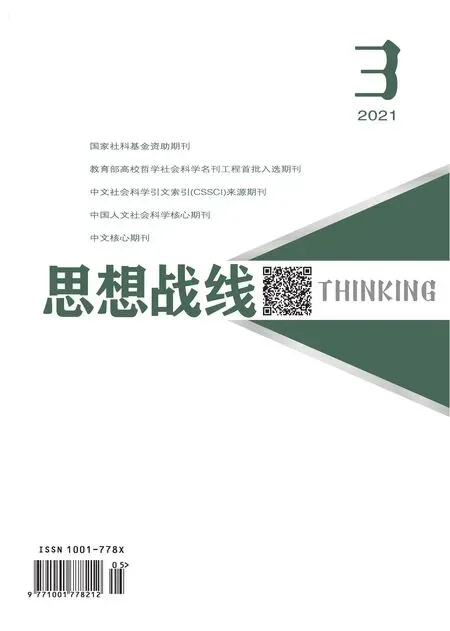重塑问题空间: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与民族志在场
刘 珩
一、当下的问题语境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当下,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格尔兹在《烛幽之光》这一本旨在探讨人类学与哲学之关系的著作中,讲过一个印第安人与透析机的故事。印第安人嗜酒如命的生活习惯与科技千篇一律的强力尴尬地对峙、相互忍受的局面,折射出我们所处的当下“凹凸不平”的现状(ragged presence)。(1)Clifford Geertz,Available Light: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80~83.文化在科技这一板块的碰撞下,似乎正在日益分崩离析。在格尔兹看来,世界由碎片构成(a world of pieces),文化已经不再是协同一致的符号和意义体系,它是时代变迁中,与其他强力碰撞挤压之后,突兀出来的众多差异。(2)Clifford Geertz,Available Light: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9-240.尽管如此,对于人类学而言,想象差异、表现差异仍然是这门学科作为科学之所在。(3)Clifford Geertz,Available Light: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ical Top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p.85.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人类学界本体论与文化论观点冲突不断的时刻,以概念的阐释来表征和通约文化差异的知识论已经遭遇多重危机,(4)Michael Carrithers,Matei Candea,Martin Holbraad,“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Motion Tabled at the 2008 Meeting of the Group for Debate in Anthropological Theory”,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事实上,在人类学界也不乏对本体论转向的质疑之声。比如哥本哈根大学的维埃认为,本体论转向的学者将社会生活扁平化,在一味强调“存在”(is)是什么的同时,忽略了社会生活中日常以及强制施加的各种权力。人类学的价值不在于将其自身倚重的民族志改造成晦涩难懂的哲学话语,民族志的作用就在于,它以一种高超的技艺,去描述、领悟且推衍出这个多元的、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但同时也是可以共享的世界所特有的主题。参见Henrik Erdman Vigh,“From essence back to existence:Anthropology beyond the ontological turn”,Anthropological Theory,vol.14,no.1,2014,pp.63~68。我们又该如何想象以及表现差异?在本体论转向的学者看来,差异既不能想象,更不能被表现和通约,它是田野调查中不能被收集的材料,(5)Martin Holbraad,“Ontography and Alterity:Defining Anthropological Truth”,Social Analysis,vol.53,no.2,2009,pp.81~82.只属于他者的不同世界(multiple worlds)。(6)Michael Carrithers,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53.如果上述观点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处理那些不能被收集的材料,从而将认识论架构下他者的“世界观”(worldviews)变成本体论架构下充满他异性的“世界”(worlds)?这一转变对于民族志的研究意味着什么?它又需要在哪些方面拓展自身的本体论视角?
当下对于人类学而言,恐怕不是一个想象异邦和差异的时刻,在格尔兹的学生拉比诺(Paul Rabinow)看来,人类学需要实践而非想象,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我们才能探寻物与物的实际联系,从而获取事实的重组形式。(7)Paul Rabinow,Designing Human Practices:An experiment with Synthetic B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p.109~164.有鉴于此,当下是一个如何通过实践重新塑造生活方式和思考习惯的时代。面对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不能像德国哲学传统那样,将科技与自然做本体论层面上的切割,必须回到当下这一问题语境,重新思考自然与文化、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8)Paul Rabinow,Marking Time: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21~25.因此,这是一个只能叫做“当下”的时代,是一个重塑问题空间的时代,是很严肃地提出问题的时代。(9)本体论转向学者之所以反复强调“严肃性”(seriousness),意在突出将物、现象以及事实当做“是什么”(“what is”)来认真对待的一种基本态度,而不是考虑运用何种概念体系将其予以再现。在这一意义上,本体论旨在严肃看待田野中所遭遇之物,严肃地看待他者以及他们真实的差异性(real difference)。参见Michael Carrithers,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75.人类学的任务就在于,将自身置于这一问题空间之中,通过实践探寻“这一空间之内现实的、新兴的以及真实的具体问题,不仅去承担其中的风险,同时也看到种种希望”。(10)Paul Rabinow,“Midst Anthropology’s problem”,Cultural Anthropology,May 17,no.2,2002,p.145.如果我们接受拉比诺对于当下的定义,确认重塑问题化空间的重要性,就应继续追问如下问题:民族志研究应该生成何种问题空间,从而将本体论转向学者重视的他异性(alterity)纳入其中予以考察?如果实践真正开启思考和探寻的起点,民族志实践应该通过何种研究路径和呈现方式,进一步拓展其在课题设计、跨领域合作、概念组合等层面的多种可能性?如果概念化是传统概念、不同学科的概念跨越时间、跨越领域的组合和重组的过程,(11)Paul Rabinow,The Accompaniment:Assembling the Contempora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129.我们又应该为民族志研究配置出何种概念化工具,以便在当下和不远的将来依然保持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借助当下经过重塑的问题语境,不妨从民族志的认识论危机开始,来思考上述问题吧。
二、民族志的认识论危机
认识论尽管探讨的是如何认识事实并加以再现,但它也关涉什么是事实这一本体论的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事实或者文化是什么往往是认识论得以形成的一个必要前提,它同时也决定着民族志呈现的方式。因此,民族志认识论包括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如何认识事实或者真实的生活,二是通过书写如何将事实作为整体予以再现,并获得一种“民族志的权威性”。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志书写,无不隐隐约约地折射出本体论向认识论“投射”的痕迹。
在古典时期的人类学著作如《金枝》《人类婚姻史》中,作者将收集到的世界各地的奇风异俗以及婚姻的样态,以自然历史般的物的分类和编纂形式予以再现,让物通过分类来呈报自身的存在。从某种程度而言,分类就是物的表现路径,就是物本身,所有学科都带有浓重的自然历史意味。(12)[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72~173页。这一时期的民族志反倒是与物最为接近,因为它没有掺入过多的概念、符号体系等中介形式对“物”“生活”这一类事实或者表象加以阐释,也并不尝试将其作为一个事实或者功能的整体予以呈现,只是提供了一个将“物与物并置在一起的清晰空间”,一切都不证自明。(13)在福柯看来,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具有自然史的编纂和分类的性质,观察(目光)显然并不重要。如果说观察还在起作用,那也不过是使语言尽可能接近目光,而被注意的物尽可能接近词。因此,摇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可以完全专注于语言,因为在一个词毫无中介地作用于物本身的分类体系中,从语言中同样能够观察到物的存在,此时的人类学家表达了一种把一个与在生物之间确立起来的秩序相同类型的秩序引入早已强加在物上的语言。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74~175页。此处的物,就是可供分析的不同的原始群体,而语言正对应着这些群体,同时也对应着这门学科。这一时期民族志权威性的获得,一来主要依靠当时读者所处的进化论这一现实语境,二来依靠作者寻获残存于现实生活中过去的种种痕迹的能力,这些都不需要提出新的概念,这是当时通行的做法。(14)Marilyn Strathern,“Out of context:The persuasive fic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comments and reply]”,Current Anthropology,vol.28,no.3,1987,p.258.难怪费边在批判“写文化”过于明显的文学转向的时候,认为弗雷泽那一代人写的民族志更符合人种学(ethnology)以及民族志的拉丁语词源,是一种更为“纯粹的民族志”(innocent ethnography)。因为描述(de scription)这一关于是什么的书写,其原意恰恰就是要减少(de)书写活动(scription),也就是减少“表象”的痕迹。(15)Johannes Fabian,“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The Other and Anthropological Writing,Critical Inquiry,vol.16,no.4,1990,p.758.
随着描述成为一种职业行为,其全部的奥秘就在于营造一种权威性的氛围,让事实与这种权威性对应,与民族志者的田野工作对应,与写作的风格、修辞、体裁对应,与表象对应,而不是与物本身对应。一句话,存在即表象,反之亦然。将帐篷搭在特洛布里恩德人部落营地中的马林诺斯基,无疑很好地营造了这种权威性。在马库斯(George Marcus)看来,民族志者的权威性以及文本自身所获得的事实效应,取决于作者宣称自己是唯一一个通过第一手材料再现一个世界的策略……阐释和分析将另一种文化、另一个世界生动系统地再现(representation)出来,在读者看来既全面又真实。(16)George E.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1982,p.29.显然,对这一时期的民族志现实主义而言,事实取决于如何将其本身予以再现,事实的效应取决于民族志者有多大勇气对外宣称历经千辛万苦获取事实之不易,取决于如何打磨一套具有现实主义意味的术语,当然,也取决于一套阐释和分析的表征体系。
到了格尔兹领军的“阐释转向”的民族志时代,文化是什么这一本体论维度,以及如何认识文化这一认识论维度同时被整合进了“文化”这一概念。(17)Sherry B.Ortner,“Introduction:The Fate of ‘culture’:Geertz and Beyond”,Representations,Special Issue,1997,p.6.将文化界定为由符号表征的意义体系,一方面是说,人类社会不分族群在世界观、价值体系以及意义的编织等层面,所体现出来的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和共性这一事实,用文化的首字母大写和单数形式(Culture)来表示。另一方面则表明,文化不是某种抽象的秩序体系,从藏而不露的深层结构中获得逻辑,文化通过社会参与者的公共展演所借助的符号来呈现自身。要认识文化,自然要借助文化的载体——符号,考察符号如何塑造社会参与者认识、感知以及思考周遭世界的方式。众多的符号,众多的因素以及众多的社会参与者的操作和阐释,可以用文化的小写和复数形式来表示(cultures)。
格尔兹将本体论整合进文化这一概念之中,事实上是为认识论的理论建构做铺垫。首先,文化的可通约性作为人类的共性,将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之间的距离拉近了,(18)格尔兹认为,这些人类共性不但通过民族志文本将“此处”和“彼处”联系在一起,并且也传递出包括分析、解释、娱乐、不安、窘迫、庆祝、启发、震惊、托辞(excuse)、颠覆以及最终的宁静在内的共同情感体验。因此,民族志从某种程度而言既不是理论与方法,也不是职业人类学家所特有的学术氛围,而是浸润着文化共性的各种情感体验的呈现和连接形式。参见Clifford 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44.民族志现实主义所面临的我者与他者之间难以跨越的认识论和伦理差异被抹平,人类学家不再背负用西方理论架构和概念体系去描述他者的伦理负担,跨越文化边界之后宣称获取事实之不易,这一权威性来源也不复存在,因为人类学家与其研究的对象,都生活在意义建构的世界之中,都是行动的主体,他们共享一种阐释的权威性(dispersed authority)。(19)George E.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1982,p.43.其次,文化不再是受深层结构支配的认知逻辑、或者抽象的秩序体系,它指向行动者的社会展演和意义的编织这一复杂性的事实,它更具有一种精神、气质(ethos)和情感的人性光芒。格尔兹将大写的文化拆解成小写的文化认识论策略,事实上更加逼近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的存在这一现象学维度,(20)格尔兹的大写的文化,在本体论层面正对应着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的存在状态”,小写的文化,在认识论层面上则对应着海德格尔界定的在存在者层次上最近的平均日常状态。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50~52页。自然也扩展了阐释的张力。因此,只要文化作为人性的可通约性和共性这一存在形式不受到质疑,文化的本质就是认识论的,或者说人类学就是有关认识论的全部知识。
然而一旦统一于文化这一概念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相互分离,则民族志的认识论危机也在所难免。这是因为,在格尔兹的本体论架构中,所有的客体、行为、事件和关系都是概念(conception)的符号,这是第一个需要表象的层次。其次,这些概念同时又表征着包括观念、判断、态度、信仰在内的普遍的人类存在形式,这是第二个需要表象的层次。如果以普同(可通约)的人类存在作为本体,则人类学家可以观察的经过公共展演的行为或者对象,与本体之间隔着表象之表象两重障碍,如同柏拉图观念中艺术作品对理念的模仿。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基于人类价值体系的普同性,概念才能得以体现,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才能展演,之后才能被观察和阐释。然而科技时代为这一表象和模仿的逻辑提出了难题,这是因为,“在话语和概念之外,总有物(things)有待观察、言说以及学习”,(21)Paul Rabinow,The Accompaniment:Assembling the Contempora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48.总有物不依附于人类既有的观念、判断、信仰而存在,不依附于福柯所谓的由“人的有限性造成的表象的真理性”而存在。(22)[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08页。人类学要想在科技时代有所作为,就必须考察这些新兴事物的本质,进而从本体论维度,探讨这些事物是什么、为什么重要、如何重要以及我们如何认识它们的独特性以及重要性等问题。这些探讨对于哲学和人类学而言,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23)Paul Rabinow,Designing Human Practices:An experiment with Synthetic B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p.2~3.
其次,同样基于人类价值体系的普同性这一本体论,人类学无形中变成了一门宽容各种特殊性和差异性的科学,宽容意味着与研究对象之间所建立的“亲密关系”(rapport);宽容也意味着在民族志中将他者的“异趣”加以适当凸显,以便增加文本的真实性和权威性;(24)George E.Marcus and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1982,p.47.宽容也意味着在认识论层面对自己的研究计划加以自我反思、反复修改,而非设计问题,并同受访者一道通过合作来解决问题。总之,宽容在成就民族志者的美德的同时,似乎忽略了他者的存在。一门研究他者的学问,却悖论式地将他者排除在外,这是因为他者是需要宽容的对象,他者的文化可以用人类价值的普同性来通约,他性(otherness)可以简约成某种相似性,因此可以当做事实来表象。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他者并不见得希望民族志者背负如此沉重的伦理负担,他者在阐释自身文化的时候,也需要共享一种道义与责任,唯其如此,自身文化的他性才不会沦为大写文化的分子,之后被简约、被再现。更何况这一大写的文化极有可能就是西方的话语和阐释架构,大多数当代社会中的“他者”,无不对这一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保持警惕。
正因为如此,与其将他者当做事实来表象,不如将他者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当成事实来表象。与其以一种无视他异性的所谓宽容,尝试着与他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不如平等地与他者建立起一种合作(complicit)的关系。与其将民族志看作事实的表象,不如将民族志如何确定自身研究对象这一过程当做事实来表象。民族志所遭遇的上述表象危机,推动着民族志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进行转向。
三、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
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根本上而言是将格尔兹业已包括本体论与认识论为一体的文化概念,全部看作表象、翻译、中介(mediation)以及阐释的认识论体系和知识范式。本体论转向的学者相信,人类学若不进行本体论转向,永远只能是一种有关不同群体表征其世界的不同方式的研究,(25)赫纳尔认为,人类学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知识论体系(episteme),事实上是一种有关他者知识的知识论,也就是说,人类学是有关他者表征体系的再表征体系。参见Amiria Henare et al.,Thinking Through Things:Theorising Artefacts Ethnographically,London:Routledge,2007,p.9.人类学家只能站在他者的身后,越过他们的肩头去观察他们的观察,阐释他们的阐释。本体论转向之前的文化,不过是针对他者知识所建构出来的另一种知识,是公共展演的客体和行为隔着符号和概念体系的双重表象。有鉴于此,在本体论转向的代表人物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看来,人类学思想从认识论向本体论转向有两重含义,其一是需要重新复活那些长期被压制在无声和统一的自然世界中的物(objects),让其发声。其二是借助本体论这一概念,我们才能避免将土著他者的思想简约成某种光怪陆离的幻想(fantasy),或者某种知识和表征体系。(26)Viveiros de Castro,“Anthropology and Science”,Manchester Papers in Social Anthropology,2003,https://cordel.fandom.com/ptbr/wiki/III__VIVEIROS_DE_CASTRO%2C_Eduardo._2003._%28Anthropology%29_and_%28Science%29?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May 15,2020.总之,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旨在形成一套有关真理的颇为激进的替代性概念体系,绕开以追寻事实为名义的表象所惯常附加的前提,并进而倡导一种“概念的重新界定”(conceptual redefinition)的事实理念。(27)Martin Holbraad,“Ontography and Alterity:Defining Anthropological Truth”,Social Analysis,vol.53,no.2,2009,p.80.。
具体而言,为了形成有关真理的替代性概念体系,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者首先应该严肃地看待本体(ontic)和物性(materiality),其次应该严肃看待他异性(alterity),最后应该严肃地提出问题。
(一)严肃地看待本体和物性:以物释物
阿普杜拉(Arjun Appadurai)在《物的社会生活》一书中认为,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将物的世界看做是惰性和沉寂的,只能通过人以及他们的词语才能变得鲜活和生动。(28)Arjun Appadurai,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5.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依靠表象(词)来认知物本身及其变化形式。我们从不在物的存在这一维度去思考物的变化,而是倾向于将物看做是对事实(通常是西方观念中的事实)的正确或者错误的再现方式,物不过是象征体系的组成部分。埃文斯-普里查德观察到,努尔人将双胞胎看做是鸟的这一现象,成为本体论转向学者考察物性时反复提及的重要例证。努尔人认为双胞胎不是人,而是鸟,这一“错误”的观念特别符合列维-布留尔想要论证的原始思维。将双胞胎当做鸟的讹误,在早期人类学家看来,正好说明“原始思维”分不清真实与观念、主体与客体、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差别,是对事实的错误表述。然而,埃文斯-普里查德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努尔人做出这一陈述并非毫无逻辑可循,因为双胞胎通常是神灵的某种特别启示(special revelation),而鸟因为有高翔于众生之上这一特有的灵性(anima),被认为与神灵最为接近,他们都是“神的孩子”。因此,鸟成为努尔人最恰当不过的符号,用以表现双胞胎与神灵的特殊关系。(29)E.E.Evans-Pritchard,Nuer Relig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56,pp.131~132.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解释在本体论转向的学者看来,正好说明面对文化差异时(他们认为双胞胎是鸟,我们认为不是),我们所使用的各种表征体系的建构路径:以此种方式思考可能是为某种目的服务(功能主义);或许是大脑运作的特定方式(认知主义);或者是特定语境中对某种观点的解释(解释主义);或许是隐喻般的表现方式(象征主义)。(30)Martin Holbraad,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83.无论哪种方式,努尔人文化中这一最具代表性的鸟,其最为重要的作用在于将不在场者(思想、观念、态度或者抽象的实体)重新予以呈现,或者作为特定符号表征着某种宗教思想,并构建人们的认知方式以及分类体系。
然而,如果我们不把现代生物学对于双胞胎的解释当做事实,不把鸟看作双胞胎的表征符号,而是将其看做一种存在(being),则双胞胎是鸟这种以本体为形式的变化(ontic shifts)和陈述,在努尔人的本体论观念中是成立的。在伊文思(T.M.S.Evens)看来,如果我们接受努尔人的世界观念是一种非二元论式的整体论思想(holistic worldhood),并且整体的就是真实的、万物的属性都依照其与整体的关系得以确立这一努尔人的事实观念是成立的,那么万物本质上都具有整体的属性这一事实也就成立了,物与物之间是一种相互对应的关系。(31)T.M.S.Evens,“Twins are Birds and A Whale is A fish,A Mammal,A Submarine:Revisiting ‘Primitive Mentality’ as a Question of Ontology”,Social Analysis,vol.56,Issue 3,2012,p.7.此外,物与物之间的这种互证关系,因为缺少符号或者概念等中介形式,反而更加通达和显明。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从物物对应这一整体论的事实观念出发,来认识人与非人之间关系(human-nonhuman connections)。如此一来,诸多由表象造成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物因此以更具效应的方式呈现出来。罗安清(Anna Tsing)所领导的松茸研究团队,通过人类与松茸对气味做出的共同的化学反应,将两者联系起来,说明气味不但从松茸的视角,也从人类的视角都表明物种多样性及其彼此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32)Anna Tsing,et al.,“A new form of collaboration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Matsutake World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36,no.2,2009,p.382.显然,松茸不再是表征的符号,松茸自身在“说话”。借用伊文思的观点:“在这样一幅没有概念区隔的整体性图画中(allness pictures),物从本质上而言都是开放的、变动的,而不是固定和封闭的。”(33)T.M.S.Evens,“Twins are Birds and A Whale is A fish,A Mammal,A Submarine:Revisiting ‘Primitive Mentality’ as a Question of Ontology”,Social Analysis,vol.56,Issue 3,2012,p.8.同样,在这样一幅图画中,人与非人(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定和封闭的,而是合作以及相互启发的。
总之,双胞胎究竟是不是鸟、松茸有没有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让鸟和松茸前来照面(34)海德格尔说:“周围世界上到手头的东西确乎不是对一个免于此在的永恒观察者现成摆在那里,而是在此在的寻视操劳的日常生活中来照面的。”也就是说周遭世界的存在,必须经过此在的日常实践才能到场,并且被此在认知。这些事物与此在照面的方式,取决于此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其“去远”与“定向”。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23~126页。(是作为本体的ontic,还是象征的symbolic)。当然,本体论者和文化主义者之间辩论的焦点,不再是说服对方接受某种事实,而是以何种觉察力(perception)来看待在田野中呈报自身的物,不要急于将其简约成某一特定的概念或者符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体论的方法“不将认识论置于优先的地位,或者专注于研究他者如何再现我们自认为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应该首先确认不同世界(multiple worlds)的存在”。(35)Michael Carrithers,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53.认识论架构下他者的“世界观”(worldviews)变成了本体论架构下充满他异性的“世界”(worlds)。
(二)严肃看待他异性:不能被收集的民族志材料
霍尔布莱德(Martin Holbraad)认为,他异性由那些不能被收集(collection)的材料构成,所谓收集是指通常意义上的精确描述。不能精确描述的材料总是以一种对立面(negation)的形式出现,否定并且改变(alter)我们惯常的描述方式和事实观念。(36)霍尔布莱德用他关于古巴占卜仪式的研究说明,占卜事实上不断否定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自认为再明白不过的一些关键概念:神祇事实并不存在;古巴占卜师所用的棕榈果,并没有沾染神圣的物质;棕榈果被占卜师掷出之后形成的卦象,完全是随机巧合的事件,与所谓的神启扯不上丁点关系,等等。古巴的占卜,似乎造成某种“改变”,因为它总是否定我在进行人类学写作时所认定的真实性。参见Martin Holbraad,“Ontography and Alterity:Defining Anthropological Truth”,Social Analysis,vol.53,no.2,2009,pp.83~84。也就是说,他异性正是指这种难以被我们的认知体系所精准描述、再现的观念和实践,它们总是以对立面的形式出现,不断质疑我们已有的认识论架构中的关键概念。无论如何努力,差异性总是存在,我们总是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若即若离、变幻不定、无法阐释、不能言说,这种不停地改变我们的认知,拷问已有概念的阐释效力,并且使人困惑不已的差异性就是霍尔布莱德所谓的不能被收集的材料。质言之,他异性来源于表征体系精准描述的努力,不断被改变(alter)、被否定、被中止这一事实。
然而,他异性真正将我们带入一个个不同的世界(本体论的),而非不同观点的世界(worldviews)(表象的)。“他异性所特有的本体论的立场,不但激发了一套有关不同的物的存在的认知体系,并且也揭示出一个多少显得唯一且具有整体性的世界。”(37)Martin Holbraad,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81.从他异性的视角来分析努尔人“双胞胎就是鸟”这一陈述,便不难发现,这属于不能被我们收集的材料。因此,与其纠结于如何百分之百地再现他者看待世界的方式,纠结于如何以翻译或者阐释的方式来化解文化差异,不如直接进入由他异性对应的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坦然承认特定材料不能被精准描述、无法通约的本质(nature)。“在这一视角之下,当努尔人做出双胞胎就是鸟这一陈述的时候,问题不再是他们理解孪生的方式与我们不同(因为我们认为双胞胎是指人类的孪生兄弟姐妹),而是他们正在谈论不同的孪生形式。这一非常有趣的差异不是表象层面的,而是本体论维度的:当努尔人谈论双胞胎就是鸟的时候,那些被看做孪生的因素,与我们将双胞胎看作人类的孪生兄弟姐妹时所考虑的诸如DNA在内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38)Martin Holbraad,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83.
通常而言,文化差异性的不能翻译和阐释,他者世界的不能通约和再现,标志着表征体系和阐释架构的全然失败。然而在本体论转向的学者看来,无法收集和精准描述的材料,反而意味着人类学家开启了靠近事实、寻求真理的正确路径。因为从他异性的本体论视角出发,当我们感觉研究对象所说所做的事情荒诞离奇、难以理喻的时候,正好说明我们既有的概念体系的阐释效力已经到达极限……人类学此时面临的任务不是去说明民族志材料如此呈现的原因,而是去理解它们是什么。也就是说,此时需要的不是解释或者阐释,而是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39)Martin Holbraad,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84.概念化既包括生成新的问题意识,也包括对既有概念的重新思考和组合,使其对应新兴的问题化空间。因此,提出问题是关键的第一步。
(三)严肃地提出问题:组合与概念化
当下这一时代极大重塑了我们生活的文化地貌。各种新生事物纷至沓来,一次又一次地刷新我们的事实观念,改变着我们对物的本质和存在的思考方式。在哈维(David Harvey)看来,这同时也是一个“资本颠覆时间的加速时期,”资本在最短时间内高效地生产可供消费的意象,以此左右大众的接受心理。资本的介入,使得公共和个体价值体系结构呈现出瞬时化的趋向,形成一个日益碎片化、价值观念多样化、一致性不断分崩离析的社会。(40)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Cambridge:Blackwell Publishers,1989,pp.285~288.相应地,人类学的田野之地也被各种实践、象征意义、消费意向以及社会控制不断割裂和重塑,民族志者面临的任务,或许不再是将这些碎片收集起来,为其重新建构一个田野之地的语境,重新运用一套既有的概念体系,以便加以精准描述,因为总有一些民族志材料不能被收集。此外,我们所观察的群体,可能未必都悬挂在地方性的意义之网中,随着全球化观念的扩张,在各种传媒的推波助澜之下,文化作为地方性的社区大众所共享的意义之网,这一概念也必须重新加以审视。(41)Lila Abu-Lughod,Dramas of Nationhood:The Politics of Television in Egyp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32~33.
为了应对当下的挑战,人类学亟须一种新的启蒙观念。启蒙的意义不在于从历史整体性的视角去把握这个时代,或者以文化阐释、翻译或者再现的方式去通约文化差异,准确回答各种问题。恰恰相反,在拉比诺看来,启蒙的意义在于揭示造成当下种种差异的问题是什么?唯其如此,才能培养一种概念化的兴趣意识,并且为人类学在当下这一问题空间的重构和探寻中,开拓一片坚实的立足之地。(42)Paul Rabinow,Marking Time: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12.既然民族志的主要任务不再是重新建构一种相对固定的田野之地的描述语境,那么它就必须转而跨越不同的领域,辗转于不同的田野之地,设计出新的田野研究概念,并探寻新的合作主体。显然,暂且搁置人类学既有的概念体系,似乎才能更好地进入充满他异性的不同世界,也才能更好地形成问题意识,从而开启富于启发性的概念化过程。这一点正如马库斯所言:“与其在认识论层面凭兴趣不断设计和打磨民族志研究的问题,认真思考人类学家和他者之间所谓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不如从本体论层面来生成复杂事物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空间。”(43)George Marcus,“The Legacies of Writing Culture and The Near Future of The Ethnographic Form:A Sketch”,Culture Anthropology,vol.27,Issue 3,2012,p.431.
问题意识形成之后,如何来设计新的田野研究概念呢?答案就是“组合”(assemblage)的研究方法。在拉比诺看来,人类学面临的任务在于,将传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研究语境中的概念、术语、实践加以重组,以便应对当下的问题。这些概念经过重组、修正、调适之后,不但彼此相关,而且重新焕发阐释的效力。(44)Paul Rabinow,The Accompaniment:Assembling the Contempora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129.简单地说,组合、重组的目的不仅意在对接新的问题空间,同时也提供一套容易上手操作的工具。拉比诺深受福柯的影响,他的这一组合概念多多少少来源于福柯所谓的配置(dispositif)观念。配置在福柯看来,就是选取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中诸多不相干的要素(disparate components),将它们颇为变通地组合在一起,之后将其融入一套统一的工具之中,用以考察某一特定的历史问题。这一配置,同时将权力和知识带入工具性的特定分析架构中,以便确定知识类型得以支撑的权力关系及其策略。(45)Hubert L.Dreyfus and Paul Rabinow,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121.
组合不仅针对学科内的既有概念进行质疑、辨析和重组,也可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进行。以合成生物科技(synthetic biology)为例,这一领域的学者们都普遍认为,合成生物学不过是模块化和标准化的一个过程,其研发和创新的动机与美国文化中的工程化理念别无二致,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有机体的实验和应用制定出精准的工具化式的操作规范……并且大多数生物学家们都相信,他们的研究将在医药、安全、经济、能源等领域带来重组和突破,最终为人类的福祉做出重大贡献。(46)Paul Rabinow,Designing Human Practices:An experiment with Synthetic B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p.36~37.然而,遵从自身科学理性的学者们却不愿意继续追问,他们所生产的物将在本体论和伦理的维度,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和实践带来何种颠覆效应。诸如“什么是人类福祉,以及合成生物学将在哪些限定范围才能更好发挥作用,以及物的哪些功能是不能重新设计的”这些基本问题,(47)Paul Rabinow,Designing Human Practices:An experiment with Synthetic B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37.显然在生物学家们的思考范围之外。然而一旦人类学与生物科学进行跨学科的概念组合,我们便可在这一充满启示意义的组合空间内,获得一种社会、科学以及伦理的复合性视角,(48)Gisli Palsson and Paul Rabinow,“The Iceland Controversy: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Market of Civic Virtue”,in Aihwa Ong and Stephen Collier ed.,Technology,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p.92.借以思考新兴的物、观念以及实践生成演变的过程,收集那些在传统的概念体系中不能被收集和描述的民族志材料。
此外,组合也可以在全球化的种种形式(global forms)与实际的全球化(the actual global)之间来进行。如果将全球化看作一个问题空间,则组合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能被简约成一种单一的全球化逻辑。组合本身具有的即发性(emergent),决定了它短暂易变的特点。作为一个全球化与组合串并而成的概念,全球化组合(global assemblage)处处表明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全球化意味着无所不包、无缝隙覆盖以及通行无阻;而组合则意味着多元、偶发、变动以及极强的地方性语境。(49)Aihwa Ong and Stephen Collier ed.,Technology,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p.12.也就是说,组合呈现出的全球化图景才是真实的,组合本身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因为它一方面对应着当下这一问题空间的存在样态,另一方面也通过概念的重组,探寻那些长期被当做符号予以再现的实体、物以及实践的本质,由此生成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使得以思考、校正和重构为特征的概念化成为可能,这当然也是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和存在形式。
近年来,组合也成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键概念。行动者网络中的网络是指诸多行动者可以依附的关系场域,它具有变化以及扩展的作用,从而将诸多人与非人的行动者组合在一起,形成异质纷呈的联合形式。备受拉图尔推崇的法国社会学家塔徳(Tarde)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实体组成的。实体指某物的存在模式,其本质就是收集(gathering or collecting)。也就是说,实体通过收集而存在。某一实体通过依附网络,将变动中且异质杂陈的元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关系的场域。由于依附关系有强有弱,随着关系场域的延伸,新的元素被吸纳进来,某一些元素则可能逃逸出去。实体作为行动者所具有的能动性,在拉图尔看来就在于“行动者在某一场域将数以万计的个体组合在一起的能力,同时它们可能会与铁、沙粒、神经细胞,单词、意见以及情感产生联系”。(50)Callon,Michael and Bruno Latour,“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How Actors Macro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Do So”,in Karin Knorr-Cetina,et al.,Eds.,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London:RKP,1981,p.292.此外,实体呈现出粒子(particles)或者液体状态,在非现代的语境中不断循环流动,是各种互动关系的集合。(51)Bruno Latour,“On Recalling ANT”,in John Law ed.,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1999,p.17.所以当塔徳说社会是由不同实体组成的时候,他意在批判杜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因为后者旨在分析规则、秩序以及逻辑逐渐萌发的本质,从而忽略那些构成实体的元素(粒子)对意义的输送、修正和转译的作用。正是由于组合所形成的关系场域,为我们揭示出异质纷呈的实体连接互动的纽带、各种行动协调一致的方式以及各种意义输送和转译的路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本质是联系(relations)和不可简约性(irreduction),很多学者将其称作“联系的本体论”(relational ontology)。(52)具体请参见Benjamin Alberti,et al.,“‘Worlds Otherwise’:Archaeology,Anthropology,and Ontological Difference”,Current Anthropology,vol.52,no.6,2011,p.898;Rita Felski,“Comparison and Translation:A Perspective from Actor-Network-The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53,no.4,2016,p.748。
总之,发生在上述三个维度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应该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严肃对待”意味着将阐释他者的愿望以自我强制的方式悬置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文化和本质之间施划泾渭分明的界限,(53)Paolo Heywood,“Anthropology and What There is :Reflections on ‘Ontology’”,Cambridge Anthropology,vol.30,no.1,Spring 2012,p.149.因此,本体论的转向似乎也并不意味着与认识论的彻底决裂。然而,如何看待民族志的作用、地位与前景,似乎正在加剧本体论转向之后两种观念取向的对立。一种取向主张人类学放弃人文主义的基石,代之以后社会/后人类(post-social/post-human)的本体论视角,(54)Henrik Erdman Vigh,“From essence back to existence:Anthropology beyond the ontological turn”,Anthropological Theory,vol.14,no.1,2014,p.53.以本体志(ontography)取代民族志。(55)在与其他学者的对谈中,霍尔布莱德将本体志的写作方法分为5个步骤,其中多次强调的还是概念重组、引发思考的必要性。本体志尽管最终以再现的形式出现,但被再现的是人类学家经历最初的各种概念交织所引发的冲突和困惑之后,所使用材料的通达和澄明性(transparency)。参见Benjamin Alberti,et al.,“ ‘Worlds Otherwise’:Archaelogy,Anthropology,and Ontological Difference”,Current Anthropology,vol.52,no.6,2011,p.908。此外,基于对传统人类学万物有灵论诸多观点的审视,霍尔布莱德认为,本体志首先有别于主流的(mainstream)的民族志,因为它针对万物有灵论中的物是什么来进行发问,而不是针对人们认为它们是什么来发问,本体志因此重视物的能动性(agency of objects);其次,本体志是一种思考的实验,这种智力训练类似于哲学家的思考状态,有别于人类学家或者考古学家所想象的科学式的侦探工作;最后,本体志意在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使用田野调查中不同寻常的材料,对于惯常的假设加以概念重组(reconceptualize)。参见Martin Holbraad,“Ontology,Ethnography,Archaeology:an Afterword on the Ontography of Things”,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vol.19,Issue 3,2009,pp.433~435。另一种取向则认为,人类学如其希腊词源暗示的那样,终究是一门有关人(Anthropos)的研究的学问,应该以人的社会和生物存在为研究对象,考察当下各种新的技术手段,对于人的存在所造成的转变。(56)Aihwa Ong and Stephen Collier ed.,Technology,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p.17.这关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确定研究对象,二是采取何种研究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如何生成问题化空间,组合概念化工具,拓展本体论的视角,进而重新刻画人的实践状态,将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民族志研究的重要维度。
四、民族志在场:问题空间与概念重组
福柯在《词与物》中批判社会科学在人类学中沉睡,人之限定性(他的身体、他的词、他所造之物)所形成的经验和表征体系相对固化,阻碍了知识空间的进一步拓展。然而一旦以探寻人的生命、劳动、语言为根本的认识论范式,受到当下社会诸多新兴事物的挤压、绘制和重塑,人类学这门学科就应该“跨越自身的领域,从它所表达的一切出发摆脱它,重新发现一个纯化的本体论或关于存在的根本思想”。(57)[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45~446页。在福柯看来,“因为现代思想不再朝向差异之从未完成的构成进行,而是朝向相同之总是被完成的揭秘前进”,(58)[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443页。才造成了人类学沉睡。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就必须将其唤醒,而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显然有助于推动这门学科反思现代性及其相应的概念体系,并进而拓展问题意识,开启探寻的起点。(59)王铭铭也敏锐地观察到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的必要性,他将其称作“新本体论的回归”,并且认为这种本体—知识兼和的“民族志理论”,才接近人文科学的那个“物”。参见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人类学向其他领域的延伸,自然就能建构起一个异质杂陈、短暂易变的问题空间,相应地也能衍生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在福柯看来,问题空间并非通过一套话语和概念创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观察对象,它的主要作用恰恰在于重新辨析已有的概念和实践方式,充分考虑当下短暂易变的诸多新兴元素,从而形成一个概念化的语境,与各种话语或者非话语实践所构成的“集合”而非“表象”相对应。集合显然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它一方面自带的问题意识促使我们不断反思既有的种种认知、行为和推理的能力,(60)Paul Rabinow,“Midst Anthropology’s problem”,Cultural Anthropology,May 17,no.2,2002,p.138.另一方面也促使人类学更加靠近当下这一纷繁复杂的实践方式(亦即福柯所谓的集合),因为在这一集合之内,正在生产着包括伦理、政治和权力在内的各种知识。这一问题空间使得人类学能够获得一种恰当的观察视角和态度,从而针对当下的问题和所面临的风险,获得一个更加细致、更具有操作性的研究空间。(61)Paul Rabinow,Marking Time: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29.本文所说的概念化,就是要借助福柯和拉比诺所界定的问题空间,将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再现(representation)概念带入人类学在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实践这一集合中予以考察,并尝试性地思考民族志在场(ethnographic present)的可能性。
威廉姆斯说,艺术和文学领域的再现,指将某一符号(symbol)、意象或者过程在眼前或者意识中加以呈现。(62)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208.如果此处呈现的不是符号或意象,而是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实践,(63)在Ortner看来,人类学的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关注的焦点,“不是真实的大众所做的真实的事情,直到1978年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的英文版出版,以实践为取向的方法才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尽管没有冠之以本体论转向,但是Ortner认为,实践可以将社会结构、文化类型、规范、价值理念和情感模式整合在一起,不必像从前一样将文化人为地划分为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参照关系来加以分析,而是将实践作为一个整体和参照系,以此将文化的不同系统融合在一起并予以阐释。参见Sherry B.Ortner,“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6,no.1,1984,p.148.则再现的表征意义可以用更具实践和过程因素的“在场”(present)来替代。(64)韦氏字典对present在动词一栏的释义分别是:1.将某种表演(a play)在公众面前呈现;2.让别人观看:展现(show);3.展演(perform,to act the part of)。有行动、采取行为之意。在形容词一栏中的释义包括:1.存在的或在过程中的(in progress);2.比较古旧的用法表示瞬间(instant)或者即刻(immediate)。剑桥词典对present在名次一栏的释义是正在发生的时间(time which is happening now)。在动词一栏,表示某事发生(it happens)。实践和呈现因此形成富有本体论维度的对应关系。这是因为,在场不再是使不在场者重新到场,而是一种缺少刻画和描述的颇为质朴的存在方式。其次,实践也不再是“符号体系的展演”(格尔兹),或者是“道德的集体表象”(涂尔干),亦或是“结构在社会行为层面的呈现(enactment)(帕森斯),实践有其自身的存在(existence)形式和逻辑,从这一意义而言,在场即实践,反之亦然。经过上述概念的重组,我们可以用民族志在场这一概念扩展民族志研究与写作的本体论视野。概括而言,民族志在场首先对应着一个新兴的问题空间,这一空间为跨学科的概念重组提供了一套分析和研究的工具。其次,在场包括了民族志研究对象被制造出来的整个过程,这当然也是民族志有关他者的书写这一实践的应有之义。最后,在场作为日常生活中支离破碎、晦暗不明的话语和非话语实践所构成一个整体、一个集合、一种表述的框架,它们将潜在的演变成真实的,将历史带到当下,将单一变为多元,在当下让曾在和未来都来照面。(65)海德格尔将保持在本真的时间中的并因而是本真的当前称为当下即是,作为本真的当前,才始让那能作为上手事物或现成事物存在“在一种时间中”的东西来照面。也就是说,以遗忘和重演为本质的曾在,因此得以在当下到场并与此在照面,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绽出样式”。同时,此在的能在性通过领会使将来回到自身,回归当下,形成一种当下即是的本真状态。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85~386页。当下统摄曾在、当前以及将来,形成一种永恒和本真的时间性的三位一体的局面。本文提出的民族志在场,在时间性中也体现出这种当下即是的本真状态。质言之,在场不是社会事实的表象,它们在制造社会事实。
玛丽·道格拉斯正好在福柯所定义的问题空间这一特定的集合形式中,考察民族志在场在时间维度上的存在方式。她认为,这是民族志研究的一种特殊时态,旨在将过去、当下和未来聚集到一种持续性的在场之中,这远比任何重构的或者错误阐释的时间维度更具价值。在场于一个当前的时刻,将不同时期的事件、概念聚合在一起(synthesis),由此形成对于当前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合力。(66)在民族志呈现这一集合中,我们当前能够观察到的商品的消费,以及民族志和其他文献中记载的非商品的物的消费,它们都贯穿着一条永恒不变的原则:消费是社会关系的物质控制手段,这一点在印第安人的夸富宴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即以物质的方式来握手。参见Mary Douglas and Baron Isherwood,The World of Goods: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London:Routledge,1996,pp.10~46。同样在这一呈现中,未来的消费也将仍然是社会关系互动和操控的重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道格拉斯尽管也使用ethnographic present这一概念,但是她旨在强调呈现的时间性(特殊时态),没有过多论述呈现的实践、过程等特质,而后者,正是本文使用这一概念试图扩展的部分。此时,在场作为民族志的特殊时态颇具有海德格尔的“当下即是”的意味,也就是让过去与将来通达地在当下显明和到场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说,在场这一人的日常行为(记忆、叙述、闲言)的集合,是此在在世的展开状态,这一状态既规定此在的平均日常生活的开展方式,(67)[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10页。也决定了其他存在者前来照面的方式,这一照面因为没有媒介或者表征体系作指引,因此与其他存在者形成映现、通达和呈报的对应关系。(68)海德格尔不断使用“映现”“通达”“呈报”以及“显现”等概念来说明周遭世界与此在照面的方式。参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8页,第85页,第86页。形象一点说,民族志在场类似于一幅日常行为的画卷,展开这一画卷,所有正在上演的事件,使得历史和记忆前来照面并获得意义,同时,正在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也逐渐显出轮廓,未来在即兴和瞬时的当下展演中也透露出某种必然性。这一点正如福田(Kim Fortun)所言,“当过去被折叠在事实呈现自身的方式和传统中时,未来的结构和任务便已明确了”。(69)Kim Fortun,“Ethnography in Late Industrialism,”Cultural Anthropology,vol.27,Issue 3,2012,p.450.
民族志在场除了时间维度的当下即是,它更指向民族志者与他者的一种互动关系,是双方通过各自的实践(言谈、行动)彼此塑造的过程。因此在场在实践这一维度上也体现出一种“交往互动即是”的本真状态。因为在场中聚合的不再是某种先在性的被实践表征的概念体系或者社会结构,而是经由询问、参与、担当、展演等一系列行为所造成的彼此身份的转换和重塑过程,其中弥散着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的精神,这正是民族志研究的真实性样态。正是因为在场所具有的实践这一本质因素,费边认为,其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民族志需要再现的不再是某种可通约的文化差异,而是将在场本身予以再现,也就是将他者被制造出来的这一过程予以再现。费边说,我们人类学家不应首先就将再现看作由人类的智识所赋予的能力(尽管相应的研究在心理学、大脑科学以及哲学领域仍然具有合法性),而是应该将其看作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看作我们的实践(praxis)。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到一个充满异趣的“彼处”(there),之后在“此处”(here)更好地捍卫这一学科的地位。同时,我们写作民族志的目的,无非是将“彼时”(then)带到“此时”(now),因此,从彼处到此处,从彼时到此时,不但是一个民族志者与他者在交往互动中相互塑造、转换和创生(creating)的过程,并且全都在呈现中交汇(converge)。(70)Johannes Fabian,“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The Other and Anthropological Writing,Critical Inquiry,vol.16,no.4,1990,p.756.不论是福柯的集合、道格拉斯的聚合还是费边的交汇,它们都表明,在场不借助中介的颇为澄明的存在样态,因此也更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本文将威廉姆斯再现的概念所包含的“使到场”(making present)改造成在场这一更为澄明的到场形式,减少了表现和阐释的意味。在场本身所具有的短暂瞬时的意义,使得它具有一种当下即是的本真性,从而将跨越不同的学科、跨越人与非人(物)的界限、跨越不同历史时期、跨越不同田野之地的各种历史的以及新兴的概念和实践带到这一问题空间,事实因此更具效应地呈现出来。此外,在场所具有的行动意义,表明人类学从根本上而言是一门以实践为导向的学科,即马库斯所谓的我们在“做研究”(doing research)。(71)George Marcus,“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24,1995,p.113.因此,将我们如何制造研究对象、与谁合作、如何设计和试验研究项目、如何探索和思考新兴的问题这一行动的过程,在民族志中予以完整的呈现,一方面让人类学获得了一个“相邻”(adjacency)的视角,(72)拉比诺认为,“相邻”暗指人类学面临的一种尴尬处境。一种既不在后,也不在前,既感到落后,又想有所作为,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踟蹰不前的田野研究的现实语境。一种想体现学科与当下的相关性,却又不得法门的尴尬、莽撞、困扰的复杂情感。参见Paul Rabinow,Marking Time: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40。拉比诺所谓的相邻的民族志研究视角,无疑与本体论转向学者所倡导的由最初概念的冲突,并进而专注于思考的实验和呈现这一状态颇为接近。从而让事实更为通达地前来呈报自身。另一方面,呈现在拓展民族志本体论维度的同时,也让这门有关人的研究的科学,仍然留在人的实践这一根本的存在方式之中。以这一重新组合的概念为工具,本文接下来将尝试分析当下一些民族志研究中的“在场”因素,这些作品通过跨越已有的学科界限,不断校正民族志者的实践方式,突破传统地方性社会研究的情境化和个案展示的孤立封闭,更好地将不同学科的各种概念、不同田野之地的话语和实践以及民族志者不断被重塑的研究体验,带入一个集合中予以呈现,在衍生问题空间的同时,也形成概念化的工具。
五、在场:民族志的概念和实践的重组方式
罗安清在印度尼西亚热带雨林中从事全球化与地方性互动关系的研究,她将热带雨林中社会-自然景观交错共生所形成的模糊地带称作“裂隙”(gaps),认为这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划分所难以界定的概念性空间和实际地点的交错形式。与裂隙对应的就是“影子社区”(shadow communities),影子社区在森林中有诸多的“标记”,比如植物、临时性农田、破旧的仪式场所等等。这些标记,对应着过去的社区,也有可能是未来社区用以联系各户的纽带。人们只要一看到某类植物,脑海中马上浮现出一段社会记忆,这些都是社会性的节点(nodes of sociality)所唤起的意识。以影子社区作为社会交往的节点和记忆,丛林中的人们得以协商当下各自应尽的各种社会性责任,稳固各种伙伴关系,寻求帮助并缔结新的同盟关系。(73)Anna Tsing,Friction: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p.175~198.在罗安清看来,裂隙是另类的带有浓郁本土化观念的全球化视野,它们在各种全球性工程的接缝处衍生出来,只有以裂隙作为拓展问题意识、生成概念的空间,“一部有关全球联系的民族志才能得以书写”。(74)Anna Tsing,Friction: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202.显然,热带雨林景观类似于在场的一种变体,因为裂隙的存在,全球化在地方性社会中进行绘制的种种企图,遭遇反作用的摩擦,面临重重困难,取得些许进展,可能随时间流逝而被湮没,如同热带雨林中隐约显现的人类活动的痕迹。但这些却都是真实存在的全球化的印记,它如同影子社区所遗留的标记一样,通过当下的存在,揭示全球化未来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以及潜在的包容、共生以及协作的关系。
与罗安清的单一地点所凸显的多点意义不同的是,劳尔(Naor Ben-Yehoyada)考察的重点是地中海南岸和北岸的西西里以及突尼斯之间的区域联系。他充当拖网捕鱼船上的水手,穿梭往返上述地域,最终写成《地中海的化身》这一部民族志。劳尔选取“裂变”(segment)这一传统的地中海区域研究的概念,通过考察结盟、联姻以及庇护等裂变性结构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展演,呈现这一区域的人们另类的时空观念以及跨地域的社会连接方式。对于裂变性概念及其变量的重新思考和组合,在劳尔看来主要面临的挑战在于,诸如结盟、联姻以及效忠和庇护一类表示彼此联系的习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维度(本质上也是裂变的)的政治进程的形态,通常被认为是前现代或者非现代社会语境中的历史遗存。因此当前对于跨国主义的理解,总是先在性地将人们看做已经彼此联系在一起,而忽略了他们如何看待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75)Naor Ben-Yehoyada,The Mediterranean Incarnate:Region Formation Between Sicily and Tunisia Since World War 2,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p.230.有鉴于此,只有将这一区域内被视作历史遗存的各种裂变性结构,带入当下各种日常行为和话语这一在场的集合体中予以考察,我们才能发现,地中海两岸的人们如何在各种情境化的舞台和场所(拖网渔船、酒吧、鱼市),仍然在展演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也是在这一充满各种裂变因素的集合中,地中海提供的长时段历史照射进来,当下跨地域联合的实践和逻辑逐渐清晰起来,人类学家便能从中窥见未来这一区域特有的充满裂变性动量(segmentary dynamics)的连接形式。因为一旦我们追随表示彼此联系的结构和习语跨越海洋,便可清楚地看到人们使用这些结构,在不同的范围和程度交往互动的形式。就在此刻和当下,他们灵活地运用这些有关结盟、联姻和庇护的裂变性结构,让其跨越边界和海洋,他们的区域就这样被召唤而来(conjure up)。(76)Naor Ben-Yehoyada,The Mediterranean Incarnate:Region Formation Between Sicily and Tunisia Since World War 2,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p.237.总之,这一区域内分合无常的裂变性因素,作为日常生活中观念和实践的在场形式,同时也作为道格拉斯所谓的一种特殊民族志时态,在一个持续性的当下聚合在一起,从中窥见地中海曾经的和将要开启的区域联系方式。
劳尔将地中海南北两岸多点的区域性连接,带入“裂变性结构”的日常展演这一实践的集合中予以考察。与此颇为相似的是,进行艾滋病、卫生以及免疫观念研究的马丁(Emily Martin),则将自己在志愿者组织、医疗机构、医学院、国家卫生部门、国际合作组织等多个田野地点的民族志材料,配置在异质杂陈的各种观念和实践的集合之中(configruration),使其到场。这些民族志材料在配置中在场,是想从另外的角度获得观察免疫这一概念体系的全新视角。与免疫体系相关的概念和实践构成一个新兴(emergent)的问题空间。(77)Emily Martin,Flexible Bodies: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Boston:Beacon Press,1994,p.16.作者借用拉图尔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权力机制正在生成的早期阶段,是一个卫生观念正逐渐被免疫观念所取代的重要时刻,因此对于我们考察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尤其重要。问题空间一旦在多点的配置中在场,接下来就是要组合概念化的工具。马丁这部民族志的本体论视角,体现在她不愿意一开始便借助包括文化、隐喻、意义以及仪式在内的表征体系,来分析免疫的观念和行动方式,而是认为,这些阐释性的概念本身就有详加辨析的必要。有鉴于此,马丁将布尔迪厄的惯习观念予以拓展,形成实践(practicums)这一概念,意指人们在各种非制度性的体系中,习得新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过程。(78)Emily Martin,Flexible Bodies: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Boston:Beacon Press,1994,pp.14~16.显然,这一实践的概念因为是在多点的配置与“无法预测的早期阶段”得以形成的,因此它没有参照系,也不是某种既存观念的集体表现,它本身就具有颇为浓郁的本体论意义。与此相应的这部有关免疫的民族志,其意义并非在于描述既有概念的阐释效力,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其作为重新思考人类学诸多分析性概念的工具,这也是众多本体论转向学者试图对民族志加以改造的一个方向。(79)Martin Holbraad,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84.
此外,为了促成不同概念的组合和重组,跨领域的合作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颇为理想的集合形式。也就是说,各学科的合作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是促成建设性的联系,并进而在这一新兴的、不太稳固且难以界定(松散)的组合中将问题予以呈现。近年来,人类学领域的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无不意在促成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在研究项目的设计过程、方法和观点呈现等层面的交流和联系,并进而达到拓展问题视野这一目的。(80)相关研究包括:Kim Fortun,“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Online”,Cultural Studies,vol.28,no.4,2014;Geroge Marcus,“Prototyping and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Experiments with Ethnographic Method”,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vol.7,no.4,2014;Paul Rabinow,Designing Human Practices:An experiment with Synthetic B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合作不仅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不同的田野之地进行,也可以在人与非人之彼此联系性这一层面展开。罗安清的松茸课题组成员在不同的田野地点,围绕松茸的知识、价值以及消费等观念的形成开展合作研究的同时,也在思考人与蘑菇能否真正成为合作者的可能性。关键的问题则在于探索蘑菇自身的存在方式,如何塑造了人们对这一物种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并进而形成某种具有启发性的社会理论。课题组成员乔伊和萨苏卡认为,松茸真菌菌根与红松树根共生关系提供了一个本体论的视角:一个人类的视角所观察不到的地表之下的世界,菌根或者植物的块茎特有的与外部世界联系、共生、互补、转换的多种形式。通过松茸的这一视角,人类才有可能调整自身观察世界的意识和视角。(81)Anna Tsing,et al.,“A new form of collaboration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Matsutake Worlds”,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36,no.2,2009,pp.383~386.也就是说,松茸菌根的独特存在方式,对于人类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具有双重的本体论意义的启示作用。这一作用在菌根的价值转换及其生长和消费的知识谱系这一树状图中呈现出来,一方面表明,松茸之所以被人类认为独具价值,是因为它促使人类重新反思自身共生合作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表明,围绕松茸的生长、保护、消费的知识的形成和转换,为人类学的理论开启了充满奇异的物性视角,也为概念的组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六、余论:本体论是文化的另一种说法?
2008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本体论不过是文化的另一种说法”的辩论会议,众多持本体论转向观点的人类学学者,就本体论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颇为激烈的辩论。杜伦大学的卡雷瑟(Michael Carrithers)认为,本体论不过是文化观念在言语和行动中加以展演所使用的一个工具,作为对事实的另外一种认知方式,它不断丰富着我们表征世界的视角(worldviews)。相应地,民族志的作用就在于,其具备一种超级的文化符号处理和意义阐释的强大能力,可以将本体论视角呈现给我们的文化差异加以通约和阐释。(82)Michael Carrithers,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p.167.霍尔布莱德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本体论的价值在于其对终极的思想、原则和物的存在方式的深邃思考,而文化则是飘浮在思想表层的无所附着之物,充满经验性、偶发性,是哲学不屑于涉足的领域。与此相应,应该对民族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其不再充当阐释或解释民族志材料的分析性工具(为什么是),而是将其作为重新思考民族志材料的工具(是什么)。(83)Martin Holbraad,et al.,“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ulture”,Critique of Anthropology,vol.30,no.2,2010, pp.179~184.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族志研究应该成为一个“制约模糊性”(controlled equivocation)的空间。(84)Martin Holbraad,Morten Axel Pedersen,“The Politics of Ontology:Anthropological Positons,” Society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y,2014,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the-politics-of-ontology-anthropological-position?from=singlemessage & isappinstalled=0,June 21,2020.显然,在霍尔布莱德看来,民族志之所以需要制约模糊性,是因为近年来人类学家们倡导的意义悬置或者建设性的误解等诸多方法,事实上是将自己缠绕在一堆有待厘清的表象、符号和概念之中,颇有点庸人自扰之意。此时,除非自己具有格尔兹一般强大的材料处理和符号阐释能力,能抑制住差异性,并将其通约为大写的文化形式。否则,对于大多数人类学家而言,不如放下各种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先入之见,在本体论的维度为自身所背负阐释的压力减负,我们就能发现一个与物对接的现实世界。
然而,民族志研究能完全抑制住模糊性吗?这既无可能性,也违背人的诗性认知途径,自然也违背社会科学归根到底还是有关“人”的科学这一宗旨。(85)刘 珩:《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因为对事实的认知必须经过怀疑、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过程,(86)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pp.247~257.这也是一个意义不断被重塑和表现的过程。只要我们像维柯一样认识到,包括明喻、暗喻在内的各种比譬或者诗性智慧,仍然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方式,我们便不难理解这些意义模糊的地带也是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人类不再思考,不需要再借助各种修辞的手段,不需要经过各种意义含混、模棱两可的过程便能让事实呈现,我们才能彻底抑制住模糊性。此外,正如赫茨费尔德观察到的那样,目前本体论转向的人类学所使用的存在(be or exist)具有欺骗性,它事实上意在将交织其间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控制策略剥离出去,(87)Michael Herzfeld,“Factual Fissures:Claims and Contexts”,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60,1998,p.74.因此有必要提倡一种人类学现实主义,将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包括进来,作为真实性的重要源泉。(88)[美]迈克尔·赫茨费尔德:《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刘 珩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
面对上述主要集中于人类学知识论和本体论的辩论,以及各种穿插其间的反思和修正观点。本文提出民族志在场这一概念,作为一个折中主义式的方案,借助对多点以及合作民族志的考察,旨在将更多的问题意识在一个组合中予以呈现。这个组合可能是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各学科的学者、病患,或者志愿者共同维护和经营的某个网站,也可能是人类学研究项目设计和试验的工作室、各种机构和场所,当然也可能是罗安清通过印尼热带雨林景观,所呈现的地方性知识和全球化摩擦、互动、协作的标志和印记,可能是劳尔所搭乘的拖网渔船上正在上演的各种分分合合的“裂变性”意识,也可能是马丁在免疫体系中对多点民族志材料的配置。然而无论是哪种集合形式,它们都使用问题化的种种概念,将有关人(anthrops)的种种主题作为民族志探索的起点,赋予各种新兴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的集合以本体论的意义。这些集合所特有的在场效应,使得与之相关的民族志实践不再是试验某一套概念体系的阐释效应,而是将这些概念作为考察和辨析的对象。本体论维度的他者的世界(different worlds),而非表征视野的他者如何观世界(different worldviews),得以更为通达地到场和更具效应地呈现。
拉比诺在《伴随:组合当下》一书中分析比较博厄斯(Franz Boas)和格尔兹两人的文化研究方法时指出,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工程旨在将不同文化通约成一种普同人性的平等表达方式,并将确认这一普世性基础(universal ground)的方法用括号标记,当做真理予以呈现。到了格尔兹领衔的文化阐释时代,已经用括号标记的各种真理的宣示,被再次用括号标记,这次要呈现的是严肃性。(89)Paul Rabinow,The Accompaniment:Assembling the Contempora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p.37~38.或许我们可以接着拉比诺的论述,在新兴即发、短暂易变,并且以分化、组合、重组为其存在样态的当下,将严肃性再次用括号标记,所不同的是,这次需要呈现的是问题。重塑问题空间、组合概念工具,不但呈现着民族志实践的整个过程,或许也呈现出我们通过操劳巡视带到近前的那个周遭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