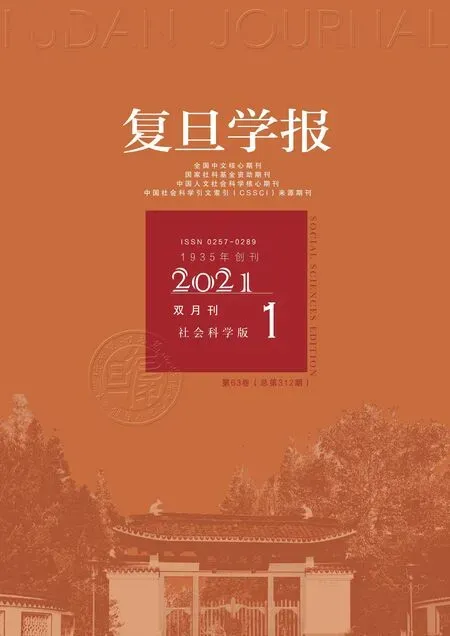严复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以新见《美术通诠》底本为中心
狄霞晨 朱恬骅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作为晚清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之一,严复为中国思想界带来的财富难以衡量。他不仅是晚清“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1)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1页。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也不容小觑。由于过去罕见其文学评论文字,严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远不及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同时代学人。近来,笔者发现了其译作《美术通诠》的底本,这是一本20世纪初流行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由于严复将原题中的“literature”译为“美术”,以致该书所承载的严复文学思想长期匿而不彰,不失为一大遗憾。通过对严译《美术通诠》及其英文底本OntheExerciseofJudgmentinLiterature的文本对读,可以看到《美术通诠》不仅是一部文学理论译著,也是严复文学思想精华的集中展现。
一、 严复何以译“literature”为“美术”?
严复以翻译驰名中外,其八大译著《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涉及生物学、经济学、法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均已探明底本。然而对文学研究者而言,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当属《美术通诠》。1906年,《寰球中国学生报》第3~6期连载了这部署名为“英国倭斯弗著,候官严复译”(2)倭斯弗原名W. Basil Worsfold,未见汉语世界内有人介绍过此人,除严复之外亦未见他人将其作品译成中文。按照现在惯行译法,W. Basil Worsfold当译作“巴西尔·沃斯福尔德”。的《美术通诠》,篇末署“未完”,但未见续译。这位倭斯弗是何许人也,《美术通诠》又译自哪部英文原著?为了探明这一谜团,笔者对1906年之前出版的西方文艺理论类著作进行了拉网式搜索,终于锁定其底本为W. Basil Worsfold所著的OntheExerciseofJudgmentinLiterature(《文学评论实践》)一书。(3)该书最早于1900年6月在伦敦由J. M. Dent & Co.出版,1901年再版,两个版本几无区别。本文参考的是1901年版,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馆藏本的扫描件。书前盖有多伦多大学的印章,上书“presented to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by Professor W.S. Milner”,W.S. Milner是多伦多大学拉丁语与古代历史教授。书的封面上书“1901 90 Wellington Street West”,书的最后印有“Printed by Turnbull And Spears, Edinburgh”。此书除了严复节译本之外,未见有其它中文译本。
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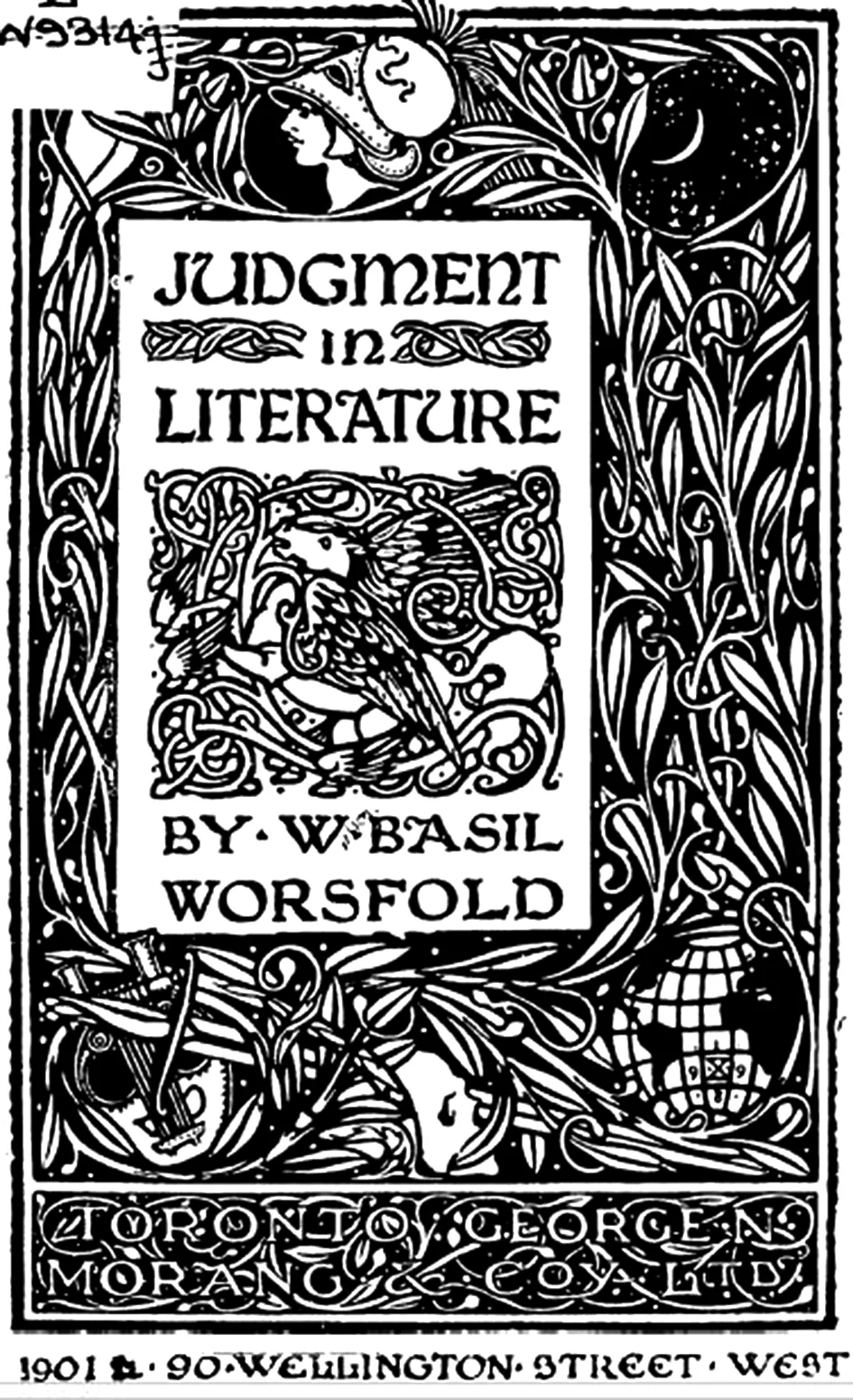
Judgment in Literature的封面
原著的发现,让我们得以了解到《美术通诠》其实是严复唯一一部文学理论译(论)著,也可能是近代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著作。
真相大白之后,严复115年前留下的悬念也浮出了水面。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严复为何要以“美术”对译“literature”?如果他当时用的不是“美术”,而是“文学”,以严复的地位和影响力,这部文学理论译著应该不会像今天这样默默无闻。那么,倭斯弗的原著是一本怎样的书,严复为何要翻译这部著作?严复既然强调“迻译是篇为不容缓”,(4)[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三(古代鉴别)》,《寰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第5~6期。为何又只翻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5)除去参考文献和索引,全书正文内容92页,各章标题如下:第一章,艺术(严译“艺术”,Art);第二章,文学(严译“文辞”,Literature);第三章,古代世界的批评(严译“古代鉴别”,The Criticism of the Ancient World);第四章,现代批评(Modern Criticism);第五章,创意文学如何诉诸想象(How Creative Literature Appeals to Imagination);第六章,当代批评(Contemporary Criticism);第七章,文学评论实践(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in Literature);第八章,文学的形式·古典型与浪漫型方法·风格(Forms of Literature-Classical and Romantic Methods-Styles)。严译《美术通诠》包括前二章及第三章的一部分。若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但要比对倭斯弗的原著及严复译本,还需了解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持有的文学思想。
纵观译文,对于原文中出现的“literature”一词,严复自始至终未曾使用“文学”来对译,而选择了“美术”“文”“文章”“文辞”“文词”“文字”等词;不仅如此,类似现象还出现在了对“art”“poetry”等词汇的翻译中,如下表所示。

《美术通诠》中“literature”相关名词译法对照表(6)原文中literature、art、poetry等词,时有句中大写以示强调或意义变化,表中示例均保留原文大小写。“architecture”在《寰球中国学生报》中登出时写作“achitecture”,亦保留原样。

(续表)
与此同时,同一个汉语词也可能对应好几个英语词。例如,“美术”有时对应的是“literature”,有时对应的是“arts”或“fine arts”;而“文章”也是“literature”与“art”兼而有之。《美术通诠》中一词多译的情况非常普遍,这种看似“混乱”的情形似与严复过去翻译《天演论》时“一名之立,数月踟蹰”(7)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全集》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9页。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在笔者看来,这些译名上的“混乱”与以“美术”译“literature”一样,背后都隐藏着严复对桐城文章理念的传承与追求。众所周知,严复受桐城派影响颇深,而桐城派向来推重韩愈“辞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严复对“literature”一词的翻译本大可采用“文章”“文辞”等更为现成、普遍的词汇,但作为一个以“雅”(出自桐城派理念“雅洁”“清真雅正”)来要求自己的翻译家、“古文”家,严复并不甘心采用这种看似平庸的译法;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不同的语境下翻译成了“美术”“文章”“文辞”“文字”等词,甚至不译。在翻译精准与文字典雅之中,严复依据桐城传统选择了后者。他接受了吴汝纶“与其伤洁,毋宁失真”(8)吴汝纶:《与严几道论译西书书》,钱基博编:《国学必读(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1页。的建议,在“信”与“雅”之间明显偏向于后者。在今天看来,这未必是一种“信”;而在当时的严复看来,这样的翻译却未必不“信”。崇“雅”的严复译文不仅得到了吴汝纶等文学名家的赞赏,连当时在华的传教士都对他的文风赞不绝口:“他的文风与周代顶尖作家齐肩。……严先生写出了最令人愉悦的清新、典雅、准确、率真的文风,不华丽、不趋俗。他言而有物,是文言文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文言。他不像长久以来的文人那样写深奥含糊的文章,它不同于那些苍白夸张的八股文,而八股文却自居为‘文章’。”(9)J.C.Garrit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iterature,”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38.6 (1907): 297.(案:原文为英文,此处中文为作者自译。)晚清西方传教士极少夸赞中国文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严复崇“雅”文风的跨文化价值。
严复之所以选择“美术”而非“文章”“文辞”来对译标题中的“literature”,同他的“节译”策略亦大有关联。倭斯弗全书主要谈文学批评的方法,其中第一章谈艺术(art,严复译为“艺术”),第二章讲文学(literature,严复译为“文辞”),第三章谈西方古代文学理论(The Criticism of the Ancient World,严复译为“古代鉴别”),均为较基础和综论性的内容,从中也最能明白地体现倭斯弗对文学及各门类艺术的一般观点。而第四至八章分别谈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的文学批评、创意文学与想象的关系、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围绕真理与理想化的批评、文学批评的实践、创意文学的种类与风格等,具体涉及到罗斯金、马修·阿诺德、斯温伯恩等各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和文学观点。显然,前三章才是严复最关心的内容;而从第四章开始谈的都是当时英语世界知名的作家、作品及理论主张,严复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在他看来中国读者也未必关心,不作翻译也在情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倭斯弗原书在当时是一本流行的文学理论著作,(10)该书出版后,多家报纸杂志很快予以评论。1900年8月25日的《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认为,从文学批评的入门书角度来看,该书为个中翘楚;但是,在立意严谨和新颖上都有所疏忽,特别是处理文学类型上显得不足。英国《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认为,该书颇具思想性和趣味性,尤其是提出了当代批评在于进行阐释这一命题。《文学世纪》(The Literary Era)及《文学世界》(The Literary World)杂志也予以转载及评论。1920年,这本书还出现在一份高中和大学教材的推荐书目上。但另一方面,英国《学院报》(The Academy)1900年9月1日刊发的评论则措辞犀利,认为该书在各方面都乏善可陈,美国《城与邦》(City and State)同年11月1日予以转载。它曾多番重印,亦有外语译本;(11)该书自1900年出版后,1901、1905、1917、1920、1925年均有再版,1906年还出版了波兰语译本。既然如此风行,严复接触到它自然不难。书中不仅谈及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学)各主要流派的观点,更渗透了西方美学与文学理论的通行见解。具体来说,倭斯弗在牛津求学期间,英国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正当其时。他的诗歌风格与文学主张被认为介于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是沟通二者的重要诗人之一,倭斯弗在书中也设专节讨论了阿诺德的观点。而另一方面,来自法国的折中主义哲学家Victor Cousin(今通译“维克多·库辛”,严复译为“孤山维陀”)也在英国受到欢迎,他的思想融合了德国古典哲学与苏格兰常识学派的观点,体现了黑格尔、托马斯·里德等思想家的深厚影响。有鉴于此,倭斯弗原书的前三章综合体现了当时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观点,在内容上也的确不仅包含了文学理论,同时兼顾一般意义上的美学阐述。这就令该书成为了管窥西方文论乃至西方美学的枢纽,而严复在标题中使用兼有艺术与文学双重含义的“美术”一词,也就比“文学”更为恰适。
将“literature”译为“美术”,使严复参与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和艺术理念建构的进程之中。在他翻译此书的1906~1907年间,“美术”一词风头正健。据日本学者铃木贞美研究,“美术”(对应“art”)一词在1880年左右开始在日本广泛使用,1882、1883年以后,“美术”开始成为音乐、诗歌、舞蹈的通称,之后小说、戏曲也成为“美术”的一种。(12)铃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东京:作品社,1998年,第193页。严复之前,中国学人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都曾使用“美术”一词,(13)中国美院的彭卿博士通过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和“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检索“美术”,发现在五四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刘师培、蔡元培、鲁迅与“美术”时常共同出现。康有为笔下的“美术”已经包含了建筑、雕刻、画学、舞蹈、音乐、诗学。梁启超在《烟士披里纯》中指出美术由灵感而发。参见彭卿:《中国现代“美术”观念的形成及其演变》,中国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16年。且蔡元培、王国维也已用“美术”来表达过包含现代“文学”的涵义:蔡元培在《学堂教科论》(1901)中指出“美术学”包含“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小说学”。(14)蔡元培:《学堂教科论》,张汝伦编:《蔡元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0页。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1904)中指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15)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集》第一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1905年,严复自己也曾用“美术”与“科学”对举,表达“艺术”的内涵。(16)1905年,严复在《政治讲义》中使用了“美术”一词,他说:“有美术、有科学,文教大开,书籍侈富,教育之事兴焉,而大小学堂林立。”见严复:《政治讲义》,《严复全集》卷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6页。由此可见,“文学”与“美术”在明治日本和晚清中国的语境中均已成为了彼此含义交叉的两个词汇。尽管“美术”一词是严复所厌恶的日本“新名词”,(17)严复曾在翻译中刻意回避日语词,曾批评梁启超大量使用日语“新名词”的文界革命是对文界的“凌迟”。但“美术”所承载的现代意义却是他所认可的。由此,以“美术”译“literature”,其实是严复文学观的一种表达:文学是一种美的艺术。
严复这一翻译显然让文学意义下的“美术”得到了更多的接受者:相继出现了金天翮的《文学上之美术观》(1907)、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1907)等专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8)、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也均使用了“美术”一词来表达现代的文学意涵。在与西方思想的不断碰撞下,20世纪初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明确拥有了广义的“艺术”(对应“art”或“fine art”)以及狭义的“纯文学”(对应“belles-lettres”)的双重含义。尽管现在“美术”已不再表达“文学”的意涵,但这一现象背后所提示的深层美学内涵,特别是其沟通中西文论的历史作用,却是不应忘却的。
二、 当“修辞立诚”遇见西方美学:中西文论对话中的严复
《美术通诠》的原著作者倭斯弗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886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却也涉足经济学、法学与教育学;他热心于政治,足迹遍布四大洲,并非专职文学研究者。(18)倭斯弗1858年生于英格兰约克郡,1883年获牛津文学学士学位,188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1883~1890年间受聘于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今南非、纳米比亚)、新西兰、新南威尔士,足迹遍访纳塔尔、维多利亚、昆士兰、爪洼等地。1887年获得律师执照,1891~1900年间在牛津延续教育代表会(Oxford Extension Delegates)和伦敦联合委员会讲授经济学和文学。1898~1899年间出访埃及,1903年出访希腊。1939年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但绝大多数与他在南非、新西兰、爪洼等地的受聘和访问有关。除《美术通诠》外,倭斯弗还有《批评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Criticism)、《南非联合体》(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等著作。OntheExerciseofJudgmentinLiterature脱胎于倭斯弗较早出版的《批评的原理》(ThePrinciplesofCriticism),并作了大量删减。另一方面,《美术通诠》虽属译著,但严复在其中不仅扮演了译者的角色,还扮演了评注者的角色。他借倭斯弗的文本煞费苦心地提出了自己融会中西的文学观,并将其归结为“讬意写诚,是为美术”。(19)[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一(美术)》,《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第3期。“讬意写诚”既以严复自己的方式提炼了倭斯弗建立在黑格尔美学基础上的文学、艺术观点,又是对中国古典文论中“修辞立诚”观念的化用,使之得以发挥出沟通中西文论的作用。
“讬意写诚”首次出现在严复翻译倭斯弗对艺术的定义中。他将原文中“Art then,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in its mental aspect”(20)W. Basil Worsfold, On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in Literature (Edinburgh: Turnbull and Spears, 1901) 5.(艺术是在精神方面对现实的表现)一句译为“美术者,以意象写物之真相者也。”(21)[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一(美术)》,《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第3期。不过,他还悄悄地在前面加上了一句话,即“美术者何?曰讬意写诚,是为美术”。(22)[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一(美术)》,《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第3期。这是他自己的提炼。严复显然对自己提炼出的“讬意写诚”颇为得意,它在译文中重复了2次,在案语中也出现了1次。(23)严复在案语中以“写诚讬意”为标准,肯定中国书法也是“美术”的一种。在第二章中,严复同样在文中未加注明地加入了自己的解释:“夫界说曰:讬意写诚,谓之美术。意,主观也;诚,客观也。”接续以所译倭斯弗之语:“是故一切之美术,莫不假客观以达其意境。独有文辞,无所假讬于客观,而其所有事者,皆主观之产物也。夫使文辞如是,则诗歌词赋者,文辞之精英也,斯其为物,又可知已。”(24)[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二(文辞)》,《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第4期。案:原文为“All art reproduces external reality in its mental aspect; but the arts — except poetry, which is the highest form of literature — emplo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bjective aspects of reality to assist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is mental aspect. But literature, with the sole exception (already noted) of the element of musical sound, does not need this assistance; for literature — as literature — is concerned solely with the subjective outlook upon the world.”[W. Basil Worsfold, On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in Literature, (Edinburgh: Turnbull and Spears, 1901) 11. ]对照原文,倭斯弗也指出表现现实有两种方法,即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认为文学有益于提升主观对世界的认识。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讬意写诚”中的“意”对应于主观,“诚”则指客观。严复用“主观”与“客观”这一组具有鲜明西方哲学色彩的术语,借题发挥地与自己给出的“意”与“诚”构成一组互文。
《美术通诠》中的黑格尔色彩似乎十分浓厚。在第一章开篇不久,便出现了“诗歌最上,营建最下”(25)[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一(美术)》,《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第3期。之说。我们知道,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提出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类型依次发展的学说,但对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及诗歌等具体艺术门类的评价是相对辩证的。建筑虽然是象征型艺术的主要代表,但建筑这一门类中也存在着古典型和浪漫型建筑,他并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作出明确的高下之分。借黑格尔之名而对它们作出价值高下判断的人其实是倭斯弗自己。为了凸显创意文学/诗歌的重要性,他有意地对黑格尔的理论作出了“曲解”,指出“黑格尔在崇高的理念之下,把诗歌置于最高,而把建筑置于最低”。(26)W. Basil Worsfold, On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in Literature (Edinburgh: Turnbull and Spears, 1901) 4. 案:原文为“On this principle Hegel places Architecture lowest, and Poetry highest, in order of dignity.”他认为,由于诗歌可以不需要凭借于外物,直接来自心灵(mind),所以是最上等的美术。(27)时人也有不同看法。功利主义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就将诗歌视为艺术的下品,因为他根据快乐量和真实性作为衡量法则。可见倭斯弗借用黑格尔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创意文学”的重要性,(28)倭斯弗所谓创意文学(creative literature),是指使用艺术(art)的方法,诉诸于想象(imagination),具有审美愉悦(aesthetic pleasure)的文学,包括诗歌(史诗、叙事诗、抒情诗、挽歌、剧诗)、戏剧(悲剧、喜剧)、散文、小说等。在他看来,只有创意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因此误导严复作出了“德哲黑格尔列美术为五等”(29)[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一(美术)》,《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年第3期。的错误解说。倭斯弗的关注点导致《美术通诠》中的黑格尔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形,而他借黑格尔的美学理论强调诗歌是艺术的极致,实则深受以诗歌为中心的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如,黑格尔对“美”的定义是“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30)[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2页。,强调“理念”。然而在倭斯弗看来,艺术还是要表现外在现实的,所以他对艺术的定义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真实”(real,即严复翻译的“诚”),而非“理念”。由此可见,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倭斯弗,对现实的注重已经超越了对“理念”的追寻。
另一方面,严复对黑格尔的接受也有自己的兴趣点。与人们的印象有所不同,严复虽以带有鲜明政治、社会色彩的译著闻名,但他对西方政治、社会论述背后深远的哲学渊源也极为关心。在发表《美术通诠》的两个月前,他发表了《述黑格儿唯心论》一文,阐发其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31)孙应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5页。这是中国第二篇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32)马君武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之学说》一文(1903年3月12日),是中国第一篇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亦足见当时严复对西方哲学的兴趣。倭斯弗在《美术通诠》中正是借黑格尔的美学建构阐述了有关文学的观念,而这可能是吸引严复翻译此书的原因之一。不过,严复看重的更多的是黑格尔有关“客观精神”的论述,特别是有关“法哲学”的内容;对黑格尔《精神哲学》中占据主要位置的“主观精神”,以及在黑格尔理论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绝对精神”,都只是简单带过甚至不置一辞。
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下,“严复所译倭斯弗著作中的黑格尔”实已经过多次阐释和变形,很难说是黑格尔思想的本来面目。然而,它也因此使一系列西方美学与西方文论的观点集结在“黑格尔”的名号下。在这一意义上,严复的“讬意写诚”不再是对倭斯弗文学理论或黑格尔美学的简单移译,而是对西方文论整体面貌及其美学框架的概括提炼。他通过“讬意写诚”一方面关联了西方美学与文论,一方面又与中国文论中的“修辞立诚”、“文”“学”之分、“情”“理”之分联系起来,是在对黑格尔、倭斯弗观点提炼基础上的一种严复式再创造,也是其个人对文学、艺术思想的表达,具有沟通中西文论的价值。
我国该说明书遗漏药效学和耐药性资料。撰写技术指导原则规定,在药理毒理项目中应设耐药机制小项,“此项应描述最新的耐药机制研究,首先描述是否已有病原菌对药物出现耐药以及发现的研究,详述耐药机制、相关耐药基因以及交叉耐药的机制。若尚未发现耐药菌株可描述为尚未在体外、动物感染模型以及临床研究中发现耐药菌株。也需对已知的或观察到的诱导耐药的情况或机制、药物引起细菌耐药的突变频率进行描述。”
“讬意写诚”这一说法出自《周易》中的“修辞立其诚”。严复对于“修辞立诚”也深有理解。早在翻译《天演论》时,他就已借“修辞立诚”来表达自己对作文、翻译的看法:“《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33)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全集》卷一,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62页。可见“修辞立诚”是其“信、达、雅”翻译理念的理论基础。在《美术通诠》中,严复也多次使用了“立诚”这一概念。例如,“夫词章美术,必首以立诚之为基”。(34)[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三(古代鉴别)》,《寰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第5~6期。这里的“立诚”对应的是倭斯弗原文中的“make‘truth’”(表现真实)(35)W. Basil Worsfold, On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in Literature (Edinburgh: Turnbull and Spears, 1901) 22.,认为它是诗歌、艺术的基础。
“修辞立诚”中,“修辞”指的是修饰文辞,“诚”指诚实不欺的道德准则。孔子因厌恶春秋时期像邓析那样的巧言利口覆邦国者,故提出“修辞立其诚”的原则。(36)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页。北宋理学大师程颢指出:“‘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37)朱熹、吕祖谦编,叶采集解:《近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5页。程颢认为要修辞就要先树立自己的诚意(即修身),没有修身的修辞是虚伪的。“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38)苏惇元辑:《方苞年谱》,严云绶等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12·方苞选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586页。的桐城派相当看重“修辞立诚”,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倾向于从修身养德的角度对其进行阐发。戴名世认为“惟立诚故有物”,(39)戴名世:《答赵少宰书》,《戴南山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32年,第12页。从“修辞立诚”中提炼出了“有物”说;而“有物”“有序”说又是方苞对其理论核心“义法”之说的诠释。桐城派对“修辞立诚”的注重,深深体现在其文论的核心——“义法”说之中。
严复深受桐城派殿军吴汝纶的“古文”观影响,感念其对自己的“奖诱拂拭”,(40)严复:《与吴汝纶·一》,《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7、125页。也很看重“义法”。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就曾言“贤者文词,当其下笔,自有义法”。(41)此外,桐城文章讲究“文气”,严复的译文中多有“嗟乎”等感叹词,而倭斯弗原文中并没有类似的感叹语。严复把倭斯弗的“aesthetic pleasure”(审美愉悦)译为“神韵、味趣”,也颇有桐城味。这在严复《美术通诠》的译文中也有直接的继承,例如将原文中的“rules”(规则)一词译为“义法”,就带有明显的桐城派色彩。而在涉及柏拉图文论的时候,倭斯弗指出柏拉图把文学、艺术视作道德的工具,严复更直接以“立诚载道”将其概括,径直在文中插入“移情之日深,而养德之日浅耳”(42)严复:《与吴汝纶·一》,《严复全集》卷八,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7、125页。的感叹,可谓是借西哲观点来发扬桐城派所力倡的德行文章合一。“讬意写诚”与“修辞立诚”虽然表述不同、对“立诚”方式的关注不同,但意图都在于强调“诚”(真实)对文学的重要性。
严复的“讬意写诚”为“修辞立诚”赋予了现代意涵,使得西方文论与美学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进而得到新文化人的接受与认可。例如,周作人说:“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43)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5期。此即直接受到严复“讬意写诚”理念的影响。周作人理解到“讬意写诚,是为美术”中的“美术”具有“文学”的意涵,因此借用了这一表述,证明小说是文学、艺术的一种,以提高小说文体的地位。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等人以“立诚”“有物”来要求新文学,进一步突破了这些词语的传统文论意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中的“立诚”也是表现客观真实的意思;胡适“言之有物”的思想亦根源于“修辞立诚”说。(44)旷新年:《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黑格尔的《美学》最终由桐城籍美学家朱光潜忠实地译为中文,可以说为这段桐城派与黑格尔美学、西方文论的对话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 情与理的对话:严复与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在《美术通诠》的严复案语中,有一条颇为值得注意。在这条案语结尾,严复感叹道:“此迻译是篇所为不容缓也。”换言之,这里隐藏着严复翻译《美术通诠》的真正目的。不妨一读:
复案:此节所言,中国为分久矣。于其前者谓之学人,于其后者谓之文人,而二者皆知言之选也。前以思理胜,后以感情胜;前之事资于问学,后之事资于才气;前之为物毗于礼,后之为物毗于乐。……斯宾塞尔曰:“渝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此迻译是篇为不容缓也。(45)[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篇三(古代鉴别)》,《寰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第5~6期。
倭斯弗的创意文学与非创意文学固然不能严格对应于中国的“文”与“学”,但严复意在借西人之语提高文学的地位。在他看来,中国长期以“学”压制“文”,在桐城派文人与汉学家论争的语境之中尤其如此。严复指出,倭斯弗强调了“美术”(文学)的重要性,而中国的浅薄之人还以为“美术”(文学)无用,因此倭斯弗之书亟需翻译成中文。这样,严复一方面加强了倭斯弗抬高文学地位的语气,一方面也有回护桐城文派之意。清代的汉学家常批评桐城文派浅薄无学,而桐城中人虽对此颇感不平,却回击乏力。章太炎1906年9月在日本讲学的时候,就曾不点名地讽刺严复“略习制义程式,粗解苏、王论锋,投笔从戎,率尔译述。其文辞之诘诎,名义之不通,较诸周诰、殷盘益为难解。此新译诸书所以为人蔑视也”。(46)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全集 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页。案:严复与章太炎曾有过一段关于翻译的争论。1898年,章太炎与曾广铨共同翻译了斯宾塞的《论进境之理》,发表于《昌言报》上,仅半个月后就遭到严复的嘲笑。严复发表了《论译才之难》,不点名地批评章太炎不学外文,却要翻译外文著作。这一批评让章太炎从此再不轻易翻译英文著作(参见傅正:《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与清季国家主义——以章太炎、严复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但章太炎也并不欣赏严复的翻译,以上议论即显示出了他对严氏译文的不满。意在指严复不通小学,其古文的功底又主要来自于八股文,所以文字佶屈聱牙,被人看轻。章太炎此言虽属偏激,但也反映了当时学人对文人的普遍态度。晚清桐城派多自居文人,在学林少有建树,难免辩驳乏力。严复借倭斯弗之言,强调文人与学人同样重要,对于当时学林轻视桐城文人的风气,无疑是有力的回击(这一见解发表于1907年6月刊载的译文案语上,极有可能是针对章太炎上述言论的回击之语)。他借倭斯弗的理论把“文”与“学”分开,体现其赋予文学独立性的主张,也体现了接近于现代意义的“文学”观念。
严复所强调的“文”与“学”之分,以“情”与“理”作为最重要的区分标准,这并不是仓促所得。早在1898年,他就曾指出“心有二用”,一为情,二为理。诗词属于情,以《离骚》为代表;理分为记事和析理两种,考订也属于理。(47)严复:《八月初三日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9页。在1906年6月上海青年会的演讲中,他也延续了这一思路,指出“西人谓一切物性科学之教,皆思想之事,一切美术文章之教,皆感情之事”(48)严复:《教授新法(青年会第七次师范研究会之演说)》,《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6、236页。,即言科学以思想为主,文学以感情为主。这里的“西人”之说明显带有倭斯弗的印记。在引述完“西人”之说后,严复话锋一转,指出“然而二者往往相入不可径分。科学之中,大有感情;美术之功,半存思理”。(49)严复:《教授新法(青年会第七次师范研究会之演说)》,《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36、236页。可见他是不主张把感情与思想理性完全对立起来的。在他的观念中,文学应当是情、理兼具的。
严复对“文人”与“学人”、“情”与“理”的辨析既依赖本土资源,也具有外来背景。从本土资源来看,至少可以上溯到晚明公安派与清代乾嘉时期的文坛元老袁枚。袁枚继承了公安派三袁的“性灵”(主要指情感)之说,既不满于宋学,也不满于汉学,自居为文士。袁枚与当时的汉学新秀孙星衍曾就“考据”与“著作”(主要指文学)展开讨论:孙星衍指出袁枚把考据和著作分开,以“抄摭故实为考据,抒写性灵为著作”,(50)孙星衍:《答袁简斋前辈书》,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89页。对此提出了质疑。经学家焦循也参与了这场讨论,他对袁枚的著作与考据之分感到不满,并认为这种分法毫无根据。文人袁枚看重文学,认为考据会伤害文章;而经学家孙星衍、焦循看重考据,认为古人重考据甚于著作,且两者不分。(51)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1~493页。袁枚的“考据”与“著作”之分,已经有了“学人”与“文人”之分的意识,并且把情感视为文学的核心要素。(52)近年来也有研究者指出袁枚的“性灵说”在当代文学中亦回响,在启功、许白凤的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参见马大勇:《“性灵说”的当代回响——以启功、许白凤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与严复同时代的刘师培提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蒋智由提出“冷的文章”(思虑周全、条理细密的文章)与“热的文章”(给人刺激、使人兴奋的文章)(53)蒋智由:《冷的文章与热的文章》,《新民丛报》1905年第4期。等二分,也都在“情”与“理”之间寻求文学核心要素。
从外来背景来看,西方学者之外,近代日本学者也在通过分类的方式来区分文学与科学。严本善治把文学分为“美文学”与“科文学”;北村透谷则提出了“美文学”与“理文学”之分(“理文学”与“科文学”意义相仿);三上参次有“纯文学”与“理文学”之分,认为“纯文学”是“美文学”的同义词。以上三位都是以美为基准的。内田鲁庵根据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帕斯卡所提出的“数学的思想”与“情感的思想”之分,把“情感的思想”作为文学定义的基础;竹越三叉提出了“软文学”(有哲学观念的,有与人生相关的思想的文学)与“硬文学”之分。(54)铃木貞美:《日本の文学概念》,东京:作品社,1998年,第193、211~228页。在1887年前后,“学问”与“文学”已经得到了非常明确的区分。而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太田善男所译介的“情的文学”与“知的文学”之分,这一说法则进一步来源于英国浪漫派批评家德·昆西的“literature of power”与“literature of knowledge”之分。(55)德·昆西所指的“power”是指情感冲击,因此将“literature of power”译为“情的文学”(日语原文为“情の文学”)而非“力的文学”,也是合理的。德·昆西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启发,其“power”主要指情感冲击。在他的心目中,情的文学才是最重要的,文学旨在传递情感的力量。这一说法经过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推广,被黄人、周作人、朱自清等所吸收。
近代世界文学领域密集出现的文学与科学之分,是伴随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构建而出现的。无论是袁枚、严复、刘师培、蒋智由,还是德·昆西、倭斯弗,又或严本善治、竹越三叉等各家,都意图以二分的方式划定文学的界限。就《美术通诠》底本所处的英语语境而言,“literature”一词之所以从包含阅读技巧、书籍特质、学问、知识、文法、修辞技巧等庞杂的意涵一步步窄化为现代“纯文学”的意涵,也是伴随着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思潮等思想的推动而完成的。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影响的倭斯弗,看重的同样是文学的创意(creativity)、想象力(imagination)及审美愉悦(aesthetic pleasure)。这些文学的现代要素被集中于“创意文学”的概念之中,已经体现了现代的“纯文学”观念,正合于今人威廉斯(56)英国文化研究先驱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梳理“literature”词义变迁时指出:“literature(文学)、art(艺术)、aesthetic(美学的)、creative(具创意的)与imaginative(具想像力的)所交织的现代复杂意涵,标示出社会、文化史的一项重大变化。……后来literature的意涵被归类于‘具想像力的作品’(imaginative writing),而这些作品符合了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参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72~273页。、伊格尔顿(57)当代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也说:“我们自己的文学定义是与我们如今所谓的‘浪漫时代’一道开始发展的。‘文学’一词的现代意义直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首先发生的情况是文学范畴的狭窄化,它被缩小到所谓‘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见[英]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页。等对现代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概括。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中,文学的“感情”意涵却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早在1908年,周氏兄弟就在强调感情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8)中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58)令飞:《摩罗诗力说》,《河南》1908年第2~3期。在鲁迅看来,纯文学以“美术”为本质,而美可以动人感情。(59)关于鲁迅早年以文学为“美术”的观点,董炳月研究员论之甚详。参见董炳月:《“文章为美术之一”——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中强调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感人:“凡自土木金石绘画音乐以及文章,虽耳目之治不同,而感人则一。”(60)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5期。新文化运动以后,感情对于文学的重要性几乎到了无出其右的程度:不仅五四小将罗家伦在《什么是文学》(1919)中指出“文学又可以算是感情的出产品”,(61)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新潮》1919年第1卷第2号。北大老牌教授朱希祖也在《文学论》(1919)中“以能感动人之多少为文学良否之标准”。(62)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1号。文史学家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1922)认为“文学……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63)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1922年第37期。诗人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1926)中指出“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64)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31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里,“感情”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其它纯文学要素。新文化人为了革除陈旧的“载道”文学传统,有意识地强化文学中感情的重要性,而审美、创意、想象力等与之关系不大的要素则被忽略。
如果说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学现代性,那它在晚清就已经开始萌芽:黄人在其《中国文学史》(作于1904~1907年间)中认同太田善男“文学为美术之一,以描写感情为事”的观点;(65)黄人:《中国文学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8~60页。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中认为“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66)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1906年第21~23期。章太炎在《文学论略》(1906)亦承认诗赋、词曲、杂文、小说是以“激发感情为要”的;刘师培在《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1907)中也强调“美术以性灵为主”(67)刘师培:《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仪征刘申叔遗书》第十一册,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4893页。……如此种种,与现代文学强调感情的观点其实同出一脉。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与钱钟书的“载道”与“言志”之争也在这条脉络之中。近年来,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这一命题在海内外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成为热点。通过陈世骧、高友工、王德威等海外中国学者的梳理与解读,抒情传统成为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重要线索;但也遭到了龚鹏程、李春青等学者的质疑。抒情传统命题提出的背后是情理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受此影响的不只是陈世骧,还有德·昆西、倭斯弗、太田善男、严复、刘师培……以“抒情”反“载道”传统,正是情理二分这条线索所引申出来的文学革命思想。
严复凭借其在晚清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在这一思维模式的传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浪漫主义以情感为重,倭斯弗的文学观念深受英国浪漫主义及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看重以情为主要特征的诗歌,与严复形成了对话。严复虽然也看重理,但他也接受了倭斯弗以文学陶冶性情的观念,在《美术通诠》中多次出现“怡情”“感人”等译语。他通过对倭斯弗创意文学与非创意文学之分的创造性解读,将其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人”与“学人”联系起来,提出了“情”与“理”的差异,为中西文论的对话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他沟通了自晚明以来的文坛与学界,为重视感情为特色的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提供了资源,至今依然有潜在的影响力。
四、 结 语
严复译著《美术通诠》底本的发现,为我们思考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展示了严复不为人知的文学理论修养及抱负,为我们纪念严复逝世百年提供了新的维度。作为严复唯一一部文学理论译著,它直接译自英语,这在大部分西方文学思想都借途日本辗转进入中国的晚清,是极为稀有的。它凭借严复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将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念第一时间传入了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严复不仅扮演了译者的角色,更是有意识地提炼出“讬意写诚”的核心观念,将中国文论中的“修辞立诚”与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美学相沟通,为晚清以来中西文学理论的对话作了极好的示范。严复提出的“文人”与“学人”、“情”与“理”之分,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现代中国纯文学观念的塑造。它一方面沟通了自晚明以来的“性灵”说,一方面又与西方浪漫主义所看重的文学“感情”要素密切相关。它与“知的文学”、“情的文学”,“美术”与“实学”、美文与实用文等许多现代热门概念相通,成为中国现代纯文学观念的重要资源。新文学中的“载道”与“言志”之争,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抒情传统”是否存在之争,都与此相关。不仅如此,《美术通诠》的翻译也对严复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明显的触动,他一改过去轻视文学的态度,提出了古文辞不亡论。(68)严复:《〈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严复全集》卷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他还将文学视为教育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其所主持的出洋考试科目的设置、京师大学堂院系的调整,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严复以“美术”对译“literature”的背后,是一种沟通西方美学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尝试,寄托着他对中国文学未来走向的期望;他有意识地参与了晚清以来以“美”与“情感”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建构,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