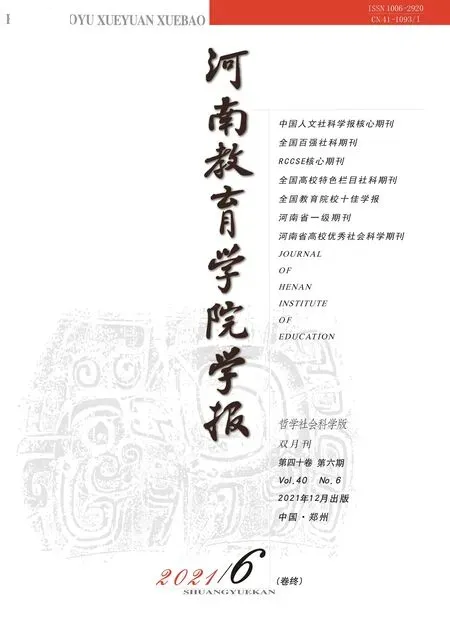《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校笺》前言(上)
乔福锦
产生于上古文明奠基时代的《诗经·豳风·七月》与问世于近古历史综汇期的《红楼梦》,是两部经典的中华民族文化叙事作品。《周礼·春官·籥章》郑笺曰:“《豳诗 》,《豳风·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豳颂》亦《七月》也。”[1]631-632郑笺所论,揭示出《豳风·七月》风、雅、颂三位一体之文本特征。“道情思者为风,正礼节者为雅,乐成功者为颂”[2]306,是对《七月》作为上古时代华夏文明之核心笺释。问世于清代中叶的《红楼梦》,“文备众体”而“包罗万象”,已然成为近古中国文化最为生动的文本象征。如果说《豳风·七月》是记录华夏文明奠基时期先民创业艰难之民族史诗,承载着华夏数千年文明成果的《红楼梦》则是一部用“假语村言”撰就的寄托着家国天下命运的文化史诗。(1)以脂砚斋为开山的“古典红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杂环境下延续学术命脉,在晚清社会巨变前夕获得“经学”认同。经过现代红学之百年转型,已然形成索隐、考证与思想艺术评论三大派别。关于《红楼梦》文本性质之认识判断,始终是这门专学的核心课题。进入“新古典红学”时代,此一课题已成为学科理论与体系建构之基点。参阅乔福锦著《石头记笺证》,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5月版;乔福锦著《红学通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一、《红楼梦》问世
作为中华数千年历史文化积累的成果,《红楼梦》的产生与时代、社会、学术背景及作者家世和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其撰著历程亦十分曲折艰难。
(一)创作背景
《红楼梦》问世的第一个背景是时代社会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辉煌了数百年的明王朝大厦在内忧外患之中轰然倒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承体系面临被摧毁的危险。顾炎武“亡天下”之论,黄宗羲“天崩地陷”之说,是对这一历史劫难的高度概括。《红楼梦》开卷所谓“天崩地陷”一词,同样是对江山鼎革、神州陆沉之文字反映。经历清初的军事征服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高压统治,至乾隆一朝,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之局面终于出现,然而武力征服与政治高压未能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抵抗,汉族士人文化上的抗争未曾中断。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所涉内容,几乎全与“夷夏之辨”与“反清复明”有关。根据《清代文字狱档》所载资料,清代文字狱大案70起,有69起发生在乾隆一朝。[3]乾隆八年(1743)杭世骏案爆发,适逢《红楼梦》动笔之时。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案出现,正值《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告成之时。
《红楼梦》问世的第二个背景是历史文化进程。发祥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大体经历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上古三代,华夏文明基本形成。秦汉至唐中叶,制度文化基本成型。赵宋一代,“礼乐文明”已臻化境。伴随着学统确立与政治“昌明”,民间社会生活亦臻于典雅、精致、成熟。元朝的统治虽曾打断这一历史进程,但经明初“恢复中华”的历史巨变,文化第三期历史仍在延续。清代初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传承体系再次遭到摧毁。但由于中原文化同化力超强,至乾隆中叶,在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华夏中原文化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进入文化集大成时代。历史文化“一统”贯“三统”之文明进程,此时已达到整合“综汇”之历史新阶段。[4]《四库全书》之编纂,是官方文化综汇之举措。学界的经典考据,民间的家谱纂修,同样是社会文化整合之体现。经过宋元明清数代之社会进步与文化积累,白话通俗小说创作经验日益丰富,适应大众社会需求的野史小说出版与阅读氛围亦日渐浓厚。
《红楼梦》产生的第三个背景是新学术动向的出现。中国传统学术,历经先秦儒学、汉代经学,发展至宋代,已然进入理学时代。伴随着理学的兴盛,回归三代之呼声日渐高涨。明末清初,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开始对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作根本性反思。清初学术,产生于“天崩地陷”时期,“返本开新”之趋势十分明显。清末学者邓实总结云:
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而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5]
顾炎武指出:“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6]13顾氏“经学即理学”之学术主张,不仅标志着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最终被取代,亦象征着汉代经学在清初的全面复兴。清代中叶,国家的统一以及官方崇尚儒学、稽古右文政策的引导,成为经学兴盛的政治前提。至乾隆一朝,“文字狱”高压之下,清初学问原有的经世倾向受到限制,部分士子学人做起了“毫不干涉时世”的纯考据之功,习典研经蔚然成风。王国维《沈乙盦尚书七十寿序》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7]720曹雪芹读书问学的乾隆中叶,正是经学史上古今转换、交替更新时期。稍后于曹雪芹“披阅增删”《红楼梦》,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等一批具有今文经学色彩的著作的完成,为乾嘉之际常州学派的兴起开了新的学术风向。完稿于乾隆甲戌年(1754)之前的《红楼梦》,比常州学派的出现还要早。大学者戴震是与曹雪芹同时代的由古文经转向今文经的代表人物。戴震将学问分为词章、义理、考证三途,不仅视义理为三者中之最高境界,而且肯定词章与义理的正当学术存在。其代表性著作《孟子字义疏证》虽冠上考据式的书名,却是学术新趋向的代表之作。与“显”者戴震相比较,曹雪芹是“隐”者之典型。从整个清代学术史角度观,《红楼梦》之问世,也是具有古今文学术转折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二)作者家世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典社会的基础,氏族文化系中国文化传承的依托。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文化的传承,主要通过门风家教表现出来。除了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影响,天才作家的出现,血脉不断、世代相续的家族传统也是重要因素。“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8]291理解《红楼梦》,同样需要“知人论世”。作者研究之所以成为胡适之先生所开创的现代新红学的两大课题之一[9]38,原因亦在于此。
与大多数书香世家一样,《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家族历史,亦可追溯至久远年代。《浭阳曹氏族谱》有六世孙曹荣之所撰《高辛氏以来年表》,其中云:“ 曹氏之先盖若有天命焉,其自高辛氏禋祀上帝元妃,诞生后稷,遂肇封有邰。十五世而叔振铎封于曹,子孙因以为姓,固无可疑者。”[10]周初分封,曹氏始祖叔振铎被封于陶邱,国号为曹,后世子孙遂以国为姓。曹姓子孙揆文奋武、代有伟人。在风云变幻、天下动荡之汉末乱世,“平阳苗裔”成为“谯国英雄”。[11]278宋代樊若水在曹谱序赞中曾讲:“曹氏厥宗,本周分封。诗礼启后,丕振儒风。文经武纬,将相王公。簪缨济美,宠渥无穷。”[12]49周汝昌先生据此指出:“我们应当把曹家称为‘文采氏族’。”[12]3
康熙十九年(1680)《曹氏重修南北合谱序》云:
爰稽世系,盖自明永乐二年,始祖伯亮公从豫章武阳渡协弟溯江而北,一卜居于丰润咸宁里,一卜居于辽东之铁岭卫,则武阳者,洵吾始祖所发祥之地也。[10]
武阳曹氏实出于进贤曹氏。从丰润一带出关的曹家先祖,先后“寄籍”铁岭、沈阳、辽阳等地。“丰润咸宁里”,即曹氏家族迁徙过程中之最后一站。满洲正白旗曹家,曾经战功赫赫。“从龙入关”,正是曹氏家族三代人四任织造官之政治资本。《红楼梦》中出现的与曹氏家族鼎盛岁月相关的南京、苏州、扬州三大都市,是当时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曹玺及后世子孙所连任之“织造”,专任皇室衣绣、日用事务,在《尚书》中为“汝明之官”,“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13]116。功勋之家家道隆盛,叶燮《楝亭记》有特别记述。其文云:
故大司空曹公于康熙年奏天子命,董治上方会服之事,开府于江南之江宁。惟昔虞庭,职为汝明之官,以佐天子垂裳黼黻之治,位近而清,尊而暇。[11]272
江宁曹府位“近”而“清”,事“尊”而“暇”,显贵远在督抚之上。这种特殊地位,与曹家同康熙的特殊关系密切相连。冯景《解舂集文钞》卷四所载《御书萱瑞堂记》云:
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宦,实维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赍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尝观史册,大臣母高年召见者,第给扶称老福而已,亲赐宸翰,无有也。[11]338
康熙之作为,颇似“三代盛时,其君之以腹心肱股待其臣”之举。御书“萱瑞”之“堂”,亲呼“吾家老人”,实另有原因。萱既萱草,古时用以尊称人之母亲。据周汝昌先生考证,曹玺之妻孙氏,曾为康熙幼年时之保姆,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实有“一奶同胞”之情。[11]209“此吾家老人”,即皇帝尊称孙氏为母之证。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曹家,玄晔与曹寅之“棠棣”深情,由此可见。
“原籍”与“寄籍”,是《红楼梦》书中反复出现的一对概念。曹氏子孙之故土情怀,实与华夏民族之精神血脉密切相连。关内中原“原籍”,是曹寅及曹雪芹心中念念不忘的神州故园。江宁织造家,是一个承载着中华文化传统的翰墨诗礼之家。曹寅藏书中,稗官、杂记、戏文、方技等是子孙“旁搜杂取”的文献依托。作为诗礼之家,曹家之藏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经史类典籍。纳兰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云:
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操惠政,久著东南;于时尚方资黼黻之华,闾阎鲜杼轴之叹;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鲷佩觿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11]254
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
楝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楝亭皆钞有副本。以予所见,如《石刻铺叙》《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诸书,皆钞本;魏鹤山《毛诗要义》《楼攻瑰文集》诸书,皆宋椠本。[14]102
古文经学初兴的康熙年间,曹雪芹祖父曹寅特别关注圣经贤传之“微言大义”。《春秋经传阙疑》与《毛诗要义》等,为曹寅“尤志于圣贤之微言大义”[11]283提供了证据。《石刻铺叙》属史部目录类,其卷所录首篇《绍兴御书石经》,为“靖康耻”后所刻之“石经”,次篇《益郡石经》则为《红楼梦》所云“残唐五代”之“石经”。除了经学典籍,曹寅于宋金、明清江山鼎革之际兴亡史实颇为留意。《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等,乃是有宋一代民族苦难历史之文献见证。记录着大明亡国史迹的《崇祯长编》,亦是外间绝少能见的禁本秘籍。此种庋藏特色,亦可说明“萱瑞堂”边苦楝亭中何以有那么多的胜国遗民。曹楝亭大量的经史类藏书,恰是华夏“文化遗民”之心的文献证明。
数代承皇恩的诗礼旧家,至曹寅一代达于极盛,江南织造曹府成为上通天子、下交士绅的显赫之门。所谓“百年望族”,正是《红楼梦》对于这个贵族之家的评价。康熙末年,曹雪芹出生。(2)曹雪芹生年,学界有多种说法。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此说有文献与文本双重证据。具体可参阅徐恭时著《红雪缤纷录》,香港阅文出版社2019年8月版。李放云:“曹霑,号雪芹,宜从孙。” 《绘境轩读画记》云:“工诗画,为荔轩通政文孙。”[15]26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云:“曹雪芹(霑)……为楝亭通政孙。”[15]153-154敦诚“废馆颓楼梦旧家”[15]1之句,敦敏“秦淮风月忆繁华”[15]7之句,既是对曹雪芹诗礼旧家“钟鸣鼎食”生活之描述,也是对曹雪芹童年生活之写照。
盛极必衰。康熙末年,曹家卷入皇位继承的宫廷斗争之中。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二十四日,江宁织造郎中曹因“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被罢职抄家。[11]529数月之后,少年曹雪芹结束童年繁华之梦,随家人离开“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北上京城。靠老平郡王纳尔苏和曹佳氏救济,变卖古董以补家用,日常生活得以维持。据《东华录》载,乾隆四年(1739)十月,允禄、弘皙、弘昇等发起宫廷政变。乾隆五年(1740),受“谋逆”案牵连,曹家第二次被抄,百年望族最终落了个“树倒猢狲散”“食尽鸟投林”之悲惨结局。[11]586《金壶浪墨》云:“传闻作是书者,少习华膴,老而落魄,无衣食,寄食亲友家。”[15]82“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15]6,是曹雪芹由富贵繁华转为“贫穷难耐凄凉”之真实写照!
(三)撰写历程
屈大均《东莞诗集》序云:“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16]180-181黄宗羲《弘光实录钞》云:“国史既亡,则野史即国史也。陈寿之《蜀志》,元好问之《南冠录》,亦谁命之?而不谓之国史,可乎?”[17]自序1“以诗证史”是既有学术传统,“以野史小说证经史”则史无前例。经历过“国难”“家仇”“文化幻灭”之悲剧,在笺经撰史、以诗写史等举动连续遭到“文字狱”打压后,曹雪芹最终决选择用“野史小说”形式撰写一部前无定例的著作。
裕瑞《枣窗闲笔》载: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闻前辈姻亲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15]14
赵烈文《能静居笔记》云:“曹(雪芹)实楝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遂成此书。”[15]378
曹雪芹撰作《石头记》的具体历程,亦反映在其好友的诗文中。《四松堂集》稿本卷上有《寄怀曹雪芹(霑)》一首。追述曹氏源远流长之家史,在描述曹雪芹之性格、命运的同时,敦诚曾向这位友人提出“忠告”:“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15]1确如敦诚诗中所言,“将军”之后曹雪芹于“扬州旧梦”醒来之后,并没有在穷困中乞食“富儿门”。即使在家人妻孥啼饥号寒的艰难困苦中,他也未放弃人生的追求。“著书黄叶村”,正是曹雪芹生命最后一个时段的主要事业。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15]1张宜泉《题芹溪居士》诗云:“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15]8张宜泉《读史有感》曰:“拍手高歌叹古今,闲披青史最惊人!阿房宫尽绮罗色,铜雀台空弦管音;韩信兴刘无剩骨,郭开亡赵有余金。谁似尼山功烈永,残篇断简尚堪寻。”[18]40最末一句,似乎是因雪芹西山“著书”事业而发,完全可以移来咏雪芹和雪芹之事业。在张氏心目中,秦皇之宫,汉宋之将,俱成为历史之尘埃,唯有尼山孔夫子“著书”事业,千载永存。《春秋》“残篇断简”,历无数劫难仍能传之后世,即是曹雪芹著书山村之精神支柱。
考察现存文献,《红楼梦》的著作历程,经历了早期《风月宝鉴》、《石头记》百十回初稿、《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定稿三个时期。[19]甲戌本开卷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20]8之记载,现存抄本开卷有“披阅十载”之字样。据此倒推,《红楼梦》初创时间,约在乾隆六年(1741)前后。在遭遇第二次抄家之祸后,曹雪芹开始“著书立说”。假设“重评”在“初评”之前三年,乾隆六年至乾隆十一年(1746)间,应为初稿形成时期。(3)《红楼梦》第五回有“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之说,学界曾有讨论。如果从1644年算起,至《红楼梦》初稿成型,亦有百年。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新索隐”一节有“孔继宗”之考索,亦是芹书形成时间之佐证。“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句下有脂批曰:“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20]7《枣窗闲笔》记录了“五次”删改《风月宝鉴》的信息。所谓“旧时真本”,即属于《风月宝鉴》时期的文本。此期之文本,尚属未定型之初稿。
《红楼梦》首回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20]7之句。从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十六年(1751),《红楼梦》经作者五次增删、十载披阅,《风月宝鉴》旧稿变为“初评整理本”。其中增订是“披阅十载”过程中最为主要的工作,删除的仅是个别有违碍之处。脂批有“全部百十回”之论,百十回本基本定型[21]51,即是分回纂目的结果。
自乾隆十六年(1751)始,到乾隆“庚辰秋月”,经脂砚斋“凡四阅评过”,全书已有了一个大致的“定稿”,“己卯冬月定本”“庚辰秋月定本”字样可为证。全部《红楼梦》为“百十回”本,脂批亦有明确记载。《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之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2]卷610据现存脂本可知,脂砚斋曾经参与了《红楼梦》后期修订的几乎整个历程。“一芹一脂”二人,即是“造化主”为人间安排的《石头记》“经传”之两位作者。[21]585
第一回“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一诗之眉,甲戌本与靖藏本均有一段署有“甲申八月”纪年批。批云:
此是第一首标题诗。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20]7
脂批所谓“书未成”,指个别文字仍未最后拟定,如第十八、十九、八十回回目尚需改订,第二十二回众金钗诗谜与第七十五回中秋诗及大量回末诗联待补,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文字需修订。实际上,直到曹雪芹卒于乾隆“壬午除夕”(4)参阅赵冈、陈钟毅著《红楼梦新探》上篇《曹雪芹的家世与生平》、外篇《〈懋斋诗抄〉的流传》,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9月版。,《红楼梦》仍然处于“未成”状态。然而这一判断,并不能否定《红楼梦》全书在曹雪芹生前即已大体完成的历史事实。
二、《红楼梦》文本
《春秋》为孔夫子一生事业之写照,脂砚斋告诉世人,曹雪芹之《红楼梦》亦是一部“反面《春秋》”。孟子讲《春秋》从文、事、义三层切入,《红楼梦》文本同样可从形式、内容、精神三个层面解读。
(一)文本形式
中国传统小说,就其产生途径与内在品质言,可分为“小说”与“野史”两大类。“小说”一词始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23]399-400一句。此“小说”与“大言炎炎,小言詹詹”[23]25句中之“小言”本义一致,均难登大雅之堂、不载“大道”。《汉书·艺文志》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24]1745
《隋书·经籍志》云: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25]101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26]1182
三大文献目录,均与《庄子》的看法一致。可见关于小说之观念,自先秦到清,一直未有大的变化。《红楼梦》第一回“历来野史”一段之下,甲戌本有眉批曰:“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20]7第十六回甲戌双行批曰:“调侃世情固深,然游戏笔墨一至于此,真可压倒古今小说。这才算是小说。”[20]200可见作者与批书人,均以“小说”看待《红楼梦》一书。邱炜萲《东门女士》云:
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覆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絜长而较短也。以其为小说之支流,遂亦赘述于后。[15]397
王希廉《红楼梦批序》云:
《南华经》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红楼梦》虽小说……通其说者,且与神圣同功,而子以其言为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实也?[15]33
由此可知,在传统读书人心目中,小说仅具经史典籍之外的参考价值。
如果说杂记“小说”主要来自文人的案头,是学问之余的闲事、趣事,其重心在“言志”,另一类“野史”或稗史则主要源自市井乡野,其意重在“讲史”。唐人沙仲穆的《大和野史》,是最早以“野史”命名的历史类笔记。后世演变过程中,小说与野史逐渐合而为一。刘知幾云:“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27]273与“正史”相对的“偏记小说”,在《红楼梦》书中亦与“野史”同义。第四十三回有“因听些野史小说”之句,可见作者与批书人均将“野史”视作“小说”,“野史”与“小说”,二词亦可互用。《红楼梦》第一回,作者借石头之口笑言: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20]6
可见作者虽欲摆脱“历来野史”之“俗套”,却仍将此书与“野史”作比较。“野史小说”在《石头记》书中,又与“假语村言”同义。“假语”即“野史”,“村言”即“小说”。
在中国传统中,“野史小说”不仅与“学”无缘,亦与源出于“先王之典”的“文”无关。“小说”在中国属“子部”之末,“野史”更无进入“史部”之资格。与传统“野史小说”相比,《红楼梦》极为特殊。这部“今古未有之奇书”,是数千年中国小说创作实践积累的结果,尤其与宋元以降长篇小说演变过程相关。它不但迥异于西方文化中作为“文学”(literature)四部类之一的“小说”,即使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是一个特殊存在。
犀山樵《红楼梦补》序云:
稗官者流,卮言日出,而近日世人所脍炙于口者,莫如《红楼梦》一书,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15]50
洪秋蕃《红楼梦抉隐》云: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见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15]236
“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均是《红楼梦》称奇之因。
《红楼梦》“文本形式”是“野史小说”,其文本性质,却不可“以小说鼓词目之”。第十二回“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一节“若不早毁此物”一句下注曰: 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20]154此即批书人对《红楼梦》文本性质之间接说明。《石头记》在第四十三回庚辰双行夹批曰:
惊魂夺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谓“痴子弟正照风月鉴”,若单看了家常老婆舌头,岂非痴子弟乎?[20]520
曹雪芹所生活的乾隆中叶,经学之势如日中天。“反面《春秋》”,正是对《红楼梦》文本性质之说明。政治高压时代,贬损当世君臣,是大忌讳。“隐”其书,是为“免时难”也。在一系列以史、诗、文等形式反抗现实的尝试在“文字狱”之祸中屡屡失败之后,“村言小说”这种最被人瞧不起、最易于“隐避”又流布最广的“文字”形式,便成为曹雪芹“立言”的最佳选择。(5)“旧红学”乃至“新红学”时代《春秋》学意义上的红学研究,笔法议论之外,尚有不少至今仍不被重视的学术发现。“宝玉”出自《春秋》之论断,“麒麟”与“小《春秋》”联系之提示,“存周”典故来自《春秋》等,均可看作文本研究关键证据获得之例证。此类创获,有待系统性梳理总结。“由《春秋》以致小说”[15]574,是曹雪芹之奇思妙想。现存文献证明,脂批所谓“反面《春秋》”之说,从背景、结构、内容、精神等方面观,均可得到证明。以“假语村言”表盛衰兴亡的《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个最奇特“文本”。《红楼梦》之所以被称为“天下古今第一奇书”,最奇之处,即野史小说之“文本形式”与经典著作之“文本性质”不相一致。
文本形式与文本性质之不一致,是《红楼梦》作为“奇书”之最主要原因,《春秋》四时结构则是《红楼梦》文本之基本叙事框架。华夏中原,是四季分明、四时交替的农耕文明地域。在天人合一的生命框架内,四季自然时序,是一年生活、生产的基本节奏。岁华流动,光景变迁,形成生命的自然节奏。暑往寒来与生产、生活的周期性运程,使得中华先人对春秋四时之变化极为关注。在四时观念形成之前,上古先民即有春秋两大岁时划分。《周礼·春官·宗伯》曰:“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1]702《诗经·豳风·七月》以一年时序为线索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华夏先民实际生存的真实反映。《礼记·礼运》云:“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28]698可见四时规律与礼乐制作密切相关。“人文”历史与“天文”四时密不可分,“春祈秋报”的农业社会生活方式,自然产生春盛秋衰之观念。以自然“春秋”节律结构人世盛衰,亦成为上古史书的基本结构形式和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年有四时之序,错举“春秋”以包四时,故鲁国等“史记”多以“春秋”命名。孔子所修之儒门六经之一的《春秋经》,即是中华史书的典范与中国叙事文本的典型模板。《国语·楚语上》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韦昭注云:“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29]485以“四时气象”为“春秋”结构模板,即是“天文”与“人文”合一之体现。
《红楼梦》之“春秋”结构,很早即受到研究者关注。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曾讲:
《红楼梦》有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王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之春也。省亲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笼可悦,梦之夏也。及通灵玉失,两府查抄,如一夜严霜,万木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哉!贾媪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惨,直如冬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15]84
作为“反面《春秋》”,《红楼梦》不仅具有“四时气象”,全部故事亦包含于“春秋”盛衰结构之中。曹雪芹以“四时”构书、叙事、记人思路,即本于中华上古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合一之理念。《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象征二十四节气,十二公乃十二月,三公为一时,年有四时,故“错举”二时以为“所记之名”。《红楼梦》中九回为一个叙事单元,十二单元与《春秋》十二公相对应,三个单元即每廿七回,是四时之一“季”。整部一百零八回,恰是一个具有“四时气象”的岁月“春秋”。第一个“廿七回”,如四季之“春”,展现春日的繁华新景。第二个“廿七回”,如四季之“夏”,贾府的繁荣正在盛时。第三个“廿七回”,似四时之“秋”,展现繁华过后的悲凉气氛。第四个“廿七回”,如四季之“冬”,繁华过后,惟留天寒岁暮、家亡人散之后的茫茫白雪。戚序本第五十五回回前批曰:“此回接上文,恰似黄钟大吕后,转出羽调商声,别有清凉滋味。”[20]655一部记载着春荣、夏盛、秋衰、冬亡完整“天年”的历史,以第五十四与第五十五回为盛衰之分水岭 。“前半部”为盛,“后半部”为衰,揭示出“荣国大族”由繁华到衰落的内在逻辑。
(二)文本内容
姚际恒论《七月》云:
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书。流火、 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织,狩猎、藏冰,祭、 献、执功,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30]164
姚氏此论,与前人用“包罗万象”“无体不备”之语论《红楼梦》用意相同。《红楼梦》以日常生活寓天下大事,与《诗经·豳风·七月》的“豳风”“豳雅”“豳颂”合一的形式正相仿。王希廉在《红楼梦总评》中说:
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畜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人、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仆、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坛、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寿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悮,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15]149
王氏此论,与姚氏论《诗》之语亦可合观。二知道人《红楼梦论梦》云:“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太史公之书高文典册,曹雪芹之书假语村言,不逮古人远矣。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15]102可知古典时代之学人,已经察觉到《红楼梦》“以小见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近代以来,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学术观念的更新,关于《红楼梦》的认识开始具有世界眼光与文化比较意味。吴宓先生在《红楼梦新谈》中讲:
《石头记》范围之广,已经前人指出。其中人物,多至五百人,色色俱备。其中事实,包罗万象。虽写贾府,而实足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全副情景……亦可为史料。……昔人谓但丁作DivineComedy一卷诗中,将欧洲中世数百年之道德宗教,风俗思想,学术文艺,悉行归纳。《石头记》近之矣。[31]28-29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开卷处讲:
《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32]12-13
吴宓、周汝昌先生的论述,既具有世界眼光,又本于中国传统。然而现当代许多学人关于《红楼梦》文本内容的评说,已经背离中国既有传统。如果说《红楼梦》是青春与美的挽歌,是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大体还接近文本原意的话,那么所谓“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之说,则是基于外来教条的庸俗社会学解释。回归固有学术立场,从学术还原的角度观察,曹雪芹用“十年辛苦”、一腔血泪撰就的这部“千古奇书”,实是“家传”“国史”“拟《春秋》”三位一体的特殊文本,是“四辈荣枯”“四朝盛衰”“四时兴亡”三层文本融会贯通,家事、国事、天下事汇于一体的文化经典。
其一,四辈家传。现代“新红学”开山胡适之先生有“自叙传”之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观点是成立的。用“假语村言”所写就的《红楼梦》,是一部中国式的“野史小说”,是可以“消愁破闷”的“适趣闲文”,也是一个贵族公子个人生命的历史记录。曹雪芹之书,是以清前期历史为背景的曹氏“家传”,也是曹玺、曹寅、曹颙与曹、曹雪芹四辈人的家史。与“荣国贾府”四辈盛衰历史密切相关的背景,是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史。“棠棣之威,鹡鸰之悲”,即是两种“弟兄”关联之提示。
其二,四朝国史。甲戌本《凡例》明言:“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20]1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叶起元在乾隆版“跋”中说:“稼部(指孔尚任)以至圣后裔,备悉时艰,欲抒其勃勃不平之气,而时多忌讳,势难指斥。旧人尚在,更未如何,不得已,寻一段风流佳话,写其感愤,故叙儿女之事少,述兴亡之事多。”[33]31可见以儿女“离合之情”叙“兴亡之感”,在曹雪芹之前已有先例。《毛诗序》云:
《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34]252
《黍离》乃兴亡之吟,《红楼梦》即是一首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乃至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歌!如果说《红楼梦》第一层展示的是“兄弟”间的“家仇”,第二层展示的则是明清兴亡之“国恨”。借家事叙说国运,正是曹雪芹著述之本意。
其三,四时《春秋》。《红楼梦》以微观见宏观,文、史、经三位一体,学、政、俗三层均备。此亦作为“反面《春秋》”的《红楼梦》区别于任何一部传统“小说”的本质所在。立言不为一代。曹雪芹笔下的荣国“昌明”之邦,处“尧街舜巷”,是人类文化的中心,礼乐文明的典范,在内忧外患交并的千古兴亡中,它曾几次“枯而复荣”“死而复生”。曹家上辈所经历的明清之际的“天崩地陷”,并非仅是王朝更替一类“亡国”之祸,实际是一场“亡天下”——亡文明的大劫难。江山易代,王朝更替,千古恨多少!然曹公雪芹并未将《红楼梦》的命意仅止于亡一朝一姓盛衰这一层面。作者所关注的重点,是与家国盛衰相关的“天下兴亡”与人类命运,所撰写的不一个王朝历史,而是如二知道人所讲的纪“百千世家”与万古兴亡的华夏文化“全程史”与人类命运“普遍史”。[35]
(三)文本精神
《红楼梦》精神主题研究,曾是现当代红学的热点。其中多重主题或主线说,曾是很有影响的观点。实际上,“春荣秋枯花折磨”“盛席华筵终散场”“更有情痴抱恨长”三大结构系统,正是曹雪芹关于《红楼梦》文本思路的诗意表达。一个“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盛衰史,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儿的命运史,一位“千古未有之奇人”之人生,即《红楼梦》全书的三条叙事线索。(6)笔者第一篇红学文章,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三线”说的具体论述。其时学界亦有相近论述。这部“今古未有之奇书”,是华夏民族历史文化之特殊载体,亦是脂砚斋所揭示的寄托着中国之命运的“拟《春秋》”之作。三条叙事主线与三层文本,“事体情理”一致,精神血脉贯通。以“三科九旨”为基本理论支柱的《春秋》大义,实为《红楼梦》全书之精神主旨。如果说是书第一层叙家庭闺阁琐事,第二层记明清兴亡历史,第三层所蕴含的,就是以《春秋》微言大义为精神本质的“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运太平之国”五千年文明圣火幻灭之后的“忧患意识”和作者“补天济世”的人生信念。文明与野蛮、繁华与衰落、入世与出世,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文化主题。向往天下化成,期望万世太平,眷恋诗意人生,是贯穿《红楼梦》始终的精神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