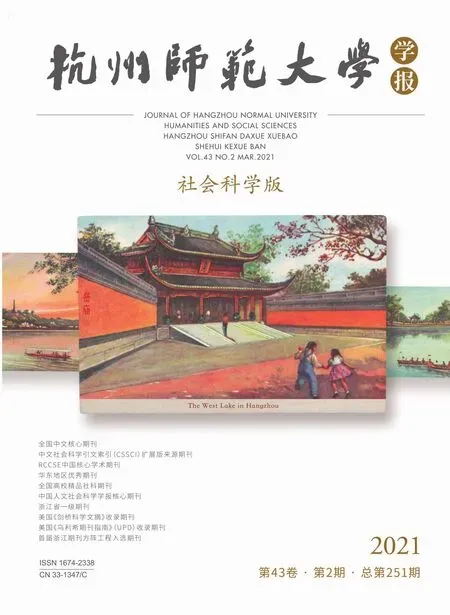章太炎《齐物论释》之经典解释学-释义学初探
李智福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
引 论
1906年6月,章太炎先生(1869-1936)“苏报案”出狱后流亡日本,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他给留日学生周氏兄弟、黄季刚、刘文典、朱希祖等陆续讲授《说文》《楚辞》《庄子》等经典,其中用力最勤者即《庄子》,后来乃成《庄子解故》《齐物论释》(1)关于此两书之版本源流,详参李智福《章太炎〈齐物论释〉“初本”“定本”版本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3月26日。等书。章太炎治学强调“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1](P.4),故他虽以朴学名世,但其学术之最后归宿当在玄学,玄学即今所谓哲学,其哲学的集大成者当即《齐物论释》。在学理上而言,他以唯识学的“真如”诠释庄子之“道”,重建庄学本体,并以此为基础而构建起一整套“内圣外王”的哲学体系,[2](PP.290-331)《齐物论释》是以解释经典为形式而进行哲学创构(刘笑敢语)的又一部典范。随着西方解释学研究在国内的方兴未艾,汤一介先生生前曾热忱呼吁构建中国解释学(偏重“方法论”或“释义学”的解释学)。(2)汤一介先生曾陆续发表五篇关于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论文,学界通称为“五论中国解释学”,包括《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1998年第13辑)、《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2期)、《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 ,2000年第7期)、《“道始于情”的哲学诠释——五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等五篇论文。相关述评可参考景海峰《汤一介先生与中国解释学的探索》,载胡军、孙尚扬主编《诠释与建构——汤一介先生75周年华诞暨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潘德荣《汤一介与“中国诠释学”——关于建构“中国诠释学”之我见》,《哲学分析》 ,2017年第2期;张志伟《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意义——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就西方解释学的两大传统即方法论诠释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与本体论诠释学(伽达默尔)两派而言,后者直面此在之在世而认为理解是一种存在状态,这无疑具有超越中西的普遍意义;前者则从《圣经》释经学(解释技艺)辗转而来故具有特殊性,而中国的经典诠释学无疑也具有特殊性。也就是说,在解释技艺的意义上,中西两种解释传统可能各具特殊性,这也是汤一介先生呼吁构建中国解释学时特别重视方法论解释学的本质原因,故本文所谓解释学-释义学主要即指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也即解释技艺。即此而言,一部“注不破经”的字词训释之作或许没有必要检讨其解释学-释义学,相反,只有发挥经典微言大义、返本开新的哲学创构作品才有必要去检讨它的解释学-释义学。章太炎《齐物论释》是一部“以注夺经”“创构哲学”的经典解释典范,考察《齐物论释》所持有的经典解释学-释义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就笔者看来,章太炎《齐物论释》的解释学-释义学主要有:(一)庄学与佛学的深度格义,以阿赖耶识、真如实相等重建庄学本体论;(二)“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3](P.71),包括以语义学分析重要名相和以近代自然科学分析庄学相关概念;(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与庄子进行心与心之映证,古今交发,以古衡今。正是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些解释方式,使得他的解释在进行哲学创构的同时,既保证了解释与经典之间的融贯,也保证了解释与解释的自洽。
一 “义有相征,非附会而然(佛学与庄学)”
古印度佛陀哲学指向“空”,而中国道家哲学则指向“无”,二者不尽相同,但不能否认老庄道家与印度佛学存在着一种先天的亲和性。佛学经典在汉化的过程中,首先即是以老庄道家的哲学术语对梵文佛经进行格义,“庄释玄同,东西理会”(《广弘明集》卷18)乃是当时僧俗两界之共识。随着学术史的发展,大量佛学经典被翻译为汉文,隋唐之后出现了大量以佛解老、以佛解庄之经典解释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之为“反向格义”(刘笑敢语)。前者是以老庄接应佛学,后者则是佛学反哺老庄,前者是佛学被老庄化,后者则是老庄被佛学化,《齐物论释》可谓是一千多年来以佛解庄传统之殿军。章太炎以佛解庄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与章太炎思想储备所形成的前识有关,章太炎并非一开始就接受庄子,其自诩其学为“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3](P.72),此中之“真”当即佛学,“俗”当指庄学,以庄之俗纠偏佛之真,将俗与真“等量齐观”(3)参见张志强《“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论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形成及其意趣》,《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3期;孟琢《齐物论释疏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转俗成真”阶段的法相唯识学为其后来以佛解庄提供了理论准备。其二,庄子哲学以“三言”作为哲学叙事方式,晚近以来则是科学昌明之世,故必须将庄学引向科学。法相唯识学与汉学(朴学)最接近科学,他理所当然地以法相唯识学为庄子进行圆理。其三,“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3](P.192),佛法驰骛于涅槃寂静是出世间法,其于世道人生毕竟有所不足,“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4](PP.62-63)。与出世间法的佛学相比,庄子哲学杂有世间出世间二法[3](PP.27-28)。以上三点理由成为章太炎以佛解庄之机缘,他坚信庄学与佛学“义有相征,非附会而然”[5](P.3),以佛学来格义庄学并非无本之木,其称庄学“圆音胜谛,超越人天”[6](P.137),盖非虚说。以下择其要而论之。
(一)以“阿赖耶识(藏识、持识)”释庄子之“灵府”和“灵台”
唯识学认为阿赖耶识为宇宙实体,一切万有皆缘起于阿赖耶识,宇宙万法为此识所变现,此佛教诸派皆无异议,但之于其本净抑或有染,诸派说法不同。虽大体都认为它是真常心与虚妄心之结合体,但其中之真常心为其根本,而虚妄心则是对真常心之遮蔽或污染,因此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当庄子对老子哲学之客观实体之道进行心灵提升和境界转化后,老子之“道”转变为庄子之“心”[7](P.214),与老子之学相比,庄学与唯识学就更近一层。唯识学的心学与庄子的心学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具有了原初契合性,此即章太炎以“阿赖耶识”解庄之根由,他认为佛学之阿赖耶识即是庄子所谓“灵台”和“灵府” [6](P.85)。章太炎云:“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6](P.78)对于《齐物论》篇首“三籁”一段风喻,章太炎完全以唯识学“八识”解之。百家物论纷争源于“我执”,而不知物、我之存在皆由心识(阿赖耶识)所变现,自心还取自心,故皆入虚妄。《齐物论》“与接为抅,日以心斗”一段描写世俗人生之种种忧患心态,这些皆是“自取己心,非有外界”[6](P.81),烦恼只是“己心”与“己心”的交相斗争。庄子所言“物物者与物无际”,物物者是见分,物是相分,“相见二分,不即不离”[6](P.79),相分为所取,见分是能取,相不在根识以外,意识起意恒审思量而误以为外,横起分别,以假为真,万物不齐,由是作矣。只有“泯绝人我,兼空见相”才能从万物纷扰中抽离出来,“彼相分自现方圆边角,……见分上之相分,本无方隅,而现有是方隅”[6](P.79)。万法之方圆边际本是相分,亦是我心之影现,故亦为见分,相分与见分皆无自性,心起而有,心灭即无。
大乘唯识学看来,万法唯识,唯识无境,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时空也不过是心识之变现,生死寿夭亦尽虚妄不真。按照唯识学相关理论,“过去-现在-未来”等时间皆由心造,时间不过是一种意识或者说是感觉,并无自性。既然时为心变,故不同主体之心对时间之长短感受亦不一,“时为人人之私器,非众人之公器”[6](P.82),孩童觉得时间流逝慢,中老年则觉得时间流逝快;淫乐之人,光阴不觉而飞逝,勤苦之人,则度日如年。时间只有相对长短而无绝对速缓,即“时分总相,有情似同,时分别相,彼我各异” [6](P.82)。这样,庄子基于相对主义而悉心论证的“大年小年之齐”“彭祖殇子之齐”被唯识学的“时由心造”而得到论证:“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而冥灵大椿,寿逾千百,庸知小年者不自觉其长,大年者不自觉其短乎。然惟证无刹那者,始能晓了刹那”[6](P.82),“一念心生,速疾回转,齐一刹那,自非应真上士,孰与于斯”[6](P.83)。既然时由心造,心不起时,时亦不生,故生死寿夭皆无意义。
章太炎以佛学格义庄学往往建立于小学基础之上,“将哲学阐释建立在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之上” [8](《前言》,P.8)。比如训“台”为“持”,梵文“阿陀那”本意为“任持根觉”,故“灵台”即为“阿陀那识”(“持识”),即对八识之总体持执;训“府”为“藏”,梵文为“阿罗耶”,“灵府”即为“藏识(阿罗耶识)”,灵府“含藏种子”;其将“以其心得其常心”之“常心”解释为“庵摩罗识”。[6](P.85)庵摩罗识为清净识、无垢识、真如识,是对阿赖耶识之识。我们看到,《齐物论》中所有与“心”有关之术语皆被章太炎“格义”为“阿赖耶识”或近似的最高之识,庄子对齐物之证成变成唯识学种种“心法”与“心所有法”,万物齐否,取决于观者之自我修持之高下,“唯证得庵摩罗识,斯为真君,斯无我而显我耳。是故幻我本无而可丧,真我常遍而自存” [6](P.85)。 “吾丧我”意味着幻我丧而真我存,真我实则即是无我,“言我芒人亦芒者,无量有情,等是一识。若有一人不芒者,则不得现此情界器界也”[6](P.86)。芒是无明,不芒即意味着亲证真如,亲证真如即是“吾丧我”,万物因此而齐。总之,阿赖耶识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万法之源,境由心造,识外无境。故万物皆无自性,一切差异皆“诸心相构,非有外尘”[6](P.114)。只有转识成智,体证真如,才能得大自在之齐物之境,这里通过庄佛互相格义完成了庄学的本体重建。
(二)以佛学“无尽缘起”释庄学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大乘佛学普遍认为,一切万法比如大地山河、一切有情无情皆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散尽而灭。《大智度论》所谓“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第一印说缘起,第二印说无性,第三印说实相。一切万法皆为假有不真,执著万法便会生种种虚妄,只有了悟无相之实相,涅槃寂静,乃能得解脱。华严宗在此基础上创“法界缘起论”之四法界说。法界缘起论认为现象界即是真如界,除现象界外别无实相界,以诸尘而见法界。其将“缘起性空”在时空三维中无限延展,因无穷无尽之缘起构成宇宙世界,整个宇宙万法融通。华严四法界中“事事无碍法界”是最高法界,缘起无尽,法界重重,万物(事)皆无碍自在,只有了悟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才能在万象森罗中亲证真如,涅槃自在。章太炎以“缘起性空”说证明万物存在皆无自性,对万物存在之独立性进行消解;其以“无尽缘起”说证成“万物与我为一”;其以唯识、华严“三性相”又将“齐物”之说归之于心。
关于《齐物论》中“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一段,章太炎认为此段“破名守之局,亦解作用道理,证成道理之滞,并空缘生”[6](P.94)。此处所谓“空缘生”即因万法缘生而证一切本无自性,缘起性空。章太炎解释“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云:“此生彼灭,成毁同时,是则毕竟无生,亦复无成。”[6](P.99)此物之成即彼物之毁,此物之死即它物之生,一切皆是因缘聚散,念念迁谢,稍不暂住,成毁道通,此与法藏“六相圆融”亦相近,庄子言“道通为一”是证“齐”,华严“六相圆融”是破“执”,唯庄子更多是一般意义上的思辨,华严却更有形而上学之味道,二者可谓殊途同归。《齐物论》之“罔两问景”章也是在说“缘生”:“夫晷景迁驰,分阴不驻,此为自无主宰,别有缘生,故发罔两问景之端,责其缘起。”[6](P.130)只有了悟万法性空才能遣执荡相,齐物逍遥皆因此而证成。
如果说,章太炎以“缘起性空”解庄是从否定方面对万物独立实在性之消解,那么他更引“无尽缘起”说从肯定方面来证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若云无者,我身则无;若云有者,此非与天地并起邪?纵令形敝寿断,是等还与天地并尽,势不先亡,故非独与天地并生,乃亦与天地并灭也。若计真心,即无天地,亦无人我,是天地与我俱不生尔。”[6](P.107)水火金铁是构成天地万物之共同本质,因缘际会而形成万物,有生无生皆是相对,皆无自性,有无一体,生灭一如。故天地万物皆因我的虚妄心而获得存在,当我的妄心灭、真心现时,天地万物也就不存在而当体即空。《寓言》篇“万物皆种”之说即《华严经》《楞伽经》所言“无尽缘起”[6](P.127),万物互相为种,成住坏空,不稍暂驻,“一有情者,必摄无量小有情者”[6](P.111),一多相摄,重重无尽,天人万物本为一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章太炎复引法藏《法界缘起章》《华严经指归》及十钱喻、椽舍喻等大量篇幅论说“无尽缘起”,并最后得出结论:“凡此万物与我为一之说,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之说,无尽缘起之说,三者无分。”[6](P.113)大乘佛学“缘起性空”是对现实世界之消解,“无尽缘起”是对现实世界统一性之证成,最终都要会之一心。章太炎复引入华严宗、法相宗之“三性相”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三种性相,“依他遍计等义,本是庄生所有,但无其名”[6](P.137)。世人之所以见万物之种种不齐、分别、优劣,皆是因“遍计所执”而妄生分别,不悟一切有为法皆梦幻泡影,依他起自性,故迷自性,生种种愚妄;只有亲证圆成实性,亲证一切有为法皆为幻相,故无增减,亦无生灭。庄子之“齐物之境”实则即是“圆成实性”:“若依圆成实性,唯是一如来藏,一向无有,人与万物何形隔器殊之有乎!”[6](P.114)在章太炎看来庄子已经证悟圆成实相这种究竟真实。
(三)以“三世轮回”释庄子之“梦”与“化”
“三世轮回”是大乘佛学诸派普遍认可之理论。轮回理论本来自古印度婆罗门教,后被佛教部派加以利用和改造,认为自无量劫以来,众生因无明而造业,因贪、嗔、痴三毒而招感,在三界六道中生死流迁,似车轮之旋转,周而复始,永不休止,故称轮回。轮回理论传入中土之后,又与中国民间之轮回信仰相结合,很快生根发芽,庐山慧远结合因果报应和三世轮回理论创建净土宗。庄子哲学中关于变化(“化”“物化”)理论和关于对梦觉关系的思辨与佛教的轮回理论有些“神似”,因此故,“三世轮回”理论被章太炎用来对庄子之“齐物”哲学进行证成。
《庄子·庚桑楚》有所谓“移是”之说,郭象认为其本意是“是无常在”[9](P.708),是非皆随境转移,章太炎却以“轮回”解之。庄子“移是”之意是说每个思考主体皆以我为本,以知为师,师心自用,故是非在每一个思考者中皆无定准,心随境转。章太炎则认为“移是”是“向之移是为今之人,今之移是为后之人”,言外之意,“移是”乃是生命主体之轮回和流转,一切流转皆是“因业所感,取趣有殊”[6](P.132)。不惟如此,在章太炎看来汉译佛典之“因果”一词,亦源自《庄子·齐物论》,“《庄子》所言果,与佛典之果同义”[6](P.132),可见庄子是深知因果轮回之人。《齐物论》终篇之寓言“庄周梦蝶”,此非论梦觉而是以梦觉隐喻“轮回之义”,每一个轮回中之主体既不能识前生,亦不能知来世,也就是说轮回中之前生、来生皆无现量,只是靠比量(推理)而知。依比量推知轮回又近似专断,故庄子以“卮言”言说之:“佛法所说轮回,异生唯是分段,生死不自主故。圣者乃有变易,生死得自主故。……而庄生亦无异文别择,皆以众说不征,不容苟且建立,斯其所以为卮言欤。”[6](PP.138-139)佛教轮回说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之上而庄子却无道及“因果报应”,原因何在?“六趣升沉之说,善恶酬业之言,……理有必至,而庄生无文焉。”[6](P.139)因果律是轮回果报说之基础,而因果律又是必然律(“理有必至”),言或不言,皆不碍因果律(因果报应)发生作用。
庄子看来,化是万物的存在方式[10](PP.111-118),一切万物皆在或隐或显的永恒变化之中,人之生死为气之聚散,聚而为生,散而为死,故生死本质是一种变化,所谓“万化而未始有极”,郭象解释为“有变化而无生死”,这是一种基于自然元气论的宇宙存在论。章太炎却以“轮回”学说解释庄子之“物化”“万化”“化”等变化理论,将庄子宇宙生成论意义上的“变化”解释为“轮回”。自无量劫以来,一切有情众生都在轮回之中,鼠肝、虫臂、蝴蝶可能都即是曾经之“我”,因此,“(若)达者知其如是,不厌转生,虽化为鼠肝虫臂,未见有殊”[6](P.99),轮回中之万物皆“不齐而齐”。“觉梦之喻,亦非谓生梦死觉。大觉知大梦者,知生为梦,故不求长生;知生死皆梦,故亦不求寂灭”(4)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齐物论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3页。此处标点与原文稍异。,庄子以梦觉而隐喻轮回,并不是要求人们寂灭,每一个轮回皆是天倪所在,众生平等,从而排遣生死,得其解脱。职是之故,章太炎认为庄子的“逍遥”即佛学的“常乐我净”:“若乃所以遍度群伦,偕诣极地者,《消摇游》已陈其说,离于大年小年,无有大知小知,一切无待,体自消摇,斯即常乐我净之谓。”[6](P.143)“常乐我净”是所谓涅槃四德,也就是亲证如来之境。在《菿汉微言》中,章太炎将佛教之“常乐我净”与庄子思想一一相映证,“无待”是常德,“逍遥”是乐德,“无待之我”之我德,因“无待”而“证无垢识”是净德。[3](P.38)应该说,章太炎这种“字字可解”式的“格义”,无论是质诸佛还是质诸庄,大概两家都不会同意,但若抛开“名字相”“言说相”,以“常乐我净”解释“逍遥”和“无待”,应该说把握了释迦、庄子二者的精神实质。章太炎以“常乐我净”解释“逍遥游”置诸《齐物论释定本》的篇末(《齐物论释初本》未见此语),正可见这是他解庄的“会归”之所在。所谓“遍度群伦,偕诣极地”,以每个人的“常乐我净”实现天下的“常乐我净”,此即章太炎以佛解庄之苦心孤诣。
二 “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
佛教史上称世尊说法四十九年三百余会却无一字可说。在大乘佛学看来,语言、名相、典籍是释迦智慧之载体,释迦通过合乎逻辑规范的名相分析、言说思辨的形式对现象世界进行彻底消解,以证成大千三界悉归虚无,唯识无境。同时,佛教承认实相无相,而名相思辨本身也是对真如实相的障碍,法平等性既不可说,亦不可知,故分析名相之后也必须排遣名相。章太炎云:“(慈氏、世亲之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3](P.71)法相唯识学这种哲学思辨的方法成为他以唯识学解庄之重要方法。大乘佛学这种“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思辨方法与中国晚周之老子、庄子等所谓“道言悖论”“齐言悖论”如出一辙。道体不可言说,齐物之境也不能言说,欲究终极本体,达到齐物深境,必须排遣名相、放弃言说。不能言说之道被言说,而言说却又遮蔽道体,因此,老庄之学表现出强烈地对语言名相进行排遣的自觉意识,此与佛学洵非二致。
(一)“真如-名言之悖论”与“道(齐物)-名言之悖论”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分析名相”在唯识学中兼具方法义和本体义,既是其哲学论证的一般方法,也是其泯相显实而构建本体的方式,二者不一不二,不过此文更强调其作为一种哲学诠释的方法。整部《齐物论释》在形式上全部是对《齐物论》的名相思辨,这与郭象解庄“辨名析理”近似,但其超越郭象者在于以唯识学、中观学、大乘空宗等佛学概念与庄学概念进行比附,然后既对佛学名相进行思辨,又对庄学名相进行思辨,二者水乳交融,合为一炉,难分彼此,这种平等的言说就是所谓“字平等性、语平等性”。然而,不惟如此,章太炎看来,“人心所起,无过相名分别三事,名映一切,执取转深”[6](P.73),故分析之后不忘排遣,只有彻底排遣名相,亲证真如,才能实现齐物境界,章太炎云:“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自非涤除名相,其孰能与于此。”[6](P.73)大千世界一切有为法,皆由心造,故为心识,因识生相,因相生名,因名而起寻思,因寻思而起分别,章太炎根据《瑜伽师地论》卷36,指出世亲言世间种种分别、无明所起之根由即“四种寻思”[6](P.74),即名寻思、事寻思、自性假立寻思、差别假立寻思。章太炎以《齐物论》四句话进行“格义”,以《齐物论》“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比附第一种寻思,“言者有言,即于名唯见名也”;以《齐物论》“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比附“第二种寻思”,“即于事唯见事,亦即性离言说也”;以《齐物论》“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比附“第三种寻思”,“即于自性假立唯见自性假立也”;以“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比附“第四种寻思”,“即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也”。[6](P.75)名、事、假立自性、假立差别皆是万物不齐之根由,因此必须扬弃和涤除,而《齐物论》“指马之喻”就是隐喻“无执则无言说”,庄子引公孙龙子“指马之喻”却反其道用之。章太炎进而认为,“可言说性非有,离言说性非无”,可言说之性并非实有,因万物皆为心造,无自性故言“非有”;离言说之性才是实在,因此说“非无”,不可言说之真如实性就是齐物之境。《齐物论》对名相之排遣与《瑜伽师地论》暗合,真如实性不能言说,一如齐物妙境亦难落言筌,“以论破论,即论非齐。所以者何?有立破故。方谓之齐,已与齐反,所以者何?遮不齐故”[5](P.7),齐物之境不可言说,当你对“齐”进行言说时,实则是对“齐”之否定(“遮”),遮之则不齐,不遮则齐,一切言说皆是对齐的遮蔽,故《寓言》篇云“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
章太炎更引《大般若经》证明此说:“若于是处,都无有性,亦无无性,亦不可说为平等性,如是乃名法平等性。当知法平等性既不可说,亦不可知。”[6](P.75)《大般若经》此语“正会《寓言》之旨”,后引《楞伽经》“我与诸佛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之语亦“与《寓言》所说,亦如符契” [6](P.76)。可见,无论是庄子的齐物之境还是释迦的真如之性皆不能言说,但庄子、释迦毕竟都已经有言说。庄子、释迦之所以要对“道”和“真如”进行言说,乃是自悟而悟他,广利有情,布道传慧,“迹存导化,非言不显,而言说有还灭性,故因言以寄实”[6](P.75)。此即《寓言》篇所谓“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道必须靠言说来显现自身(“言以寄实”),而言说本身无自性(“有还灭性”),因此言说也无妨,但切记不可执着名言,而且必须涤除名相,只有彻底消解名相,道与真如才能自在涌现。总之,名言是虚无的,但世人生活在一个名言的世界里,“画空作丝,织为罗縠”[6](P.101),作茧自缚,不能自解,要了究竟实相就必须排遣名相。“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是齐物之真义。齐物之境不可言说,大道之体难落言筌,而且这种“不可言说”“难落言筌”也终不可言说,这无疑都能得庄子要领而原来有自。可见,所谓“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分析”突显的是方法论,而“排遣”则更兼具存在论之意义。人生活于一个名言之世界,只有勘破名言之封执,才能见自在之真如,大千世界悉归平等(齐物之境)。
(二)让庄学变成科学,以科学为庄学和佛学去魅
与重视名相分析相关,章太炎特别重视实证主义,即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对名相进行分析,他有以科学解释玄学(哲学)的抱负,其试图让庄学走向科学。陈少明教授观察到,严复以来的中国大多数知识人都有一种“科学情结”[11](PP.17-23),这种“科学情结”固然与近代西方学术的渗透有关,但也与清儒的汉学(朴学)传统一脉相承。章太炎早年服膺朴学,中年崇尚佛学特别是法相唯识学,其云:“(法相学)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3](P.71)朴学与唯识学之内在关联是什么,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给出了答案,朴学与唯识学的共同特点就是科学:“近世三百年来,学风与宋明绝异。汉学考证,则科学之先驱,科学又法相之先驱也。盖其语必征实,说必尽理。” [3](P.192)职是之故,章太炎治学始终渗透着一种朴实的科学精神,王中江教授以韦伯之“近代世界的祛魅”理论来解释章太炎之理性主义态度[12],可谓公允。章太炎以科学的态度对大乘诸派进行判教并最终认定法相唯识学是释迦真传,当他以渗透着科学精神的法相唯识学解庄时,《齐物论释》因此而理所当然地渗透着一种科学实证的味道,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襟抱之一即让庄学变成科学,以科学为庄学祛魅。
在对《齐物论》“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一段文献解释时,章太炎引入脑髓、神经这两个近代自然科学领域之概念,之所以说脑髓、神经并不能成为人体之“主宰”[6](P.85),是因为脑髓、神经也不过是血肉组织(“筋肉膏肪”),这和身体中其它器官并无本质区别;况且,单细胞动物以及花草树木虽没有脑髓、神经,但也有生命,有些植物可以吃苍蝇,但并没有指使其去吃苍蝇的脑髓、神经,可见脑髓、神经并不能成为人体的真宰。但人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当有一个幕后的决定者,这个幕后的决定者就是“真我”,“真我”就是“真宰”,也就是佛学中的阿赖耶识。显然,章太炎在证成“真宰”即“阿赖耶识”的过程中用了自然科学实证的方法。章太炎在解《齐物论》“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时,引入语言学、语义学相关问题进行论证。他以实证的态度指出,语言是用来表义的,但同一个义可以用很多种语言来言说,可见名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6](P.90)人不能听懂鸡鸣犬吠之意义也听不懂操陌生语言的人说话,可见语言、名相本身并无意义(“向无定轨”),而其意义是人心所赋予的(“惟心所取”),一切唯心,名言亦不例外。章太炎通过语言学实证的论证方式将一切言说的意义进行消解,从而证成庄子所谓“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章太炎将隐训为凭)是正确的。关于《齐物论》一段文字:“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按《齐物论》这段文字旨在说明一切对万物存在动因之追寻都是毫无意义的,其强调万物存在的背后并没有一个“造物者”或“第一因”。章太炎引入当时自然科学中之化学概念“细胞”[6](PP.95-96),人由细胞构成,既然万物都是动的,那么细胞作为万物之一种,因此也应该是动的,至于万物为何动,乃是因为万物内在皆有动力,动力来自哪里,动力即万物之自然属性。这样,对细胞何以动之原因追寻最后归之于细胞之自然,这是一种无意义的解释回圈(黑格尔所谓“恶循环”),其实也就相当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见我们并不能找出细胞之所以动的最后原因。同样,如果说知母、苦参能退热乃是因为知母、苦参含有退热成分,那么冰雪本身是凉物(即退热成分),何故服之却不能退热,这样说来,知母、苦参之所以能退热之原因并不能找出最后根由。再比如,井水现丹是因为水中有澒,朽骨发焰是因为含有磷。至于澒何以能现丹,磷何以能燃烧,却不得而知,因为这是它们的本身属性。章太炎以当时进步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庄学提供了进一步证明,庄子“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这种思想不仅是思辨的,而且是可以实证的。
又如,章太炎以物理学知识解释“天地与我并生”:“今应问彼,即我形内为复有水火金铁不?若云无者,我身则无;若云有者,此非与天地并起邪?”[6](P.107)这时以人与天地万物的物质统一性上论证“天地与我并生”。同时,章太炎解此语亦引入《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之说,认为这个“种”即指分子、微分子[6](P.110)、原子、细胞[6](PP.112-113)等物理学概念;其论证黄金颜色与黄金物质相分离时(相当于“白马非马”),引入光照原理[6](P.110);其解《齐物论》寓言“罔两问影”引入光的传播原理,“罔两”待影,影之成待物和光,光之传播靠“游气”,“游气”传播靠的是“伊态尔”(即energy)[6](P.130),而“伊态尔”究竟是什么,无从知晓,缘缘相推,未有了境,这样,“罔两问影”所隐喻的哲理与佛学“缘起性空”之说并无不同,自然科学、庄学、佛学被章太炎理所当然地熔铸于一炉。
总之,佛教诸派中,唯识学最近科学;既然唯识学接近科学,那么唯识学相关理论必然能得到科学之证明。同样,如果说庄子哲学是超越古今中西的真理,那么这种真理必然也能经得起自然科学的证明,否则,庄子的真理义就会大打折扣。在近代科学昌明之世,让庄学仅仅停留在玄思层面是不够的,要真正发挥庄子“利用厚生”之道,必然要引庄学走向科学,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庄学祛魅。当然,章太炎以自然科学解庄之论证过程,一方面受时代限制,在今天看来,其自然科学知识并非没有错;另一方面,庄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其以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庄子的古典理论进行证明,可能终究会隔上一层,其中不乏诡辩色彩。
三、“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齐物论释》涌动着章太炎先生本人的才情气质、忧患意识、担当精神,字里行间风发泉涌,元气淋漓,此书是章先生本人的生命在场,可谓是孟子所言“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注经实践。“以意逆志”是一个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中国古今经典解释学传统,事实上,我们在中国古今大量的读书法、治经法、论学法中到处可以看见这种解释传统的影子。比如:司马迁看到古简的碎片强调“书缺有间矣”,“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13](《五帝本纪》,P.46);郭象解《庄》特别说明“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9](P.3);王安石强调读书要“善其为书之心”[14](P.242);朱子论读书法强调“文字血脉”[15](P.2632);王阳明解经强调“在自心上体当”[16](P.69);方廷珪注《文选》强调“得作者之用心”[17](P.1);章学诚特别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当“论古必恕”[18](P.278);以及今人陈寅恪提倡对古人“了解之同情”[19](P.247),徐复观强调读书论诗应“追体验”[20](P.232),唐君毅强调论诸子要“略迹原心”“求吾心直契于古之心”[21](P.47)。这些古今说法固然有微妙的不同,限于篇幅,此处不能一一展开,但这种读书法、读史法、解经法等解释传统都强调解释者对经典或古人的“神交”“心解”或“体贴”,以解释者之“心”对经典之“心”进行“把捉”“体贴”“印证”从而给予同情理解式的深度诠释以避免隔靴搔痒之病。这种解释传统的个中悖论是:解释者在解释经典过程中至少在形式上和主观动机上以追求经典原意为鹄的,但在实际的解释过程中,由于强调的是“心”与“心”的“神悟”与“体贴”而相对忽略文本和语言本身,往往使得思想的重点由经典转向解释,由古典转向现代,“我注六经”变成“六经注我”,经典因此而获得新的意义,这是中国哲人进行哲学创造的重要范式。
(一)乱世庄学:以庄子之世道论庄子之用心
章太炎《齐物论释》形式上虽然是以佛解庄,但其超越传统以佛解庄远甚,这种超越不仅是以法相学这种科学解庄,更在于其超越佛学而抉发庄学“内圣外王”之道。章太炎抉发庄学“内圣外王”之道首先即是以近乎是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式去体贴庄子为何写《齐物论》,他在《序》中以沉重的笔调写到:“昔者,苍姬讫录,世道交丧,奸雄结轨于千里,烝民涂炭于九隅。其唯庄生,览圣知之祸,抗浮云之情,盖齐稷下先生三千余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5](P.3)若非是以心与古人进行神交或体贴,章太炎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文字。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篇中云:“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18](PP.278-279)章太炎的庄学诠释学可谓是从孟子到章学诚“尚友古人”“知人论世”“论古必恕”这一中国古典解经传统的典型。这里将古代文献中关于庄子的一系列记载(包括“寓言”)进行一种哲学发生学意义上的心理还原,章太炎是在用“心”去追问(“追体验”)庄生一言一行背后的心理依据和现实依据是什么,追问的结果是,庄生创作《齐物论》是要匡正天下、拯救生民。所谓“苍姬讫录,世道交丧”,“苍姬讫录”用赵歧《孟子题辞》之语,是指姬周季世,他认为天下乱离、生民涂炭皆源于圣知之祸,故他志抗云表,不屑与“不治而议论”之稷下先生为伍;当然他也不是避居山林之隐者,因为尚不能忘怀世情,故甘作“抱关击柝”之士(庄子任“漆园吏”之事);他拒绝楚相是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之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盗贼,他需要对政治社会更深刻之理解,故不为政客而仅为哲人。章太炎用《易传》“作论者其有忧患乎”一语与《庚桑楚》篇“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徐无鬼》亦有类似之语)一语互相发明,他意识到晚近世界的局势正是庄子所预言的“人与人相食”之世(“今适其会也”)。章太炎正是带着这种对世道的忧患之“心”体贴处于“苍姬讫录”时代的庄子之“心”,从而抉发《齐物论》中的“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上悟唯识,广利有情”[6](P.76)或“内存寂照,外利有情”[6](P.118),他援引《天下》篇“内圣外王”一语来表达他所理解的庄学真精神。不难发现,“内圣”即指“上悟唯识”或“内存寂照”,“外王”即指“广利有情”或“外利有情”,然而,庄子果然能了悟“究竟实相”吗?可能是否定的,至少我们没有任何历史、文献的根据。不过,正是立足于心与心的印证,解释与经典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思想弥合,达成这种思想弥合的媒介并不是语言而是心,章太炎以自我之心去体证庄子之心,最终认定庄子之学是内圣外王之道。
(二)以古典思想观照时代:庄子哲学的周延性在于庄子之心
《庄子》寓言中,章太炎最看重的是《齐物论》中“尧伐三子”章。他评骘这则寓言云:“精入单微,还以致用,大人利见之致,其在于斯。”[6](P.77)《齐物论释·释题》中最后提到这则寓言并认为这是庄子“终举”之所在,是一篇《齐物论》之最后归宿,关乎着整部庄子哲学的“微言大义”。那么,这则寓言究竟何以能让章太炎如此“神往”呢?郭象曾以“物畅其性,各安其所安”[9](PP.85-86)解之,在章太炎看来“子玄斯解,独会庄生之旨”[6](P.118)。郭象认为逍遥是对自我性分之体认,本身即蕴含了一种“存在即是平等”的立场,这种基于“自我体认”的平等观若换一个视角即是“互相尊重”,章太炎因此而引申出“文野异尚”的理论:“(《齐物论》)终举世法差违,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于娴,两不相伤,乃为平等。”[6](P.76)“原夫《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贯利,无所慕往。飨海鸟以大牢,乐斥鷃以钟鼓,适令颠连取毙,斯亦众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6](P.118)庄子之学是“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之学,“齐物”的题中之义即是对差异的尊重,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独异个体甚至是“野蛮民族”也要等而视之,这就是所谓“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也”。宗、脍、胥敖虽处于蒙昧状态,但舜看来,即使如此,也不应该以“文明”“开化”“仁义”等“高义”去征伐他们,此正是“世情不齐,文野异尚”。章太炎云:“小智自私,横欲以己之娴,夺人之陋,杀人劫贿,行若封豨,而反崇饰徽音,辞有枝叶,斯所以设尧伐三子之问。”(5)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齐物论释定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页。此处用孟琢《齐物论释疏证》书中之标点,与王仲荦标点稍异。一些国家以“使彼野人获与文化”为名,蚕食弱国,不仅得兼并之实且得高义之名,使得一切侵略、屠杀、劫掠皆名正言顺,而事实上却是大道凌迟,正义缺位。
因此,章太炎指出:“下观晚世,如应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圣智尚文之辩,孰为之哉。”[6](P.76)这大概即在影射社会达尔主义、黑格尔主义、甚至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主义(康有为反复强调“大同世”是去野蛮而进文明之世),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文明民族高于野蛮民族,故文明之国有理由去征服野蛮之邦,这使得征服者师出有名,故可以说“文野不齐之见”是“桀跖之嚆矢”(先锋)。章太炎以著名的“葛伯仇饷”(《孟子·滕文公》)为案例来论证之。孟子虽然反对杀人(“善战者服上刑”),但承认商汤以“放而不祀”为理由消灭葛国是正当行为。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祭祀”是当时主流文化之传统,但葛国并没有“祭祀”这种传统,“放而不祀,非比邻所得问”,即“祀与不祀”是一国之“内政”,邻国无权过问,但商汤为铲除其征服天下之羁绊,因此不惜用种种计谋,这实质是“借宗教以夷人国”。不过,这种灭国征服的行为以“仁义之师”为名号,因此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以至当时竟有“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孟子·梁惠王下》)的说法,诸侯四夷都盼着商汤前来征服。章太炎云:“今之伐国取邑者,所在皆是,以彼大儒,尚复蒙其眩惑,返观庄生,则虽文明灭国之名,犹能破其隐匿也。”[6](P.118)“灭国之师”被称为“仁义之师”,大儒孟子亦被其迷惑,更何况其他人。可见,“文野不齐”为文明灭国之罪魁祸首,而庄子“齐物”说之可贵处正在于能遮拨其中之隐匿,“向令《齐物》一篇,方行海表,纵无灭于攻战,舆人之所不与,必不得借为口实以收淫名,明矣”[6](PP.118-119)。思想的洞见纵使不能阻止“剑”地滥杀无辜,却足以让不义之行大白于天下,这大概就是“笔”的无用之用吧。以古典精神观照时代是经典生命力之所在,也是解释之意义之所在。
(三)从佛陀的“以佛陀心为心”到庄子的“以百姓心为心”
正如张志强教授所指出:“《齐物论释》是‘转俗成真’的至高点,同时也是‘回真向俗’的原理起点。”[22]换言之,章太炎“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这两次重要思想转捩都集中在《齐物论释》一书中。其中,从“回真向俗”方面来看,章太炎是以庄学之俗取代佛学之真,是以佛学“以佛陀心为心”的涅槃妙心转胜为庄学“以百姓心为心”的随俗任运之心,这种对庄佛之异的哲学考察正是章太炎“以意逆志”的结果。在解释“庄周梦蝶”时,他正是用自己之心去体贴庄子之心,从而看到庄子的“百姓心”:
(庄生)特别志愿本在内圣外王,哀生民之无拯,念刑政之苛残,必令世无工宰,见无文野,人各自主之谓王,智无留碍然后圣,自非顺时利见,示现白衣,何能果此愿哉。苟专以灭度众生为念,而忘中涂恫怨之情,何翅河清之难俟,陵谷变迁之不可豫期,虽抱大悲,犹未适于民意。夫齐物者以百姓心为心,故究极在此,而乐行在彼……外死生,无终始,即知一切法本来涅槃,应化不尽,即毕竟不入涅槃也。[6](PP.141-142)
庄子《齐物论》卒章寓言“庄周梦蝶”,在章太炎看来庄子是在隐喻轮回,“庄生多说轮回之义,此章本以梦为同喻,非正说梦”[6](P.138),故庄学与佛学六道轮转无异。但庄与佛所不同者在于,佛以轮回为苦,故以摆脱六趣、寂静涅槃为解脱之道;庄子却不以轮回为苦,随顺生死,任其轮转。“原夫大乘高致,唯在断除尔焰,译言断所知障,此既断已,何有生灭与非生灭之殊”[6](P.140),大乘高致已断所知障,即已经领悟无上正觉菩提智,故能超越生灭与非生灭之殊,庄子已然超越生死,轮回与否对其已经毫无意义。然则,庄子还是多次言及轮回,此何以故?章太炎看来,“菩萨一阐提,知一切法,本来涅槃,毕竟不入,此盖庄生所诣之地”[6](P.140)。庄子尽管已超越轮回之见,但终究不能涅槃,是因为不能舍弃众生,其轮回之说是“欲人无封执”的“机权”之语。换言之,众生并不能都有“大乘高致”之觉悟,因此他不得不说以轮回之理让众人消解生死之封执,从而能随顺生死。庄子已然是大乘菩萨或大悲阐提,庄子不以灭度众生为念是因为“难忘中涂恫怨之情”,“(庄子)知一切法本来涅槃,应化不尽,即毕竟不入涅槃也”[6](P.142),庄子深知涅槃而不入涅槃,其齐物哲学是以百姓心为心而不是以佛陀心为心。庄子抱有大悲,怀有大愿,断所知障而不断烦恼障,顺时利见,白衣说法,大有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之精神,不过他不是让众生涅槃成佛,而是让百姓立足世间而随顺生死。
不难发现,章太炎这段解释文字距离《齐物论》“庄周梦蝶”原文已经迂回不少,但这种解释的确是庄学史上对“庄周梦蝶”最精彩的解释之一,这种解释是自洽的、融贯的,他以佛学解释庄学,又以庄学超越佛学,他以“心知其意”的方式为庄子的“轮回”观进行圆场,解决了“永在轮回”的庄学与“超越轮回”的佛学之间的两难。庄子白衣示相,本来涅槃而毕竟不入,他以否定之否定这种精湛的解释技艺让庄学成为兼世间出世间二法之学。章太炎通过对庄子“为书之心”的追问,将驰骛于彼岸世界的出世宗教进行了此岸世界之还原,也让立足于此岸世界的庄学有了超越涅槃的大乘高致。
总之,《齐物论释》在侧重“名相分析”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与古人的“心灵交融”。如前文所指出,章太炎用《易传》“作论者其有忧患乎”一语与《庚桑楚》篇“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一语互相发明,意识到晚近以来的世道正是庄子所预言的“人与人相食”之世。章太炎正是带着对近代乱世的忧患之“心”去体贴处于战国乱世的庄子之“心”,从而抉发《齐物论》中的“内圣外王”之道,让两千年之上的庄子来拯救两千年之下的天下与中国。同样,他以佛学解释庄学而没有流于出世间法的理障,其对“庄周梦蝶”的诠释也是对庄子哲学之“用心”的同情体贴,庄子形象被他的菩萨行情结理所当然地塑造成誓不成佛的大悲阐提,这种迂曲诠释的背后依旧是古今两个心灵的凑泊。如果说,伽达默尔的“前理解”学说始终强调的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存在论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在追问解释过程中“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23](P.481),即“解释”不过是一种“此在”不自觉的在世方式,那么孟子“以意逆志”这种理论恰恰强调的是一种自觉地、积极地、有意识地去神交古人、体贴经典(当然,背后依旧有“前理解”的影响,此非本文的问题),事实上,这构成中国解释学中一个极重要的传统。如前文所引述,这种解释传统在中国经典解释实践中源远流长,直至陈寅恪先生强调对古人思想要“同情之了解、徐复观先生强调读古书要“追体验”、唐君毅重视“略迹原心”等犹是这一解释传统的现代表达。章太炎《齐物论释》应该说是这种解释传统的一次成功落实,不要小瞧这种传统之于章太炎庄学解释学的意义,其所谓“庄子特别志愿本在内圣外王”云云,庄子的“特别志愿”是解释者对经典进行“以意逆志”的结果,正是得力于这种“以意逆志”的解释传统才最终发皇了庄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才将佛教的出世间法和佛陀心还原为庄子的世间法和百姓心。若不是他“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语),很难想象他的解释有如此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结 语
《齐物论释》作为一部经典解释之名著,若依刘笑敢先生对经典解释中“哲学创构”的三种范式之划分,《齐物论释》既不是王弼式的完全“顺向”,也不是郭象式的完全“逆向”,而是朱熹式的“徘徊”,是将“历史的、文本的解说”与“当下的、理论的创造”[24](P.134)两相结合。《齐物论释》是哲学创构的典范,解释者为经典重建本体,并将经典之本意进行纵深推进,以古典的精神世界来表达现实关怀。这种解经范式实质上是中国经典解释史中的一种重要传统,我们不妨用《易传》“钩深致远”这四个字来表示这种传统。钩深即发掘经典之深意,化潜为显,致远是以古论今,表达现实关怀,以经典观照时代。章太炎曾批评清代史家赵翼云:“近世如赵翼辈之治史,戋戋鄙言,弗能钩深致远,繇其所得素浅尔。” [25](P.335)赵翼训史考异却不能看到古史作者的深意,不免流于素浅。章太炎虽尚经古文学,但始终强调的是,“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庶几无愧于作者”[25](P.335),只有通过“古经说”而发现“新思想”,这样的解释才有更深远的意义。钩深致远意味着将经典本意向纵深推进,实则也就是通过“古经说”而发现“新思想”,其钩深经典的能力与经典的致远能力始终是成正比的,其钩越深其致越远,这样才能实现经典诠释学的返本开新,以古观今。“钩深致远”意味着将经典的隐题变成显题,将经典的实谓变成创谓,[26](P.10)当这种将经典本意进行纵深推进并达到一定程度时(标志之一即是否重建经典本体),经典解释就变成哲学创构。
《齐物论释》可谓是通过“钩深致远”而实现“返本开新”“哲学创构”的经典诠释典范。本文所提炼出来的这几种章太炎之经典解释学-释义学从来都不是单独被使用的,而是结合在一起并力发用。佛学与庄学的深度格义使得“大而无当”“犹河汉而无极”(《庄子·逍遥游》)的庄学变成像法相学、华严学一样有“阿赖耶识”这种本体论和认识论自觉的哲学,让庄子以“三言”为主的哲学叙事方式变成“语必征实、说必尽理”的科学理论;“名相分析”本来也从法相一系的佛学而来,章太炎始终相信一切学问以语言文字为本质,《齐物论释》对庄学中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都做了辨名析理,但其与晋人的分析不一样,他分析名相是为了排遣名相,从而对真如实相进行遮拨,正如真如实相不可言说、不可思议一样,庄子的“齐物”也必须“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如果说前两种释义方式侧重于文本和语言,那么第三种释义学即“以意逆志”则侧重解释者之心与经典作者之心的交相映证,逆觉体证,神交古人;同样,如果说前两种释义方式侧重庄佛之同,则第三种释义方式侧重庄佛之异,把出世间法的佛学还原为世间法的庄学,章太炎通过让自己的心灵与庄子的心灵冥契,使得庄学穿过佛学的层层理障而直接与世间众生照面,无论是对“庄周梦蝶”的诠释还是对“尧伐三子”的诠释,我们都看到庄学是以一阐提证法身,一切法本来涅槃而毕竟不入,庄学毕竟不是佛学一样的涅槃之学。若与西方哲学诠释学相对照,本文所开显的章太炎的经典解释学-释义学属于方法论一系的解释学,这正是中国经典解释学-释义学的特色之所在,既属于“中国式”又属于“解释学”。就中国经典解释的传统来说,章太炎《齐物论释》是足以和王弼《老子注》、郭象《庄子注》、朱子《四书集注》、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等相颉颃而成为中国经典解释传统成熟(刘笑敢语)之后的典型范式,他以解《庄》为形式而抉发出一整套基于佛学和庄学而形成的“内圣外王”哲学体系。注经只是形式,创构哲学体系才是目的,通过诠释经典而返本开新,以古老的经典世界观照现实世界。孟琢曾经对《齐物论释》有一个很公允的评骘:“《齐物论释》是传统的疏证文体,依据《齐物论》的文本次序进行阐释,并不利于独立的思想论述;但它犹如老杜笔下的七律,虽然背负着沉重的形式镣铐,却走出了清晰整齐的哲学步伐。”[8](《前言》,P.18)诚哉斯言!解释与经典之间总是有一种无形的形式镣铐,章太炎却在其中挥洒自如,技经肯綮之未尝为碍,善刀而藏之,此境端赖于他有一套与之匹配的经典释义学。换言之,为消解解释与经典、现代与古典之间的隔阂和扞格而不得不借助一套行之有效的经典释义学,此本文所作之由生也。
——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