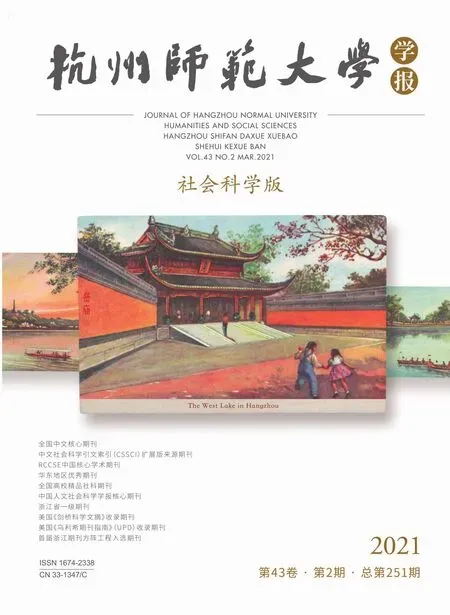“齐物哲学”与华严宗之离合
——以章太炎在《齐物论释》中对法藏的辩难为中心
周展安
(上海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44)
一、引言:建立“齐物哲学”的佛学坐标
欲把握章太炎(1869-1936)的学术、思想与实践,需从根本上了解其哲学。
章太炎之重视哲学,可从以下两则记录中窥得一斑。在1906年7月6日的日记中,宋教仁记道:“枚叔于前月出沪狱,特来掌理《民报》。与余一见面时,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以日本现在之哲学书以何为最,余以素未研究,不知门径对之,盖孤负其意不小矣。”[1](P.190)出狱未久,且身在异国,甫通姓名,就谈论哲学,可见章太炎对哲学研究之热切。在1909年11月给《国粹学报》的一则通讯中,章太炎曾简要勾勒自己的学术进路,而以哲学真理为旨归:“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2]正因为以哲学真理为尚,所以章太炎对同时代的汉学、今文经学、理学均抱不满,认为汉学“病在短拙”,今文经学“以文掩实,其失则巫”,理学则仅是“道德之训言,不足为真理之归趣”。[2]
对哲学研究的热切投身,终于成就其深湛的哲学造诣。他曾自信地对弟子吴承仕说:“常念周秦哲理,至吾辈发挥始尽,乃一大快。”[3](P.354)侯外庐也曾指出,章太炎“运用古今中外的学术,揉和而成一家言的哲学体系,在近世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4](P.861)。此处所说“古今中外”,诚非寻常套语。在章太炎笔下,既有对《易经》而下至颜元、戴震等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有对自己同时代的思想人物如康有为、严复、欧阳竟无、太虚等人的评价,也有对古希腊哲学至近世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引介。又因其流亡日本多年,对日本特别是明治时期的思想状况了解颇深。(1)可参小林武《章太炎与明治思潮》,白雨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特别是书中第1章第3节和第2章第1节。
作为这一深湛哲学造诣之结果的,即是其以《齐物论释》所集中表达的“齐物哲学”。他自认面对“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这种纷纭复杂的状况,唯有自己的哲学能够“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逊顺”。(2)见章太炎《菿汉微言》,收入《菿汉三言》,虞云国标点整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页。标点有改动。《齐物论释》成书之后,好友黄宗仰视之为“将为二千年来儒墨九流破封执之局,引未来之的,新震旦众生知见,必有一变以至道者”[5](P.58)。
而要深入了解章太炎之“齐物哲学”,又需首先研究章太炎之佛学。
佛学为章太炎的哲学世界撑开了一个更加深隐、精微而玄远的空间。这也是一般人以王阳明为大哲,而章太炎反而以其缺乏玄远之思而加以批评的根本原因,正所谓“斯乃过于剀切,夫何玄远矣哉?”[6](《检论·议王》,P.460)
钱穆曾将章太炎之学术分为四根支柱,“一为其西湖诂经精舍俞樾荫甫所授之小学;一为其在上海狱中所诵之佛经;一为其革命排满从事政治活动,而连带牵及之历代治乱人物贤奸等史学理论;一为其反对康有为之保皇变法,而同时主张古文经学以与康氏之今文经学相对抗”,他特别指出,“而其崇信印度佛学,则尤为其四支柱中擎天一大柱”。[7](P.340)钱穆这一论断独具慧眼。“苏报案”之后在狱中读佛书的经历对于章太炎思想的形成的确深具转折意义,正所谓“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8](P.60)。概而言之,对佛书的研读使其获得了思想的制高点。此后所写定的《检论》《国故论衡》等著作均显示了佛学的深刻影响,被其誉为“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更是其佛学思想的集成之作。
章太炎对于浩繁的佛教经论可称娴熟,他曾为频伽精舍所校刊的八千余卷《大藏经》作序,倡导有识之士对佛乘的精研,其中这样说:“往者经论不宣,学者以寡闻为惧。缩印已成,流通始广,然则密意了义,佛不自言,依义依文,定于比量,闻熏之士,其超然自悟于斯!”[9](《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P.519)章太炎对于同时代佛学论争亦有积极的参与。他曾积极介入“大乘非佛说”(3)围绕这场讨论的不同观点,可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张曼涛主编的《大乘佛教的问题研究》。的讨论,写出《大乘佛教缘起说》;也曾参与《大乘起信论》真伪的聚讼公案,写出《辨〈大乘起信论〉之真伪》。他与欧阳竟无、唐大圆、太虚、月霞、宗仰上人等同时代佛教人士都有较为密切的交游,对于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以及早期印度佛学的宗要都有深入的理解并形成自己的论述。他对自己研读佛典的心得极为自信,曾说“鄙人研究《起信》《唯识》二论,皆已通达,二论即是《楞伽》注释,而反观本经,则犹有未能解了者”[10](《与黄宗仰》,P.93)。他甚至还有佛教实修的经验。综合这些角度来看,章太炎毋宁是一个佛学学者,只是他在小学、经史之学以及革命实践等领域影响太大,以至于其佛学造诣常被后者掩盖。因此,对章太炎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必要从底下翻上来,聚焦于章太炎和佛学的交涉,以佛学义理以及近代佛教史为参照坐标以把握章太炎哲学思想所处的位置。
既有的章太炎研究不乏对章太炎思想中佛学因素的关注。这大致可分为史学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两类。其中大多数研究可说是从史学的角度来展开的。它们着重梳理章太炎学佛的过程、学佛的动因、对佛教事业的推动、对佛学重要性的评价等等,其中也间或涉及对佛学义理的探讨。从哲学的角度立体地探索章太炎佛学思想的研究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在范围更大的“晚清思想史”或者“近现代哲学史”的脉络中来把握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它们着重章太炎运用佛学视角对同时代的流行思潮,如进化、科学、公理、唯物、无政府主义、立宪、革命、文明等等的批评与解析,也就是说,着重的是章太炎佛学思想的使用与影响,是佛学思想与时代的交锋;第二类则是注重从佛教思想史或者佛学知识史的脉络来把握章太炎的佛学思想。(4)如张志强《“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论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形成及其意趣》,《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3期;石井刚《“随顺”的主体实践:〈大乘起信论〉与太炎的“齐物哲学”》,《汉语佛学评论》,2018年第6辑;龚隽、陈继东《从〈訄书〉初刻本(1900年)看章炳麟的早期佛教认识》和《章炳麟与〈大乘起信论〉真伪之辨》,二文收入龚隽、陈继东《作为“知识”的近代中国佛学史论——在东亚视域内的知识史论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孟琢对于《齐物论释》所涉佛学经论亦多有引注,见孟琢《齐物论释疏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晚近以来,这方面研究积累颇多,此处仅略加提示,挂一漏万。从晚清思想史或者哲学史的脉络上来把握章太炎的佛学思想诚然具有更宏观的意义,但考虑到阅读佛学对于章太炎思想形成影响之深,也考虑到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的佛学界参与之广,同时也是考虑到佛学在近代以来的思想与社会巨变中所彰显的革命性与创造性,本文认为,将章太炎佛学思想之展开坐标从晚清思想史转移到佛学思想史或者一般佛教史,或许有助于从更细微的层面来摸索章太炎佛学思想的理路,进而为从整体上把握章太炎思想提供基础性的材料。
从佛学的角度来把握章太炎的思想,可再进一步细分为两种进路:第一种是依据佛学各派的一些共同特点,从较为普遍的佛学义理角度来考察章太炎对佛学的理解;第二种则是进入章太炎佛学知识和思想的内部,考察章太炎对佛学各派之抉择与判摄。用章太炎自己的话说,即是“仆于佛学,岂无简择?”[9](《答铁铮》,P.386)以笔者所见,章太炎在大小乘之间,在中印佛学之间,在华严宗、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天台宗等不同佛学宗派之间各有抉择。
本文即尝试以章太炎对华严宗的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其“齐物哲学”与华严宗之离合关系。接下来我们首先在同时代的脉动中略微勾勒章太炎对华严宗的接受状况。
二、同时代的华严宗状况与章太炎对华严宗的接受
华严宗是中国佛教的一派,以立足《华严经》而得名。关于华严宗的学说传承,颇有争论。[11](《华严宗》,PP.2954-2955)一般认为其初祖为杜顺(557-640年),相传著有《华严五教止观》和《华严法界观门》等文;二祖为智俨(602-668年),著有《华严一乘十玄门》《华严搜玄记》等,初步阐发了十玄门、六相义等思想,奠定了华严宗的理论基础;三祖为法藏(643-712年),武则天赐名贤首,著作宏富,其中有《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师子章》等,被认为是华严宗的真正创立者,华严宗也因其名而被称为贤首宗;四祖为澄观(738-839年),又称清凉国师,著有《华严法界玄镜》《华严疏钞》等;五祖为宗密(780-841年),又称圭峰大师,著有《原人论》《起信论注疏》等。吕澂认为,宗密之后,华严宗传承不明,特别是宋初净源(1001-1088年)之后,逐渐消沉。[11](《中国佛学源流略讲》,P.2748)
这里无法详述华严宗历史,只想就章太炎同时代之华严宗发展状况略加勾勒,以显示章太炎接触华严宗的周边语境。而此同时代之状况或直接或间接都与章太炎有关,因此,勾勒此状况,也将更加凸显章太炎和佛学的内在关联。依照笔者管见,关于近代华严宗的发展,约略可以从三条线索来进行梳理。其一,为杨文会居士(1837-1911)自1866年成立金陵刻经处起陆续刊刻包括华严宗经论在内的各种佛学著述,其中特别重视贤首法藏的著作。法藏著作在唐以后大部分散佚,正是靠杨文会从日本等地多方搜集,重新刊刻,才广为人知。他曾自述学佛之历程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12](《与某君书》,P.120)。杨文会以《华严经》为诸经之王,而以法藏的著作为学习华严的圭臬,以此不遗余力地推动华严宗经论的流通及华严教理的宣讲。弟子辈中有谭嗣同以擅长华严而著称。其所著《仁学》,宣称“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5)谭嗣同《仁学》,收入《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3页。《仁学》中提及《华严经》的地方颇多,不一一列举。,书中引以解释“仁学”之“仁”的“性海”“一多相容”等概念主要出自华严宗经论。他甚至引《华严经》来论证男女平等。其二,为康有为自1891至1897年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对华严宗的推重。其时康有为常在讲课中提及佛学,作为授课记录的《万木草堂口说》中关于佛学与儒家思想之互释的提点可谓俯拾皆是。其中尤其重视《华严经》,认为“《华严经》与四书、六经比较,无不相同,但人伦不同耳”[13](P.280)。同时期写成的《春秋董氏学》在论天人关系时,更明确将董仲舒“人之元在乎天地之前”的思想比附于华严宗的毗卢性海之说,认为“精奥之论,盖孔子口说,至董生发之,深博与华严性海同”[14](P.126)。后来的《大同书》及《诸天讲》等著作也都透露华严思想的影响。其弟子梁启超后来总结乃师之宗教思想,认为康有为“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15](P.70)。其三,为佛门中之月霞法师(1858-1917)尤其在僧伽教育领域对华严宗的推广。月霞法师也被认为近代华严中兴的关键人物。自24岁出家以来至1917年在杭州圆寂,学习和宣讲华严即成为月霞法师的志业。期间,曾在1894年起在安徽九华峰宣讲华严两年之久,又于1913年在上海与黄宗仰等一起创办华严大学。[16]月霞对华严教理的弘扬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后来成为革命家的恽代英1917年就曾持续聆听月霞对《大乘起信论》的讲解。[17](PP.78-83)
章太炎与这三条线索均有交集。杨文会在近代佛学复兴潮流中有普遍的影响,是章太炎佛学上的授业之师,章太炎在行文中多有称引;康有为与章太炎先是以经今古文问题而产生争论,章氏之《春秋左传读》即为针对康氏之《新学伪经考》而发,戊戌变法之后更成为学术兼政治上的论敌;月霞法师和章太炎多有过从,可谓挚友,1915年致法师的信中曾称赞其“主讲华严,想听受正法者,当如竿蔗竹林”,又推重月霞“独有大雄无畏风概,即此可昌吾宗”。[10](《与月霞法师》,P.611)概而言之,章太炎之同时代有较为浓厚的研习华严宗的氛围,而此氛围沾溉太炎也甚深,这构成我们理解太炎佛学思想的前提。
章太炎直接接触华严宗的经论,当在1897年30岁或之前一年。其《自定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平子因问:‘君读佛典否?’余言:‘穗卿尝劝购览,略涉《法华》《华严》《涅槃》诸经,不能深也。’”[18](P.46)这是1897年事,而与穗卿即夏曾佑相识则是1896年的事情。但无论细节如何,此时章太炎对佛典包括华严宗经论的接受都是非常有限的。太炎亦曾追溯这一历史,说“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专精也”[19](P.165)。如前文所述,直到因“苏报案”入狱并在出狱赴日之后耽读佛典,章太炎才真正领会佛义的渊海。其中特别指出,“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19](P.165)。《楞伽》,全称《大乘入楞伽经》,即是华严宗建立所依据和吸收的主要经典之一。章太炎接触华严宗经论之后,对华严宗最有代表性的推崇,应当是他在出狱赴日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其中,他提到要以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而这里的“宗教”即是华严和法相二宗。章太炎提出要用这二宗来改良旧法,因为“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又说:“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督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20](《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P.4)这里所说的“靠的自心”正与他在几乎同时给友人的信中所说“依自不依他”[9](《答铁铮》,P.386)一语相呼应。在提出“依自不依他”的语境中,章太炎特别推举禅宗,就此说,则华严宗与禅宗对于章太炎来说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对华严宗的提及,也见之于章太炎给佛界友人的信等处(6)如1905年致黄宗仰的信中,依据“华严世界”谈黑格尔和叔本华哲学;如1916年致黄宗仰信中比较天台和华严的不同“观”法。参见章太炎《章太炎书信集》,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7、93页。。但更直接、更集中的论述,则是在《齐物论释》中。《齐物论释》不仅显示了章太炎对华严宗的吸收,更呈现了其对于华严宗的辩难。对佛学的辩难,乃基于章太炎之看待佛学的基本方式。章太炎之看待和接受佛学,不是以信徒的方式,不是以将佛法把握为宗教的方式,而是以求智的态度将佛法把握为哲学,提出“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20](《佛学演讲》,P.102)。从这个角度看,辩难实属题中应有之义。
并且也可以说,正是在这种似乎不甚起眼的辩难当中,更多隐含着章太炎佛学思想的幽微之处。本文接下来就主要依据《齐物论释》及其他相关材料,从“辩难”这一角度切入,以其对华严宗的辩难为中心,尝试摸索章太炎佛学理路之一端。
三、法藏“十钱喻”与“椽舍喻”的脉络
章太炎对华严宗的辩难主要围绕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而展开。这首先见之于《齐物论释》中对法藏的“十钱喻”和“椽舍喻”的批评。“十钱喻”和“椽舍喻”见于法藏的《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十钱喻”出自其中的“十玄缘起无碍法门义”一节,这是法藏为了说明法界缘起而列出的十个层次,也即十玄缘起或者十玄门,以解明事事无碍法界的特点;“椽舍喻”出自其中的“六相圆融义”一节,这是法藏就法界缘起之相状的说明,也说是十玄缘起之相状的说明。这两者配合起来共同解明法界缘起的内在逻辑,所谓“十玄六相”。具体来说,在“十玄缘起无碍法门义”一节中,法藏提出从两个层次来理解法界缘起,即“十佛自境界”和“普贤境界”。前一个境界为“明究竟果证义”,是不可言说其相状的自在境界,后一个境界为“随缘约因辨教义”,是可以从缘起角度来分析的境界,十玄缘起就是这种分析的具体展开。法藏对此进一步指出,可从两个角度对此加以解说,即“以喻略示”和“约法广辨”。而十钱喻,就是“以喻略示”的具体表现。所谓“喻”,即佛教因明学论辩的三个层次即“三支”之一,所谓“初立所信,是名曰宗。次出所由,是名曰因。后引譬合,是名曰喻”[21](P.15)。而就缘起来说,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即“以诸缘起法,皆有二义故”[22](P.188)。这两个方面,即“相即”和“相入”,它们用来解释诸缘起法内部的关系。从而,十钱喻也就既要用来解说“相即”,又要来解说“相入”。
关于相即,法藏说:“初中,由自若有时,他必无故,故他即自。何以故?由他无性,以自作故。二,由自若空时,他必是有,故自即他。何以故?由自无性,用他作故。以二有二空,各不俱故,无彼不相即;有无无有无二故,是故常相即。”[22](P.188)这是从“自”和“他”有无自性的角度来展开的分析,也就是从自体之空有的角度展开的分析,是“体”的层面。“自”若是有,则“他”必是“无”,这种情况下,以“自”为主,“他”随顺“自”,从而是“他即自”;“他”若是有,则“自”必是无,这种情况下,以“他”为主,“自”随顺“他”,从而是“自即他”。从而,“相即”就不仅指示着多缘不相分离的状况,而且指示着这不相分离内部的构造。这是说在缘起的世界中,不同的因素在缘成某一结果时,其中有的因素是在主位的,所谓“有”;而有的因素是在辅位的,所谓“无”。这里所说的“有”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并非真正的“有”,而是在自他关系中的关系性的“有”。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相即的关系,法藏以“一”和“十”的关系来譬喻:“一者一,何以故?缘成故。一即十,何以故?若无一,即无十故。由一有体,余皆空故,是故此一即是十矣。”[22](P.189)这是以“一”为有,以“十”为空,此处所说“此一即是十”若顺承上文的自他关系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十即一”。法藏接着说:“一者十,何以故?缘成故。十即一,何以故?若无十,即无一故。由一无体,余皆有故,是故此十即一矣。”[22](P.189)这是以“十”为有,以“一”为无,顺承上文的自他关系而言,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即十”。无论“一即十”还是“十即一”,都在说明“一”和“十”之间不相分离、相互成就的关系,也就是“一”和“十”之间的缘起关系,这种“相即”的缘起关系,最终在于说明“缘起性空”的道理。
关于“相入”,法藏说:“明力用中自有全力故,所以能摄他;他全无力故,所以能入自。他有力,自无力,反上可知。不据自体,故非相即;力用交彻,故成相入。又,由二有力二无力各不俱,故无彼不相入;有力无力无力有力无二故,是故常相入。”[22](P.188)这是从“自”和“他”的力用关系来做的分析,和“相即”在“体”的层面展开不同,这是从“用”的层面展开的分析。如果“自”有力,则“他”无力,在这种“自他”力用交彻的关系中,就是“他入自”的形态。反之,如果“他”有力,则“自”无力,就成就为“自入他”的形态。“入”表示的是无力者对有力者的随顺。和“入”相反,则是“摄”。那么,以十钱喻来加以说明,则是:“一者,一是本数。何以故?缘成故。乃至十者,一中十,何以故?若无一,即十不成故。一即全有力,故摄于十也,仍十非一矣。”[22](P.188)这是以“一”为有力,以“十”为无力,从而一摄十,或者说十入一。另一方面,“一者,十即摄一。何以故?缘成故。谓若无十,即一不成故。即一全无力,归于十也,仍一非十矣”[22](P.188)。这是以“十”为有力,以“一”为无力,从而十摄一,或者说一入十。
“相即”是就“体”的层面而言,“相入”是就“用”的层面而言,在体用一如的视野中,相即和相入是互相阐释的,都在说明诸缘互相涵摄、不碍不离的关系,从而共同促成大缘起陀罗尼法。“一即十”和“十即一”所传递的意思是相同的,就“十”以及百千万等总要由作为“本数”的“一”组成而言,则是“十即一”。所谓“十”,并非特定的“十”,而是“说十者欲应圆数显无尽故”[22](P.188)。而就“一”总是组成“十”乃至千百万等他数的“一”,则又是“一即十”。“十”是由“一”所缘成的,“一”同样是由“十”所缘成的。没有一个孤立的、具自性的“一”。因为如果“一”有自性,则“一”只是“一”而已,就不成缘成“十”乃至千百万等。对此,法藏这么说:“所言一者,非自性一,缘成故。是故一中有十者,是缘成一。若不尔者,自性无缘起,不得名一也。”[22](P.188)“十”是由“一”所缘起,“一”就其总是作为“十”中之“一”这一点而言,则“一”也是由“十”所缘起,从而法藏说:“是故一切缘起,皆非自性。”[22](PP.188-189)
“椽舍喻”出自“六相圆融义”。所谓“六相”,指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六相既是上述十玄门所具有,也为一切缘起法所具有。所谓“圆融”,即此六相相即、相入、相摄,圆融无碍的相状。这六相包括三个对子,即总别、同异、成坏。在本文看来,这是对前述相即相入关系的进一步说明,就是相即相入在诸多相状之间的表现,而非只是由“自他”关系来说明。法藏说:“此义显前,一切惑障,一断一切断,得九世十世惑灭;行德即一成一切成,理性即一显一切显,并普别具足,始终皆齐,初发心时便成正觉。良由如是法界缘起,六相熔融,因果同时,相即自在,具足顺逆。”[22](P.197)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普和别、始和终、因和果等等一般被认为是存在区别的相状都呈现为彼此相即相摄的关系,而且是同时并起,无有先后,这些一般被认为是彼此区别的相状也就对应于“六相”所指示的。这一同时并起的诸法无有隔阂而相互缘生,普现为大缘起陀罗尼法。在这里,一般被认为是分离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相涵相入,此三世各自所具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成九世相即相入,此九世相即相入而成一世与九世合为十世,这正是十玄门中十世隔法异成门所指示的十世。十世相即相入,凸显了万相全部相即相入的状态,这就是所谓“九世十世惑灭”,从而成就“六相圆融”、无一遗漏的法界。
为了进一步解明这一点,法藏举出“椽舍喻”的例子:“椽即是舍。何以故?为椽全自独能作舍故。若离于椽,舍即不成;若得椽时,即得舍矣。”[22](P.197)椽对应的就是六相中的别相、异相、坏相,舍对应的就是六相中的总相、同相、成相。椽即是舍,就是别相等即是总相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所谓“椽”,是此块木料乃相对于“舍”而言,一说“椽”,即意味着“舍”的存在,“舍”在此构成“椽”的前提,“椽”之为“椽”,在于其总是“舍”的“椽”。椽即是舍,反过来说,舍即是椽,因为所谓“舍”,亦正是由“椽”所成就起来。甚至,说“椽”成就了“舍”还保留了构造论的意味,也就是把作为别相的“椽”与作为“总相”的“舍”视为各有自性的实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椽即是舍”乃“椽”本身即是“舍”,正所谓“若是椽者,其毕全成,若不全成,不名为椽”[22](P.197)。作为别相、异相、坏相的“椽”实质只是从分别的、各各自立的、自分的角度对总相、同相、成相的把握而已,别相总是总相的别相、别相与总相为不一不二的关系,椽也就是从分别的、各各自立的、自分的角度对舍的把握而已,椽总是舍的椽,与舍乃是不一不二的关系。法藏从“断”和“常”两个方面来指斥将椽和舍分离开来的做法:“若不全成但少力者,诸缘各少力。此但多个少力,不成一全舍故,是断也。诸缘并少力皆无全成,执有全舍者,无因有故,是其常也。”[22](P.197)就是说,如果只是就椽而谈椽,就别相而谈别相,则将椽执实而没有所谓舍,这是断见;如果只就舍而谈舍,就总相而谈总相,则是将舍执实为有自性而无所谓椽,这是常见。堕入断见或者常见,都是对椽和舍相互缘起之关系的错误理解,惟有非断非常,才能避免构造论的误区,而体会到诸缘并起融合无碍的状况。进一步说,不仅舍即是椽,余下的所谓板瓦等也都是椽。因为“若无椽即舍坏,舍坏故不名板瓦等,是故板瓦等即是椽也。若不即椽者,舍即不成,椽瓦等并皆不成。今既并成,故知相即耳。一椽既尔,余椽例然”[22](P.198)。“椽”之为“椽”,是因为其缘成为“舍”,而既然有“舍”,则“板瓦”之名也由此成立,在这个意义上,是“椽”又与“板瓦”相互缘成。椽与板瓦,都是别相,不仅别相与总相相互缘起,别相与别相也同样相互缘起。
说到底,无论是十玄缘起还是六相圆融,都在指向缘起性空的道理。其最终所成就之玄海或者说大缘起陀罗尼法也都是空无自性。相即相入相摄的普遍存在,在一种极致的意义上指示了诸缘之空性,若不是空性而是自性,则相即相入相摄就因为自性之障碍而无法完成。不仅如此,就是“即”或者“入”或者“摄”等词也都是虚说,并非真有“即”或“入”或“摄”的动作之发生。所谓动作,总有其发生时间之先后,而在缘起法中,则总是“始终皆齐、因果同时”。正如牟宗三所说:“实相一相,所谓无相,即是如相。此时亦无‘即’相可言。此即是《般若经》之精神。而贤首于此则是寄空有方便说‘相即’以示法界缘起之无碍耳。不可因其说‘常相即而无不相即’,便把此‘即’字定死也。是则总归‘即而无即’也。”[23](P.413)
四、章太炎的辩难
章太炎对法藏的辩难首先见之于其对“十钱喻”和“椽舍喻”本身的批评。关于“十钱喻”,太炎认为“此但进位退位命分之义,然以说数目可,以之说事,即又不可”[24](P.91)。所谓“以之说数目可”,是在太炎看来,就作为数目字的“一”和“十”之关系而言,可以说“一即十”或者“十即一”。太炎认为,这可以从进位和退位这种数学规则来认识,“以有退位,故知一亦缘成,若无小数之十,一不得成故。以有进位,故知一摄于十,谓此一数,即是十数十分之一,非是他数十分之一故。以有退位,故知十是缘成,若无一数,十不得成故。以有进位,故知十亦如一,十之进位望十,亦犹十之望一故。如是递进递退,无不皆尔”[24](P.91)。就“一”能够进位而成“十”,即总是作为能够缘成“十”的“一”而言,则“十即一”;就“十”能够退位而成“一”,即总是由“一”所缘成这一点而言,则“一即十”。一和十都是缘成的,相互之间是相即相入的关系,从而推而广之,可以成就法藏所说的法界缘起之理,所谓“良由一无定数,是故一即一切,一切即一”[24](P.91)。所谓“以之说事,即又不可”,是因为在太炎看来,作为数字的“一”可以退位而更多细分,但作为更具体的“一钱”而言,则不能做更多细分,即“一钱更无退位,若析一钱为十,便不名钱,是故一钱非十小数钱所缘成也”[24](P.92)。一铢钱若再加细分,则不称其为钱,从而就无法成立“一即一切”的道理。
这种“以之说事,即又不可”的问题也表现在“椽舍喻”上。太炎说:“本以缘成舍,名为椽,不作舍,故无椽,此谓椽名由舍而起,若不作舍,只名木梃,不名为椽,义亦得通。然若例之版瓦,是亦有过,舍虽因版瓦,而有版瓦,不定作舍,此即与椽有异,椽名缘舍而得,版瓦之名,不缘舍得,以作几案榜牍棺椁者,亦名为版,作瓶瓯壶缶者亦名为瓦故。若椽即是舍,版瓦不得非舍,而彼版瓦名实皆不因舍。”[24](P.92)就是说,就椽之命名因“舍”而起这一点来说,椽即舍的意思是可以成立的。版或瓦这些同样可以缘成“舍”的要素其命名却并非因“舍”而来,从而不能成立版瓦即舍的道理。推而言之,也就不能成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综合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太炎认为法藏之喻并不能彻底指示法界缘起,正所谓“法藏未得名言善巧,有类诡辩者也”[24](P.92)。
对于太炎的这些辨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其一,太炎的辨析有过于执实的倾向,从而使得其论述有构造论的意味。如上一节所分析的,在法藏,一钱和十钱、椽和舍等只为明晰化相即相入相摄的道理,原不能从逻辑关系来解析。一和十的关系不能用进位退位这种“命分之义”来对应,“椽”和“舍”也不能以实际的部分与整体之关系来对应。且在因明学中,所谓“喻”本来就是进一步说明“宗”而列出的。“喻”即梵文“达利瑟致案多”,直译即“见边”。所谓“见边”,就是“凡圣见解一致之事件曰见边,谓一般人共认无违之事件之关系者也”[25](P.125)。太炎所论,将“喻”执实,逆推至“宗”。其二,太炎对法藏两喻的辩难,并非与法藏立异,而是认为法藏并未彻底化其理论,所谓无尽缘起并未实现。法藏乃至整个华严宗所提出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意思正是太炎反复提及,并将之与庄子所论并举的:“《华严经》云: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法藏说为诸缘互应。《寓言篇》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义谓万物无不相互为种。《大乘入楞伽经》云:‘应观一种子,与非种同印。一种一切种,是名心种种。’法藏立无尽缘起之义,与《寓言篇》意趣正同。”[24](P.91)
那么,要将法藏无尽缘起之义彻底化,究竟该怎么做呢?太炎提出:“今依《寓言》以解《齐物》,更立新量,证成斯旨。”[24](P.92)所谓“新量”,概括来说,即阿赖耶识。换言之,章太炎要立足唯识宗来补充华严宗之不足,或者说,以唯识宗来圆满华严宗之本义。这是章太炎对法藏更进一步的辩难。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太炎又首先对唯识宗做了修正,修正的要义在于完成“唯识无境”的理论。这也正是整篇《齐物论释》所贯穿的逻辑。太炎说:“往昔唯识宗义,不许四大名为生物。”[24](P.93)所谓四大,即地、水、火、风四种因素。在古印度思想中,这被普遍认为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基本元素,就其能造成物质而言,又被称为能造色。太炎认为古唯识宗也有此思想,也因此有情界、器界之分。但太炎进而认为,这种将四大归于无生之元素、归于器界的做法当然不能完成唯识的定义。他依据《大乘起信论》中关于无明业相、能见相、境界相这三种细相的说法,论证金亦有识。三种细相是依“不觉”之体性而在心念中所生起的三种相[26](P.46),而就此三种相乃依“不觉”之体性而生起这一特点而言,太炎就认为此三种相正好对应业识、转识、现识这三种识。而以金为例,并推及四大:“金有重性能引,此即业识;能触他物,此即转识;或和或距,此即现识。是故金亦有识,诸无生者皆尔。”[24](P.93)从所谓“无生者”皆有识这一点而言,则情界器界的区分实际也并不存在,而只是一种随俗假说而已:“尔何故旧分情界器界?应答彼言但依智慧高下,假为分别,如珊瑚明珠等物,是情是器,本难质定,而可随世说为器界。是故虽说金为器界,不碍有生,此但依唯识俗谛为言,若依真谛,即唯是识。”[24](P.94)极致化唯识宗的逻辑以完成“唯识无境”的道理,目的在于以“唯识无境”之“识”的普遍性来证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法藏那里的本义。从而,法藏“以说数目字可,以之说事,即又不可”的局限在“即唯是识”的状况下就得以克服。正所谓“下逮金石,既亦含于人体,或啖云母,或餐钟乳,悉可摄受为人身分。乃至岩石水银,食之殒命,既有相害之能,即有相和之道。譬如缓触即抚,急触即檛,远火即煖,逼火即焦,是故无不更相为种也”[24](P.95)。“更相为种”即《寓言篇》所说“万物以不同形相禅”,也即《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相比于对法藏二喻的批评,以唯识补华严,是章太炎对法藏之辩难的深化。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章太炎对法藏的辩难更进一步表现为对“法界缘起”本身的不满。缘起是佛教的基本概念,表达了佛教对于万法存在的基本看法,是对成、住、异、灭之过程的总说明。所谓缘起,即因缘而起,指向的是缘起性空的道理,就万法之本质而言,是性空,就万法之存在形态而言,则是缘起。缘起说更是华严宗的理论基础,法藏所著《华严金师子章》即以“明缘起”为第一义。[27](P.2)一般所说的缘起依据佛教本身的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四种,即业感缘起、阿赖耶识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7)可参杨政河《华严法界缘起观简释》,收入北京图书馆影印出版、张曼涛主编的《华严思想论集》,第170-171页。业感缘起是小乘佛教对缘起的看法,也叫做“分别爱非爱缘起”[28](《缘起与实相》,P.1344)。它以众生因迷惑而造作诸业,以此诸业为人生转变的原因,即因业力而现苦道的生死果报,合起来就是惑、业、苦三道的辗转相续。阿赖耶识缘起是唯识宗对于缘起的看法,顾名思义,是以阿赖耶识为有情之根本依,即为缘起之根据。阿赖耶识中包含有无量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生种子,往复循环,而生起万法,以此成立万法唯识的道理。真如缘起是大乘法性宗对缘起的看法,也叫如来藏缘起,是以不变之真如心随缘起灭而现起诸法。其理论依据来自《大乘起信论》关于真如心和生灭心的区分。法界缘起则是华严宗对缘起的看法,也叫无尽缘起。它以法界为一大缘起,此法界既指诸法,又指法性,有将现象与实相通而为一的含义。华严宗以自己的法界缘起为涵盖以上三种缘起的究竟缘起:“约教辨者,若小乘中法执因相,于此六义,名义俱无。若三乘赖耶识,如来藏法无我因中,有六义名义,而主伴未具。若一乘普贤圆因中,具足主伴,无尽缘起,方究竟也。”[22](P.185)这里所说“六义”,即作为缘起的“因”有六个涵义,即空有力不待缘、空有力待缘、空无力待缘、有有力不待缘、有有力待缘、有无力待缘。提出这“六义”,是为了强调“因”的多种形态以及“因”和“缘”结合的多种形态,从而展现这种缘起不落入任何窠臼而融通无碍的特点,从而成就其无尽缘起的说法。因此法藏赞叹法界缘起为“无碍容持,如帝网该罗,若天珠交涉,圆融自在,无尽难名”[29](P.222)。
然而,章太炎在此诸种缘起中却并不以法界缘起为殊胜,相反,他说:“此无尽缘起说,惟依如来藏缘起说作第二位,若执是实,展转分析,势无尽量,有无穷过,是故要依藏识,说此微分,惟是幻有。”[24](P.96)这是将“如来藏缘起”为殊胜,以“无尽缘起”为第二。然而,此处所说“如来藏缘起”究竟是何所指?太炎继续说:“沙门愚者谓无尽缘起说,视如来藏缘起说为胜。此既颠倒心色,又不悟有无穷过也。又谓如来藏缘起说,视藏识缘起说为胜,不悟藏识即如来藏,《楞伽》《密严》皆言之。”[24](P.96)很显然,这里存在章太炎对佛教缘起说一般认识的辩难乃至颠覆:其一,如来藏缘起即藏识缘起;其二,在章太炎这里,不存在一般所说之如来藏缘起即真如缘起;其三,藏识缘起高于法界缘起。所谓藏识缘起,即唯识宗的阿赖耶识缘起,因此,概括而言,章太炎的缘起论乃最终落脚于唯识宗的阿赖耶识缘起,其与华严宗的法界缘起保持了较远的距离。推而言之,就《齐物论释》所见,太炎并无意在唯识宗和华严宗之间谋求折中或者会通,相反,是以唯识宗判摄华严宗。
华严宗将法界细分为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四个层次,又以事事无碍法界为究竟。从事法界到事事无碍法界,存在一个逐步落脚于“事”的逻辑,也是一个从假有到真无到假有真无之无碍再到真空妙有的逻辑,法藏以“从心现境妙有观”[30](P.105)解之,这代表华严宗观法的最终目标。所谓“事”,本来是相对于“理”而言,指向分殊的事象,但在华严宗的脉络中,毋宁要于此分殊的事象中来体会法界之理,从而更凸显其“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圆融义。法藏在《华严三昧章》中曾论及“理事圆融义十门”,即理事俱融门、理法隐显门、事法存泯门、事事相在门、一事隐现门、多事隐显门、事事相是门、一事存泯门、多事存泯门、圆融具德门,每一门又析为十义。[31](PP.240-243)仅从此十门而论,即可以见出“事”在华严教义中所居之重要地位。概而言之,在无尽缘起的视野中,存在一种将事和理对应的立体结构消弭而即理即事的境界,亦可说是一个囫囵的无隔阂的境界,是佛在定中圆明性德的全幅呈现。正因此,才有上文法藏所说“始终皆齐”“六相熔融”“因果同时”的状况。但是,也正是在这里,章太炎认为存在“颠倒心色”的危险。这种“颠倒心色”的危险,亦可说就是“颠倒理事”的危险。华严宗对于“事”的肯定性把握,虽然这种把握是在“真空妙有”的框架中展开的,但这种把握在章太炎看来,恐怕是存在对于“事”也即“色”的过分执著。他批评无尽缘起时说的“若执是实”[24](P.96)说到底即是对此分殊之事象之“执”。而这一点正与他在整本《齐物论释》中反复论及的“唯识无境”相冲突。他还曾批评法藏之“椽舍喻”存在“堕因中有果之过,与说泥中有瓶相似”[24](P.92),也正是着眼于华严宗即事象而求实相的逻辑,所谓“因”即“事象”,所谓“果”即“实相”。这一批评是颇为激烈的。因为“因中有果”之论即认为结果已预先含于原因之中乃是数论学派以及吠檀多哲学的理论,相对于佛教来说,这属于外道。
论述至此,又产生一个问题。章太炎既然对华严宗之教义有如此激烈的批评,何以又肯定华严宗的“性起”论?1911年在一次面对日本僧众的讲座中,章太炎曾这样说:“但有一端长处,也是印度人所不能想到的,就像《华严经》有‘性起品’。华严宗取到‘性起’两个字,犹有几分悟到。”[32](P.306)“性起”的概念出自晋译的《华严经·如来性起品》(唐代实叉难陀译为“如来出现品”)。这是华严宗的核心概念之一,也称为法性缘起。它指的是万法之生起都依据佛所自证的法界性起心或者说真心。关于性起,华严诸师解说纷纭,概括而言,它强调的是法性现起的能力。可以从与缘起的对比中来把握性起的特点。华严四祖澄观曾说:“若以染夺净,则属众生,故唯缘起;今以净夺染,唯属诸佛,故名性起。”[33]可见性起更侧重于“净”,相对于缘起,更具有一种本因的意味。有论者这样分析:“以法性湛然而随诸缘为全体起用,其所现起于法性一边名为性起,所现起于随缘一边说为缘起。”[34](P.127)法藏更明确以“体”来界定法性:“谓依体起用,名为性起。”[30](P.103)而所谓“体”者,乃是一真心,也即法藏反复论述的自性清净圆明体,也就是如来藏中法性之体。从而,性起的提出,比之缘起,更能凸显佛在定中所示现之法界主伴具足、本末同具、无有先后的特点,更能凸显即事象即实相的特点。但是,章太炎之肯定“性起”却并不是从这种即事象即实相的特点出发,也不是从自性清净圆明体的含义出发,而是着眼于“无明”!太炎从“性起”能补充“缘生”之不足开始说:“因为第一因缘不能指定,所以虽说缘生,不过与泛泛无根一样。又像《楞伽》《起信》,都把海喻真心,风喻无明,浪喻妄心。但风与海本是二物,照这个比例,无明与真心也是二物。海的外本来有一种风,照这个比例,心的外本来也有一种无明。这就与数论分神我、自性为二的见解,没有差别。唯有说成‘性起’,便把种种疑难可以解决。因为真心绝对,本来不知有我。不知有我这一点,就是无明。因为不知有我,所以看成器界、情界。这个就是缘生的第一个主因,一句话就把许多疑团破了。”[32](PP.306-307)可见,太炎之肯定“性起”,主要是因为“性起”可以避免“缘生”说之“泛泛无根”的缺陷,从而指明世间万法之本,此本即是“真心”,但此真心不是自性清净圆明体的真心,而是和无明非一非二的真心,在太炎的逻辑中,更准确地说,这“真心”就是“无明”。相比于上述法藏对于“体”的诠解,则太炎之论毋宁说乃恰相反对。(8)关于真心与无明之不一不二的关系,也可参章太炎《菿汉微言》,第3页。其中特别提到:“而此真如心,本唯绝对。既无对待,故不觉有我,即此不觉,谓之无明。”前引书,标点有改动。
五、章太炎佛学的位置
以上就章太炎与华严宗特别是法藏学说之张力关系加以勾勒,略可窥见其佛学思想之一斑。但是要系统把握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以及由此而把握其“齐物哲学”,还需有更广阔的佛学和佛学史视野,从其在和周边知识网络的比较中来获得新的认识。这里姑且以吕澂和熊十力、牟宗三关于性寂、性觉说之辩论为参照坐标来摸索章太炎佛学所处的位置,以进一步深化对“齐物哲学”与华严宗之离合关系的认识。
吕澂曾围绕“心性”的解释区分了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他认为印度佛学原来是以寂灭寂静的意义来解释心性,而中国佛学则以灵明知觉的意义来解释心性,前者他称之为“性寂说”,后者他称之为“性觉说”。他具体这样说道:“印度佛学对于心性明净的理解是侧重于心性不与烦恼同类。它以为烦恼的性质嚣动不安,乃是偶然发生的,与心性不相顺的,因此形容心性为寂灭、寂静的。这一种说法可称为‘性寂’之说。中国佛学用本觉的意义来理解心性明净,则可称为‘性觉’之说。从性寂上说人心明净,只就其‘可能的’‘当然的’方面而言;至于从性觉上说来,则等同‘现实的’‘已然的’一般。”[28](《试论中国佛学有关心性的基本思想》,PP.1417-1418)这里的关键在于,性寂说对于心性明净这一认识来说是消极的,其意在摆脱苦恼,而性觉说对于心性明净这一认识来说是积极的,其意在于成佛。吕澂进一步认为,因为性寂说的消极认识,导致印度佛学更注重现实的变革,他由此提出“转依”的概念,即转变藏识这一“所知依”由染而净以摆脱烦恼;[28](《正觉与出离》,P.1337)而看上去对心性有积极认识的性觉说反而容易流于“返本还原”的路径而谈不到实质上的变革从而流于政治上的保守。在此脉络中,吕澂特别提到作为中国佛学之代表的华严宗。他说:“华严宗用十玄解释缘起,意在发挥‘性起’的理论,以为‘此心’本来具足一切功德,不假修成而随缘显现,佛和众生只有迷悟的不同,主伴的各异而已。华严宗就从这种论点和天台宗所谓‘性具’立异,而中国佛学里‘一切现成’的思想发展,到此也可说是登峰造极了。”[11](《华严宗》,P.2966)很显然,吕澂是立足性寂说而批判性觉说。
如所周知,吕澂亦曾在20世纪40年代依据其“性寂说”与熊十力展开辩论。其间吕澂以熊十力不辨析性寂性觉而批评熊氏“自是热情利智,乃毕生旋转于相似法中,不得一睹真实,未免太成辜负”[35](P.179),而熊十力则回以“言性觉,而寂在其中矣。言性寂,而觉在其中矣。性体原是真寂真觉,易言之,即觉即寂,即寂即觉”[35](P.183)。吕澂和熊十力的辩论可说是性寂说与性觉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具象化,值得再行追索。但熊十力在《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最终归宗大易的思路使得此辩论溢出了佛学的脉络而变得稀释了。熊氏在辩论的最后声言“我对于佛,根本不是完全相信的,因为对于伪不伪的问题,都无所谓。我还是反在自身来找真理”[35](P.199),即是以将佛学搁置的方式终结了辩论。倒是在熊氏弟子牟宗三那里,这一辩论得以部分的延续。
牟宗三以“真心系”和“妄心系”这一个对子来作为把握佛教思想演变的抓手。其所谓真心系,可以说正对应于吕澂所说之性觉说,而妄心系则对应于性寂说。和吕澂以性寂性觉作为区分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之判准不同,牟宗三将真心系和妄心系的区别置于印度佛学内部,具体说是置于唯识学内部来理解。他以唯识宗大德无著所造之《摄大乘论》入手,认为真谛先译之《摄大乘论》可称为前期唯识学,而玄奘重译之《摄大乘论》为后期唯识学。他认为“前期唯识学是向真心走,所谓真心系,后期唯识学则决定是妄心系,此亦是无著世亲造论所表现的系统的唯识学之旧义也”[23](P.229)。顾名思义,真心系即是以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为主体的阐释系统,而妄心系即是以生灭迷染的妄心或者说阿赖耶识为主体的阐释系统。以此为起点,牟宗三进至中土佛学的脉络,以《大乘起信论》为“典型的‘真心为主虚妄熏习是客’的系统”[23](P.356),并视“华严宗是以《华严经》为标的、以《起信论》为义理支持点而开成者”,而且在如来藏缘起乃超越性的分解这一脉络上,“顺分解之路前进,至华严宗而极,无可再进者”。[23](P.381)在牟宗三的判摄系统中,真心系和妄心系虽各自成立为独立的系统,但“真心派实高于妄心派”[23](P.260),而“无著世亲归于妄心系统不得不谓之为歧出”[23](P.307)。也由此,其对于吕澂所属的支那内学院派时相辩难。他特别抓住“如来藏识”之别于且高于“藏识”这一点来批评内学院之等同如来藏识与藏识,认为“就《楞伽经》而言,欧阳竟无与吕秋逸以妄心系统之赖耶缘起视经中所说之‘无我如来藏’,‘藏识’,以及‘如来藏名藏识’,未见其是,至少不能决定《楞伽》必如是,至少亦不能决定彼等之解释比《起信论》为更顺为更佳”[23](P.346),且更明确批评吕澂将阿赖耶识藏识等同于如来藏,乃是“将如来藏拖降于阿赖耶识矣”[23](P.260)。
如前所述,章太炎在论述注重缘起的时候,也正是将如来藏缘起等同于藏识缘起,而此藏识缘起也即阿赖耶识缘起又高于无尽缘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章太炎和吕澂类似,同属于“性寂说”或者牟宗三意义上的“妄心系”。1918年在为支那内学院开办所撰写之《支那内学院缘起》一文中自称“始窥大乘,终以慈氏、无著为主”,并推举欧阳竟无区分唯识法相之见解为“足以独步千祀”[36](P.311),同样具体而微显示了其对内学院脉络的亲近。
在《齐物论释》中,作为“妄心”的阿赖耶识乃作为章太炎回击同时代各种流行话语如文明论、进化论、无政府主义论等等学说的理论基石而存在的。阿赖耶识之“妄”亦正对应于文明论、进化论等各种流行名目之“妄”。太炎曾将“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无尽缘起”等并举,但切莫望文生义,将此万物与我之论顺承于后世儒家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生生”之论。“齐物哲学”的第一要着,不是“生生”,而毋宁说是“无生”,不是“并生”,而是“并灭”,正所谓“故非独与天地并生,乃亦与天地并灭也。若计真心,即无天地,亦无人我,是天地与我俱不生尔”[24](P.90)。也因此,此处所说“万物与我为一”之“一”也并非沛然充实之“一”,而是“性寂”之“一”,所谓“一种一事一声,泊尔皆寂,然后为至”。[24](PP.96-97)这也正与《般若经》所说“诸法一性,即是无性,诸法无性,即是一性”若合符节。太炎最后断言“齐物之至,本自无齐”[24](P.97),为什么“本自无齐”?正因为万法之本乃“无性”,乃“寂”,乃“无生”,乃“妄心”,乃“阿赖耶识”。
但是,“本自无齐”并非终点。在回击了各种虚妄假说之后,“齐物哲学”要求积极地创造和树立,因为“苟专以灭度众生为念,而忘中涂恫怨之情,何翅河清之难俟,陵谷变迁之不可豫期,虽抱大悲,犹未适于民意”[24](P.120)。由此,“齐物哲学”之树立,必将是基于且适于“民意”的树立。这也正是太炎所说“夫《齐物》者以百姓心为心”(9)参见章太炎《齐物论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以此为题,笔者另撰有《“以百姓心为心”:章太炎〈齐物论释〉阐微》(《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2期即刊)一文,专论章太炎的“齐物哲学”。所要表达的意思。而能够“以百姓心为心”而践行这种“齐物哲学”的担纲者则非“若一众生未涅槃者,我终不入”的“菩萨一阐提”[24](P.119)不能为。
和这种“菩萨一阐提”“哀生民之无拯,念刑政之苛残,必令世无工宰,见无文野”[24](PP.119-120)的志愿与行动相比,本文关于“齐物哲学”与华严宗之离合的辨析、太炎在性寂与性觉或者真心与妄心之间抉择的辨析之种种,都属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