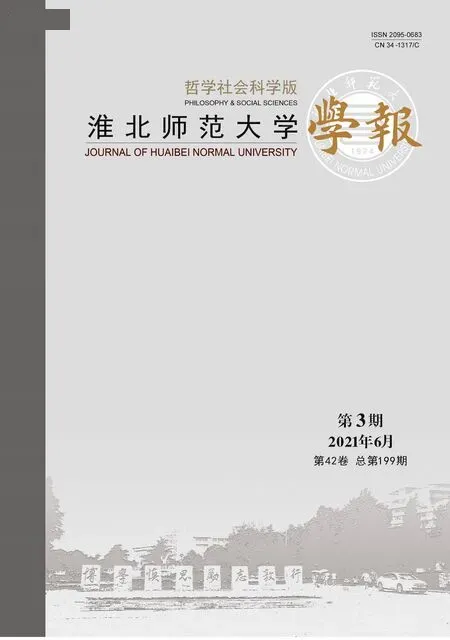论曾国藩的气性与其古文思想之关系
柳春蕊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曾国藩的古文思想和理论,有很多独创,在晚清古文思想和理论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本文将古文置于曾国藩整个人生中加以考察,哪些因素影响到曾氏的古文思想和理论,同时,曾国藩的古文思想和理论又如何影响或参与其儒家人格理想的实现。做这样的分析,旨在说明属于曾国藩一己之独得的古文思想和理论都与曾国藩自身有内在一致性,而非泛化的影响之谈。曾国藩嗜好古文,而古文更关乎其内在的个人气性,因而我们以曾国藩的气性变化、认识境界为主要关注点,从曾氏的“类”思想、认识事物“推”的思维方式、书法与古文相通、阴阳刚柔人格互补的自觉意识以及曾国藩诵读古文的习惯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类”的思想
曾国藩读书得“类”之妙者甚多,如:
二更后温《孟子》,分类记出,写于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属,目曰性道至言;言取与出处之属,目曰廉节大防;言自况自许之属,目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厉之属,目曰切己反求。①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条,页951。将《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为条类,别而录之,庶几取“象”于天文地理,取“象”于身于物者,一目了然。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条,页1920。又“温《集解》,将‘象’类分条记录。”(《曾国藩全集》第18册《日记》“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条,页1921)“夜温《周易传义音训》《谦》、《豫》二卦,将《同人》、《大有》等四卦‘象’类分条录记。”(《日记》“同治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条,页1922)
曾国藩在姚鼐文章阳刚阴柔之说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阳刚阴柔与古文创作实践的关系问题: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①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十年三月十七日”条,页475。
姚鼐在《复鲁絜非书》《海愚诗钞序》中将文章分为阴柔阳刚两类,阐明其审美特性,最后归于创作主体的气质和禀赋,主张阳刚与阴柔交错成文,“时时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或能避所短而不犯”。但姚鼐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两方面:(1)文与人一,“观其音,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②姚鼐《惜抱轩全集·文集》卷八,中国书店,1991。。(2)姚鼐此一认识,有一个从“天地自然之气”到“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再到常人偏于阳刚、阴柔的逻辑。姚鼐的古文偏于阴柔,这与其性情、学养及其阅历有关,因而,姚鼐此一理论虽然说的是古文风格问题,然而实质上谈的是创作者“才性”问题。
曾国藩《日记》“乙丑(1865)正月廿二日”条记载:“余昔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中国文论史上,《二十四诗品》早就有系统地以四言诗形式对诗歌的体性进行了描绘,曾国藩也以四言诗四句的形式来赋赞文境,但他是“蓄之数年”,而后才“发为文章”,一是说明这些文字的“含金量”比较高;二是他将文境之美分为八类,而不是分为九类、十类,似乎这分类本身就有更深的意义。如何理解曾国藩古文“八美”?总体上将它们理解为古文风格,似无疑问。他分为“阴阳”“八美”的内在依据是什么?从其《日记》材料来看,无疑是受到《周易》思想的影响。《周易》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它留下了早先人们认识万物的方式和既有成果。这种思维方式是“类”思想的发明,换言之,早期人们认识自身和对象,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式对其对象世界予以分类并加以推衍。
曾国藩对文境的把握是建立在他熟读体悟自得的基础之上,而体悟自得与曾国藩爱好分“类”这一思维方式密不可分,换言之,“类”思维是曾国藩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有效途径。分类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现在看来它的意义似乎不大,因为我们很难确定“类”在其未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之前,究竟蕴藏着哪些东西。当我们追问人类为何需要或选择用“类”来思考时,用“类”来看待我们的思维是处于什么层面活动时,这样或许对我们认识日渐遗忘的“类”的原始经验有启示作用。当我们追问曾国藩何以成为曾国藩之时,——他由一个世泽不厚的乡村家族中走出,开启宏伟大业,他的内在依据是什么,这确实有其得时势的一面,但我更倾向于将这些内在性问题作一学理上的清理。“类”的认识方式对其认识对象和认识自身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类”对曾氏古文思想及理想的积极影响,今举其《经史百家杂钞》关于“文”的分类加以说明:
曾国藩将文章分为“三门”:即“著述门”“告语门”和“记载门”三种。其中“著述门”包括“论著类”“词赋类”“序跋类”。“告语门”包括“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和“哀祭类”。“记载门”包括“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四种。姚鼐将文章分为十三类,较《昭明文选》所分更能“当”文之体式。曾国藩为何要将文章归为三大类呢?
“著述门”指的是创作主体面对自己的叙事。“记载门”指的是创作主体对其一己之外的对象世界的叙事,包括物、人、自然界、事、理、历史制度等。“告语门”指的是创作主体与他人的关系世界的叙事。这样,作为“有心之器”的人而言,其所创作内容都不会超过这三个层面。其中“告语门”又分上下、下上、同辈、人与鬼神等,厘清了创作主体“人”的关系。这是从文体上分,而曾国藩另一古文选本《古文四象》则是从文境上分,将古文分为“四象”,“象”,即“类”。检其晚年日记,他更看好《古文四象》,诵读《四象》的比例要比《杂钞》多得多。“四象”是指识度、气势、情韵和趣味③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页1296。,这四类对应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四属。
曾国藩以类别来选文,藉此把握古文,这样的做法与其察人、用人、行军、读书分类一样,都是为了有效地把握对象世界,只是这一对象是历代古文,而彼一对象是具体生活中的事,包括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在曾国藩看来,自从有了“文”之后,这些“文”自然不超过这“三门”(从文体上界定)和“四象”(从文境上界定)。刘勰将“文”分为“天文”“地文”“人文”,同样体现其对“文”的深刻认识。当然,将文章分为“三门”和“四象”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不过,曾国藩对此是相当自信的,这并非我的臆断,关于“类”思想以及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内涵,曾国藩有说明,其《谕纪泽书》云:
目录分类,非一言可尽。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钞之法。若从本原论之,当以《尔雅》为分类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鸟兽草木,皆古圣贤人辨其品汇,命之以名。《书》所称大禹主名山川,《礼》所称黄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后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车、弓矢、俎豆、钟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后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礼乐、兵刑、赏罚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经纶天下。或先有事而后有字,或先有字而后有事,故又必知万物之本,而后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后有文词。①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页772-773。
“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此为客观的科学认识。“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钞之法”,此为主观之爱好。
曾国藩以《尔雅》为例考究了文字的起源、万事万物的“名”出现的“前状态”。这里,他思考的是概念与现象之间有无同步性,类别与指涉对象之间有无同一性的问题。试图找到概念和“名”所可能凸现的全部意义和丰富内涵。曾国藩把概念和“名”背后隐藏的全部意义界定为“本”和“原”,即“物必先有名,而后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必先有器而后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和“或先有事而后有字,或先有字而后有事,故又必知万事之本,而后知文字之原”。
而且,曾国藩从《尔雅》中厘定了概念、“名”产生之前的三种物质形态——物、器、事。故而《尔雅》解释的所有对象都包含在“物之属”“事之属”和“文字之属”里面。后世人事日多,史册日繁,必然导致事多而器物少,所以后世的分类“惟属事者最详”,而《尔雅》之分类,“惟属事者最略”。
应该说,曾国藩在“类”方面的认识相当深刻,他在古文方面分类的做法,究其原因,与这一“类”思想有重要关联。其古文思想及理论之所以高人一筹,亦与此“类”的思想有大关系。
二、“推”的思维方式
与“类”相联的是“推”。“类”为归纳,“推”为演绎。
曾国藩由一端而悟出另一端,由一事物推及万物。检其《日记》,此类经验异常之多,像天道“三恶”、人事“四知”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九年五月初八日”条,页384。;凡人凉薄之德有“三端”、君子有“三乐”③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九年九月廿日”条、“九月廿一”条,页421。“君子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十“三”字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条,页432。十“三”字:谓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古文“八字诀”⑤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廿三日”条,页487。;“居高位者之道,约有三端”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十年六月十二日”条,页511。;“求人约有四类,求之之道,约有三端。治事约有四类,治之之道,约有三端。”⑦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十年七月廿九日”条,页516。“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⑧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条,页740。;“欲求养气,不外‘自反而缩,行慊于心’两句;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并将此三“字”阐明为“十二语”⑨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条,页802。;“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善端无穷”⑩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条,页851。;“偶思古文、古诗最可学者,占八句”[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同治五年正月十五日”条,页1226。“八句”:《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等等。
可以看出,在各种各样的现象世界中,曾国藩试图找出“一理”和“万殊”。这本是理学家看待事物的固有方法,在道、咸时期京师理学人士身上极为常见。当然,曾国藩以上所悟并不全是真知灼见,却不妨碍我们对其“类”、“推”思想的认识。通读其集,这些提法由他说来颇显真切,而且,曾国藩将读书、作文、习字、行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集于一身,比京师理学家多一分躬行之实,比其他文士多一分博见之知,这样也为其“推”思想的展开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
书法与古文这两门艺术基本上终曾氏一生,故曾国藩这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书法与古文互通,熟习之后,颇多见道之语。这方面材料很多,如论书法、作文皆阴阳刚柔相济,“庶几成体之书”。其言云:
偶思作字之法,亦有所谓阳德之美、阴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为“阳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觩、曰勒、曰努;为“阴德之美”者四端:曰骩、曰偃、曰绵、曰远。兼此八者,庶几其为成体之书。在我者以八德自勖,又于古人中择八家以为法,曰欧、虞、李、黄、邓、刘、郑、王。①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七日”条,页829—830。
又,曾氏认为书与诗文在艺境上相通,主张雄奇和淡远,俊拔之气与自然之势,节与势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廿三日”条载“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页771。,着力与不着力,比兴之体与盛气喷薄,奇横之趣与自然之致,相互为用,二者兼营。又论书法之“势”与古文立意之“取势”,书法之结体与古文之谋篇布局,书法之气势与古文之吞吐断续,书法之神情风韵与古文之情韵趣味相通:
偶思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余近年于书略有长进,以后当更于意态上着些体验功夫,因为四语,曰骩属鹰视,拨灯嚼绒,欲落不落,欲行不行。③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7册《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条,页930—931。
这些文字写于咸丰八年(1858)至同治五年(1866)间。此一时期,曾国藩对于书法、古文二艺相通发明甚多。如果说此前这类领悟受其所接受“知识”影响,还只是一种“悟”和“识”的浅层次的话,那么这时期由于实践之功,在熟读古文和习字中相互印证、相互提高、相为圆融,又为一层次。人们讨论曾国藩的古文思想和理论,往往忽略其与书法理论的联系,这不利于全面理解曾国藩古文思想和理论,也难以理解其古文理论之所自。同时,还应看到,一旦诗文和另一门艺术相结合,互为参证,身体力行,那么这样出来的诗文理论,它的蕴藉可能更为丰富。姚鼐、曾国藩、张裕钊和林纾,既是古文家,也是书法家,其古文识解之所以超乎常人,除其功深独到之外,也与参悟另一艺术门类有很大关系。
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将读书、修身打成一片,由所读之书推之于将为之事,并以修身约之。
以上分析了曾国藩“推”思维的特点。下面再补充三点:
(1)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四日立下的每日所习课程起,至去世之前,曾国藩按此而行,少有懈怠。每日除处理事务之外,为读书和修身,坚持不懈。他的视野在立德(义理)、立言(辞章、考据)、立功(经济)三个层面推进。同时,其阅读经验与自身经历所昭示的“世界”也在三个层面展开,这使得其“推”思想本身就潜在涵盖着一个大的空间,而这个大的空间对于曾国藩事业的状态而言无疑是一种推进;事业上的进境又使其所“推”之对象日益丰富,包括万事万物的自然秩序和法则。当然,在历史语境中,曾国藩所推之事物由于实用特点而略有“陈言”之嫌,然而由于曾国藩读书行己的全部意义在于修身和经世,因而由“推”而来的认知结果并不机械,而具有实践能动性,这对古文同样是适合的。
(2)大凡其“推”之事皆有本有末,有一个内在逻辑,即艺术(从诗文习字开始)→心性→事理→实践,这符合曾国藩人格理想的预设。
(3)由古文而“推”及他物,或由他物而“推”及古文,这样使得曾国藩古文思想及理论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并与其他门类如事功、书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三、不同时期的个性与古文理论的完善
这种动态特征还体现在其古文思想和理论不断完善上面。综曾国藩一生,强调刚健、俊伟的气势,取法天地义气,一主阳刚的文境为其论文之主要观点。尽管咸丰八年(1858)之后他主张“刚柔相济”说,但这与我们对其古文理论的总体判断并不抵牾。曾国藩早年论文,云:
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页54。
从禀性上说,曾国藩的刚毅受其母亲和祖父星冈公的影响①曾国藩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全集》第17册《家书》,页1139)。从后天学习上说,与其事业型的人生期待互相促进。《杂著》“阳刚”条云:
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霸上还军之情,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杂著》“阳刚条”,页394。
曾国藩一生私淑孟子③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条,页114。,缘于“善养吾浩然之气”。惟有阳刚之气,才可能立其规模,才能做到真正的勉强,是基石,是“穷理”最为关键一步。他认为“强毅之气,决不可无”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页364。。“强”指的是后天的勉强,由不可能而臻及可能的坚车行远之功和贞恒之性,即《淮南子·修务训》所说“名可务立,功可强成。”⑤张双棣《淮南子校释》(下),页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在他看来,万事皆可强恕而为之:
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董生有言:“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强之为道甚博,而端自强恕始。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杂著》“勉强”条,页378。
我们可以处处看到曾国藩“强恕”的一面。其一生经常反省自己多言、傲、要人说好、自恃过多以及早年屡禁难改的下棋、抽烟、打牌、淫想等习气,处处以墨、禹的“勤”“俭”来要求自己⑦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条,页574。,这些都可在“强恕”二字中得到印证。而“强恕”的目的无非是复性,在曾氏看来,“性”有两层:一是由于性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本性日失,藉学和勉强以复全;二是“性”犹如孟子所说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⑧杨伯峻《孟子译注》(下),页333,中华书局,1960。,为自然而然之状态。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极力肯定勉强之功所体现的精神状态:崛强和刚毅。
以刚健之才,挽回士气,本为曾国藩一生的理念,为“猛火煮”,而其后“鸡伏卵”“慢火温”这些阶段,不应作“柔”视之,更有刚健、自强不息之意。曾国藩以庄子、司马迁、司马相如和韩愈为宗,即取阳刚雄健一路,《古文四象》以“气势”冠首,亦此意。晚年朗诵最多的即“气势”类诗文,亦此意。虽然曾国藩晚年常叹文境之不至,但刚健之气溢于其间,当属事实。
曾国藩论文重视文气,主张以行气为第一义。曾氏为文有从气势上著力,有从揣摩上著力。认为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固属切实工夫”,“四象表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⑨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页1204—1205。,无气势之磅礴,自不能生出平淡之境。
曾国藩的古文理想只是价值论判断,而非事实逻辑,不能取代他的认识论。他的认识论从来是两分或是兼容。他认为西汉文章有“天地之义气”与“天地之仁气”二种,而文章之变,殆不出乎此。⑩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页249。
咸丰八年(1858)之后,曾国藩论文主张“合雄奇于淡远之中”[1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条,页632。,发现了洒落之机、胸襟淡宕的意义,诗文兴趣由孟子、扬雄、韩愈、王安石转向陶渊明、柳宗元、白居易、韦应物、邵雍、苏轼、陆游,这一转向有着相当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为支撑①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攻湖北,武汉危急,朝廷命曾国藩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汉策应。太平军进逼安徽庐州,曾国藩屡次抗命,负气强硬。直至庐州三河镇失守,湘军死亡无数,曾国藩始稍有改势。咸丰八年(1858),清廷因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保奏,谕令曾国藩即行率部援浙。曾国藩反省所作所为,幡然悔悟,一法黄老柔弱之旨,知雄守雌,为争夺皖北势力范围,湘军集团与满蒙亲贵进行长期的斗争。同治二年(1863),僧格林沁借词奏劾湘系骨干安徽巡抚唐训方,唐以藩司降补,曾国藩受此打击最大。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公开决裂。同治五年(1866),剿捻欠效,朝廷上下群起交攻,御史弹劾,廷旨训斥,曾国藩一挫再挫,这在其奏稿中最易体现。曾氏早期戆直、激切与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平淡质实。(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页15—2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是与其事业期待当中的“格物”有直接关联。“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是他亲证的结论。此后,他对于诗文的理解,于“诙诡”“闲适”的“趣味”多有接纳:
凡诗文趣味约有二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尔胸怀颇雅淡,试将此三人之诗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②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页1332—1333。
读书贵在变化气质,使自己的人格和胸襟得以扩广,这本是曾国藩读书之旨趣。曾氏以古文完善自己的气性,表现在文学鉴赏和批评上,则主“刚柔相济”说。比如,他说张裕钊“气体近柔,望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③曾国藩《加张裕钊片》,《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页934。,即此义。同样,曾国藩晚年所选《古文四象》,强调“气势”和“识度”的同时,对“趣味”和“情韵”亦相当重视,这些看法恐怕与他自觉地以柔补刚的气性观念有大关系,一言以蔽之,曾国藩古文理论的形成与其气性之完善密不可分。
四、曾氏的至性与善诙谐
曾国藩自小善诙谐、有真切之仁心。据黎庶昌《曾国藩年谱》记载:“三岁,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花开鸟语,注目流眄,状若有所会悟。”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页2,岳麓书社,1986。验诸日记、家书,其于兄弟、友朋之间,周济邻里,皆以义行,概有“仁”之用。⑤朋友离去,亲人故旧,死生契阔,尤难为怀。此方面材料太多,兹不具引。“仁爱有余,威猛不足”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页256。,这是他与兄弟说的诚心话,当为可信。
古文可以情当之,只是有的情以理为主,有的情以事为主。情、理二谛,曾国藩身上兼而有之:由情而至者言,故而文事在他生命中乃一重要事情,从未断绝,而且能静心养气,通于道⑦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条载“果能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曾氏理念是“诗通于艺”,只是他修炼未至。何绍基所谈,曾氏认为“甚知要,得艺通于道之旨”(《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又,“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条记“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说明曾国藩习诗文意在知言养气功夫,可视为“穷理”之一端。,此不类于理学家;由理而至者言,故在情上难能一往情深,故不类于文人情志游荡者。曾国藩古文造诣不高,与其用情未能缠绵悱恻、一往而深而时时存一“理”在心中不无关系。此从积极方面说。
从消极方面说,曾国藩善诙谐,谑言不敬、不诚、夸诞无衷,曾国藩早年经常自省,以为耻。⑧如《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条记“说话又多戏谑”,“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五日”条记“是日,与蕙西有作伪之言,夜多戏言”,“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初四日”条记“席间,因谑言太多,为人所辱,是自取也”,同年三月初五日记“至岱云家赴饮约,语次屡有谐谑之言”,《日记》“同年十月十三日”条记“是日,口过甚多,中有一言戏谑。”“同年十一月十八日”条记“余言多夸诞,”“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记“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与此相关的是,话多、语浮、议人短长、内有矜气、房闼不敬、狎亵而无庄重,这些都是曾国藩痛省的主要内容,这是诙谐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文事方面,更复如是,像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月二十八日大雨,冯君树堂、周君荇农、郭君筠仙方以试事困于场屋,念此殆非所堪,诗以调之》一诗,中一段云:
冯君枯坐但闭目,急溜洒面不曾开。周侯仰天得画本,倚墙绝叫添喧豗。郭生耐寒苦索句,饥肠内转鸣春雷。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脢。明朝日晴各转斗,老罴战罢还归来。为君广沽软脚酒,泥污不洗且衔杯。①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页50。
极尽谑笑之能事,曾国藩颇以此得意。文学要状万物之变态,曲尽幽远细微之境,使之成为其特有的“这一个”,所以文学创作是不同于“道”体那样主一为静,而是居奇主变。曾国藩认识到大多数古文都具有奇诞、寓言的特点,这表明曾国藩对于文学审美愉悦的功能的认识相当深刻。他认为读《左传》《庄子》《史记》、韩愈五言诗当从这方面着手方能体会,兹举两例: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②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页248。
韩公五言诗本难领会,尔且先于怪奇可骇处、诙谐可笑处细心领会。可骇处,如咏落叶,则曰:“谓是夜气灭,望舒霣其圆。”咏作文,则曰:“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可笑处,如咏登科,则曰:“侪辈妒且热,喘如竹筒吹。”咏苦寒,则曰:“羲和送日出,恇怯频窥觇。”尔从此等处用心,可以长才力,亦可添风趣。③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0册《家书》(二),页916。
刘蓉《曾太傅挽歌百首》有不少关于曾国藩此方面的记载,其“筹笔”诗云:
筹笔频年历百艰,寸心终夜懔如丹。漆园傲吏何曾达,恢诡文章只自谩。
公每谈燕,好举蒙庄旷达之语,用相谐笑,及遇事用心精细,终夕惕厉。予每笑之曰:“何不唤取庄生来也。”④刘蓉《养晦堂诗集》卷二,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刻本。
曾国藩讲仁爱,仁爱是一种宽大的“情”。无论是言情或言志,在儒家文论中,最终要落在“仁”上来。然而只有仁爱,则倾于义理道学一途。如果能做到奇⑤“奇”指的是文能穷尽万有之变态,穷形尽相。,则仁爱之情才能较为具体而形象地体现在文章中,而这有赖于荒诞、诙谐、寓言等艺术手法。文学只有在表现每个具体的理、事、情上,才可能做到艺与道合。在通往“道”法则的途中,文学显然与理学、经济所呈现的具体情形截然不同。
五、朗诵、熟读与曾氏古文鉴赏学
曾国藩人生“三乐”之一便是“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九年九月廿一日”条,页421。,自入翰林院之后,朗诵古文成为曾国藩每日的必修课,曾国藩在古文创作方面强调一个“熟”字。《日记》“咸丰九年(1859)四月初八日条”云:
夜阅韩文《送高闲上人序》,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⑦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咸丰十年初一日”条,页542。
“熟读”是学文的基本功夫。对于曾国藩而言,熟读经典有两层意义:一是如前所论,为养气,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是在熟读过程中的自得与妙悟,并由此形成了曾国藩古文理论中独特的评点和鉴赏之学。检《日记》,其“读”书之法又分“温”“默诵”“朗诵”“放声朗诵”“细诵”“涵泳”等。次列其兴来所会者,如:
“温《伯夷列传》,诵十遍。”“夜温《报扬广书》、《与吴季重书》,细诵数次,稍有所会。”“读《下系》十一爻,若有所会。”“夜涵咏熟书,不办公事。”“夜温古文,将《幽通赋》细读数过,若有所会。”“在外厅上欹坐,默诵苏诗至傍夕。”“疲倦已极,温杜诗五律,朗诵几不能成声矣。”“夜温《孟子》,朗诵数十章,声气若不能相属者。”“二更后温《古文·辞赋类》,朗诵之下,气若不能接续,盖衰退之象也。”“温《易经·系辞》,朗诵似有所得。”①引文分别见于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页418,页487,页519,页467页,628,页1176,页1156,页1265,页932。
又,次列其古文评点及理论有所自得者,如:
“夜温《长杨赋》,于古人行文之气,似有所得。”“思《书经·吕刑》,于句法若有所会。”“是日酉刻温苏诗,朗诵颇久,有声出金石之乐。因思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魄耳。”“细玩孟子光明俊伟之气,惟庄子与韩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阳明亦殊磊落,但文辞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因读李太白、杜子美各六篇,悟作书之道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乃能渐入证果。”“念古文之道,亦须有奇横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进,乃为成体之文。”②引文分别见于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页419,页419,页698,页661,页735,页638。
又,次列其温读于心性有闲适之效,能引其情韵,为之一慰者,如:
“温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渐渐可入佳境。”“夜教纪泽读书宜放声歌诵,以引其情韵。”“温《孟子》,二更后放声朗诵数十章,音节清越,有如金石,为之一慰。”③引文分别见于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页420,页1056,页1157。
以上材料旨在说明:(1)曾国藩古文理论是在其长期不断地熟读朗诵古文基础之上形成的,因而其古文理论个人感悟性色彩明显。由朗诵中形成的感悟与评点,很自然使其古文理论偏重在鉴赏批评上面,故而其古文理论可看作是古文鉴赏批评之学。(2)曾国藩认为“文章之道通乎声音”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16册《日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条,页945。,高度重视古文的声音性。(3)曾国藩在具体诵读的情形又自不同,有的是在夜阑人静,有的是在黎明破晓,有的在长江两岸,有的则在星月旷野,军次行兵之时,高声迈古,这样的气氛和境地,古文本身所蕴蓄的“意义”更容易“唤醒”,而这一“意义”更能充分展露出来。这一点,有清一代古文家是很难达到曾国藩这样“情景”——既包括能在多种环境、不同时段内诵读古文的可行性,又包括诵读古文时得到的那种独特的审美悦怿:阔大与幽深,雄气与情韵。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同是评点,同是体悟,曾国藩要比姚鼐、梅曾亮等桐城诸家要高得多,其高深处集中体现在《古文四象》的编选上面,后来桐城派大师吴汝纶不甚明白《古文四象》的分类以及入选篇目的主旨,曾氏得古文之深,盖可知矣。(4)通过一己之独得,常常能印证此前古文理论中既有的经验和成果,因而,曾国藩古文理论原创性不多——整体来说,自韩愈以降古文家,理论独创性都不明显。后来古文理论的建树与阐发,大多都可在韩愈那里找到相应的答案,但一经曾氏道出,却异常亲切,这样的阅读效果,同样可归于他的熟读善悟上,这也是曾国藩古文思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