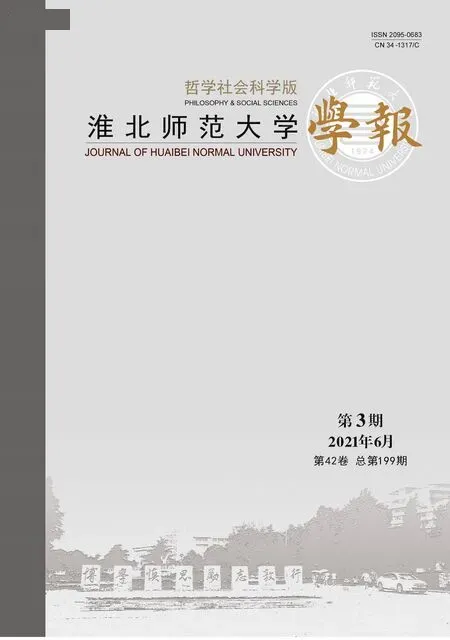从屈民伸君到以民为本:董仲舒政治哲学解读
康喆清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董仲舒是汉代以降第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儒学大师。他早年在民间讲学,学生众多,影响很大,汉景帝时出任博士官,讲授《春秋公羊传》。汉武帝时,董仲舒由“天人三策”系统阐发其政治哲学,得到汉武帝认可,儒学一跃成为显学,开始对后世社会长达二千多年的持久影响。董仲舒的思想内涵丰富,学界已从多角度开展研究,对其政治哲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点。董仲舒一生历经西汉三朝,恰逢王朝盛世,他将先秦儒学与汉初社会现实结合,杂糅各家思想,创建了一套以儒学为核心的政治哲学体系,这是其思想中的宝贵遗产。目前学界对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时代背景、天道基础及当代价值的阐发,而对其政治哲学体系的还原及现代性解读着力不够。本文从董仲舒思想本源处找寻政治焦点,推衍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思想脉络和完整结构,尝试进行系统性还原。在董仲舒看来,要实现理想的王道政治,君民关系最为重要,而君民关系的核心在民不在君,“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1]275由此思想引申,董氏的政治哲学首先回答了君王的地位(沟通天人)和责任(教化万民),然后论述了为政的核心(教本狱末)和旨归(以民为本),其政治哲学的根本在于王权制衡,以德化民,造福百姓。
一、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基础:君者何位
有学者指出,“汉代的儒者为了取得与君王合作的机会,他们的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在依然保留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的同时,由高调理想主义的道转变为现实功利主义的治,这是儒家士大夫寻求与君王合作的重要调整和实际代价。”[2]这种倾向在董氏这里亦有所体现,董仲舒政治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积极寻求与王权的合作。董仲舒作为一介儒生,其思想只有获得政治话语权,才可能被君王认可接受,进而对社会实践产生影响,所以董仲舒政治哲学首先论述的是王权合法性,通过天人间关系的比附论证,赋予君王特殊地位,从而明确其合法性。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君王是联结天人的枢纽。
(一)“天—君—民”受命秩序的建构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其天道哲学,而“天人关系素来是儒家的核心议题,每一次对天人关系之认识的转折都标志着儒家对于秩序和价值之理解的新发展。”[3]儒家天人关系论在董氏这里的转折在于将阴阳家思想作为方法论,构建起一套天道运行系统,作为人间秩序的遵循,天是世间终极范畴,也自然是人间的源头,天道是人道之本。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总体上讲究天人之间的感应,但人是有等级区分的,又分为君和民,民追随君、君追随天,并由此展开论述,“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1]559这就形成了“天—君—民”的受命秩序。也就是说,作为类群的人虽然在总体上可与天相感应,但必须通过上一等级的人方可发生,这样一来,只有君王可以与天直接感应,承担着与天沟通的任务,是天人感应的第一责任人。为什么君王这么重要?“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1]421在董仲舒看来,君王这种地位的获得也是自有天意,所谓“王道通三”,起着沟通联结“天、地、人”的作用,在这种上乘天意、下达人间的过程中,君王自然拥有权威。通过“天—君—民”受命秩序的建构,董仲舒从理论上解释了汉初一直困扰刘氏政权的王权合法性问题。
(二)屈民伸君与屈君伸天的平衡
天人之间如何受命?董仲舒认为,君王作为联结天人的枢纽,是通过“郊祭”这种方式体察天意的。“《春秋》之法,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四祭于宗庙……每更纪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贵之义,尊天之道也。”[1]179自周代开始,统治者已经将郊祭作为一种隆重的仪式,表达对天的敬畏,也是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维护。到了汉代,郊祭更是成为使君王体察天意,感受上天恩德的重要方式。“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1]421-422通过郊祭的方式,君王主要是感受上天的仁德。上天通过仁德之情,化育世间万物而不求自身功绩,周而复始,永不停歇。“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1]445君王通过天人感应受命于天,在社会中也要法天而行,施行仁政。通过重视并沿用周代开始的郊祭,董仲舒将儒家传统的仁政思想附会于天意,由人道法天进而形成对王权的必要限制。可见,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中,君王是关键一环,这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决定的。
先通过受命秩序的建构论证王权合法性,再通过附会天意的儒家仁政思想限制王权,董仲舒试图达到一种制衡,这种制衡的成立和稳定,是其政治哲学展开的逻辑基础。从春秋战国到秦王朝的覆灭,历史一次次证明,王权若不受限,不仅会造成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而且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所以董仲舒将天置于君王之上,在人间社会之外为王权设置一种约束,所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27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中,屈民伸君是前提,屈君伸天是目的,两者密不可分。“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1]199首先要明确王权、承认王权。另一方面,在汉代这样的统一王朝,对君权的限制又显得非常必要,这种限制同样是借助天来完成的。董仲舒提出,“天子号天之子也。奈何受为天子之号,而无天子之礼?天子不可不祭天也,无异人之不可以不事父。”[1]544按照对“天子”这一名号的理解,君王作为天之子,理应按照父子之间的伦常关系,对天行孝道,“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1]368这就把人伦关系中的忠孝观念延展到天人关系中,通过虚拟血缘的父子关系,以天的名义对王权进行必要限制。而在天背后,是儒生根据儒家经典对天意所进行的解释,这又在“天—君—儒”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制衡关系,只要这种制衡关系保持一定的张力,就能保证社会政治生活的合理稳定。这种理论设计使儒学获取政治话语权成为可能,“天是什么意思,这就靠儒家来解释。儒家当然按儒学来解释。这样,儒学也就冠以天的名义。换一说法,天的意思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天意。用天制约皇权,实际上就是用儒学制约皇权。”[4]从此,先秦儒家的政治理想从一种元典理论转向政治实践,即儒生解释天意教化君王,而君王受命于天教化万民。
二、董仲舒政治哲学的起点:君者何为
先秦儒家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教化社会民众,这不是单纯的教育过程,而是一种政治观念和价值观念的有效灌输,化民成俗,使社会各阶级在根本观念上保持一致,从而维护政权稳定和巩固。“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5]董仲舒同样认识到教化对巩固王权合法性的重要性,他认为教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君王。
(一)君王承天意以化万民
董仲舒是研究《春秋公羊学》的儒学大师,他深谙春秋大义,“给世人树立衡量是非的标尺与行为准则,才是《春秋》的基本目标,而这正是《春秋》实现理想政治的基础。”[6]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董仲舒说道,“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7]2502这里,董仲舒再次强调了君王居于天人之间,所以需要“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那么君王要承什么样的天意呢?董仲舒接着从人性成善的角度展开论述,“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1]369人性中有向善的本质但却并未成善,所以上天设立君王通过教化使民性成善,这就是天意。所以,在“天—君—民”的受命体系中,君王上乘天意下达民众,通过教化转达天意,自然是万民之师。这样,儒家的价值精神通过天意的传达授予君王,君王用以正人正己,社会民众要经由教化感受天意,也就是儒家精神理念,这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高明之处,也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真正落到了实处。君王教化万民的现实性在于,君王自幼生活富足,具备良好的教育条件,往往较之常人聪慧,而普通民众大多为生活所累,疲于奔命,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要差得多,所以人性应善未善,这种情况下君王不仅要承担富民的重任,更要化民成善,使民众言行合乎礼法,遵守社会规则,此之谓“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8]231
(二)君王应善为师
君王作为万民之师,应当如何开展教化?董仲舒讲到了“善为师者”的基本原则,“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1]36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化者,首要的标准是具备高尚的道德,这是因为“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秩序不仅需要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护,也需要道德伦理规范的协调。”[9]当然这里指的主要是具备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伦理,其次还要对自身行为举止保持谨慎的态度,身教更胜于言传。儒家历来注重君王的榜样示范给民众带来的影响,孔子曾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董仲舒同样重视君王身教带来的积极影响,提出显德以示民的要求,他说,“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1]330也就是说,君王自身道德品质的感召性对民众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可以说是关键一环,“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7]2514西汉时期的君王也都非常重视身教,例如以劝课农桑为目的的出巡亲耕等,就是由君王开始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显德以示民,从而起到“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的目的,使社会民众潜移默化接受教化。
先秦儒家讲内圣外王,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外王是内圣的目的。君王通过道德修养锤炼内圣,在此基础上践行外王理想,内圣外王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统一。董仲舒对君王德行的论述也体现了这种内圣外王的精神,他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7]2497作为君王,要实现由内而外的“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的过程,必须始于自我内在的道德修养,方能终于对外事功的王道政治。汉代君王的内圣修养,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对孝的重视,这是由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带来的忠孝一体观念,孝是修身齐家的底线,忠是治国理政的前提。汉代君王大都能够率先垂范,推崇孝道,通过这种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在家为孝子,出门为忠臣。总之,赋予君王万民之师的责任,以天人关系所要求的王道教化,论证君王应当如何作为,这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起点。
三、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教本狱末
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在宏观的思路上就是道德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地位。基于秦朝速亡的教训和汉初的社会实际,董仲舒主张道德教化在社会中应当起主要作用,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1]88受法家思想影响,董仲舒认为法律对政治生活同样具有一定价值,所以吸收阴阳家的思想,将法律视为道德教化的一个层面、一种辅助手段。董仲舒的“教本狱末”思想在汉代影响很大,基本成为汉代思想家治国思想的主基调,认为“刑以佐德助治”。[10]526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教与狱应当相互协调,目标一致,共同为汉王朝的政治统治服务。
(一)道德教化是为政之本
董仲舒政治哲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所构建的本体性“天”,这是一个道德化、拟人化的天,是人间秩序的至高权威和遵循。在董仲舒的建构中,天的本性是一种道德仁爱的化身。“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1]421可见,仁爱之天的天意天命,就是施行道德仁义,沟通天人的君王也应在人间社会中推行道德教化。应该说,董仲舒的政治哲学首先是以德为基础的,他一方面强调屈民伸君,王权具有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强调民为邦本,人民是王朝兴盛的保障,决定了治乱兴亡,“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275所以君王要有爱民之心,广施教化。董仲舒指出,“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1]171国家的治理要保证长治久安,就要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而不能主要依靠严刑酷法。“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则四方莫不响应,风化善于彼矣。”[1]532这同样是强调道德教化对于为政的重要性。
(二)德主刑辅是天道伦常
董仲舒政治哲学与先秦儒学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在方法论上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的部分思想,如阴阳刑德等。而阴阳五行作为“古代中国人能够构想的最终原理”[11]254,也使董仲舒政治哲学的论证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在董仲舒看来,阳气和阴气是自然界的两种构成元素,但有多少强弱之分,正是两者间一定比例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能带动自然界万物生息,保持一种平衡。具体而言“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数随阳而终结。”[1]410阳气能够决定物的出、盛、衰,在自然界中占主导地位,但阴气的存在也有其作用,“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1]433在这里,董仲舒首先明确了自然界中阳气为主、阴气为辅的地位,即“贵阳而贱阴也。”[1]433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接着讲“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1]410这又是将人类社会的德与刑,分别比附于天道的阳和阴,为下一步论证打好基础。“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1]411可见,天道天意在于重德轻刑,正是由于天道的阳主阴辅、任阳不任阴,才有君王为政之道的德主刑辅、好德不好刑,否则,“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1]417通过论证阳气和阴气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进而论证德与刑在天道中的地位,最终是为了得出教本狱末的结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7]2502如果君王善用严刑峻法而忽视道德教化,就是违背了教本狱末的天理天道。
总之,作为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教本狱末既强调道德教化的主导地位,又重视刑罚作为教化补充的必要存在,本质上是要实现儒家的德政理念。
四、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旨归:以民为本
民本思想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中分量很重,也是其学说内容虽杂但仍归于儒家的重要原因。儒家的政治思想本就重视人民的力量,强调社会民众是王道政治的根基。但董仲舒之前,更多还是以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态存在,没有真正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到了汉代,目睹秦王朝覆灭过程的儒生再次看到社会民众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意义,“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以之为民无不为本也。”[1]377贾谊的这番话讲的就是民众乃社会的根本,也是政权稳固的根本,需要君王高度重视民众的福祸安危。在继承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董仲舒基于现实民众疾苦发展出自己的民本理论。汉初虽然经历了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的文景之治,经济基础得到较好恢复与发展,但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太多改善,反而是地主豪强不断兼并土地、盘剥财富、与民争利。由于汉武帝的“外事四夷,内兴功利”[7]1136,需要进一步筹措财富以补国库,桑弘羊等人建议实行“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经济管控举措,竭泽而渔,底层民众生活更加困难。对此,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7]1136
在董仲舒看来,要想实现善治,需要采取一系列举措改变汉承秦制的问题,如通过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限制豪强地主对农民土地的兼并与掠夺;取消盐铁国家专营,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等等。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始终强调君王的作用,即便是在其民本思想中,也没有大谈民众的权利或重要性,而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对君王进行劝诫。这是因为在君民关系中,君王是强势一方,唯有突显君王的政治责任,才能真正实现民众权利,才能将民本思想落到实处。总之,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基础,应当是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通过对汉武帝的极力劝诫,董仲舒试图由上而下在全社会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只可惜在武帝时,董仲舒的民本建议难以得到认可,所以才会出现“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7]1137的局面。
结语
以上系统梳理了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基础、起点、核心和旨归。从孔子始,先秦儒学就致力于构建理想的道德化政治秩序,形成了以德政为核心的儒家政治哲学,主要回答了执政者合法性的问题、执政方式的问题和执政理想状态等问题。到了汉代,董仲舒系统回答了上述问题,体现了其民心关切,传承了儒家传统的德政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也体现出自身特点,主要是论证方式中大量借用阴阳家的思想,以天人感应的天道观为基本的论证模式。正是天人感应的基本架构,使其政治哲学得以从对君王地位的论证开始,在“天—君—民”的受命系统中得出君王在人间至上权威的地位。董仲舒在秦汉时期统一政治制度基本成型的历史背景下,探讨王权的合法性权威性,对于汉王朝的巩固乃至封建统一政治制度的巩固都具有重要意义,“是最能够满足时代需要的建设性思想。”[12]同时,这种王权合法性的论证也是附有条件的,即君王要法天而行,才能得到上天认可。就现实政治层面,天背后的力量除了儒生依儒家经典所做的解释外,更为普泛的力量是社会民众。从对王权的尊崇到对百姓的维护,可以清晰梳理出董仲舒政治哲学的逻辑脉络,这是一条从维护君权以获得认可,到强调教化以限制刑罚,再到省徭薄赋以宽限民力的政治理路。这一思路突破了先秦儒家偏向理想主义的政治伦理倾向,是一种实践性较强的学说。遗憾的是,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恰逢汉武帝大兴事功,所以其政治哲学未完全得到认可和推行。尽管如此,汉武帝仍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儒术,设立以儒学为内容的博士官制度,建立了以儒学为主要讲授内容的中央太学和地方官学教育体系,儒家学者入仕也更加畅通,形成了制度化的选拔机制。这对后世王朝政治形态和文化模式的确立起到示范作用,“初步完成了汉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并在后世经过历代王朝的补充、完善和发展,直至清末才宣告终结。”[13]更为重要的,或许是董仲舒政治哲学中灿烂的人性光辉和朴素的民本思想,这是超越时代和社会形态,在当今仍值得珍视的政治思想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