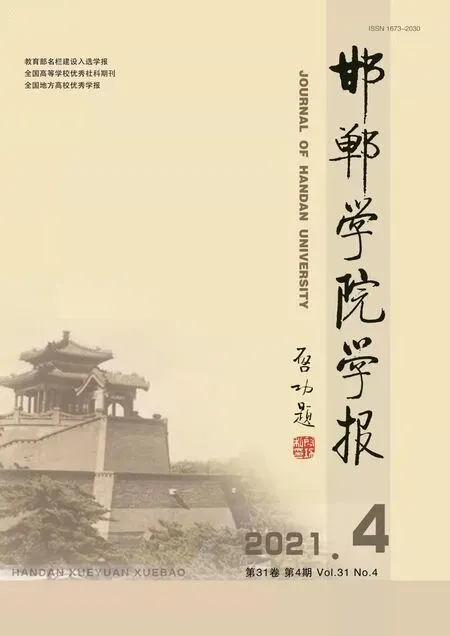论贾公彦的汉字学思想
郭照川,邓红爱,王 颖
(1.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2.廊坊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河北 廊坊 065099)
贾公彦(今河北省永年县人)是我国唐代著名经学家,其所著《周礼疏》和《仪礼疏》是中华核心经典“十三经注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学角度看,其中蕴含了很多对汉字的理性认识成果,在汉字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贾氏的汉字学思想可分为两大块:一是对前代理论成果的继承,主要是形义统一思想;二是在前代成果基础上的创新,包括汉字职能思想和汉字形体组构思想。《周礼》和《仪礼》在汉代已由郑玄系统整理、注释,贾公彦即在此基础上进行疏解,既解经文又释郑注。唐人注经的前提是 “疏不破注”,贾氏也遵循这一原则,主要致力于对郑玄注解的统一、疏通和补充,这种体例决定了贾氏一般不会系统阐述其对汉字的看法,而是将之作为指导原则或操作规程融入注疏过程之中,因此对贾公彦汉字思想的归纳要通过考察其具体的注疏实践来实现。
一、形义统一思想
汉字自产生以来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表意性质,这个事实塑造了汉字使用者“形义统一”的观念。在面对文字材料时,“因形见义”几乎成为我们一种本能的预期;另一方面,根据意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定其所对应汉字的形体。贾公彦继承了这一思想,在疏解二《礼》过程中将之落实为“因形定义”和“以义证形”两种注疏方式。
(一)因形定义
因形求义的思想自先秦以来历代承袭,由汉至唐在理论认知上并无实质性突破,贾公彦完全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疏解实践中。
①《周礼·天官冢宰》:笾人,奄一人,女笾十人,奚二十人。
郑玄注:竹曰笾。
贾疏:知“竹曰笾”者,更无异文,见竹下为之,即知以竹为之,故云竹曰笾也。
又《笾人》:笾人,掌四笾之实。
郑玄注:笾,竹器如豆者,其容实皆四升。
贾疏:郑知笾是竹器者,笾之字竹下为之,亦依《汉礼器制度》而知也。
按:本例中笾字的意思文献已有明确记载,如《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说文·竹部》:“笾,竹豆也。从竹,边声。”郑玄只是引用成说,贾氏则着力申述作为义符的“竹”与字义之间的联系,为前代的释义阐明字形上的依据,因形求义的思路更明显。下面两例也属于同类情形:
②《仪礼·士婚礼》:妇执笲枣、栗,自门入。
郑玄注:笲,竹器而衣者,其形盖如今之筥、䒧蘆。
贾疏:知“䒪,竹器”者,以字从竹,故知竹器。
③《周礼·醢人》:加豆之食,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
郑众注:箈,水中鱼衣。
郑玄注:玄谓“箈,箭萌。”
贾疏:此箈字既竹下为之,非是水物,不得为鱼衣,故后郑不从。
按:形声字包含声符和义符两种构件,声符表示字音,义符表字义,这是许慎以来的基本认识。关于义符和字义之间的关系,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得最为明白,即“以类为形,配以声也”[1]12。也就是说义符表示的是整字字义的意义范畴,而非具体的字义,贾公彦在注疏实践中继承了这一思想。上述三例中“笾、笲、箈”作为语词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即它们所表示的对象在材质上是相同的,这在字形上以义符“竹”来体现。贾氏在注解中将字形和字义进行分解,通过义符确定其所表示的意义范畴,进而明确整字所指代对象的属性。这种做法虽并未突破“六书”理论,但相对而言,更加明确、精细,理论性也更强,显示了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进步。
会意字的构造原理是“比类合谊,以见指撝”,因此解释了字形结构同时也就解释了意义,贾氏有时也通过解释会意字的结构来证明字义。
④《周礼·掌囚》:上罪梏拲而桎。
郑众注:拲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
郑玄注: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
贾疏:先郑云“拲者,两手共一木也”者,于义是,以其拲字共下著手,又与梏共文,故知两手共一木,以桎与梏同在手则不可,故后郑不从。
按:《说文·手部》:“拲,两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声。”与郑玄说同。贾氏之所以断定先郑 “拲者,两手共一木也”之说“于义是”,是因为从字形看“拲”上“共”下“手”,会“两手共同之义”,而同时又与“梏”连文,又《说文·木部》:“梏,手械也。”由此可以确定“拲”为“两手共一木”的刑具。这里的判断实际上是依据了字形和语境两方面的标准,单从字形“从‘共’从‘手’”看并不能断定其为刑具,因与“桎”“梏”连用,所以可断定其为刑具。又结合“共手”的字形信息即可断定其为“两手共一木”的刑具。可见“因形定义”之“义”有时并非确定的语言意义,而只是一个大致的意义范畴,需要结合特定的语言环境才能确定其准确含义。又如:
⑤《周礼·大司徒》: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
郑玄注:忠,言以中心。
贾疏:“忠,言以中心”者,此以字解之,如心曰恕,如下从心。中心曰忠,中下从心。谓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
按:贾氏谓“此以字解之”即从字形释字义。这种做法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如《左传》中即有“止戈为武”的说法。此种析字方法的事实依据是汉字中“偏旁连读成语”的造字途径,如“任几为凭”“少力为劣”等。[2]135贾公彦对“忠”和“恕”的解释即继承了先秦的做法。马叙伦《六书疏证》中说:“贾谊书道术:‘爱利出中谓之忠。’以中释忠,乃以声训之例。而贾意出中为出心也,后人中心为忠之说,即由是附会矣。”[3]957可见贾公彦的说解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结果。
⑥《周礼·司救》:掌万民之衺恶过失而诛让之。
郑玄注:过失亦由衺恶酗醟好讼,若抽拔兵器,误以行伤害人丽于罪者。
贾疏:云“酗醟”者,孔注《尚书》云:“以酒为凶曰酗。”此据字酒旁为凶,是因酒为凶者也。
若然,醟者,榮下作酉,小人饮酒,一醉曰富,亦因酒为荣。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
按:贾氏比附孔颖达“以酒为凶曰酗”之说,认为“醟者,榮下作酉,小人饮酒,一醉曰富,亦因酒为荣”,将之认定为会意字,由字形以解字义。《说文·酉部》:“醟,䣱也。从酉,荧省声。”非如贾氏所说从“荣”,如此则“饮酒为荣”之说也就没了着落。此类现象正是为清代朴学家鄙薄之处,但贾氏通过分析会意字的结构来解释意义的思路和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因形求义作为一种训诂方法,其前提就是形义统一;而要自觉运用这种方法,就要认可汉字形义统一的特征。贾公彦在疏解经文和郑玄注解过程中都自觉运用了这种方法,虽然有些具体结论未必准确,但其对形体统一思想的贯彻是彻底的,在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以义定形
形义联系是双向的,在形体和其所表示的内容确立了稳定的联系之后,二者之间就建立了可以互相推知的机制,也就是根据形体可以推知意义,反过来,在意义已定的情况下也可以由此推定形体。这在贾公彦的注疏过程中也被广泛应用,且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表达程式,如“于义是”“于义合”“于义无取”“于义不可”等。
①《周礼·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与其用,使六宫之人共奉之。
郑玄注:齍读为粢。六齍,谓六穀:黍、稷、稻、粱、麦、苽。
贾疏:读齍为粢者,《尔雅·释草》:“粢,稷也。”粢字从米,以次为声,其齍字从皿,以齐为声,从皿不如从米,故读粢也。
按:汉字的意义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形体所取像的依据,称为“造义”,二是其所表示语词的意义,称为“实义”,不管哪一种都和形体有稳定的联系,因而都可作为确定形体的依据。 此例中,“六齍”为祭祀时所用六种谷物,依种类不同分别盛于不同器具内,如黍稷用簋,稻粱麦苽用簠等。许慎《说文·皿部》:“齍,黍稷在器以祀者。从皿,齐声。”郑玄读“齍”为“粢”,谓六穀“黍、稷、稻、粱、麦、苽”,孙诒让认为“盖许、郑二家说本不同”。以今天的眼光看,许慎和郑玄在观察同一个对象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反映到语言上就产生了两个近义词,这直接导致了相应字形的差异。许慎的解释着眼于“器”,所以字从“皿”,郑玄着眼于“实”,故字从“米”。贾公彦注经宗郑,遵循郑玄的思路,也从谷物名称的角度着眼,所以说“从皿不如从米”。将词义的区别特征和字形的构成部分对应,由词义而确定字形,这是以义定形的典型例子。将字和词明确区分开,贾氏当时未必有这样的明确的观念,但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却和今天的理论暗合,显示了贾公彦实事求是的作风以及客观规律对主观认识的制约作用。
②《周礼·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
郑玄注:展衣,以礼见王及宾客之服。字当为襢,襢之言亶,诚也。
贾疏:《礼记》作“襢”,《诗》及此文作“展”,皆是正文。郑必读从襢者,二字不同,必有一误,襢字衣旁为之,有衣义;且《尔雅》展亶虽同训为诚,展者言之诚,亶者行之诚,贵行贱言,襢字以亶为声,有行诚之义,故从襢也。
按:郑玄弃“展”从“襢”,是依据声义关系。我们知道形声字的声旁对整字的意义有示源功能,“亶”有诚义,所以“襢”也就有了这方面的含义。“王后六服”所穿着的场合和目的不同,各自体现一定的礼仪制度,不管在哪种场合心诚都是高尚的品质,“襢”本身含有“诚”义,以之作为衣服的名称体现了郑玄的崇礼思想。但据《尔雅》,“展”同样有“诚”义,是其本身的含义,表义更直接,不像“襢”要借助声符示源。这样郑玄的解释就显得说服力不足,为此贾公彦进一步申述,“展者言之诚,亶者行之诚,贵行贱言,襢字以亶为声,有行诚之义,故从襢也。”通过比较“展”和“亶”侧重点的差异,说明取“襢”更合理,又指出“襢”从“衣”,字形与六服之义联系更直接,根据字的意思,从声符和义符两个方面申述取“襢”的依据,体现了以义定形的传统汉字学思想。
③《周礼·肆师》:以岁时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郑玄注:故书“祈”为“幾”。杜子春读“幾”当为“祈”,“珥”为“饵”。玄谓“祈”当为“进禨”之“禨”,“珥”当为“衈”。 禨衈者,釁礼之事。
贾疏:云“故书祁为幾,杜子春读幾当为祁,珥为饵”者,皆义无所取,故郑不从之也。……云“珥当为衈”者,经言珥当是玉珥,非取血之义,故读从《杂记》下血旁为之也。
④《周礼·小子》: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
郑玄注:玄谓珥读为衈。祈或为刉。刉衈者,釁礼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谓始成其宫兆时也。《春官·肆师》“祈”或作“畿辅”。《秋官·士师职》曰:“凡刉珥则奉犬牲”,此刉衈正字与。
贾疏:刉从刀,衈从血,于义合,故以此为正字也。
按:由于汉字是据义构形的,其形体的构成部分分别对应所记录词义的某些区别特征,据此,在确知词义的前提下就可以推知形体的组成状况。判定的标准是形体所表示的意义信息是否适合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上述两则材料中经文所说“祈珥”是刲割牺牲、取血祭祀的环节,据《说文》“祈,求福也”“饵,粉饼也”,与经义不合,故贾氏谓“无义所取”,因为意义与语言环境不合,据以否定杜子春“读幾当为祁,珥为饵”的主张。而“刉从刀,衈从血”,正合刲割、取血之义,即贾氏所谓“于义合”,所以赞同郑玄的主张。这同样是以义定形的典型例子。又如:
⑤郑司农:“菁菹,韭菹”,郑大夫读茆为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读茆为卯。
郑玄:菁,蔓菁也。茆,凫葵也。
贾:“菁菹,韭菹”者,以菁为韭菁,于义不可,后郑不从。若为“菲”字,菲则蔓菁,于义为是。后郑不应破之,明本作韭,不作菲也。“郑大夫读茆为茅。茅菹,茅初生”者,茅草非人可食之物,不堪为菹。或曰茆,水草,后郑从之。“杜子春读茆为卯”,于义亦是。
按:此例据孙诒让等考证,行文有脱误,文义不连贯,不好判定是非,但贾氏解说中连用“于义不可”“于义为是”“于义亦是”,集中的体现了据以证形的思路和做法,故亦附于此以为旁证。
贾公彦是一位经学家,其注释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阐释经义,文字作为记录经义的载体,是首先要面对的对象,虽然对文字的形义关系有精细的分析,但其初衷却不在于总结汉字本身的规律,这是训诂学家的共有特征,也是传统小学的固有特征。但规律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其对形义关系的制约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作为严肃的研究者,贾公彦对文字现象的阐述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事实求是的。正因为如此,虽然没有明确的阐述,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操作规程实际上已经与形义统一的规律相合。也就是说汉字形义统一思想已经成为贾公彦的自觉认识,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只是还没有明确地将之表述出来而已。这正显示了唐代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平。
二、汉字职能思想
汉字本质上是一种交际工具,因此关于汉字使用情况的考察也是汉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古书注释面对的是书面语,以字为单位解释、分析意义,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其职能情况的辨析,只不过是以随文释义的方式分析个体现象。到唐代,这种认识更加自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总结。贾公彦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他对汉字职能分合的认识更加理性,对相关现象提出了理论解释,这在注疏二《礼》过程中有明确体现,主要包括同形异职和异形同职两个方面。
(一)同形异职
汉字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交际符号,其形体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变化,由此形成形体和音、义的复杂对应状况。梁代顾野王总结这种现象说“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4]1。对此自汉代以来学者就有清醒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了古书注解中“随文释义”的基本方法。顾野王的《玉篇》是这种方法的集大成,其基本体例是将不同典籍中的相关义项汇集到同一个字头下,所谓“总会众篇,以成一家之制”,如“讲”:
讲古项反。《论语》:“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也。”野王案:讲,谓谈论以解说训诰也。《左氏传》:“讲事不令。”杜预曰:“讲,谋也。”《国语》:“一时讲武”,贾逵曰:“讲,习也。”又曰:“仁者讲功。”贾逵曰:“讲犹论也。”《史记》:“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苏林曰:
“讲,和也。”《说文》:“和解也。”《广雅》:“讲,读也。”(原本《玉篇》残卷“言”部)
就上例来看,到顾野王时代,对汉字义项的认识和分析已非常深入,总结也很细致,但这仍属于现象的罗列,本质上还是“随文释义”,并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贾氏在“二礼疏”中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如:
①《周礼·大宗伯》:以丧礼哀死亡。
贾疏:诸经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经郑不解“亡”,则“亡”与“丧”为一,以其逃亡无可哀故也。
按:这里贾氏总结了“亡”的两个基本意义,即“逃亡”和“死亡”,从字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职能分化,而从词的角度看即是词义引申。这种做法往往需要进行不同语例的对比,如:
②《周礼·天官冢宰》: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注:胥读如谞,谓其有才知,为什长。
贾疏:《周礼》之内称“胥”者多,谓若大胥、小胥、胥师之类,虽不为什长,解是有才智之称。彼不读从“谞”,从此读可知。唯有追胥,胥是伺搏盗贼,非有才智也。
按:上例中,“胥”义为“有才智”,读为“谞”。此字在《周礼》可读为“偦”, “伺捕盗贼”之义。如《小司徒》:“以比追胥。”郑玄注“胥,伺捕盗贼也”,段玉裁云“此当云胥读为偦,而不言者,互见。”[5]778《士师》:“以比追胥之事。”郑玄注“胥读如宿偦之偦。偦谓司搏盗贼也。”可见“胥”字一形二用。这种现象在汉字发展史上常见,不同的意义共用了同一个字,后来又分别加注义符创造了各自的专用字。在未造出专用字以前,原字的意义只能靠语言环境显示出来。
有时候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同一个字可作两种理解,贾氏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如:
③《周礼·太宰》:八曰友,以任得民
郑玄注:友谓同井相合耦锄作者。《孟子》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贾疏:注云“合耦,使相佐助”者也。云“《孟子》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引《孟子》“乡田同井”者以证友是同井之友,但乡遂为沟洫,不为井田,而云乡田同井者,乡遂不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税,与井田同,故云同井。或解同井水,义亦通也。
按:“井”释为“井田”或“井水”都符合原文之意,故两存之。这也是职能分化的现象,只不过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两种意思恰好都讲得通。可见贾氏处理此类现象是从语言实际出发,并非都是主观臆断。
贾公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局限于单个字意义的解释,而是更进一步,对典籍中此种现象进行了理论的概括和归纳,提出了“望文为义”的概念,使汉字职能研究由现象的开掘进入的理论的归纳层面。如:
④《周礼·司市》:以量度成贾而征儥。
郑玄注:儥,买也。物有定价则买来者也。
贾疏:知儥为买者,以言征召买者,故以儥为买。此字所训不定。案:下文所云“贵儥者”,郑注:“贵卖之。”郑亦望文为义,故注不同也。
⑤《周礼·地官·胥师》:察其诈伪、饰行、儥慝者,而诛伐之。
郑玄注:饰行儥慝,谓使人行卖恶物于市,巧饰之,令欺诳买者。
贾疏:此经云“饰行儥慝”,明儥为卖,不得为买。上文每云賣儥,儥不得为卖,故为买,是郑望文为义,故不定也。
按:儥,徐铉《说文解字》释为“卖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释为“见也”。段玉裁等小学家认同徐锴的说解,认为“儥”为“覿”的本字,义为“见”,《周礼》中以“儥”用作“卖”,为形近致伪或声近通借,又可转训为“买”。郑玄注经对此已做了明确区分,贾公彦则归纳了此种区分的依据,即“望文为义”,也就是根据语言环境确定具体意义。此种解释,传统训诂学一般定性为“随文释义”,将之视为训诂理论的进步。如孙良明先生所说:“这本身反映了古代注释学在唐代的发展。汉代注释家进行了卓越的注释实践,但未提出什么释义原则和理论;而唐代注释家则明确的提了出来。”[6]14孙先生从训诂学的角度肯定了贾氏的理论创新。如果将语言和文字分开来看,所谓的“随文释义”应该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词在特定语境下的具体意义,二是汉字形体和语言音、义的对应关系,前者属于语言学范畴,后者属于文字学范畴。上述二例中“买”和“卖”不是一个意义的概括性和具体性的关系,而是两个不同的词义共用了一个字形。贾氏以“望文为义”概括这种现象,是对汉字同形异职现象的理论归纳。
与“望文为义”类似的说法还有“望经为注”“望经为义”等,如:
⑥《仪礼·士冠礼》:爵弁服,纁裳,纯衣,緇带,韎鞈。
郑玄注:纯衣,丝衣也。余衣皆用布,唯冕与爵弁服用丝耳。
贾疏:郑解纯字或为丝,或为色,两解不同者,皆望经为注。若色理明者,以丝解之;若丝理明者,以色解之。此经“玄衣”与“纁衣”相对,上玄下纁,色理自明,丝理不明,则以丝解之。《昏礼》“女次纯衣”,注云“丝衣”,以下文有“女从者毕袗玄”,色理自明,则亦丝理不明,故亦以丝理解之。
按:《说文·糸部》:“缁,帛黑色。”根据贾公彦的意见,“帛黑色”之正字为“䊷”,而“纯”是“䊷”的误字。此字的意义包含两个语义特征,即质地(丝织品)和颜色(黑色)。所谓“望经为注”就是据字所处经文的语言环境解释:如果语言环境能确定其质地,就解释其颜色;如果能确定其颜色,就解释其质地。从现在的眼光看来,这里区别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词义不同的区别特征,似乎不能算作同一个字记录不同的词“同形异职”现象,考虑到贾氏所处时代并没有明确的字、词之分,所以将之作为“同形异职”的例子。但这也表明贾公彦对汉字职能的认识还处在萌芽阶段,基于语言事实的感性认识成分较大,站在训诂学的角度解释词义的色彩明显,文字学的相关思想尚未从训诂学里独立出来。
(二)异形同职
汉字使用过程中由于同音假借、字形分化或词义引申等原因,造成不同的字之间会发生职能交叉,即不同的字形表示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在注疏二《礼》的过程中,贾公彦于此多有阐发。如:
①《周礼·校人》: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
郑玄注:马步,神为灾害马者。
贾疏:马神稱步,谓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类。“步”与“酺”字异,音义同。
按:《周礼·族师》 “春秋祭酺”,郑玄注云:“酺者,为人物烖害之神也。故书酺或为步,杜子春云:‘当为酺。’玄谓《校人职》又有‘冬祭马步’,则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与?人鬼之步与?”可见郑玄也不能确定“步”和“酺”哪一个为正。而贾公彦则指明二者“字异,音义同”,由此明确其异形同职关系。从文字学的普遍规律看,文字的功能是以形表音义,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字形和其所记录的音、义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为规约的。由于二者关系的确定是在社会中自发形成的,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规约方式,这就有可能造成同一个语词用不同的字形来表示的现象。贾氏对“步与“酺”关系的判断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又如:
②《仪礼·士虞礼》:举鱼、腊俎,俎释三个。
郑玄注:个犹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
贾疏:经中个人下竖,牵俗语名枚曰個者,人旁著固,字虽不同,音声相近,同是一个之义。
按:据考证“个”为“介”的变体分化字,[7]407用作数量词,《尚书·秦誓言》“如有一介臣”,或作“一个臣”。“個”即“箇”,义为竹干,《说文·竹部》:“箇,竹枚也。”引申为表单个的量词。“个”“個”义近,汉代的郑玄只是说它们音相近,意义上有间接关系,而贾公彦则明确说明它们“字虽不同,音声相近,同是一个之义”,确立了二者的异形同职关系。
③《周礼·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
郑注: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
贾疏:云“色如鞠尘”者,麴尘不为麴字者,古通用。
按:鞠衣,指浅黄色礼服。鞠,《说文·革部》:“蹋鞠也。”为古代一种游戏时所踢的足球,与衣义没有关系。“麴”本作“”,《说文·米部》:“酒母也。”,其上所生霉菌淡黄如尘,故称“尘”。孙诒让说:“ 鞠衣鞠为之借字,即《地官·叙官》注之麴”。[4]583从共时的角度看,本字和假借字之间就是通用的关系。贾公彦谓“古通用”也是概括了汉字形体之间的职能交替关系。又说“赊”“貰”通用、“胥”“须”古通,都是对此类现象的解说。
汉字在使用过程中会有意义引申和形体借用等现象,由此会造成原初形体和音义关系的脱离;同时其他的一些主客观因素也会破坏原来的形义联系,或建立新的形义联系,因此字形职能的变动很常见。传统的训诂学立足于意义的阐释,根据特定的语言环境确定某个字的意义,不能反映字形职能整体的发展演变情形。贾公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某些语言事实归纳出条例,提出判定字形职能关系的标准,将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从感性认知上升为理论总结,体现了在汉字职能问题上的进步,为后世对汉字职能的系统研究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三、汉字形体组构思想
汉字的物质形式可分为形体结构和功能结构两个层面。功能结构是指包含不同记言功能构件的构形模式,形体结构是指单纯的部件摆布方式。如“机”包含表义构件“木”和表音构件“几”,从功能结构看属于“义音结构”,从形体结构看属于“左右结构”。
以“六书”为代表的汉字结构理论关注功能结构,对形体结构基本未涉及。这与传统的汉字观有关,在传统文字学中,汉字被认为是“王政之本,经义之始”,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手段,因此关注的重点是其表示的意义和功能。而实际上,形体是汉字发挥作用所依赖的物质形式,是意义和功能的载体,其本身除了记录语言意外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融入了汉字创造者的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是汉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在汉字形体结构研究方面贾公彦是个先行者。他在利用“六书”理论分析汉字功能结构的过程中,开启了对汉字形体的组构状况分析。如:
①《周礼·秋官》: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郑注:玄谓蝈,今御所食蛙也。字从虫,国声也。
贾疏:云“字从虫,国声也”者,国与蝈为声,所谓左形右声也。
②《周礼·秋官》:硩簇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郑注:玄谓硩,古字从石,折声。
贾疏:“玄谓硩,古字从石折声。”者,以石投掷毁之,故古字从石,以折为声,是上声下形字也。
③《周礼·冬官》:凡攻木之工七……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郑注:故书“七”为“十”,“刮”作“捖”。郑司农云:“十”当为“七”, 捖摩之工谓玉工业。捖读为刮,其事亦是也。
贾疏:先郑云“捖读为刮”者,舌为声,刀为形,左声右形,刮摩之义,是故读从之也。
按:贾公彦分析汉字形体的初衷是阐明经义,在形声字来说,声符表示所记录词的语音,义符表示其所属的意义范畴,只要明确整字的声符和义符就能理解整字所记录语词的意义。贾氏对形声字形体构成的分析,立足点即在于此。他对形声字构成的考察不是个别的、零散的,而是做了系统的归纳,这在《周礼·保氏》中有系统的陈述:
但书有六体,形声实多,若江河之类,是左形右声;鸠鸽之类是右形左声。草藻之类,是上形下声。婆娑之类,是上声下形。围国之类,是外形内声。闤闠衡衔之类,是外形内声。此形声之等有六也。
如前所述,贾氏此种归纳的目的在于更好地阐释经义,但在客观上也归纳了汉字形体结构的三种基本类型,即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和包围结构,此后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一直遵循这个思路。
贾公彦之所以要明确区分形声字义符和声符的组合状况,其着眼点仍在于意义,主观上还是站在“六书”的立场,但客观上却对汉字的形体结构模式做了归纳。传统的“六书”主要着眼于汉字的功能结构,着眼点在以形索义,对字形各个构件的具体位置不大关注;而贾公彦根据义符和声符的位置的对形声字进行分类实际上是在做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工作。
当然,从汉字形体的研究来说,贾氏的归纳远算不上完备,首先他的出发点仍是字形的功能结构,并非有意识的分析汉字形体;其次他的归纳仅限于形声字,非形声字未涉及;再次,对于形声字形体结构方式的归纳也只限于事实的归纳,并没有任何动因、机制等深层次的分析。虽然如此,毕竟此前未有研究者进行过此类的工作,贾氏在汉字形体研究方面道夫先路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贾公彦汉字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地位
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史家罗宾斯所说:“每一代科学家都不是从头做起的,而是在他们的学科以及整个科学在他们的时代和他们的文化中所继承的成果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工作的。”[8]3这种事实决定了身处其中的研究者们工作的时代特点,这一点在贾公彦身上有很鲜明的体现。贾氏汉字思想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继承为主,间有创获。具体说是以继承郑玄以来的传统汉字学思想,对于郑说几乎是无条件的接受和遵从。其所作的主要工作就是申述、弥合郑玄的相关观点,而很少去分辨郑玄所说是否正确,这样就会产生郑玄的意见不合适,而贾氏仍不遗余力地阐释佐证的现象。另一方面,贾氏毕竟是“汉唐朴学”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实际注疏工作中践行实事求是的传统家法,这样在尊重材料、尊重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就可能得出和前辈学人不一样的结论,客观上超越或纠正郑玄,成为自己独有的创获,如对形声字结构类型的分离即是其一。这样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毕竟是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下一个阶段发展的萌芽和起步。
二是理论思考优于事实开掘。贾氏在注疏过程中的一些理性思考和操作方法在今天看来有可借鉴之处,而其对具体文字现象的说解却很多不甚高明,以致清孙诒让说“贾氏于小学尤疏,未足冯也”[4]678。之所以得到这样的评价,固然有贾公彦小学造诣方面的原因,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工作性质与指导思想也是重要因素。如前所述,贾氏疏证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疏不破注”,即无条件接受郑玄的解说,将之作为语言事实进行申述和解释,这实质就是寻找现象背后的联系和规律,所以理性思考成果较明显。同时囿于研究思路的限制,有时郑玄说错了,贾公彦仍要为之寻找理由,极力维护,这样就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不是贾氏一个人的问题,是当时此类工作的通病。梁启超评价孔颖达说:“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故遇有毛、郑冲突之处,便成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勉强牵合打完场,那疏便不成片段了。”[9]224-225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历史悠久,自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绵延不绝。不同时代的研究者都置身其中,在已有的条件下展开自己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各个时代的研究成果既是前代历史的继承,又是未来发展的源泉。对贾公彦汉字学思想的观察,也应坚持这样的眼光和标准。有唐一代在汉字学史上无开拓性贡献,少有开风气之先的名家和造诣卓绝的大师。身处其中的学者更多是以学术“传灯者”的身份出现,即将前人学术成就和学术传统薪火相传,延续下去。这对于学术传统而言,本身就是一种贡献,贾氏在汉字学史上的地位也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