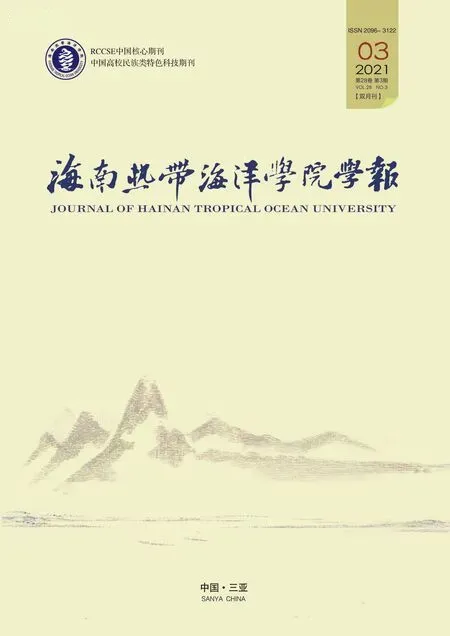《左传》的小说因素
霍建波,王 菲
(延安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夏志清先生曾说:“无论大陆的批评风尚如何,我以为有一点是不辩自明的,尽管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小说有许多特色,但这些特色唯有通过历史才能充分理解。”[1]的确,孕育在早期文、史、哲一体化场域里的中国文学,不管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它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意义上“小说”是舶来语,是20世纪后中国学者将西方对于文体的划分引入以对中国文学进行分类。但是任何文学的发生,都离不开本民族土壤的浸润,也自然而然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先秦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不仅孕育着我们民族的精神风貌,且对后世各类文学文体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史”的特征,与从先秦发展而来的史传文学有着密切的渊源。正如郭丹先生所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与史传文学有着更加深刻的血缘关系,史传文学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2]
《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3]。在《左传》中包含着许多后世小说的因素,影响着古典小说的创作。根据后世小说的概念,“小说是一种侧重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的文学样式”[4]171。除此之外,创作手法也常常被用来评判一部小说创作得成功与否。所以在本文中,笔者拟从人物、情节以及创作手法三方面来分析《左传》中的小说因素。
一、 鲜明的人物形象
《左传》在对历史事件进行记录时,还为我们刻画了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展现出各色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左氏春秋》写人物一千有余,约对四五百人的形象进行了详细的描摹,上自天子、王侯,下至役人、谋士、盗贼,囊括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其中有些人物个性鲜明富有特色,如郑庄公、齐桓公,管仲等,对后世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树立了典范。
首先,作者善于运用语言描写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语言是一个人思想、性格最直接的反映。如《左传》中第一位提到的鲁隐公,虽然只是代理国政,在位的时间也并不长,但是通过人物的寥寥数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位仁爱的君主形象。在隐公五年(前718),臧僖伯去世时,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5]51并且在原等级的丧仪上再加一等来安葬他。之前由于隐公想要前往棠地观看捕鱼,臧僖伯以其行为不合正轨而劝阻,但是隐公没有接受纳谏,执意前往;而今又提及旧事,可见隐公的悔过之心,至十一年(前712),羽父请求隐公杀掉鲁桓公,获得长久的统治权;然而面对王权的诱惑,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矣。”[5]93公当时年少,隐公代他执政,但是在位十一年,很难想象一个站在权力顶峰上的人却在等着桓公成年,然后将一切拱手相让。作者用简短的对话勾勒出了一位仁爱、善良、正直的隐公形象。
除此之外,作者写曹刿的勇气和智慧,郑庄公的阴狠有算计,曹共公的轻薄无聊,秦穆公的善于投机以及宫之奇的深谋远虑,宋襄公的徒有霸心而无霸谋等,都是借助人物的语言来体现性格,基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展开。作者对相关人物并无一评判之语,但是经过精心的语言建构,自会让读者观察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其次,作者还善用细节来描写人物。细节描写往往通过看似简单的行动,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形象,并对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可谓一举两得。如在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就有很多细节描写。在第三十六回,一天天气炎热,宝钗去往怡红院看望宝玉,恰巧宝玉睡着了。袭人因有事要外出,托宝钗在一旁照料。宝钗看到袭人未做好的肚兜,上面正在绣鸳鸯,也不知怎么的,就忍不住拿起来绣几针。而这一幕,又恰好被前来的黛玉看到。黛玉转身刚走,宝玉便在梦中呼喊道:“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6]听闻此话,宝钗放下手中针线活,不觉怔住了。这系列细节描写,很微妙地道出了宝黛钗三人的关系,对我们理解人物内心活动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左传》中也有许多细节描写,通过简单的细节动作来写人,无疑具有小说的特质。
例如发生在僖公三十二年(前628)的秦晋殽之战,晋国俘获了秦国的三员大将。但晋襄公却误听文嬴的话释放了三人。晋国老臣先轸知道后非常愤怒,当着君王的面“不顾而唾”[5]560。但实际上自己对此事耿耿于怀,在后来与狄人的战争中,说道:“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又“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5]563。这一系列描写,将一个刚正不阿、勇猛无惧、以死殉国的忠臣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其他如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崔杼弑齐庄公,晏子“枕尸股而哭”[5]1347又“三踊而出”[5]1347,体现出他的忠诚和刚正。桓公十年(前702)虞公向自己的兄弟虞叔索求宝玉、宝剑,所表现出的贪得无厌等都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来突出人物形象,使得人物性格更加鲜明富有特征。
二、 完整的故事情节
虽然《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作,至今学界有不一的看法;但是通过对比《春秋》与《左传》的文本,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左传》对于历史事件本身有着较为详细的描写。它不像《春秋》那样仅仅记载事情的发生,而是对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都做了翔实的介绍。在讲述历史事件时,非常注重情节的完整性,同时还运用生动的笔触,增强其故事性,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可以说“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7]。我们举两例来看:
隐公元年(前722)“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只用六字概括事情的发生,但《左传》却将事情发生的始由、经过、结果全部讲述了出来。春秋初期,伴随着诸侯间争霸的还有各国内部的钩心斗角。郑国在此时就发生了争权夺位的斗争,庄公之弟共叔段联合母亲姜氏想要篡夺王位。而姜氏对共叔段的偏爱则是从兄弟俩生时就开始的,因为“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5]7,但是却遭到郑武公的拒绝。在庄公即位后,姜氏依然处心积虑地为共叔段筹谋。而郑庄公在得知此事后,按兵不动,欲擒故纵,等待最佳时机,最终一举击灭共叔段的政变。全文叙述层次清晰,详略得当,将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僖公二十三年(前637)、二十四年(前636)“晋公子重耳之亡”,《春秋》对此并无记载,《左传》却用大量的篇幅来写重耳在外逃亡的经历。作者先用追叙的笔法,从重耳在蒲城之乱中不愿与君王对抗而选择逃亡讲起,然后讲述了重耳出奔狄国一直到最终回归晋国,一共19年的历史。一路上他饱尝艰辛,历经磨炼,最终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全文叙事脉络清晰有秩,在完整的故事情节中向我们展现了各色人物性格。重耳“过卫”“及齐”“及曹”“及宋”“及郑”“及楚”,逃亡路上经历的磨难不言而喻。从“公子怒、欲鞭之”“公子安之”“醒、以戈逐子犯”最初的这些任性举动,到后来对楚成王谨慎成熟的答复、对子犯赤城相待的言语、重新接见寺人披与头须等人可见,重耳已经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成长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霸主了。左丘明用高超娴熟的叙事技巧,将一个完整的故事线勾勒出来,向我们展现了晋文公的性格养成之路。
叶朗先生曾说“情节的本质就是人物的性格,情节不过是性格的运动而已”[8],可以看出,《左传》中的诸多故事情节确实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很好的突出作用,使得人物更丰满立体、有血有肉。但不仅仅如此,跌宕有序、高潮迭起、引人入胜的情节叙述也增加了《左传》的文学性,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这一模式与叙事文学的典范——小说不谋而合。
三、 多样化的创作手法
作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左传》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体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钱锺书就曾评论《左传》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摹,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为过也。”[9]可见,《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创作技巧,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渗透在古典小说创作的始末。
(一)虚实结合
作为“史”与“文”的出色结合,《左传》在秉持“实录”原则的基础上,又常常记录一些神怪之事,烘托主题,让读者置身于文本环境中,体验审美情境。
首先是将神话怪异之事与梦联系起来,一同呈现在人们面前。如成公十年(前581):
晋侯梦大历,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5]957
事件的前因是成公八年(前584)时,晋景公枉杀了赵同和赵括,大概一直有愧于心,于是梦中见二人变为厉鬼向自己讨命。景公因此得了心病,不久果然如巫史所言未能等到新麦成熟而死。这样奇异的事情还有许多,如宣公四年写楚令尹子文的诞生,也颇有神话色彩;城濮之战,晋文公战前之梦、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等。虽然这些奇异之事与原始先民们的巫术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也与作者欲借事件传达某种道德意识紧密联系;但不可置否,他们都为《左传》的环境描写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使得文本极具艺术魅力。
其次是对于密闭空间内人物言行的想象。按正常逻辑,在密闭空间内,人物的言行是不可能被旁人知晓的,更别提被史官记录了;在《左传》中,我们却发现作者仿佛无所不知。宣公二年,晋灵公派鉏麑去刺杀屡次向自己进谏的赵盾。鉏麑来到赵家,见天色尚早,但是赵盾却已然端坐在厅内等待上朝。见此情景,鉏麑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5]736这一段鉏麑死前的心理独白,当然是作者虚构而来。却显得合情合理,对于人物形象也起着烘托作用,为故事增添了几分文学色彩。
《左传》虚实结合的手法,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一方面,它决定了古典小说‘史’的特征。后世小说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往往以史切入,尽可能地赋予人物一个相对真实的成长空间。比如历史演义小说,假托时间与空间,生出一段传奇故事来;又比如通俗话本,在开始时也常常是“话说明成化年间”“陕西省大同府长安县”之语,以此揭开一个个故事。另一方面,如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以及明清神魔小说,不但从《左传》中提取大量素材,而且也常常以虚笔入文,写神奇古怪之事,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具有代表性的如《东周列国志》《吴越春秋》《搜神记》《聊斋志异》等。
(二)巧用修辞
惯用比喻、夸张与对比的修辞手法,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特征。在《左传》的行文中也包含着许多这样的手法,使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故事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左传》中最引人注意的修辞手法便是比喻。如隐公四年(前718)“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5]39,文公七年(前620)“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5]626;再如宣公十二年(前597)楚王抚三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5]825等,都是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以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中内容所表达的意义。
“夸张是运用想象与变形,夸大事物的某些特征,写出不寻常之语。”[4]296在《左传》中,也多次用到夸张手法。如宣公十二年(前597),“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5]813;定公四年(前505),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5]21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对“勺饮不入口七日”的解释为“此言或太过,以生理言之,七日不饮水,不能生存。”[10]从修辞学的角度言之,这种表达是为了极言申包胥请求得到秦国帮助的决心,也属于夸张手法。
对比的手法在《左传》中使用较多。如宣公三年(前606)“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5]744,说明持鼎者的德行其实比鼎本身的大小更为重要。再如庄公十年(前684),曹刿论战时将自己与“肉食者”之类作对比,得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5]213的结论,对比之中突出曹刿的勇敢与自信。僖公十五年(前645),阴饴甥对秦穆公所言“小人戚,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5]410。作者运对比的手法,两相对照之中展现了“君子”与“小人”完全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含蓄的风格和反讽的意味。
(三)零聚焦叙述
通常,我们在阅读某一个文本时,常常会注意作者是从哪一视角来记录或者讲述事件的。所谓“视角”,即是“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1]19。法国学者热奈特将视角分为三种,分别是“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他认为“零聚焦”就是叙事者“从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的叙述”“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4]272。从先秦发展而来的史传传统,要求史官本着实录的原则,以冷静、客观、超然事外的态度对历史进行记录。因此中国的史传文学多采用这种“零聚焦”的叙述视角,由《左传》开辟出来的这种叙述方式被后世沿用。古典小说在讲述故事时,往往就采用这种“零聚焦”的视角,讲述者多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观照着整个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与行动,并且紧跟故事的发生向读者讲述一切。唐僧师徒去往西天取经过程中经历的各种艰难险阻、三国风云中激动人心的战事描写、水浒英雄们的行侠仗义以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起落,其作者都是采用这种“零聚焦”的叙述视角,将故事娓娓道来的。
除了视角之外,《左传》还出现了非叙事性话语,即“叙事者对故事的理解和评价”[11]103。开辟了古典小说的第三人称评点式话语模式——“君子曰”。在《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完全是冷静的,有时候他也会忍不住做出有感情色彩的评价,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是假托“君子”,但君子象征着品德高尚美好的人,其所言自然存有大义,对后世有启发意义。如隐公元年(前722),在“郑伯克段于鄢”故事结束后,就有“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5]14这样一段话。作者通过公开式评论,对事件做了评判与总结,同时又让人注意到叙述者的存在。这种笔法,在《聊斋志异》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蒲松龄也常在故事结束,有一段“异史氏曰”,让人注意到叙述者的声音,点明故事道理,堪为点睛之笔。
当然,《左传》的创作技巧远远不止以上三个方面,其他诸如使用插叙、补叙、预叙手法叙述历史,使用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运用“春秋笔法”进行道德劝善,借助民间传说强化故事情节以及颇富戏剧性的情节嵌入等,都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结 语
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叙述以及创作手法三个方面,作为先秦叙事文学代表的《左传》与古典小说有着非常复杂的渊源关系,它不仅开辟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也在行文叙事等方面奠定了古典小说的雏形,使得古典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史传文学的因子。正像胡适先生在其著作《白话文学史》中所说的中国文学有两条发展线,“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12]。长期以来,小说不被纳入正统文学的范畴,一直被划在民间文学里,但这条线是富有生机的一条线。沿波讨源,我们便可以发现,其实在早期的正统文学中便蕴含着俗文学的因子,不仅《左传》如此,之后的另外一部鸿篇巨制《史记》也是如此。因此,关注史传文学中的小说因素,以全方位、多融合的角度考察不同文体间的相通之处,在现代学术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