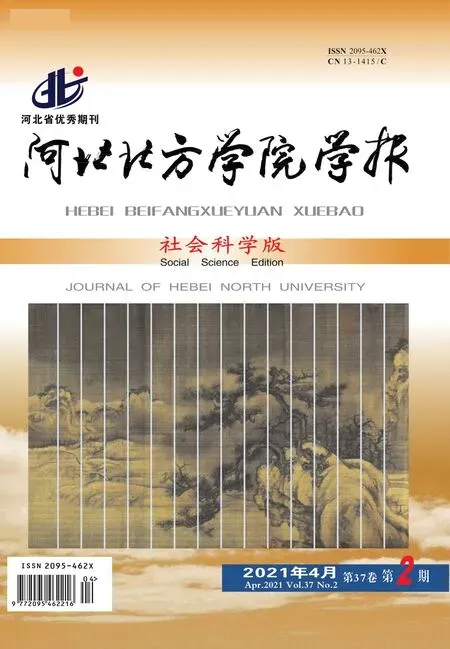现代性视野下的城市书写
——小说《炸裂志》的主体性问题探析
贾 彬
(重庆工程学院 通识学院,重庆 400056)
现代性虽含义繁复,但其所指代的时间和价值层面的渴求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性话语与秩序在学术层面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识。近代以来,中国在一种“前现代”的境遇中不断地生发出存在的焦虑。生存的危机一度决定着历史走向,所谓“救亡压倒启蒙”[1]在一定意义上符合现实的逻辑。当“生存”的“当务之急”[2]解决后,面临的应是“温饱”问题。但在“现代性”威逼的焦虑下,“发展”问题不断逾越“温饱”问题。甚至,人们无条件地相信发展的力量。“现代性”的利好也反复得到事实的佐证和强化,但“现代性”的后果却像一条细细的隐线,埋伏在畸形城市崛起的炫目光景之下。在这场独到的现代性追求中,内在于人心的精神陷落以及现代性所导致的某种危机成为人们始料未及的附加品,更成为社会发展的代价和阵痛。阎连科的《炸裂志》是一次带有批判意味的书写,也使人们在字里行间读出其心灵的纠结隐痛:在现代文明观念没有内化在心之时,超出现代性的后果已经悄然而至,人们在未老先衰的现代社会里挣扎破碎,并承受着这场内部危机的病痛。
一、生存境遇的危机
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社会,城乡市镇都是人们的聚居地。因此,城乡的变化便意味着社会的变化。恒久而稳定的农耕生活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存方式,当这种生存方式被追逐现代社会的节奏打破后,人们的生存境遇也随之被改变。小说《炸裂志》中,千百年来的农耕发展并没有改变自然村的面貌和环境。因此,作者对“炸裂”作为自然村从宋代到民国这一如此大的历史跨度的叙述仅占全书的1页篇幅。“炸裂市”的历史之所以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变得更加详细,这不能不说城乡的变化有着“现代性”的象征意义,即“现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据几乎完全不同于旧有的将前现代的城市从早期的乡村中分离出来的原则确立的”[3]。然而,书中的“炸裂市”并不遵循这样的原则,因为城市的形成并没有脱离“村”的根本性质。“炸裂市”的不同就在于其对现代城市发展路径的背离,它并没有从早期的乡村中脱离出来蜕变成文明的现代城市,而是从之前的“自然村”变成了后来的“社会村”。因此,属于“现代性”生存境遇层面的危机便开始了。如果“社会村”的产生意味着与传统“自然村”的迥异,那么它们之间还应有颇为不同的历史意涵。“炸裂市”从北宋开始出现,那正喻示着城镇初发的萌芽,但经过宋元明清再到民国,无论是依山傍水的久居为安,还是战乱兵燹的民不聊生,都不能改变自然主导天地人的大势。因为循规蹈矩的变化更多地是简单地求诸于自然,回馈于自然。资源的发现与交通的发达才是“炸裂”的开始,“民国中期,因邻县发现特大煤矿,有铁路延伸而来,在二十里外设下车站,这儿便弃静奔繁,物流便利,自然村落逐渐失去而成为社会村落之组成”[4]10。从此,人们便开始主导自然的进程,人的蛮力逐渐把城乡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村子的变化由“孔老二”①明亮当上村长开始,而明亮当上村长又是从全村做的同一个梦开始。这个梦便是人们醒来后随便先看到什么,以后的命运便随着看到的东西而被决定了[4]21。也许这里喻含着当时人们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尝试,只要一心向“梦”,便就能在某一方面“大展宏图”,这是“投机者”的胜利,也是“敢为时代先者”的舞台。因此,“火车扒煤致富”的新闻成为阎连科笔下自然村变革的转机,“有雄心的老二”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引领村民致富的重任。而尤为明显的是,在村子经过了“炸裂”式发展之后,人心似乎变得更加叵测,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变得更加复杂。在更多的改革利好所带来的喜悦中,往往潜伏着思想的博弈与暗战。传统心理与现代畅想的某种交错混乱成为新“炸裂市”一场场闹剧的“草灰蛇线”。由村变镇,由镇变县,由县改市,由市再到超级大都市,从中可以看到“乡村”的无限膨胀,而由此带来的城市裂变也一步步地纵容着人们的贪婪。一方面,人们急于享受发展带来的欲望满足,如孔家的父亲孔东德甚至死在妓女的身上;另一方面,人们却忘记了既往的风俗传统,如人们常常忘记哭坟的传统习俗。在这样悖论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明争暗斗都在为城市的变迁提供着某种具有“原罪感”的动力源。的确,城市的发展让人们摆脱了物质贫困,但不计代价的发展也让人们失去了质朴之心。因为城市的超节奏生活永无止歇,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城市更进一步的扩容和炸裂,这是一个无法停步的漩涡,裹挟着每个人都卷入了欲望的试验场,或沉默或聒噪地承受着现代之神的刻意嘲笑,而内在的自省和更具精神向度的生活在城市不断发展的大势中被有意无意地蔑视。
在“城市”对乡村的反叛中,乡村丢失了,连带着血缘家族的维系关系也被城市发展的洪潮淹没了。人们之间变得陌生而木讷,“疏于省亲,到现在,似乎有些想不起哥哥长的怎么样,名字叫什么”[4]233。内心的安谧被市声的喧嚣吵得焦虑不堪,送礼的礼品甚至使院里的“榆树”都夸张到有了烟瘾的地步。当老四明辉不堪送礼的搅扰而拒收礼品时,当“这个局长有车不坐,偏要步行上下班”[4]271时,“炸裂人”把这样的乡村憨人当成“精神病人”也就再正常不过了。由此,乡村的宁静成为一种历史的回响。相应地,城市在这样畸形的发展中快速陷落了。小说最后,“天空中布满了炸裂从来没见过的黑雾霾,大白天三五几米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在那雾霾中,所有的鸟雀如凤凰、孔雀、鸽子和黄鹂等,都被雾霾毒死了,而人在那雾霾中,个个都咳成了肺病、哮喘病。当几十年不散的雾霾散去后,炸裂再也没有鸟雀、昆虫了”[4]371。可以讲,这是外部生存环境遭遇的危机。但之后的一段叙述——“但那些活着的人们看见几十年前他们跪着走过的路面上,那些跪出的膝血和泪水打湿的泥,等日光落在那些血渍和泥浆上,又生出艳丽的牡丹、芍药、玫瑰来。而孔家跪流过的血路上,几十年后不光开出了各样的花,还又长出了各品各样的树”[4]371,便是作者对生存境遇的彻底哀悼。那些血泪是人们在艰难时世下为了发展所付出的沉痛代价,是城乡里最后一抹属于“人”的带有悲剧意味的生存痕迹。那些用鲜血所浇灌出的花朵和树,仿佛象征着人们奋力追求却未能实现的理想,美好而虚幻。它们置留在孔家跪流过的血路上,执拗地召唤着城乡早已逝去的灵魂。
二、表征自我的危机
超越一般经验的现实巨变让人们开始疯狂地欣赏自己的创造力,而忘却本应具有的现实警觉。“就这么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队伍着,从矿业总公司的门前朝西正步走,到了一栋盖了几年不知何故没有盖起的楼前停下来,吹一阵,又集体朝那垮塌的脚手架和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楼前停下来,吹一阵,又集体朝那垮塌的水泥烂楼的正面吹了军乐,再带上十二个方阵队伍绕着那烂楼走一圈,那些脚手架也就不见了,露在天空锈蚀的钢筋也都没有了,几年没有竣工的烂楼在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里,不仅竣工完成,而且还都装修成了城里最时新的意大利的瓷片砖。”[4]238这种现实的疯狂变换不仅使小说中的人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表述危机,更使作家自己面临着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的危机。毋庸讳言,用“地方志”的形式来书写“炸裂市”的发展史,是一个讨巧的选择。阎连科在一次签书会上明确表示,这部小说是他很长时间以来想对社会巨变作出的一次文本阐释,但苦于形式的思考而未动笔,后来想到“地方志”才认为是找到了最为贴切的表现形式。作者的创作犹疑足以说明,在现有的生存经验范围之内,小说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受到现实巨变的某种挑战和反驳。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殊难表达一种剧烈的震荡,而且“影响的焦虑”时时成为困扰小说家的无形力量。
但就《炸裂志》这部作品而言,尤其作者在对结构的设置与内容的处理上,小说形式更像是一个虚设的框架,用来框定“时代巨变”这样一个宏大的主题,而在根本的情节、人物与环境等方面的表现却不能不说少有突破。某种意义上,作家选用“地方志”的形式来写小说,既突破了旧有的写作陈规,也找到了较为贴切的传达其内在精神的写作路径。但一定程度上,作者却没有逃脱传统小说的写作限制。也就是说,一种唐突的且先入为主的形式观并没有对小说叙述形成有效的规约和写作自觉。这种不像地方志的“地方志”与其说是形式的创新,不如说是理念的嫁接和盲目的嵌套,这也是小说本身的噱头大于实质意义的原因,因为全书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地方志”式的写作肌理。显然,这更像是一种表征自我的慌乱和危机。表征自我的危机也并非仅在于写作主体对小说形式的选择层面,更在于其对理念的运用和语言的组织,表现在《炸裂志》中便是阎连科对具有特色的“神实主义”写法的着重强调和有意运用。赫尔曼·布洛赫有言,“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5]。在阎连科的想象里,小说知识的确立是一种心理真实的书写,是运用心理的真实来推动现实的真实变化,这表现在小说的叙述上即为神实主义。利奥塔在质疑话语元叙述时认为,所有的“关于知识‘真实性诉求’的标准都来自于分离的、语境决定的‘语言游戏’,而不是绝对的规则或标准”[6]。在阎连科对现实真实的指涉上,并非是出于元叙述的垮塌前提和对图像世界的忽略,而是基于心理真实的一次书写。在此种意义上,它不仅没有很好地推动现实,反而造成了对现实的疏离。这种语言的运用通篇皆是,第一次发生在程菁听明亮说她哥的坟头草变成了花,“她穿好衣服,重又往着村里、家里去,重又来到十字路口上,看见哥哥的坟上原来枯干的草,果然全都开了花,盘飞了很多蜜蜂,蝴蝶和啁啁啾啾黄鹂鸟”[4]43。这就是人物心理的真实,即心理上相信现实的力量可以撼动某些情感而造成感觉的位移。枯干的草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马上变成花的,但在心理真实上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小说语言甚至连情节发展都是为了心理真实而服务的。但必须注意到,当语言脱离其本身语词的含义而成为另一种指涉的意义时,语言就产生异化,造成了无关语词本身意义的游离。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语词本身就具有(分异)延异[7],而《炸裂志》里不断的变化和隐喻又强化了语言的这种延异,能指和所指丝毫不相干,“红的灯发出绿的光”和“牡丹上开菊花”等指向的并不是事物的本身。换言之,小说语言所表达的含义并不和这些物件发生直接的意义关联,而在于语言的暗示层面,即隐喻和象征以及夸张化的效果才是叙述的真正意义。语言的效力在达成这些效果之时,也正是作者流于符号化的叙述之时,这种符号化的串联让所有的事物变得模糊而不再明确,一旦书写的笔触落入具体的事物时便被这种符号化的叙述所搅扰,“你不是你,他不是他”,便构成了深刻的语言危机。此外,符号化写作本身意义的效力变化所带来的遗憾更为显著。这体现在当通篇语言充满现实的魔力时,语言的意义也会随着这样的习惯使读者不再惊异于这种匪夷所思的表述,而对于指示意义的表达也会相应地被稀释,现实化的寓言的启示意义和现代的悲剧性就得到了语言的拆解,进而使作者的写作愿望遭遇到自己语言的反驳。这不是一个震撼人心的悲愤叙事,而更像一场荒诞的闹剧。在小说的意义层面,语言的利弊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进而局限了小说本身的价值。
话语的运用除了作者的叙述语言以外,还有作者构造的对话语言,这也是小说《炸裂志》颇具特色之处。从村改镇后,人们的对话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先前人们的沟通是无障碍的,那么村改镇后人们的对话都变成了自说自话的答非所问。如新晋升为镇长的孔明亮视察山梁时和随从人员的一段对话:
“炸裂发展好快啊!”镇长感叹着。
“他们哭他们没有地种了。”随着的答。
“全镇一共有多少户人家住别墅?”
“都哭闹整整三天三夜了。”[4]121
虽然对话语言是小说人物陈述各自想法的专属工具,却不能再承担语言的交流意义。至此,语言的危机已不仅是语言本身的危机,其背后是说话者的精神危机。对说话者而言,已无意去听取他人的任何信息。每个个体关注的其实是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是否能够获得与实现。这是一场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下撕扯出来的分裂的主体性的危机。
三、主体性的危机
生存境遇的变化及语言世界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人自身的变化。现代性发展的旨归应是康德所讲的“决不把人这个主体单纯用作手段,若非同时把它用作目的”[8]。然而,“炸裂人”却被城市的发展所挟持,沦为城市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首先,“炸裂市”本身就是一种伪饰的现代社会。从“乡长当场宣布了撤去老村长朱庆方的职,让年轻的孔明亮做了炸裂村变革元年的新村长”[4]24开始,再到民主选举的冠冕堂皇,从中看不到任何属于现代社会的法治与民主观念。“炸裂市”为了城市的发展,不计任何代价,也不遵守任何现代秩序,更没有考虑到人自身的发展。其次,城市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都是靠纵容而非限制人的欲望实现的。小说中对人的权力、金钱以及美色等欲望的描画俯拾皆是。在“现代社会”的外衣之下,暗藏的是无法登上台面的“男盗女娼”式的欲望,这些“欲望”恰恰是主宰社会的核心力量,是推动“炸裂市”发展的源动力。从村民一同在火车上扒煤开始,就开启了“炸裂市”奔向现代社会的步伐,而无论是村改镇、镇改县以及县改市,都少不了各种欲望的叠加作用。
权欲从根本上决定着孔明亮的行为,他的自说自话正是其真实欲望的表达。每个人的话语都代表着自身的一种欲望,而个体欲望又是互相排斥的,故而造成了彼此之间的隔膜和沟通的不顺畅。诚然,每个人的欲望并非是单一的。孔明亮心中除了权欲外,还有其他欲望的纠缠。而主导着现实世界发展的往往是个体更强烈的欲望。孔明亮的权欲似乎可以撼动任何现实,但面临更强烈的性欲时,权欲就暂时不起作用了。当明亮把村改镇的文件在各种物事上晃一晃时,每一种物事都发生了超越现实的变化。可以讲,这是权力对现实的有效更改。但当文件把程菁的衣服晃光以后,文件便暂时不具备现实的效力了。“他不知道她这样是为了他还是为了那文件,就想把文件再在她身上抚过去,看事情会有怎样的变端和幻异。然却不行了,他不能管控自己了。在她的裸体前,他忽然浑身哆嗦,文件从手里滑出去,飘在了地面上。”[4]108当性欲得到了宣泄,现实紧接着又会回到欲望之前的所欲状态,这种所欲状态还表现在对周遭的物象描述上,“‘天!大冬天泡桐开花了,刚才还是满树枯枝呢’”[4]110。欲望暂时的停止并不意味着欲望的结束,而是喻示着下一欲望的到来,欲望的交替让原罪的动力源永不止歇。
在小说里,这样的情节设置是十分自觉的。对他人欲望的满足往往成为交易,如朱颖以不断满足别人欲望的方式来获取自己利益的满足。但这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奏效,当两个个体所代表的欲望相遇时,哪种欲望能够占据上风则取决于哪个个体的欲望更强。朱颖找到孔明耀,拿粉香作为筹码,想让他把程菁和孔明亮拆开,但明耀的民族情结一直左右着他,成为主导他的潜在心理,“——‘大使馆都被美国炸掉了,如果这时候我还想着你和粉香和程菁们那儿女情长的事,我就白白当了这么多年兵’”[4]231。由此可见,明耀的民族情结是一种渴求现代的欲望。当朱颖的欲望与这种更高层次的欲望短暂碰撞时,欲望之间便起了冲突,交易也就不能够顺利达成。当欲望主体之间互不让步,现实便会发生悲剧。这样的现实逻辑无限推衍下去,就只有在遭遇死亡时才能得到止歇,最终酿成一幕更大更彻底的悲剧。如结尾处孔市长最终被人刺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有一把并无什么特殊的匕首从他的后背刺进去,从他的前胸又露出一个指甲样的匕首尖”[4]367。在这场无限的“炸裂”运动中,没有永久的受益人,只有悲剧的承载者。这种悲剧从一开始就被注定,当合作化剥夺了民众土地的那一刻,人就已经成了城市发展的手段,主体性的危机便开始显露。个体所依赖和认同的生活由此丧失,“孔市长的爷爷坐在田头号啕大哭,三天三夜,哭声不止,引来了几乎各户土地的主人——村民们都到田头为失去土地而哭泣”[4]11,“然炸裂之‘哭俗’,也就源此而初成”[4]11。显然,这哭俗并非是多么久远的可贵习俗,而是现代的一曲哀歌,在烟云雾罩的炸裂社会里更成为个体的有限表达,代表着仅有的一丝真实悲欢。当“炸裂市”成为现代的废墟时,作者用了一个微妙的时间隐喻,一个城市就这样被坏钟坏表淹没了,“现代停滞了”,没有人知道未来在哪里。小说最后是一副末日的景象,几代人充满着惶惑与遗憾,“也就在这天的黄昏间,留在炸裂的老人们,他们想起他们几十年没有去坟上诉说他们的欢乐苦难了。就有人在日落月升时,哭着朝自己的坟地走过去……东区和西区,都呜咽泱泱,连天扯地,一个世界都是诉说苦难的眼泪了”[4]370。
在城市的现代化征程中,“现代性”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姿态,也具有无与伦比的阐释力。然而,在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中,“炸裂市”是违反现代秩序的畸形城市,这不免给“现代性”的合理性带来了根本挑战。其具体的表现在于,不同欲望纠葛下的“男盗女娼”成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并表现出不同层面的深刻危机,其中包括由牺牲自然环境换来的城市发展所导致的生存境遇的危机、由追求个体欲望带来的自我表征危机以及个体沦为了手段而非最终目的的主体性陷落危机等。这些构成了一部以呈现现代性危机为核心的叙事小说,也为反思城市发展的弊端和现代性的消极后果提供了很好的文本阐释。
注 释:
① 孔子也曾被戏称为“孔老二”,小说此处的“孔老二”似乎在有意地进行调侃。传统社会的“孔老二”是精神文明的象征,而小说中带领村民致富的“孔老二”似乎是物质文明的象征。另外,除了“炸裂市”的第一大姓是孔姓外,第二大姓和第三大姓分别是朱姓和程姓,应该是对程朱理学的调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