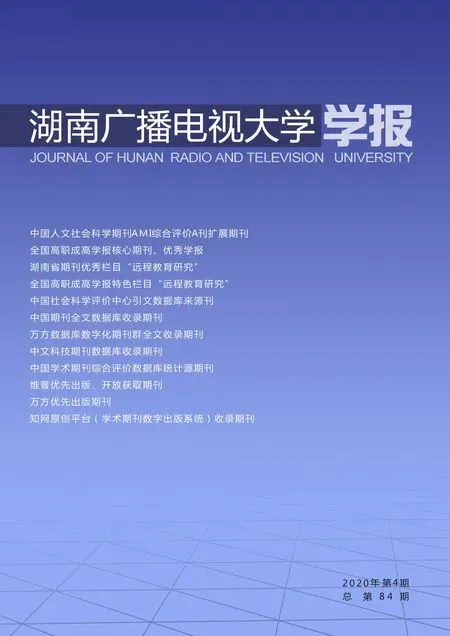人神恋歌:《九歌》祭祀主题的心理诠释
冒婉莹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241)
学界目前并未对《九歌》的祭祀性质达成共识:多数学者以王逸为准,认为《九歌》是屈原被放逐沅湘时的抒怀之作;闻一多、汤炳正等人认为《九歌》是屈原为宫廷所作的祭祀乐歌;姜亮夫等人认为《九歌》乃屈原对楚地民间祭歌的雅正之作。本文对以上争论存而不辨,立论则采用《九歌》是屈原改作的楚地祭祀乐歌之说。鉴于祭祀活动是人神关系集中展现的载体,本文试图从文本分析入手,对《九歌》中所展现的楚地先民祭祀活动的心理进行诠释,以期一探先民人神关系中的巫文化基因。需要说明的是,《楚辞》的版本流传情况复杂,但本文是针对《九歌》祭祀主题的心理诠释,相关论述以林家骊校注、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版本为蓝本,而不涉及不同版本之间的考据与比较。
一、相遇——神至人亦来
《九歌》所反映的楚地祭祀活动以迎神为开端。万物有灵观念是祭祀活动得以开展的心理基础,人与神的相遇相通是人神圆融一体的象征。楚地先民之神类似于人,“凡楚之神,在男则庄肃敬穆,在女则轻盈缥缈,与人世之生活性习相调遂,而非剑拔弩张,面目狰狞”[1]。《九歌》所咏乃是先民在交感巫术中与天神、地祇、人鬼间的心心相惜之情。
(一)万物有灵观念下的人神交融
自然界有其运行规律,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般的温和与狂风肆虐、惊涛骇浪式的凶恶都是它的模样。先民通过对世界的变幻无常与人的喜怒哀乐进行类比后,形成万物有灵的观念,这种观念成为先民神话思维及祭祀行为的心理基础。万物有灵观念是人类体察自然的窗口,它形塑了神灵的样态,慈悲的、善良的、易怒的、狂暴的等各色有形有性的神灵接连登场。《九歌》中的神灵就被塑造得形态各异。
当人将个性化的情感与性格赋予神灵时,无疑是以人为认识本位的,因此万物有灵心理的外化即是为神赋形赋性的行为。对比《大司命》与《少司命》,可以明显感知二者的不同。大司命是掌管夭寿、生死之神,与死亡、毁灭这些无法抵抗的命运相联系的神自然被塑造得庄重、冷酷,仿佛一位杀伐果决的判官。在《大司命》的描述中,他在萧瑟而阴郁的天气中降临,冰冷的暴雨为他除尘开路,漫天的乌云是他的坐骑:“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氵东雨兮洒尘。”[2]56即使凡尘中痴情的姑娘也不能将他挽留,他决然离去:“吾与君兮斋速,导帝之兮九坑。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2]57-58临走也不忘严肃地告诫人们生死离合自有天定:“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2]58大司命何其绝情,何其冷酷!但是当画面转移到掌管生育、子嗣的少司命时,又是另一番景象。她一手执长剑一手抱婴孩:“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2]62她温柔善良,宛如一位勇敢的母亲,时刻心系人间子嗣:“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菲兮袭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2]60她对人间之情更是深有感触:“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2]61她是如此令人倾慕与爱戴。生命的诞生与结束是先民无法理解的秘密,他们只能以最直观的方式表达对变幻莫测的生息运行之道的崇尚与敬畏。
显然,加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密联系,才能更好地消除人与自然的冲突,先民为自然神赋形赋性则是力求与自然本身圆融一体。万物有灵观念下所信仰的自然神在被具象化后,终于回归信仰发生的初衷——人对人本身的关切。祭祀活动是呈现这种具象的最佳时机:一方面,祭祀目标是降神祈福,当诵祷对象被形象化和人格化后,能够使人从心理上更加认同祭祀行为的可靠性;另一方面,祭祀氛围能够强化人对神的感知。当那些原生态的、真实的生活记忆片段以夸张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时,先民无疑会更加确认神的世界,荣格将其描述为“原始意向的世界”[3]100,它既是真实的又是幻想的。祭祀活动总是试图创设相似的原生态生活情境,促使人神相通的观念成为先民心理的认知常量。
(二)交感巫术中的人神离合体验
先民在祭祀活动中感受到神的世界,实际上是在交感巫术之下潜意识的自我沉浸与认同体验。弗雷泽曾以先民对性行为与农作物丰产之间关系的认识为例[4]372,说明人极易在祭祀这种交感巫术实践中获得人神离合的奇妙感受。《九歌》所述祭祀活动首先是迎神,以交感思维降神是祭祀活动的重要手段。站在人本位的角度想神之所想,事神如事人。在《东皇太一》中描述的迎神仪式如同在现实中迎接贵客一般。虽然在该篇中神灵并未现身,但迎神仪式却丝毫不能马虎,要择良辰:“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缪锵鸣兮琳琅。”[2]37要备美酒佳肴:“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2]38还要安排歌舞鼓乐:“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2]39这样的场景不禁使人产生人神共愉的自信与强烈的自我认同感。除了代入人对物的欲望的共情理解,情爱之思也是《九歌》中先民以自身经验推演出来的主要的迎神方式。两性关系与生息社稷有着天然的联系,闻一多就曾言,以女巫媚男神和以男巫媚女神确乎是十足的代表着以生殖技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礼俗[5]。

和物欲的代入感相比,先民与湘君、湘夫人的情感交感更具感染性。在一曲神的恋歌中,先民体验着爱恨离合的错综——恍兮神兮,惚兮人兮,化万物为灵乃是人对世界深深眷恋之情的体现。“有灵观的核心,实在是根据人性所有的根深蒂固的情感这个事实的,实在是根据生之欲求的。”[6]
二、共生——祭典即情境
迎神之后,祭祀活动进入飨神阶段。《九歌》中的飨神既表现为人神同形,巫者在神、巫、人的不同角色中穿梭,又表现为人神共舞,由巫者带领,先民仿佛与神一同在迷幻的时空中遨游。对于先民来说,想象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边界是如此模糊,在祭祀中对具有超越性的错乱身份的理解和对迷幻时空转换的呈现,使那些关于神、神迹以及神境的潜意识内容复苏于迷狂的氛围中——祭典成为人神共生的真实情境。
(一)错乱的巫者
巫者是祭祀仪式中的行为艺术家,他(她)们在祝颂表演中穿梭于多重身份,既可能是人神交感的中介,要上呈疾苦、下诏神谕,又可能是神本身降临。巫者是异能的持有者,《山海经》中记载的巫众就具有玄妙的本领:“有灵山,……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7]275他(她)们可以问诊施药。而《国语·楚语下》中的巫觋更是具有沟通天地的本领,所以司职甚为重要:“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8]515巫者成为祭祀中的焦点,他(她)们以其错乱的状态来完成先民对人神共生渴望的心理投射。荣格曾说信仰者必然要将内心的矛盾冲突交付给另一层人格(神),个体通过这种交付而自觉获得了更高的人格,从而就能够获取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3]167。直接向神交付是困难的,因为成功的娱神技巧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掌握的,因此巫者成为先民在祭祀过程中飨神实践的交付对象,先民期待由神通广大的巫者来实现飨神、娱神的目标。
巫者祭祀飨神的过程有严格的规格与程序要求。《山海经》曾记载:“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烛,斋百日以百牺,瘗用百瑜,汤其酒百樽,婴以百珪百璧。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烛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纯之。”[7]32可见祭祀规仪繁复。祝颂辞是最为直观与重要的环节,巫与神要展开“直接对话”。《九歌》作为经典的祭祀祝祷辞,其中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者在祝祷过程中为实现与神共形,进入身份错乱迷离状态的情形。朱熹曾经指出,《九歌》“宾主彼我之辞,最为难辨”[9]。在《东皇太一》中,东皇太一并未现身,因此巫者仅以巫的身份吟诵准备,所行之事只是择良辰、备祭品,身份比较明确。而到了《东君》中,巫者先为东君代言:“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2]64然而当东君御风而来后,巫者又转换回巫的身份再为东君颂歌:“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纟恒 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龠虎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2]64-66颂歌完毕,巫者重新化身东君而去:“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2]66《云中君》则以另一种方式反映了人物身份的模糊,吟诵过程中既有扮演云中君的巫者:“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虎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2]41-42又有对着“云中君”祝祷的巫者:“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2]42-43人神同台共叙。
最为明显的是《山鬼》,开篇巫者以巫的身份赞扬山神的娇美:“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2]72之后,化身山神诉说自己的寂寞与相思之苦:“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2]72-73最后一节对环境的描写,又像是在场旁观者的一声感叹:“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2]73由此,巫者完成了在三重身份中的穿梭。
在先民的交付中,巫者的身份变得错乱离奇,祭祀活动将巫者裹挟到了神的世界之中,这无疑使人的世界与神话世界有了衔接。弗雷泽把这种连通的意义归结为对精神的慰藉,他认为巫者应该通晓一切有助于人与自然艰苦斗争所需的知识,一切可以减轻人们的痛苦并延长其生命的知识[4]58。但唯有巫者化为神,那笼罩在肉体凡胎上的神性的光晕,才能慰藉先民的心灵。
(二)迷幻的时空
楚地先民的祭祀对象有多种类型,覆盖了天神、地祇、人鬼。在《九歌》所展现的祭祀中,除了巫者的身份表现得错综迷离之外,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祭祀时空的迷幻。由巫者的诵祷带领,祭祀者集体进入与神共游的状态,或突然直上九天,或倏忽云端漫步,或遨游深渊如履平地,或在崇山之间任意穿梭嬉戏。詹姆士把这种迷幻的时空感阐释为宗教式的神秘体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詹姆士所谓的神秘体验具有不可言说性与私人性,而《九歌》中所呈现的错落的时空感必须借由语言来反映,并且这确实是一种群体性的神游状态。神秘体验的私人性与《九歌》中狂欢时群体性神游的表现似乎有所冲突,但是在特定的情境(巫的带领)下,神秘体验会朝向大我(宇宙)的体验发展,最终形成集体性的合一认识。对于这一点,詹姆士也曾提及。他认为宗教经验中不朽的感受,是一种永生的意识,人们并不是相信自己在未来可以得到永生,而是觉得自己就是在永生中了,这种时空的错落感是共同的,是超我意识达到宇宙(大我)层次的表现,并将其称为超我意识的层次进阶[10]。弗洛伊德曾用自居心理[11]来论证巫者的虚伪与神秘体验的虚幻,这里暂且不论其结论如何,但是自居心理确实很好地诠释了祭祀中先民与神共舞的精神状态。自居心理即是一个自我向另一个自我的趋近,在此过程中通过模仿与吸收而逐渐形成对另一个自我的认同。巫者的错乱迷离是其自我与神性相混融的结果,而由于巫者的渲染和带领,参与祭祀的先民也会在自居心理的带动下进入与神共舞的状态。
比如在《河伯》所营造的巫者与河神共同畅游的情境中,先民仿佛集体进入了那个迷幻的时空,那是现实的虚幻却是意识的真实。河面水波涌起,在这情境中突破了交通的限制,竟然有螭龙为“我们”在水面御车而行:“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2]68转瞬之间,“我们”就登上了那遥不可及的昆仑之巅:“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2]68倏忽一瞬,又来到河神的宫殿,鱼鳞为瓦,珠贝饰墙,在水中犹如在陆地上一样畅快:“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2]69沙洲绵延,可是鱼儿列队把“我们”护送上了南岸:“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隣隣兮媵予。”[2]70与神同游何其欢乐,深渊大泽亦能驰骋无碍。
这种祭典与神境交错形成的迷幻的时空在《国殇》中也有体现。在祭祀人鬼时,先民仿佛都化身英勇的将士在战场上搏杀。眼前是短兵相接、战车隆隆、旌旗翻飞的景象:“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2]75战马就在身边狂奔嘶号,勇士尸骨遍野:“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2]75-76战场渺远却仿佛身临其境,热血沸腾过后又瞬间回到祭典中,与鬼杰共誓:“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2]76从祭典到沙场,再从沙场回到祭典,在时空的交错中,完成了个人对鬼杰身份的自我认同与沉浸。
祭祀为人神共在提供了时空维度,先民在祭典上对巫者的精神信仰及其在交付与自居心理中的神境沉溺,都是对未知世界的虔敬。错综迷幻是神境,诚明虔敬是情境,祭祀中神的伟岸正是彰显于人的诚明之中。
三、迷狂——娱神以安人
飨神完毕,祭祀活动已近尾声,《礼魂》中的送神阶段是伴随着先民群体性的歌舞狂欢而展开的:“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2]78鸣鼓高歌,轮番狂舞,先民迎神与飨神阶段的惴惴不安在祭祀宣告完成的那一刻一扫而空,由神游的空灵直接进入酣歌畅舞的迷狂之中。《九歌》中丰富的神话意象与祖先祭祀之实为先民带来了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快感,迷狂状态正是双重快感的爆发:一方面,先民在神话意象中实现了对孤独感与紧迫感的超越,送神的狂喜之姿散发着超脱的纵情之美;另一方面,先民可以在祭祀内容中实现切实的、紧要的祭祀诉求,即去除生息之忧。
(一)神话意象与纵情之美
《九歌》中祭祀的诸神大多有着神话背景,比如东君与日神传说,上古时代就有日神崇拜的传统:“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其闇。”[12]再向前甚至可以追溯至炎帝时期的羲和传说,《山海经》就曾记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7]269湘君、湘夫人与舜、娥皇、女英的传说有关。河伯则是黄河之神,《史记·滑稽列传》中记载了西门豹整肃邺城,禁止行河伯娶妻之事的故事。山鬼被认为是指巫山女神瑶姬,其向楚襄王自荐枕席的典故[13]流传甚广。
大量的神话意象与祭祀神灵交织一体,实际上反映了先民潜在的寻求超越的心理,因为那些神话意象都蕴含着某种能够超脱或者对抗世间之苦的特质。荣格将这种对神话的崇拜心理解释为对原始意象的回溯,认为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碎片,都有着在人们祖先的历史中重复过无数次的乐观和悲哀的一点残余[14]217。神话所传达的意向,那些无所不能的神力都是祖先通过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窘境的反思得来的精神结晶。当这种意向具有了信服力,它就可以把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从而唤醒人们身上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长夜[14]121,支撑着人类的精神世界走过人类最艰难的童稚期[15]。
正是这些携带着先民憧憬与悲伤的神话因子融入祭祀之中,使得祭祀成为一个可以供人抒发与宣泄原始情感、激情、冲动的平台。孤独感、紧迫感是与生俱来的悲情因子,如:《云中君》有“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2]43,思念是孤独的叹息;《山鬼》有“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2]73,不遇是孤独的等待;《湘君》有“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2]48,《湘夫人》有“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2]54,都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喟叹;《大司命》有“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2]58,人们被命运支配,无可奈何。这些潜在的悲伤情感时时会涌上心头,而在祭祀活动降神、飨神的过程中体验到的与神圆融、与神共生的感觉无疑极大地缓解了这两种痛感。歌舞形式是进入忘我境界的手段,狂欢开始前的一切圆融、共生状态的情绪铺垫,推进并达成了狂欢这一刻超越与解脱的喜悦。尼采曾说:“在这惊骇之外,如果我们再补充上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划入浑然忘我之境。”[16]人的个体感知逐渐消融在民族感或者集体感之中,从而得到升华,达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而激情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歌舞的狂欢与信仰的狂喜须臾不可分离。送神之后的歌舞狂欢是对先天存在的孤独感、紧迫感暂时被压制的庆贺,消除这些限制,情欲才能完全被满足。
依尼采之言,《九歌》祭祀中最后的狂欢正是一种酒神崇拜精神的展现,尤其是楚地祭祀具有浓厚的“巫风淫祀”[17]意味,那种奔放的、狂野的咏叹与摇摆,是基于情欲的生命力的绽放。首先,酒神精神的释放,说明了人格结构的多层次性与丰富性。祭祀中的神话意象类型丰富,每一场都是情感与理智的对决大戏,这种强烈的人神融通感牵引着人的态度与情绪发生强烈转变与剧烈起伏。其次,酒神精神是具有外倾性的表达,是触发感官共鸣后的感性抒发,因此会自发形成形式化的审美表达。祭祀中的情境创设完全摆脱了现实生活的实在性束缚,避免了现实性的、功利性的审美发生。最后,酒神精神的复苏,是内在感知功能与潜入感觉的情感意向的瞬间碰撞,是一种直觉性的内在观照,因此这种纵情之美是快速而短暂的。
(二)祖先祭祀与生息之思
在《九歌》祭祀送神阶段的迷狂中,除了包含那短暂纵情的美的享受外,以祖先祭祀为实的神灵高度,也为这番迷狂景象增添了一抹关于生息之思的理性色彩。以祖先祭祀为实的一个依据是东皇太一为天神,《史记》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18]1386东皇太一是《九歌》祭祀的主神,而古代祭祀中祭天是以祖先配享的。《国语·鲁语》云:“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8]159可见夏朝的祭祖与祭天是一体的。到了殷商时期,商王死后可以“宾于帝”。至于周朝,则称为“配天”,《诗经·周颂·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尔极。”[19]278《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也说:“诒厥孙谋,以燕翼子。”[19]235从周朝开始,祖先神灵就居于帝庭,与天同体,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逐渐接近、融合。
因此,可以说《东皇太一》反映的既是楚人的祭天仪式,同时也是祭祖仪式。另一个依据是楚地之人极其崇拜太阳。《史记》中有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18]1689显然,楚人以太阳神高阳为先祖,因此他们十分崇拜祝融,而《九歌》中第二位重神就是东君,东君即太阳神,楚人祀东君即祭祀祖先。另外,《九歌》其他篇目虽然多反映自然神祭祀,但祭祀手段多为情爱降神、娱神,目的仍以庇佑子孙、繁衍生息为主。
祭祀中的迷狂状态可以理解为一种高峰体验[20],它是最高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销魂与狂喜体验。对于先民来说,对自我的认识需要凭借两点:一是观照祖先,以确定来处;二是观照所处的群体,以确定此刻的真实。唯有这两点被确证下来,生息的往复无常才不会变成生命的枷锁,而变成一个个可以为自己书写意义的时刻的总和。
《九歌》的祭祀迷狂,正好能够带来这种高峰体验,它是祖先祭祀所带来的理性的狂喜感。《国语·楚语》如此阐释祖先祭祀的意义:“国于是乎烝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8]519思来处,则生于伟岸的灵魂,祖先神不是外在于群体的存在;观众生,则亲朋近邻皆意乱情迷。正如同涂尔干所指出的,祭祀祖先神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全部集中在共同信仰和传统上,集中在对伟大先祖的追忆之中,集中在集体理想上,社会比起凡俗时期更为有利、更加生动,也更趋真实。所以这种时刻,人们感觉到某种外在于他们的东西再次获得了新生,有某种力量又被赋予了生机,某种生命又被重新唤醒[21]。
《九歌》迷狂状态的喜悦既源于纵情超脱,又源于对生息的通达。在祭祀主题之下,其心理流变包含着两条主线,一是放弃自我的与神同形,一是肯定自我的与神同欢。祭祀活动在这两个互斥又相融的命题中迎来了先民的狂欢。或许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神对人的意义仅在于以神性度量自身[22],使灵魂得到呵护。“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2]78草木皆有情,四季亦不住,似是《礼魂》的最后两句早已道尽了先民在祭祀迷狂中的哲思。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