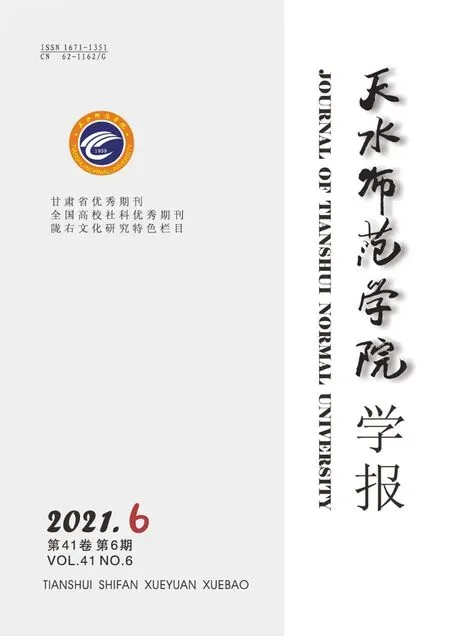口头诗学视野下的敦煌佛教歌辞论析
——以“重句联章体”佛教歌辞为例
许柳泓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佛教歌辞占据了敦煌歌辞的半壁江山,可称得上是敦煌歌辞的主体部分。任中敏先生在整理敦煌歌辞时特地分出“重句联章”一类。所谓“重句联章”即“在同一格调之同组多辞中,如已有五首或达全组之三分之二首以上,其同位置之某句或某数句文字首首相同者,始构成‘重句联章体’”。[1]663这一类歌辞全为佛教歌辞,且多出自讲经文、变文,而这两类正是佛教特有的说唱艺术。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它应是长期流传于人们的口头之间,并且是以非常纯粹的口头表演形式存在的。“口头诗学理论”所要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口头传承内部运作的规律。“歌辞”一称已表明它绝不是一种仅供世人阅读的案头读物,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表演艺术。在这种艺术中,口头上的歌唱表演起着重要作用,而诗歌语言是服从于音乐歌唱表演的。因此,将敦煌佛教歌辞置于口头诗学视野下进行理论观照,是对敦煌佛教歌辞“口头性”特征的揭露,也是由静态的文本研究迈向动态的表演研究的重要一步。
一、歌唱——“表演中的创作”
敦煌佛教歌辞数量众多,这是历史现实的一种自然反映。“盖终唐之世,虽曰三教抗衡,儒究非教也,要以佛教之渗透民间,最深且广。”[2]231既深且广,这缘于佛教传入中土后努力适应中土文化,并汲取中土优秀民间文化的养分,将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佛家教义完美结合,并通过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各种讲唱活动加以宣扬。为了警醒民众,佛门弟子在歌唱表演之时会反复譬释,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从而使得佛教宣唱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讲唱这一艺术形式也取得了深入人心的强烈效果。敦煌歌辞中的佛教歌辞多为讲唱辞,而讲唱又是一种口头表演艺术,故其文本可视为这种口头表演的文本。在口头诗学视野下对其加以观照,其口头性特征则显露无遗,这也恰恰是这类讲唱辞最引人之处。
笔者认为在分析敦煌佛教歌辞的歌唱表演之前,有必要认识口头诗学理论中的“口头表演”。口头诗学的理论核心便是“表演中的创作”。口头诗学理论的奠基人——洛德在其著作《故事的歌手》中明确指出:“对口头诗人来说,创作的那一刻就是表演。在书面诗歌的情形中,创作与表演、阅读有一条鸿沟;在口头诗歌中,这条鸿沟并不存在。因为创作和表演是同一时刻的两个方面。”[3]17这实际上点明了创作与表演的时间关系。在“口头传统”中,创作与表演同时发生,诗人于表演中进行思维创作,又于创作中开嗓歌唱进行表演,使得表演与创作呈现出共时性的关系。从这一核心特征向外延伸则可发现表演者和创作者是“一人分饰两角”的独特扮演。在口头诗学理论中,谁是表演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才是表演者?根据洛德的研究,这两个角色的共同承担者是既不识字又想从歌唱中获益的“歌手”,他们不属于特殊的阶层而很有可能来自任何一个阶层,但社会地位的高低与否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名“口头诗人”。由于每一次创作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可变的,故而口头诗歌的文本也染上了无定性的色彩。
明确了口头诗学理论的核心是“表演中的创作”,再回到“重句联章体”的佛教歌辞上来,我们会发现这些歌辞都带有一定的口头性特征,联系歌辞的歌唱表演环境,又可印证这类歌辞的口头性特征尽从“表演中的创作”这一特殊的歌唱方式而来。如《三冬雪·望济寒衣》和《千门化·化三衣》两套歌辞均是僧侣募化衣装时所唱,前者是秋冬募寒衣的歌辞,后者则是春夏时募夏衣的歌辞。两套歌辞虽然长短不一,却都采用“三三七七七”的句式来构建辞章,并且重句部分均落在每首歌辞的结尾处。《三冬雪·望济寒衣》十五首中,有十一首以“御彼三冬雪”五字作重句,已占全辞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千门化·化三衣》全套七首,每首均以“千门化”三字作结。为何会出现如此醒目的“重句”表达?这恐怕还应从其创作环境说起。上文已提到这两套歌辞是僧徒募化衣装时的唱辞,那么僧徒又是如何募化衣装的呢?自然是走出寺门,当街演唱,引人注意,诱导沿街的民众为其募衣。既然是当街而歌,必定无较多的准备时间,于是僧侣只能依靠自己平时的积累,将内心对获得寒衣或夏衣的渴望通过老妪能解的歌辞唱出来,期许能直击民众的恻隐之心,为他们募捐衣装,如此一来,僧侣的目的就达到了,也就不虚此行。在这场即兴的歌唱表演中,僧侣既是表演的主角,也是创作的主体,他们边走边唱,歌唱的同时也是其创作才能的展现。每首歌辞可能对应一个乐段,而在歌辞的结尾处反复歌唱同一内容,可能也恰好处在每个乐段的高潮之处,此刻,人声与旋律所产生的共鸣最能触动人心。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不可否认的是歌辞的反复总会给听者留下深刻印象,僧侣歌唱时采用此举,只为达到其目的。同时,这种特殊的重复又为创作者节省了思考的时间。僧侣边唱边作,相同的结尾则无需花费过多的思考时间,从而可以把精力用在下一首歌辞的创作之上。应当讲,这一特别的“重句”表达是“表演中的创作”的深刻体现,因此此类歌辞的文本是属于“口头传统”的,其歌唱表演也是口头诗学意义上的表演。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重句联章体”的佛教歌辞大多摘录自讲经文、变文,而这两类正是佛教特有的一种说唱艺术。说唱艺术本应是通过人们口耳相传得以传播的,是作为一种非常原始的口头表演形式存在的,而非以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说唱文本的形式存在。说唱艺术是一种动态的口头传播,而非静态的书面流传。“转变艺术原本是一些天才个人的现场表演”“尽管在转变艺术中,不排除部分说唱者背诵旧本的可能,但更主要的和真正能代表其艺术水平和艺术表演的,却无疑应该是那些真正的出口成章的现场创编,真正的具有口头性的现场说唱。”[4]既然讲经文和变文都具有口头性特征,那么穿插于其间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歌辞也定是通过现场创编而带上了口头色彩。
二、程式——表演中的精髓
“程式”是口头诗学的关键概念,虽然口头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等过程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却无一不受“程式”的制约,因而,“程式”是贯穿于口头文学的始末的。洛德对“程式”的定义是:“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3]40在洛德给出的定义中,程式首先是“一组词”,这是诗歌内容方面的体现;其次,程式的分析又必须“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这又是诗歌形式方面的反映。恰如洛德所言:“程式是思想与吟诵的诗行相结合的产物。”[3]42因此,任何一种程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可以说,程式是歌者现场创编的最基本的材料,犹如建筑所用的砖块,歌者所要建构的歌辞大厦就是用这样的一块块砖头垒搭而成的。这些“砖块”看似朴实无华,但却是口头表演的特色所在,自然也是口头表演的精髓之处。
佛教歌辞中的“重句联章体”一类,其最大的特色便落在“重句”二字之上。这些“重句”是一种程式化的表达,这种特殊的表达恰恰是其“口头性”特征的突出表现。“重句”因现场创编之需要而产生,亦最能体现歌唱表演之精妙。任中敏先生整理出的“重句联章体”佛教歌辞共19套,每套歌辞的程式情况各不相同,下面将其一一列出:
《三冬雪·望济寒衣》:全套歌辞共15首,其中有11首歌辞于结尾处以“御彼三冬雪”作重句。
《千门化·化三衣》:全套歌辞共7首,每首结尾处均以“千门化”三字作重句,前4首末句均为“三衣佛教千门化”。
《归去来·宝门开》:全套歌辞共6首,其中有4首以“归去来”为开头。
《归去来·归西方赞》:全套歌辞共10首,每首均以“归去来”为开头。
《失调名·出家赞文》:全套歌辞共10首,每首均以“舍利佛国难为。吾本出家之时。舍却□□□□。惟有□□□□”的程式构成一辞。
《十无常·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10首,每首均以“不免也无常”一句作结,且每辞结尾处带有和声辞“堪嗟叹。堪嗟叹。堪嗟叹。愿生九品坐莲台。礼如来。”
《失调名·和菩萨戒文》:全套歌辞共10首,每首均以“诸菩萨。莫□□”为开头,结尾处有和声辞“佛子”。
《化生子·化生童子赞》:全套歌辞共10首,每首均以“化生童子”四字为开头。
《驱催老·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5首,每首均以“也遭白发驱催老”一句作结。
《无常取·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8首,每首均以“限来也被无常取”一句作结。
《愚痴意·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9首,其中有7首以“不修实是愚痴意”一句作结。
《为大患·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6首,每首均以“也是于身为大患”一句作结。
《无餍足·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6首,每首均以“心中也是无餍足”一句作结。
《先祗备·闻健先祗备》:全套歌辞共6首,每首均以“也不如闻健先祗备”一句作结。
《抛暗号·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10首,每首均以“犹不悟无常抛暗号”一句作结。
《十空赞·调名本意》:全套歌辞共11首,其中有8首以“也是空”三字作结。
《行路难·无心律》:原作16首,今仅存12首,每首均以“君不见。无心□□□”为开头。
《易易歌·解悟成佛》:全套歌辞共9首,每首均以“解悟成佛易易歌”一句为开头。
《失调名·阿娘悲泣》:全套歌辞共3首,每首均以“阿娘悲泣”一句作结。
由此看来,“重句联章体”佛教歌辞的程式化表达多出现在歌辞的开头和结尾。这种程式化表达并非是一种文本上的简单重复,而是与歌者的表演息息相关的。“程式是由于表演的急迫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形式。只有在表演中程式才存在,才有关于程式的清楚的界定。”[3]44由于歌者的表演是一种特殊的“表演中的创作”,歌者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内构筑诗行,并配合旋律将其唱出。即便歌者已唱出诗行的最后一个音节,而下一诗行的构筑任务又开始向他逼近,迫使他的思维飞速运转起来以完成创作,从而顺利地推进表演。正是表演中所产生的这种急迫感使得歌者不得不去寻求一种快捷简便的方法来满足这种“表演中的创作”的需要,于是,聪明的歌者建立了一系列的诗行模式,歌唱时只需要在此模式上添砖加瓦即可。常言道“万事开头难”,歌者选择在开头处作程式化的表达自然是为了将开头之难简单化,从而将精力投入到接下来诗行的创作中。而多数歌辞的程式化表达是在结尾,此处既是一首歌辞的结束,也是对歌者创作新的一首歌辞的提醒。因为“重句联章体”的歌辞是多首歌辞合为一套,所以歌者选择在结尾处作重句,是考虑到下一首歌辞的创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与时间,采用重复的形式显然是省事,这样可以快速投入到新歌辞的创作表演中。同时,以程式化的表达作结,又可以提示听众一首歌辞已唱毕,即将进入新歌辞的演唱。听众在聆听的过程中,对重复出现的演唱会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也会让他们感受到演唱的层次感。所以,洛德对“程式”的判断又更深了一层:“程式的核心意义是歌手意识中的产物,是他在编织诗歌时进行快速创作的反应行为。”[3]92因此,程式在静态的口头文学文本之中是内容与形式的交相辉映,在动态的口头歌唱表演之中是歌者与听众的互动反映,这种反映是口头表演区别于其他表演形式的独特表现。程式因独特而成经典,抓住了口头表演中的程式,也便抓住了口头表演的精髓。
若将程式置于文本之中,从书面文学的角度来看,它更像是苍白无力的陈词滥调,因而须将其还原到歌唱表演的环境之中,用口头诗学理论来重新看待它们,我们将会发现程式是口头歌唱表演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歌者顺利完成表演和听众顺畅接受表演的重要保证。然而,正是因为程式的使用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歌辞中因语义重复而显得赘余的现象出现。如《失调名·出家赞文》一套,每首歌辞都以“舍利佛国难为。吾本出家之时。舍却□□□□。惟有□□□□”的程式进行诗行构筑,而其主要意义则集中在“舍却”和“惟有”后边所接的内容。“舍利佛国难为。吾本出家之时。”两句在多次重复中逐渐失去其精确的意义,从而成为“套语”存留于歌辞之中。这反映了歌者为合乐方便的考虑,这种情况也源于创作与表演的共时性特征。歌者“似乎不太关心语言的修饰,只是顺着故事的发展次序,凭着自己对演唱套路的熟悉来进行即兴表演。”[5]当歌者将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创作表演之中的时候,全神贯注的他未必能意识到歌辞中出现的这种问题,这也许是口头表演中难以避免的,但瑕不掩瑜,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口头表演的特别之处,也是一位歌者艺术修养的体现,是值得我们欣赏的。事实上,听众对这样的重复并不反感,相反,听众在反复聆听程式化的歌辞中获得了一种熟悉感,因熟悉而逐渐与歌者产生共鸣,由此萌动起向善皈依之心。程式的精妙就在于此,表演的精髓也在于此。
书面文学的欣赏和接受方式早已成为我们的一种思维定式,然而口头文学的创作方式与书面文学的创作方式截然不同,若我们还以这样一种思维惯性来欣赏口头文学自然发现不了其独特的韵调。“这一簇簇诗行、程式,常常互相纠缠在一起,重复出现,这是口头文体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标志。”[3]80程式是为了应付如闪电般迅速地创作而诞生的,因此在程式模式下遣词造句最见歌者的功力,这才是口头表演的精髓所在。
三、主题——创作中的灵魂
程式是在急迫的创作表演中产生的,是一定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表现,而表演的主要内容反映则是“主题”。主题是构成诗歌的基本内容,歌者需要通过创造性的思考,在短时间内将主题丰满起来,从而构筑出更大的结构,以推进表演的顺利进行。洛德认为:“主题是用词语来表达的,但是,它并非是一套固定的词,而是一组意义。”[3]97可见口头诗学理论中的“主题”并不是一些固定词语的呈现,它要表达的是固定的意义。主题与程式一样,都是在歌者的演唱实践中产生的。在这种特殊的表演状态下,口头诗人从不刻意地记忆他的歌唱文本,他的创作是运用程式来构筑诗行,运用主题来引领创作。因此,主题是歌者创作表演的灵魂所在,有此灵魂的支撑,其表演才言之有物,也不至于堕落成为空有形式外壳的“行尸走肉”,这时的表演才是生动的,是充实的。
敦煌佛教歌辞是“为适应佛教的歌唱宣传的需要而创作的”,也“是面向广大民众进行佛教宣唱时所用的内容材料”。[6]6既然是为佛教宣唱所用,那么歌辞的主题大体离不开佛家教义。从19套“重句联章体”佛教歌辞的文本内容来看,其主题可归纳为“劝善皈依”,这是每套歌辞的核心内容,是歌者创作的灵魂支撑,是歌辞的精神引领,但不同的歌辞又有不同的内容表现。下面对每套歌辞的具体主题表达进行概括分析:
《三冬雪·望济寒衣》:劝民众行善,募捐寒衣。
《千门化·化三衣》:劝民众行善,募捐夏衣。
《归去来·宝门开》:佛门圣洁,劝民众皈依。
《归去来·归西方赞》:俗世痛苦不堪,劝民众皈依。
《失调名·出家赞文》:抛却俗世,劝民众皈依。
《十无常·调名本意》:世事无常,劝民众皈依。
《失调名·和菩萨戒文》:欲望过多,劝民众向善。
《化生子·化生童子赞》:佛门圣洁,劝民众皈依。
《驱催老·调名本意》:世事无常,劝民众皈依。
《无常取·调名本意》:世事无常,劝民众皈依。
《愚痴意·调名本意》:欲望过多,劝民众向善。
《为大患·调名本意》:欲望过多,劝民众向善。
《无厌足·调名本意》:欲望过多,劝民众向善。
《先祗备·闻健先祗备》:劝民众行善,及时施舍供养。
《抛暗号·调名本意》:世事无常,劝民众皈依。
《十空赞·调名本意》:万事皆空,劝民众皈依。
《行路难·无心律》:万事皆空,劝民众皈依。
《易易歌·解悟成佛》:佛门神圣,劝民众皈依。
《失调名·阿娘悲泣》:劝民众向善,及时行孝。
从上述分析可见,“重句联章体”佛教歌辞中“劝善”主题的歌辞有8套,“皈依”主题的歌辞有11套。但其实“劝善”与“皈依”两大主题并无明确的界限,佛教讲求向善,劝善之时必包含着对民众皈依的期盼,皈依之时也必定是心怀善念的,故笔者认为将这19套歌辞的主题概括为“劝善皈依”是合理的。
“主题并非静止的实体,而是一种活的、变化的、有适应性的艺术创造。主题是为歌而存在的。主题在以往所采取的形式曾在那个时候适应了具体的歌的实际。”[3]136主题是“固定的意义”,但表现“固定的意义”的内容却是多样的,从这层意义上讲,主题又是灵活多变的。歌者为了演唱的需要,在明确了自己所要运用的主题后,尽可以结合实际的演唱环境,并根据自己所储备的材料,在主题的引导下进行内容创作,因此主题既可以被浓缩,也可以被丰富,但无论如何变化,主题始终藏于创作之中,且贯穿于歌唱的始末,使得歌者的创作表演不至于患上“失魂症”。如《失调名·和菩萨戒文》《为大患·调名本意》《无餍足·调名本意》三套均意在歌唱人于世俗间有太多的欲望,而欲望过多必将导致人性的迷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向善才是根本之道。《失调名·和菩萨戒文》一套,十首歌辞分别歌唱了杀生戒、盗戒、邪淫戒、妄语戒、沽酒戒等十戒,即希望听众能戒除这十种欲望而一心向善。《为大患·调名本意》一套则歌唱贪玩、恋家、爱美、贪吃、懒惰等情欲,指出如此种种俱为身之大患,当戒除以向善。《无餍足·调名本意》一套专唱人之贪欲,珍宝田屋、粮食衣裳无不希求多多益善为好,由此点明人人“心中也是无餍足”。贪欲乃佛家之大忌,视为不善。歌唱种种贪婪行径,只为了奉劝民众引以为戒,皈依佛门,心向善道,方可修成正果而得以善终。三套歌辞的主题相同,而在内容表达上显然不同。但是,相同的主题自然可以有相同的内容表现,所谓“相同的内容”并非是完全一致的语言表达,而是歌辞意义的一致。如《驱催老·调名本意》和《无常取·调名本意》两套歌辞都是通过歌唱来道出世间一切生灭都在刹那之间,变幻无常,亦无法挽留的道理,从而期望听众能看透这世间的无常而选择皈依佛门。两套歌辞都以美人为例,唱出“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的幻灭感。《驱催老·调名本意》中言:“说西施。妲己貌。在日红颜夸窈窕。只留名字在人间。也遭白发驱催老。”[1]702《无常取·调名本意》中道:“说恒娥。谈洛浦。美貌人间难比喻。端严将谓百千年。限来也被无常取。”[1]704无论是人间的西施、妲己,还是天上的嫦娥、洛神,都是美得不可方物的存在,但这“存在”却仅停留在人们的意识中。西施、妲己的美貌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历史尘封,人们记得的也不过是她们的名字而已,有谁还会记得她们的容颜呢?嫦娥、洛神的美艳被传说了千百年,可这千百年来又有何人能真正目睹其真容呢?一切不过是虚幻的神话罢了。
主题也是为了适应“表演中的创作”这一特别的方式而诞生的,“可以想见,歌手是在表演中,在坚实的实践中编织出自己的一个主题形式。所以,一个歌手的主题可以与其他歌手区别开来。程式结构的可变性允许我们在这一层次上确认个性风格。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主题层次上确认歌手的个人风格。”[3]133-134不同的歌者可以歌唱同一主题,但围绕主题而歌唱的内容定然不会是千篇一律的。歌者在主题这一“灵魂”的牵引下,凭借自己毕生所学,构建出只属于自己的且又有血有肉的歌唱诗篇。主题是核心内容,基本上无多大变化,易变的是服务于主题的内容叙说,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这些佛教歌辞会看起来好似相同却又不尽相同了。
四、余论
一次口头歌唱表演的完美落幕,靠的不仅仅是歌者高超的“表演中的创作”的技艺,更需要听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因此,“口头诗人并不追求我们通常认为是文艺作品的必要属性的所谓‘独创性’或‘新颖性’,观众也并不做这样的要求。一个经历了若干代民间艺人千锤百炼的口头表演艺术传统,它一定是在多个层面上都高度程式化了的。而且,这种传统,既塑造了表演者,也塑造了观众”。[7]听众在口头表演中亦是举足轻重的。上面的论述以“重句联章体”的佛教歌辞为例,揭示了敦煌佛教歌辞的“口头性”特征。而数量庞大的敦煌佛教歌辞绝不只是“重句联章体”一类带有此特征,“定格联章体”佛教歌辞的“口头性”特征亦十分明显。所谓“定格”,指的是歌辞在谋篇布局上遵循特有的结构。这种固定的结构格式可看成是“程式”的一种表现。同时,这又与歌辞曲调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口头歌唱表演中,曲调的选择事关重大,既要适合表演者歌唱,又要考虑到听众的接受情况。
敦煌佛教歌辞中,“定格联章体”一类有数十首调名为《五更转》的作品。可想而知,《五更转》应是当时极为流行的曲调,人人乐于唱之。于是,僧侣便利用此调来宣扬佛教教义,让表演者与听众都处在熟悉的音乐旋律的环境中,对彼此都是非常有利的。从歌辞的文本上看,调名虽然是相同的,但内容和篇幅却相差甚远。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阐释佛家教义,二是颂扬释迦牟尼。篇幅长短各异,短则五首为一套,长则十五首为一套。一般情况下,《五更转》一调多是由一更唱至五更,五首歌辞即可构成一套,歌唱完毕即可结束一次表演。然而,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意识:佛教讲唱是一种“现场创编”的艺术,它具有巨大的可变性。因而,歌辞的长度是灵活多变的,“如果暂时撇开歌手才气高下这一要素,我们可以说歌的长度取决于听众”。[3]22若表演者发现听众无多大的兴致,那么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进行创作表演即可;若他觉察到听众热情高涨,其自身的表演激情也会随之调动起来,创作思维飞速运转,多作几首歌辞,多唱几段又何妨?“一个成熟的歌手的标志是他在传统之中游刃有余”,[3]35既尊重传统,又能突破传统的束缚而有所创新。从这层意义上讲,当年那些不知名的僧侣都是一位位了不起的“口头诗人”,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艺术家。
如此看来,大部分佛教歌辞都保存着“口头传统”的痕迹,其“口头性”特征在为数众多的敦煌歌辞里格外突出。正是有这些特征的引导,才让我们了解到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同时,这些特征又是唤醒那纸页上已沉睡了千年的文字的独特法门,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不再是一个个冰冷死板的方块字的拼凑,而是一次次鲜活灵动的口头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