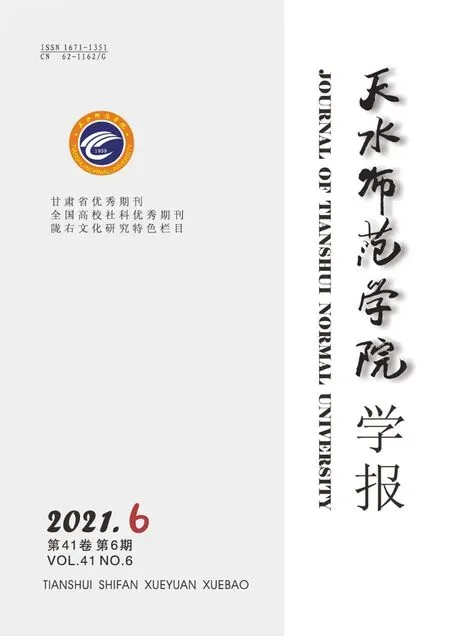敦煌文书动产买卖契约中如何规避民间纠纷
巨 虹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杂志社,甘肃 兰州 730070)
《唐律疏议·名例律》疏:“嫁娶有媒,买卖有保。”这说明在田产、房屋、奴婢、大牲畜等交易、买卖时需要保人,在达成婚约时需要媒人。保人与媒人,分别在买卖契约、婚书上“副署契约”,也要承担一定的连带责任。这种做法既是对当事人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日后有可能发生争议、民间纠纷的一种规避手段。
敦煌出土的契约文书有300多件,起讫时间是唐天宝年间到北宋初期,反映了西北地区普通民众的民间经济往来和一些社会生活,也展示了他们的法律生活。在敦煌文书的买卖契约中,价金是一项必备内容,价金有即日付款、预付款、分期付款等三种支付方式。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是即日付款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有利于买卖活动迅速完成,避免因为价金的预付或者滞纳而影响到买卖活动的顺利进行,甚至引发民间纠纷。即日付款也是我们在敦煌买卖契约文书中所见的较多的价金支付方式。预付款是指由买方先付款,到约定的时间后卖方再交货。价金的分期付款,即买方先支付一部分价金,在约定的期限内付清余款,这种支付方式存在一定的风险,一般会在契约正文中加上约束性条款。例如,如果到期后买方还不能付清价金,需要加付所欠款的百分之多少的月利息等。
以往的研究在敦煌文书动产买卖契约的释读、录文、内容分析、分类、专题内容的探讨等方面已经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主要以如何规避民间纠纷为切入点,深入阐释买卖契约中的约束性条款,分析其中的违约罚则,观照相关追夺担保、恩赦担保制度,通过对“和同立券”“两和立契”“双方合意”等契约文书中相关套语的梳理,分析双方达成“合意”、通过预防条款规避纠纷在敦煌动产买卖契约中的重要性。
一、预防条款:买卖契约中的约束性条款
本文所说的预防条款,指在买卖契约中对契约双方预先做出的约束性规定,在契约中进行类似规定,主要目的是警醒、约束买卖双方,规避风险。“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1]622这是《唐律》“买奴婢牛马立券”条的规定。疏议曰:“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若立券之后,有旧病,而买时不知,立券后始知者,三日内听悔。三日外无疾病,故相欺罔而欲悔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若有疾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1]622由以上记载可知,在牛马驼等动产买卖过程中,必须订立当地本司本部的公验,而不是私券。严禁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牛马等有病而诈称没有病),同时严禁违约行为(牛马等标的物没有病,在买卖完成三日以后借故悔约者)。此外,过价后三日以内,买卖双方必须到指定的部门订立市券,如果超过三日,买方要被笞三十下,卖者要被减一等。
余欣提出敦煌出土契券中,具备违约条款的估计在80%以上,并且按表现形态将其分为三类:“罚则型”“任夺家产型”“罚则、任夺财物综合型”。[2]
“缔约双方通过一种商定的罚款,而打算使专卖具有其不可反悔的特点。这种罚金是随着物价而变化的,它能起到双重作用:对于不恪守自己义务一方的惩罚,对另一方给予赔偿。”[3]这是谢和耐针对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4]这是现代法律对违约金及赔付情况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在仲裁实务方面,“只要当事人明确约定违约金责任与违约损害赔偿并存……就支持守约方的仲裁请求”。[5]
余欣认同谢和耐提出的敦煌契约中的“悔”——主观上的过错只要存在就可实施罚则,即其中的违约条款具有惩罚性作用。余欣进一步区分敦煌契约文书中相关违约条款的不同情况,提出敦煌契约中违约条款的罚金性质不确定。即使具有赔偿功能,表现出赔偿金的一些形态,但“订立此条款的本意在于防止反悔,起警示作用,而赔偿作用则是从属的……倒不如说是一种以惩罚违约为目的的独特的罚金更妥当些”。[6]
杨际平在读了余欣的《敦煌出土契约中的违约条款初探》一文后,写文章进行了学术探讨与商榷,[7]从唐耕耦、陆宏基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第1页至第140页中,翻检、判断是否具有违约责任条款的101件文书,并分七大类,对相关契约的年代、契约性质或名称、违约罚则进行了详细的罗列与介绍。研究指出其中买卖、典押、博换土地、宅舍契14件,租佃土地契8件,卖牛契3件,这25件文书都有明确的违约条款:雇牛、驴、驼契(含典雇)6件中的4件有明确的违约条款,其他2件中的1件是典雇,1件已付雇价清结;卖儿、卖婢、典儿、典身契6件,其中3件有明确的违约条款,其他3件中的2件是典契,1件已付买价清结;雇工契13件,其中12件有明确的违约条款,其他1件有抛工罚则;贷粮契32件,其中25件有明确的违约条款,其他7件无明确的违约条款;贷绢帛契19件,其中15件有明确的违约条款,其他4件没有明确的违约条款。合计101件契约,其中81件有明确的违约条款,占83%。“当时在各种契约中订立违约条款是一种普遍现象,该条款在唐五代的敦煌地区已经广泛推广。少数几件契约非正常缺失违约条款,只能视为特例,而不具普遍意义。”[7]
笔者认为,买卖契约中的这些违约条款,不如直接称它们为约束性条款。在契约中明确规定违背契约、反悔之后如何赔偿和惩罚,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为了赔偿而赔偿,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提醒、警示当事人,不要轻易反悔,不要轻易违背契约,其最本质的作用在于“约束”。这样的约束性条款,既可以保证契约的有效性和顺利实施,又可以规避有可能出现的民间纠纷,非常实用,确有存在的必要。我们不能把它们只视为契约中的套语而匆匆一读而过。
二、违约罚则:规定对悔约行为以经济惩罚为主
北朝以来就有“悔约罚”的习惯,这在敦煌文书中得到很好的沿用。敦煌文书中的相关契约一般规定,对悔约行为的处罚,以经济处罚为主。要求违约的“先悔者”,必须承担违约责任中的财产责任,即在返还、赔偿“标的物”损失的基础上,再予以经济处罚,这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比如,S.1285《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百姓杨忽律哺卖舍契》:“如先悔者,罚麦拾伍驮,充入不悔人。”①本文引用敦煌文书较多,所引录文主要参照以下文本,后文不再一一注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1-14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合编:《俄藏敦煌文献》(1-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2012年。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S.1356《唐大中五年(851年)僧光镜负似布买钏契》中则规定:“如先悔,罚布壹尺,入不悔人。”S.1946《宋淳化二年(991年)押衙韩愿定卖妮子契》中规定“如若先悔者,罚楼绫壹疋,仍罚大羯羊两口,充入不悔人”。S.5820、S.5826《未年(803年)尼明相卖牛契》:“立契后有人先悔者,罚麦三石,入不悔人。”此外,还有S.466中的“若先悔者罚青麦拾驮充入不悔人”,S.1475v的“如先悔者罚麦伍硕入不悔人”。S.3877v中有“如若先悔者罚上耕牛一头充入不悔人”,P.3331中有“如先悔者罚黄金三两充入官家”,P.3649v中有“如若先悔者罚上马壹匹充入不悔人”,北图生字25v中有“如先悔者罚楼机绫壹匹充入不悔人”,吐鲁番出土文书《前凉升平十一年(367年)王念卖驼券》(65TAM39:20)[8]5中有“若还悔者,罚毯十张供献”,《唐孙玄参租菜园契》(73TAM506:04/5a)[9]301中则约定“如限未满,改租别人者,罚钱叁阡(仟)入孙”。以上的约定,主要目的是确定“乡法”——契约的法律效力,保障契约双方当事人中“不悔者”的权益。
可见,在经济惩罚中,除了粮食、羯羊、耕牛、马匹等生产生活资料之外,还有生绢、机绫、布、毯等。“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已后,与钱货兼用,违法者准法罪之。”[10]这是《全唐文》卷25《令钱货兼用制》中的记载。那么,绫罗和绢、布,其实是可以担任商品交易中的货币职能的。钱帛并行货币政策的实行,可以弥补唐代钱币的不足。
还有,互易契约P.3394《唐大中六年(852年)僧张月光博地契》规定的经济制裁是“如先悔者,罚麦贰拾驮入军粮”,其违约责任除了规定经济处罚之外,还包括刑事处罚——“决丈(杖)卅”,即用杖责三十下。
另外,“悔者一罚二”的处罚标准,适用于对契约当事人中的“反悔者”的处罚,这种处罚标准在敦煌吐蕃文契约、吐鲁番契书中有所体现。“假定借人到期不还,将罚两倍。”[11]191这是《亥年阿骨萨部落王阳准借布契》中的规定。“如不能按时归还或图谋不还,将被罚还两倍。”[12]226-227这是《悉宁宗部落曹玛赞借麦契》中的规定。《高昌某人夏镇家麦田券》(67TAM364:5)则规定:“二主先和后卷(券),卷(券)成之后,各不得□□,悔者壹罚贰,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11]191“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13]339这是《高昌赵阿头六举钱券》(72TAM153:35a)中的规定。
当然,这些与“悔者一罚二”有关的规定,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是确实落实执行的,需要在对应的契约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吐鲁番文书《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康保谦买园券》,原文中早已对先悔约一方需要付出的赔偿金额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若先悔者,罚银钱壹百文入不悔(者)。”而在契约的最后却依然写有悔约担保:“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因此,该契约中的所谓“悔者一罚二”,只是一种习惯的套语,并不代表实际悔约时需要付出的赔偿金额。
三、约定追夺担保、恩赦担保制度
何谓担保?《辞源》中指出,“担”是“承当、负责”,[14]1319“保”是“负责、保证”,[14]216所以笔者认为,“负有责任”是担保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担保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标签,能够适用于不同的事物上。”[15]2这是法国学者Cabrillac的看法。其实,在契约文书中,担保主要指债的担保或者债权担保。保障债权的实现,应该是担保的最直接目的。王欣怡认为:“担保,即为债权人与担保人相互约定的,在一定条件下须代债务人偿还的债务,或者仅承担催促责任的契约。这里面‘一定条件’包含债务人逃亡或死亡,或债务人不按时履行债务的情况。”[16]4担保能够促进债权债务关系的及时了结,防止债务纠纷的发生。“担保制度首先是与债的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为强化债权信用、保证债的实现的一种制度。”[17]2
在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中,“恩赦”往往是君主治国临民的重要手段。“赦谓放免……宥谓宽宥”“人君于人之有过者而赦之,有罪者而宥之”,[18]522恩赦通常为赦免、宽恕犯罪者的刑罚。唐律中有“经恩不尝”的说法,就是说,遇到恩赦大赦的情形,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宋代洪迈《容斋三笔》中记载朝廷的恩赦大赦可以免除相关的担保责任。而在相关的借贷契约方面,恩赦主要是国家对债务的本金、利息通过颁布法令来全部(或者部分)免除的措施。由于民间高利贷对百姓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影响的,过度的盘剥甚至会导致穷苦百姓因债台高筑无力应对而家破人亡。这样的结果对国家财政赋税的征收、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为了避免或者缓解这种情况,唐代国家往往会发布一些法令敕文,既赦免官债和公债,又赦免民间私人债务。我们可以在唐代皇帝颁布的敕令条文中,看到国家对债务的赦免的有关记载。“其公私债负及追征输送,所至处,且勿施行。”[19]788这是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六月乙未诏中的文字,见《册府元龟》卷70《帝王部·务农》。“门下……御史台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公廨及诸色本利钱,其主保逃亡者,并正举纳利,十倍已上;摊征保人,纳利五倍已上及辗转摊保者,本利并宜放免……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徒扰公府,无益私家。应在城内有私债,经十年以上,本主及原保人死亡,又无资产可征理者,并宜放免。”[20]2140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中的文字,见《文苑英华》卷422。此外,还有如以下文字:“契不分明,争端斯起。况年岁寖远,案验无由,莫能辩明,只取烦弊。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21]414这是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三月三日制节文中的文字,收入《宋刑统》卷26。
“或有恩赦大赦流行,亦不在论理之限”,这是敦煌买卖契约中通常的规定,体现了在切近实用的前提下,为了维护当事人利益,买卖契约对国家法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抵制。比如,在S.1946《宋淳化二年(991年)押衙韩愿定卖妮子契》这件买卖奴婢的契约中,既有追夺担保的约定,也有对恩赦担保或者说抵赦条款的约定。其中的追夺担保即规定“其人在患,比之十日后不用休悔者”,即如果买卖的奴婢有病,允许买主朱愿松在十天以内悔约。对恩赦担保的约定是,“或遇恩赦流行,亦不在再来论理之限”。
又如,在敦煌文书S.1473下部落百姓曹茂晟向僧海清借贷“豆”的借贷契约中,就规定“中间或有恩赦,不在免限”。即拒绝把朝廷的恩赦适用于该借贷契约,僧海清借给曹茂晟(十八岁的沙弥法珪的父亲)的豆种,必须在规定的偿还期限以前准时偿还(从三月一日到秋八月卅日,借期约半年)。如果超期,曹茂晟就要按契约规定偿还最初借的豆种的两倍的量。甚至,当曹茂晟没有能力偿还时,放债的僧海清可以出卖借债人曹茂晟的“家资杂物”,这是唐律所允许的。如果曹茂晟在契约存续期间去世,他的儿子沙弥法珪作为保人,就要负责归还债务,即“如身东西[不在],一仰保人代还”。由于规定了抵赦条款,在此期间,如果遇到朝廷下诏宽免所有债务,曹茂晟所欠僧海清的债还是保持不变,依旧需要偿还。
在敦煌文书中,不少为了帮助借贷人渡过难关,借贷种子、谷物,到收获季节归还的借贷契约中,都明确规定了“遇赦不除”的抵赦条款,在山本达郎与池田温的著作中,就列出了41个例子,#291—#332。显然,签订契约的百姓平民并不认同朝廷用恩赦来取消他们的私人契约的做法。比如,在借贷契约中,明确标示排除恩赦效力的就有:第一,S.1475v《卯年(823年)悉董萨部落百姓翟米老便麦契》中的“不在免限”;第二,S.1475v《酉年(829年?)下部落百姓曹茂晟便豆契》中的“中间或有恩赦,不在免限”;第三,P.3444p1+P.3491p2《寅年(834年?)丝绵部落百姓阴海清便麦粟契》中的“中间如有恩赦,不在免限”;第四,P3444v《寅年(834年?)上部落百姓赵明明便豆契》中的“如后有恩赦,不在免限”。
在吐鲁番文书中,同样有类似的抵赦条款。例如,“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这是吐鲁番文书《唐乾封元年郑海石举银钱契》中的一条声明。即使一切债务被宣布免除,也不包括该契约;充分说明该契约的有效性,在该契约的有效存在期限内,即使政府宣布解除所有债务,也不能影响该契约的执行。霍存福认为,诸如“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22]
当然,实际上,唐王朝的大部分赦令,主要目的是蠲免逋欠官府的债务(比如逋赋),对私人债务很少涉及。“有私债经十年以上,本主及原保人死亡又无资产可征理者,并宜放免。”[20]11上这是公元819年的一份诏书中对私人债务的赦免规定,即欠债人、保人都已经死亡,并且都没有资产可征收处理的,官府会确定赦免债务。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的赦免,应该说是一种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纠纷、导致更多社会问题而采取的无可奈何的处理方式。“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21]414这是《宋刑统》记载的公元824年的规定。许多已经签订时间较长(三十年以前)的契约,欠债人、保人已经逃离本地或者去世,只空留一纸契书,面对这样的情况,官府出于无可奈何,只能借恩赦之机免去该借贷契约,由于当事人的缺位,这些契约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效力和作用。
四、强调“和同立券”“两和立契”“双方合意”的重要性
在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二主和同立契”“两和立契”“两共对面平章”“先和后券”的惯用语不时出现。所谓“和同”,就是双方所达成的合意。
罗马契约法规定,只有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契约才能成立。无独有偶,《唐律·名例律》《唐律·杂律》等律文中都强调买卖的两和(双方合意)。强调当事人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缔结契约。《宋刑统·杂律》引《唐令》:“诸出举两情和同。”《唐律疏议·杂律》律疏甚至将买卖行为的“两不和同”解释为犯罪。
敦煌文书中的契约文书,由于大多数民众不识字,所以由别人代写的文书占大多数。代写的文书只要有双方当事人的亲自签署,或者采用“画指”的方式,由当事人在契约文书后部自己的名字下面画出自己一节手指的长度,再点出指尖、指节的位置,更简约的可以只画指尖、指节的位置。文书上通常把这种行为称为“画指为信”或“获指为信”,其法律效力和当事人亲笔书写是一样的。敦煌文书中的牒辞、诉状、供词等都比较普遍地采用了“画指”签署的方式。在敦煌文书的契约文书中,一部分留有“代书人”或“倩书人”的副署,说明他们有证明文书真实性的责任,也有证明当事人双方属于“和同立券”“两和立契”“双方合意”的义务。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同样明确规定了买卖双方二主“和同立券”的有:《高昌延寿五年(628年)赵善众买舍地券》(69TAM135:2)、[11]243《高昌延寿十四年(637年)康保谦买园券》(64TAM15:29/2)、[23]37《高昌张元相买葡萄园券》(69TAM140:18/4)[24]53等。其中明确提出买卖双方“二主合同立券,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入不悔者,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若有先悔者,罚银钱壹百文,入不悔□□□和同立卷(券),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指明买卖双方要经过商议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再订立契约,强调了买卖双方自愿合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