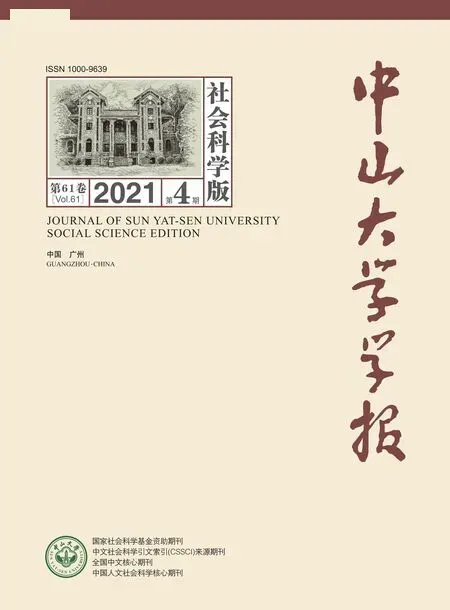论传统小说文体在民初的通变*
孙 超
“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等古体小说在民初呈繁荣之势,由于糅入时新兴味而具独特的现代品性,颇受读者欢迎①所谓“古体小说”不是一个通行的概念,本文指“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四种古代文体的小说作品。。不过,在遭到坚决与传统决裂的“五四”新文学家批判后,特别是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推行“废文言兴白话”的教育政策,使得古体小说或黯然退场,或顶风坚守。从此,学界普遍将民初古体小说称为“旧文学”,作为落后腐朽的代表,视之为“新文学”打倒的“文坛逆流”。本文拟通过对民初古体小说的系统考察来揭示传统小说文体在现代转型语境中的通变,认识民初文人从事古体小说创作“不在存古而在辟新”②冥飞、海鸣等:《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第144页。。
一、沿传统轨辙书写的笔记体小说
清末梁启超曾举《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着意强调笔记体小说随意杂录的撰述特点③《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民初的笔记体小说也多遵从此例。例如,何刚德在《〈平斋家言〉序》中说:“夜窗默坐,影事上心,偶得一鳞半爪,辄琐琐记之,留示家人。自丁巳迄去秋,裒然成帙。”④何刚德:《春明梦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7页。王揖唐序《梵天庐丛录》曰:“此书乃其平日搜讨所得,随时掇述者。”①王揖唐:《王序》,柴小梵:《梵天庐丛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页。徐珂自序其《清稗类钞》云:“辄笔之于册,以备遗忘,积久盈箧。”②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5页。从“琐琐记之”“随时掇述”“辄笔”一类字眼可辨其撰述方式一如传统的随意杂录,从“一鳞半爪”到“裒然成帙”“积久盈箧”等表述足见其由短章汇为巨编的辑录方式。对于笔记体小说一事一记的特点,管达如在《说小说》中说:“此体之特质,在于据事直书,各事自为起讫。”③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1912年第3卷第7期。对于包罗万有之特征,蔡东藩称其《客中消遣录》“立说无方,不拘一格。举所谓社会、时事、历史、人情、侦探、寓言、哀感顽艳诸说体备见一斑”④蔡东藩:《客中消遣录》,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年,第2页。;胡文璐称誉《梵天庐丛录》“上而朝廷之掌故,下而里巷之隐微,纵而经史之异同,横而华夷之利病,无不能说,说之无不能详”⑤胡文璐:《胡序》,柴小梵:《梵天庐丛录》,第8页。。对于全面继承古代笔记小说的体式,民初文人常常表而彰之,如冯煦《〈梦蕉亭杂记〉序》说“其体与欧阳公《归田录》、苏颍滨《龙川略志》、邵伯温《闻见前录》为近”⑥冯煦:《梦蕉亭杂记·序》,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页。;易宗夔《〈新世说〉自序》直承“仿临川王《世说新语》体例”⑦易宗夔:《新世说》,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2,2,2页。;吴绮缘称《新华秘记》“体仿《秘辛》《说苑》”⑧吴绮缘:《吴序》,许指严:《新华秘记(前编)》,上海:清华书局,1918年,第6页。,等等。研阅民初各家作品便知以上序说乃是据实而论。这些小说大多摇笔成文,每条(则)往往不设题目,一事一记,合集众事而成编。因此,从单条(则)来看,其篇幅短小,整体观之,又卷帙浩繁。相较而言,民初报载笔记体小说体式稍异,单篇作品为数甚夥,一般每篇都有标题。
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古代笔记体小说的实录原则始终不变,这规定了它追求史著品格:不重修饰,崇尚简约。这也使其与有意幻设、追求辞采的传奇体区别开来。“在纪昀看来,所谓笔记体小说之‘叙事’即为‘不作点染的记录见闻’。”⑨谭帆:《“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民初笔记体小说在理论与实践上皆沿此实录旧轨而行。管达如说:“此体之所长,在其文字甚自由,不必构思组织,搜集多数之材料,意有所得,纵笔疾书,即可成篇。”⑩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85页。这就重申了笔记体小说应“据见闻实录”,指出其优点是随意杂录。该体小说作者也普遍重视实录。例如,孙家振《〈退醒庐笔记〉自序》谓“吾犹将萃吾之才之学之识仿史家传记体裁将平生所闻见著笔记若干万字”11颍川秋水:《退醒庐笔记》,1925年石印线装本,第2页。;蒋箸超褒扬《新华秘记》“事事得诸实在,不涉荒诞”12蒋箸超:《蒋序》,许指严:《新华秘记(前编)》,上海:清华书局,1918年,第1页。;易宗夔声明《新世说》“纪载之事,虽未能一一标明来历,要皆具有本末”13易宗夔:《新世说》,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2,2,2页。,著述目的是成“野史一家之言”14易宗夔:《新世说》,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第2,2,2页。。民初笔记体小说无论是以笔记集行世,还是单篇载于报端,大多遵循实录原则,追求朴质雅洁的风格。也有一些作品由于受到《聊斋志异》和西方小说观念影响,开始喜装点,重修辞,呈现出与传奇体合流的趋向。
民初笔记体小说既然仍沿随意杂录与讲求实录的书写轨辙前行,势必保持古代笔记小说内容广博、功能多样的文体特点。从创作实际看,既有野史笔记类小说、稗官故事类小说,又有杂家笔记类小说。由于受到民初小说界“兴味”主潮的影响,以消遣为主的稗官故事类小说最为流行,其次是意在存真的野史笔记类小说。
民初稗官故事类小说题材广泛,思想驳杂,富有供人消遣的兴味。代表作有《铁笛亭琐记》《〈技击余闻〉补》《退醒庐笔记》《黛痕剑影录》《民国趣史》等。这些作品有的记杂事以志人,有的录异闻以志怪,一部笔记中往往还兼收两者。臧荫松评林纾《铁笛亭琐记》云:“今先生所记多趣语,又多征引故实,可资谈助者。”①臧荫松:《〈铁笛亭琐记〉序》,林纾:《铁笛亭琐记》,北京:都门印书局,1916年,卷首。该书杂记朝野逸闻,篇幅短小,笔墨超妙。钱基博《〈技击余闻〉补》记录活跃在江南的侠客,每则文末均言明故事由来,谨守实录原则。该作叙述简洁有味,写人白描传神,令人读之不厌。孙家振《退醒庐笔记》以记录市民轶事为主,兼有少量志怪,尤喜记录日常琐屑,适宜市民阅读消遣。胡寄尘《黛痕剑影录》则兼记异闻、琐事,说鬼怪、记名人、写各类女子,语言简雅,颇有六朝志人志怪之风。李定夷《民国趣史》记录“官场琐细”“试院现形”“裙钗韵语”“社会杂谈”等,所写奇闻逸事着眼于一个“趣”字。
民初稗官故事类小说普遍以奇闻趣事来满足读者的消遣需要,同时也注意增强文学审美性。周瘦鹃在《〈香艳丛话〉弁言》中称著阅笔记是“茶熟香温之候乃于无可消遣中寻一消遣法”②周瘦鹃:《香艳丛话》,上海:中华图书馆,1914年,第1页。,所记多是香艳故事。该书采用随笔摘录、连缀成篇的传统笔记成法,同时贯注周瘦鹃“小说为美文之一”③鹃:《自由谈之自由谈》,《申报》1921年2月13日。的现代文学观念,呈现出“情文兼茂”的文体风格,是周氏所谓“有实事而含小说的意味者”④周瘦鹃:《说觚》,周瘦鹃、骆无涯:《小说丛谈》,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第73页。,与其所作传奇体爱情小说异曲同工。“有人喻之为:如‘十七妙年华之女郎,偶于绮罗屏障间,吐露一二情致语,令人销魂无已。’”⑤郑逸梅:《民国笔记概观》,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101页。值得注意的是,《香艳丛话》虽体式古色古香,意趣也很传统,但其笔触已伸向现代和域外,受到了西方文学观念与印刷文化的改造。它在当时吸引了不少读者,开辟了笔记体小说现代转型的一条路径。徐枕亚、朱鸳雏创作的稗官故事类小说也意图创变,在突出强调消遣功能的同时揉进传奇体因素,明显增强了文学性。收在《枕亚浪墨续集》中的此类作品文笔流畅,叙事生动,讲究塑造人物。尤其是搜奇述异的作品叙述恍惚迷离,辞藻趋于华美,已有明显的传奇化倾向。朱鸳雏《红蚕茧集》收录的作品短小精致,饶富趣味,且多文学的描写和虚构,亦是传奇化的佳作。
民初野史笔记类小说突出的特征是补史存真。其作者不少是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闻见者,他们力图将某段史事实录以存真相。其中《德宗遗事》《辛亥宫驼记》《辛丙秘苑》《梦蕉亭杂记》《春明梦录》《清代野记》《国闻备乘》等是当时的名著。我们略观一斑。《德宗遗事》的作者王照是翰林学士、戊戌变法的积极支持者。他晚年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这部笔记主要记述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前后史事,笔墨集中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斗争。由于“皆实录所不敢言者”⑥语出王树柟,载王小航述,王树柟记:《德宗遗事》,北京师范大学藏本,第1页。,该笔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叙说清末宫廷轶闻历历在目,人物对话口吻毕肖,多具小说风味。对读陈灨一《睇向斋秘录》中的《德宗轶事(三则)》,光绪这位忧国忧心、可怜可悲的傀儡皇帝就真实地呈现出来。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撰《辛丙秘苑》记录辛亥(1911)至丙辰(1915)间袁世凯及其周围人物的掌故。虽有人批评该书因“既以存先公之苦心,且以矫外间之浮议”⑦寒云:《〈辛丙秘苑〉序》,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页。,故子为父讳之处甚多,但作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所记多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加之叙述饶有趣味,故受到当时读者热捧。《梦蕉亭杂记》由清末重臣陈夔龙撰述,主要记录他亲历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签订、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史料价值颇高。同时由于作者精心结撰,文笔生动有趣。另外,《新世说》《新语林》《清稗类钞》等几部仿作也很有名,是“世说”“类钞”类笔记的最后代表。
民初野史笔记类小说除了上述立本守正的作品外,也涌现出一些趋时创变的作品,其中许指严的作品最为典型。许指严素以创作“掌故小说”闻名,范烟桥称“历史小说允推指严”⑧范烟桥:《小说话》,《商旅友报》1925年第20期。。许指严有很强的文学加工意识,其所谓“采摭已征夫传信,演述奚病其穷形”⑨许指严:《〈泣路记〉自叙》,上海:《小说丛报》社,1915年,第1页。,希望在实录基础上演述得穷形尽相。因此,他的笔记体小说揉入了传奇笔法,明显增强了兴味娱情功能。《南巡秘记》是其掌故笔记的定型之作,专记乾隆巡幸江浙秘极奇极之事,随意装点,趋近传奇体。郑逸梅曾回忆说:“所记《幻桃》及《一夜喇嘛塔》,光怪陆离,不可方物,给我印象很深,迄今数十年,犹萦脑幕。”①郑逸梅:《民国笔记概观》,第100页。从此书开始他形成了“述历史国情,本极助兴趣之事”的看法,从而确定了将闻见与稗乘相发明的创作方法②许指严:《〈南巡秘记〉自序》,上海:国华书局,1915年,卷首。。《十叶野闻》是其笔记掌故的代表作,就清代十世杂史进行文学加工,以渲染清室趣事秘闻为能事,亦富传奇性。当然,许指严笔记掌故也想为历史“存真”,但又追求写人绘景“穷形尽相”,叙事“必竟其委”,因此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概观之,许指严的野史笔记类小说融笔记和传奇于一体,“因文生情,极能铺张”③凤兮:《海上小说家漫评》,《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1年1月23日。,增强了文学魅力,“有羚羊挂角之妙”④范烟桥:《小说话》,《商旅友报》1925年第20期。,吸引了大量读者。
二、尊体与破体意识影响下的传奇体小说
一部分民初小说家创作传奇体小说具有明确的尊体意识。林纾在《〈畏庐漫录〉自序》中声明其“着意为小说”“特重唐之段柯古”⑤林纾:《畏庐漫录·自序》,林薇选编:《畏庐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显然意欲承续唐传奇。叶小凤在《小说杂论》中说:“唐人自有唐人之小说,文不可假于父兄,而小凤独可假诸唐人乎?小凤曰:是有说也。畅发好恶,钩稽性情,乃天地造化之功;如我陋劣,何敢以此自期。然俯视斯世,凡作文言小说者,或斜阳画图,秋风庭院,为辞胜于意,臃肿拳曲之文;或碧璃红瓦,苗歌蛮妇,稗贩自西之语;其最高者,则亦拾《聊斋》之唾余,奉《板桥》为圭臬……蒲留仙、余澹心等不过如小家碧玉,一花一钿,偶然得态耳。在彼犹在摹抚官样之中,何足为吾之师……此小凤摹抚唐人之所由来。”⑥叶小凤:《小说杂论》,《小凤杂著》,上海:新民图书馆,1919年,第40—41页。由此可知,叶小凤认为唐传奇是文言小说创作的最佳范本,他的一些作品就直接标明“效唐人体”。姚鹓雏赞同叶氏看法,曾在《〈焚芝记〉跋语》中说:“丁巳除夕,偶与友论说部,友谓近人撰述,每病凡下。能师法蒲留仙,已为仅见,下者,乃并王紫铨残墨,而亦摹仿之。若唐人小说之格高韵古,真成广陵散矣。余心然之。”⑦鹓雏:《焚芝记》,《小说大观》1917年第11集。在上述名家的号召与示范下,民初传奇体小说宗唐之风兴起,而自清末流行的“聊斋体”势头稍稍减弱。不过,站在民初那个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的时间点上看,无论是以唐人小说为师,还是以《聊斋志异》为范,都是赓续固有传奇体小说的尊体表现。
尊体意识影响下的民初传奇体小说在题材上依然是婚恋、侠义和神怪三足鼎立;在笔法上多采用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的形式,讲求辞章结构;在创作旨趣上作意好奇,注意畅发性情,追求一种诗意美。
民初婚恋传奇脉承了唐传奇以来的传奇笔法和传奇性,旨在传播爱情奇闻和礼赞真爱精神,有的作品还意图抨击旧的婚姻观念,引导时代新风。如叶小凤的纯情类传奇《石女》《塔溪歌》《阿琴妹》等,歌颂男女间纯洁美好的情感,是唐传奇真爱精神的回响;奇情类传奇《忘忧》《嫂嫂》《男尼姑》等,叙奇人、奇事、奇情,明显继承或戏仿唐传奇的“艳遇”主题,但严守情淫之辩,旨趣仍在一“情”字。徐枕亚《箫史》写落魄文人萧啸秋与客舍主人侄女小娥之间因箫声相知、相恋,最终亦因箫而双双殉情的故事。从文体上看,该小说刻意规摹唐传奇,传示奇异之外,追求浓烈的诗意氛围,叙事婉转,抒情缠绵,形式上夹杂诗词,使用丽词藻句,兼有“文备众体”之妙。民初侠义传奇主要以唐传奇为范本。特别是那些写救厄济困、复仇报恩故事的作品模仿痕迹更重,如姚鹓雏所作《觚棱梦影》《犊鼻侠》明显模仿《昆仑奴》;李定夷《女儿剑》、张冥飞《雪衣女》则不脱《谢小娥传》窠臼。这些作品所承续唐传奇的诗意、理想特质仍为民初乱世中的读者所喜爱。有些作品则在沿袭唐传奇的基础上,呈现出一些新气息,如林纾所作《程拳师》《庄豫》等精于描写高超武技,以尚武精神鼓动国民斗志;李定夷的《鸰原双义记》倾心于展现侠义人格,以侠义精神砥砺民族士气。还有一些作品将英雄与儿女合为一体,以侠风奇情娱目快心。叶小凤所作《云回夫人》可为代表。它以《虬髯客传》为范本,写一位类似“红拂妓”的女侠。民初神怪传奇在体制上虽沿袭传统,但因受西方科学文明的冲击在创作旨趣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借写神怪来讥刺现实丑恶;一是借写神人相恋歌咏爱情美好;一是借写神怪使读者获得消遣。第一类作品首推许指严的《喇嘛革命》和《九日龙旗》。这两篇小说以大胆的想象,恍惚迷离的情节曲折地反映民初世相。第二类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有吴绮缘《林下美人》、程瞻庐《婴宁第二》等,这些小说亦可划入婚恋题材。第三类作品单纯讲述鬼怪故事,如阿蒙《冢中人》、聊摄《甘后墓》等,这类小说主要满足读者的猎奇、消遣需要。
民初小说家在创作传奇体小说时亦具自觉的破体意识。他们受域外小说影响,在写人、叙事及环境、心理描写等方面积极进行创作试验,拓展了传奇体小说的创作内涵,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和创作旨趣。
民初传奇体小说在创作内涵上有较大拓展,数量较多且较有影响的有都市情感传奇、家庭传奇和社会传奇等。都市情感传奇源出于传统婚恋传奇,是其富有现代性的变体。民初趋新求变的小说家如苏曼殊、包天笑、周瘦鹃等活跃在繁华都市上海,面向西方文化一直持开放心态,对欧美小说积极译介吸收,这就使他们有条件采用新的叙事技巧来呈现现代都市男女的情感世界。苏曼殊所作《焚剑记》《绛纱记》《碎簪记》和《非梦记》揭露礼教和金钱势力对都市青年爱情的破坏,积极回应民初婚制变革这一社会热点。虽叙之以传奇体,但又确如钱玄同所说其“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①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1号。。包天笑所作都市情感传奇颇具当下性和真实感,如《电话》《牛棚絮语》等写当时妓女的情海沉浮,试图引发读者对妓女归宿问题的思考。《泪点》叙飘渺生与其表妹的一段情缘,其纯洁真挚中的哀伤让读者不禁扼腕。这些作品表现出对过度提倡“恋爱自由”的警惕,同时又反对“盲婚哑嫁”,呈现出一种徘徊在新旧之间的过渡性特征。周瘦鹃创作的都市情感传奇有三类:一是作者本人恋爱生活的艺术化呈现,代表作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午夜鹃声》等;二是在言情中贯注着爱国观念,如《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诺》等;三是富有现代意味的至情、畸恋,代表作有《画里真真》《西子湖底》等。这些小说所写“奇情”“痴情”“至情”明显继承了唐传奇以来礼赞真爱精神的传统,同时也自觉汲取了西方自由恋爱的思想。家庭传奇主要展现新旧家庭观念的激烈碰撞及家庭生活的新气象。代表作品有周瘦鹃的《冷与热》,程瞻庐的《但求化作女儿身》《七夕之家庭特刊》等。
在破体意识影响下,一些传奇体作品借鉴外国小说艺术技巧在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非情节化叙事等方面进行了自觉变革,呈现出迥异于传统的现代性特征。整体来看,这些作品多截取一个生活“断片”,而非纪事本末体和传记体。例如,包天笑的《电话》写忆英生与旧情人蕊云的一次电话通话,除开头与结尾外,通篇是对话;周瘦鹃的《午夜鹃声》采用自述体反复渲染失恋的悲情;许指严的《女苏秦》以旅途中谈话起首写一个独立事件。这些作品普遍使用第一人称叙事,增强真实效果,还有意打破传统叙事时序来形成陌生化。如包天笑《牛棚絮语》先作回忆式倒叙,然后转向主要情节的正叙,又以“牛棚絮语”的对话方式让正叙暂停,变为追叙往事、谈时下处境,最后才将叙事拉回现实,把故事讲完。周瘦鹃《西子湖底》首先以老桨月下殉情开篇,接着以第三人称叙述老桨的神秘身世和怪异行为,然后又叙述“予”与老桨的相识相交。小说主体部分回到传统的叙事人听故事模式,老桨自述其三十年来的诡异畸恋。末尾又返回“予”的视角,呼应开头的老桨沉湖殉情。小说叙事视角的多次转换,仿佛文艺片中的镜头切换,使叙事曲曲折折,也使老桨这一“畸异怪特之人”得到精细刻画。单纯从艺术技巧上看,这已是一篇很“现代”的小说了。有些作品还注重非情节叙事,加强了场景及心理描写。周瘦鹃的作品就常以景色描写开篇,包天笑的作品则常常穿插大段环境描写,这大大改变了传奇体以情节为中心的固有叙事模式,增添了更多诗意。包天笑、周瘦鹃、刘铁冷的一些作品还直接描写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甚至完全以人物抒情和心理剖白为主体,这种“心理化”叙事更接近现代小说,而与古代小说渐行渐远。
三、保留说话虚拟情境的话本体小说
在民初古体小说中,话本体的文体变异最大。在体式上,该体作品多数不再使用入话,而直接进入故事主体;基本不再使用韵文叙事,叙事完全散文化;一般篇幅不大。在功能上,该体作品赓续古代话本小说娱乐、教化的传统,主要写家庭、社会、情感、伦理、滑稽等内容,充满了娱乐性、民间性和世俗性。
作为传统话本小说的变体,民初话本体小说已呈现出不少现代性特征:更普遍地使用第一人称,采用插叙、倒叙、补叙,进行横截面式描写,出现大段的心理、景物刻画,谈论时新对象,关注热点话题,等等。例如包天笑的《友人之妻》演述“我”的友人之妻,谈论对象是留学生和新派人物,关注的是小家庭建设这一热门话题。他的《富家之车》一经刊出便被读者视为创新之作,凤兮指出:“描写一个问题或一段事实者,如天笑之《富家之车》《邻家之哭声》……均确为自出心裁而有目的(指其小说之感痛力所及)者,均无所依傍或脱胎于陈法者也。”①凤兮:《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1年2月27日。这篇小说的问题意识和横截面式描写确有难得的创新,其半新半旧的小说体式也如凤兮所说“尤能曲写半开化社会状态,读之无不发生感想者”②凤兮:《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1年2月27日。。再如徐卓呆的《微笑》《死后》则以心理刻画见长。它们不像传统话本小说单纯通过外部言行来展现人物心理,而是加入了对心理活动的直接描摹。《微笑》中男青年的心理活动是贯穿全篇的叙述主线,情节推进与其心理活动相辅而行。《死后》则将一个一度屈从于命运的知识女性如何追求人格独立、如何成就文学梦的心理过程真实地描摹出来。又如周瘦鹃的《良心》开头是一段景物细描:“话说上海城内有一个小小儿的礼拜堂。这礼拜堂在一条很寂寞的小街上,是一座四五十年的建筑物。檐牙黑黑的……”③瘦鹃:《良心》,《小说月报》1918年第9卷第5期。这种种创变是其作者主动学习域外小说的结果,其突出的现代性几乎让人忘记它们由古代话本小说演变而来。
不过,从上述作品中的“看官”“在下”“你道”“话说”“看官听着”之类的“说话人”口吻中,我们仍能确认其话本体小说特有的说话虚拟情境——“作者始终站在故事与读者之间,扮演着说故事的角色”④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4页。。这种具有虚拟在场感和参与性的小说曾经让数百年的中国读者娱目醒心,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食粮。虽然在民初读者那里话本体已远没有过去的魔力,但这种熟悉的“说-听”虚拟情境仍能吸引一部分读者。古代话本小说设置说话虚拟情境追求把人物、事件讲活讲真,民初话本体小说赓续这一传统,运用白话俗语、通过塑造言行毕肖的人物来形成“似真”效果。比如包天笑《友人之妻》中钱玉美和孙玉辉的对话,让民初读者觉得人物很真实,就是身边受过新式教育又情同姊妹的闺蜜间推心置腹的窃窃私语。“看官”仿佛看着她们,听她们絮谈,这正是话本体的长处。再如看胡寄尘《爱儿》中演述的瓶居、松雪夫妇在育儿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龃龉、误会与和解,仿佛观赏一幕名为“成长烦恼”的家庭剧。更有趣的是,因了文中那声“看官”,读者仿佛也可走入剧中来。
对比古代话本小说,民初话本体小说虽还能借助说话虚拟情境“建立起真实客观的幻影”⑤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4页。,但已不能通过“说话人”之口讲出“一种集体的社会意识”①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6,93。原因在于古代相对稳定的道德伦理观念可以推出“说话人”作代言,而民初思想混乱、道德重构的现实使“说话人”失掉了集体代言的资格。因此,我们看到包天笑、周瘦鹃、姚鹓雏等的话本体作品不再通过“说话人”评议跳出情节来劝惩教化,而是借助情节自身的推动力量,自然流露个人对事件的态度。如姚鹓雏《纪念画》的结尾是两首诗,仿佛传统话本体的下场诗,可不同的是那诗是顺着小说情节自然生发的,是“我”为外祖母扫墓之后和在外洋轮船之上两次万感如潮而作的,言说的是个人化的情感。再如包天笑的《富家之车》,结尾是顺着情节发展讲述祖孙三代不同的出行方式,不露声色地传达作者的褒贬态度。又如周瘦鹃的《良心》虽仍以“话说”设置说话虚拟情境,但已是一种类西方短篇小说的结构,故事也在情节叙述中自然收束,并借梅神父的态度传达作者对沈阿青因追求真爱而杀人的赞赏。
由于抒情、评判的个人化与新体白话短篇小说日渐趋同,设置说话虚拟情境变得越来越没必要,“说话人”完全隐形成为小说发展之必然。正如王德威所说:“在作家强调抒发个人欲望及企图的冲动下,说话传统无可避免地被贬抑甚至消失。”②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6,93页。
四、正宗与特创的章回体小说
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长期以来主要使用白话创作,民初文言章回体小说的大量出现打破了白话一统的局面,使章回体有了正宗与特创之别。从小说文体发展史来看,章回体具有与时流变的特点。作为正宗的白话章回体发展至民初,在保持基本体制风格不变的基础上积极响应时代需求,产生了种种新变。而作为特创的民初文言章回体更是时风激荡的产物。
民初白话章回体小说并非如新文学家所说全是“旧思想,旧形式”③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而是继续保持与时流变的特点,面向广大市民读者写作,与世俗、时俗相通,呈现出很强的通俗性。因此,该体作品在语言、题材、适应报刊及类型化等方面都呈现出创变特征。
民初白话章回体所用白话与时变迁,大致形成三种情况:以《广陵潮》为代表的向俗倾向;以《古戍寒笳记》为代表的尚雅倾向;以《人间地狱》为代表的趋新倾向,体现了民初小说家对白话语言的多元追求,意图满足各阶层读者的不同需要。这些白话均由传统白话化出,以当时社会流行的白话为根本,同时吸收民间俗语和域外小说的某些语法及词汇,形成了有别于新文学“欧式白话”的“中式白话”。当时,过于高古的文言和过于欧化的白话都只能局限于某些特定的读者群,而“中式白话”倒是能够雅俗共赏。这一点,从此后新文学家内部对语言问题的论争和调整,从“五四”前后章回小说读者数量之大、层次之广都可得到确证。
民初小说的首发载体是报刊,白话章回体小说作为通俗文学适于在此大众传媒上发表,但同时也易于被其改造而发生文体变化。其最显著的变化有两点:一是有强烈的新闻意识,一是呈现出明显的类型化。民初白话章回体小说受新闻意识影响,大多跳脱讲史、神魔、传奇等传统题材,更倾向于写当下,甚至将新闻融入小说,如《山东响马传》《人间地狱》《茶寮小史》《新旧家庭》《交易所现形记》等皆是富有新闻性的作品。受新闻大众性、时效性影响,该体小说使用大众最快接受的通俗语言,结构也普遍采用短篇连缀的《儒林外史》式。这样可高效完成独立故事讲述,并可时时调整叙事视角、叙事内容和叙事节奏等,适应舆论或形成新的舆论。民初章回体小说的类型化与报刊进行小说的分类标注密不可分。因为作者要想投稿成功必然要看所投刊物的分类标注,读者阅读也必然受其引导,从而形成某种类型化的阅读品味。
民初白话章回体大致形成了社会小说、社会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四种类型,它们在近现代通俗小说类型史上具有奠基地位。社会小说佳作很多,诸如《如此京华》《留东外史》《傻儿游沪记》《怪家庭》《茶寮小史》《新旧家庭》《交易所现形记》等。这些小说叙事多元,侧重于现代生活启蒙。有的作品展现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乱世情态,表达一种激愤又无奈的爱国情绪和社会批判;有的作品描摹家庭生活,由家庭连接个人与社会,呈现独特视角下的社会观察。整体来看,其叙事场景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叙事结构一般采用《儒林外史》式的“短篇连缀”或《孽海花》式的“串珠花”;叙事焦点与时流变,从北京到上海,从总统府到小家庭;叙事关节则是其中的“怪现状”“活现形”。该类型小说的叙事模式对之后的张恨水、刘云若们有直接影响。社会言情小说以社会现状为经,以男女婚恋为纬,侧重于通过言情来反映社会。《广陵潮》是此类型经典,它让言情与社会紧紧捆绑,在民初言情小说潮中另辟出一条社会言情的道路。在《广陵潮》的成功效应下,社会言情小说迅速定型,在民国时期仅以“潮”命名的同类型作品就出版不下几十部。历史小说赓续传统“演义体”,在蔡东藩手中走向成熟。蔡东藩作品以朝代更迭为序,将中国两千多年的正史加以演义,叙事曲折有味,形成了独特的类型特征。另外,许慕羲、许啸天等的同类型作品在民初也较流行,与蔡东藩作品一道成为现代通俗历史小说的前驱。武侠小说没有沿晚清侠义小说开启的驯化英雄道路前行,而是回到《水浒传》开辟的仗义行侠、聚义犯禁的英雄传奇传统。叶小凤的《古戍寒笳记》是发生这一转变的关键作品,其叙事立场明显从官家转到民间,完全摆脱了清末侠义+公案的叙事成规,突出强调打斗场面的“武”与义薄云天的“侠”。此后,顾明道、陆士谔、向恺然等的武侠小说逐渐形成了两大基本叙事模式:一是以自圆其说的叙事逻辑叙述亦真亦幻“江湖”中的奇侠奇武奇情;一是以“尚武”“侠义”为叙事关节叙述某段特定“历史”中的侠义英雄。这为现代武侠小说所传承。
民初文言章回体小说发生的变化之剧,数量之多,影响之大,都堪称特创。它保留了章回体的基本特征,篇幅蔓长、分章列回、回有回目、注意谋篇布局,兼采传奇小说、骈散文及诗词等的艺术技巧和审美旨趣,从而形成了崭新面目。今人一般将民初文言章回体小说分称为“古文小说”与“骈文小说”,或曰“史汉支派”与“骈文支派”①“古文小说”与“骈文小说”之称见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 卷,“史汉支派”与“骈文支派”之称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这在总体上抓住了该体小说受古文与骈文影响形成的体制分野。但真正如《燕山外史》那样的骈文小说或纯粹的古文小说在民初是找不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诗骈化或古文化的章回体。
民初创作诗骈化章回体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民权报》作家群,他们以这种特创别体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哀情小说潮”。如徐枕亚《玉梨魂》《双鬟记》,李定夷《霣玉怨》《鸳湖潮》,吴双热《孽冤镜》《兰娘哀史》,等等。这些小说引骈入稗,大量穿插诗词,在文体上形成典雅的陌生化,在题材上呈现通俗的焦点化,故能化古生新。从小说文体的演进过程看,该体小说明显赓续传统而来。中国古代从唐传奇《游仙窟》引诗骈入小说到《红楼梦》雅化白话章回呈现诗意美,再由《燕山外史》用骈文写章回到《花月痕》在白话章回中大量镶嵌诗词,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典雅修辞浪漫言情的书写范式。该体小说正是沿此范式在中西古今的交汇点上再次嬗变。在嬗变过程中,该体小说还从整个古代言情传统中汲取养分,夏志清曾说:“徐枕亚充分利用并发挥中国文学史上的‘言情传统’(the sentimental erotic tradition),这个光辉的传统囊括了李商隐、杜牧、李后主的诗词之作,并《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红楼梦》等戏曲说部名著。我以为《玉梨魂》正代表了这个传统的最终发展,少了那部《玉梨魂》,我们会感到这个传统有所欠缺。”②[美]夏志清:《为鸳鸯蝴蝶派请命——〈玉梨魂〉新论》,《“中国”时报(台湾)》副刊,1981年3月17—19日。另外,因要满足读者兴味娱情及确立小说审美独立性的需要,该体小说还借鉴了一些时新的西洋思想和小说技巧。例如《玉梨魂》中梨娘送别梦霞时唱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诗句;《霣玉怨》中史霞卿大谈西方激进的“不自由毋宁死”言论;《孽冤镜》中王可青引欧西自由婚恋思想来控诉旧式婚制的罪恶。在叙事方式上,该体作品学习西方小说使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由此形成浓郁抒情的自叙传风格;运用倒叙法,形成强烈的悬念以吸引读者;着意于场景描写,形成了大段景物描摹的叙述模式;效仿《巴黎茶花女遗事》《鱼雁抉微》在叙事中穿插日记和书信,等等。整体观之,诗骈化体式使叙事节奏舒缓,抒情性增强,变情节中心为写人中心,形成了哀婉凄迷的风格。此外,该体小说叙事与抒情的文本冲突,落后和先进的思想矛盾艺术地象征着如麻如猬的民初文人心态。这却不期然而然地适应了民初那个新旧杂糅的过渡时代,因而风行一时——有人玩味其绮丽香艳的辞章,有人叹赏其中西合璧的浪漫,有人沉迷其伤心伤逝的氛围,有人在其中觅得坚守旧道德的偶像,有人却恰恰由此产生反抗礼教的愿望。
林纾自清末用古文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大大拓展了古文的疆域。1913年开始他陆续推出多部用古文创作的章回体小说,不期又引出一股章回古文化的潮流。除林纾《金陵秋》《剑腥录》诸作外,姚鹓雏《燕蹴筝弦录》、叶小凤《蒙边鸣筑记》、章士钊《双坪记》等也是民初流行的古文化章回体作品。这些小说总体上是言情与历史题材的融合,林纾所谓“桃花描扇,云亭自写风怀;桂林陨霜,藏园兼贻史料”①林纾:《〈剑腥录〉序》,《剑腥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页。。在运用古文的基础上,该体作品也借鉴了外国小说的一些叙事技巧,从而改变了古代章回体单一的全知叙事模式,注意叙事视角转换;场景、心理描写增多,叙事节奏放缓,增强了主观抒情性,不再以情节叙事为中心,而是侧重于塑造人物;注意叙事时间的变化,倒叙、插叙、预叙与顺序相交织,使文本结构也出现一些新变。不过,由于林纾和其他作者都恪守古文笔法,苛求情中寓史,故而使作品束手束脚,没有产生出诗骈化章回小说那样的强大魅力。
五、古体小说的衰亡及其影响
经民初小说家一番守正出新的努力,古体小说呈现出一时繁荣的景象。可由于遭到“五四”新文学家的激烈批判,其创作开始走向衰落。
“五四”新文学家对用文言写的古体小说批判最烈,认为“《玉梨魂》派的鸳鸯胡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也”②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新文学家提倡“新文化”,主张“废文言兴白话”,自然彻底否定赓续传统的文言章回体、笔记体和传奇体。
以言情为主的民初文言章回体小说最先遭到新文学家否定。刘半农宣告:“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③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号。胡适提出的“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摹仿古人”等④胡适:《寄陈独秀》,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也直刺文言章回小说的要害。徐枕亚、林纾等原以为趟出了化古生新的古今转型之路,本自许著作堪能与古之作家相颉颃,堪与世界文豪竞短长,没料到竟成陈腐典型,革命对象。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行政性地支持“废文言兴白话”,导致文言小说创阅后继乏人。加之文言章回体主题题材单一、后期模式化严重,它在19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成功后迅速消亡。
“五四”后婚姻自主已成社会普遍思想,“五四小说”甚至追求彻底的个性和肉体解放,民初诗骈化章回体小说那种摇摆于自由婚恋与遵奉礼教间的言情书写已失去现实基础。随着《玉梨魂》等作品风行,市场化使得原本富有创新性的文体日趋模式化。对于诗骈化言情作品整体的堕落,不仅新文学家大加鞭挞,就连曾与徐枕亚同为《民权报》编辑的何海鸣也痛批曰:“学之者才且不及枕亚,偏欲以其拙笔写一对无双之才子佳人,甚至以歪诗劣句污之,使天下人疑才子佳人乃专作此等歪诗者,宁非至可痛心之事耶。”①冥飞、海鸣等:《古今小说评林》,第106页。读者对于动辄“嗟乎,伤心人也”“我生不辰”一类的哀伤调子,对于“笔头已深浸于花露水中,惟求其无句无字不芬芳”的词章点染已不再欣赏②范烟桥:《小说话》,《益世报》1916年9月24日。。正如落华所说:“致以骈四俪六,浓词艳语,一如圬工之筑墙,红黑之砖,间隔以砌之,千篇一律。行见其淘汰而无人顾问,移风易俗则瞠乎后矣。”③落华:《小说小说》,《礼拜六》1921年第102期。古文化章回体小说也犯了同样毛病,题材单一且模式化严重,林纾甚至成为新文学家打击所谓“旧文学”的活靶子,而那些“效颦者都画虎成了狗”④朱天石:《小说正宗》,《良晨》1922年第3期。,遭到淘汰成为必然。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民初以文言写章回的文体试验及其试图以中化西的写作实践对于章回体小说的雅化及对新文学的孕育曾做出过一定贡献。它进一步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试探出了小说文体革新的限度。诗骈化与古文化合力推动了章回体小说的雅化,形成了范烟桥所说维新以来重词采华美与词章点染的时期⑤范烟桥:《小说话》,《半月》1923年第3卷第7号。。它们在题材选择和主题表现上还启示了新文学。如《玉梨魂》,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就不得不承认它所记的婚恋悲剧“可算是一个问题”⑥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1919年第7号。,当代学者章培恒认为《玉梨魂》这一类的小说是新文学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性解放要求的滥觞⑦详见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8—600页。。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这部小说首创的“恋爱+革命”模式影响深广,不仅被其他章回体作品所用,还启发了新文学中“革命+恋爱”小说的产生。
民初笔记体小说与传统文化捆绑得最紧,“五四”前后一系列文化、文学、语言的激烈变革都以彻底反传统为鹄的,传统语境消失使该体小说迅速丧失现代转型活力,但源远流长的书写惯性使其一直到20 世纪中叶才彻底消亡。需要注意的是,笔记体小说随笔杂录与讲求实录及朴质雅洁等文体特点,似乎都与讲究结构技巧、虚构的、情感的、审美的西方小说大异其趣。那么,民初笔记体小说坚守的传统书写范式及其现代性探索是否对现当代小说产生了影响呢?据实来看,其文言笔记体的形式虽被淘汰,但其传统书写轨辙一直延伸到当代“新笔记小说”之中。孙犁、汪曾祺等创作的“新笔记小说”就有意识地继承随意杂录、讲求实录的传统,追求朴质雅洁的风格。
传奇体小说因其幻设性、辞章化和诗意美契合了民初小说家对小说文学审美性的现代追求,故而很自然地发生着现代转型。在艺术上,该体小说布局精严,情节曲折;人物形象塑造不重精描细刻,而重传神得态;整体营构出诗般意境空间,召唤读者流连其中;可以起到娱情作用,是作者“畅发好恶”的抒情载体,亦是阅者“钩稽性情”的移情媒介。加之有的作品还融入场景、心理等西方小说技巧,更进一步强化了该体小说的诗意浪漫特征。可以说,传奇体小说在民初已初步完成了现代转型。不过,与其他文言小说一样,传奇体小说在“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后便一蹶不振了。虽然传奇体小说在上世纪中叶以后难觅踪影,但由民初传奇体小说传承下来的传奇性——“作意好奇”的书写本质及浪漫品格——并未随之消失,而是以新的样态和意蕴转化到了现当代诸体小说之中,这已被相关研究所揭示⑧可参看吴福辉:《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东方论坛》1994 年第4 期;逄增玉:《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齐鲁学刊》2002 年第5 期;闫立飞:《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的“传奇体”》,《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8期;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话本体小说在民初之所以还能留下最后一抹余晖,一是因“撰平话短篇,尤能曲写半开化社会状态”⑨凤兮:《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申报·自由谈·小说特刊》1921年2月27日。,一是复古、试验、转型的时代语境使然。“五四”后,在新文学家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话本体小说存在的空间变得更加逼仄,不仅“五四”短篇小说势不可挡地要将其淘汰,白话章回体和新体白话短篇这两种同源小说也在有限的阅读市场上完全遮住了它。随着民初话本体小说的某些创变成果被新体白话短篇吸收,1920年代中期后,短篇白话小说完成了由“说—听”虚拟情境到“写—读”创阅模式的现代转型。至此,话本小说的文体体制彻底终结。
白话章回体小说在“五四”前后已基本完成现代转型,该体作品以切近大众生活的“中式白话”在富有现代性的报刊上叙写市民喜闻乐见的主题题材,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章回小说的四种基本类型,整体呈现出满足广大读者多元兴味、与时流变的通俗性。不过,因其为古体,亦遭新文学家批判。例如周作人说《广陵潮》《留东外史》等在“形式结构上,多是冗长散漫,思想上又没有一定的人生观,只是‘随意言之’……他总是旧思想,旧形式”①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1号。。在这类成见支配下,新文学家不断否定章回小说的价值,以致1947年张恨水发文感慨说:“自五四运动以后,章回小说有了两种身份。一种是古人名著,由不登大雅之堂的角落里,升上文坛,占了一个相当的地位。一种是现代的章回小说,更由不登大雅之堂的角落里,再下去一步,成为不屑及的一种文字。”②张恨水:《章回小说在中国》,《文艺》1947年第1期。实际上,白话章回体非但未像其他古体那样在1920 年代后渐趋消亡,还以另类“白话”“通俗”征服了文化市场和市民大众,甚至影响到解放区文学的创作,出现了《洋铁桶的故事》《吕梁英雄传》那样的作品。在当代,各类型的章回小说仍在持续创作,如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侠小说,高阳、二月河等的历史小说都曾掀起阅读热潮,进而成为被研讨的文化热点。现在方兴未艾的网络小说用章回体创作的各类型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这都证明根植于传统的白话章回体具有与时流变的文体活力,它在当代小说创作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我们对古体小说在民初的繁荣、衰亡及影响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从中可见传统小说文体发生通变的真实过程。清末“小说界革命”以来求新求变的现代性诉求加速了传统小说文体的演变,而民初小说家创作古体小说“不在存古而在辟新”也意欲开辟中国小说发展的新路。民初古体小说创作积极转化古代文学遗产,化用域外文学资源,汲取民间文学营养,曾取得了不少实绩。当“五四”时期古体作品被斥为“旧小说”而遭全盘否定时,其作者坚持认为“中国之旧小说固然有坏处,但须以中国之法补救之,不可以完全外国之法补救之”③胡寄尘:《小说管见》,原载1919 年2 月《民国日报》,见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第9 册,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439页。。中国传统小说文体原是在中华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长的,对此,民初小说家有自觉认识,故希图推动它们完成现代转型。历史证明,他们的观点与实践,为中国小说在古今巨变中避免与阻挡“全盘西化”起到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