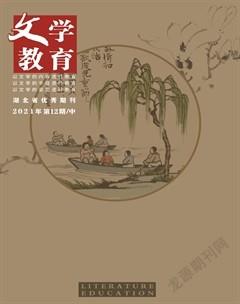写作中的突转艺术
胡敏
内容摘要:突转是叙事性的作品情节设置的常用手法,这种小说情节或人物命运发生突然的转变往往能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审美刺激,同时突显主题。
关键词:突转 写作 技巧
在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往常看到—种令人们拍案叫绝地的富于戏剧性的突然变化,比如说,—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声势浩大的抢劫化肥案眼看即将发生,瞬息之间却改变了性质,抢劫者纷纷排队掏钱,由“劫”变成了“购”(楚良《抢劫即将发生》);一个平时牢骚满腹、玩世不恭的农村远输专业户,在大坝出现险情时,竟会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冲进堤坝泡眼,舍身护堤(陈世旭《车灯》),一个离家才几天,就给丈夫打半小时长途电话倾诉思念之情的女演员,刚放下话筒,却立即投入另一刚刚相识的男人的怀抱(丛维熙《霉雨》)……
这都是“突转”技巧的运用。
所谓“突转”,是指小说情节或人物命运发生突然的转变,而且这种变化是读者和作品中人物始料不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突转”并不等同于—般意义上的转变。可以说,所有的小说情节或人物命运、人物性格,都处在不停的转变之中。就情节而言,或由高潮转入低潮,或由低潮转入高潮;或由紧张变为松缓,或由松缓变得紧张。就人物而言,或由顺境转入逆境,或由逆境转入顺境;……停滞的一成不变人物和情节,在小说中几乎是不存在,然而这种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很早就能感觉到这种转变。而“突转”却与之相反。
一.“突转”是大跨度的转折
“突转”的概念最早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虽然他是针对戏剧而谈的,但在小说中同样适用,尤其是那些篇幅短小、戏剧性很强的性格小说。
在创作中,“突转”运用最早、最多、最好的是戏剧,《俄狄浦斯王》《威尼斯商人》《雷雨》等许多古今中外名剧,都是运用“突转”的典范作品。十八世纪末以后,随着小说结构由故事型向性格型转化,这一技巧逐步被批判地吸收到小说中来,在《项练》《胖子与瘦子》《我的第—个上级》等名作中,“突转”都显示出了它迷人的艺术魅力。
当代小说中,“突转”越来越受到作家的青睐,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不乏其例。
“突转”技巧在作品中的成功运用,能强烈地震撼读者。究其原因如下:
其一,“突转”可以使表面单纯的情节,实际上变得复杂起来,使静止的、平面的情节变得大起大落、摇曳多姿,象流水突然跌下悬崖,激起奇妙壮观的飞瀑。
“突转”可以使人物性格由扁形一跃而成圆形,由单维的低层次进入双维的高层次,成为多样统一的结合体,变得丰满,变得光彩。
“简短”、“单纯”与“复杂”、“丰富”是一对矛盾,“突转”技巧,则是解决这—矛盾的一把钥匙。
我们先来看陈世旭的小说《车灯》。这篇六千多字的短篇,情节十分单纯:新提拔的县长夏邦清下乡指挥抗洪,碰上了中学同学、运输专业户胡月生。胡因自己的意中人嫁了夏而对夏不满,又因自己读了十二年书而仍在农村觉得屈材,便牢騷满腹,怪话满嘴。他明明知道夏县长正在第一线指挥抗洪,却对前来视察的地区专员说“不知道”、“大概没来过”,害得地区防汛指挥部点名通报了夏邦清。谁也想不列,就是这位“老油条”式的人物,在堤坝出现险情时,竟毫不犹豫地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冲进洪水,舍身护堤。
小说至此嘎然收尾,读者的思维却无法煞住。对于胡月生的壮举,他们会想得很多很多!为什么这位护堤英雄在平时反给人一种落后的印象?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客观社会的原因,还是主观性格的因素?这不仅激发读者对小说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更深入地体会、把握,还往往会跳出作品的框框,到广阔的现实世界中去找答案。这就无形中加深拓宽了作品的容量,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使读者对人物从外部和内部全面把握,并不断有新的认识。不难设想,假如《车灯》中砍掉“突转”的文字,情节将会变得怎样单薄,人物也将会怎样的黯然失色啊!卢卡契在评论《十日谈》时说:“薄伽丘短篇小说的结构——是主观的故事的结构,虽然象剪影一样地明了,但也象剪影一样地是静的性格的葛藤。”这间接地证明,在创作中运用包括“突转”在内的一些结构技巧,对于创造复杂的人物性格是多么重要。
其二,在于读者万分惊讶后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发现,从而获得审美快感。
“突转”之所以会使读者惊讶,是因为“突转”所产生的结局往往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那种“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观前文使知其有后文”的情节,自然不会使人惊讶。
另外,从小说的基本构成单位——“场面”来看,“伟大场面十分之八九及由突转造成的。”在这些场面中,除了情节陡折急转,朝着出乎意料的方向发展外,人物也往往亮出他们性格中最隐秘、最主要的那部分,使读者从中有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认识,从而留下最鲜明、最突出、最生动、最深刻的印象。比如《车灯》中胡月生英勇献身后,人们不能不对他的平时的表现重新加以认识,也不能不对自己的看法来个反省,从中一定会有所“发现”。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突转”技巧时,往往和“发现”并举,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不妨再举一例。丛维熙有一篇四千余字的小说《霉雨》,大意是:老导演要拍一部歌颂人间坚贞爱情的伦理道德戏,戏中要求主人公的心胸如同浪花一样晶莹和透明。女演员阿眉恬静文雅的气质和脱俗的仪表一下被老导演看中了。阿眉离家才几天,便给丈夫挂了近半小时的长途电话,畅述别后思念之情,这位老导演“异常欣慰”,觉得自己“眼力深邃”,没有选错人。谁知情节来个“突转”,老导演在屋里听见阿眉挂了长途电话,出来寻她时,却突然“发现”她已和另一个男人搂在一起,用“一团黄黄的”风雨衣挡着,正恣意发泄情欲!这一“发观”,顿时使老导演“一阵胸闷”,差点儿“心肌梗死”!同样也使读者大吃一惊,陷入深深的思考。
二.哲学依据和生活基础
“突转”技巧的成功运用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主观臆造,而有其哲学依据和生活基础。
“突转”的哲学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现象都是复杂多样的,既有与本质相一致的表现形态——真象,也有与本质不相一致的甚至颠倒的表现形态——假象。列宁“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中的表现。”一个本质高尚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以“落后”的假象表现出来;而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以“高洁”的假象表現出来。“突转”技巧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也正由于作者较好地认识处理了这二者的辩证关系。对《霉雨》来说,阿眉对丈夫的难分难舍,软语缠绵,很难说不是为迷惑对方而有意做出的假象。
从读者角度来看,“突转”令人吃惊,在其本质上,是因为它带有偶然性。胡月生假如一直以“英雄”、“模范”、“优秀党员”的面目出现,那么他的献身是顺理成章的事,决不至于使人吃惊;阿眉假如平时作风不检点,或夫妻不和,那么她离家才几天就与人勾搭也是在意料之中,不会使人惊讶。偏偏他们在常态下都以相反的面目出现,这就使“突转”带有偶然的性质。也许有的读者觉得这种“偶然性”不合常理而难以接受,其实这是欣赏水平不高所致。从哲学上说,只承认必然性而否认偶然性,这是机械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因而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的外在条件之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建立在大量的偶然性基础之上,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有些具有生命力的事物在发展的阶段往往是以偶然的形式出现的。
那么,从偶然性极强的“突转”中,能否找到必然的原因呢?应该是肯定的。以《车灯》为例,如果试图从作品中去找“暗示”,那也许会令人失望,即使找出一两句话,也难免失之牵强。但如果跳出作品的框架,将生活和作品结合起来,就会发现“突转”确实含有合情合理的因素。胡月生虽然平时牢骚满腹、玩世不恭,但毕竟生长在新社会,党的教育,正面力量的影响毕竟占主导方面,并且,他平时的所谓“牢骚怪话”,与他爱情上的失意,与对夏邦清的误解,与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的看不惯,有很大关系,并非出于人品本质上的原因。况且,在出现险情的关键时刻,他听到“共产党员留下来”的响亮号召,看到身为县长的夏邦清带头冲上去,他的性格中的正面因素便立即得到升华,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行动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至于“突转”技巧与生活的关系,更是显而易见,我们平常所常见的一些生活现象,如“好心办了坏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祸得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等,都可说明“突转”源于生活。
三.巧设伏兵,欲擒故纵
运用“突转”技巧,首先,必须创造一个特殊的条件。即在读者眼皮底下“设伏”,而读者又不以为这是“伏”,这样,才能使突然暴发的结尾有必然性和震动性。阿眉如果不是远离家庭,如果不是碰上另一个风流哥儿,她的轻浮本性也难以表现出来;胡月生如果不碰上堤坝险情,可能还会继续扮演“老油条”的角色。其次,要千方百计地使读者对“伏兵”暂时地忘却,这样,设伏之后,往往就要用更新奇更富有吸引力的情节把读音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第三,“突转”要符合艺术真实,不能凭空捏造,脱离现实。用奇人怪事、神魔鬼怪拼凑的“突转”,读者在思想、感情上都难于接受。当然,非现实主义的神怪小说等,又另当别论了。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