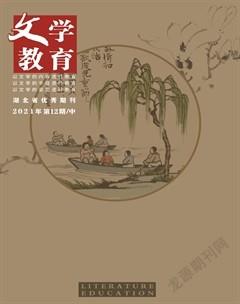康拉德《秘密的分享者》中的异化与成长
何文熙
内容摘要:马克思理论框架下的异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具有扬弃精神的异化。马克思的异化最终目的是消除异化,实现解放与发展。现实主义先驱约瑟夫·康拉德在《秘密的分享者》中暗合了马克思异化发展模式,他描写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异化,并表明了人与周遭、与自我的异化,最终是为了突破异化、找寻自我、解放自我,从而实现自我成长,达到个人追求与社会使命感的完美契合。
关键词:《秘密的分享者》 约瑟夫·康拉德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 成长
异化一词在西方现代文化中通常具有消极的含义,表现为人“失去感知、麻木冷漠、人际疏离”。[1]异化在最初并非表现为与人对抗的关系,而是用来界定人与神、人性与神性相区别的关系。《圣经》中的亚当下贬为人,后来又上升为神,这种脱离人性、神性的过程就是最早的异化过程。在基督宗教神学中,异化表现于人远离了上帝。直到17、18世纪,英法的启蒙思想家们才明确地提出来“异化”的概念,将异化从宗教领域引入了社会文化领域。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异化是转让、让渡,是“个人的自然权力就异化为国家的意志和公共利益。”[2]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始将异化引入哲学范畴。黑格尔认为宇宙万物皆是绝对精神的异化形式,而费尔巴哈则从宗教批判的角度出发,认为宗教中的神是人的异化形式,却反過来压迫、统治人。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有关异化思想中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异化思想中唯物论基础,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他早期的异化理论。他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整个异化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的劳动对象化为商品后,劳动者拥有的劳动产品同自身的劳动付出成反比,即“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这种现象必然导致创造劳动产品的劳动者被剥夺拥有劳动产品的权利,进而受到劳动产品的统治。马克思认为,劳动本质的异化导致劳动者的异化,他在《手稿》中提到“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人回到了野蛮的劳动,并使一部分工人变成了机器。劳动生产了智能,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与痴呆。”[3]46劳动本质的异化从“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异化”、“人与劳动活动之间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直接发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但是,马克思表明,这一过程并非前因后果的关系,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劳动本身是异化的,而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导致了劳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导致劳动异化的罪魁祸首就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同时,马克思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异化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是自我否定、扬弃的过程。他认为扬弃在于把异化中存在的外化复归到自身的对象性运动。这种扬弃本身就包含在异化过程中,是一个主张在异化的过程中消灭异化,现实地占有自己的过程。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者认识到自身被异化,并不得不改变异化的处境时,他们才会打破异化的束缚,实现自我解放。资产阶级创造了私有制,私有制创造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又掘了资产阶级的坟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分裂、复归、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历史往前进步的过程。
欧美文学有描写异化的传统,从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上帝和撒旦,到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中的杰基尔博士和恶棍海德,再到王尔德的《道林·格雷自画像》中的道林·格雷,这些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都表达出作家对异化的思考。20世纪以来,异化主题在现代作品中备受青睐,其主要原因是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现代人在“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4]康拉德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积极讨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不管是《黑暗之心》中揭露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戕害,还是《吉姆老爷》中控诉违背人性的社会理想道德,作品中的主人公都经历了漫长的从自我认识、自我反思到自我救赎这一过程。
他的短篇小说《秘密的分享者》里的主人公、叙述者船长也经历了相似的心灵旅程。这篇小说并非只是简单地描述犯罪与包庇犯罪的短篇小说,也展示了现代生活中的荒凉,贫瘠,与异化。小说的主要情节讲述了一位年轻的船长发现并包庇失手杀人的赛弗拉大副莱格特,最终帮助他逃亡的故事。在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康拉德阐述了叙述者船长与自然之间、与社会之间、与自我之间缺乏交流沟通,导致了船长与它们之间的异化。康拉德通过描写船长与大自然、社会、自我的异化,来表明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规范压抑、束缚个人,人在错误扭曲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实现自我的矛盾,以及个人如何消除异化打破束缚追求自我的过程。同时,通过船长的经历,康拉德还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个观点:异化并不是终点,是扬弃、发展的过程。康拉德在《秘密的分享者》所描述的异化-否定-复归-发展这一模式,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劳动异化的异化、否定、发展模式不谋而合。本文将以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发展模式来分析《秘密的分享者》中主人公的异化与成长,借以表明异化不是堕入谴责的虚无,而是积极的否定,是否定后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成长。
一.个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异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自然界既是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人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同时作为人“精神的无机界”,也是“艺术的对象,是人意识的一部分。”[3]52自然是人实践活动的对象,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3]53因此,自然不免打上了人类意识的烙印。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象化后的劳动逐渐被异化,资本家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控制了用于劳动对象的“固有尺度”。[3]53也就是说,工人按照资本家的意志去改造自然,而人的能动性实践活动成为人谋求基本生存的手段。人所创造世界不能揭示人的本质,反而成为束缚人性的枷锁,也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3]53。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作为劳动改造对象的自然界必然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集体意识,成为了一种异己力量,是一种“主观的自然界,变形的自然界。”[5]
《秘密的分享者》中的自然具有强烈的异化色彩。小说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诡秘气氛,颇具象征意义。康拉德用“荒凉”“不见半点儿人烟”“光秃秃的小岛”“废墟”“硕大无比的苍穹”等词来暗示船长所处的异化的自然环境。[6]船长眼里的大海,是他意识的产物。他认为大海没有生气,大地也是“冷漠的”,在他周遭,没有一件活物可见。视觉上是空茫的,听觉上是死寂的。这里的大自然通常是空洞、无情的,无法与人沟通的荒原。现代派作家笔下的“美丽的大自然消失了,它不再是独立的自在物,而成了人物意识的象征。”[5]8大自然是人生存的基本生活场所,被异化后的大自然与人的失落感、孤独感相互呼应,正如船长在周遭环境中看不到生机一样,他本人也是孤独的。他孤零零地站在甲板上,深感大海的辽阔无边,船只的孤独无助。此处的船长与周围大自然失去了交流与联系。他眼中的大海的诡秘无常,裹挟航船向前,失去了航行目标;而人的命运,神秘未知,个人在命运面前显得茫然无助,没人知道命运的船只驶向何方。
康拉德笔下的自然是充满敌意的,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较量的关系。尽管人在大自然神秘而强大的力量面前通常显得无助,但康拉德在《秘密的分享者》中提出了一种悖论:一方面,大自然残酷肆虐,大多人在自然面前束手无策,一场暴风雨差点儿让塞弗拉上全体成员殒命;另一方面,康拉德借莱格特之手,表明人在自然面前也不是完全被动的。顽强有拼搏精神的人可以抵抗自然的挑衅,战胜大自然。逃犯莱格特具有挑战者精神。他意志堅定,头脑冷静,决断果敢,在危难关头,挽救了全船人的性命。这种大无畏,奋力向前的精神,正是年轻的船长所缺乏的。作为一个刚上任两周的新手,船长毫无经验,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潭,饱受孤独、失落的折磨。这种感受被康拉德以印象式的写作手法,描绘出主人公与自然之间的疏离感,以及人与大自然的陌生感:
高高的海岸线,蓝色背景中,这些岛屿仿佛在一小片、一小片银色的、宁静的水面上飘浮,光秃秃,灰蒙蒙,或是深绿的、圆圆的像一丛丛常绿的灌木。……对于商人、旅游者、甚至地理学家来说,这些都是陌生的,岛上的生活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6]220
这种陌生疏离感直接导致了人在自然面前感到压抑。大自然不再是浪漫主义文学中充满灵性和治愈能力的存在,其色调也不再是明快热烈或鲜活跳动的,而是笼罩在停滞死寂的灰黑色调中,给人带来沉闷压迫感。人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巨大的吞噬感:
万籁俱寂,陆地黑色的轮廓越来越大,越来越浓,我望着可受不了了。我闭着我的眼睛……这片静谧难以忍受。科林道黑色的南岭好似悬在船上,就像那永恒的黑夜的高耸的断片一样。一片漆黑中,看不到一线光亮,听不到一个声音。岛屿不可抗拒地向我们逼来,仿佛我们的手可以摸到它了。[6]227-228
大自然带来的是死亡威胁。文中船长在驶向科林岛途中甚至称他们的航船为“死人之船”,而他们正设法通过阴阳交界地的“艾勒伯斯”之门。[6]228这里的自然异化为死神的象征,随时可能夺人性命。现代派作家笔下的自然是贫瘠的,没有生命力,没有意义的,康拉德本人也认为自然是“碎片化的”、“偶然的”、“暂时的”。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将自然比着“冷漠的机器”,认为“自然创造了时间、空间、痛苦、死亡、堕落、绝望以及所有的幻想——而什么都不重要。”康拉德文中的大自然,不再象征着生机勃勃,不再是人类寻找心灵慰籍的场所。[7]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帝国主义历史浪潮中,大自然也无可避免地贴上了人类贪婪的标签,成为人性堕落的原罪。康拉德丛林小说中的太阳往往象征了殖民者掠夺的资源:黄金、铜、土地。康拉德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对其他不发达国家资源掠夺的基础上。这种文明充满了罪恶,成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诅咒,最终会让“太阳消亡,星星一颗一颗地消亡,整个宇宙将笼罩在冰天动地的黑暗中。”[8]西方殖民者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同时,也改变了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使得西方人困于自己创造的现代工业文明中。虽然殖民国家依靠掠夺的资源极大地丰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形态,但是殖民者自身也越来越依靠殖民体系来进一步掠夺资源,人也逐渐成为了“他们改造了的自然与社会的囚徒。”[8]93康拉德小说中的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异化特征正体现了这种困境,他认为现代西方人失去了文明的照拂,终究会面临这一困境带来的后果。最终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会注视着太阳的消亡,那时的他们中的某个人,会像艺术家一样,或用严肃的反驳,或用冷峻的嘲讽来表达和诠释人类消亡前夕的最后体验。
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异化
社会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集合体,它与个人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两者之间本是健康和谐、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尽管人类历史以来,不乏个人与社会相对抗的例子,但大多是个人命运与具体环境、具体事件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是社会普遍事实。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人人追逐物质满足私利。整个社会成员对私利的追逐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逐渐恶化到无法沟通的地步。社会作为个体关系的集合体,其异化往往是由于个体在社会中的实践结果与个体发展之间产生了相互对立的关系。不过,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异化是无法避免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与社会异化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失效,个人在社会中失去自我选择的自由。尼采的“末人论”也秉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与他人在一起,便失去了自由而异化为没有自我的平庸的“末人”。[9]诚然,在个人社会关系失衡的异化环境中,个人发展与社会整体要求往往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通常要求牺牲个人自我来满足社会的一致性。而个人自我觉醒、自我解放的需求又会与现行的社会规范相冲突,有些甚至会违反社会规范来摆脱社会束缚,以实现自我成长的目的。
《秘密的分享者》中的叙述者船长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船长与社会的关系最初是疏离、缺乏的沟通的。直到他远航前夕,他与船,与船员之间还处于相互陌生的状态。船长与社会关系的异化,首先表现在他与自身社会角色之间的异化。“船长”职务,是社会关系在船上的延伸,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船长能否充分认识以并履行这一义务决定了他能否“完成对个体的社会化”和对作为船长这一社会属性的“认知、认同、选择和扮演”。[10]显然,他并没有很好地理解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对自身的社会属性比较陌生。从船长衡量他“是否有能力从事这番漫长而艰巨的事业,履行我们共同指定的任务”上可以看出,船长与他的社会职责之间不是和谐、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是陌生、割裂的关系。[6]173因此,船长与自身社会职责之间的陌生化导致了他与自身社会属性之间的陌生化。
导致船长与社会关系异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船长与船员关系的异化。社会作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首先由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以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之上的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总和。[10]125因此,船长角色的定位,既由“船长”这一社会职能决定,也由他与这个行业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决定。换而言之,社会职能给予船长社会属性,而同事关系给予船长具体定位。在《秘密的分享者》中,船长与船员之间缺乏交流互动并不合符船长的角色要求。在整体船员面前,船长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认为自己“处于船上唯一的陌生人的地位”。他对手下们了解甚少,甚至从与人目光相遇时,他“即刻垂下了目光”中可以看出,船长是主动地与船员们保持了陌生的距离。[6]174船长最初刻意与船员之间保持的陌生感,是他与他的社会职能之间产生的陌生感在人与人关系上的延伸。在船长眼里,船员们是时刻提醒他自身社会属性的象征。船长与船员们关系的陌生化也是相互的,一方面船长主动将彼此之间的关系陌生化,另一方面,船员们对他们船长的社会角色也不太认同。在形容船员对船长指令的反应时,康拉德时常会用到“惊诧”、“惊异”、“诧异”来形容船员对船长指令的反应;同时,船长也认为在船员的眼里他是不可理解的,“形迹可疑的”陌生人。[6]193
莱格特到来后,船长与船员关系的异化僵局越加白炽化。与主动与船员关系保持陌生的距离不同,这一次船长积极主动地帮助莱格特,认为两人之间有“神秘的沟通——面对着这片寂静、漆黑的热带海洋。”[6]181船长先从形象上将自己与莱格特等同起来,而后发展到从精神上将自己同和莱格特等同起来。他所思所想,与莱格特如出一辙。从某种意义上看,船长主动与莱格特认同的过程,也是他与其他船员进一步疏离、陌生的过程。
不过,船长与他的社会职能、与船员之间关系的异化,并非是徒劳无意义的。在康拉德的时代,资本帝国主义,对金本位的疯狂追求,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扭曲变形,而扭曲的社会对个人的期待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制约力量”,并“限制着角色扮演者的行为。”[10]126在这种环境下,船长深感人命运的不可掌控性,以及社会关系对人强大的束缚力。因此,康拉德在小说一开始让船长与他社会角色之间保持了陌生的距离、与其它社会成员之间也保持了陌生的距离,其意在将船长暂时从普遍的社会规范中分裂异化出来,促使他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觉醒。
三.个人与自我关系的异化
个人自我关系的异化,是现当派文学的重要议题之一。19世纪末,尼采的上帝死亡论宣告了资本主义世界精神信仰的彻底崩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技术、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机器都成为了异化吞噬人性的利器。依照马克思的异化观点,资本主义私有制物化了工人的劳动,劳动产品成为了制约人、反对人的东西。人因此异化为物的附属物,活成了人的对立面。在这个概念下,个人的异化分离为“人与类本质相异化”与“人同人相异化”。[11]“人与类本质相异化”展示的是用非人化来描述人在现代生活中的扭曲变形,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卡夫卡《变形记》、王尔德《道林·格雷画像》、奥尼尔的《毛猿》以及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小说讲述的就是人在欲望、机器、制度的压制下异化为非人,失去自由、人性的过程。
“人与类本质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发生在人不能拥有创造的劳动产品,不得不将劳动产品让渡给“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11]67也就是说,劳动者不能占有劳动产品,劳动本身也不是满足自我需要的自发行动,而是资本家主导的强迫劳动。这种强迫劳动成为个人对抗他人、个人对抗社会的主要原因。因此,从这一层面上讲,个人与自我关系的冲突与异化,实则表现为个人与整个社会规范的冲突与异化。《秘密的分享者》中的船长自我的异化首先表现在他不认识自己。正如他不了解其他船员一样,他对自己也感到陌生。在文中他说到:
让我当时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我是那艘船的陌生人;如果一定要把心里话和盘托出,那么连我对我自己,也多少是个陌生人。[6]174
在这里,船长明确地指出了自己的迷茫。他的孤独感来自于他既不了解他人,也不了解自己。他无法从周围、从船员集体中获取力量,也无法从自己内心、精神中吸取力量。船长受困于环境、也受困于自我的迷失。然而,造成船长迷失的原因却是时代的,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整体悲剧。尽管当时的人们为找寻自我进行了不少的尝试,但是他们始终“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意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4]22康拉德本人对这一点也深有体会,他在致信友人加内特时提到:
我像一个没有上帝的人。我所作所为和整个宇宙没什么关系,普天下的东西像迷雾一样无法触摸。就连写作也容易受到影响,你发现了吗?……所有的形象漂浮在怀疑的海洋中——就连怀疑本身也无法探寻,消逝在不确定的宇宙中。[12]
在《秘密的分享者》中,康拉德通过船长的口吻表达出生存的陌生感、对自我的不确定感。船长感到孤独苦闷,他无法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产生联系,处于一种自我怀疑的状态。再者,船长与自我关系的异化,也表现在他与莱格特的关系上。莱格特与船长之间紧密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船长与自我的异化。莱格特如同幽灵一般地出现,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年轻的船长却找到了熟悉感。他不仅凭直觉邀请身为逃犯的莱格特上船,还让他穿上自己的睡衣,将他安置到自己的睡舱里,认为莱格特“好像穿着另外一套的就是我本人。”[6]184莱格特的到来,将这艘船划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船长和莱格特的世界,一个是两人之外的世界。船长完全沉浸在他與莱格特构建的特殊联结中,分裂出两个自我,一个是受困于船上、经验不足的陌生人船长,另一个是与莱格特高度认同、藏匿罪犯的秘密分享者船长。前者是社会自我,后者是精神自我。莱格特冷静、沉着、决断,船长从莱格特身上看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他说到“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树起自己的理想的人格,对于自己的理想人格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是忠实的?”[6]174当船长惘置法律与道德,包庇莱格特时,他已经选择了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人格。这一选择,将他从社会道德规范中异化出来,从而违背了他的社会自我。不过,船长的行为看似不合规则,却折射出船长和莱格特希望摆脱社会束缚,成为选择的主人。在船长眼里,莱格特虽然失手杀人,但却挽救了整船人幸免于难,这是英雄的举措,是船长希望拥有的精神品质。莱格特也因此成为了船长精神理想的投射,成为船长的秘密自我。
四.异化后的成长
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人与自然、社会、自我关系的异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分工细化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是人的异己面、外在力量控制、反对人的主体性,那么异化对人是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他的异化理论中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异化是“人类社会无可规避的历史过程。”[13]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否定、扬弃,实际上也是不断进步的过程。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发展的必然阶段。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是异化否定-扬弃的最终目标。他相信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了全人类需求,人们按需劳动时,社会也就消除了异化,人也会得到全面的发展,他把这个阶段寄托到未来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里。
同样,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异化主题寻常可见,但是除了揭露批判孤独、荒诞、虚无外,一些作品也注意到异化本身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扬弃作用。这些作品大多遵循着从展示异化(非人化)到克服异化(回归到某种优秀的文化传统或者救助于某种精神)再到重生的过程。艾略特的长篇叙事诗《荒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艾略特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是一片死寂的荒原,只有死而复生后,回归到人性、宗教信仰,人才能得到彻底的重生。《秘密的分享者》中的船长也经历了从异化到成长重生的过程。
船长的成长经历了放弃社会的自我、找到内在的自我、重塑完整的自我这一过程。他放弃社会自我的过程,是同社会关系、同社会关系赋予的自我之间异化的过程。一开始船长并不自信,缺乏领导力,直到莱格特出现后,情况才开始好转。莱格特登船后,船长心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最初的孤独陌生到萌生出帮助莱格特上岸的使命感。在帮助莱格特逃脱追捕的过程中,船长不顾社会道德法律,以及自身的社会职责与全船人员的安危,执意要达成救莱格特的目的。如果说“社会异化是违己而从众从上,遵守社会规范,服从社会意志的社会行为”[9]35,即表现为遵从社会道德和国家法律,那么船长的行为旨在打破这种社会行为,遵从自由意志。无疑,船长救下莱格特,铤而走险地帮助他逃脱是有积极意义的,表明他挣脱异化的自我成长。船长通过从社会道德、法律中分裂出来,实现了自我成长。尽管按照社会道德的批判、国家法律的惩戒,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会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当评价是非的社会规则、法律本身是病态的时候,人“违背社会正确,去追求更为伟大的健康”却是进步的。[14]不过,个体与主流社会异化的过程是孤独痛苦的,会导致个人的人格分裂:人的社会追求与人的自我追求之间的矛盾。船长在履行职责与冒险放走莱格特之间选择了后者,表明他暂时违背社会要求,选择遵从内心,堕入社会道义上的黑暗。此处,康拉德所传达的思想与但丁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人只有经历了内心的黑暗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掌控”。[14]因此,虽然船长异化是孤独痛苦的过程,但是这种孤独痛苦是他成长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阵痛,它虽然置船长于社会道德法律的拷问之下,但又帮助船长打破病态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捆绑,寻找和实现更为健康的自我。
船长找寻自我同他与莱格特认同的过程是一致的。船长逐渐将自己从衣着、背景、经历到精神同莱格特等同起来。这个认同过程,也是船长获得理想人格的过程。船长认为莱格特身上“有种东西,使人无法做评论;一种情感,一种品质。”[6]192从船长和莱格特的关系变化中可以看出,船长获取理想人格的过程,也是莱格特失去独立人格的过程。莱格特从一开始拥有自己姓名的独立人“莱格特”[6]180逐渐背景化为“我的幽灵”[6]186、“我的第二个自我”[6]199、“我身上某种使他想起他正在追寻的人的东西而惶骇”[6]205到“我和我秘密的幽灵如此浑为一体”[6]212,和最终的“我几乎没有想到我的另一个自我”[6]231。船长从最初只是同莱格特衣着、早年经历相似,但莱格特的执着、沉稳、魄力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事”,[6]188到后来在塞弗拉号船长阿却波尔特登船寻凶时,船长对阿却波尔船长的厌恶与莱格特对他的厌恶如出一辙。
对船长而言,莱格特是他理想品格的象征。而这种理想品质明显与当时社会要求不符。他救助、藏匿、放走莱格特的过程,也是他与社会要求渐行渐远的过程,同时也隐喻了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在他迷茫时,莱格特神秘地出现;他藏匿莱格特的过程,是同社会规范象征者的船员们斗智的过程。在与他们较量的过程中,船长逐渐变得冷静、笃定、决断。尤其是当船长面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卫道士塞弗拉船长阿却波尔特,并与他言语对峙时,康拉德对当时社会道德、法律的反思、质疑、嘲讽达到了高潮。船长眼中的阿却波尔特是“无精打采的固执”[6]200、“毫无恻隐之心”[6]201,把人的功劳归结为“上帝的力量”,[6]203习惯于“听命于某种无情的义务”。[6]203从其中可以看出,这些特质与莱格特所展现的理想品格完全相反。因此,船长不惜冒着牺牲全船人的生命危险放走莱格特时,也是船长蜕变重生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这个关键时刻的书写也暗示了船长对当时整个社会规范的最大挑衅。
这场风波之后,船长成功地帮助莱格特逃走,他也获得了自己的理想品质,完成了自我成长的旅程。在处理这场风波的过程中,船长逐渐具备了领导品质,赢回了领导权。他对如何指挥船员、如何处理紧急事件開始变得得心应手。而此刻的船长,与航船、船员之间不再是孤独和异化的状态,而是相互协作、信任的关系。当船长成功地指导船员将船驶出危险之地,他和船只之间实现了“完美的沟通”。[6]232诚然,这里的沟通更是暗示了船长自我成长后,与自身使命感、责任感之间的沟通。因此,康拉德在此处除了批判社会道德规范对人性的束缚压迫外,也指出个人赢得掌控力、获取领导力需要一种由内而外的大无畏精神。这种在关键时刻所展示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也许会“背离社会规则”、会“脱离传统道德、责任评价体系”,[15]但同时往往也能扭转局势,实现更高层面上的解放与成长。对康拉德而言,这种大无畏精神或者说他眼中的理想品质是康拉德式的英雄主义——挣脱病态社会束缚、实现自我成长的反叛精神以及英雄领导下的人类协作精神。
综上所述,尽管康拉德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其《秘密的分享者》以隐喻的方式,展现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異化理论的主要发展历程——异化、否定、消除异化、复归、发展。马克思认为消除异化的方法是提高生产力,丰沛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让人为自己而劳动,从而消灭异化;与马克思给出的解决方式不同的是,康拉德以作家式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希望人可以通过从“异化到奉献”来实现将异化转变为一种积极、推动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的力量,以完成个人的使命,承担更重要的社会责任。[12]26因此,康拉德笔下的异化,并不仅仅是失去,更是获得,他没有堕入异化后的道德与责任的虚无主义,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一种行动力,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赋予了一种责任感。
在这一点上,康拉德不同于多数现代派作家。他们在作品中展示了扭曲、异化、迷失,却很少给出解决方法,容易落入虚无的苦闷。康拉德的表现手法是现代派的,其精神内核又不尽然是现代派的。他目睹了整个现代社会的颓丧,但又寄情于西方传统的英雄主义来拯救所处时代的各种危机。因此,康拉德并不是绝对的悲观主义者,他在描述黑暗、悲观、绝望的同时,也称赞了人的英雄举措,以及人类共同协作的兄弟情谊,认为人类通过英雄行为,可以战胜社会危机,赢得希望的曙光。
参考文献
[1]M.H.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2]关键. 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9-10.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46.
[4]袁可嘉. 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徐立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先锋小说审美批判》,载《云南社会科学》2017(2):180.
[6]康拉德. 康拉德海洋小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7]KENNETH GRAHAM. Conrad and Modernism[A]. In J.H. Stape(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203-222.
[8]ALLEN MACDUFFLE. Joseph Conrad’s Geographies of Energy[J], ELH,2009(1): 75-98.
[9]王海明. 社会异化论[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1):34-37.
[10]任志峰. 角色理论及其对集体行为者的可行性分析[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122-127.
[11]王思鸿.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历史生成与当代价值[D].天津:南开大学,2014:65-67.
[12]IAN WATT. Joseph Conrad: alienation and commitment[A]. Essays on Conrad[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马小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化问题》,载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53.
[14]STANLEY W. RENNER. The Secret Sharer, Nietzsche, and Conrad’s New Man[J]. Conradiana, 2012(2-3): 145 -161.
[15]THOMAS VARGISH. Conrad’s “The Secret Sharer”: A Private Ethics of Leadership[J]. War, Literature &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2010(Nov.):12.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