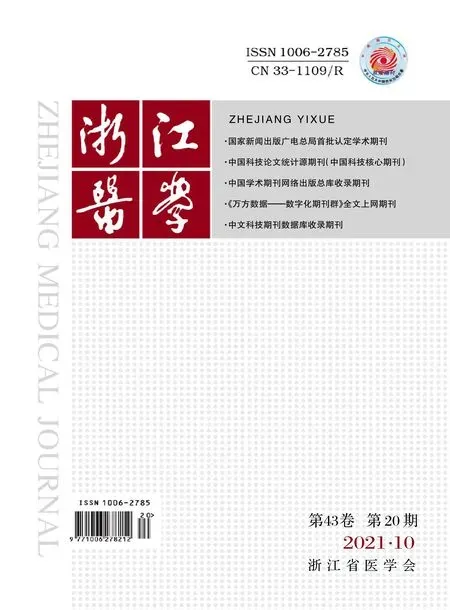治疗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研究进展
尤莎莎 钱申贤
治疗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therapy-relat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t-AML)是原发性肿瘤疾病或非肿瘤性疾病经细胞毒性治疗(化疗或放疗等)后发生的一种罕见而严重的晚期并发症。2016年WHO将t-AML及治疗相关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therapy-related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t-MDS)合并列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的一种单独分类—治疗相关髓系肿瘤(therapy-relatedmyeloidneoplasm,t-MN)[1]。继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secondary acute myeloid leukemia,s-AML)目前缺少明确的定义,通常包括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或骨髓增殖性肿瘤(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MPN)转化而来的AML以及t-AML。t-AML通常预后不良,Ssmra等[2]研究发现,t-AML患者普遍年龄较大,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和无复发生存期(relapse-free survival,RFS)均较差。然而关于t-AML或s-AML的临床数据十分有限,循证证据通常是从相关AML试验中推断出来的。t-AML患者的治疗仍充满挑战,本文就成人t-AML患者的治疗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t-AML的定义
t-AML是AML的一种亚型,是指既往接受过化疗、放疗或免疫抑制治疗后发生的AML[3]。大多数化疗诱导的t-AML病例是由细胞毒药物引起的,这些药物主要分为两种[4]:(1)烷化剂,包括马法兰、环磷酰胺和氮芥等;烷化剂可以共价修饰DNA,导致DNA交联、双链断裂、突变,从而发生细胞毒性反应。研究发现,烷化剂治疗后发生t-AML潜伏期长(约为5年)、细胞遗传学不良,往往预后较差[5]。(2)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包括依托泊苷、阿霉素、柔红霉素和米托蒽醌等。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可阻止DNA链断裂,促进复制过程中DNA解离。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治疗后发生t-AML潜伏期较短(约为1.5年),与KMT2A/MLL-MLLT3等融合癌基因相关,预后较好。治疗强度和/或持续时间的改变以及辅助支持治疗的使用可能进一步增加罹患t-AML的风险。
而其他类别的药物(如羟基脲、生长因子或其他抗代谢药物),很难分析明确的致白血病作用。这是因为大多数患者都选择接受联合治疗,但也可能是因为这类药物本身致病作用较弱。在一项国际多中心、单臂试验纳入的137例具有生殖系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的晚期卵巢癌患者中,有0.8%~2%患者在接受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 1(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1,PARP1)抑制剂Olaparib治疗后发生MDS和/或AML,提示Olaparib可能增加t-MDS/t-AML发生的风险[6]。有研究显示,免疫抑制剂(如硫唑嘌呤)使用后罹患t-MDS/t-AML风险增加(OR=7.05)[7]。
在癌症治疗中,髓系肿瘤的发病率与放射剂量成正比,而在某些疾病背景下,化疗方案中增加放射治疗会增加t-AML的风险。一项国际队列研究亦证实,长期低剂量辐射暴露与白血病发病率之间呈正相关[8]。
2 t-AML的发病机制
t-AML的发病机制可能是通过染色体易位诱导癌基因融合,导致基因组不稳定,或直接选择现存的耐药造血细胞进行克隆[3]。分子生物学研究亦阐明了t-AML的发病途径。t-AML的基因组异常谱与原发AML相似,提示化疗等治疗可能并不会造成全基因组DNA损伤[9]。此外,在最初诊断、治疗尚未开始时,即可在t-AML患者的外周血和/或骨髓中检测到白血病前期异常克隆性造血[10]。
全基因组测序表明,TP53是t-AML患者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9-11]。大约1/3的t-AML和t-MDS患者存在TP53突变。现已证实TP53与白血病的发生和复杂的核型有关,预后不良[12]。Wong等[9]对22例t-AML患者进行研究,有4例在t-AML发病前3~6年,就在外周血或骨髓中发现了低频率的基因突变,2例在化疗开始前就发现TP53突变。没有接受化疗的健康老年人外周血细胞中也可以存在TP53突变。综上所述,化疗可能不是TP53突变的直接诱因,而是其促进年龄相关的TP53突变的造血干/祖细胞进行克隆性扩增。
3 t-AML的预后相关因素
对t-AML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助于临床医师危险分层及治疗方案的选择。与普通AML人群特征一致,年龄、健康状况、细胞遗传学特征和基因突变等众多因素均会影响t-AML患者的预后。Kayser等[13]研究发现,与原发白血病患者相比,t-AML患者发病年龄更大,且更易出现细胞遗传学异常。丹麦的一项队列研究显示,既往罹患髓系疾病、年龄和细胞遗传学是决定预后的关键因素[14]。瑞典的一项研究中纳入了259例t-AML患者,结果显示,t-AML对生存的负面影响高度依赖于年龄[15]。体能状态不佳的患者通常只能接受低强度的治疗方案,且在诱导化疗期间死亡的风险较高。因此,研究发现,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体能状况评分>2分是AML(包括s-AML患者)的不利预后因素[16]。
在2017年版欧洲白血病网(European Leukemia Net,ELN)针对成人AML的诊断和管理建议中,根据细胞遗传学异常和基因突变情况,将危险分层分为良好、中等风险、高风险3个风险组[17]。Dhakal等[18]提出,具有良好细胞遗传学特征t-AML患者一般预后较好,可以采用与原发白血病相似的治疗方法,其在首次完全缓解时是否需要序贯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尚待进一步研究。具有中等风险细胞遗传学特征t-AML患者,建议进行强化治疗或低强度化疗后再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具有高风险细胞遗传学特征的t-AML患者预后极差,临床试验是最佳选择。
4 t-AML的治疗进展
可惜的是,研究t-AML患者的前瞻性临床试验非常少。部分t-AML患者因高龄、合并症多或存在复杂的细胞遗传学改变等特点使治疗方案的选择更为棘手。若有可能,t-AML患者首选推荐参加临床试验。近年来,CPX-351等新药的治疗进展也为t-AML患者创造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但这些选择大多尚未在t-AML患者中验证;t-AML患者的治疗策略仍待进一步的研究。
4.1 化疗 常规治疗方案(conventional care regimens,CCR)包括强化化疗(包括“7+3”方案诱导或大剂量阿糖胞苷)、低剂量阿糖胞苷(low dose cytarabine,LDAC)、最佳支持治疗。大量研究证实,对于年轻、体能状态良好的t-AML患者,更推荐强化化疗方案,包括CPX-351方案或7+3方案(阿糖胞苷7 d联合蒽环类药物3 d)[19-21]。这类人群治疗的目标是通过强化及巩固化疗来获得完全缓解。
CPX-351是阿糖胞苷和柔红霉素的摩尔比固定为5∶1的脂质体制剂。研究发现,阿糖胞苷与柔红霉素的摩尔比为5∶1的时候在体外表现出最大的协同作用和最小的拮抗作用,对AML的治疗效果最佳,且人体可在脂质体注射后24 h内均保持该比例[22]。在Ⅰ期试验证实安全后,CPX-351的Ⅱ期研究纳入了老年AML患者,并将他们随机分为CPX-351组和7+3组。结果显示,CPX-351组的缓解率较高(66.7% 比51.2%,P=0.07),无事件生存期(event-free survival,EFS)和OS未见统计学差异[23]。但亚组分析显示,s-AML患者使用CPX-351有效率增加(57.6% 比31.6%,P=0.06),且OS延长(HR=0.46,P=0.01)。Ⅲ期临床试验纳入了309例60~75岁的新诊断AML患者,再次对CPX-351与7+3方案的疗效进行了比较[24]。研究对象包括t-AML患者、MDS病史的AML患者、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emia,CMML)病史的AML患者、MDS相关细胞遗传学异常的AML患者。既往接受过去甲基药物(hypomethylating agents,HMAs)治疗的患者也符合纳入标准,主要终点是总生存率。所有患者随机接受CPX-351 100 U/m2方案或阿糖胞苷100 mg/m2+柔红霉素60 mg/m2标准诱导方案。研究显示,CPX-351组的OS显著延长(9.56个月比5.95个月),且CPX-351组的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完全缓解伴血细胞不完全恢复(CR with incomplete count recovery,CRi)比率亦高于7+3组(47.7%比33.3%,P=0.016)。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除t-AML外,既往有MDS或CMML病史的AML患者使用CPX-351的OS亦优于使用7+3方案的患者(7个月比 6个月,HR=0.7)。另一项亚组分析显示,在91例进行了同种异体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中,7+3组的100 d病死率较高(20.5%比9.6%),且CPX-351组的OS明显好于7+3组(HR=0.46,P=0.0046)。虽然这项研究并未将CPX-351与7+3方案在60岁以下的患者中进行比较,但根据以上数据,美国FDA批准了CPX351用于18岁以上的t-AML患者或AML伴骨髓增生异常相关改变(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myelodysplasia-related changes,AML-MRC)患者。
Walter等[25]开展了一项研究以分析CPX-351不同剂量的使用疗效情况。实验分为低剂量组(32或64 U/m2)与标准剂量组(101 U/m2)。其中,s-AML患者占总数的55.3%。由于低剂量组中有4例患者早期死亡,64 U/m2亚组被迫提前停止试验,其余患者均接受32 U/m2剂量的治疗。然而,研究显示低剂量组疗效不佳,总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仅为26.3%,中位OS为3个月,28 d内病死率为28.9%。
高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或体能状态差的患者可能无法耐受强化化疗的治疗方案。Canaani等[26]研究发现大剂量阿糖胞苷等强化疗方案对于细胞遗传学不良或继发性疾病的患者获益不大。299例高危MDS和s-AML患者的回顾性分析表明,与未接受强化化疗的患者相比,接受强化化疗的患者总体存活率并没有改善[27]。低强度化疗不但可以限制不良反应风险,同时也为部分患者提供了获得缓解的机会[28]。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了931例新诊断的60~75岁的s-AML患者[29],结果发现使用低强度方案(去甲基药物或低剂量阿糖胞苷)的患者OS优于使用高或中剂量阿糖胞苷为主的强化化疗方案的患者(6.9个月比5.4个月,P=0.048),且使用低强度方案的患者更有可能进行干细胞移植(10.% 比4.3%,P=0.001)。亚组分析显示,t-AML患者使用低强度化疗或强化化疗治疗的OS相似(6个月比 5 个月,P=0.92)。
4.2 去甲基化药物(hypomethylating agents,HMAs) 研究已证实MDS和AML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大量DNA甲基化,对于MDS患者或者不能耐受常规诱导化疗的AML患者,HMAs已成为一种可行的治疗选择。在一项比较单药阿扎胞苷和CCR治疗AML的Ⅲ期研究中[30],招募了488例年龄≥65岁的新诊断AML患者。结果发现,阿扎胞苷组患者比CCR组患者具有更好的OS(阿扎胞苷组10.4个月,CCR组6.5个月,HR=0.85)。该项研究只包括一小部分t-AML患者(阿扎胞苷组8例,CCR组12例)。
另有一些数据表明,t-AML患者的某些突变特征可能赋予HMAs这类药物特殊的敏感性。已知具有高风险细胞遗传学改变和/或TP53突变的AML患者对细胞毒性化疗的反应相对较差,但对HMAs这类药物却并非如此。一项纳入了116例AML/MDS患者的单机构研究发现[31],那些具有高风险细胞遗传学和/或TP53突变的患者在接受10 d的地西他滨治疗后,比那些具有良好或中等风险细胞遗传学特征的患者有更高的应答率,尽管应答持续时间很短。该研究中21例TP53基因突变患者均对地西他滨有效,中位缓解期为12.7个月。但可惜的是,这项研究并未纳入t-AML患者。Calleja等[32]的研究包括7例t-AML和12例t-MDS患者,结果亦发现TP53基因突变与阿扎胞苷的疗效相关。
4.3 新药
4.3.1 B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ell lymphoma/leukemia-2,BCL-2)抑制剂 近年来BCL-2抑制剂在AML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BCL-2是一类可调节线粒体外膜通透性的抗凋亡蛋白。Venetoclax是一种口服小分子BCL-2抑制剂,可选择性地针对AML细胞[33]。Konopleva等[34]进行的Ⅱ期试验中,Venetoclax单药治疗AML总有效率为19%。然而,应答时间短暂,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仅为2.5个月。此外,在纳入该研究的4例t-AML患者中,单药Venetoclax并未显示出抗白血病效果。
研究发现,Venetoclax与低强度的抗白血病药物,如低剂量阿糖胞苷或HMAs联合使用,在不适合强化化疗的初治老年AML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Wei等[35]的研究中,初治老年AML患者接受Venetoclax联合LDAC治疗,CR+CRi率为54%;且在获得CR+CRi的患者中,32%微小残留病灶为阴性。在这项试验中,49%属于s-AML患者;该亚组的CR+CRi率为35%。一项ⅠB期临床试验对Venetoclax联合HMAs方案治疗疗效进行了研究,共纳入145例不适合标准诱导治疗的初治AML患者[36]。所有患者年龄均≥65岁,25%的患者诊断s-AML。结果显示,总CR+CRi率为67%,总中位OS为17.5个月。在s-AML亚组中,CR+CRi率为67%,且应答持续时间和OS更长。基于这些临床数据,FDA批准了Venetoclax联合HMAs治疗≥75岁的新诊断AML或是不能耐受强化诱导化疗的AML。
4.3.2 Hedgehog信号通路抑制剂 Hedgehog信号通路在维持白血病干细胞更新扩增以及促进白血病耐药性形成中起重要作用[37]。Glasdegib可通过抑制Hedgehog途径中关键的smoothened跨膜受体以阻断信号传导。Cortes等[38]进行的一项Ⅱ期研究发现,与LDAC单药治疗相比,Glasdegib联合LDAC治疗显著延长了不适合强化化疗的初治AML患者的OS,且CR率亦更高。因此,FDA批准了Glasdegib+LDAC用于治疗年龄≥75岁、不适合强化诱导化疗的初诊AML患者。正在进行的Ⅲ期临床研究BRIGHT AML 1019中,初治AML患者按是否适合常规诱导化疗分类,之后随机分为化疗+Glasdegib组或化疗+安慰剂组。这项试验纳入了s-AML患者,Glasdegib在这一特殊人群中是否有效,仍有待观察。
4.3.3 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IDH)抑制剂 研究发现,t-AML患者中IDH1和IDH2突变的频率约为10%[11]。Ivosidenib和Enasidenib分别通过抑制突变的IDH1和IDH2促进骨髓分化以减少原始细胞。Ivosidenib的Ⅰ期试验结果显示,Ivosidenib单药治疗复发/难治性 IDH1突变 AML患者,CR+CRi率为30%[39]。t-AML占该总研究人群的9%;然而,这类AML亚组的结果尚未报道。在Enasidenib单药治疗复发/难治性IDH2突变AML患者的试验中,CR+CRi率为26%,中位OS为9.3个月[40]。在这项研究中,t-AML患者占患者队列的2%;但这类亚组的结果也尚未被分析。基于上述结果,IDH抑制剂Ivosidenib和Enasidenib被FDA批准用于治疗复发或难治性AML患者。
4.3.4 Fms样酪氨酸激酶3(Fms-like tyrosine kinase 3,FLT3)抑制剂 25%~30%的AML患者中存在酪氨酸激酶FLT3的激活突变,提示着预后不良[41]。FLT3突变在s-AML患者中发生的频率低于原发AML患者。Midostaurin是FLT3的小分子抑制剂,于2017年被FDA批准与阿糖胞苷和柔红霉素化疗联合治疗新诊断的FLT3突变AML患者。Stone等[42]在一项关键的随机Ⅲ期试验中,纳入了≤60岁新诊断的FLT3突变AML患者。可惜的是,该项研究未纳入t-AML患者。结果显示,与单纯化疗相比,midostaurin联合常规化疗(阿糖胞苷/柔红霉素诱导治疗+大剂量阿糖胞苷巩固治疗)延长了OS和 EFS。
Gilteritinib和Quizartinib是另外两种FLT3抑制剂。Gilteritinib已被FDA批准用于治疗成人复发/难治性FLT3突变AML患者。Gilteritinib的Ⅲ期结果显示,该试验群体的CR+CRi率为21%。此外,在ASH年会上发布的Quizartinib的Ⅲ期试验结果表明,与挽救性化疗相比,单药Quizartinib延长了复发/难治性FLT3突变AML患者的OS。然而,t-AML患者同样被排除在Gilteritinib和Quizartinib的临床试验之外。在常规治疗方案上加用FLT3抑制剂对FLT3突变的t-AML患者是否有益仍待进一步的研究。
4.3.5 抗CD33抗体 正常造血干细胞并不表达CD33,CD33大多由AML患者中的原始细胞表达[43]。Getuzumab ozogamicin(GO)是一种人源化抗体-药物结合物,它将抗CD33免疫球蛋白G4抗体与DNA毒素Calicheamicin结合[44]。FDA批准GO联合阿糖胞苷和柔红霉素治疗新诊断的成人CD33阳性AML患者;GO亦可单药治疗≥2岁复发/难治性CD33阳性AML患者。
在评估GO联合化疗(伊达比星+阿糖胞苷)治疗高危MDS或由MDS演变而来的AML患者的Ⅱ期研究中,CR+CRi率为43%[45],低于其他强化化疗方案所得的CR+CRi率。Burnett等[46]进行的一项Ⅲ期试验显示,在各种化疗诱导/巩固方案中加入GO后,s-AML患者或有高风险细胞遗传学的AML患者存活率或缓解率均未提高。尚不确定在诱导治疗的基础上加用GO的治疗方案对CD33阳性t-AML患者是否有益。
4.4 造血干细胞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HCT)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治愈t-AML的方法,通常适合已获得CR、一般状况良好、有合适供体的AML患者[47]。国际骨髓移植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纳入了545例t-AML和323例t-MDS患者。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35岁、不良细胞遗传学特征、t-AML未缓解或t-MDS进展、供者不是HLA相合的兄弟姐妹或部分或完全匹配的非亲缘供者4个因素与较差的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 OS 相关。具有0~4个危险因素的患者5年OS率分别为50%、26%、21%、10%和4%[48]。此外,研究发现,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巨细胞病毒感染以及细胞遗传学特征等因素均会影响HCT术后患者的OS和无白血病生存期(leukemia-free survival,LFS)[20,49]。Middeke 等[50]的研究纳入了 97例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具有不良细胞遗传学特征的AML患者。结果显示,TP53突变是OS的独立危险因素。TP53突变组患者3年OS和EFS仅有10%和8%。因此,Middeke等[50]认为,TP53突变或可作为预测HCT术后预后的重要工具。
欧洲急性白血病工作组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评估了4 997例HCT术后的s-AML患者[49]。分析显示,2年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发生率、复发率和非复发死亡率(nonrelapse mortality,NRM)分别为33.5%、33.7%和27.5%。2年OS、LFS和无复发无 GVHD 生存期(GVHD-free,relapse-free survival,GRFS)分别为44.5%、38.8%和27.2%。日本的一项研究纳入565例HCT术后的t-MN患者,66%的患者移植时未得到缓解。数据显示,3年OS率为31%,3年复发率和NRM分别为40%和33%[51]。HCT可以提高部分t-AML患者的存活率,然而移植后复发的s-AML患者的中位存活率为4.7个月,2年存活率仅为17.7%[52]。
研究表明,进行干细胞移植患者使用CPX-351诱导治疗可能获益。在比较CPX-351和7+3的Ⅲ期试验中,91例(29.4%)的患者接受了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在t-AML患者亚群中,CPX-351组比7+3组更有可能获得缓解(47%比36%)和进行干细胞移植(37%比27%)[24]。此外,对于已经接受移植的患者,CPX-351组比7+3组OS更长。CPX-351组中移植结果改善的原因尚不清楚。
5 小结
T-AML患者的治疗复杂,需根据年龄、合并症、体能状态、细胞遗传学特征等特点个性化定制。参加临床试验是首选;HCT是唯一可能治愈的方法。对于年轻、体能状态良好的t-AML患者,更推荐强化化疗方案;与传统7+3方案相比,CPX-351方案可显著延长OS并提高缓解率;对于不适合强化化疗的t-AML患者,venetoclax联合LDAC或HMAs方案亦是一种不错的尝试。Hedgehog信号通路抑制剂、IDH1/IDH2抑制剂、FLT3抑制剂、抗CD33抗体等各种新药为t-AML患者方案提供了更丰富的治疗组合选择。新的临床试验也在不断展开,为进一步改善t-AML患者预后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