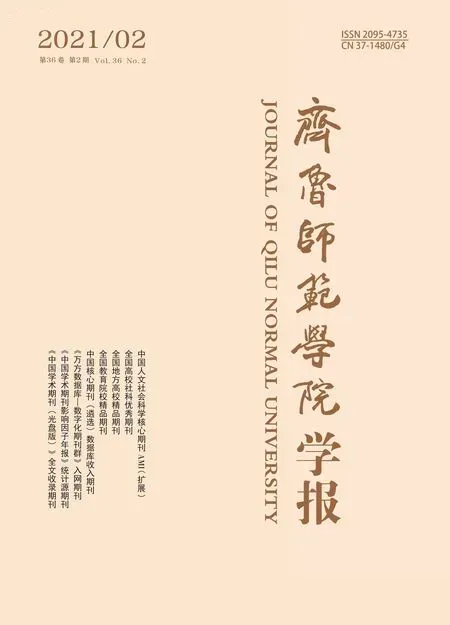《说文解字》从“又”诸字归部理据探索
张明慧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许慎建立的540个部首系统统摄9353个字,《说文》按照某种原则对这9353个字进行归部,使每一字都有部可归。通过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说文》系统中某些字的归部是明确、没有疑问的,包括:(1)单形形声字,即形体中只包含一个义符的形声字,这类字依义符归部,如“江”(从水工声)归水部;(2)同形复体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形体组合而成的会意字,这类字随单体归部,如“聶”归耳部;(3)附体象形字、加体指事字,它们不同于纯象形字、纯指事字,是由义符和非字符号组合而成的,这类字只能依其中的成字义符归部,如附体象形字“果”归木部、加体指事字“本”归木部;(4)变体字,包括反文、倒文等,这类字一律随正体归部,如“乏”(反正为乏)归正部。以上四类是可以明确归部的,还有一部分多义符合体字,如多形形声字、异形会意字、亦声字等,这些字的形体中往往包含多个义符,因而理论上可以取任一义符归部,但《说文》选取某个义符进行归部的原则是什么,许慎并未言明,我们只能根据《说文》实际的归部材料进行研究追索。
《说文》中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由同一个义符参构的一组会意字并非被归入同一部,而是分散归入了各个不同部中,如从“又”的一组会意字在《说文》中并非同归又部,而是被零散归入22个不同部中,这不仅与《说文》所言“凡某之属皆从某”的说法相悖,且不同于同义符的形声字(单形)都归入一部的归部原则,这种归部现象,如果不是许慎随意为之,那么一定是另有原因。段玉裁、王筠认为会意字按“所重”条例归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义有所重”说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首先是运用该说去衡量会意字的归部时会遇到许多问题,如某些会意字的义符并无主次轻重之分、某些会意字并未按照“所重”义符归部等[1]20。王智群同样指出该说作为会意字的归部标准来说不可行[2]101。刘忠华先生认为“义有所重”说从偏旁与字义的角度看待会意字的归部,不合《说文》的归部实际[3]133。从当前的研究来看,“义有所重”说缺乏普遍适用性,不会是会意字归部的通例。在此基础上,刘先生提出要“抓住与会意字一起归部的一组字的共同字义特点来考察会意字的归部”[4]15,而不是偏旁与字义的关系。我们认为,刘先生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是极为正确的,打破了“所重”说的局限性,是研究《说文》会意字归部问题的突破口,但由于《说文》有一千多个会意字,逐一分析较为费力,因此这个观点尚未有详细充分的字例来佐证。而研究会意字归部的重要材料之一就是同一个义符参构的一组会意字被《说文》分别归部的一组字,但学术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不够。因此本文将以从“又”的一组会意字材料为例,对其归部理据依次进行分析,“根据《说文》部内字‘以类相从’的编排原则,抓住与会意字一起归部的一组字的意义关系和特点来考察会意字的归部”[3]133,以求探索多义符合体字的归部原则。
大徐本《说文解字》从“又”作义符的字61个,其中归入又部者27个,包括单形形声字6字、亦声字1字、纯表意字18字、注阙字2字;归入其他各部者34个,包括12个部首字、22个部属字(其中多形形声字4字、纯表意字18字)。单形形声字依《说文》体例只能按义符“又”归部入又部,12个部首字的设立是为了统辖它字,这里不作立部原因的分析。多形形声字、合体表意字、亦声字由于存在多个形符,从理论上讲归部不定,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又部18个纯表意字、又部1个亦声字和2个注阙字、其它诸部18个纯表意字、4个多形形声字的归部理据。
一、又部纯表意字的归部理据
1.“及”(逮也。从又从人)。按,“及”字造义为用手抓住人来表示“追上、赶上”。“及”与形声字“曼”(引也。本文按,用手提物)排列在一起,4字共同的意义特征是以手抓取某物,而形声字“曼”只能取义符又归部。可见,将“及”归入又部与“曼”类聚,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2.“㕞”(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彗”(掃竹也。从又持甡)、“秉”(禾束也。从又持禾)。按,“㕞”字义为手持巾布以擦拭、“彗”字表示手握竹以拂扫、“秉”字字义为手握禾束,3字与形声字“”(又卑也。本文按,用手自高取下)、“叔”(拾也)、“曼”(引也)排列在一起,8字同属以手抓取物件的手部动作类,将“㕞”归入又部与形声字“叔曼”类聚,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另,“㕞”字同样可以与巾部形声字“饰”(㕞也)、“㡨”(拭也)等字类聚,归入巾部。3字共同的意义特征是以巾布擦拭,将“㕞”归入又部或巾部都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说文》一字只入一部的原则决定了“㕞”没有在巾部重出。此外,与“秉”字造意相同的“兼”(并也。从又持秝)之所以归入秝部实际上也是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详见后文分析。
4.“反”(覆也。从又,厂反形)。《说文通训定声》:“反,谓覆其掌。”[5]391按,即翻转手掌。“反”与形声字“叔曼”排列在一起,同属手部的动作义类,将“反”字归入又部而与“叔曼”等字类聚,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5.“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按,“右”即以手口助人,着眼于手部动作。又部所辖字中,大部分表示手的动作,如“叔”(拾也)、“取”(捕取也)、“”(又卑也)等,“右”字与以上诸字排列在一起,同属手部的动作义类,将“右”归入又部而与“叔取”等字类聚,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同时,“右”字在口部重出,详后文分析。
6.“厷”(臂上也。从又,从古文)。按,“厷”字的两个义符分别是又和古文,是臂上之形,如果没有表示手的象形字来烘托,则不知为何物。“厷”字属于附体象形字,由成字部件“又”与非字构件“”组合而成,按《说文》体例只能归入又部,遵循了“据形系联”的原则。
7.“叉”(手指相错也。从又,象叉之形)、“㕚”(手足甲也。从又,象㕚形)。按,“叉”“㕚”二字所从之“又”是手之形,叉中的一点及㕚中的两点是用来提示字义的非字构件。“叉㕚”属于加体指事字,由成字部件“又”与指事符号组合而成,指事符号属于非字构件,按《说文》体例只能归入又部,遵循了“据形系联”的原则。
8.“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徐锴《系传通论》:“又者,手也:|,杖也。举而威之也。”[6]412按,“父”的小篆字形像一手形举杖,和“厷”字一样属于附体象形字,其中的“杖形”是非字构件。按《说文》体例只能归入又部,遵循了“据形系联”的原则。
11.“友”(同志为友。从二又)。按,该字字形从二又,《说文》同形复体字随单体归部,“友”字归入又部,遵循了“据形系联”的原则。
12.“燮”(和也。从言从又、炎)。按,“燮”之和为和谐、调和义,徐灏《段注笺》:“戴氏侗曰:、、燮,实一字。之譌为辛,辛之譌为言也。灏案:戴说是也。盖‘’为烹饪熟物之称,从又持二火,会意,羊声。引申为调和之义。”[6]413可见,“燮”是由“”演化而来的,但它已经与“言、又、炎”三个构件找不到什么字义上的联系了,与言部、又部、炎部字均不类,但《说文》是一个完整封闭的系统,许慎不会让任何一字游离在系统之外,因此他只是从可供选择的三个部中选择了“又”进行归部。
二、又部亦声字及注阙字的归部理据
2.“叜”(老也。从又从灾。阙)。按,《说文通训定声》:“叜,即搜之古文,从又持火屋下索物也。会意。为长老之称者,发声之词,非本训。”[5]398许慎没见过甲骨文,而以“老”为本义,故不知“叜”两个构字部件与字音字义有什么关联,所以他只能按照字形结构归部,而《说文》并无灾部,因此“叜”字只能“据形系联”归入又部。
3.“叚”(借也。阙)。段注:“谓阙其形也。其从又可知,其余则未解,故曰阙。”[7]463按,借的动作与手有关,但从形体上看,许慎仅能看出“叚”字形其中有“又”,其余构件则不知所象何形,因此注阙。因此“叚”字只能“据形系联”归入又部。
三、从“又”字多形形声字的归部理据
从“又”字的多形形声字共有4个,分别是“疌”(止部)、“”(止部)、“”(寸部)、“䅓”(部)。
四、从“又”而未入又部表意字的归部理据
《说文》中有18个既未归入又部,又非部首字的从“又”的表意字。分别是“丈”(十部)、“隻”(隹部)、“雙”(雔部)、“兼”(秝部)、“奪”(奞部)、“矍”(瞿部)、“㘝”(囗部)、“帚”(巾部)、“灰”(火部)、“”(炎部)、“奴”(女部)、“亟”(二部)、“侵”(人部)、“圣”(土部)、“妻”(女部)、“爵”(鬯部)、“蒦”(萑部)、“右”(口部)。下文逐一分析这18字的归部理据。
1.“丈”(十尺也。从又持十)。按,“丈”为量词,是一种长度单位。《说文解字注》:“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7]353“丈”字与“千”(十百也。本文按,数词)字类聚,二字同表数量单位,取共同的义符“十”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2.“隻”(鸟一枚也。从又持隹)、“雙”(隹二枚也。从雔,又持之)。“隻雙”二字分别归入隹部、雔部。
刘忠华先生说:“‘隻’表示‘隹’的计量单位,‘隹’是‘隻’的计量对象。二者构成一个计量事件,字义关系密不可分。”[8]66可见“隻”归隹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雙”字与“靃”(飞声也。雨而双飞者,其声靃然)同归雔部,“雙靃”二字共同的意义特征是二隹,重在二鸟并列,取共同的义符“雔”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对于此二字的归部分析,刘忠华先生已有专文详论,我们十分赞同刘先生的观点,此不赘述。
3.“兼”(并也。从又持秝)。秝部只辖“兼”字,“兼”字字义为“并”,《说文》:“一曰从持二为并。”可见“兼”字字义特点为并持二禾,与单纯表握持义的“秉”不同,因此无法归入又部。刘忠华先生说:“‘兼’与‘秝’是动作与其特征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8]66可见将意义关系密切的“兼秝”二字取共同的义符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4.“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从奞)。按,“奪”字字义为鸟从手中飞走了,奞部只辖“奪奮(翬也。按,即鸟在田上大飞)”二字,共同的意义特征是鸟飞翔。取共同的义符“奞”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5.“矍”(隹欲逸走也。从又持之)。按,瞿部只辖一字“矍”,“瞿”《汉语大字典》训为“惊视貌”[5]2517、“矍”《汉语大字典》训为“惊慌四顾貌”[5]2520,二字共同的意义特征为惊慌,且“矍”与又部表手部动作的字不类,专立瞿部统辖“矍”字,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6.“㘝”(下取物缩藏之。从囗从又)。按,“㘝”字义为向下取物并将物围藏起来,与形声字“囹”(狱也)、“圄”(守之也)、“固”(四塞也)、“围”(守也)排列在一起,共同的意义特征是围困,将“㘝”字与“囹圄固围”等字类聚,取相同的义符“囗”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7.“帚”(糞也。从又持巾埽冂内)。徐锴《说文系传》:“扫除曰糞除也。”[6]1054按,“帚”义为扫除。“帚”字与形声字“㡨”(拭也)“饰”(㕞也)类聚,3字共同的意义特征是扫除污垢,取相同的义符“巾”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8.“灰”(死火余㶳也。从火从又)。按,“灰”即火烧尽后所剩下的余灰。“灰”与形声字“炦”(火气也)、“炱”(灰,炱煤也。本文按,即火生发出的烟尘)排列在一起,同属火焰生发之物,3字取相同的义符“火”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0.“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奴”字与形声字“㜎”(女隶也)、“婢”(女之卑者也)排列在一起,3字共同的意义特征是奴隶,取相同的义符“女”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1.“亟”(敏疾也)。“亟”字指人之敏疾,引申为屡次、一再,指的是反复不变的行为。与二部“恒”(常也,按,指恒常不变)、“亘”(求亘也,按,指回旋,引申为连绵不绝、恒久不变)排列在一起。“亟恒亘”3字共同的意义特征是恒常不变,取相同的义符“二”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2.“侵”(渐进也)。林义光《文源》:“(侵)象埽者持帚渐进,侵迫人也。”按,“侵”与形声字“傍”(近也)排列在一起,共同的意义特征为靠近、迫近。二字取相同的义符“人”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3.“圣”(汝颖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按,“圣”字义与“掘”同,为挖掘之义,大概是居住在汝水与颖水之间的人们所说的方言,所谓“致力于地”就是指在土地上用力挖掘。“圣”字与“垍”(坚土也)、“埵”(坚土也)、“埐”(地也)等字类聚,属于动作与动作的对象,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事件。4字取相同的义符“土”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4.“妻”(妇与夫齐者也)。按,“妻”字与“嫁”(女适人也)、“娶”(取妇也)类聚,3字字义关系密切,“妻”为事件的主体,与“嫁娶”共同构成了一个婚嫁事件,3字取相同的义符“女”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5.“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按,鬯部辖“爵”四字,“”(芳艸也),是一种香草,是酿造鬯酒的原材料之一;“”(黑黍也),用黑黍酿造出的黑黍酒同样也是制造鬯酒的原材料之一;“”(列也),《说文解字今释》:“,酒气酷烈。”[6]689指鬯酒散发出的酒气;“爵”为盛放鬯酒的礼器。4字字义关系密切,共同构成了一个酿制鬯酒的事件,取相同的义符“鬯”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6.“蒦”(規蒦,商也。从又持萑。一曰视遽皃。一曰蒦,度也。)。“蒦”另一字义为“视遽皃”,即惊慌四顾的样子,与部首字“萑”(鸱属)字义关系密切,属于动作与动作的主体,二字共同构成了一个萑鸟惊慌四顾的事件。“蒦”字取义符“萑”归入萑部,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
17.“右”(助也,从口从又)。“右”字在口部重出。按,口部所辖字众多,多属口腔器官、话语、呼吸等义类,“右”与口部部内字均不构成同义类关系,许慎“只是出于入部的需要,从可供选择的两个义符中选择了‘口’进行归部罢了”[9]58。“又”字字义由“手口并用以相助”会意而成,可见“右”的两个义符并无轻重主次之分,按理说归又部口部皆可,因此会出现“右”字在口部重出的现象。段玉裁认为“右”的字义所重在“口”,强调“手不足,以口助之”[7]58,又部所辖“右”当删,不妥。“右”归又部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不可将其删除。
本文分析了43个从“又”做义符的字,其中有32字的归部遵循了“以类相从”原则,占比约74%。由此可见,多义符合体字归入何部主要是由“以类相从”原则决定的,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从“又”的一组会意字被零散归入22个不同部中的现象。少数字由于自身字形特点和《说文》部首字的制约,按照“据形系联”的原则进行归部。如“厷父叉㕚夬友”6字的归部是由于自身形体只有一个成字义符,“”归又部是因为另一义符并非《说文》部首。总结来看,“以类相从”是许慎对会意字选取义符进行归部的基本原则,对某些字形受限的字采取“据形系联”的方法进行归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