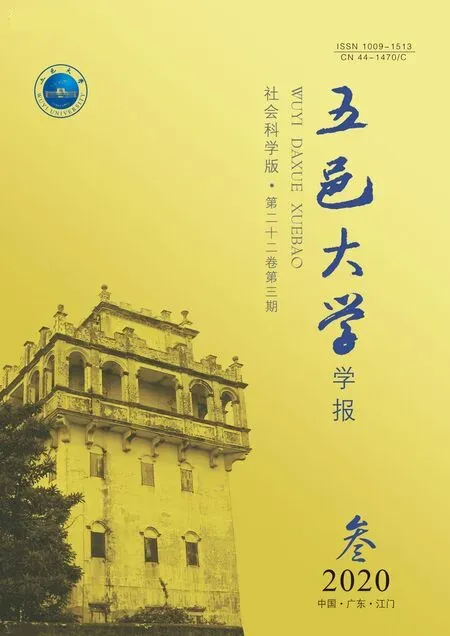民国时期侨乡女性社会状况探讨
——以台山、开平侨刊为主要史料的分析
姚 婷
(五邑大学 广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江门 529020)
近代以来,中国侨乡逐渐形成。伴随着人员在侨乡和海外之间往复流动的是物质、资金和信息从海外向侨乡的输入,这使侨乡民众的衣食住行和民间习尚发生了变化,侨乡呈现出与邻近的传统乡村不同的文化面貌。[1]中外文化融合的碉楼、商业繁荣的侨圩、“半唐番”的侨乡方言……都展示着侨乡的社会转变。处在侨乡社会中的“人”,也在受着这种社会转型的影响,并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社会转型中的一环。侨乡女性即是如此。她们在扮演传统分配给她们的“贤妻良母”角色的同时,又努力填补着由于大量男性出洋而留给家庭乃至社区的空缺,独立地处理或参与其中的种种事务。
20世纪30年代,陈达指出粤东和闽南侨乡(其在著作中并未使用“侨乡”一词,而以“华侨社区”称之)的女性当家是常见之事,当家女性要承担起家庭经济、儿女训诲、社交及家长所应负的责任,这使女权得以伸张。同时,侨乡民众对于女性嫁给华侨,持矛盾心理,既羡慕华侨的富裕,又忧虑此种婚姻的不稳定。[2]谭雅伦分析近代四邑侨乡中的很多父母乐意将女儿嫁给有较优裕物质基础的北美“金山客”,形成“钱人交换”,但这种婚姻带给女性精神上的折磨。她们是丈夫缺位的家庭中的主力,但一般教育水平不高,继承重男轻女的“妇道”思维,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只能以歌谣发泄孤独和悲怨。与此同时,在海外华人社区流传的金山歌谣也反映了华侨还乡的心愿之一是回乡之后娶一个年轻女子,以补偿其逝去的青春和多年的辛劳,这便形成了侨乡的“嫁老郎”现象,是中国传统的男权意识的体现。[3]沈惠芬认为海外移民并没有改变侨乡的儒家文化传统,甚至儒家文化传统还是海外移民的精神寄托。海外移民依赖儒家文化延续家庭,使妻子服从丈夫和家庭,并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这种观念。而华侨妻子在照顾家庭、延续家族、参与社会发展方面则发挥极大的作用。[4]她们并非被动、消极地陷于“守活寡”的婚姻形式里,也以自身的智慧和策略积极应对恶劣的环境以更好地存活。[5]
侨刊是从侨乡向海外华侨传播信息的媒介,其创办人、发行人、撰稿人基本是男性,受众也以男性为主。这种信息传播的性别构造在近代是正常的,毕竟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女性群体处于失语的状态。[6]而男性的女性观和女性的女性观是不同的,两性在对待女性的恋爱、婚姻、家庭、独立、平权等方面的态度和要求都有差异。[7]本文以江门五邑侨乡中的台山、开平出版的侨刊为主要史料,分析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侨乡女性的社会状况,包括她们的教育发展、职业选择和家庭地位等,及其中所透视的男性视角。
一、在兴女学的呼声中缓慢发展的侨乡女性教育
始自清末,华南侨乡的知识分子便极为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台山《新宁杂志》在创刊首年——1909年,便有专门讨论兴女学的文章,从国家、地方社会、男性与家庭的角度论述兴女学的必要性。如有人提出,从国家来说,“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中国日被他国所凌辱,与“国民之母者之无学”不无关系。从男性来说,“女子不学,则不独不能为男子之助,又从而牵累之,琐屑细故,扰及清思,血汗生涯,仅供坐食”。从侨乡当地社会来说,“闻学堂不信菩萨,竟阻其子求学矣。……若夫因负气而轻生,泥陋俗而不革,此皆由于女子无学之所致也”;而台山出洋人多,“若使女学既兴,则书信之往来,数目之登记,不知其若何便捷也”;再者,女子久居学校,可以革除早婚之害,有益于母健儿肥。[8]又有人认为,在种族方面,因为“我汉族女子,素不解教育为何事。何为卫生,何为体育,何为胎教,何为女子之职任,何为保种之机能,均懵然不知”,因此要急兴女学,以图种族之幸福。在国家方面,“是知国民良否,系于母教,而养成母教,端在女学”;而且女性有了知识,还可以参加国家建设,促进国家经济与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方面,由于长期女学不兴,女性整体迷信、愚昧、无知;如果女子接受教育,她们便能参与改革社会陋习。[9]诸如此类的论述表明了清末侨乡知识分子对兴女学的意识与认知,这些呼声也推动了清末及至民国时期女学在侨乡的兴起与发展。但这些由男性发出的声音,只关注兴女学对国家、社会、种族、男性的益处,却忽略了女性自身对教育的诉求。
在兴女学的呼声发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台山、开平一带的女子教育尚是缓慢发展。直到1926年,台山县立中学校开始兼收女生,开男女同学的风气,随后成立台山女子师范学校。即使如此,台山普通初中的女子教育发展还是远落后于当地社会的需要。[10]20世纪30年代,台山《居正月报》曾刊登《台山最近教育状况统计》,记载:“中等学校七间,四三班,男一五五八人,女生一六○人,总数一七一八人。师范学校五间,三一班,男生六五○人,女生五五六人,总数一二○六人。(小学校)初级小学七八九间,八八八班,男生三六一二○人,女生八三二七人,总计四四四四七人。高级小学七九间,八三班,男生四○○○人,女生一五○人,总计五五○○人。①完全小学二三七间,三三七班,男生七三二三人,女生三一七三人,总计一三四九六人。②幼稚园一间,三班,男生六○人,女生四○人,总计一○○人。职业学校三间,一四班,男生四一七人,女生三人,总计四二○人。”[11]可见,在所有阶段的教育中,男生人数都多于女生人数;除了师范学校和幼稚园的男女生人数相差不大,其他都有较大差距,差距稍小者如完全小学,男生人数也为女生人数的2倍多,而中等学校的男生人数几为女生人数的10倍,职业学校的男女生人数比更是达到139∶1。女子教育的普及度远不及男性。实际上,当时侨乡民间尚有不少抱持传统封建思想、食古不化者否认女子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台山县立中学校有一位学生写过一篇小小说,主人公是一位12岁的姑娘,其父是美洲归侨,“但对于美洲的文化,倒没有一点感受。……他偏倡孔老夫子的道理:男女是不同的,授受都该不亲”,因此女孩的父母虽然极爱女儿,却始终不肯让她上学,固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直至女孩坚持争取,又得叔叔帮助劝说父母,才能圆了上学梦。[12]这篇小小说表明,即使从西方国家归来的华侨,也不必然有开放的思想,而这又与侨乡内部观念之开放互为影响。有一个学生在总结其所在学校的救亡工作团1938年暑期工作时提到,他们排演的一些戏剧,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比如没有女孩子愿意扮演母亲的角色,作者推测这“大概是文化落后,民众闭塞的缘故罢”;更没有女孩有勇气扮演被日军凌辱的角色,“在旧礼教的枷锁还没有彻底解除的本乡,是大大不容的”,即使由男孩出演这个角色,并避免了一些敏感演出,还是“遭受少数观众的恶评”。[13]侨乡对于与封建礼教和已有的民间认知相左的行为,同样会产生批评性舆论,女性便是那些舆论首当其冲的承受者。因此,即使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侨乡女性,大多数还是依社会认可的传统道德规范行事。
二、基于家庭角色分工的侨乡女性职业选择
民国时期,女性教育的逐渐普及、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经济的变化,都使愈来愈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谋职,或获取独立的经济地位,或帮补家中的生活。关于女性应该在职业和家庭间作何取舍及女性应从事何职业的讨论也因此在国内持续不断,其中有对“娜拉精神”的肯定或批评,也有对“贤妻良母”定位的支持或反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学家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写道:“新妇女虽然都是具‘超于贤母良妻’的人生观的,但贤母良妻的知识,似乎应当知道。失却母性的女子,或不知怎样做女子的女子,说她便是能尽‘超于贤母良妻’之责任的人,这一定是欺人的话,信不得的。”“受到高等教育的女子,自然是优良孩子的最好的母亲,她若牺牲了这光荣的职责,便是她对社会不能尽她底唯一的义务了。”[14]即使社会已经为女性就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而且一部分女性已经具备从业的资格,但传统的社会分工和刻板的性别角色要求却令大多数女性在婚后以做“贤妻良母”为己任,由此而致的是她们独立的经济地位的丧失和对男性的长期依附。
侨乡独特的经济来源方式,使那些丈夫在海外谋生的女性更缺乏从事职业的动力和必要。当时有知识青年批判说:“讲到台山女性的职业,除掉少数跟男子一样工作的农妇,和少数受过较高等教育的智识分子以外,简直没有独立的‘女性的职业’可言。这因为:第一件她们多数未受教育,智能薄弱;第二件她们有的是华侨血汗换来的洋钱,经济问题可以解决”[15]。
这个时期,侨乡女性不是没有从事职业者,台山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陈婉华就是一个典型。但如陈氏这般的职业女性在1949年前的五邑侨乡实在有限。当时女子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学校教员,这是社会认可的职业;而在更多的职业领域里,女性遭到了恶性排斥和打击。1947年,《新宁杂志》刊登一篇题为《女掌柜》的杂文,以广州的故事讽喻台山女性职业情况。文章写道,不仅娱乐场所和餐室的女侍多了,连西药房和百货公司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司数之职,这“掌柜权力是在各伴伙之上的,在各伴伙之上的掌柜而有女人为之,女权的发达,不可谓之不大了”,“然而这是不移的事实,脸儿不漂亮的女人不会做掌柜,做了掌柜的女人没一个不是抹粉涂脂,打扮得牡丹花一样浓艳。”[16]这便暗示了女性获得掌柜职位不是靠才能,而是靠容貌。这般不尊重乃至侮辱女性的文字,宣泄了男性因无法遏止女性从事职业的趋势而产生的不满及他们对女性职业能力的不服,也显露了侨乡男性所持有的对女性职业种类和职业地位的偏见,以及女性谋求职业自立之路的不易。
同样的职业偏见呈现于对女性出洋谋生的批判上。1926年的《溯源月刊》登载过两篇与女性出洋谋生相关的族闻,内容相类。如《得意而往者失意而返》的女性主角被作者称为“一般无知妇人”,并被“推其意,以为居家捱苦食贫,旅洋佣工,定可得达其发财之目的”。当她们因“人地生暴,谋食艰难……垂首丧气而返”时,作者庆幸:“此后该族妇人对于飘洋一事,或可不禁而绝也。如此未始非该族之幸欤!”[17]“不禁而绝”一词,说明当时台山乡村宗族是不赞成女性出洋谋生的,她们一旦逾越社会分工的界线,则被认为是异常的社会行为,遭到否定和谴责,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支持。
三、独立与依附并存的侨乡女性家庭地位
由于男性旅居外洋,留守的女性便成为家中的主事者,这在民国时期各侨乡中是大致相同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的台山籍大学生如此描述当地女性:“台山,因为华侨的向外发展,居乡的成年人,女性人数,约多于男性一倍。因为这个缘故,女性在台山社会,便占至重要位置。……我们的华侨,多役隶于相隔万里的资本主义新进国里,一去十年八年,回来歇下一年两年,便又为生活的驱策,不得不再跑向海外去,幸而满载荣归,得享余年,但都已老朽龙钟,行将就木了。因此一般所谓‘金山婆’,除掉处理自己的家事以外,还要参加其他的社会工作。像作者生长的都斛区,有些乡村,从前怕贼的时候,妇女们要轮流去看更守夜;有些乡村里的一切大事,要取决于太太团。这便足证明我们台山的妇女不但治内,又兼治外了。”[18]1949年台山西村黄宗望祖房一众耆老给台山县新白沙乡西村堡自治会的一份呈文也提及女性在侨乡社会的作用:“况我乡族男性大多外出,仅留妇女主持家政。”[19]侨刊经常刊登的华侨从海外发回的声明,也显示女性对家政的主持。如华侨李奕瑶1927年的一则声明,开头即说自己“远离家乡旅居外洋,一切家务,交由妻室萧氏主理”。[20]20世纪20年代初华侨陈光锦寄信给家中的两个女儿陈逢清、陈逢春,信中每每告诉她们,付来银两,以作家用。[21]可以推想,此姊妹二人亦是家事的管理者。当家庭出了事故,出面处理的也经常是女性。有一则新闻说一个30余岁的妇女因被人疑为盗匪而遭拘拿,但事实是她的儿子被匪掳去,而她带银前往赎人。[22]
显然,侨乡特殊的人口结构和家庭形态将很多女性由家内推向家外,代表家庭对外进行社会交往,参与处理乡族事务,甚至履行本应由男性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在男性缺位的家庭中,她们是“一家之主”,并由此养成独立的处事能力与态度。
然而,应该看到,侨乡女性主理家政、“一家之主”的地位和权力不是社会赋予她们的,而是丈夫暂时让渡于她们的。因此,侨乡社会在强调女性的重要性、赞扬她们兼治内外的贡献的同时,又都指明一个前提——男性远居外洋。这意味着,男性才是真正的家长,他们在地理上的远离,给予女性独立处事的空间,但女性处事的结果要向他们交待,当他们不满意时,可以将授予女性的权力收回。1947年,旅芝加哥华侨梅友泽的妻子将家中田地出卖或典当,梅友泽闻悉,便在《新宁杂志》上发表声明,指责妻子“不肖”,并郑重声明:“非经鄙人允许,罔生效力。”[23]家庭主要事件的决断权同样由旅居外洋的男性掌握,比如家中子女的婚事安排、女儿上学读书的决定等。陈光锦家中要建厕所,他除了汇款回家作建筑之用,并在材料和人事方面对女儿做出具体嘱托。男性本来就是父权制宗族社会中的家长,加上家庭经济由其提供,其掌握家庭事务的终极处置权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侨乡女性的家庭地位也体现于社会对她们在婚姻关系中的行为的期待与评判。1927年,《颍川月刊》的“杂俎”有一则《抗议反对娶妾通电》,理直气壮地宣称支持娶妾的原因是对自由恋爱的倡导与对夫权的维持:“自由恋爱,思潮新涨,小家碧玉,犹将婢学夫人,况以堂堂七尺之丈夫,而甘受箝制于一老婆,不得自由行动乎?”[24]如果这篇文章写的不是“反语”,便是表达了那种长久以来为男性所认可的婚姻观:三妻四妾——“不甘受箝制于一老婆”,而一旦女性有相似的行为,则会受到比男性可能受到的严厉得多的批判与惩罚。《开平明报》有一则《儒良截抢案真相》,被抢妇女胡氏从未见过出洋丈夫,只与公鸡拜堂便嫁入了夫家。后来她与一男性亚灿相好,被散仔当场捉奸及抢了金饰。事发后,亚灿被罚款30元,胡氏则被家姑及其他女性鞭挞一顿,赶出家门,无家可归。[25]中国儒家传统“以夫为纲”、要求女性忠贞于男性的规则在民国时期的侨乡始终存在。
四、结 语
民国时期,侨乡女性的社会发展并没有超越中国女性整体的发展框架。侨乡女性的社会状况是复杂多样的,但大体而言,她们如中国其他地区的女性一样,开始自我觉醒。部分人开始争取自身的教育权利,尝试自由恋爱,从事适合自己的职业等,而且她们中的很多人得以独立地主理家政、参与处理社会事务。她们虽然没有为家庭提供经济资助,却是家中无可质疑的顶梁柱,照顾家人,坚忍不拔地守护家庭,给予远离家乡的丈夫坚实的支持,使他们有一个稳固的家园——心灵家园和事实家园。尽管这些于她们而言可能很艰难,但她们还是顶住家庭、宗族、社会、时势的种种压力,迎刃而上。
尽管侨乡女性呈现出独立的一面,但她们对于男性的依附并没有消失,或者说,社会的权力控制者依然竭力保持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地位,在并不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她们无论在教育、职业或家庭等领域,均容易遭到由男性主导的社会的制约、反对与惩罚。这意味着在侨乡的经济形态、文化意识未完全实现近代化转型的情况下,女性的社会状况难以发生根本的转变,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依然是禁锢她们的一个枷锁。
侨刊主要由侨乡乡村中的知识男性编撰,满足以男性为主的华侨的心理需求和阅读兴趣,女性在其中处于附属位置,只被称呼为某人之妻、某人之母或某人之女,缺乏独立的人格,且经常以负面形象出现。③因此,侨刊所呈现的更多是侨乡女性受制并依附于男性的历史图景。要对侨乡女性社会状况作更深入的探究,还需解析更多不同质类的历史文献,尤其是那些从女性视角做出的纪录和叙述。
本文原题为《性别权力与女性形象——清末民国时期侨刊对女性的描述分析》,曾在第三届“侨乡研究”工作坊(江门,2018年11月3日)和第五届“国际移民与侨乡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江门,2018年12月9日)上宣读,并得到与会专家的点评和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也感谢学报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注释:
① 此处应有印刷错误,女生应为1500人。
② 完全小学的男生和女生数目相加,总数应为10 496人。原文数字有误。
③ 如1917年第15期《四邑杂志》,关于女性的文章共22篇,其中有14篇描述女性的负面形象,占比是63.6%;1939年第18卷第12期《开平明报》,相应的数字分别是6和10,即女性负面形象文章占比为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