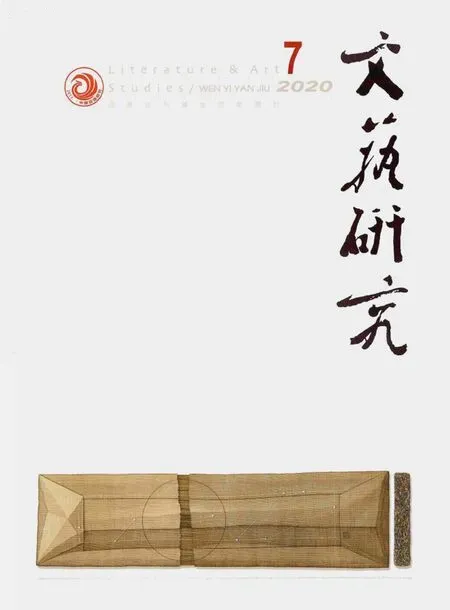傅尧俞生平与著述考
裴登峰
傅尧俞是北宋名臣,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为官三十年,多有政绩、建言。《宋史·傅尧俞传》(下文简称《傅传》)称其“厚重寡言,遇人不设城府,人自不忍欺”①。成语“胸无城府”即出此。傅尧俞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他所建济源草堂,名盛一时,是北宋颇有影响的文士唱和中心。可能因为傅尧俞著作散佚较早、较多,目前尚未有人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拟以《傅传》为基础,旁参他书,考论其生平事迹、文学主张、创作风格等,并对其著述的编刻、著录、版本、存佚等情况作一分类稽考,辑补《全宋文》漏收的文章及言论,详考作年、背景,以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一、傅尧俞生平考
傅尧俞,字钦之。祖上为大名内黄(今属河南安阳)人。自曾祖傅世隆,迁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后徙孟州济源(今河南济源市)。生于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卒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享年六十八岁。
傅尧俞少年得志,庆历二年(1042),年未及冠,即登进士第。曾监西京税院事。晏殊、夏竦皆赞其有卿相才。后知新息县,累迁太常博士。嘉祐末,为监察御史。英宗立,转殿中侍御史,迁起居舍人。上书皇太后,请还政。迁右司谏、同知谏院。其间,出使契丹。治平三年(1066),兼侍御史知杂事,坚辞,遂出知和州。神宗立,徙知庐州。熙宁三年(1070)至京师,授兵部员外郎、直昭文馆、权盐铁副使。四年,出为河北转运使,改知江宁府,徙许州、河阳。五年知徐州,为春秋政治家、军事家目夷(字子鱼)建墓立碑,碑上正面阴刻其撰写的篆文“宋贤目夷君墓”,落款题“徐州知州傅尧俞立”(墓与碑在今山东省微山县微山东峰,皆存)。七年末,提举崇福宫,后监黎阳县仓草场。哲宗立,自知明州召为秘书少监兼侍讲,后以目疾改侍读,擢给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元祐二年,诏尧俞更举御史,未受,即以为吏部侍郎,尧俞不可,遂为龙图阁待制、知陈州。三年复为吏部侍郎。四年再为御史中丞。进吏部尚书兼侍读,拜中书侍郎。六年卒,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献简”。
傅尧俞秉性耿直,沉稳内敛,饱读经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兼融道家精神。政事上,他强调循天道,得人心,倡导变通,反对因循。监察御史赵屼称赞其有“才能学术,忠言嘉谋”②。日常生活中不阿权贵,是非分明。“公在上前,吐论激动,事已,则终不复言”③。驸马李玮受到不公平对待,他仗义执言,批评仁宗“甚悖礼,为四方笑”④。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有司处理不力,他向仁宗反映。他反对重文轻武,请求恢复武举。“濮议”(详见下文)中,他先后上十余疏,言辞激烈地指斥英宗称其父为“皇考”,与人情、礼法皆背道而驰。他素与王安石交善,还请其为父写过墓志铭,但却当面指斥王安石,言世以为新法不便,由是“安石恶尧俞不附己”⑤。他与苏轼相知,但不顾太皇太后动怒,反复直陈苏轼策题不当。凡此种种,足见其为人行事不阿权、不徇私。傅尧俞一生磊落坦荡,“清立安恬”⑥,志节一贯。“历事四朝,白首一节,端方重厚,中外共知”⑦。他不管是做朝廷重臣,还是被贬看管草场,无论得志还是失意,都遵循“君子素其位而行”⑧的原则,尽心做好份内事。傅尧俞卒后,哲宗辍朝,与太皇太后哭临奠祭。“太皇太后谓执政曰:‘尧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司馬光尝谓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难兼,吾于钦之畏焉。’雍曰:‘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温,尤为难矣。’”⑨
傅尧俞天资聪颖,自幼喜书,十岁能文,曾受石介赞赏。他肯定文学针砭时弊、引领风气的社会功能,强调言浅意深、言之有物,反对不切实事的浮文。他称赞陈师道“文词高古”⑩,但也提倡文学创新。哲宗年间,“科举兼用辞律,使天下学者习之矣”,而词律之学,亦有提前记诵、类集,“临场套用”之患。他建议“其御试对策,虽有文采,而于所问义不相当,若词涉谀媚及文理疏浅者……不得雷同入等”⑪,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的进程。
傅尧俞与当时许多文学名士,如晏殊、夏竦、王安石、秦观、陈师道、司马光、苏轼、苏辙、秦观、黄庭坚、苏颂、范祖禹、刘攽、郭祥正等,或为好友,或交往甚密。其所为诗,状物态、叙人情,语言质朴,风格平淡、自然。如《读书》:“吾屋虽暄卑,颇不甚芜秽。置席屋中间,坐卧群书内。横风吹急雨,入屋洒我背。展卷殊未知,心与古人会。有客自外来,笑我苦痴昧。且问何为尔,我初尚不对。强我不得已,起答客亦退。聊复得此心,沾湿安足悔。”⑫宁静淡泊、超然脱俗,有陶渊明田园诗的意趣。
傅尧俞以奏疏为主的时政文章,往往切中时弊,说理透辟。当时文坛领袖晏殊,“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⑬的夏竦,均称赞其“文约而理尽”⑭。南宋中期文坛盟主,有“文中虎”美誉的周必大,也赞傅尧俞从孙傅察“文务体要,辞约而理尽,甚类献简”⑮。
二、傅尧俞著述考
《傅传》未载傅尧俞著述情况。下文拟按内容对傅尧俞著述的编刻、著录、版本、存佚等情况作一分类稽考。
(一)《傅尧俞集》(《傅献简集》《草堂集》)
《傅尧俞集》。《宋史·艺文志》:“《傅尧俞集》十卷。”⑯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傅尧俞集》七卷。”⑰卷数不同,“十”或为“七”之形讹。
《傅献简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傅献简集》七卷,中书侍郎献简公河阳傅尧俞钦之撰。”⑱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六“经籍考”因袭陈氏著录⑲。
《草堂集》。未见书志著录。傅尧俞后人、清代傅以礼所辑《傅献简公奏议》(详见下文)卷末有辑本,该书“例言”云:
是书外,公尚有《草堂集》七卷。各家书目或署《傅献简集》,或题《傅某集》,皆未明著书名。考之周文忠必大《平园续稿·傅忠肃公文集序》,始知公所著名《草堂集》,为五世从孙枢密公编定。忠肃公盖公从孙,而枢密公则忠肃公孙也。草堂者,在济源县济渎庙西。盖公知河阳军时所筑,故以名集。至其卷帙,《书录解题》作七卷,《文献通考》《经籍志》并同。惟《宋史·艺文志》作十卷,以“七”为“十”,或字之讹。今《集》已不传。只《宋文鉴》有诗文五首,祝穆《方舆胜览》有断句一联,翁方纲《复初斋诗注》有手札一通。录附是编,用存吉光片羽。⑳
按:《傅尧俞集》《傅献简集》明代以后未见著录,《草堂集》则一直未见著录,盖早已散佚。刻本时代的书籍,各起炉灶编辑的可能性不大,且《国史经籍志》云《傅尧俞集》七卷,《直斋书录解题》载《傅献简集》亦为七卷,卷数相同,故诸志所录,应为同书异名,或以名名、或以谥名、或以堂名。傅以礼即这样认为。周必大《傅忠肃公察文集序》言,傅尧俞五世从孙傅伯寿(1138—1223),“文采益高,方以直焕章阁按行畿部,兴念前烈。既编定献简公《草堂集》,又裒公遗稿成三卷”㉑。周氏此“序”作于庆元元年(1195)正月。傅伯寿“以直焕章阁按行畿部”的时间难考,然“焕章阁”为淳熙十年(1183)置,则傅伯寿编定《草堂集》在1183—1195年间。又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录》云:“戊辰,圣锡云:‘幼年初读《陈无己集》,有《代人乞郡札子》,一见便疑为代傅尧俞作,后阅傅集,果然。’”㉒则至晚在南宋“戊辰”(1208)前,傅尧俞集已编成流传,与上述推断相合。
(二)《傅公嘉话》(《傅献简佳话》)
《傅公嘉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三“小说”类:“《傅公嘉话》一卷,右皇朝傅尧俞之子孙记尧俞之言行。凡四十余章。”㉓《遂初堂书目》“小说类”仅著录书名㉔。《文献通考》卷二一六“经籍考”因袭晁氏著录㉕。
《傅献简佳话》。《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傅献简佳话》一卷,不知何人作。记傅尧俞所谈。”㉖《文献通考》卷一九九“经籍考”因袭陈氏著录,然书名误“话”为“语”㉗。
傅以礼所辑《傅献简公奏议》卷末有辑本《嘉话》。“例言”云:
公别有《嘉话》一卷。《书录解题》云不知何人作,记公所谈。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乃子孙记公言行,凡四十余章。各家著录,卷帙尽同而标名不一。《读书后志》《遂初堂书目》作《傅公嘉话》,《书录解题》作《傅献简佳话》。《文献通考》因晁、陈两家所载互异,遂误认为两书分隶两类。岳浚等《山东通志》称《傅某言行录》,又曰《傅公嘉话》。足征名虽歧出,实一书也。其书传本久佚。今据李元纲《厚德录》,吴曾《能改斋漫录》,采录五则,用存崖略。若《事实类苑》所引一条,因与《漫录》同,故不复采。
则《傅公嘉话》和《傅献简佳话》,乃同书异名,早佚。《傅献简公奏议》卷末从他书辑录了五则,可窥一斑。
(三)《傅尧俞奏议》(《傅献简奏议》)、《三老奏议》、《傅献简公奏议》
《傅尧俞奏议》。《遂初堂书目》“章奏类”:“《傅尧俞奏议》。”㉘《宋史·艺文志》:“《傅尧俞奏议》十卷。”㉙《国史经籍志》卷五同㉚。
《傅献简奏议》。《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二:“《傅献简奏议》四卷,傅尧俞撰。”㉛《文献通考》卷二四七“经籍考”因袭陈氏著录,然书名误“献”为“显”㉜。
《三老奏议》。傅以礼所辑《傅献简公奏议》“例言”云:“公与范忠宣纯仁、刘忠肃挚,皆尝以谏官补郡,先后出知和州。元祐中,孙贲建三老堂,以志遗爱。庆元中,池州程九万继为州守,景仰前政,因裒集三公章疏为《三老奏议》。《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即《文渊阁书目》《菉竹堂书目》《国史经籍志》亦载之,则其散佚,当在有明中叶。《宋志》作七卷,焦《志》作十卷,今亦无从考定矣。”按:《遂初堂书目》“章奏类”:“《三老奏议》。”㉝《宋史·艺文志》:“程九万《三老奏议》七卷。”㉞《文渊阁书目》卷四:“(宋)傅、范、刘《三老奏议》一部十册。”㉟《菉竹堂书目》卷二:“(宋)传、范、刘《二老奏议》十册。”㊱误“傅”为“传”,误“三”为“二”。《国史经籍志》卷五:“《三老奏议》九卷,傅献简、范忠宣、刘忠肃。”㊲《宋史·艺文志》与《国史经籍志》著录卷数不同,如“例言”所说,因为散佚,现已无从考定了。程九万于绍熙五年(1194)至庆元元年知和州,《三老奏议》在此期间编成。
《傅献简公奏议》四卷,另有卷首、卷末各一卷。傅尧俞后人、清代傅以礼辑,“光绪丁酉(1897)夏演慎斋编辑刊行”,为“傅氏续录之一”,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卷一至卷四为傅以礼所辑奏议,大致按作年编排,凡八十五通,附录二通。卷一为“嘉祐封事二十五通”,卷二为“治平封事二十九通”,卷三为“熙宁元祐封事十八通”,卷四为“元祐封事十三通,附二通”。傅以礼所撰“例言”详细交代了辑佚的文献来源及体例:“卷中各疏,计采自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者最多,其次则赵汝愚《诸臣奏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吕祖谦《宋文鉴》。或两书均载,字句小异,则择善而从。惟所收必全篇,其首尾不具者不与。间亦有两书参订者,如《请远窜蔡確并究党与疏》出《历代奏议》,而篇末‘贴黄’,则据《通鉴长编》补列。《请经筵侍读》仍居苏颂之次,疏出《通鉴长编》,而中段数语,则据彭龟年《止堂集》所引增入。此外悉仍原文,一无增减。”
《傅献简公奏议》卷首为他人所作关于傅尧俞之“制诰、祭文挽辞、史传、遗像”。卷末为傅以礼所辑《草堂集》和《嘉话》佚文,以及《资忠崇庆禅院疏》和傅尧俞之“遗事”。“例言”云:“《资忠崇庆禅院疏》石刻,载公《奏乞僧院看管先茔事》,所列申状,与奏议体裁少殊,故不编入此。碑见存济源县,亟依拓本具录全文,并采金石家跋语附入卷末。不特存家世旧闻,且以征前代故实焉。”“公事迹,见诸宋代杂史、说部暨各家文集者甚夥,往往可补史传之阙。今采录如干则,并奏状残文之仅存者附入简末,以备参考。”
关于傅尧俞奏议的诸家著录及存佚情况,“例言”亦辨析甚精:“是书各家书目均著录,惟或系谥,或署名,标题互异,卷帙亦不尽同。尤袤《遂初堂书目》,固无卷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作四卷,托克托等《宋史·艺文志》、焦竑《国史经籍志》作十卷。《宋史》多误,《经籍志》不考存逸,一概滥登,均不足据。是书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已不载,其佚当在明初。焦竑万历间人,岂能复见传本?其从《宋志》辗转贩鬻可知。今仍依《解题》《通考》之旧,勒为四卷。”
三、傅尧俞文与言论辑佚
傅尧俞文集早已散佚,《全宋文》第70册据诸书辑录文101篇㊳,多为奏疏。然如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云:“公为御史谏官四年,所上百六十余章。”㊴仅反对濮安懿王称皇考,尧俞就上十余疏。他为官三十年,所上奏疏,远不止《全宋文》所录。其言论,史籍亦多有所记。现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文简称《长编》)、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等书,辑补如下。为便于论述,根据篇幅长短以及“写”与“说”表达方式的不同,大略分为“文”与“言论”两类编年排列,文之标题为笔者所拟。
(一)文(6篇)
1.《论增财用疏》(1061—1062)
臣伏闻陛下自亲揽政事,留神财用,虑因访对,讲求利益,有以见圣度忧勤之深也。方今岁入,不充所出,天下共虑者久矣,固待陛下以救之,宜乎以为首务而垂意于其间也。虽然,为病已深,未可猝改。诚恐环首观望,言利者争进,未有纤芥之益,而为扰更多。何则?臣自省事以来,日闻更弊变故,公私缺乏,盖自如也,岂非救之或未得当乎?臣虽无智术,为国家陈力,亦有愚见,庶裨万一,惟陛下详择。如臣意者,独愿陛下痛自俭刻,身先天下,信赏必罚,以驭群臣。其能济务而不害民者,宠擢之以劝勤瘁;其好兴事而讫无补者,痛绳之以杜纷更。姑务静安,休养黎庶,然后澄经费之源,敦厚生之本。掌金谷者不以资序入,有绩效者不以日月迁,知横赐之无纪极也。虽近亲,不可妄与,虑积小至于成大也,虽一毫不可虚用。不作无益,以害农时,必固与之,以通商贩。严管库之禁,俾爱惜见物;重郡县之诛,无失陷常赋。切责司计,共为远图,庶几其可也。至于规规劳心,非帝王事。苟无验于目前,为奸佞窥伺,使言利者宠而聚敛之臣进,则天下殆矣。臣所陈者,初似常谈,倘垂省录,必有深益。
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四㊵。按:《傅传》记载仁宗年间,“时乏国用,言利者争献富国计。尧俞奏曰:‘今度支岁用不足,诚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俭刻,身先天下,无夺农时,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纷更,为之无益,聚敛者用,则天下殆矣。’”㊶与此文主旨同,《傅传》乃摘要耳。以《长编》观之,傅尧俞向仁宗上言,主要在嘉祐六年(1061)至七年为监察御史时。《傅传》叙此次上书,亦在嘉祐六七年傅尧俞弹劾李允恭、蔡世宁等事后,云“仁宗春秋高”㊷之前,故此文应作于嘉祐六年至七年间。
2.《论章奏宜即达圣听疏》(1063—1065)
臣伏以近侍、台谏官,皆天子耳目心腹。所上章奏,宜即达圣听,乃与其他文字,一例进入。脱有留滞、遗失,内外不得相知。自来别无关防,窃虑未为便稳。欲乞指挥禁中置簿,专令人管勾。逐日具有无及职位、姓名、章奏道数,画一抄上。仍令通进司逐日亦依此画一开坐,关送门合门。门合门每日于引事前,先次进呈。俟陛下亲览讫,然后付内照会。遇前后殿不坐,即令门合门具状直进,如有留滞、遗失,可以根逐施行。
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九九,英宗治平中,“起居舍人傅尧俞上奏”云云㊸。按:仁宗无子,嘉祐七年八月诏曰:“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㊹遂立为皇子,赐名曙。仁宗于嘉祐八年三月卒。四月,英宗即位,次年改为治平元年。初即位,因身体染疾,皇太后垂帘听政。治平元年四月,“戊申,皇太后出手书还政,是日遂不复处分军国事”㊺,英宗亲政。宰臣韩琦等议尊称濮王为“皇考”,傅尧俞等坚决反对㊻。尧俞于治平三年三月出使契丹回来后,“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㊼,后知和州。故上引傅尧俞云云,应在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后,治平三年三月前。
3.《论法官不得首误疏》(1065)
陛下不以臣言为然,不过以水灾归之于天数而已。臣请以政事明之。大理误断郑州严奕狱已决,辄请对举,觉法官不得首误也。今审刑、大理,匿法罔上,而乾刚未奋,阳明未融,亦致异之一端也。
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京师大雨逾月,郡国多水灾,公上书”云云㊽。按: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傅尧俞乞下诏求言以消灾。英宗下诏,以为大雨或由“天下刑狱滞冤”等所致,望大臣献言,“协德交修,以辅不逮”㊾。傅尧俞上疏,既言水患,又责审刑院、大理寺断严奕案时,明知故犯,“误用格条”,匿法罔上。“郑州严奕狱”始末待考。
4.《与司马光书》(1069)
昔我王考,材气过人,宦不遂以没。尧俞幼鞠于王妣,以至成人,恩隐殊厚。尧俞或以事夜艾未寝,王妣常危坐待之。及仕而之四方,王妣不见再逾月,则忧念,气涩而成痈。逮王妣之亡,竭尧俞之泣,不足以偿痈之血也。今将以某月某日,举吾王考妣之柩,葬于济源。吾尝与子同在谏省,子幸而知我,必为我铭其墓。子苟自谓不能,是爱其少顷之勤,而使我抱终已之恨,非仁人之为也。
按:司马光《右班殿直傅君墓志铭》云:“熙宁二年春,傅钦之遗光书曰。”司马光应傅尧俞之请,为其祖父傅珏写了墓志铭。
5.《论弃置患害之地奏》(1086)
陛下欲养民,足国用,则须皆弃置此等为患害之地,乃可以内得休息,不然,后患无穷,又终不可保。臣今且据为害于两州者言之,如出于朝廷及取于他路者,万数不可胜计。乞陛下令有司会计,即可见不知是多少生灵膏血。早罢得一日,则争一日事。大臣七八人议论不能齐一,须是陛下圣断。若非陛下一言断之,无由得了。
见《长编》卷三九三,云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子,傅尧俞、王岩叟同入对太皇太后。岩叟言晋州上二等人户,于葭庐、吴堡两寨纳税,往来凡一千四百余里。“自有两寨以来,一年税赋乃十年之费,遂为大患,不复乐生”,请废止。傅尧俞亦上奏云云。
6.《论苏轼策题不当奏》(1087)
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譬如误入禁门,于法罪亦不可轻。何则?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今若不以此事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舆,而云本出于误,亦可恕否?陛下虽欲恕之,七庙威灵在上,岂得容恕!昨执政于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既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朝廷事则不可如此。臣等为朝廷持风宪,若凡论奏,常指挥令休,要将安用耶?是臣等坏却风宪,更有何面目居职。真宗朝,知制诰张秉撰一叙用官制辞云:“顷因微累,谪于荒遐。”真宗览之曰:“如此,则是先帝失政。”遂罢其职。今所论苏轼,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被书在史册,后世视朝廷如何哉?传入四夷,必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辽使发问,不知如何为答。
见《长编》卷三九四,载哲宗元祐二年正月辛未,傅尧俞等认为苏轼策题不当,有讥讽祖宗意,向太皇太后弹奏云云。
(二)言论(28条)
1. 主恃爱薄其夫,陛下为逐玮而还隶臣,甚悖礼,为四方笑。后何以诲诸女乎?
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按:兖国公主下嫁李玮,在仁宗嘉祐二年。因“玮貌陋性朴,公主常傭奴视之”,却与内臣梁怀吉等饮酒为乐。嘉祐七年正月放逐梁等,但“公主恚怼,欲自尽,或纵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怀吉等还。上不得已,亦为召之”,却出玮知卫州,故尧俞云云。
2. 陛下惜清,恐不复闻外事矣。臣以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赏罚焉,则事之上闻者皆实,乃所以广视听也。纵而不问,则谗者肆行,民无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
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按:仁宗嘉祐七年十二月,皇城司逻卒吴清等密奏富人张文政尝杀人,实为诬告。有司处置不公,傅尧俞云云。“诏清等决杖,配下军”。
3. 枢密院既不治颖士,求内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举之?且汴口岁兴大役,责亦甚重。今上下相结,迭相阿循。其盗陛下名器,将不但一汴口而已也。
4. 忠义之言日切,而陛下不亮;权幸之交日深,而陛下不察。自夏至今,如朱颖士等已三犯法,内侍省法且尽废矣。
均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背景为:“内侍朱晦子颖士以内降,监汴口,而都水监复荐之。公(傅尧俞——引者注)言……后既罢颖士,公又屡请治枢密、都水罪,以戒欺罔……久之,未听。则又曰……章各数上,每上盖切,权幸惮焉。”事在嘉祐七年八月英宗被立为皇子后至八年三月仁宗卒前。
南宋谢维新《事类备要》后集卷二五、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新集卷一八,均引傅尧俞“枢密院既不治颖士”言论,以朱颖士为朱晦之子。朱颖士犯何法,未详究竟。其犯法,本应由枢密院定罪。林駧编《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八“宦官下”:“观傅尧俞奏枢密不治内侍求干降之罪,则宦官有过,枢密得治之矣。”但朱颖士犯法后,未由枢密院治罪,却由宫内径发诏令“内降”,或是因为朱晦打通了关节,即《傅传》所谓“朱晦屈法任其子”。仁宗嘉祐三年设都水监,“凡内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管干汴口事宜,责任重大,不应荐举朱颖士担此任。“尧俞以为嬖宠恩幸过失,当防之于渐,悉劾之。”
5. 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系上所化。
见《傅传》。英宗亲政之初,器重傅尧俞,“尝问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尧俞云云。
6. 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
7. 若付之公议,臣但见襄办山陵事有功,不见其罪。臣身为谏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均见《傅传》。其载英宗亲政之初,器重傅尧俞。“英宗曰:‘卿(傅尧俞——引者注)何不言蔡襄?’对曰……英宗曰:‘欲使台谏言,以公议出之。’对曰……”英宗与傅尧俞的对话,应在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三年三月间,原因详见上文辑补《论章奏宜即达圣听疏》之考释部分。
蔡襄于嘉祐五年权三司使。欧阳修《辨蔡襄异议》:“初,上入为皇子,中外相庆,知大计已定矣。既而稍稍传云有异议者,指蔡公为一人。及上即位,始亲政,每语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乐之色。”英宗曾“数问襄如何人”,问者包括傅尧俞。英宗多次想罢蔡襄三司使之职,但欧阳修等人力保。嘉祐八年四月,“发诸路卒四万六千七百八十人修奉山陵”,“权三司使蔡襄奏大行山陵一用永定制度”。因乾兴元年(1022)仁宗为真宗修永定陵耗资巨大,故蔡襄提议遭众人反对。傅尧俞向英宗上疏,乞减昭陵用度。六月,“时三司使蔡襄总应奉山陵事,凡调度供亿皆数倍,劳费既广,已而多不用,议者非之”。傅尧俞否定蔡襄议论立皇子事,且对其修仁宗永昭陵的主张与做法不满。
8. 此与人情、礼文,皆大谬戾。是必邪人有为为之。
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按:傅尧俞反对称濮王“皇考”,故云云。
9. 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
10. 诲等已逐,臣义不当止,愿得罪去。
第9条见《长编》卷二○七,第10条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按:傅尧俞于英宗治平三年三月出使契丹,“比还,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皆以谏濮议罢,复除尧俞侍御史知杂事。尧俞拜疏必求罢去”,且云云。
11. 前日言,职也,岂得已哉?今日为郡守,当宣朝廷美意,而反呫呫追言前日之阙政,与诽谤何异?
12. 君子素其位而行,谏官有言责也,为郡,知守法而已。
均见《傅传》。傅尧俞因不接受侍御史知杂事一职,遂于治平三年四月知和州。通判杨洙言:“公以直言斥居此,何为尝言及御史时事?”尧俞云云(第11条)。其时“众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从,尧俞一切遵之”,云云(第12条)。
13. 新法世以为不便,诚如是,当极论之。平生未尝好欺,敢以为告。
见《傅传》。按:傅尧俞虽素与王安石交好,但反对变法。熙宁三年,至京师,当面直言云云。
14. 非所望也,吾将见之。惧其不吾见也,子能介于陈君乎?
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四,“傅公钦之初为吏部侍郎,闻其(陈师道——引者注)游京师,欲与相见,先以问观(秦观——引者注)”,云云。按:其为吏部侍郎在哲宗元祐初年。
15. 但恐陛下临御日久,稍有怠惰。如能兢兢业业,日谨一日,常以大公之道自守,则天下无不治。
16. 大率昨来新取者城寨皆可废,不独此二寨也。
17. 王岩叟忠实,言不轻发。
均见《长编》卷三九三。其载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子,尧俞、岩叟同入对。太皇太后问天下政事如何,“尧俞称善”,且云云(第15条),又请废葭庐、吴堡等寨(第16条),评王岩叟(第17条)。
18. 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
19. 有一人论之,且观朝廷行不行。中间或有差失,方当继言。昨朱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指挥,则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须言。后见反汗,又是非颠倒,臣等方各论奏。
20. 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
21. 此在陛下。假令暂责,随即召之,亦是行遣。
22.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乃所以为平。今待轼如此,轼骄,将何以使之?
23. 臣尽至诚告陛下,陛下不察,亦无可奈何,愿为国家更深思远虑。
均见《长编》卷三九四。其载哲宗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元祐二年正月八日辛酉,尧俞等又各上疏论之。正月辛未,傅尧俞、王岩叟等面奏太皇太后,论苏轼策题不当云云。
24. 旱灾久,致陛下焦劳如此,由臣等不职。
25. 李清臣非才无补,玷位日久,公议不允,合罢免。
26. 过明堂,望其自请,又不请。过奉安,不自请,不免须言。
均见《长编》卷三九八。其载哲宗元祐二年春天旱情严重。四月己亥,傅尧俞与王岩叟入对延和殿,尧俞先奏云云(第24条)。听闻太皇太后之言后,“尧俞前启曰:‘更有愚恳上陈。’应曰:‘何事?’尧俞”云云(第25条)。太皇太后言“别无他,只谓旧人”,尧俞云云(第26条)。
27. 都堂聚议,臣实不知,略加究诘,必见诣实。
见《长编》卷四四九。其载哲宗元祐五年十月,傅尧俞先上札论官制不可遽改,“后数日,尧俞又入札子”云云。
28. 莫少俟之。君锡必与雍难共立,须至陈乞,候至时指挥。
见《长编》卷四六三。其载哲宗元祐六年八月壬辰,诸人奏议御史中丞赵君锡、右谏议大夫郑雍,尧俞云云。
四、傅尧俞的书帖及伪诗
傅尧俞在书法上颇有造诣,然其墨迹仅有《蒸燠贴》传世。以内容观之,《全宋文》卷一五二四称“瞻奉贴”,似更恰当。此贴笔法清峻峭拔,如其为人,其文曰:“尧俞再拜:气候蒸燠,伏惟台体万福。来日瞻奉,此不详尽。尧俞恐悚。”
傅氏此贴,原致苏轼。熙宁四年前后,傅尧俞与苏轼均因反对新法遭贬。傅尧俞“徙许州、河阳、徐州,再岁六移官,困于道路,知不为时所容,请提举崇福宫……凡十年”。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1079)间,苏轼知密州、徐州等地,其间又涉“乌台诗案”,迭遭打击。两人任所距离不远,傅氏此贴或此时转递,故苏轼书《赤壁赋》相赠,且跋云:“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足见相知之深。叶盛《水东日记》卷八“东坡《赤壁赋》真迹”条云:“东坡《赤壁赋》真迹,寄傅尧俞者。尝于俞尚书家见之。”傅、苏二氏帖,现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全宋诗》卷六一九收录傅尧俞诗四首,其中《诗一首》云:“微官共有田园兴,老罢云寻退隐庐。栽种成阴十年事,仓皇求买万金无。”出处标注为:“元《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卷三。”然《全宋诗》卷七八九所收苏轼《傅尧俞济源草堂》七律,前四句与此诗相较,仅第二、第四句个别字不同,余皆同。诗当属苏轼,理由如下:第一,苏轼手自编定《东坡集》卷二即收《傅尧俞济源草堂》;第二,《全宋诗》乃据元代未著撰人之《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补辑为傅诗,其标注为“卷三”,不知据何版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卷一七“傅尧俞”条云,“傅尧俞,字钦之……孟州济源县有别业,作草堂。坡有诗云”,下即《全宋诗》所录。足见辑录者未细审,忽视了“坡”字,误将此诗当作傅尧俞诗。
⑮㉑ 周必大:《傅忠肃公察文集序》,《周必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90页,第490页。
⑰㉚㊲ 焦竑:《国史经籍志》,《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69页,第243页,第243页。
⑱㉖㉛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7页,第209页,第636页。
⑲㉕㉗㉜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82页,第1764页,第1665页,第1950页。
⑳ 傅尧俞著,傅以礼辑:《傅献简公奏议》“例言”,清光绪丁酉演慎斋刊本。本文所引《傅献简公奏议》皆据此本。
㉒ 周必大撰,李昌宪整理:《乾道庚寅奏事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所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8册,大象出版社2016年版,第324页。
㉓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
㉔㉘㉝ 尤袤:《遂初堂书目》,《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2页,第31页,第32页。
㉟ 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4页。
㊱ 叶盛:《菉竹堂书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