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吻非吻
◎刘志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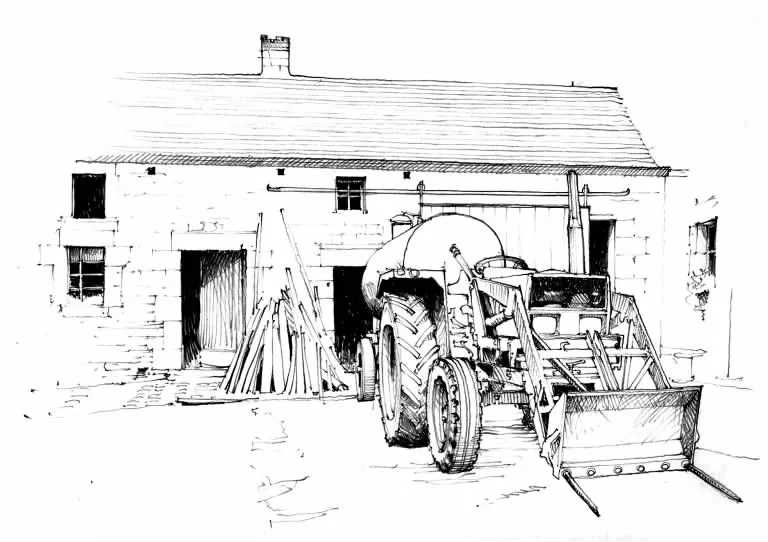
柳溪村的柳小苏一直很健康,25岁了,从未进过医院。那年夏天,她身上突然冒出许多红疱来。那些疱比粟米大,比豆子小,不像是痱子,也不像是疹子。“哎哟喂,该不是红斑狼吧!”邻居毛婶一声惊叫,把柳小苏吓了一跳。柳小苏不知道红斑狼是什么病,但从毛婶那惊诧的叫声里知道不是小病。柳小苏丈夫黄大毛是个屠夫,家里经常吃肉,她怀疑这病是吃了问题肉吃出来的。她打算跟丈夫打声招呼,去乡卫生院看医生。
出门后,柳小苏沿着潺潺的小溪走,亭亭玉立的身影倒映在溪水里,惊得小溪里的小野鱼响箭一般乱射。黄大毛的肉摊摆在柳溪村桥头的大柳树下。所谓的肉摊,也不过是两条长凳,搭一块门板,外搭一个帐篷。肉摊虽然简陋,但柳溪村和周边的塘下村、葫芦村、张家湾上千位村民吃的肉,都是黄大毛的肉摊提供的。
柳小苏走到肉摊前,黄大毛正在称肉。见柳小苏来,几个闲人不怀好意地拿眼睛瞄柳小苏。柳小苏干咳一声,对黄大毛说:“我走了!”黄大毛一手提着秤扣,一手抹着秤杆,眼也不抬一下,两片嘴皮一碰:“干嘛?”柳小苏说:“我痒!”黄大毛嘴皮又碰一下:“哪里痒?”黄大毛的心思,显然没放在柳小苏身上,柳小苏记得昨晚睡觉前跟他说过的,还让他帮忙挠痒痒。黄大毛显然把这事忘记了。柳小苏说:“哪里都痒……”哈哈!肉摊旁几个闲人轰的一声爆笑起来。
柳小苏面红耳赤,猛的一转身,一口气出了村。从柳溪村到乡卫生院有二十多里山路。日头当顶时,柳小苏才走到乡卫生院。第一次来,柳小苏对乡卫生院十分陌生,她站在乡卫生院门口,看着这栋高大陈旧的白色建筑,有些茫然。忽然,“嘀”的一声响,把柳小苏吓了一跳。柳小苏一回头,看见背后有一辆吉普车,吉普车的保险杠已经抵到她的屁股了。她“哎呀”一声闪到一旁。
驾驶室里有一位留着长发的小青年,对柳小苏坏笑。“你要死哟!”柳小苏轻轻骂了一句。小青年眉清目秀,他握着方向盘,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他显然对亭亭玉立的柳小苏充满了好感。柳小苏用一对丹凤眼瞪他,小青年发现柳小苏瞪他,从驾驶室里伸出右手,高高扬起后,往嘴巴上一贴,啪的一声又朝柳小苏一扬,给柳小苏抛了个飞吻。那个飞吻抛得十分的利索,嗖的一声,像燕子飞过。
那时,这个源自意大利,后来被欧洲人用于社交场合表达感情的动作,刚刚传到我国,开始在农村扩散,很受当时青少年的青睐,被他们广泛地传播和效仿。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的柳小苏,不明其意。在她25岁的生命里,还是第一回有人用这种动作对她表达情感。柳小苏误以为小青年叫她闭嘴,所以,她也模仿小青年,伸出她的右手,给了小青年回了一个同样的动作,意思是也让小青年闭嘴。
哈哈!小青年乐坏了,大笑。笑后大声喊:“大姐,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交个朋友好不?”柳小苏又瞪了小青年一眼说:“你太皮了,我才不要你这样的朋友呢!”小青年愣住了,自讨没趣,一踩油门,把吉普车开进了乡卫生院。柳小苏朝吉普车瞪了一眼,也进了卫生院。卫生院大厅里空荡荡的,墙上有个计划生育宣传栏,一位少妇抱着一个胖娃娃,胖娃娃胖得有点失真,像个娃娃气球。
在柳小苏的印象里,医院应该是人来人往的,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她很想有个人告诉她,医生在哪里,怎么看病。她站在大厅里等,等了上十分钟,忽然发现墙上有一个窗口,窗口上方写着“挂号收费”字样,看见有人往里面递钱,柳小苏也走过去。窗口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大姐,看病怎么看?”柳小苏轻轻地问。中年妇女问:“你哪里不舒服?”柳小苏说:“我身上长红疱!”
“挂号五角!”窗口里伸出一支白净的手,话像是手说出来的。柳小苏掏出五角纸币,递给那只手。那只手收回了,马上啪一声,递过来一张处方纸。接着里面传出声音:“妇科!”柳小苏不知道妇科在哪里,向右拐,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都是分门别类的门诊室,柳小苏从右边第一个门诊室找起来。找到最后一个门诊室,才看见“妇科”两个字,里面一位穿白大褂的女医生,看见她,从座椅上站起来说,“吃中饭了,下午来看吧!”
柳小苏想,等下午来看,那她回家就晚了些,便双手张开拦住医生说:“帮我看看嘛,我就是身上长红疱!”说着,将脸上、脖子上、手臂上的红疱指给医生看。医生扫了柳小苏一眼,啪的一声,夺过柳小苏手中的处方纸,龙飞凤舞几个字,又啪地甩回来说:“先化验吧!”“化验?”柳小苏重复着医生的话。女医生说:“是的,快去吧,下班时间快到了!”
柳小苏转身出了妇科门诊室,等她找到化验室,化验室果然关门了。看来只好等下午看病了。柳小苏受不了医院里来苏儿的气味,来到卫生院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卫生院大门前有一棵偌大的樟树,撑起一片华盖,一位瓜农在树下卖西瓜,旁边有个小凳子。柳小苏走过去坐下来,朝瓜农笑笑。女人漂亮,笑就很值钱,瓜农将一块切好的西瓜送到她面前说:“大热天,当口水!”柳小苏很不好意思,连忙推辞:“不吃啦!不吃啦!”瓜农说:“别客气,帮帮忙,免得我又担回去!”
话说到这分儿上,柳小苏只好接了,将身子转过去,背对瓜农坐在小木凳上吃起来。正吃着,一双大脚不知何时就站在了她面前。柳小苏的视线,沿着两根柱子一样的大腿往上移,发现面前竟然站着刚才开车的小青年。“吓我一跳!”柳小苏说着,突然站起来,往樟树背后躲。小青年说:“青天白日的,你躲什么?缘分啊!”“我才不跟你缘分呢!”柳小苏在心里说,就躲在樟树背后用手帕擦嘴巴。
小青年挨个地拍着西瓜,嘣嘣地响。一边挑西瓜,一边吹着口哨。他上身穿着红衬衫,下身穿着藏青色的牛仔裤,衬衫的下摆扎在裤腰里。这使他看上去高挑而又精神。拍了几个之后,小青年终于挑到了一个满意的西瓜。他拿起刀,切了一块对樟树背后的柳小苏喊:“哎,吃西瓜啵?”柳小苏从樟树背后探出头来:“谁稀罕你的西瓜!”小青年捧着西瓜走过来说:“又不是老鼠药,怕什么?!”
柳小苏态度很坚决,摇摇头说:“不吃!”小青年不好再劝,自己呱叽呱叽吃起来。一边吃一边没话找话:“哎,大姐,我怎么好像见过你?”柳小苏说:“你做梦吧?”小青年拍着脑袋说:“对,是做梦,我梦见跟大姐亲嘴儿!”“亲你的西瓜头哟!”柳小苏骂了一句。两人目光相碰,卟哧一声笑起来。瓜农被青春的笑声吸引,扭过头来看。小青年朝他喊:“看什么看,有人偷瓜了!”
柳小苏对小青年的智商还是满意的,笑他:“哪里有人偷瓜啊,瞎说!”小青年却对柳小苏说:“我们换个地方聊聊好不?”柳小苏没吱声。小青年仿佛得到了鼓舞,话题就更直接:“大姐嫁人了没有?”柳小苏斜了他一眼说:“结婚都5年了!”小青年就叹气,他望了望头顶的樟树,因为太热了,叶子都自我保护似的卷了起来。微风吹过,一片叶子在空中悠悠地飘下来。柳小苏顺着小青年的视线望去,正好看到了那片飘落的树叶。
阳光穿透密密麻麻的树叶筛下来,小青年的脸有些斑驳。柳小苏把目光收回来,偷偷地停在他脸上,她这才发现,小青年有两片又红又厚的嘴唇。她恍然忆起,外婆曾经说过厚嘴唇的人心地善良,对小青年的态度便明显有了好转,小声地问:“你今年多大?”小青年说:“差不多二十了!”柳小苏又问:“找对象了么?”小青年说:“找了,又吹了!”柳小苏又问:“干嘛吹了?”小青年说:“人家嫌我开车的,一只脚在天堂,一只脚在地狱!”
“光光!”医院门口有人朝这边喊,小青年回过头回应答:“哎,来了!”柳小苏好奇地问:“你叫光光啊?”小青年这才告诉她,他叫丁晓光,是乡政府的司机,刚才送人来医院看病。他没有马上离开,催促柳小苏:“大姐叫什么名字,哪个村的?”柳小苏心软了,想了想,像是下了好大的决心说:“嗯——柳溪村,柳小苏!”丁晓光从上衣口袋抽出一只笔,在手掌上写下“柳溪村、柳小苏”就跑开了。跑了两步,猛地转过身来,给柳小苏抛了个飞吻。柳小苏心想,怎么又叫我闭嘴,难道我说错了什么?便也还了丁晓光一个飞吻。
医院下午的上班铃声响过后,柳小苏重新回到化验室。她从窗口上拿了一只小瓶子,取了尿样,两根手指夹着瓶子,送到了化验室窗口。大约一个小时后,化验结果出来了。柳小苏拿着化验单,兴高采烈地找到了妇科医生。“怀孕了。”医生在化验单上扫了一眼,指着化验单上的“+”号说:“你看这个‘+’号,你的尿检呈阳性,这说明你怀孕了!”
“不是红斑狼?”柳小苏两只葡萄般的眼球定格了,像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射向医生。“你瞪我干嘛?”医生不解地问。柳小苏哇的一声哭起来。哭声像一群受伤的蝙蝠,在走廊里扑扑地飞。病人和医生将柳小苏团团围住,“这孩子怎么了,哭得这么伤心?”有人同情地说。这种场景,女医生大约见得多了,她拍拍柳小苏的肩膀说:“平时腿夹紧点,就不会有今天,不要哭了,不想要就流产,免得丢人现眼。”
柳小苏这才止住哭,哽咽着说:“我结婚5年才怀上,我干嘛流产?!”医生更不解:“那你哭什么?”柳小苏擦一把泪水说:“你怎么像三岁的毛孩,哪来那么多为什么?我就是想哭嘛,关你什么事?!”然后,抹着泪走出了卫生院。回到柳溪村,天差多不黑了,路过肉摊时,黄大毛已经收摊了,一条狗卧在哪里,咬牙切齿地啃一根骨头,见到柳小苏,叨着骨头跑开了。柳小苏走上溪水桥,咕噜一声水响,小溪里的小野鱼,响箭一般地射走了。
柳小苏回到家时,黄大毛不在家。柳小苏猜想黄大毛又打麻将去了。黄大毛白天卖肉,晚上打麻将,这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结婚后,他的生活都是这么过的。那时,农村电力非常紧张,柳溪村晚上要到8点开始供电,供到11点就拉闸。柳小苏去房里拿火柴点煤油灯。她习惯于把火柴放在枕头边,这样晚上停电,起来大小便找火柴点灯就非常方便。
黑暗里,柳小苏很快就摸到了那半盒火柴,抽出一根,嚯的一声,把火柴擦着了。一豆兴奋的火苗,摇曳着,将黑暗撕破。灯泡把柳小苏的寂寞放大了。没有黄大毛的陪伴,夜晚对柳小苏来说是无边无际的漫长。午饭和晚饭都没吃,柳小苏都不觉得饿。柳小苏现在什么都不想,5年的委屈化着一肚子的泪,柳小苏就是想倒在黄大毛怀里哭一场,把那个天大的喜讯告诉他。但是,黄大毛却不在家。
柳小苏想,她得找到黄大毛。于是卟的一声,一口气把灯吹灭了。黄大毛晚上的活动范围,柳小苏大致是了解的,她推开黄巴柄家的门,就看见黄大毛在跟人打麻将。“黄大毛,你出来一下!”她说。“干嘛?”黄大毛头都不抬。“我有话跟你说!”她说。“等一下哈。”黄大毛说着,埋头叠着麻将。柳小苏就靠在黄巴柄家的门框上等。黄巴柄的老婆在屋里喊:“柳小苏,进来坐一会嘛!”柳小苏笑笑:“不啦!”
柳小苏想,黄大毛叫她等一下,肯定马上就会出来的。她打算把怀孕的事告诉他就回家。她可不愿当那么多人的面说怀孕的事,那是她与黄大毛之间的隐私。她要让黄大毛第一个知道。她想,黄大毛要是知道她怀孕了,会发疯的。黄大毛发疯了,说不定就把她抱起来,当那么多人的面抱她,太羞人了。
电还没有来,月亮却先出来了,在夜空中弯弯地忧伤着。山上山下,屋里屋外就涂了一层薄薄的月华,水汪汪的。柳小苏等了一阵,还未见黄大毛出来,就有些气愤,她气冲冲地走到黄大毛的背后,用手指轻轻在他的腰眼处掐了一下。黄大毛突然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说:“你还没走啊,我还以为你走了呢。”这句话像一瓢冷水,凉透了柳小苏的心。弯弯的忧伤,顿时穿透了柳小苏的胸膛。
柳小苏悠悠地回到家里,生活用电开始供应了。可她肚子里装满了委屈,仍然没有饿的感觉。她和衣躺在床上,赌气似的朝肚子上拍打,“打你,打你,谁叫你爹不回家!”拍了十几下,肚子好像有点疼。柳小苏吓坏了,双手捂着肚子哄起来:“啊,乖乖,不打了哈,不打了!”她反复重复了几遍,肚子好像不疼了。便叭的一声,把电灯关了,闭着眼睛在心里数数,希望自己早点入睡:一、二、三、四、五……数到一千了,就是睡不着。
黄大毛回家时,柳溪村的晚间用电停止供应了。柳小苏听见黄大毛把椅子踢翻的声音,因为黄大毛出去打麻将的晚上,柳小苏一般不栓门,习惯地用一把椅子把门栓抵住。这样既可以避免她晚上起来为黄大毛开门的麻烦,又可以不让黄大毛在外面等太长的时间。她听见了黄大毛的小便把尿桶射响的声音,闻到了来自尿桶里汹涌的氨味。但柳小苏仍然闭着眼睛,一动不动。
柳小苏之所以装睡,那是想把幸福的路程拉长一点。她不想让幸福的时刻草率地来临。床摇晃了两下,柳小苏就知道黄大毛上床了。随即,柳小苏觉得整个身子往下沉。“你有什么话跟我说?”黄大毛问,一支手不安分地伸过来,抓住她左边的奶子,搓了搓。柳小苏一动不动。“这么早就睡着了?”黄大毛自言自语着,用他的左手搂住她,另一只手从她的腋下插过去,抓住她右边的奶子,捏了两下。见柳小苏没反应,黄大毛换了个姿势。
黄大毛习惯于一只手枕在柳小苏的脖子下睡觉。结婚之后,他们慢慢养成了这种固定的睡觉姿势。这种姿势的好处就是,黄大毛枕在柳小苏脖子下的那只手,在她上部动作的时候,搂住她腰部的另一支手,就能配合他在下部动作。黄大毛的动作,使柳小苏重温了那半新半旧的快感,但她还是犯错了。她的错误在于,黄大毛在她身上动作时,她仍装得像睡死了一样。她应该想到,黄大毛打了一夜麻将,已经很困了。
黄大毛的双手,突然在柳小苏的期待中停下来。就像家里的自鸣钟,走着走着突然不走了。时间顿时凝固了。柳小苏觉得无可救药。她一翻身,搂住黄大毛,轻轻地掐他:“黄大毛,我有话跟你说!”她想把黄大毛从沉睡中拯救出来。但是,黄大毛睡得像个植物人一样。
过了几天,柳小苏就开始呕吐。黄大毛问:“你怎么了?”柳小苏说:“没怎么!”黄大毛又问:“是不是病了?”柳小苏说:“你才病了呢!”柳小苏也不知为什么,她就是不想轻易告诉黄大毛她怀孕的消息。她说:“今后不要再打麻将了,钱要存起来,将来做大用!”黄大毛问:“做什么大用,我又不找小老婆!”柳小苏就很生气,她认为她是在提醒黄大毛,她觉得刚才他看见她呕吐,黄大毛应该意识到她怀孕了。黄大毛说:“你可能是吃多了,撑的!”“不错,撑的!”柳小苏狠狠地说。
柳溪村人刚吃过早饭,丁晓光的吉普车就开进了柳溪村。他是送乡干部来柳溪村检查防暑抗旱工作的。当然,就他个人来说,也不排除顺便看看柳小苏的意思。丁晓光把吉普车停在村民组长家门口,就向人打听柳小苏的住处。被他打听的是一位叫黄皮皮的小青年。在黄皮皮的指引下,丁晓光朝柳小苏家走去。但他没想到,黄皮皮会悄悄地跟踪他。丁晓光走到柳小苏家院门前,柳小苏正坐在门槛上呕吐,近来她常常呕吐。
丁晓光看见柳小苏呕吐就兴奋地喊道:“嗨,大姐!”柳小苏抬起头来,她一看见丁晓光就不吐了,脸上露出惊喜而又动人的笑容。丁晓光马上扬起手,啪的一声,给柳小苏抛了个飞吻,柳小苏兴奋地从门槛上弹起来,扬起手啪的一声,还了丁晓光一个飞吻。她现在觉得这种手势并不像是叫人闭嘴,她完全把它当做好玩的游戏。两人做完飞吻后,忍俊不禁地笑了。“进屋坐吧,家里有些乱!”柳小苏说着,将丁晓光迎进家里。
丁晓光说:“乱点好,我就喜欢乱!”然后,两人就坐在竹床上聊天。丁晓光走进柳小苏家后,黄皮皮才从屋角边出来,刚才发生的一幕,让他大饱眼福,他总算明白了,那个穿红衬衫青年的意图,明白他与柳小苏的关系。他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于是,他径直走到桥头上,他并没有马上把他看见的镜头告诉黄大毛,他想柳小苏他们做那事,一定要做些准备工作,他要让黄大毛看到精彩片段。
于是,黄皮皮就站在肉摊旁,看黄大毛和几个闲人打扑克。看完一局之后,他拍了拍黄大毛的肩膀说:“你家有人打麻将!”黄大毛问:“谁呀?”黄皮皮说:“我不告诉你!”黄大毛说:“神经病!”黄皮皮笑了笑,又不动声色地看黄大毛打扑克,打完一局,黄皮皮又拍了拍黄大毛的肩膀说:“你家有人打麻将你也不管?”黄大毛不耐烦了:“谁嘛?”黄皮皮说:“一男一女,女的是你老婆,男的我不认识!”黄大毛说:“两个人打什么麻将,神经病!”
黄皮皮说:“这你就不懂了,那种麻将人多了不好打,因为只有两张牌!”黄大毛不解——“两张?”黄皮皮说:“没错,一张是白板,另一张是中钻!”打牌的人都坏笑起来,黄大毛不笑,他突然站起来,朝黄皮皮飞起一脚,把黄皮皮踢倒在地就回家了。黄大毛走到他家的院门前,就看见家门前站着的丁晓光。事实上,当黄大毛踢倒黄皮皮的时候,丁晓光正好从他家里出来。黄大毛并不知道丁晓光到他家干什么,但是,他恰好看见了丁晓光向柳小苏抛飞吻。他觉得应该相信黄皮皮的话。
丁晓光在抛给柳小苏一个飞吻后,就朝村民组长家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他从黄大毛身边走过时,仍然吹着口哨,这使黄大毛觉得丁晓光有点流氓习气。黄大毛并不认识丁晓光,也不知道他是乡政府开吉普车的司机,当丁晓光吹着口哨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拍拍丁晓光的肩膀说:“嗨,我是柳小苏老公,到我家坐坐吧,我有话跟你说!”柳小苏老公相邀,丁晓光有些心虚,可为了证明自己没做亏心事,还是跟着黄大毛进了他家。
丁晓光一进屋,黄大毛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质问:“你来我家干什么?”丁晓光吓坏了,哆嗦着说:“没……干什么……我就是来看看……小……苏……”“没干什么,你给我老婆抛什么飞吻?”黄大毛说着,在丁晓光的腹部来了一拳。见黄大毛打丁晓光,柳小苏知道黄大毛误会了,扑上来拉黄大毛,一边拉一边喊:“不要打了,什么是飞吻啊?”黄大毛暂时停止暴力,推了柳小苏一把:“别装了,飞吻就是亲嘴!”说着,向柳小苏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天哪!”柳小苏惊叫一声,哗的一声,呕吐起来。
柳小苏把早晨吃下的菜粥吐了一地。黄大毛突然记起柳小苏已经吐过多次了,他放下丁晓光,关切地问柳小苏:“你到底怎么了?”柳小苏觉得现在应该告诉黄大毛了,也许他一高兴,就放过丁晓光。便说:“我早就想告诉你,我怀孕了!”说完,委屈突然涌上心头,哇的一声哭起来。黄大毛显然误解了柳小苏的哭,早不怀孕,晚不怀孕,偏偏这个小青年来家就怀孕?他指着丁晓光,恶狠狠地问:“是不是你干的?”
太突然了!丁晓光显然没想到会出现这戏剧性的一幕。他想,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他拔腿就跑。他这一跑,黄大毛更加坚信了黄皮皮的话,他随手抓起身旁一条板凳扔了过去。与此同时,还骂了一句:“吻死你!”黄大毛没想到,他会那么准,板凳不偏不倚,正好“吻”在丁晓光的后脑勺上。丁晓光倒在黄大毛家的院子里,身子弹了几下就不动了……
黄大毛盯着丁晓光看了好一会儿,发现丁晓光的后脑勺有一个洞,有血从那个洞里流出来。他又用手指在丁晓光的鼻孔试了试,吓出一身冷汗——丁晓光没气了!黄大毛知道自己闯大祸了,头脑一片空白。他感到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村里人看见丁晓光的尸体。他像抱一头猪一样,将丁晓光抱进次卧的床上,用毛毯盖好,然后将家门锁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和柳小苏一起去桥头肉摊卖肉去了。他叮嘱柳小苏,不许走漏半点风声。他想,他必须尽快想一个周全的办法,处理好眼前这桩人命关天的事。
中午,当乡政府的干部结束检查,到村民组长家吃饭时,才发现丁晓光不见了。有人告诉乡长,看见丁晓光去过柳小苏家。乡长便找到黄大毛,问他是否知道丁晓光的去向。黄大毛说:“那个小青年确实来过我家,他来我家就是想买两斤肉,他说他父母亲好久没吃肉了,他买好肉就离开了!”村长找人心切,没有留意黄大毛的表情。黄大毛说这些话时,脸皮是苍白的,头上冒虚汗,整个人不停地颤抖。检查组还去其他人家找了找,都没找到丁晓光,干脆吃了午饭继续找。山上山下,田畈地头全找遍了,丁晓光像人间蒸发一样。
乡检查组的人离开后不久,有人慌慌张张地爬到肉摊上告诉黄大毛,他家里有人在喊开门,还把大门敲得咯咯响,问黄大毛家里是不是关了贼。黄大毛二话不说,丢下屠刀往家里跑。果然不出所料,他打开门发现,丁晓光竟然活过来了!他一把抱住丁晓光号啕大哭:“小兄弟,你可吓死我了……”听到黄大毛喊自己兄弟,丁晓光不再那么害怕了,他壮了壮胆,将他“飞吻”柳小苏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黄大毛。“飞吻即非吻,本来就是无中生有的!”丁晓光说。黄大毛的疑虑终于烟消云散了。事情很快传遍了柳溪村。后来,柳小苏生了个男孩,黄大毛给儿子取名“黄非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