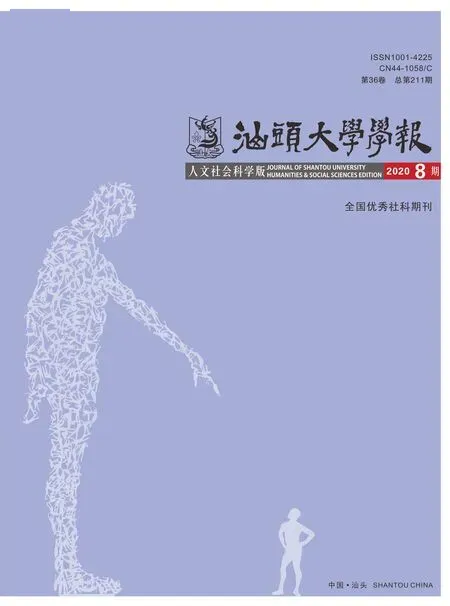民国旧体诗“落花”意象之变迁
(嘉应学院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诗歌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联。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人将个体之情绪与自然之迁变沟通联系起来。
落花,是暮春时节花木凋零的自然现象,然而诗人在感物与物感过程中,赋予其青春易逝、美人玉陨、士之羁旅等文化意义。胡晓明教授在《略论文化意象的诗学》一文中,将“落花”作为“文化意象的诗学”之一,认为它在近代有“文化托命意识的精神传统”[2],此论一语中的,具有建设性意义。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落花诗创作繁盛,以此名篇者甚夥,围绕“落花”酬唱赓和、争奇斗胜者不在少数。因此,晚清民国批评家刘衍文在《雕虫诗话》中云:“咏落花者诗家俱有,虽各有寄寓,而出色特难。”[3]495今人也说:“从古至今因‘落花’这一意象较普遍地被历代诗词人所运用,因此也较难另翻新意。”[4]但黄晓丹在《明清落花诗研究》中提出:“随着时代大主题的变迁,明清落花诗表现出对传统主题意蕴的突破和新变。”[5]34她着力研究明清两代的落花诗创作,也论及民国落花诗的新变。其论详实可信,也颇有见地,但于民国落花诗还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郑逸梅曾说:“民国以还,以落花诗负盛名者凡二人,一吾吴贝大年,别署南园逸史,有落花诗十六绝;一番禺沈太侔,有落花诗三十律”[6],因落花诗二人一时博得“北落花”和“南落花”之誉。清江后裔贝大年的落花诗,今未得见,而番禺沈太侔(宗畴)的落花诗,后有潘飞声、李东沅、杨葆光、杨彦深、赵时桐、夏仁端、三多、王寿恩、江峰青、蒋兆燮、何震彝、高翀、朱兆基、李宗藩等32 人唱和,1898 年结集为《落花酬唱集》。沈宗畴自序曰:“蕊芬词史误嫁冬风,求死不得,予闻而伤之,为赋落花七律十章,并具清酌,哭吊于小阑干畔,花魂有知,庶几来享。”江峰青作序云:“生之者不甚爱惜,怜之者无可挽回,此甘溪沈孝廉落花诗之所为作也。”[7]由是知,沈宗畴的落花诗延续的是传统伤悼主题。不过,民国时期“落花诗”在继承传统思想主题的基础上,抒发的禾黍之叹、文化失落、家国不幸更见新意。
一、民国初期:禾黍之叹
禾黍之叹是中国人特有的精神情感。每逢易代之际,就会出现一批不仕新朝的文人,他们在作品中寄托易代之悲、禾黍之叹,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南唐后主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相见欢》)抒发亡国之痛,从此“落花”染上了一层故国飘零的文化意蕴。[5]32明清易鼎后,以落花反映“禾黍之叹”的思想主题更为显著。广东潮州诗人黄锦作了《落花诗》九首后,引起同社诗人陈衍虞、郭辅畿等人的唱和,他们皆以“落花”悲慨“大树飘零之感”。而借落花抒发兴衰之痛、飘零之感成绩最为突出者是王夫之,他一人即有落花诗99 首,寄托遥深,意旨隐微。朱则杰教授在鉴赏王夫之《正落花诗》时指出:“因为花色红,红即朱,所以诗歌借咏落花,凭吊朱明王朝的灭亡,同时抒写自己的民族气节。”[8]点出了“落花”意象所蕴含的政治意味。
清朝覆灭,民国建立,辛亥鼎革的历史变故与明清易代的情形相似,这让身处朝代更替中的诗人有异代同悲之感。中国文人惯于从传统中汲取文化资源以获得现实力量,于是沿用明清“落花诗”的思想主题,哀挽王朝的没落,抒发当下家国之痛与身世之悲,成为题下应有之义。
这首先要提到的即是以“前后落花诗”名后身的陈宝琛。1919 年,陈氏有《次韵逊敏斋主人落花四首》,世称“前落花诗”。此诗为和作,和作主人是“逊敏斋主人”,即爱新觉罗·载泽,晚清宗室重臣。一为末路王孙,一为胜朝遗老,二人围绕“落花”而托物寄怀,足以赚人眼目。又因王国维自沉前一日,为门人谢国桢题扇面诗,所题之诗其中两首即是陈宝琛前落花诗第三、四首,此事亦为落花诗增添了神秘色彩。其三云:
生灭原知色是空,可堪倾国付东风。唤醒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雨里罗衾寒不耐,春阑金缕曲初终。返生香岂人间有,除奏通明问碧翁![9]180
诗人以“落花”自况,落花挂在蛛网上不忍落去,形容自己对幼主的忠贞不舍之情。又引李煜《浪淘沙》和杜秋娘《金缕曲》感叹故国覆灭、时光流逝的悲痛怅惘。第四首曰:
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骀荡碧池头。燕衔鱼唼能相厚,泥污苔遮各有由。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庇根枝叶从来重,长夏阴成可小休。[9]180
以“余香骀荡碧池头”传达1917 年张勋复辟失败的惋惜落寞之情;又用“伤心最是近高楼”抒发自己忠于逊帝并努力挽回清王朝,然而清朝灭亡已成定局的无奈孤愤心境。据《闽县陈公宝琛年谱》载:“虽以次逊敏斋主韵为题,实即用公乙未《感春》原韵,大抵皆哀清亡及自悲身世之意,亦为时传诵。”[9]759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亦有载:“此四诗亦有本事,先生未尝详述其寓意。以余测之,大抵皆为哀清亡之作,自憾身世,以及洵、涛擅权行乐,项城移国,隆裕晏驾之类。”[10]由此可信,陈宝琛前落花诗因清朝亡祚而为,摅发忠爱恋主之情。
随后,也即是民国十三年(1924)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间,陈宝琛又作有《落花续作》四首,世称“后落花诗”。吴宓在《空轩诗话》中逐一为之解读,以为第一首总叙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之情形;第二首指民国十三年冯玉祥以兵逼清帝出宫,劫取故宫珍宝;第三首似言中国各派军阀之混战兴灭;最末一首似言清帝居津及作者忠爱之意。[11]197-198除此之外,陈宝琛在1931 年还作有一首《次韵仁先春尽日赋落花》,对时局表露更为深沉的失望与哀伤。
在陈宝琛一系列的落花诗中,由花及人,通过“落花”飘零倾吐自己的身世遭际,表达对幼帝溥仪的孤忠节义、对清室覆灭的不尽哀思,缠绵悱恻,哀婉动人。陈绛先生以“落花”诗钩沉陈宝琛的晚年心迹云:“陈宝琛所以因落花而引起对清朝覆亡如此深切持久的哀痛,是因为他身受孔孟儒学的熏陶,以‘君君臣臣’伦理礼教作为自己行为的最高规范。”[12]胡马也说:“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官吏的升迁擢拔同其实际的经世济国的才干毫不相干,而仅仅看他们的所谓的道德修为。权力运作体制所提倡的道德,最终都要归结到忠君爱国的终极目标上去,于是,愈是善于伪装的人,愈是平庸而恭顺的人,便愈能高踞要路津,而像陈宝琛这样的精英分子既不能依靠揣摩上意飞黄腾达,也不愿退而求田问舍,早营良窟,就只有通过苦力经营的吟咏,来表白其忠贞怛恻之心了。落花,便成为他们最喜采撷的意象。”[13]诸人都将陈宝琛的落花之咏,归结到陈氏对清朝的“孤忠”上,是有道理的。
陈宝琛“前后落花诗”,首首咏落花,叹花果之飘零,而句句寄托感慨,挽清朝之覆灭,比物达情,神味隽永,可谓是呕心沥血之作。林葆忻赞曰:“殿柳官莺春欲晚,禁城传遍落花诗”,足见感人之深、传诵之广。同时,陈氏落花诗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如黄濬《落花诗四首次沧趣楼均》、剑秋《次韵沧趣楼主后落花诗》、赵尊岳《后落花诗和弢庵太傅韵》等,都表达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惘与痛楚。
其实不止是帝师陈宝琛,帝后师陈曾寿(任先)也有多首落花之咏。在其《苍虬阁诗》卷一中收有《感春四首次韵昌黎韵》及《落花》诗,是为辛亥鼎革之前作。清室亡祚三年后,他又有《落花四首》,张眉叔先生批语云:“第一首殆讽逊清显宦之入仕民国者。”[14]492几与陈宝琛《次韵逊敏斋主人落花四首》作于同时的《落花十首》,张氏有批语称:“此寓记复辟前后诸事,愤惋深矣。”[14]4931931 年,他还有《落花简自玉》一诗,张氏评点说:“写析津密谋,事多睽阻,闲庭花落心情。”[14]497诸首落花诗突出展现了陈曾寿对满清政权的无尽留恋以及大势已去的无比惋惜。
陈宝琛、陈曾寿等人的“落花诗”创作与明清易代之际陈衍虞、郭辅畿、王夫之等人的“落花之咏”,在情感上具有一致性,都以“落花”的凋零感慨个人身世的沦落和自己所忠恋之王朝一去不复返。不过,这种情感也并非只是禾黍之悲这样单薄纯粹,其中多少有文化挽歌的意味在其中。任聪颖说:“他们(陈宝琛、陈曾寿,笔者注)创作的《落花》诗在主观上抒发的是对胜国故主之思,但从更为深广的层面上看,这些诗作未尝不能被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衰残的挽歌”[15],此论是颇值得注意的。
二、民国中期:文化失落
华夷之辨主要是为了维护华夏文明与尊严。每当异族凌侵,以共同的文化认同凝聚广大百姓,激起他们的民族主义气节以极力抵抗,是一种文化政治策略。即使当异族统治中原,以华化夷,大行儒道,以道教胄子,依然是一部分士子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满清取代明朝,在异族统治下,文化危机涌动于士子之心,这种忧患意识也体现在诗人的落花诗中。王夫之《续落花诗三十首·二十五》“天已丧文悲凤凤,人皆集菀忍乌乌”、尹民兴《落花诗》“重华已被灵根薄,云汉无光文种衰”,感怆的不仅是山河沦落,也是文化失落。因此,当他们参加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失败后,纷纷转向文化救亡事业上,以道统、学统为职责,担负起传承道统文脉的重任。
晚清民国之际,西学东渐,“华夷之辩”思想得到空前的高涨。只是此时之“华”“夷”已然演变为中国与外国之别。比之明末清初的“斯文扫地”,晚清民国则为“文化澌灭”。陈三立“天纲日坠九维坼,倏忽揖让移征诛”(《古微同年归鹤图》)痛感皇纲解纽、伦纪荡尽,王国维“末流那解盗圣智,异俗何时还淳厚”(《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追怀醇厚素朴的民风习俗,孙雄“论语付薪衅,六籍万古厄。毁詈及孔孟,保乂鲜旦奭”(《愤言二十韵效郭功父五侧体》)哀叹学统崩塌、文化黯淡。恰如高嘉谦所云,“帝国崩坏而迈入民族国家,透过建立新文化秩序,封建的政治道统消亡,政治遗民的正当性削弱,古典遗民论理应失去对应的条件。然而,士人百姓感受到另一种文化与时间的断裂,格格不入的新生活,使得他们对传统眷恋,心怀忧思。”[16]于是文化失落成为他们心头最大的焦虑。
而这焦虑的爆发,集中体现在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沉行为上。1927 年6 月2 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引起世人一片唏嘘。围绕其自沉,时人提出“殉清”“殉文化”“逼债”“畏惧南北军阀”“自亡学术”等种种猜疑。而在王国维自沉前一日所题的扇面诗,分别为唐韩偓七律二首和时人陈宝琛“前落花诗”第三、四首,这是他诗性人格的最后一笔,也成为后人探寻其死亡的精神符码。
前文提到,陈宝琛“落花诗”抒发的是对逊帝之忠贞和清朝之怀念,那么王氏之“殉清说”便有了着落。不过,与王国维知交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17]他以为王国维是“一死从容殉大伦”,通过“落花”之飘零,寄托文化之凋敝。对于王国维之死,吴宓在日记中也屡有提及[18],他既肯定“殉清室”之说,也认同“殉文化”之论。不仅如此,1928 年6 月2 日,即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之际,吴宓作有《落花诗》八首,“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为宓落花诗之所托兴。”[11]196
那么吴宓《落花诗》所“托兴”者为何?他在《释落花诗》中披露:“予所为《落花诗》(《吴宓诗集》卷九)虽系旧体,然实表示现代人之心理,即本刊第74 期所译登罗素评克鲁奇(J.W.Krutch)之书,所谓过渡时代之症候。而在曾受旧式(中西)文学教育而接承过去之价值之人为尤显著者是也。惟予诗除现代全世界知识阶级之痛苦外,兼表示此危乱贫弱文物凋残之中国之人所特具之感情。而立意遣词,多取安诺德(Matthew Arnold)之诗,融化入之。”[11]148所谓“过渡时代之症候”,梁启超早在1901 年《过渡时代论》中就有论述,要之,旧的文化制度悉遭破坏,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人们处于思想真空、精神迷茫的状态。要了解吴宓《落花诗》的“立意遣词”,还需进一步剖析“安诺德之诗”。在《论安诺德之诗》一文中,吴宓说:“安诺德及克罗之诗,皆写此种已失旧信仰,另求新信仰而不得之苦……吾侪生当其后,承十九世纪之余波,世变愈烈。安诺德等之所苦,皆吾侪之所苦,而更有甚者焉。且中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社会、学术、思想各方变迁之巨,实为史乘所罕见。故生于今日之中国,其危疑震骇,迷离旁皇之情,尤当十倍于欧西之人。”[11]77以时代背景而论,安诺德生活于19 世纪的欧洲,当是时,欧洲旧日之宗教道德悉遭屏弃,而新道德尚未确立,整个社会思想淆乱,与吴宓生活于过渡时期的晚清民国,文化信仰失落、道德价值失范,情形何其相似;就个人而言,安诺德是大批评家,平生奉行古学派之旨训,吴宓是学衡派领袖,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何等契合。因此他说,安诺德之苦,皆是吾侪之苦;安诺德之诗,吾多有所取。在《挽阮玲玉》中,吴宓道“我是东方安诺德,落花自忏吊秋娘”,自比为东方安诺德,表明二人在文化观念上的遥想呼应。
回到落花诗本身,吴宓所表白的意思大体有两层。如“桑成忽值山河改,葵向难禁日月沦”“每缘失意成知己,不计缠绵损道心”,感怀中国由衰乱而濒于沦亡,世变俗易,人们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同仁普渡成虚话,瘏口何堪众楚咻”“歌成不为时人听,望里白云是帝乡。”[19]174表明自己于道德之原理,有得心之处,欲救国救世,然文明世运操之于新文化之手,新说伪学流行,自己志向难以施展,但仍勉强奋斗,不计成功之大小,至死方休。归结到一点,吴宓乃假春残花落,表达对传统道德文化的依恋之情。
在同日,吴宓又有一首《六月二日作落花诗成,复赋此律,时为王静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诗中“叹凤嗟尼父,投湘吊屈平”,与陈三立1914 年《诵樊山涛园落花诗讫戏题一绝》“仲尼已死文王没,乞得闲愁赋落花”颇为相似,以“落花”哀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于此,他将“落花”的思想主题彻底从“禾黍之悲”中剥离出来,赋予她以文化失落的审美意蕴。
吴宓《落花诗》成后,一时驰诵,和作颇多。如杭县张尔田《题雨生落花诗后》云:“应有高枝果落时,近前粉黛已纷披。早拼绛蜡同寒烬,忍委红蚕与断丝。常是开迟那易谢,便教空遣更难持。情知此恨人间别,怊怅吴郎锦段辞。”诗下自注曰:“尊诗凄泪哀断,读之辄唤奈何。宗教信仰既失,人类之苦将无极。十年前曾与静安言之,相对慨然。静安云:‘中国人宗教思想素薄,幸赖有美术足以自慰。’呜呼,今竟何如耶!”[19]174-175表明哀国人宗教信仰缺失,文化精神匮乏。贵州张友栋《和雨生先生落花诗》哀今之智识阶级无团结力,揭露“芳华唯是竞妍宠”是他们被打倒之总因。萧公权和雨僧之作《落花》八首,第七首伤“时人但知宝重古物,而不爱惜固有之精神文化”,第八首“刺新文化运动者之学行浅薄”。1946 年,何传骝寄吴宓诗函《落花〈敬和雨僧学长兄原韵〉》第二首感“文物凋零,返魂无术”,第四首叹“人才销歇,国是可知”,第六首痛“斯文扫地,学者心灰”,也是借“落花”喻传统文化之飘零。除此之外,徐际恒、刘盼遂等人也有和诗,大抵表达文化失落的感伤。
以王国维自沉前手抄“落花诗”为起点,围绕吴宓等人的落花之咏,主题思想已然发生了重大转变。胡晓明教授论道:“从陈宝琛到王国维,再到吴宓,表明‘落花’之咏,是一承传的心灵诗学之统。其中,殉清的政治意味,由于陈寅恪的解读,渐转而为文化兴亡的意味。”[20]而以“落花”表“文化兴亡”的确立,无疑是由吴宓等人完成的。
三、抗战时期:家国不幸
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前所未有之屈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自此长驱直入内陆,给人民带来惨重打击。而与中国毗邻的日本,三番五次挑衅,直把中国当作“冒险家的乐园”,甚至视为囊中之物。“九·一八”事变的烽火举燃,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随后,日寇迅速占领沈阳、长春等主要城市,并继续向南进攻。1933 年春,热河战役告急,侵略军又觊觎北平,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危机当中。
面对日寇的铁蹄践踏东北,大好江山卷入烽火狼烟之中,而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联盟,采取“不抵抗”政策,深深刺痛了诗人林庚白赤诚的爱国之心。于是在1933 年6 月17 日,他愤慨而作《落花四首》。序曰:“辽沈变作,党国仓皇,而士论甚嚣,若将与偕亡者,余至今犹厕名党末,抚时感事,不能无言,爰窃取所怀,赋落花四首以见意,非敢自托于讽谏之列也。”[21]232他虽自谦“非敢自托于讽谏之列”,但诗中的讽刺意味甚是浓厚。其一曰:
坠溷飘茵未解羞,名花身世属离忧。皈依西土知何补?!许嫁东风肯便休?!铲地无情红间白,随波作态去还留。莺嗔蝶骂浑闲事,萍末鸳鸯自并头。
全诗以“落花”喻国民党之堕落,嘲讽怒骂,极尽讽刺之能事。特别是颔联一句之中,两处连用问号和感叹号,这在中国古典诗歌和当时的旧体诗中,都不曾识见。通过醒目的标点符号,也能想象诗人对国民党依靠西方联盟来调和解救中国的强烈质疑与极度愤怒。
同年10 月1 日,萧公权重读吴宓1928 年所作的《落花诗》八首,于是兴而赋作《秋兴八首》,亦以寄家国身世之感。其三云:“酒共愁添哭是歌,悲秋意苦奈秋何。挥戈究竟难回日,落叶飘零易逐波。自写新辞伤国破,只从绮语见情多。蕉心本已因风碎,那禁敲窗夜雨过。”[19]176“挥戈回日”一语双关,不仅形容难以挽回危局,也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艰难。诗人并非消极厌战,而是自感国危时难,自己却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挽救国家,表示痛楚懊恼。在此,萧公权以“落叶”为物象,象征战乱中动荡离析的家国。其实,不论是萧公权有感吴宓的“落花诗”而兴“落叶”之叹,还是林庚白因国难而生“落花”之咏,都以自然凋零的景象为托情之物,象征美好事物的渐行渐远,喻国家之飘零衰危。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局日危,国势日蹙。于此情势下,林庚白又作《“九一八”变后,余曾赋落花诗传诵一时,客秋以来寇深国蹙不绝于予心,更续为四首以寄意》。如其三:“一树轮囷劫后身,乱栖鸦雀最愁人。岁寒曾是经风雪,代谢由来有故新。社燕相逢非旧土,城孤所践有惊尘。伤心不为高楼近,水面文章若可亲。”[21]429感慨战乱以来,物是人非、惊魂失魄的凄怆伤痛。“花近高楼伤客心”写国家艰难之际,登楼见繁花似锦而黯然落泪;陈宝琛“伤心最是近高楼”表达清朝覆灭,作为帝师在溥仪身边而无可挽回局势的伤痛;但林庚白“伤心不为高楼近”所愁的是“乱栖鸦雀”,它们聒噪不休,无情讽刺了一帮政客,于救亡图存无实际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华,铁蹄所到之处,无不嚣尘四起,令作者忧心不绝,此处作者亦是以“落花”象征国家之危亡。
更为集中的以“落花”寄托家国不幸,是林则徐侄孙林葆恒在上海孤岛发起的酬唱活动,此乃文坛大雅之事,颇为引人注目。1939 年5 月,陈三立的入室弟子袁伯夔(思亮)有《落花诗》之作,林葆恒依韵和之,然后分寄南北诸亲友,一时酬唱者如陈诗、夏敬观、姚景瀛、杨无恙、孙元芳、严昌堉、吴庠、胡嗣瑗、叶尔怆、张鸿、金兆蕃等37 人,得诗248 首。与此同时,广东惠阳廖恩焘(忏庵)用六一体填词《蝶恋花》六阙,和者亦得二十余阙。次年四月,林葆恒将原诗与和作结集为《落花诗》。除已收录在《落花诗》中的诗词外,尚有一些文人的和诗未来得及收录,如余绍宋《落花诗八首次韵和袁巽初伯夔》、无名氏《和蘉庵丈落花》、陈道量《追和蘉庵丈落花诗》等,不计其数。此次落花唱和之活跃,规模之宏大,可谓前所未有。
那么如此盛大的“落花”唱和活动,其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刘衍文在《雕虫诗话》中载:“汪精卫附逆,袁思永(伯夔)尝首倡《落花诗》叹惜之,各家和者颇众,皆系亲笔书写,诗书可称二妙,装帧为《落花诗倡和集》,极为精致……读各名家所赋和《落花诗》,可窥见当时诸老心态。”[3]463知此次落花之咏,乃为汪精卫附逆而作。
如众周知,汪精卫在辛亥鼎革前是一位革命志士。1910 年,他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在监狱中留下一绝明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人一身浩然正气与杀身以成仁的英雄形象,呼之欲出。民国建立后,汪精卫曾陪伴孙中山左右,出谋划策,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而努力奋斗。孙氏去世后,他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武汉政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公开提出“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22]。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前半生光彩夺目的革命领袖人物,却在抗日战争最艰难关头,民族生死存亡最关键时刻,罔顾国家利益,于1938 年年底公开叛国投敌,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总头目,中华民族的大罪人。从革命志士到民族罪人,这样的人生逆转,怎不令人惋惜?
汪精卫叛国事故,袁思亮首倡《落花诗》八首。如其四曰:“摇落深知百不辞,翻从决绝费然疑。回身背面肠堪断,忍泪无言意更悲。如此才华终负汝,自成馨逸待贻谁。可怜堂坳余春在,只有诗人解作痴。”[23]作者感慨,这样一位才华横溢、英伟奇绝的革命志士,却在抗战关键时刻,幡然公开反共,卖国事敌,作了日本人的傀儡,感到无比痛心。但即便如此,诗人依然幻想着“堂坳”中的“落花”余香犹在,当然作者自己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痴念”罢了。由此可以看出,诗人对汪氏附逆深表惋惜。袁伯夔诗成后,和者如云,如杨无恙《和作》:
战雨鏖香运命轻,盛衰花事露峥嵘。粉身玉石同遗憾,绝意熏莸共此情。一代绚华归净土,十年欣向策冬荣。偶然飞近弹棊局,最不心平是此生。(其一)
竞凭謦欬吐芬芳,文沉当年并擅场。粉碎可能成片段,色空聊尔托篇章。但祈黄妳留春腊,不坏金刚只晚香。投阁辞枝同一喟,未妨惆怅是轻狂。(其三)[23]
为汪精卫当年“绚华”而今“投阁”甚感不平。张鸿在杨无恙和袁氏原诗后,继而和杨氏作《落花八首寄和无恙》:
当年品格领群芳,独立嫣红姹紫场。大愿化泥供践踏,偶然落水弄文章。可留南国相思子,输与东篱晚节香。剩有故人添怅惆,惜春心事寄佯狂。(其三)
碎玉残香百不辞,传来消息不胜疑。成灰空付漫天劫,埋骨难忘入地悲。漂泊关山凭所寄,追随莺燕更留谁。劝花莫作邯郸梦,梦醒黄粱也是痴。(其四)[23]
作者对汪氏晚节不保表示痛惜不已,同时也警告他莫作邯郸美梦。未收入林葆恒《落花诗》中的诗作,如余绍宋(越园)的《落花诗八首次韵和袁巽初伯夔》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主旨。其六曰:“忆自辞根怨阻修,故枝回复已无由。空嗟节物频推换,忍委芳情忘寇仇。痴蝶徘徊犹恋惜,佳人惆怅且归休。园中草木春无数,一样飘零替我愁。”[24]民主战士查猛济读后,立成《次余越园先生和袁巽老韵》八首。第八首云:“闻道王孙欲赋归,东风吹面叹无衣。抽身富贵羡君早,设想繁华觉我非。晚节岂甘迎夕照,素心何以答春晖。晓来故学痴儿女,招手天娥启半扉。”[25]这些落花诗唱和,表面上纯为描写自然景物,抒发“落花”“春逝”引发的伤感之情,实则有感于汪精卫叛国投敌之事而作。
林庚白“落花”象征国民党的堕落,萧公权之“落叶(落花)”感国家之危亡,袁思亮等人的“落花”挽汪精卫附逆,虽然从浅层面观之,他们的“落花”所象征之事不尽相同,然而从大处着眼,皆可视为国家不幸的托体。相比前代的落花之咏,抗日战争时期的创作显得别具特色,富有时代气息。
四、结语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由此形成独特的精神文明。同样,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也有一致的审美趣味,以至形成特有的审美意象群,如花、鸟、月、柳等。这些审美意象,经诗人代代袭用,而有约定俗成的文化指向。但是,意象的旨意也并非一成不变。胡峰指出:“意象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要受诗歌中与之相关联的其他意象以及整体语境的影响,被重新唤起与排列组合的意象,都会在情感内蕴上发生变化,从而成为一种适用于当下诗人表情达意的新意象。”[26]以“落花”意象为例,她自先秦发端,经几千年的历史沉淀,审美意蕴也逐渐丰富与迁变。到了民国时期,她依然具有“可塑性”。如果说民国初年遗老的“禾黍之叹”还是继承传统已有的落花思想主题,那么民国中期的“文化失落”,则突出展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苦楚;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家国不幸”,又呈现出不同历史事件下文人的情绪、心态。可见,“落花”意象的每一次蜕变,无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