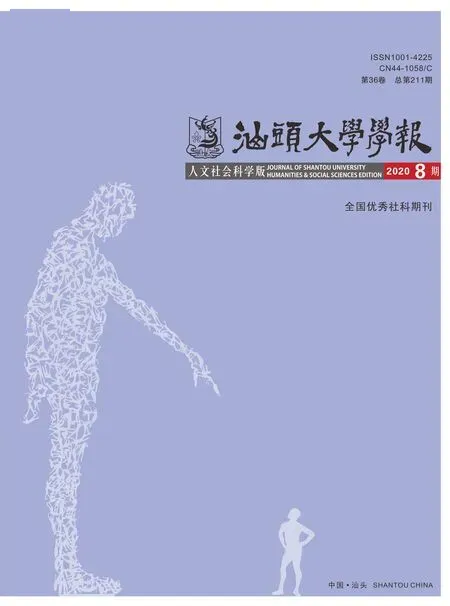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探究吴文英的词风
(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存词340 余首,其词历来褒贬不一,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吴文英生平史料的缺失,使学界对梦窗词风形成过程的研讨略有不足,已有的研究略有注意到吴文英游历区域对其词风的影响,有从吴文英所属的仓台幕府及其职能探索其词风成因[1],也有以吴文英交游为中心对其不同时期的词风进行总结[2],还有对吴文英游历之地进行词中指事与时地的对应研究[3]。本文将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通过探讨吴文英的出生地、经行地的人文地理,分析它们对梦窗词的影响,这将对解释梦窗词风的成因有着重要意义。
一、梦窗词的文化基因及其影响
杨义先生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中提到:“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体现了作家文化基因的生成、传递和迁移。”[4]他在比较李杜诗风的不同时,就曾着重提及李白出生地碎叶“胡汉杂处”的人文环境以及宦游地四川所属的黄河文明对其诗风的重要作用,还有杜甫的京兆出身所代表的长江文明和祖辈杜预、杜审言给他带来的影响。这些都说明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对作家的文化基因进行探索时,不仅要关注到具体地点的人文环境,还要看到其所属的区域文化。
(一)四明士风对梦窗词雅化倾向的影响
吴文英词被周济誉为“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其后又解释道:“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5]这种“秾挚”并非简单地回归到北宋软媚绮靡的文风,而是脱去了俚俗之语,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熔炼在一起,从技巧到用词全方面雅化,词的士大夫气息更为浓郁。如《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本为故地重游、悼念亡妾的词作,但“湖山经醉惯”“又客长安,叹断襟零袂,涴尘谁浣”体现出对飘萍国运的感伤;“紫曲门荒,沿败井、风摇青蔓”,通过周遭破败环境的描写体现了对当时危难局势的感怀。
这种雅化倾向与吴文英的文化基因有着很大的联系。据《吴文英年谱》,吴文英出生于鄞县(四明),该地在战国时期与越州(绍兴)同属越国的疆域。春秋末年,越国灭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此时吴、越、楚三地的文化开始相互兼并融合。然而大量吞并土地的楚国最终也在秦统一六国时灭亡,许多中原汉族人迁入越地,原有的古越文化渐渐从越地淡出。东汉时期越州出现大量学者和文学家如王充、吴平、赵烨等。此后通过三次汉人的大规模南迁——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后的衣冠南渡,以及建炎南渡,越地的士族文化渐渐走向成熟。唐代时期,越地因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秀美的景色吸引了如孟浩然、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慕名游历,从而成为“唐诗之路”的重要一站。南宋中期,四明地区有楼氏、史氏、袁氏、汪氏等大族通过科举崛起,使得当地科举风气高涨,中举人数增加,当地研习理学尤其是陆学的风气浓郁,出现了舒麟、沈焕、杨简、袁燮等理学大家。此外,南宋是明州文学的勃发期,据统计,“这一时期明州至少拥有30 位词家,大多为鄞县籍,存词880 多首,名列浙省之冠。”[6]南宋后期,理学弊端凸显,江湖词人反对理学家们重义理轻辞章的文风,转而重视文学创作技巧,吴文英成为其中的代表之一,但是其词作中的雅化趋向还是具有理学的影子。
(二)四明学风对梦窗辞赋笔法的影响
梦窗词中的辞赋笔法凸显四明文化基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骚体造境法”上。吴蓓曾提出梦窗词有一种典型的写作手法“骚体造境法”,是“借了屈原‘香草’、‘美人’的手法,以男女之情赋友朋情谊”[7]6,如《水龙吟·用见山韵饯别》《尾犯·赠陈浪翁重客吴门》等。据吴蓓统计,梦窗集中运用“骚体造境”写作手法的词作多达20 首[7]7,可见其已成为梦窗词作的一种常用手法。
骚体造境法不止以男女之情比附友情,也有以美人比附景物的,如《水龙吟·惠山酌泉》“吴娃点黛,江妃拥髻”句以西施和舜妃的容貌比喻山峦在烟雨中若隐若现的美景。《丑奴儿慢·双清楼》“遥望翠凹,隔江时见,越女低鬟”句以女子的发鬟比喻山色。这种人与景物合咏的写法在梦窗咏花词中尤为多见,如《琐窗寒·玉兰》则以美人“绀缕堆云,清腮润玉”的容貌比喻玉兰枝叶与花瓣的颜色。又有《金盏子·赏月梧园》中“篱角。梦依约。人一笑、惺忪翠袖薄”呼应其题序所咏桂花“朅来西馆,篱落间嫣然一枝可爱,见似人而喜”。
梦窗咏花词中还有一种写作手法,即以美人比附花,再以花比附自身。如《过秦楼·芙蓉》结句“能西风老尽,羞趁东风嫁与”以美人宁愿老去也不托于非人,来比喻荷花当在适当的季节盛开,暗喻南宋目前的局势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腐朽不堪,自己也不会因追逐表面的繁华而放弃原则投身官场。又如《庆春宫·残叶翻浓》“别岸围红,千艳倾城。重洗清杯,同追深夜”句,是以其它盛放的花朵反衬荷花的凋零,比喻在宴席上,他人皆沉醉于纸醉金迷之中,而唯有老伎是清醒的,进而隐喻吴文英对时局冷静的判断和对个人立场的坚持。这种以“美人-花-自身”双重转喻的表现手法是屈原“香草美人”表现手法的延伸。
梦窗词的辞赋笔法,纵然受到了周邦彦、柳永等人的影响,但也与其接受的教育,即四明地区的整体学风有关。首先是南宋中期,洪兴祖、朱熹等人对屈原及其辞赋的再解读,将屈原在汉代“怨君”的形象转变为“忠君爱国”的形象,从而掀起一阵楚辞研究及骚体赋创作的热潮。其次,陈晓兰在《南宋四明地区教育和学术研究》一书中提到,四明地区对士子的培育一直以服务科举为主,所以“自南宋进士科分为经义和诗赋以来,传习诗赋之学的人数一直占优”[8]。与梦窗同为鄞县人的楼钥即以诗赋取科,楼钥称赞其师郑锷时曾说:“文备众体,尤工于赋……集古人之长,而藻思绝人,兴寄高迈,闻见层出。立词用韵,精切平妥,古语随用,奔凑笔端,而一语不出程度之外。”[9]由此见四明文人对词赋之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其对发意、用韵、引典、技巧是十分讲究的,梦窗词擅炼字面,引经据典,与当时辞赋研究的热潮和四明地区的教育风气有着很大的联系。
二、从苏杭词看地域文化对梦窗词风的影响
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中提出文学作品蕴含了三个空间:客观的自然空间、作家的审美空间以及读者的联想空间。“文学家通过自己的地理感知和地理想象在文学作品中所建构的审美空间”[10],不仅含有作家对客观空间的感悟,还有作家对创作地点人文信息的接受,创作地所属的区域文化及历史积淀会为后世文人所继承,从而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这一点在吴文英的苏杭词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据《吴文英年谱》,吴文英曾在杭州袁韶幕下10 年(1220-1230),在苏州为仓台幕僚约13 年(1231-1244),在越州史宅之幕下6 年(1244-1251),后又重回杭州,客嗣荣王赵与芮府邸。虽有时行役于湖州、常州等地,但总体而言,梦窗在苏杭两地的时间最长,词集中与苏杭相关的词作亦最多,所以本文将以与苏杭有关的词作进行对比分析,探索两地的历史文化等因素对梦窗词作的影响。
(一)梦窗词之苏杭都市印象对比
1.杭州词中的汴京旧影。吴文英可考地点的词作中,在杭州所作或描写杭州的词达57 首之多,词中多以“长安”“东华”“洛阳”“灞桥”等地名指代杭州,如《绕佛阁·与沈野逸东皋街卢楼追凉小饮》的“浪迹尚为客,恨满长安古道”,《丹凤吟·赋陈宗之芸居楼》的“丽景长安人海”,《浣溪沙·仲冬望后》的“数家灯火灞桥东”等句,这些地名实际都指向一个地方,即北宋的都城汴京。梦窗词,抑或说唐以后词作中出现“长安”一词,并不一定实指西安,有时是国都的泛指,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中的“长安”,即指代北宋都城汴京。同样地,洛阳作为四大古都之一,也时常被用作国都的代指。靖康元年,金人攻占汴梁,赵构南逃并定都临安,大量文人南渡后将汴京文化带入杭州,吴自牧的《梦梁录》就从方方面面阐述了杭州对汴京都市风貌的“模仿”,如“杭州食店,多是效学京师人”[11]264,“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饰车盖担儿,盘合器皿新洁精巧,以炫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11]281,“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11]144。南宋统治者竭力在杭州恢复汴京旧貌,一是不愿接受当前半壁江山不保的局面,二是对北宋太平盛世的怀念。然而这两个原因的背后都体现了统治者对当前形势的逃避。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也反映了这一点:“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除了以地名代指杭州以外,梦窗词中还常以“软红”二字指代杭州,如“卜筑西湖,种翠萝犹傍,软红尘里”(《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软红路接。涂粉闱深早催入”(《暗香》),“料应花底春多,软红雾暖”(《绛都春·饯李太傅赴括苍别赋》),“澄碧西湖,软红南陌,银河地穿”(《沁园春·冰漕凿方泉》)等。“软红”一词,化自苏轼《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的“半白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苏轼自注曰:“前辈戏语,有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12]380意为西湖美景比不上汴京的繁华热闹,高观国《烛影摇红》也以“软红”形容杭京:“行乐京华,软红不断香尘喷。”梦窗词集中“软红”一词出现10 次,且皆用以形容或指代杭州,由此可得“软红”一词当是吴文英对杭州的整体印象。这种印象的实质是当时杭州日渐畸形的繁荣景象。这时期杭州的商品经济达到空前繁荣,《都城纪胜》对当时的情况有着详细记载:“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11]79但实际上,理宗时期的南宋已经陷入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然而理宗仍大行奢靡之风,为了满足统治阶层的物质欲望,理宗政府敛聚民财而忽视生产,导致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物价飞涨,贫富差距加大,杜范在《八月已见剳子》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天灾旱暵,昔固有之,而仓廩匮竭,月支不继,上下凛凛,殆如穷人,昔所无也;物价腾踊,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于前,昔所无也。民生穷瘁,昔固有之,富户沦落,十室九空,灶罕炊烟,人多菜色,昔所无也;楮券折阅,昔固有之,告缗讥关,钱出楮长,而物价反增,人以为病,昔所无也。[13]
穷奢极欲与民不聊生两极分化的现实状况导致梦窗词中的杭州有着十分矛盾的形象。一方面繁华热闹,如《莺啼序·丰乐楼》中对丰乐楼集会的描写,“面屏障、一一莺花,薜萝浮动金翠”“明良庆会,赓歌熙载,遣丹青、雅饰繁华地。”再有《扫花游·西湖寒食》中描述了游人争看竞渡时“绮罗争路”“乘盖争避”的熙熙攘攘。以及《江神子·赋洛北碧沼小庵》中以“绮罗尘满九衢头”描写都市繁华。另一面却衰败颓废,如《声声慢·凭高如梦》“乘半暝、看残山濯翠,剩水开奁”,《西平乐慢》“废绿平烟带苑,幽渚尘香荡晚”等。
2.苏州词中的吴苑古迹。吴文英的苏州词共有87 首,大概占存词的1/3,且以吊古怀今之作最多。梦窗词总以“吴苑”“吴宫”“吴门”“吴地”等指代苏州,如“吴宫娇月娆花,醉题恨倚,蛮江豆蔻”(《瑞龙吟·送梅津》),“念省惯、吴宫幽憩”(《莺啼序·荷和赵修全韵》),“犹记初来吴苑。未清霜、飞惊双鬓”(《水龙吟·癸卯元夕》)等句。因为苏州所在的太湖流域是古吴国的中心,且苏州是吴国后期的都城,所以在吴文英眼中,苏州俨然是吴地的代表。公元前473 年,吴国为越国所灭,光辉不再,吴文英也常以“残吴”“残霸宫城”“故宫离苑”“故苑”等词指代苏州,如“吴王故苑。别来良朋雅集,空叹蓬转”(《宴清都·万里关河眼》),“回首沧波故苑,落梅烟雨黄昏”(《木兰花慢·虎丘陪仓幕游》)等。
从苏杭两地的代称可以看出吴文英对两地印象的不同。“长安”“软红”体现出吴文英眼中的杭州有着汴京繁华的残影,一派绮罗香泽之态。然而“故宫”“吴宫”等词却显示其对苏州描写的侧重点在一个“故”字。苏州城中留下了不少古吴遗迹,如垂虹桥、虎丘、灵岩、沧浪亭等,自古以来都是文人骚客争相吟咏的对象,刘长卿有《谪官后却归故村,将过虎丘,怅然有作》,张祜更有《题虎丘寺》四首,白居易也有《灵岩寺》一诗,宋代词人苏轼、辛弃疾、卢祖皋等皆有咏怀苏州古迹的词作。吴文英苏州词中的吊古之作也是苏杭越三地词作中数量最多的。
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吴文英的苏州词往往更为雄快清健、疏阔放达。吴文英的疏放雄健之作不多,但绝大部分出于苏州词,如《木兰花慢·游虎丘》《齐天乐·齐云楼》《金缕歌·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等,有“千古兴亡旧恨,半丘残日孤云”“问几阴晴,霸吴平地漫今古”及“华表月明归夜鹤,叹当时,花竹今如此”之句写尽古今兴亡、历史沧桑。究其原因在于苏州词的登临游历题材比较多,写景状物多从高处着笔,如写灵岩时,就有“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云气楼台,分一派、沧浪翠蓬”(《满江红·淀山湖》)描写淀山湖的视角也在高处。这种角度显得视野更为开阔,词风亦随之变得雄快。反观杭州词则多从细处着笔,如描写西湖时,就常写岸边花柳,“羞红颦浅恨,晚风未落,片绣点重茵”“千丝怨碧,渐路入、仙坞迷津”(《渡江云三犯·西湖清明》);或用如“尘”“雾”“香”等极微小缥缈的意象,以及如“侵”“拂”“沁”等代表轻柔缓慢的、潜移默化的动词,例如描写元夕夜市中的女子是“暮寒愁沁歌眉浅”(《烛影摇红·元夕雨》),回忆杭州时用“软红雾暖”(《绛都春·饯李太博赴括苍别驾》)。要之,杭州词的描写重点多在细节,通过这种细节描写凸显都市生活的精致与奢华,词风亦随之富丽典雅。
(二)苏杭时期的隐逸思想对比
梦窗词中多隐逸之思,其表达隐逸思想的方式有三,一是通过酬赠之作劝人归隐,如“泠然九秋肺腑,应多梦、岩扃冷云空翠”(《金盏子·赋秋壑西湖小筑》)化用苏轼“花开酒美盍不归,来看南山冷翠微”(《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以劝谏贾似道归隐山川。吴文英投赠史宅之的《瑞鹤仙》中也劝其莫管政事,隐居度日为上:“算金门听漏,玉墀班早,赢得风霜满面。总不如,绿野身安,镜中未晚”,即便是为政事日夜操劳,也不过赚得风霜满面,与其这样,还不如归隐山林。此外,《烛影摇红·寿荷塘》《扫花游·赠芸隐》《瑞鹤仙·癸卯寿方蕙严寺簿》《木兰花慢·赠赵山台》等酬赠词作皆有劝人归隐之意,由此可见吴文英不仅自身重视归隐,更乐于以自身的隐逸情怀影响友朋,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政局和国家前程的失望。二是通过繁华热闹的都市景象与独处时冷清的境况对比以抒发隐逸之思,如《丑奴儿慢·双清楼》中,以“歌管重城,醉花春梦半香残”的杭京盛景,与自身“乘风邀月,持杯对影,云海人闲”对比,突显自己高洁隐逸的情操。三是以目遇古迹后生发历史兴亡之感引出隐逸之思,如《八声甘州·姑苏台》中,先回首姑苏台旧时盛景,联系范蠡携西施归隐之事,发出“问当时游鹿,应笑古台非。有谁招、扁舟渔隐”的感慨。其中第一种方式重点在于投赠之人,苏杭两地皆有;第二种多见于杭州词;第三种则多出现在苏州词。
南宋时期的江湖词人主要以行谒权贵、客食诸侯、鬻诗坊间、教授生徒、替人撰作为生,吴文英就属于客食诸侯的词人。张春媚在《南宋江湖文人研究》中阐述了这类词人的生存方式:“有一些声名显赫的江湖文人则索性寄居豪门,以幕僚食客的身份长期依附某些权贵要人,以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14]吴文英所客如赵与芮、史宅之、袁韶等都是当时显贵,出入场所自然相当奢华,但南宋已陷入一种畸形繁荣的境况,词中通过冷热景象的对比所抒发的隐逸之思,实际上是表明自己“心远地自偏”的情怀,如《水调歌头·赋魏方泉望湖楼》中,先描写“绣鞍马,软红路,乍回班”的杭京繁华,再以“残照游船收尽,新月画帘才卷,人在翠壶间”写宴阑人去后望湖楼主人独处的闲适心情,结句“天际笛声起,尘世夜漫漫”实际上是通过尘世间的漫漫长夜和悠扬的笛声对比,衬托出望湖楼主的超逸心情。望湖楼主独处的情景显然是吴文英想象的,也从中折射出词人的隐逸之思:望湖楼处繁盛之地,楼主却能过着清逸的生活,这如同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境界。梦窗词中也对《饮酒》多有化用,如《满江红·翠幕深庭》“人境不教车马近,醉乡莫放笙歌歇”,体现了吴文英对《饮酒》隐逸精神的认同,但这种隐逸精神是婉转幽深的,只限于笙歌散尽后个人独享。
受到历史古迹的影响,吴文英苏州词中的隐逸情怀更为疏阔放落,是杭州词内敛的、自悟式的隐逸情怀加入了对历史兴亡的感慨的结果。如《木兰花慢·重游虎丘》中,吴文英亲见虎丘年年游人不断,却无人能看破红尘而清心寡欲,他发出“尘缘。酒沾粉汙,问何人、从此濯清泉”的喟叹,接着付之一笑,以清健之笔结句:“一笑掀髯付与,寒松瘦倚苍峦。”再如《木兰花慢·重泊垂虹》,起句“酹清杯问水,惯曾见、几逢迎”,举杯问吴江,见证千百年来多少人来人往、历史兴亡,颇有太白把酒问月之遗风。“自越棹轻飞,秋莼归后,杞菊荒荆。”此处连用范蠡、张翰、陶渊明三个隐逸典故,将过往的隐逸之士揉入历史兴亡中,最后描写如今的场景“孤鸣。舞鸥惯下,又渔歌、忽断晚烟生”,表明自己也将加入隐士的队列。《十二郎》写重到垂虹亭,萌生人生失意的无限感慨,接着实写吴地风物,“嗟绣鸭解言,香鲈堪钓,尚庐人境”,又暗含隐逸诗人陆龟蒙斗鸭、“秋风斜日鲈鱼香”之典,升发起“结庐在人境”的心愿,下阙透露产生隐逸之念的原因是“念倦客依前,貂裘茸帽,重向淞江照影”,一生羁旅无定,如今一事无成,像苏秦游说秦国不成,破帽貂裘,形容枯槁归乡一般,最后只能“酹酒苍茫,倚歌平远。”“倦客”在集中出现了6 次,表现了词人是因倦而归,因倦而隐的,如《齐天乐·齐云楼》以“倦客”形容范蠡:“宫里吴王沈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宴清都·病渴文园久》“吴宫乱水斜烟,留连倦客,慵更回首”。由此看来,苏州词的隐逸思想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游历古迹时顿感朝代兴亡终将湮灭,对追名逐利顿生倦意,因倦而生隐退之意。这种隐逸精神将个人与历史兴亡联系起来,跳脱出自悟的圈子,因而意境高格局大,词风也较为疏阔。
总之,文化基因、经行地的文化对梦窗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四明文化基因中的士大夫气息为吴文英的词作典雅化奠定了基调,四明地区研究辞赋的热情,加之当时宗柳、宗周的潮流,使得梦窗词中有相当明显的辞赋痕迹。经行地的文化对词人、词作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如苏州浓郁的吊古之风使梦窗词暂时脱离了一贯的软媚绮靡,进而开拓了词集中少有的疏阔雄快的词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