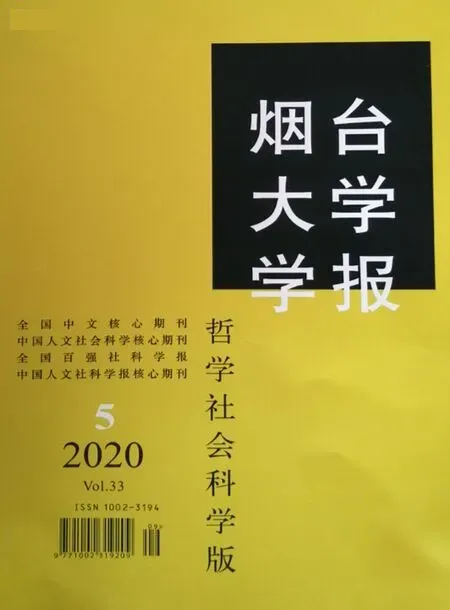历代文献记载中的昭君墓及相关问题
王绍东,汤国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作为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她因容貌出众、品性贤淑被选秀入宫,在宫廷中却备受冷落。昭君不甘于命运的摆布,主动要求远嫁呼韩邪单于到塞外。为了维护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她接受成帝敕令,尊崇匈奴风俗,嫁父子两代单于。昭君去世后,她的女儿、女婿、侄儿及后代亲属继续为汉匈友好贡献力量。个人命运的转折,民间、宫廷、塞外的穿越,胡汉风俗的冲突,民族间战争与和平的选择等种种元素,都凝结在昭君的身上。两千多年来,人们以种种方式表达对昭君的同情、赞美、怀念之情,昭君也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1)崔明德:《和亲 和亲文化 和亲文化馆》,《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众多昭君墓葬的修建,也成为人们歌颂昭君、缅怀昭君的一种方式。
提到昭君墓,常见研究者宣称,除了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座昭君墓。(2)林干、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至于这十几座昭君墓到底分布在哪里,则往往语焉不详。一般人们列举的是呼和浩特市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墓(青冢)、呼和浩特东郊的八拜昭君墓、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朱堡昭君墓、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的昭君坟。近年来,有学者论证山西朔州市朔城区青钟村的昭君墓为昭君真正的埋藏之地。此外,则难以见到其他有关昭君墓的具体记述。本文力图通过对历代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梳理,尽可能对文献记载与传说中的昭君墓的数量、分布区域及其文化意蕴进行分析,请方家指正。
一、历代文献与民间传说中的昭君墓
有人认为,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墓葬最多的女性。通过对历代文献和民间传说的梳理,可以发现,昭君墓葬遍及北方各地,确实达到了十几处之多。
1.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杜佑在《通典》记载:“单于大都护府,战国属赵,秦汉云中郡地也。大唐龙朔三年,置云中都护府,又移瀚海都护府于碛北,二府以碛为界。麟德元年,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领县一:金河。”在“金河”条下杜佑自注:“有长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台、王昭君墓。”(3)《通典》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 单于府》,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5册,第4744-4745页。金河即今呼和浩特市的大黑河,经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北侧南流,这是历史文献中最早的见于记载的“王昭君墓”。
2.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坟。民国修《阳原县志》记载:“然昭君在绥之墓有二。除此墓在归绥外,包头尚有其一,俗称衣冠冢,然包头者固非。绥远者亦未必是。余别有考,见拙著方志学。”(4)民国《阳原县志》卷十五《金石》,《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2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419页。此昭君坟位于包头市和达拉特旗交界处,因民国时期这里归包头管辖,该昭君坟也被人称为包头昭君坟。
3.山西朔州昭君墓。据明万历年间的《马邑县志》记载:“青冢,阔四五亩,高丈余,俗传王昭君墓。”(5)万历《马邑县志》上卷《杂附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石印本,第二十二页a。民国时期的《马邑县志》也记载:“青冢,在县西南三十里,阔四五亩,高三丈余,俗传汉王昭君墓。”(6)民国《马邑县志》卷一《舆图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7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61页。马邑即今天的山西朔州,该昭君墓位于朔州市朔城区青钟村。
4.河北保定定兴昭君墓。清光绪年间刻《定兴县志》记载:“此志乘纪古迹之所由来也。顾代远年湮,传闻异词、附会失实者不少,如青冢在塞外,而本邑有青冢村,遂谓昭君墓在此,此不辨而自明者,然与其过而废也,宁过而存之,以俟怀古者之考证焉。”同卷还记载:“青冢,旧志云,昭君墓在塞外,墓草独青,故曰青冢,今县境东南有青冢村,相传是其葬处。”(7)光绪《定兴县志》卷十四《古迹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第3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367-368页。定兴即今河北保定市定兴县,按志中记载,昭君墓在定兴县东南方向。
5.河北保定高碑店昭君墓。《新城县志》记载:“青冢,汉明妃墓也,吾乡紫泉有大小青冢之村,不知始于何时。杜诗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是青冢宜在塞北极边之地,及检《山西通志》,今在归化城南十余里,黑河之侧。按归化城汉五原郡,距塞北绝远,岂其时王歙辈实导之而遂克返葬,于是与至吾邑。青冢之名,则固歧而又歧者也。”(8)民国《新城县志》卷二十三《识余》,《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5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951页。文中新城即今河北保定高碑店,此地亦有昭君墓、青冢村。
6.河南许昌昭君墓。据明嘉靖年间修《襄城县志》记载:“王昭君墓在县西北”(9)嘉靖《襄城县志》卷一《地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第24页。。在比《襄城县志》早修十几年的《许州志》也有同样的记载:“青冢,在襄西北十五里,旧传为昭君墓。”(10)嘉靖《许州志》卷八《杂述》,《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第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影印本,第480页。许州即今河南许昌,襄城在今河南省中部、许昌市西南部。通过两本地方志的记载,可知许昌市襄城县西北也有一座昭君墓。
7.山东菏泽东明县昭君墓。据清乾隆年间修《东明县志》记载:“青冢在县北十八里,柿子园迤南,冢上各有青草,故名俗传为昭君墓。”(11)乾隆《东明县志》卷一《舆地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51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14页。民国时期的《东明县新志》卷五也同样提到:“青冢,距城十六里,俗传为昭君墓。”(12)民国《东明县新志》卷五《经制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6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68页。
8.山东菏泽单县昭君墓。明嘉靖年间修《山东通志》卷二十二:“青冢,在单县南八里,相传为王昭君墓。”(13)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二《古迹》,明嘉靖十二年刻本,第十五页a。
9.陕西神木昭君墓。在今陕西神木,也有关于昭君墓的记载,清康熙时期与雍正时期修的两版《神木县志》都有“青冢,相传为王昭君冢,塞草皆白色,惟此冢独青”(14)雍正《神木县志》卷三《古迹·陵墓》,《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28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32页。的内容。
10.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八拜村昭君墓。当地民间传说有昭君墓,也有被称为昭君墓的遗迹,尚未发现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
11.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朱堡昭君墓。当地有有关昭君墓的民间传说,也有被称为昭君墓的遗迹,村民经常举办纪念昭君娘娘的活动,但尚未发现相关的文献记载。
也有文章指出:“在安徽、山西、甘肃甚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也流传着青冢的故事和传说。”(15)刘洁:《昭君和亲文学景观的双重呈现——以昭君村、昭君墓、昭君庙为例》,《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这些地区昭君墓的故事和传说源自何处?地理位置处于何方?由于作者没有进一步说明,相关资料尚需继续关注搜集。
在上述十几处昭君墓中,历史上记载最早、关注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墓。继唐代杜佑《通典》后,宋代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述金河县时也提到了昭君墓:“武徳四年平突厥,置云中都督府于此地。青冢,在县西北。汉王昭君葬于此,其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冢。”(16)《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八《关西道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2册,第806页。文中云中都督府即《通典》中记载的单于都护府,并指出昭君墓葬在金河县西北,进一步说明了昭君墓所在的地理位置及青冢的命名原因。
《辽史》在记述丰州时提及昭君墓:“太祖神册五年攻下,更名应天军,复为州。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碛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统县二。”(17)《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册,第508页。清人李慎儒撰《辽史地理志考》卷五则对昭君墓介绍得更加具体:“青冢,即王昭君墓,在今山西大同府治西五百里,辽丰州故城西六十里,今归化城南二十里,蒙古名特木尔乌尔虎,塞草色皆白,惟冢草青,故名。”(18)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卷五,见《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影印本,第8132页中栏。文中介绍了青冢的具体方位,即辽丰州故城西六十里,归化城南二十里。辽丰州故城在今呼和浩特白塔村,归化城即呼和浩特旧城,二者所指向的位置都是今呼和浩特南郊昭君墓。
明清时期,提及该昭君墓的古籍逐渐增多,李贤《大明一统志》记载:“王昭君墓,在古丰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冢独青,故名青冢。”(19)李贤:《大明一统志》卷二十一《大同府·古迹》,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330页。王在晋撰《历代山陵考》,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清官修《通鉴辑览》,明彭大翼撰大型类书《山堂肆考》都有同样的记载,认为昭君墓在古丰州西六十里。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志提及该处昭君墓。《大同府志》卷四:“汉明妃墓,在府城西北五百里大边外,古丰州西六十里。”(20)正德《大同府志》卷四《陵墓》,明嘉靖两淮盐政采进本,第三页。《归绥县志·舆地志》:“汉王昭君墓,在旧城南二十里,高二十丈,阔五十亩。”(21)民国《归绥县志·舆地志》,《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1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115页。《朔平府志》卷四对昭君墓的地理位置介绍得又具体了一些:“青冢一在杀虎口外,归化城东南三十里,黑河南岸路西,高丈余,围亩许。”(22)雍正《朔平府志》卷四《建置陵墓》,清雍正十一年刻本,第一百五页b。文中提到的黑河就是今天呼和浩特的大黑河,而呼和浩特南郊昭君墓正是在大黑河南岸。
不仅有众多的正史、地理书、地方志记述该处昭君墓,历史上也有众多文人笔记提及该处昭君墓。清人钱良择在《出塞纪略》中提到:“昭君墓冢在城南,高阜岿然,望之可见……行三十里至冢前,冢高三十余丈,广径数亩。”(23)忒莫勒、乌云格日勒等编:《奉使俄罗斯日记》,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4页。在一些涉及边疆民族事务及对外交往的文献中,也记述了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明代诸葛元声撰的《两朝平攘录》:“俺答春、秋、冬住牧丰州滩昭君墓,入夏避暑青山。”(24)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一《顺义王》,明万历刻本,第十五页a。在俺答汗时期,昭君墓几乎成为了土默特平原的标志。清代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在记述归化城时写到:“城南负郭有黑河青冢古迹,远望如山,策马往观,高二十丈,阔数十亩。”(25)忒莫勒、乌云格日勒等编:《奉使俄罗斯日记》,第29页。
从唐代以来,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不仅屡见于正史、各类典籍、私家著述中,还大量出现在官修地方志中。历史上很多文人墨客吟咏该处昭君墓,也有很多地方官员到这里进行拜谒题记。再加上该处昭君墓冢体高大,在呼和浩特平原上引人瞩目,所以成为众多昭君墓中认同度最高的一座。以至于历代文献中记述其他昭君墓时,作者往往认为是“衣冠冢”或“讹传”。如《阳原县志》在记述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墓时,认为此处墓葬“俗称衣冠冢”(26)民国《阳原县志》卷十五《金石》,第419页。。《绥远通志稿》:“按此坟以形似青冢得名,本一天然之石丘,并非人造之墟墓也。”(27)绥远省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册,第320页。《马邑县志》记述山西朔州昭君墓时也认为:“考昭君墓在化外丰州沙滩,今以为在此或传者讹也。”(28)民国《马邑县志》卷一《舆图志》,第61页。清光绪年间刻《定兴县志》在记述该县有昭君墓时辨析认为:“汉代范阳为内地,岂得混指,讹,不待辨而明。且传曾有人夜行见火光,因入其中,得与昭君相叙说,更荒唐,必因牛僧孺之记行而效尤者也。昔兵乱时,有人欲发之,会风雨大作,若有大人长丈余护之,遂惧而止。按《新城志》亦有青冢在县东,皆俗说传讹也。”(29)光绪《定兴县志》卷十四《古迹志》,第368页。其他几处见于文献记载的昭君墓,作者也以“俗传”“旧传”等解释之。
二、昭君墓的真伪与墓葬范围
对于昭君的去世时间和埋葬地点,在《汉书》《后汉书》等早期文献中并无记载。前面梳理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发现却有十几处昭君墓。那么,这些昭君墓中哪个是真的昭君墓呢?或者说,其中有没有真的昭君墓?昭君的墓葬范围和分布区域应该在哪里呢?
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墓在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它不仅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而且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对它的吟咏之作,再加上它位于塞外草原,墓冢高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大多认为这里就是昭君的埋葬之地,以至于历史文献记述其他昭君墓时,几乎无不加上“相传”“旧传”“讹误”“衣冠冢”等字样。真正对此墓真伪进行系统考证的,是孙利忠先生的《青冢考》一文。孙先生认为该墓确为真正的昭君埋葬之地,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根据敦煌文书中的《王昭君变文》(《明妃传》)“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一语,考证认为受降城是指唐代的东受降城,它位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境内,呼和浩特南郊昭君墓的地理位置与变文中描述的基本吻合。第二,考古勘探证明该墓确为汉代遗址。“综上所述,得出最后的结论,只有呼和浩特市南郊现存的昭君墓遗址,才是符合历史史实和有据可考的汉代昭君墓。”(30)孙利中:《青冢考》,《中国·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1-171页。
近年来,山西学者撰文,考证山西朔州市朔城区青钟村的昭君墓才是真正的昭君葬地。代表性文章有郑凤岐、齐宏亮先生的《昭君坟茔今安在——王昭君葬在朔州市青钟村的几个证据》。此说提供了以下几条证据:一是根据明清以来的《马邑县志》,“青钟村”曾被记为“青冢村”。二是依据《王昭君变文》,从匈奴牙帐(该文作者认为位于今呼和浩特市)到昭君葬地600里,与呼和浩特到朔州市的距离正好符合。三是《王昭君变文》中“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一语,认为“受降城”可能指唐代的朔州受降城,“黄河”可能是该昭君墓北面的“黄水河”的误记。四是墓葬周围发现了许多汉代瓷片。(31)郑凤岐、齐宏亮:《昭君坟茔今安在——王昭君葬在朔州市青钟村的几个证据》,《山西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A03版。
不论是对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的考证,还是对朔州昭君墓的考证,最重要的依据都是敦煌文书中的《王昭君变文》。《王昭君变文》产生于距离王昭君去世800多年的唐代后期,是一部俗文学的作品。该文对昭君事迹及丧葬情况的描写,主要是一种文学想象,不能把它作为可靠史料对待。实际上,一些学者对昭君墓的真伪考辨持慎重态度,林干、马骥先生就认为:“尽管在青冢(指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附近曾发现零星的汉瓦残片,但毕竟不是用科学方法从墓中发掘出来的,而且数量也少,因此不足以确定青冢确为汉代墓葬。”(32)林干、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第222页。
昭君究竟安葬何处,需再回到《汉书·匈奴传》的原始记载中。匈奴早期崛起于阴山地区,那里曾经是匈奴的“苑囿”,匈奴的单于庭自然也位于阴山地区。汉武帝发起对匈奴的持续进攻,特别是在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卫青击败匈奴主力,“行捕斩首虏凡万九千级,北至窴颜山赵信城而还”(33)《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1册,第3769-3770页。。同年,霍去病发动河西之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左王将皆遁走。票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34)《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70页。汉朝军队的两次大胜,将匈奴赶出了漠南地区。“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5)《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第11册,第3770页。从此,匈奴的统治中心由漠南转移到了漠北。呼韩邪单于附汉后,为了便于获取汉朝的支持,早期主要活动于南部地区。在西汉王朝的支持下,呼韩邪单于势力强盛,“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36)《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11册,第3801页。。随着郅支单于被杀,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匈奴各部,“其后呼韩邪单于竟北归庭,人众稍归之,国中遂定”(37)《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第11册,第3801页。。自此,在整个汉朝,匈奴再无将单于庭迁移漠南的记录。王昭君作为两代单于的阏氏,其生活的地区也必然在漠北地区。
在内蒙古地区及外蒙古地区都有匈奴墓葬发现,但内蒙古地区陪葬品较多且等级较高的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墓葬,如鄂尔多斯杭锦旗的桃红巴拉匈奴墓为春秋末期,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毛庆沟匈奴墓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发现金王冠的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是战国晚期。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西汉时期的匈奴墓则等级较低,随葬品也比较简单,如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补洞沟等西汉时期的匈奴墓,葬具多为木棺,偶有木椁出现,但大多数墓葬没有葬具,这一状况也与匈奴政治中心从漠南转移到漠北的过程相一致。而在蒙古国,“匈奴大型墓葬主要分布于蒙古中部偏北的省份与蒙古中北部和西北部接壤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图瓦地区”(38)潘玲、萨仁毕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在大型墓葬周围,一般分布有普通墓葬组成的陪葬坑,进一步表明了这些墓葬的贵族身份。考古学家认定,“可以将已经发现的匈奴大型墓葬的年代断代为公元前、后之交至公元一世纪早、中期”(39)潘玲、萨仁毕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这一时期与王昭君在匈奴生活及去世的年代相一致。大型墓葬中随葬品丰富,许多物品来自中原地区,表明与中原汉朝有密切联系。“其中高勒毛都2号墓地M1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匈奴墓葬,墓穴边长达46米。该组墓葬都随葬一辆汉式马车,随葬贵重的鎏金或包银的马具,常见随葬品较多的汉式漆器及汉式金属容器,棺外均有金箔装饰。”(40)潘玲、萨仁毕力格:《匈奴大型墓葬概述》,《草原文物》2015年第2期。2019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北麓发现了匈奴大型祭祀性台基遗址,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匈奴的政治中心“龙城”所在。(41)屈畅:《考古学家解密匈奴“龙城”猜想》,《新华网》2018年9月16日。从匈奴墓葬和遗址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在王昭君的时代,匈奴的政治中心及贵族的墓葬地点均在漠北地区。
呼和浩特地区在汉代归定襄郡管辖,属于汉地。王昭君出塞后与汉朝的联系,以及他的儿女、女婿与汉朝的联系,史书中多有记载。出塞后的王昭君没有回过汉朝,也是可以肯定的。可以设想,昭君死后如果归葬漠南汉地,那么史书缺载的可能性较小。从西汉到魏晋时期,昭君的故事广为流传,并且经过了演绎发展,但是,“南北朝以前的著作中,至今没有发现关于昭君墓的记载,特别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对大青山南麓的文物古迹搜罗丰富,记载甚详,如果当时这里有昭君坟墓,他是不会忽略不记的”(42)林干、马骥:《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第221页。。如此看来,昭君葬于漠北地区的可能性更大,而漠南地区的众多昭君墓,很可能都不是王昭君真正的埋葬之地。
目前已知的十几座昭君墓,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地区,这些地区历史上既有民族间的冲突与战争,也有民族间的交汇与融合。这里的人民深受战争之苦,也分外珍惜和平。昭君出塞,化干戈为玉帛,变战争为和平。人们缅怀昭君、赞美昭君,愿意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希望昭君保佑自己的和平生活。昭君成为了一种精神、一个象征、一个各民族间和平友好相处的传说。“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而成为一个中心。”(43)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6页。无疑,昭君墓也成为了昭君精神的纪念物。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44)翦伯赞:《内蒙访古》,《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3日。各地人民通过建筑昭君墓,将昭君的英灵安葬在了自己的内心深处。
三、昭君墓别名“青冢”的文化意蕴
历史上,以“青冢”代指昭君墓,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昭君墓”一词。唐代诗人吟咏昭君墓,多以“青冢”指称。王昌龄(698-757)在《箜篌引》一诗里,最早使用“青冢”:“弹作蓟门桑叶秋,风沙飒飒青冢头,将军铁骢汗血流。”(45)《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一《王昌龄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点校本,第4册,第1436页。李白(701-762)《王昭君二首》(其一),将昭君故事写入诗歌:“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46)《全唐诗》卷一百六十三《李白三》,第5册,第1691页。常建(708-765)《塞下曲四首》(其四):“汉家此去三千里,青冢常无草木烟。”(47)《全唐诗》卷一百四十四《常建》,第4册,第1464页。白居易、杜牧等人,更是直接以《青冢》为题写诗。在唐人众多以昭君为题材并使用“青冢”一词的诗歌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该诗将昭君的出生地昭君村,昭君入宫后的紫台,昭君的归宿地青冢连接起来,刻画了昭君不平凡的一生,也描写了昭君故乡与归宿地的不同景色,广为人们所熟悉。
昭君墓何以被称为“青冢”,历代文人有不同解释。
其一,认为昭君墓上生长的草与周围地区草色不同。《舆地纪胜》认为:“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48)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四《归州》,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本,第3册,第2472页。《读史方舆纪要》对“青冢”记载说:“在府西北塞外,相传王昭君冢也。地多白草,此冢独青,因名。”(4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四《山西六·大同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点校本,第4册,第2018页。此说历代相沿,流传最广。班固《汉书·西域传》在记述鄯善国时写道:“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颜师古对白草进行注释:“白草似莠而细,无芒,其干熟时正白色,牛马所嗜也。”(50)《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12册,第3876页。这种白草一般长在比较干旱的草原地带,昭君墓位于大青山下,黑河南岸,这一区域降雨量相对充沛,并有河流浸润,不是盛长白草之地。白草春夏仍为绿色,深秋季节草干变白。白草的生命力极强,如果昭君墓葬地区生长白草,墓冢之上独变青草的可能性不大。这一说法尽管广为流传,实际中却难以得到验证,因此历代多有质疑。
其二,认为昭君墓上寸草不生,墓冢本身为青色。清代李慎儒在《辽史地理志考》中记述:“案宋荦《筠廊偶笔》,嘉禾曹秋岳先生尝至昭君墓,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蒙作黛色,据此则是冢色自青,非草青,也可证古人记载之误。”(51)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卷五,见《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影印本,第8132页。清王应奎《柳南续笔》:“青冢,王昭君青冢,在归化城塞上,遍地白草,惟冢上不生,故名青冢。非谓冢上草独青也。”(52)王应奎撰,王彬点校:《柳南随笔 续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44页。昭君墓位于大黑河畔,是用泥土堆起的高台,历来草木青葱,何以会出现没有植被的情况?当地土壤呈白黄色,也并不是青色泥土,此说无疑存在漏洞。
其三,认为远望昭君墓,水汽笼罩如同青色雾团。张相文写到自己拜谒昭君墓时的观感:“昭君墓烟霭蒙笼,远见数十里外,故亦曰青冢。”(53)张相文:《塞北纪行》,《南园丛稿》(民国丛书第五编第98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9页。韦岸也认为:“昭君墓位居黑河之旁,远远地隔河望去,湿气蒸腾氤氲,旷野苍天之下,墓冢兀起之状遥遥入眼帘,仿佛青光所聚,时人名为青冢,亦合法度。”(54)韦岸:《青冢琐议》,《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崔迈农写自己到昭君墓时,“也曾‘远而望之’但看到的是一个高大的坟堆,并没有冥蒙作黛色的景象”(55)崔迈农:《“青冢”新解》,《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1期。。这样看来,这一解释的认同度也并不高。
以上对昭君墓别名“青冢”的种种解释,看似各有理由,实则多有牵强。诸说既难以获得学界普遍认同,也不能得到实际验证。我们认为,要想准确理解“青冢”的含义,需要从其本意和接受史的角度加以分析。
在王昌龄、李白、常建等唐代诗人较早使用“青冢”一词时,都没有解释该词的特定含义,那么我们应该回归“青冢”本身。查《故训汇纂》,对“青”字的解释达30种之多,但用于“青冢”中,似乎两个含义较为贴切:一是“青,东方之色,以取发生之象”。东方之位与春天对应,东方之色也就是春天植物初生时的绿色,发生之象是指春天万物生长的景象。一是“青,谓草色也”。(56)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下册,第2467页。是说“青”指青草的颜色。青冢的“青”当指绿色的草原。对“冢”的解释包含:“冢,高坟也。”“冢,本意为山顶。山顶必高起;凡丘墓封土高起为垅,与山顶相似,故亦通为之冢也。”(57)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上册,第205页。那么“青冢”的本意无疑是指“绿色草原上的大墓”。这一含义无需过度引申发挥,也符合古代人们初见昭君墓时的印象。昭君墓位于呼和浩特南郊,在历史上,周边是一片绿色草原。昭君墓主体高大,在草原上引人瞩目,人们远望该墓,犹如一座小山,无不留下深刻印象。胡凤丹在《青冢志》序言中写到:“客有自塞外归者,语余曰:‘间尝涉大汉历绝徼,黄沙卷地,白草黏天,有坟三尺,孤峙其间,断碑无字,郁郁芊芊,斗高月黑,微闻佩环,盖昔明妃埋玉之乡也。’”(58)可永雪、余国钦编纂:《历代昭君文学作品集》第七编《散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写的也是在辽阔草原上看到一座凸起的大墓,当得知是明妃葬身之地时,留下了诸多的感慨和叹息。“青冢”指“绿色草原上的大墓”,犹如呼和浩特的蒙古语为“青城”,意指“绿色草原上的城市”一样,不必过多诠释,亦无违和之感。
以“青冢”代指昭君墓,符合人们初见昭君墓时的印象。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参观昭君墓,在未过大黑河时,就能够远远看到在绿色青葱的田野里,矗立着一座如同小山一样的圆丘墓冢。实际上,历代文人墨客及人民大众愿意用“青冢”指代“昭君墓”,还在于“青冢”本身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人们对“青冢”意蕴的领会、解读和接受。
首先,以“青冢”代称昭君墓,意指人们对草原环境的描绘与接受。青草绿茵、蓝天白云,是最美的草原景色。风吹大地,牧草起伏,犹如碧波荡漾的大海,让人心潮澎湃,心旷神怡。提到“青冢”,人们自然联想到莽莽草原上的昭君墓葬。杜甫诗《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59)《全唐诗》卷二百三《杜甫十五》,第7册,第2511页。此诗指明青冢位于朔漠草原,人们来到昭君墓区,“青草和大冢是映入眼帘的最醒目、最有特征、最具典型性的事物。不仅如此,诗人又以山清水秀之乡村、人迹罕至之朔漠、黄昏残照之时节,孤零零之青冢布局,营造出一种凄凉气氛,催人遐想、感慨”(60)陆德阳:《青冢之辨及其意象——兼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三的艺术特征》,《学术界》2015年第6期。。以“青冢”代指昭君墓,自然令人联想到昭君从汉宫来到草原,并将自己一生献给这片美丽草原的不凡人生。
其次,以“青冢”代称昭君墓,意指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与接受。绿草茵茵,牛羊成群,是草原人民生活宁静幸福的象征。游牧生活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在风调雨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牛羊得到丰美的水草,膘肥体壮、繁衍生息;人们有充足的奶肉食品供应,生活富足惬意。孩子们骑羊捉鼠,尽情嬉戏;大人放牧挤奶,自由自在。牧民定期聚集,摔跤射箭,“走马及骆驼为乐”(61)《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10册,第2944页。。牧草青青,草原人民过着一种“宽则人乐无事”(62)《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点校本,第9册,第2900页。的生活。但游牧生活也极易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旱灾和雪灾。草原出现大旱时,牧草稀疏枯黄,蝗虫遍野,牲畜得不到充足营养。史书记载匈奴时期北方草原多有旱灾发生,“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63)《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10册,第2942页。。大规模降雪则将牧草覆盖,牲畜无法觅食。有时大雪发生在春季,牧草不能及时返青,也会导致牲畜瘦弱病死,无法保羔。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和产品难以长期保存的特点,当灾荒发生、牲畜大量死亡时,牧民生活难以为继,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或各部落间彼此征战,或者对农耕民族发起掠夺战争,必然出现“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64)《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9册,第2879页。的局面。牧草茂盛,对游牧民族也意味着和平和安定;而牧草不能正常生长,往往伴随的是灾难和战争。昭君被埋葬在一片绿色的草原之上,则意味着那里的牧草繁盛,能够和平安定。昭君出塞,极力维护汉匈之间的和平,人们自然希望昭君的英灵仍然护佑草原的和平。
最后,以“青冢”代称昭君墓,意指人们对昭君形象与人格的赞美与接受。昭君以美丽绝伦的容貌,秀外慧中的气质被选秀入宫。在临辞大会上,她“丰容靓丽,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65)《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10册,第2941页。,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尽管昭君为了维护汉匈友好关系远嫁塞外,最后终老朔漠草原,但昭君在人们心目中,总是“沉鱼落雁”的美好形象。以“青冢”代指昭君墓,人们想到的是美丽的昭君、青春的昭君。昭君的一生,既有为追求个人幸福而毅然出塞的果断抉择,也有为了维系汉匈关系而“从胡俗”的忍辱负重。昭君将自己献给了汉匈双方的和平事业,带来了汉塞安宁、匈奴统一、战乱消弭的和平局面。“汉家天子镇寰瀛,塞北羌胡未罢兵。猛将谋臣徒自贵,娥眉一笑寒尘清。”(66)《全唐诗》卷六〇二《汪遵》,第18册,第6961页。昭君的笑容,具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力量,胜过了那些自以为是的贵臣猛将。青山埋忠骨,青冢葬英灵,在人们的意识里,“青冢”里必然安葬着一个不朽的灵魂。
总之,人们看到昭君墓时的最初印象就是一座“绿色草原上的大墓”,王昌龄、李白、常建、杜甫等唐代诗人以“青冢”入诗。由于“青冢”一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象,更被历代人们所接受并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