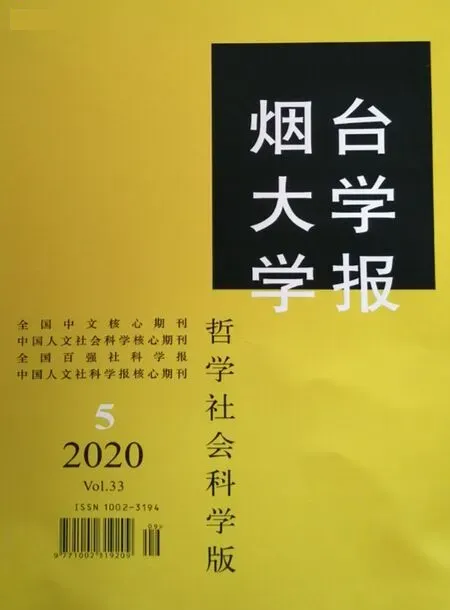日常生活视野下诗歌的生命关怀意蕴探索
——以《诗经·卷耳》为例
杨增艳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回归生活世界是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的普遍趋势,即通过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关注来考察现代性大背景之下人的存在状况和困境,并思考超越“当下”困境的路径,以期为生命的价值意义及其安顿作出各自的探索和解答。以此视野观之,不难发现《卷耳》一诗也是围绕着“采卷耳”这一日常之事而展开的,这种对日常生活场景的表现似乎并不具备形而上的超验意味,也没有为生命提供某种本体性的依据。《卷耳》对日常生活二重性之特质的展示显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悖论式的艰难的生存处境,但全诗并未营造出一个逼仄的意境空间,从而将人引向往而无返的空虚绝望,而是在忘与不忘的往而有返间,展开一种整全视野之下的统一的生活何以可能。由此可见,《卷耳》一诗中含藏着生命安顿智慧,可以为我们反思现代生命分裂和异化的存在现状,实现对生命的关切、关怀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和切入点。
一、从遗忘到回归:西方日常生活理论兴起的缘由
“回归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以来的西方哲学或现代哲学的普遍趋势,也是现代的基本或根本精神。”(1)李文阁:《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回归与背离相对,这里隐含了一个从遗忘再到重拾的转变过程。需要阐明的是,将回归日常生活作为理解现代哲学的关键,并不是讲在东西方传统中不存在日常生活的概念,也不是说先贤们对此问题并无关注和反思,是指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概念范畴重新进入哲人们的视域。抑或说,日常生活作为社会理论或文化表征的主题是在现代才形成的。(2)参David Chaney, Cultural Change and Everyday Life,Palgrave,2002,p.5.那么我们可以思考这种对生活世界的暂时“遗忘”是如何发生的?由“背离”到“回归”的缘由究竟为何?这种“回归”对于反思生命的困境有何现实关怀意义?既然现代日常生活理论发端于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探讨现代哲学的这一重要转向,势必要回溯至西方文化的发展脉络中。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哲学的概念进行界定,都不能忽视哲学在古希腊的起源和开端源于对如此这般存在着的现象世界的“惊讶”。而对具有形而上超验意义的世界本原的探讨,也是由具体的客观自然界开始的,希腊早期的自然哲人甚至将水火土气等物质性的存在视为世界的本原。只是经过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巴门尼德的推动和发展,在柏拉图的学说中,超越物质性与现象世界的不变的“相”成为万物存在的本体性依据,进而严格地区分出感性世界与本相世界两个不同的世界。古希腊对于世界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虽然为生命存在提供了某种同一性的始基,奠定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但这种对世界的超验性根据的重视,也是丰富、鲜活、具体的现象世界被遗忘或否定的开始。
从十七世纪开始西方近代哲学将探问的目光着眼于人对世界的认知问题,突出思考主体的理性的认知功能和作用,试图通过演绎、推理等获得对事物以及世界的清晰认识。自笛卡尔以来,揭示知识的本性与可能性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必要前提,成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可以说近代哲学从本体论朝认识论的转向,基于人对自身和自我与周围世界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而“笛卡尔完全拒绝了古代目的论的思维模式,并抛弃了所有关于实体逻各斯的理论。借助伽利略倡导的分解/综合法,宇宙被机械地加以理解”(3)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王成兵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关于世界本性的基本图景作为一个时代的人对世界整体性的理解,会直接影响、作用、显化于人的思想和观念。以机械论世界观为指导的科学实证方法“以实验为知识来源,以数学公式为描述语言,以数学演绎为指导原则,寻求可由实验确证的新现象”(4)戴克斯特霍伊斯:《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7页。。这就促使物理科学蓬勃发展,加速了近现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机械化与工业化的进程。近代科学革命带来知识观念的变革,再经过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科学被视为人类一切认知的典范。实证方法一般被运用于物理科学领域,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这种研究方法也开始渗透到其他非自然研究的学科之中。当以科学计算与数学实证方法对人类文化进行重新的建构与解释,认为借助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一切时,导致的结果是理性自身的内涵发生了嬗变,理性由主体内在对自然秩序的觉知或一种万物依此运行的准则下降为工具理性。对精确性和明晰性的追求不仅成为科学自身的追求,甚至连哲学都需要建构出具有“几何学样式”的统一的理性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
依据前述思路,当数学作为科学的本质特征,具有数学精密性的自然科学成为严格且富有成果的科学学科的典范时,哲学不得不面临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胡塞尔对哲学的重新建构,其初衷是想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间找到哲学的位置,以期哲学“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需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都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支配的生活何以可能”(5)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 这种以构造现象学形态呈现的严格意义的哲学,是想为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奠定基础。毋庸置疑,以严密、精确的数学逻辑为基础的近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知识结构,世界可以凭借实验测量等实证方法成为我们认知的客体,但是这种“以用数学方法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生活世界”(6)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4页。。换言之,近代哲学以实证方法来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却造成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这种被数学重新赋予意义的理性观念世界反而取代了鲜活的生活世界,加剧了理性世界与日常生活的分裂。因感性会造成认识的谬误与错觉,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遂将关于人性的精神性的东西抽离出来,那些交织构成生命内在的或明或暗的非理性因素也都被科学排除在外,科技成就所带来的满足感,似乎使得人们不再需要思考生命的价值与安顿等诸多“无意义”的问题。在胡塞尔看来,哲学所遭受的危机同时是作为哲学的多方面性的诸环节的一切近代科学的危机,归根结底则是人的实存性危机。想要解决这种危机,就必须回归到这个比科学世界具有优先性的,人生活在其间并保持着目的、意义与价值的,被科学世界所遗忘的生活世界。虽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念并非现代意义的体系性的日常生活理论,却是一次对已然被“遗忘”了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对于二十世纪的哲学诸流派重新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具有深刻的奠基性作用。
海德格尔在胡塞尔的基础上,看到了在科学技术时代生活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人的实存性危机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阐释。前期海德格尔是在“基本存在学”的视域之内,以“此在(Dasein)”为中心来探讨和处理人的存在问题以及日常生活的观念,在海德格尔看来,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一种基本建构,此在不仅是在世界之中并且是以日常生活的方式而活动于世界之中。“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己就是常人自己。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常人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的方式而存在。一作为常人自己,任何此在就涣散在常人中了。”(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80-183页。因此,日常生活状态作为此在之存在模式,可以更为根本地揭开此在之在世特征。通过对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非本真状态的揭示与分析,海德格尔对人的异化处境作了全面的论述和展开。
由于理论化的思辨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分离,以及现代日常生活自身边界的模糊性,使得日常生活更多地是作为一个被各个学科划分之后所剩余的残留之物,未曾得到真正的关注,人们对这个自身所处的生活世界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样,列斐伏尔看到了日常生活作为人所有活动发生和交汇的场所,在人的生存与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正是这个人生活在其中的微观世界,却能映照出复杂而丰富多维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但是列斐伏尔同样看到了日常生活之结构和实质在现代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通过对“每日生活”“日常”“日常性”等概念的分析,指出现代日常生活已然呈现出同质、重复且碎片化的特征。基于此视角,如何让这种同质化、无差异的日常生活回归本真面貌,充分发挥其在生存与交往中的基础性作用与价值等问题便凸显出来。
列斐伏尔创新性地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指出在现代社会异化已经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倘若哲学想实现对生命存在境况的把握与关切,必然得重回日常生活世界,并通过对现代性文化的批判与重建使自身重获生机。于是,他将“哲学上的日常生活概念与它的演进形式的社会学分析系统地合并在一起”(8)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5-266页。,明确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的概念。尽管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体系异常庞大,且在不同时期对日常生活的界定与批判也各有不同与侧重。但总体而言,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于研究具体的人性,考察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生命的异化状态,并最终扬弃这种异化,实现人全面的发展和自由。概言之,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的任务就是研究‘我们如何生活’”(9)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除此之外,卢卡奇、科西克与赫勒等思想家也对日常生活进行了考察,并形成了各自的日常生活批判体系。现国内亦有不少名家对他们的理论体系作了详细深入的探索,且成果丰硕,故本文不再展开论述。
从以上不同哲学家对于日常生活概念的阐释来看,倘若我们想要厘清日常生活这一概念,并对日常生活所面临的危机加以把握时,不难发现日常生活是一个立体多维的概念,现代哲学家们对其定义和反思也是从多个角度来切入的。当从哲学、社会学、美学等视野下去考察日常生活所受到的冲击时,因反思主体的差异,对此问题的探索和解答也会有深浅、高低等程度的不同。若暂时搁置对诸多思考差异之对比,可以发现对理性主义传统之弊端所引发的哲学乃至日常生活的危机和现代人之生存困境的清理、审视共同构成了哲学家们回归日常生活的重要缘由。他们关心和直面的都是日常生活境域中人的意义实现和命运归宿的问题。而在具体的探问方式和价值旨归上也能找到几者间内在的一致性:第一,都是从日常生活出发,通过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状态和运作模式,来贴近、考察鲜活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揭示人的基本处境;第二,立足于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现状,思考克服生命异化状态,进而重启一种本真的、统一的、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第三,从日常生活内部挖掘其自身潜藏的生机与价值,充分发挥日常生活对于生命安顿的奠基性作用,实现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生命关怀。总述之,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理论与实践探讨,都是牢牢围绕着考察生命困顿,回归生命本真,实现生命的自在与安顿这一核心而展开的。从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提出再到现代日常生活理论的建构,都可视为对这一生命关怀精神的不断推进。
二、稳固与断裂:《卷耳》对日常生活的展开
“中国文化及其审美的情理结构是以此世人生为根基、为极限。生活的意义就在生活之中,就在自觉地享用这状似琐碎平凡却正是人生实在之中。”(10)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5-126页。尽管《卷耳》一诗没有建构出西方式的日常生活理论体系,但是其从平凡琐事出发,对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与一般图式作出展示,并对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处境和根本问题,以及人类生活的意义和可能方式进行了探索和思考。(11)参柯小刚:《生命的余闲与整全:诗经〈葛覃〉〈桑中〉读解》,《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在这个意义上,《卷耳》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西方日常生活理论有紧密的内在一致性。而挖掘《卷耳》所包含的生命关怀智慧,无疑对审视与反省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超越生命的物化、异化状态提供了值得参照和借鉴的重要资源。鉴于此,下文将展开细致的论述。
对《卷耳》之诗旨的解释,历代都有不同,《诗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12)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7页。因《郑笺》多依据《诗序》和《毛传》之说,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也是以《诗序》为根本并在整合诸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解释传统,因此“后妃之志”可以视为汉唐《诗经》学对于《卷耳》诗旨的通常理解。至宋代,对《卷耳》诗旨之阐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朱熹在《诗集传》中注解《卷耳》时,认为此诗不仅有“后妃怀文王之意”,同时也突出了“文王后妃之德”。因身处特定历史时期,船山在《诗广传》中认为《卷耳》兼具“慎密”与“广博”的智慧。(13)见柯小刚主编:《诗经、诗教与中西古典诗学:古今通变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尽管各家都对诗歌中物象的名实做了不同程度的考辨,从不同层面对其诗旨进行了阐释,但是可以看出几种解读要么侧重诗歌“言志”和“载道”之功能,更加突出诗歌对于大众群体的道德教化作用,要么更为重视诗歌展示的形而上的精神内涵。于是乎,作为日常生活经验的“采采卷耳”似乎作为一种思想的起兴或理解诗歌的背景而被隐匿或消融在解释者的视野之外。概括地说,比起诗歌中鲜活但是处在形而下层面的物象,解释者们似乎更偏重于诗歌所揭示的深层寓意。不可否认,《诗经》中的物象大多是为“起兴”之用,与山水田园诗歌中详细描摹的具体之物存在一定的差异;从《毛诗正义》“诗者,设言尔”的解释传统来看,《诗经》中的物象不一定是实指,而是传达特定的思想;并且《诗经》作为经典,具有劝谏或道德教化之作用,本身就有形而上的精神实质。但无论《卷耳》本身蕴藏着多少迄今为止仍未被彻底展开的意蕴空间,都不能遗忘所有超越性意义的阐发都建立在采摘这一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之上,也正是这些鲜活的日常生活经验本身构成了诗歌创作主体丰富的精神空间得以呈现的坚实基础。也就是说,所有“情”与“志”的生成都无法离开与创作和思考主体产生沟通与交往的“物”,以及这个让“物”生长与居留的日常生活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卷耳》中的采摘卷耳,《芣苢》和《蒹葭》中的采摘芣苢、荇菜,《葛覃》中的采葛做衣,以及《七月》里的农事劳动,因是对日常生活场景不厌其烦的反复描写,便会显示出日常生活的细碎、繁琐与杂芜,但回到略带粗糙质感的日常生活本身,却使得我们真正触摸生活之肌理。日常生活中交织着诸多或明朗或幽暗的变幻因素,使得人在此间能够遭遇生发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蕴藉出复杂深邃而又模糊不定的生命内在体验,于是我们在看到日常生活多维多层次的丰富性的同时,也对人的生活常态和生存状况有了一个近距离的体贴,由此可以从一个更加广大和完整的视野来察照和理解生命本身。
因此,暂时悬搁采卷耳、采葛等是否为纪实的论证,仅从采摘卷耳这一生产活动来看,似乎日复一日的劳作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论采集的对象为何,手头上所做的具体的事情填充了日常生活,重复而单一性的采摘劳作使得日常生活呈现出某种稳定和不变的特质。而农事之为农事,预示着植物生长在这土地上,以及人在其中的“看守”与“管理”。在传统农耕社会,劳作意味着人们需要深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历法,遵守固定的自然节律,在这种时节的固定变换中筹划自己的生产生活,进而形成一种相对固定而重复的日常生活。列斐伏尔指出:“在古代社会,基本过程是循环,而且这些循环非常接近宇宙循环和来自自然的节奏。而节奏作为一种组织因素支配着农业社会:时和日、季节和年份、代、年轻和衰老。”(14)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第二卷)》,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07页。将稳固不变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并不是讲日常生活中没有波澜起伏的变幻莫测,也不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人无需遭遇生死等极端性生存困境,也不意味着不同个体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同质化的理解,因为每个人所面对和体验到的生活世界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也只有从每个独特个体的生活世界出发,才能对个体生命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生活世界作出理解。
所谓日常生活的稳固不变性,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其一,在这个循环的时间结构之中,人们因循四季的变化来从事日常生产,在生命的诞生消亡中人类历史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因此,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斗转星移的季节变化,生老病死的生命来去,但恰恰是在这交替循环变换的固定节律中,使得日常生活在沉潜往复的时光变迁中,仍旧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寻觅得到这种不变的特质。其二,日常生活以宇宙自然的节奏作为参照,则意味着人对这个节奏的体认和应和,在这种顺应之中人建构起一种与天地自然和谐一致的关系,从而消融了主客之间紧张、冲突的对立,呈现出人与自然平和稳定的一体性。其三,虽然在四季之中的劳作聚集着人对土地的操劳、忧心、筹划,应时而作的繁重劳作也显示出时间之于人的紧迫性,人需要经受住蕴藏于时间中的不稳定因素。但这看似紧迫匆忙却仍旧固定的劳作节奏,却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了时间与人律动协调的有序,反倒削弱了时间所带来的紧凑和压迫。尤其人对土地的守护与土地之于人的馈赠,使得人的存在获得一种切实的物质性保障,给予人一种稳妥的生存的踏实感。于是,这种稳定性构成日常生活平凡却生生不息的前提。
显然,这种涵盖了人的整体性生存活动的相对重复却稳固有序的日常生活模式为生命的存在构建了一个稳定自足的生存空间,提供了一个立足点,在这种安稳处境之中人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审视、反思自我生存处境时的冲突和断裂,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之价值和意义的始基,人在日常境域中获得与世界整体性的统一。但人作为日常生活之主体,亦是一个能思的主体,对存在“发问”是其独特的存在方式之一。人一旦发问,即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对象,对象意识的建立同时意味着主体区分出自我与他者的差异,预示着主体发现生命内在潜藏着的不能被一个宏大的意义整体所覆盖的复杂性和悖论性。这就说明,“日常生活的图式和结构具有抑制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的倾向”(15)李小娟主编:《走向中国的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页。。而当日常生活的稳固结构与主体的能动性之间产生了冲突时,“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行就会中止,而进入一种冲突与裂变状态,日常生活主体开始体验到日常生活的沉重、痛苦、不幸,会感到无法继续承受日常生活,或感到日常生活的劳作已失去意义。这属于日常生活的内在冲突或裂变”(16)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那么,这种对平静无虞之日常生活状态的打破是如何发生,或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到《卷耳》一诗中。
在《卷耳》中,这种稳定的日常生活内在所发生的裂变大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思之不见的愁绪。且不论思之主体以及对象,“嗟我怀人”都是诗歌的重要主题。从诗歌的内容来看,采摘随处可见的卷耳却始终装不满这浅浅的小筐,心有所念故登高山而远望之,道阻且长,茫然四顾无所依,以致马瘏之、仆痡之,由此采卷耳之人内在深深的惆怅和情绪便扑面而来。诗歌通过对主体情绪的把捉和细致描述,一种缠绕心间却又无法言说的内在情感便流露出来,而诉之不尽的情感和无处诉说的无力构成一重矛盾,于是一个无法被共相化、抽象化的活生生的内在充满纷乱、紧张情绪的整体人的形象就被勾勒出来了。第二,山河悠远与生命渺小的对比。从宏观的生命现象来看,生命在不断繁衍,在生生不息地延续着。个体生命却有生有灭,生命再激烈的情感和体验在宇宙天地间都显得微不足道,相较于循环不息无始无终的时间而言,人不过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碎片,《卷耳》中“怀人”与“崔嵬”“高冈”的对立,都真实地表现了有限自我与无限世界的一个潜在冲突。由是可知,从微观的情绪所引发的内在惆怅无奈,再到宏观的有限与无限的遥远距离,归根结底是个体生命在连绵无限的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隔离与断裂,最终关涉到生命安身立命根基的确立,以及生存之终极价值的解答和实现的难题。
因此,《卷耳》对日常生活内在稳固但又断裂的二重性的展示,也说明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存在悖论。假若过一种纯然顺应稳定的自然性的生活,则人便沉溺在一种庸碌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重复在日复一日的循环时间里,这不仅会造成对主体生命意志的忽视或削弱,而且人生的意义也得不到进一步的深化和确认,那么生命可能会陷入无所适从的茫然与焦虑之中,主体失去了本真的自在与自由。但是主体一旦面对自我,试图在这浩渺的时空之中寻找自身的存在位置时,就会看到各种细微而深层的生命意绪在暗流涌动,就必须得经受自身内在的分离与对立,承受找不到“我”的失落。那么,从日常生活本身存在的矛盾二重性中便引导出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如何在日常生活境域中安顿好生命?或者说,如何透过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悖论来研究“我们如何生活”?
三、往而有返: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安顿
《论语·阳货》中记载:“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17)《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9页。《卷耳》为《国风周南》第三篇,《卷耳》全诗描绘了人在此世不可不面对的忧思别离、求不得的苦楚,不得不直视的生死、有限,故诗歌凸显的不再是某一个体的情绪,而具有了集体无意识般的普遍性,抒写出一种存在论意义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感受得到的正墙面而立的逼仄之感。但《卷耳》通篇却没有将人拖曳进一种悲愁凄惨的小我苦情,相反,表现出经历过种种求之不得的哀伤之后,仍旧可以坚实地站立在这大地之上的深情。在采卷耳与寘周行的“忘”与“不忘”之间,使生命显现出能够“承重”的力量感和柔韧性,展开整全视野之下的统一的生活何以可能。
诚如雅斯贝尔斯所言,“人在生存之中必然会遭遇到‘界限状况(Grenzsituationen)’,如‘痛苦(Leiden)’‘死亡(Tod)’等”(18)俞吾金:《生存的困惑:西方哲学文化精神探要》,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那么当日常生活的平和被打破,生命被逼进一个无法回旋的狭窄空间时,人会倍感意义的失落,生命赖以存在的根基被攫取,人在这种边缘化甚至极端化的困境中触及到生存的“界限状况”。在《卷耳》中因怀人而忧思深重,于是才有了“采采卷耳”却“不盈顷筐”甚至“寘彼周行”,感觉到生的徒劳及劳作的无意义。《荀子·解蔽》云:“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壹于道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身尽其故则美,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19)《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5页。从这个层面来看,在这种难以让心专注于一事的处境中,人便会一心二用,于是连易得之物、易做之事都很难得到和完成。若依循引文思路,当作为手头上不断重复的日常经验“采采卷耳”与生命内在强烈的“嗟我怀人”的情绪产生冲突时,可以通过专心其中之一来弥合这种分裂:向内溯源至更加深沉的自我,抑或回归到脚下的生活大地,从而让浮动不止的纷杂的心绪得以平复,让生命获得一个委身的栖居之地。
具体而言,第一条探寻路径就是专心怀人而“寘彼周行”,进而退回到内在自我,将自我之视域全然附着在自己所思、所想的人事,或者缠绕在这股萦绕不去的悲愁情绪里,人经由情绪或感受带来的实在而确证到自我。可问题在于,一旦固着于“我”,人要么怨远方之人一去不顾返,杳无音讯,要么哭诉心中悲悲戚戚无尽感伤之情。如此一来,看似人全然专注于一物,专心地守着这些内在的情感与感受,不可不说是“情之深也”。但是,这种对内在自我的“专心”,反而又将自我规定在一个更为狭窄的境域之中。看似是一往情深,反而是情的贫乏。换句话说,这种对“自我”的过分固着,不仅将自我封闭成一个与外界隔离开来的“单子”,甚至连自我内在都是分化、不合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看似是对他者之爱的充盈,实则很容易变成一种爱的“暴力”。从另外一条解决路径来说,将远眺的目光收拢到当下的日常劳作之上,回归于日常生活之中,让这些思绪都消散在这无边广袤的日常境域之中,生活就是当下,这年年岁岁的平凡生活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其结果就是生命无法从滞缓的日常生活之中抽离而出,在对日常生活的顺服与妥协之中,生命因被降解为自然性的存在而显出疲乏之态,丰富生动的意趣被淹没,使得日常生活也被板结为同质化、单一化的了无生趣。这种稳定固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整齐划一的同一性,却也阻碍我们走向万物以及活泼泼的生活本身。据此可知,固执于“一”虽能将心制于一处,却会加剧心灵与生活空间的封闭和狭窄,使得生命缺乏可以伸展的空间和弹性,这恰恰是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界限和限度。
诗之为诗的根本在于“有余,有间,使生命免于‘正墙面而立’的逼仄。使人对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有一种通达的理解和想象力,可以感受万物的生气……待人接物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20)柯小刚:《生命的余闲与整全:诗经〈葛覃〉〈桑中〉读解》,《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卷耳》一诗虽抒发“怀人之意”,却嗅不出一丝令人无法忍受,乃至将人带入空虚绝望之境地的压抑气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诗歌对于意境空间的建构,使稳固平凡却又是生发价值、意义等超越性精神之源的充满无尽可能性的日常生活与主体丰富的生命意趣之间建立起一个张力场,让人的视域在退回到内在一隅时,仍旧看得到一个外在的超越自我的广大天地,那朝向远方的忧思目光,最后都能聚拢到鲜活而踏实的日常生活。这种由上及下、由远及近、往而返之的空间构筑,是诗歌蕴含的精神意境,从根本上来说,则让生命有一个可以回旋的开阔空间,是诗歌含藏着的生命在日常境域中的安顿智慧。关于这一点,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作了细致的阐释:
中国人与西洋人同爱无尽空间(中国人爱称太虚太空无穷无涯),但此中有很大的精神意境上的不同。西洋人站在固定地点,由固定角度透视深空,他的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中国人对于这无尽空间的态度却是如古诗所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中国人面对着平远之境而很少是一望而无边的……我们向往无穷的心,须能有所安顿,归返自我,成一回旋的节奏……中国人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他的意趣不是一往不返,而是回旋往复的。唐代诗人王维的名句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韦庄诗云:“去雁数行天际没,孤云一点净中生。”(2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95页。
结合《卷耳》的具体内容来说,诗歌以卷耳、高山、马等这些常见的意象来描述日常生活场景,但是随着主体内在情绪的变化和推进,同一个意象所营造和带出的意境氛围却截然不同。例如,同样都是“老马”这一意象,却有“我马虺隤”“我马玄黄”“我马瘏矣”的前后变化,再对照结合“周行”“崔嵬”“高冈”等意象,在这个由意象相似反复却又随时空变换而带动产生的思之变境中,整首诗便呈现为一个由上到下、由小到大的回旋往复的叙事结构,进而引出无限与有限即绵延不息的日常生活和倍感断裂的个体生命之间的紧张。但是诗歌没有一味描写山岗之广袤而将人的目光牵引至一个遥远无尽的无极之处,也并未极尽渲染凄凉情绪而将人带向虚无,让人在驰向无极之时却不知归处,而是目向无极亦能复回活生生的卷耳、老马。在这种从有限到无限的往复回旋中,打开的是一个越来越丰富生动,越来越明朗开阔的空间场域,呈现的是一个更加多维整全的观照视野。这样一来,即便在广袤的山河天地间看到了个体的生死有限,生命的断裂也没有被弥合,却能感受到生生不息的鲜活的日常生活朝人展开的无限生机,获得了一种对生命的重新体认,继而能以一种更加坚韧有力的精神与态度走向生活。
从这个角度再来重新引入船山对于《卷耳》一诗的解读:“不忘其所忘,慎之密也;忘其所不忘,心之广也”(22)王夫之:《诗经稗疏·诗广传》,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02页。,就能愈加深刻地理解《卷耳》所彰显的生命安顿智慧:不因卷耳易得,浅筐易满,而一味埋头采之,遗忘了周围的空间与远方之所思;也不因牵挂远方之人,而一味忧虑甚至怨恨,忽视了这活生生的生活境域,看不见手边鲜活的卷耳。在这“忘”与“不忘”之间,看似采卷耳之人未专于任何一事,却与“远方之人”和“手边的卷耳”都处在一种“切近——远离”的亲密而疏离的关系中。恰恰是在这种看似或远或近的不定的张力中,方显出其情之真、其意之切。由此,也让看似已然陷入断裂、空漠和虚无的生命,重又经受住这无可排解的忧愁,重又满怀期待与向往地捡拾起这浅浅的小筐。
四、结 语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异化是永不停歇的,由是观之,亦可谓只要有生命现象存在,异化就无法避免。尤其随着现代性的进程,现代人的生存处境较之前现代时期有了巨大的差异,生命的物化和异化程度更甚。如果说《卷耳》建构了一个能让生命朝向无限而返归有限的张力空间,而单向度的统一的现代社会,则诞生了一种看似繁荣充实却扁平压抑的逼仄空间。诚然,透过《卷耳》来分析日常生活并审视人的存在困境,或许会因时空差异而显示出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以日常生活的视野考察生命在日常中的处境和生活状态,挖掘诗歌蕴藏的生命安顿智慧,并非试图以诗歌的精神内涵去统摄现代日常生活,让渗透于日常生活诸方面的异化现象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而在于突出重复平凡且琐碎的日常对于生命生存的重要意义,探索日常生活所含藏的生命关怀价值,并进而让这种思考以及这种思之方式达乎的“同一者”,启发我们通达一种富有生气与活力的整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