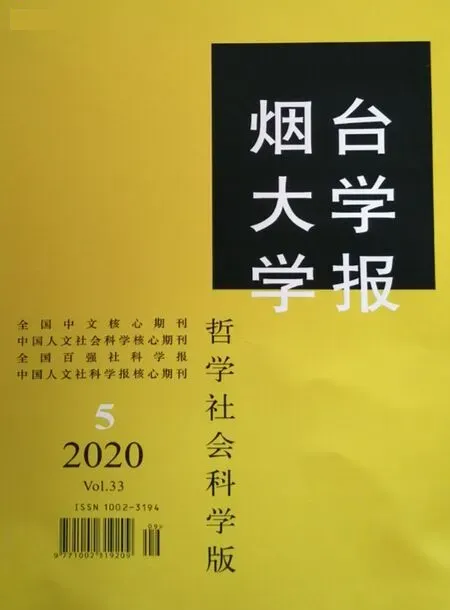无名的天下:《诗经·黍离》中的春秋微言
柯小刚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家国天下的关系是先秦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线索,《大学》曾对此有系统总结。考其源流,《大学》家国天下之思的本源在六经,尤其在《诗经》《尚书》。《大学》多引《诗》《书》即为明证。详玩《大学》所引《诗》《书》文句,多在商周易代之际。这也许是因为天命转移、朝代更迭之时,家国天下之间的关联在松动,国作为家与天下之间的中介开始动摇(国往往是政治危机的中心)。于是,在危机之中,家与天下对于国的本源意义更容易得到重新思考。
国是所有政治思考直接面对的对象,但也是最容易“对象化”的对象。所谓“对象化”就是把一个事物从它的本源中脱落出来,使之物化、固化、孤立化和工具化。所以,正如《大学》的论述思路所示,儒家政治哲学思考的要害便在于从国出发,向下奠基到家庭生活,向上开放为天下大道。这诚然也是关于“如何治国”的思考,但首先更是关于“何以治国”和“为什么治国”的思考。在《大学》的思路里,修身齐家是“何以治国”的答案,平天下则是“为什么治国”的旨归。两者加在一起,便成为“如何治国”的大前提。
与商周易代之际的历史处境相类似,《诗经·王风》诸篇也处在一个行将变革的时代转捩点。关于这个变革,孟子曾有精辟的概括:“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此语所指的时代,正是周平王东迁洛邑,从一个负有天下之义的周堕落为一个诸侯国之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王城洛邑之诗采编入《诗经》就是《王风》。《王风》是周天子王畿之诗,然而不列雅颂而降为风,就是因为此时的周只是周国,不再有其天下。《王风》首篇《黍离》以凭吊宗周废墟的形式,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变化。细读这篇感人至深的诗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晚周变革中的国与天下的关系,以及《诗》与《春秋》的政治哲学关联。
一、“此何人哉”:始亡天下之际的忧思
《周南》《召南》《王风》《豳风》都是编在国风里的周诗。其中,二南和《豳风》都相关于周之始兴,而《王风》则涉及周之始亡。说“始兴”“始亡”,是因为周之兴亡都不是忽然兴、忽然亡,而是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一个漫长过程来说,考察其始兴始亡之“始”便成为本源之思。始兴之思,始亡之思,皆相关于本源。
传统经学解释以平王东迁之后的《王风》为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时间节点,即以天下之义的存废而不是周国之兴衰为判断标准。平王东迁,周之为国并未灭,乃至其为天下共主之名亦未失,但实际上,无论诸侯之视周,还是周之自视,都已经遗忘了天下之义。所以,于周而言,始兴始亡之思,非周之为国的始兴始亡,而是天下之义的始兴始亡。
更可悲的是,在《王风》的“诗亡”之际,天下之义非独失之,且失之而不知之。此时,文明礼乐的周天下日益堕落为暴力争胜的春秋战国,但表面上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在这个漫长的蜕变过程中,除了个别有识之士有感于时世之变而无能为力之外,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世界已经改变了。《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是个别有识之士的同情同感,“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大多数人的浑噩无识。在《王风》所标识的“诗亡”节点之后,“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成为历代士人学者的基本状态,“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或“不合时宜的人”成为学者的通名。
《黍离》末句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根据毛诗的解释,是在追问周之所以衰的根源。但这一追问的深度如果不是从天下之义出发来思考,而是从周之为国的盛衰来提问,那么,《黍离》之思就被降低到梁惠王问题意识的层面了(即孟子见梁惠王而后者仅关心“何以利吾国”)。于是,我们作为读者,也就实际上成为“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一员,而不是“知我者谓我心忧”的同道。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读者能否成为诗人的知音,能否知其心之忧悲究竟何在,能否知其何所求、何所不求,成为《黍离》对于后人的永恒发问。如果我们可以面对《黍离》的发问,聆听诗人的哀歌,思考周之所以兴、所以亡,思考当前的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思考未来人类生活的可能性,那么,《黍离》之诗才仍然是一篇咏道之诗、《诗经》之诗,而不只是“文学”之诗(当然,“文学”之本义实不离经与道,只是后世用法与道脱离)。
所以,“此何人哉”的追问如果只是被理解为对于某个人的追责(譬如周厉王、幽王、平王等),那我们可能还没有触及《黍离》之忧的深处。但如果我们把“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理解为诗人自问,理解为一个不合时宜之人的自嘲,以及理解为在人世的颓坏中向天道的发问,《黍离》之思的问题深度似乎才开始向读者敞开。
二、《黍离》的苗与孟子的苗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状况持续到孟子的时代,不就是梁惠王的“何以利吾国”和孟子的“何必言利”吗(《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为什么开篇就摆出义利之辨的尖锐问题?岂不是因为全部孟子的所见所思所为,都已经是在“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的古今之变中了吗?在这个变迁中,时人之所求、君子之所求已经分道扬镳:“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在战国君主看来,他们对于土地、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无异于任何别的统治者,而孟子知道,真正的王者之求即天下之义已经很少有人懂得了。孟子对梁襄王说:“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然而,梁襄王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莅中国”,因而也不懂得什么是天下意义上的“朝秦楚”,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欲求什么,就像梁惠王乐观鸟兽、齐宣王好听音乐,但都不知道真正的快乐是什么。“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些僭称王者的战国君主至死都没有明白孟子所求的王道究竟是什么。甚至对于他们自己所欲求的事物,也并不真正懂得。孟子对时王言王道,而“王顾左右而言他”。
梁惠王们之所求,是把“天下”和“一”降低为“辟土地”,把“莅中国”降低为统治四方的帝国。“莅”之为“去打开一个敞开位置”的“中国”含义,“中国”之为去敞开天下、使万物相见的文明含义,(1)《周易·说卦传》:“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离卦之义包含华夏政治文明的基本取象。在“辟土地”的霸道中荡然无存。于是,孟子所谓“天下定于一”之“一”,以及《春秋》“大一统”之“一”,被这些战国君主理解为兼并战争。当战国时代最后的兼并战争终于赢得秦帝国统一的时候,天下之为天下、中国之为中国的本义却湮没无闻。一直要到汉代经学重建之后,人们才能从六经和《论语》《孟子》等文献中略微找回一点消息。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当孟子苦口婆心地以天下王道劝谕君主而不可能被真正理解的时候,他的心中肯定一直回响着《黍离》的绝唱。当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时候,这绝唱的音调达到了绝望的极点,但同时也蕴含了希望。这希望便在“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起兴之中。
面对梁襄王问天下“孰能一之”的问题,孟子取譬于苗来回答说:“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这让人想到《春秋公羊传》开头的那个春天:“元年春王正月”。在“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句下,何休的注文提到“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正如孔子论学《诗》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或如《尚书·汤诰》的“贲若草木,兆民允殖”,都是国家之上的天下视野。所谓王道,就是从这些草木和禾苗之间发生出来的。《易经》乾坤两卦之后,第一个始建人类政治生活的卦象“屯”也是这样一棵草:“屯者,草茅穿土初出之名;阳气动物,发生而未遂之象也。”(2)王夫之:《周易内传》,见《船山全书》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91页。草是至微之物,天下是至大之物,而至大之物却往往须由至微之物来起兴发端。《黍离》见黍稷之苗而忧天下,孟子取譬于苗而喻王道,皆因于此。
孟子苗喻的关键在自然生长的养护:既是人为养护,也是自然生长。天人之际的张力如何调解,取决于养护之人对于自然生长的物性认识,以及对于自己作为人的自然天性所达到的自觉反省认识。“天地无心以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不自知其性的人是天的貌似的对立面,自知其性的人则是天的自我觉知和自我长养。自我觉知乃有天知,自我长养乃有天养。天知天养,然后可免揠苗助长。
免于“揠苗助长”的养护是“让苗生长”。在孟子那里,“让苗生长”既是王道仁政、天下政治的原则,也是养气工夫的原则。为什么在论王道和养气的时候,孟子都取譬于苗之生长来展开论述?是不是因为这两件事原本就是一件事?养气的结果“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正是王道天下的气象。浩然之气是个人身心的王道,王道是天下的浩然之气。两者都像禾苗的生长一样,忘则荒,助则惫,只有通过“让生长”的养护才能自然生长,不期然而然地“浡然兴之”。
“让生长”的“让”首先是“让出来”,使物自生,其次才是“我让你长”。在“让生长”的养护中,首先要做的工夫是“我”的让出。只有首先让出“我”,“我的帮助”才不至于成为一种“揠苗助长”。“我”与“让出之我”的关系,便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中的“我”和“吾”的关系。孟子对公孙丑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知言之人对于“我”和“吾”的精微使用,决不是现代人所谓“同义词”所能涵盖。同样的语法,在南郭子綦对颜成子游说的“今者吾丧我”(《庄子·齐物论》)中,有着同样值得深思的工夫论义涵。
“我”里面的“戈”正如“國”里面的“戈”,都是一个封闭范围的界定和守护。“丧我”,然后能打开自己,成为隐机的“吾”、养气的“吾”。如果懂得“让生长”的“直养而无害”“勿忘勿助长”,那么,这个“吾”便可以成为天下的公民,(3)“公民”在此取其中文本义,并非“Citizen”的翻译。“Citizen”本义“市民”,乃至“私民”,并非公民。其气象可至于“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以苗喻道的孟子,歌咏《黍离》的行役大夫,都是有如此气象的天下公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唯吾知我,唯我不自知。知我者忧吾天下,“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知我者求我所欲,“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天下无道,则无一国能自保,亦无一人能自安。天下似虚,而其实如此;王道虽远,而其近如此。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理实通之。
儒道皆出先王大道,其别如国与国之别、人与我之别,其同则如草野之生长蔓延、天下之大公无疆。百家争鸣伴随诸侯争霸而来,都是战国时代“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表现。“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黍离》之悲,亦悲此也。一悲诸侯国家之丧天下,一悲诸子百家之失大道,其所悲者不同,而其所以悲者一也。
三、芃芃离离的天下
王道不行于天下不只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危机,而且本质上是天人关系的危机。当天道之于人事的意义被人遗忘,《黍离》大夫只能独自面对苍天之悠悠、黍稷之离离。悠悠离离的,都是绵绵不绝之物。无论人世的历史如何断裂破碎,苍天依然悠悠,禾苗永远离离。白居易诗以“离离原上草”对置荒城古道、王孙离别,而最后能慰凄凄别情者惟此野草。
周之兴历经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文王、武王,《大雅·绵》一句“绵绵瓜瓞”道尽其中欣喜和艰辛。人家世代之绵绵,大地野草之离离,苍天日月之悠悠,一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黍稷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草,稷尤其是周借以兴起之草。周之始祖后稷,其名即来自这种活命的庄稼和粮食。庄稼的生长、粮食的收成,始终指示着周之家国天下的命运。
《大雅·生民》叙生民之初,后稷即以农耕为本:“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那时候,禾苗和果实的旆旆、穟穟、幪幪、唪唪,全都是实实在在的绵绵之貌:“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而现在,当周失天下之义,绵绵瓜瓞之末,却只见“彼黍离离,彼稷之苗”,一片一片的空濛,以及在这空濛中不知所之的“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在周天下的另一次政治危机中,故国覆亡、孤立无援的许穆夫人最后也只能面对这旷野的空濛:“我行其野,芃芃其麦”(《鄘风·载驰》)。在人事的危机中,麦之芃芃,黍之离离,越茂盛蓬勃,越令人怅惘迷离。人类生活秩序、政治建构和房屋宫室诞生于旷野,无论多么文明辉煌,终将回到旷野:或在颓坏之后被迫回到旷野,或在文明中保有天质而自由地回到自然。后者正是孔子所谓“通三统”而“文质彬彬”的政教理想,但它几乎从未实现,而且总是被遗忘,只有在文明因脱离自然而颓坏的危机中才被人重新想起。
“天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建构,不如说是一种不离自然而“文质彬彬”(即文质相配)的文明秩序。与“国”相比,“天下”甚至不像一个名词,而只是一个状语式的描述指示。国可以是“实坚实好”的,而天下永远只能是“离离”“芃芃”的。“实坚实好”的国可以藏诸天下(天下有道之时的国),也可以藏诸私囊(天下无道之时的国),而天下却只能藏诸天下本身之中,如庄子所谓“藏天下于天下”(《庄子·大宗师》)。(4)更多相关分析,参拙文《藏刀与藏天下》,见柯小刚:《道学导论(外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如果有僭主想藏天下于私囊,那么,在他那么做的时候,天下之义立刻就丧失了,他所私藏的只不过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天下是无形的、不可对象化的大道。天下之义体现于地上的国,就是天下有道的时代,反之就是天下无道。天下是国之为国的公义,犹如道是器之为器的原理。
“天下”这个指示性的词语并没有具体规定什么,它只是指示了一个空间以及在这个空间中发生的所有事物(“天下万物”)。就像《千字文》结尾的“谓语助者,焉哉乎也”是对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回应和指示,而中间道及的任何一种具体事物都只不过是在这空间中的气化呈现。地上的万物,没有什么东西不在天下。《春秋》“王者无外”亦此义也。《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其意并不是在国家的层面上指一个帝国征服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而是在天下之义的层面描述王者无外的理想状态。
“天下”是道,不是某种国家制度那样的名器(最大的国也只是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所以,关于“天下”的道说,人间的“富强盛世”不如旷野的“芃芃”“离离”更接近。孔子体天地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而欲无言,正是他言说天下之道的方式。至于国家政事,则“夫子以温良恭俭让而得之”(《论语·学而》)。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公冶长》)与《春秋》之义的“丘窃取之”(《孟子·离娄下》),可能有某种关联。
四、诗亡弦歌中的《春秋》
《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讲天下王道的方式,就是一种“芃芃”“离离”的书法、“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书法,而不是“富强盛世”的修辞。何休注“元年春”云:“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之所出,四时本名也。”“王”则既不是时王,也不是确称其谥号的某位先王,而是一个虽然已经死去但以某种方式仍然活着的文王。正如何注所云:“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5)《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8页。
所以,这个王不只是周作为国家意义上的周文王,而且是周作为天下意义上的受天命之王。在国之君主的意义上,周文王早已死去;而在天下的意义上,文王却是一个永远活着的天命领受者。所以,《公羊传》云“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并无“周”字,并没有说“谓周文王也”。虽然文意所指就是周文王,但仅称“文王”而不称“周文王”,突出的是周之为超出国家的天下含义。这一点在《春秋》经文仅称“王”字,连“文”字都不用的书法中,得到了更本质但也更隐微的表述。“元年春王正月”的“王”是指周文王,但又不只是那个作为历史人物的周文王,而是周文王所代表的本质意义上的王。
本质意义上的王是无名的,正如天下总是无名的。人有名,家有姓,国有号,而天下只是天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某个特别的名称。周国号周,天下是天下;汉、唐国号汉、唐,天下还是天下。天下本身永远保持无名,虽然在不同朝代,会有不同的国号来领有天下的使命。所谓“周天下”并不是天下之名叫做“周”,而是那时周国领有天命,正在照看着天下。朝代更迭之所以叫作“革命”,是因为领有天下使命的国家主体变更了,所以叫作革命。改朝换代改的是国名,更准确地说,改的是领有天下使命的国家之名,而不是改天下之名。天下本来无名,无所谓改不改。天下如天地万物和人民一样,永远只是它自身,无须也无法以另外的名字来代称。在这个意义上,天下之义与天道一样,总是保持在无名之中。所以,对于承受天命的王者,《春秋》称之为“天王”。这并不是一个寻常的称呼。关于这一点,何休用“假以为王法”的“假”字(即“借”字)点明了。(6)参见《春秋公羊传注疏》,第8页。假借或托名一个上系于天而不只是系于某国的王者,其用意在于重新凸显天下之义对于国家政治的规范意义,而从东周大夫悲歌《黍离》的时候开始,这一意义早已被人遗忘。
《黍离》悲歌之时,正是“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之时。《春秋》之始的鲁隐公,正值周平王东迁之末年。东迁之后的周之为周,表面上并无变化:作为国的事实继续存在,承担天下之义的天王名义也继续存在。然而,实际上,周平王之为天下的“王”已经名存实亡。这并不只是在国家层面上说周的国家实力削弱了,不能控制其他诸侯国了,而且是在天下之义的层面上说周王不再是真正的王者了。
《诗》之降王为风,《春秋》之借始于文王正月,都是出于天下之义的问题意识。在国的层面,周文王时的国家硬件实力并不见得比周平王时强盛;但在天下层面,文王以德配天而志在平天下,平王则自居诸侯而与列国争胜而已。《春秋》之开端,其事则鲁隐公即位,其义则取诸文王受命之始:孔子简直是用一种蒙太奇式的书法把鲁隐公与周文王错置到一起。这种错置的悲痛和反讽,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绝望的希望,正是《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追问所蕴含的深意。如果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可信的话,那么,可以想见,孔子作《春秋》一定是在《黍离》之诗的弦歌中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