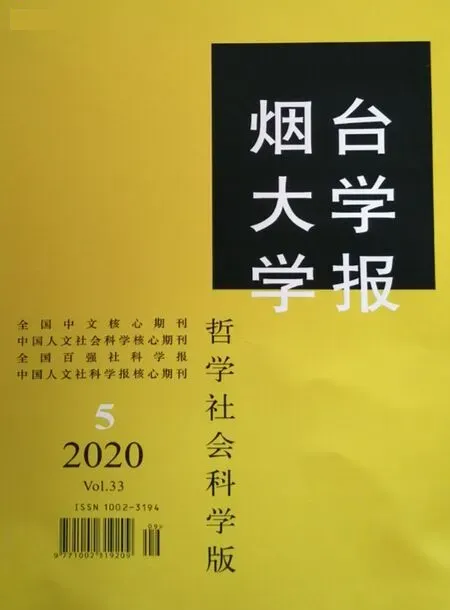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
——论卡森·麦卡勒斯对犹太人形象的文本再现
尚玉翠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美国重要的南方作家卡森·麦卡勒斯非常重视美国南方的种族问题。她既对遭受种族歧视最为严重的黑人群体深表同情,也对遭受反犹迫害至深的犹太人群予以积极观照,进而塑造出一系列鲜明独特的黑人、犹太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形象。其中,犹太人形象因极富张力而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既不同于反犹文学所歪曲附会的那般灰色、负面与丑陋,也迥异于犹太作家自己所构建的正面与多元,而是在被赋予“智慧和受难”(1)Hershon,Larry,“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The Jew’in the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vol. 41, no. 1 (Fall 2008),pp. 52-57.突出特征的同时,也被打上了神秘化和女性化的东方主义印记。在麦卡勒斯笔下,不论是有名有姓的哈里·米诺维兹和莫里斯·范因斯坦,还是无名无姓的犹太人众生相,大都是一些着墨不多、仅为陪衬的次要角色,仅通过全知叙述者或故事中的视角人物呈现出来,并任由全知叙述者或视角人物对其进行表述、言说和褒贬。这种始终处于被表述和被言说的失语状态,使犹太人的形象几近沦为被忽视和被淹没了主体意识的“他者”存在。正因如此,麦卡勒斯对他们的文本再现,就不完全是客观、公正的如实反映,而是选择、筛检甚至遮蔽的人为过滤,而这种人为的过滤主要是通过叙述视角的选取隐蔽实现的。
叙述视角作为“叙述时观察或感知故事的角度”(2)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页。,不仅是视觉的眼光,还包括诸如价值判断、道德评判等意义层面在内。因而,它作为传递作品主题意义的一种重要方法,虽属于形式因素,却能有力强化小说的主题诉求,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所以,麦卡勒斯选择怎样的叙述视角和选择谁做视角人物来再现犹太人形象,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写作技巧,而且是关涉价值评判和话语霸权的意识形态问题,它既直接影响着再现对象的呈现样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再现主体的文化心态,同时还覆蕴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特定叙述视角下再现对象的呈现样态
麦卡勒斯在对犹太人形象进行文本再现时,大都综合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但不论是采用知晓一切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还是使用选择性讲述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麦卡勒斯都是将犹太人形象作为被讲述、被观察和被凝视的对象,着力传达全知叙述者或视角人物所认为的犹太人应有的特性,借助他们的叙事话语建构起“聪明智慧”“受难”、神秘化与女性化等犹太人形象。
首先,犹太人被赋予了“聪明智慧”的族裔特质。麦卡勒斯选取与犹太人有生活交集的南方白人作为视角人物,向读者展现出了一系列拥有聪明头脑与非凡智慧的犹太人形象。《心是孤独的猎手》虽采取了多变的叙事视角,但关于正统的犹太人哈里·米诺维兹的形象主要是通过白人女孩米克的有限视角呈现出来的。她以回忆的方式讲述出哈里在求学阶段的聪明优秀,认为他不但拥有很强的语言天赋,而且还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因而“在语法学校他跳了两级,十一岁时就准备上职业学校了”(3)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陈笑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35页。,并且是“职业学校数学和历史课上最聪明的学生”(4)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155页。。《没有指针的钟》以白人药师J.T.马龙的有限视角展示了犹太人的勤奋刻苦。他记起上医学院时,“班上有许多刻苦读书的犹太学生。他们的成绩都在年级平均水平之上”(5)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金绍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7页。。短篇小说《神童》则通过白人女孩弗朗西丝的有限视角为读者引出了犹太人海密·伊斯雷尔斯基,随后全知叙述者交代了海密在音乐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是一个极具天分的音乐神童,不但练就了纯熟精湛的演奏技巧,而且还能准确恰当地体悟到音乐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能够完美无缺地演绎出音乐本身的生命力,因而,还不到十五岁就已成为小提琴界名副其实的最“年轻的大师”(6)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李文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77页。。在这些视角人物和全知叙述者的叙述中,不论是普通的犹太学生,还是杰出的音乐天才,都凭借着聪颖天资与努力勤奋取得了耀眼的成绩,成为犹太人拥有聪明头脑与非凡智慧的最佳例证。
其次,犹太人被刻显为受迫害的“受难者”形象。短篇小说《外国人》通篇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首先从外部观察犹太人菲利克斯·克尔的外貌、衣着与言行举止,继而描述他在客车上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对其进行了从外到内的全方位扫描与展示。通过全知叙述者的叙述,我们得知菲利克斯·克尔是一个曾生存在慕尼黑的犹太人,幸运地逃脱了纳粹的政治迫害,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生命暂时处于安全之中,但无辜被害的政治恐惧和妻离子散的现实境遇,使他过着毫无尊严和幸福的生活,只能自我麻木、谨小慎微地苟活于世。在与邻座青年短暂与友好的即景闲谈中,邻座青年热情直爽地向他敞开心扉,和盘托出自己的内心愿望与情感状况,而他却一直心存戒备,吞吞吐吐。他这种心事重重的谨言慎行,既暴露出他遭受迫害后的痛苦与恐惧,又反映出他对未来叵测难料的忧心忡忡。身为“外国人”的他,虽然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安稳家园的渴望,但现实中家“有却似无”的实际情况,却使他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者……旅行的时间不会以小时来计算,而是以年来计算——路程不是几百英里,而是上千英里。甚至像这样的衡量尺度,也只是就某种意义而言”(7)卡森·麦卡勒斯:《抵押出去的心》,文泽尔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63页。,难以准确丈量自己长途接短途的、无法用地图和时间来衡量的逃亡之旅。对于他这种无家可归、漂泊不定的流亡之旅,全知叙述者将其定性为“更接近于一种心理状态的旅行”(8)卡森·麦卡勒斯:《抵押出去的心》,第63页。——既不会因此次客车的到站而结束,也不会因现实旅程的结束而停止,而是永远流浪在路上,不知终于何时、止于何处。
第三,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被扑拓上一层“神秘化”色彩。移民到美国后,犹太人的饮食习惯和日常生活都被人为地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饮食习惯方面,犹太人的饮食因与一般的南方人完全不同而被加以特别关注,因为“主流美国人经常以饮食习惯作为区分次文化群体的因素,他们在与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同的‘他者’的传统菜式和用料中发现一套归类族裔和区域性格的方便之法”(9)Brown Lindk and Kay Mussell,Ethnic and Regional Foodway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Performance of Group Identity,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4,p.3.,所以,他们通过食物的“微观差异”来彰显民族、文化的“宏观差别”。《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全知叙述者叙述莫里斯·范因斯坦“每天都吃发得很松的面包和罐头鲑鱼”(10)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第7页。,但美国南方人却很少食用,因而对他们每天都不变花样只吃这两样食物的怪异饮食习惯充满好奇。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米克很“珍视对犹太人生活所持的浪漫观点”(11)Hershon,Larry,“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The Jew’in the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vol. 41, no. 1 (Fall 2008),pp.52-57.。当她与哈里相约去郊游野餐时,认为他会带冷猪肝布丁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因为他们家吃的是地道的犹太食品”(12)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254页。,因而对新鲜刺激的野餐食物充满了浪漫期待。在此,无论是犹太人的日常饮食习惯,还是犹太人所食用的“犹太”食品,因其所遵从的犹太教Kosher(可食)饮食法规的洁净与饮食戒律,而都被晕染上一层宗教、民族和文化色彩,成为承载着宗教、民族与文化特性的特定习惯,凸显着犹太民族与美国南方人的截然差别。这些因新奇古怪而不断被神秘化的饮食差别,深深激发出美国南方人对其强烈的好奇心。
第四,犹太男性被打上明显的“女性化”烙印。《心是孤独的猎手》中,尽管哈里比米克大两岁,长得很帅很干净,但却比她“矮几英寸”(13)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106页。;那些在商业中心精于钟表修理工作的犹太工人,也都是些“动作敏捷、皮肤黝黑、个子矮小”(14)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95页。的犹太人;而《神童》中,在弗朗西丝看来,犹太人拉甫柯维奇“是那么小的一个小个子”(15)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第75页。,神童海密的身材也比她矮得多,“只能够到她的肩膀”(16)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第81页。。这些出现于不同作品中的犹太男性,虽然年龄、职业各个不同,但就体型而言,无一例外都没有高大强壮的身材,都“个头矮小……‘长得干瘪’”(17)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沈宗美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92页。,极其缺乏男性气质。在性格方面,犹太男性的感情较为丰富,情绪容易失控。莫里斯·范因斯坦每当被人说是他“杀了基督,他就要哭”(18)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第7页。,他这种爱哭的性格,使其成为爱哭和缺乏男性气质的代名词,以至于此后“只要有人缺少男子气概,哭哭啼啼,人们就说他是莫里斯·范因斯坦”(19)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第8页。。拉甫柯维奇的声音,在弗朗西丝听来觉得带着柔滑、让人听不清楚的嗡嗡声,感觉“更像是女人的”(20)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第74页。。可见,在这些与犹太人接触的视角人物的感知中,犹太男性的身材都不够高大,性格也比较脆弱,男性气质明显偏“女性化”。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犹太男性所表现出的“女性化”特征,是视角人物自身个人化与情绪化的主观感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美国南方人对整个犹太民族共有特征的集体认知。
二、叙述视角选取与再现主体的文化心态
叙述视角作为故事得以呈现的手段,既控制着文本再现的内容和样态,也浸透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态度。因而,选择怎样的叙述视角和选择哪个人物作为视角人物,往往内隐着作者本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立场。麦卡勒斯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此时正是法西斯、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文学盛行的时期,但她并没有明确的反犹倾向,而是对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并且强烈谴责“容许这样的堕落发生的社会”(21)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冯晓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43页。。尽管如此,她却没有将生活在南方的犹太人视为南方“白人”。在她看来,南方“白人”不仅是白色人种,还是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优越感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群体。因而,犹太人虽是白色人种,但却不具有成为南方“白人”的其他标准,只能是和黑人一样,成为种族上的“他者”。正因如此,秉持“除非角色是南方人,否则我几乎不让他们开口说话”(22)卡森·麦卡勒斯:《抵押出去的心》,第205页。的创作理念的她,在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对犹太人形象进行文本再现时,没有将犹太人与南方白人平等地并置在一起,以双向视角对双方民族文化进行互映式烛照,而是选择全知叙述方式和以南方白人为视角人物的有限叙述方式,对犹太人形象进行单向展现。这种叙事方式通过将犹太人淡化为主体意识被遮蔽的沉默“他者”,进一步凸显了全知叙述者和视角人物的价值判断与主观态度,尤其是他们对犹太人或赞赏或同情或向往或不满的文化心态,更成为文本的中心,令读者一览无余。
(一) 赞赏与推崇
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虽有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但却一直非常弱小,不断遭受其他民族的迫害与凌辱,以至于流散世界两千多年,饱受颠沛流离与灾难浩劫之苦,然而他们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奇迹般地不断发展,涌现出诸如斯宾诺莎、卡尔·马克思等众多辉耀史册的天才人物,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犹太民族往往被描绘成智慧的化身。《神童》中的海密被称为神童,因为在小提琴界取得斐然的成就,受到了报纸和杂志的极力赞誉。《心是孤独的猎手》中,黑人医生考普兰德喜欢阅读“斯宾诺莎、威廉姆·莎士比亚和卡尔·马克思的书”(23)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85页。,尽管“他不太懂概念的复杂游戏和复杂的词组,但他在字里行间闻到了强烈而真正的动机,他感到自己几乎是明白了”(24)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67页。斯宾诺莎的自由学说,找到了“整个黑人种族都病了”(25)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77页。的病因所在。他对卡尔·马克思更是推崇备至,不但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卡尔·马克思,而且还在圣诞节年终派对上对黑人同胞热情宣讲马克思思想,鼓励他们积极争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6)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179页。的理想生活。在此,不论是虚构的文学形象海密,还是实有其人的斯宾诺莎与马克思,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都因非凡成就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受到了世人的赞誉与推崇。
(二) 同情与艳羡
由于历史、政治和宗教原因,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典型的流浪史。不论是传说中向上帝所指引“流着奶和蜜”之地的主动迁徙,还是现实中为逃避欺凌与戕害的被迫移民,以及基督教中关于惩罚犹太人永世流浪的精神包袱,都使得犹太人的命运深深涉入“流浪”的旋流之中,历经岁月的流逝,逐步风干为一种族裔形象的刻板印记,蚀刻在世人认知与记忆的深处。自“巴比伦之囚”之后,犹太人开始流散到世界各地,纳粹的迫害更逼使他们再次流亡,成为居无定所的、永远在路上的“流浪”旅者。遭受纳粹迫害被迫流亡到美国的菲利克斯·克尔,作为移民到此的外来族群一员,生活中充满了无助、失落与无所适从,身心皆处于漂泊无定的流浪状态。但对于他在客车偶遇的旅伴——一个终日劳作、久困南方的青年农民来说,由于身心皆被现实束绊,不能随心所欲地想走就走,因而在不知他犹太人身份与可怕遭遇的情况下,对其来自陌生的异国他乡并去过自己心仪已久却无法前往的巴黎时,充满了羡慕与仰望,不时用“崇拜的神情”(27)卡森·麦卡勒斯:《抵押出去的心》,第62页。看着他。可见,对于犹太人的现实流亡,作者既突出了犹太外乡人“在路上”的漂泊感和急盼回家而却不知家在何处的感伤,凸显出个人乃至整个世界对犹太人悲惨遭遇的同情,又暗示出了困守南方的美国人对于犹太人能够“自主自如”地进行跨国旅行的羡慕与向往,隐约透露出南方人对于诗意远方的内心热望和浪漫想象。
(三) 想象与臆构
遥远的东方在美国人眼中充满了异国情调和神秘色彩,在猎奇心理驱使之下,他们对东方密切关注、充满了探寻的热情,但各种因素制约下的他们并不能真正走进东方、切实了解东方、理性对待东方。所以,他们便将这种关切和热情,掺杂进对自己文化的优越和对他者同情与拯救的悲悯之中,就着自己文化的根脉流向,热情编织着关于东方的种种想象。当古老的犹太文明与年轻的美国文化在美国正面相遇时,由于宗教疏离和犹太教徒的固守传统,导致两种文化没有产生真正的沟通。哈里母亲为了生计忙于工作,始终无暇顾及外面的人与事,因而“透过窗户,你可以看到她在后面的缝纫机边埋头干活,或者把长长的针穿进厚厚的布料”(28)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262页。,但“你看她时,她从不抬头”(29)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手》,第262页。,完全是与外界隔绝的自我存在。在此,借助“看”这个动词,米克将观看者与被看的对象区分开来,以看者的姿态建构起自己有别于被看者的身份,进而单方面地对犹太人的生活进行审视、想象和臆构,而第二人称“你”的运用,更是体现了一种共指身份,使表述者的个人经历或感受带有了一定范围的普遍性,令读者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真实卷入感,“愿意依赖这些典型的非犹太人虚构出的神话”(30)Hershon,Larry,“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The Jew’in the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The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vol. 41, no. 1 (Fall 2008),pp.52-57.,对犹太人独特的异质文化族群的差异性魅力展开丰富的想象。
(四) 不满和排斥
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虽然是少数群体,但随着犹太社团的成长壮大和犹太精英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白人新教中产阶级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和威胁,认为他们是“美国经济的攫取者”(31)石涵月:《美国历史上反犹主义的宗教文化根源》,《世界民族》2005年第5期。,控制着美国的商业,抢夺了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机会与财富。米克的父亲从事修理钟表工作,但生意萧条冷淡,米克认为是商业中心的那些犹太人抢夺了父亲的生意,使其一直处在事业受挫的灰心丧气之中;已过不惑之年的马龙认为“刻苦攻读的犹太学生把他挤出了医学院,摧毁了他当一名医生的前途”(32)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第7页。,以至于在很多年后依然无法释怀,始终不能客观地直面自己学医生涯的半途而废;弗朗西丝更是过分敏感于外部世界的干扰,因为报纸上对海密的称赞超过了对她的称赞而备受打击,便将海密和音乐教师视为自己无法超越的巨大压力,最终主动放弃了钢琴生涯。犹太人在商业和就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使白人不满的情绪迅速积加,直至出现强烈的排犹与憎犹浪潮。莫里斯·范因斯坦因“碰到了一件倒霉的事”(33)卡森·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第8页。而不得不搬离小镇的遭遇,便是当时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生活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的异教徒,面对谋杀基督这一老生常谈的指责与攻击,初到小镇的他根本没有自我辩驳的机会,只能通过哭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被冤屈,但这种示弱的表现并没有帮他摆脱困境,反而使他被小镇居民贬斥为缺乏男性气概,只能以搬离小镇的方式来躲避周围居民的敌意与攻击。
三、叙述视角运用与再现行为的意识形态
麦卡勒斯在对犹太人形象进行文本再现时,综合运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使文本中的客观叙述和主观讲述遥相呼应,互为印证,达到了最佳的修辞效果和最理想的意识形态表达。对作家而言,“确定从何视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因为它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应”(34)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28页。。即作者根据自己的叙述意图选择怎样的叙述视角,挑选谁来作为视角人物,会操纵和引导着读者对文本的认知,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着读者的阅读视野。因而,读者会受到作者个人意图和叙述技巧以及叙述者身份和地位的引导与制约,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对人物的情感态度置于作者的掌控之下。
首先,叙述视角对读者同情心的控制。经典叙述学认为,小说的叙述视角操纵着读者的同情心。在《小说修辞学》中,韦恩·布斯指出,作者对读者的控制是通过叙述视角作用于读者的同情心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读者“对人物的同情不是一个鲜明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由在小说视角中新出现的这些可描述的技巧所制造并控制的”(35)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页。。在他看来,小说中同情的产生和控制多是通过叙述者进入人物内心及与人物距离的远近掌控来实现的。读者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态度了解越多,便对故事所述人物或事件的知晓程度越高,更容易自觉地与小说里的视角人物拉近距离,并因理解他们而对他们产生同情的意向性,因而,视角人物往往是读者的同情心所在。在此,叙述视角造成的读者与人物之间的心理距离,成为读者同情人物的先决条件。麦卡勒斯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多将南方白人作为视角人物,这样就有效地拉近了读者同他们的距离,更容易与他们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尤其是通过他们的内视点,读者能清楚地看透其内心,了解到他们更多的内在思想感情,产生置身其中的体验感和真实感,而“持续的内视点导致读者希望与他共行的那个人物有好运”(36)李丹:《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兼论后现代元小说的叙述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使读者容易对他们产生同情和友善的态度。因而,就叙事效果而言,小说的叙述视角决定了读者对视角人物的同情,并进一步由同情而产生与叙述者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对读者情感态度的控制。
其次,叙述视角对读者主体性的建构。“假如布斯表明小说控制了读者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又决定了同情的问题的话,那么,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就只增加了这么一点,即小说通过控制读者的立场,使得读者不仅能够同情,而且与某种主体立场完全一致并因此而具有主体立场和社会角色。”(37)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第33页。在阿尔都塞看来,文学不仅操控着读者的情感态度,甚至还建构和生产着读者的主体立场和社会身份。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一文中,阿尔都塞从主体性建构的角度描述了意识形态运作的具体过程,认为意识形态的主要产物是人的“主体”,它确保了主体能把自己的受动地位“误识”为独立自主。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和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38)陈然兴:《叙事与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5页。。它作为先于个体而存在的文化客体和社会结构以无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并通过“传唤”或“询唤”机制将某个主体构筑到意识形态之中,它“通过我称之为传唤或呼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作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人)”(39)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使人从一个现实的自由个体被“招募”为顺从的、无需暴力看管的、自己起作用的“主体”,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有用的主体。因而,当现实个体被“传唤”为主体之后,就会“内在地觉得自己是自由、自足的,觉得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40)李丹:《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兼论后现代元小说的叙述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并把自己的臣服误认为自由,成为具有自由幻觉的受动的主体。而文学或许是实现意识形态运作的最好手段,它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叙事文本作为话语对读者进行质询,并将其“传唤”为意义建构的主体,使读者一方面受制于文本这个权威机构,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进入文本是一种自主行为,导致这个主体性建构的过程虽然是由文本控制着,但读者却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的主体立场的选择是自由自在地达到的。麦卡勒斯选择与犹太人混杂居处的南方白人作为视角人物,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和评价其周围的犹太人,展现他们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态度,从而使读者自觉地对他们产生好感,把他们当成值得信赖的自己人,进而与他们感同身受,产生出与他们相近或一致的主体立场和身份,最终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由此,作家的文学再现行为所产生和流通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将介入现实生活,促使读者通过再现的过程参与、改变和干预它所在的现实世界,进而对真实世界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产生一定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美国文学中犹太人形象的历史也是美国反犹主义历史中的一章”(41)Dana Mihǎilescu,Jewish Stereotypes in Critical Focus: From Christian Archetypes to Representation Practi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Jewish Studies,2007,January,p.201.。
在后经典叙述学的研究视野里,“叙事作品塑造的这个特殊主体——读者的同情反映,成为一个兼具被动和主动两种属性的复杂现象。这种新的读者同情是通过读者对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身份认同来实现的。”(42)索宇环:《叙述视角与文学交流:是谁在操纵读者的同情心?——以〈印度之行〉为例》,《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2期。读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历自主地选择同情对象,以此反抗作者对读者的控制。《伤心咖啡馆之歌》出版之后,麦卡勒斯受到“取笑犹太人”的匿名指控,即是一位在莫里斯·范因斯坦的命运里发现了自己影子的犹太读者指控作者的政治和文化立场。暂且不论他的指控正确与否,他抗拒作者控制意图的反抗行为本身,也印证了作者操纵读者同情这一事实的真实性存在。
四、结 语
麦卡勒斯以特有的洞察力,密切关注着犹太人在美国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身上固有的美德和优长,但她对犹太人形象进行文本再现时的叙述视角和视角人物选择,却使犹太人的形象以被讲述的面目呈现出来,使他们的情感历程、行为动机处于被遮蔽状态。他们的被观察与被讲述,既形象地反映出他们在其文本中的边缘与轻微,又有力地强化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存状态的被动与无奈。在麦卡勒斯的文本再现中,作为视角人物的南方白人跃居中心,掌控着言说自我和言说他人的权力,而犹太群体的声音却在认知暴力和主流表征系统的框架下被匿声,完全丧失了再现自我和他人的权力和能力,进而在文本和现实中都处于边缘的失语状态。南方白人对犹太人的单向再现,既是再现者拥有言说他人权利的权力表征,又是他们对固守自己民族边界意识的积极认同,并隐喻出将犹太移民视为种族“他者”的共同偏见,这种明确的政治信息,使作为“他者”的犹太移民与作为“主体”的南方白人之间存在着无法消弭的疆界与裂痕,只能消极地回缩在自己民族或文化的螺壳之内。由此,麦卡勒斯对犹太人形象的文本再现,就体现出指意功能与实践功能的双重特性。她通过对叙述视角和视角人物的选择,既掌控着文本再现的整个叙述过程,又对读者的情感态度甚至是读者的主体性构建施以控制,“在推进文本叙事进程的同时,引导读者进入社会大背景展开意识形态层面的思索”(43)荆兴梅:《卡森·麦卡勒斯作品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8页。,使文学实践与意识形态紧密关联起来,为我们从叙述视角与意识形态相互关联的角度去发掘她文本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踪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