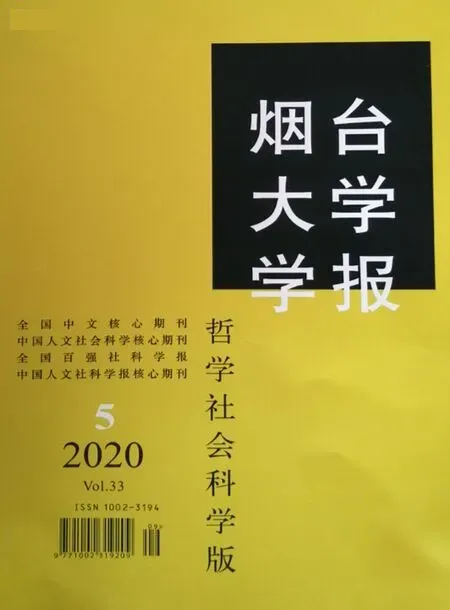金起林诗歌的道性世界
——以《波涛》为例
裴书峰,丁凤熙
(烟台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金起林(1908-?),本名金寅孙,号片石村,韩国现代主义代表诗人、评论家,代表作品有《气象图》《太阳的风俗》《文学概论》《诗的理解》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韩国现代主义文学奠基者之一的金起林率先将西方的主知主义和意象主义介绍到韩国,开启了韩国现代诗歌文学创作新里程。他的早期创作在重视技巧性的同时,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展开了无情批判,然而到了中后期,这种创作倾向发生转变,开始重视诗歌内容,重新回归到了“东洋文化”,试图在探寻传统文化中重构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金起林并未明确指出可借鉴的“东洋文化”为何物,但其后期诗论和作品中的文化倾向却与中国道家生态理念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这种契合并非偶然,因为金起林在借鉴庞德意象主义和朝鲜传统时调创作理念的同时,也无意识地继承了二者内在的道家文化元素。关于金起林诗歌的前期研究,大都立足于西方现代或后现代主义文化视角,忽略了其诗歌创作中特有的东方文化属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旨在探索道家文化与金起林诗歌创作的历史关联性,并以其后期代表诗歌《波涛》(1)诗集《新歌》1948年4月由雅文阁出版,诗集共分为Ⅰ、Ⅱ两部,诗歌《波涛》收录在Ⅱ中。为例,阐释其文学创作中所呈现的道家文化,从而进一步印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东亚文学创作的影响力。
一、道家文化的隐性继承
(一)金起林与庞德意象主义
金起林继承了庞德的意象主义诗论,强调意象的视觉性。他在《诗的绘画性》中写到:“当以可视的影像浮现在读者的意识中作为目的时,诗歌内容就会具有绘画性,……也是庞德所说的‘形诗’”。这种观点与庞德“形象在视觉想象上的投射”的表述相一致。事实上,庞德的意象主义深受中国古典诗论的影响。正如洪雪花所言:“庞德把握了中国古典诗歌注重‘意象’‘简洁’和‘含蓄’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巧与他领导的意象主义运动的诗学观不谋而合。”(2)洪雪花:《意象主义在东西方文学中的回返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2006年,第24页。在中国,“意象”一词最早由刘勰提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文心雕龙·神思》)。 他借用《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典故,赋予了“意象”视觉性的特点,即事物在头脑中的投像。作为中国古典诗论核心的“意境说”也与道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王汶成认为,“意境说” 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老庄的“言意之辩”和《易传》的“言、象、意”论,而“言、象、意”论又是对庄子“三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3)王汶成:《论中国古代的语言美学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道家文化对语言充满了批判性,主张“言不尽意”“言者不知”“得意而忘言”“不言之教”。在老庄看来,语言是抽象的、有限的,会遮蔽他们所追求的“道”,“道可道,非常道”。 庄子“三言”之一的“寓言”便是对一般抽象语言的克服,它通过直接、形象、可感的“象”或“境”来间接喻“道”。这种形象性思维与庞德提出的“按照我所见的事物来猫绘”(4)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9页。的原则一脉相承。不难看出,道家文化对金起林诗歌的影响具有回返性的特点,“绘画性”理论表面上是受到了庞德的影响,而实际上却是无意识地继承了道家的“三言”理论。
(二)金起林与黄真伊时调
除了庞德的意象主义诗论,朝鲜时调可以说是金起林隐性继承道家文化的另一种介质,对其后期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金起林在《时调与现代》中,主张“时调题材的复活”,并高度评价黄真伊时调,认为其女性个人经验的诚实表现与近代个人抒情诗传统相连贯。(5)高明秀:《韩国文学理论与现代主义》,《韩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6期。秦香莲进一步指出,金起林“诗的明朗性”和黄真伊“诚实的情感表现”一脉相通。黄真伊与道教颇有渊源,她一生寄情山水、寻仙问道、放荡不羁,极力挣脱封建礼教文化的束缚。朝鲜民间文学《於于野谈》评价黄真伊为“女中之倜傥任侠者也”,并记载了其“自戴松萝圆顶穿葛衫带布裙拽芒鞋杖竹枝”与李生员仙游的轶事。李天认为,黄真伊的诗歌具有明显的道家文化倾向和男性化特征。可见,黄真伊时调中“诚实的情感表现”正是其处世风格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更是道家文化审美情趣的自然流露。庄子主张崇尚真情,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庄子·渔父》),并在《养生主》中用秦失“三号而出”的故事批判了强哭者“悲而不哀”的伪情。同时,他还提出了“法天贵真”的理念,通过回归自然之性达到最初的本真状态。
(三)金起林与复古情怀
金起林与道家文化潜在的关联性还表现为一种东洋文化的复古情怀。他在《关于东洋的断章》中写到:“我们打算去古代和中世去寻找东洋文化最闪光的一面 ……去它的创造力中去寻找东洋的光荣。” 金翰成指出,金起林把古代新罗和中世高丽看作是异质文化怒放的社会,他所说的“创造力”是出自于对文化最为繁盛的唐朝—统一新罗—平安时代文化交流的盛评。(6)金翰城:《金起林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尔大学大学院,2014年,第197页。事实上,金起林的上述论断,是针对固化的儒教——程朱理学提出的,他所寻找的东洋文化不是排斥异己的李朝文化,而是开放的蕴含着“创造力”的唐朝、新罗文化。那个时期的文化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道家文化的治国理念。唐朝和新罗的统治者都把道教定为国教,整个社会阶层洋溢着崇道的风气。张爱民认为,唐朝崇道的原因在于“道教中老子的治国理论有利于维护统治”。(7)张爱民:《唐朝统治者对〈庄子〉的阐释与接受》,《岱宗学刊》2005年第1期。一般说来,老子治国理论的核心是“无为而治”,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换言之,老子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顺应天道,任物自然,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这促使唐朝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繁荣局面,也正是金起林追寻的东洋文化之“创造力”的根源所在。
二、诗歌《波涛》中的道性世界
《波涛》是金起林后期诗歌的代表作,收录于诗集《新歌》中,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涛泛滥的自然景象。这首诗是金起林民族文学理念的诗化具现,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粹主义等权力话语的批判,呈现出了自然性、开放性、平等性、创造性的文化特征,与老庄的“道性思维”一脉相承。
(一)虚无与生命
“无”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道”的基本属性之一,“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庄子·大宗师》)。庄子将“无”看作是原始性的本然存在,并且赋予其生成意义,“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庄子·齐物论》),“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庄子·知北游》)。赵丽端指出:“这种本然的存在作为世界的原始之在,呈现的是浑而未分的统一形态,具有已然与应然的双重特征。”(8)赵丽端:《存在之通:庄子“道通为一”的哲学阐明》,《江淮论坛》2014年第3期。
1945年韩国光复后,金起林认为建设新民族文化必须要“扫荡日帝残余、清算封建残余”(9)金允植:《解放空间的诗歌现状》,《解放空间的民族文学研究》,首尔:阅音社,1989年,第145页。。这与他在30年代提出的“原始明朗性”是一致的,“关于诗歌原始明朗性的要求,并非野蛮的回归,而是为了在文化领域恢复重新开始所需要的力量”(10)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933年8月10日版《朝鲜日报》刊载的金起林《关于现代艺术原始的欲求》一文中。。换言之,金起林所谓的文化建设是一种原始性回归,具有破坏和建设双重属性。如果把《波涛》中的“新世界”理解为文化回归的终极目标,那么“波涛”便是践行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诗中的现实世界是被封建文化(王宫)和帝国主义(华尔街)封锁的“荒芜地”,把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放在了对立、异质、分裂的关系框架中,也就是庄子所讲的“有封”的世界。“波涛”是具有“破坏性”的意象。在泛滥中,“王宫”的“柱基”开始晃动,“华尔街”闭锁的“门”“窗”被冲开,“摇晃着蛀蚀王宫的柱基/环绕着华尔街冲天的房屋/扒开着门扇,扭曲着窗棂”;地上的“迎春花”“樱花”等与天上的“星辉”融为一体,“陆地”和“海洋”也被“水”覆盖了,“迎春花/樱花/金达莱/百合、菖蒲……/吞没着一切/在无数的夜晚,融化倾泻的星辉/化成如今的江水,打着旋儿/奔涌而来/席卷无数的陆地和海洋/汹涌而来”,现有的文化景象被毁灭殆尽,世界重新回归到了原始的浑然状态。但是“波涛”并非是“野蛮”的,它在摧毁固化文明的同时,还将把“迎春花”“樱花”等生命意象融入其中,使自身成为了富含生命力的整体性存在。这些传统的本土生命意象正是金起林在东洋文化中寻找的有价值的部分,为新文化“创造力”的孕育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波涛”还是具有复原性的时间意象,“喔,波涛/你沿着整个地平线均匀地扩散开来”。它沿着“地平线”前进,和“地平线”卷曲在了一起,而“地平线”又和“明日”作为整体意象存在,所以“波涛”也就与“明日”具有了同一性。“明日”是具有复原性的未来时间意象,即金起林“力图通过新的未来复原被帝国主义主体他者化的自我”(11)赵慧珍:《193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他者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诚信女子大学大学院,2017年,第78页。。由此以来,浑然、玄同的“新世界”又被赋予了创生意义,蕴含着无限生机,这也是“波涛”建设性功能的所在。
不管是“荒芜地”的殖民地文化还是金起林向往的新民族文化都与庄子所言的“伦”“象”相同,是现实世界“有”的能指。“波涛”通过破坏现有的文化景象,把我们带入了“无”的本然世界,而这个“无”同时又是孕育新民族文化的母体。可见,这种由“有”到“无”,再由“无”到“有”哲学逻辑正是道家“无中生有”创生理念的诗化具现。
(二)具象与大美
关于“道”,老子做了如下论述,“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天地间最高的价值本体,与自然规律一样是客观的,可感不可言。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说法,在《大宗师》里对“道”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描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基于“道”的以上特点,老子主张“希言自然”。笔者认为,“言”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话语的教令;二是作为表述的语言。“希言”则意味着要做到以下两点:首先,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避免语言对事物本然的遮蔽,即“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其次,减少人为的干涉,任凭事物自然发展,保持其“常然”(《庄子》)。
金起林反对语言的抽象性说教和情感的矫揉造作,主张诗歌的绘画性和明朗性。“绘画性”不同于抽象语言,与“日常语言”一样都是具象思维的体现;“明朗性”则是黄真伊“诚实的情感表现”,强调自然与真实,与“暧昧”和感伤形成了鲜明对比。诗中,“波涛”是一个“虽然无名”的最高价值本体,类似于不可言说的“道”。诗人没有给它赋名,而是采用了比喻手法对其性状进行具象描绘,“像香气、像潮水、像音乐、像风、也像云”。名字(能指)是人为主观概念化的东西,具有抽象性,一定程度上会遮蔽事物的本然。而金起林借助感官意象对抽象事物进行描绘——“绘画性”,却最大限度地呈现了事物的本真。这与老子“以水喻道”、庄子“由形入道”做法是相同的。老子“通过水本根意义的提升来达到对道本体的比喻”(12)黄承贵:《水:老子“道”论的本喻》,《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庄子“将形视为道的直接显现”(13)贡华南:《从无形、形名到形而上》,《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不难看出,不管是金起林的“绘画性”还是老庄的“喻道”,都意识到了抽象语言认知的有限性,从而在直接、形象、可感的“象”或“境”中完成了对事物的本真表达。
诗中,创造新世界的“波涛”还象征着自然规律,虽然“无形”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不可阻挡。空间上,“喔,波涛/你沿着整个地平线均匀地扩散开来”,将“陆地”“海洋”“天空”囊括其中;时间上,“喔,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时时/刻刻/赋形而来”。诗人借助“太阳”这个隐性意象,说明了“波涛”到来的客观规律性。之所以说“太阳”是隐性的,是因为藏在了“明日的地平线”之下即将升起,此时它与“新的世界”是等同的。他曾在《黎明的亚当》《太阳的风俗》等诗歌中借助“太阳”把断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看成了有机循环的整体,暗示着历史总是在黑暗和光明的交替中不断发展。这一点与庄子的循环观极为相似,“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后成功。是出则存,是入则亡。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庄子·田子方》)。“波涛”的到来摧毁了“宫殿”“房子”等人为的权力话语,使万物重新回归到了自然而然的规律运行中。换言之,垂直建筑代表的封建、殖民话语与庄子所言的“仁义”“礼乐”本质相同,损害了事物的“常然”。它将自身(殖民者/人类)之外的事物(殖民地/自然)他者化或对象化是“削其性”“侵其德”的“有为”。而在“波涛”创造的“新的世界”里,人为的秩序不复存在,自然规律重新成为了支配世界万物的最高法则,这也是金起林情感自然性的深层哲学内涵。
(三)混同与齐一
“齐一”是庄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强调平等性和整体性,追求无差异的混同境界。庄子认为,作为宇宙之源的“道”存在于万物之中,“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 (《庄子·齐物论》)。万物因“道”而获得了同质性,这为本质意义上的平等性提供了前提条件,“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正如陈红映所说,“庄子是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看万物皆平等而没有贵贱差别的”(14)陈红映:《庄子平等思想解说》,《思想战线》1992年第6期。。这种平等性使人类放弃了优越性,并对“载万物”的“道”(自然)充满了敬畏:“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庄子·秋水》)此外,庄子还主张万物的有机整体性,“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王攸欣认为,“‘磅礴万物为一’(《庄子·逍遥游》),‘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之‘一’,即把万物作为一个整体看”(15)王攸欣:《道通为一,逍遥以游——〈庄子〉要义申论》,《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春之卷。。而作为整体组成部分的万物又是“并生”的,处在相互依存的普遍联系中。
金起林指出,“侵略者的干涉阻断了先进知识与大众的文化交流”(《诗和民族》),因此光复后文化应重新回归大众。他将“共同体意识”融入了后期诗歌创作,注重“大众”情感和生活体验的表达,并在《民族文化的性格》中主张“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民族文学应是“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文学。同时林敬美认为,金起林的后期诗歌还表露出了理念对立所造成的分裂危机感。由此可见,金起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民族、阶级、文化差异的超越,又是对分裂意识的弥合,与庄子的“齐一”思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这种“共同体意识”在诗歌《波涛》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现实中的“你”和“我”象征着充满差异、对立、异质性的封建、殖民话语。“波涛”泛滥过后,“早已,不是/你或我/你或我/不过是波涛所遗留的波纹/不过是交织在波动的弯弯”。在这里,固化的概念遭到了解构,“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 “我”,“你”和“我”成了“波涛所遗留的波纹”“交织在波动的弯弯”。“波涛”“波纹”“弯弯”是水不同的呈现形态,“你”和“我”通过与“波涛”的转换具有了同质性。这也意味着人类放弃了中心主体地位与自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没有了尊卑优劣之分。如此看来,诗中的“水”与庄子的“道”或“气”一样,是具有本体性特征的意象,使万物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平等。诗人还通过“波涛”来弥合万物间的裂痕,积极构建有机整体的宇宙世界,“在这/浩荡的泛滥之中/埋葬我们,一——切的昨天吧/清扫我们破碎的记忆吧”。泛滥的“波涛”并非简单、粗暴地破坏,而是将万物有机地“融化”在了一起,使世界具有了整体性。泛滥过后,封建、殖民话语中碎片化的“你”“我”,和“波纹”“弯弯”一样,缠缠绕绕“交织”在一起,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由此一来,被“波涛”吞并的万物不仅是同质平等的,还是普遍联系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
三、结 语
庞德意象主义和黄真伊时调对金起林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二者又都将文化源头指向了中国道家文化。从这点来看,金起林对道家文化的继承是隐性的,而道家文化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也是无意识的。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基因的作用下,金起林对充满文化创造力的唐朝和新罗产生了无比的憧憬和向往。金起林诗歌的“绘画性”虽受到了庞德意象主义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却是传承了中国古典诗论意象说身后所隐藏的庄子“三言”理论。而其诗歌“明朗性”及黄真伊“诚实的情感表现”本质上又和道家的“无为自然”哲学理念一脉相承。金起林的后期诗歌《波涛》集中体现了这些文化理念,向我们描绘了一个有无相生、无为自然、混同齐一的道性世界。换言之,《波涛》中的道性世界是一种自然整体性的回归,呈现了小我(物)融入大我(宇宙、天、道)的有机统一的生态理念。
——大型民族歌剧《涛声依旧》 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