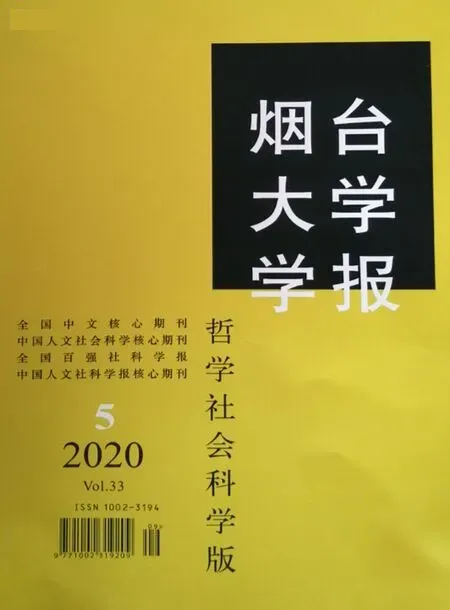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的个人自由时间叙事
赵 斌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77)
个人公共时间是现代社会中的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集体生活时间,包括个人参与政治革命的生活时间、参与社会文化改革的生活时间、参与社会经济建设的生活时间等;而个人自由时间则与个人公共时间是相对的,主要包括个人融入家庭、娱乐等私下的世俗生活时间。具体言之,个人自由时间与日常生活结伴而行,赋予人“按照自己的思想”“筹划生活”(1)郝春鹏:《作为一种社会学建构的历史学——雷蒙·阿隆的社会历史学》,《世界哲学》2016年第4期。的权力。从人类学、社会学来看,个人自由时间是私人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3页。,其不能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也与人类的历史时间不太一致。但在小说时间美学中,这种表面上缺少历史能动性的自由时间却被赋予多副面孔,它留给读者的不只是“映像或摹本”,更是“包含着一个创造性的和构造性的过程”。(3)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5页。小说家会根据创作的需要对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赋予不同的时间意义。
在现代小说中,小说家析取个人公共生活时间以达到建构英雄、重塑历史的目的,析取个人自由生活时间则截然相反。这一时间塑形策略往往受制于时代环境。如民国初期世俗之流漫漶,各类期刊杂志对拿破仑的个人自由生活时间的塑形特别卖力,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拿破仑书写热潮。《礼拜六》《小说时报》《中华小说界》《小说丛报》《女子世界》等所谓的“鸳鸯蝴蝶派”的杂志“都加入了拿破仑文本的生产,不约而同地沿着大众文化‘反英雄’的路向”,“专注其私人生活,对他的婚姻家庭与风流韵事津津乐道”。(4)陈建华:《拿破仑“三戴绿头巾”——民国初期都市传播文化的女权与民主倾向》,《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从拿破仑英雄式的个人公共时间书写滑向“婚姻家庭”“风流韵事”等“反英雄”的个人自由时间塑形,是与民初“情”潮泛滥密切相关。拿破仑被通俗化了,英雄被“还原为一个血肉之躯的‘人’”,其“迎合了渐高渐涨的张扬女权的潮流,另一方面与袁世凯倒行逆施而引起的政治幻灭相关,借暴露或丑化拿翁隐私破除对于‘伟人’的幻想”(5)陈建华:《拿破仑“三戴绿头巾”——民国初期都市传播文化的女权与民主倾向》,《学术月刊》2013年第3期。。这确实是高见。小说家选择人物的个人公共时间还是个人自由时间自然有多种因素的限制,而问题在于,由于时代、作家的迥异,个人自由时间塑形千差万别,甚至截然相反。周作人说:“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西方小说《一生》“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其区别在于作家态度(“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与“材料方法”则没有多少关系。(6)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1918年12月15日。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现代转型中,小说中的个人自由时间会被塑形为“落后”“进步”“异化”等多种丰富的时间意义。
一、“人性论”“阶级论”之争
鲁迅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个人自由时间用在了学习、工作上,周作人则工作之余,醉心于“无用的游戏与享乐”,徜徉于“看花”“听雨”“喝不求解渴的酒”(7)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见谢冕主编:《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散文卷)上(1895-1949)》,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年,第565页。等个人闲暇时间。可见,周氏两兄弟处置个人自由时间的方式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生活时间观念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鲁迅把“喝咖啡、聊天”的自由时间纳入到“学习、工作”的公共时间里,有其积极的时间意义,周作人“小资情调”式的自由时间观却很受当下年轻人的推崇。“小资情调”本属于一种审美范畴,没多少政治倾向,后来,它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构成了某种威胁,因而被人为地加以批判。“小资情调常常表现在旅游、服饰打扮、居室布置、音乐等方面”(8)包晓光:《小资情调:一个逐渐形成的阶层及其生活品味·序言》,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年,第1页。,把人置于游戏娱乐的自由时间之中,毫无进取精神。在小说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追求时间的进步性成为小说的叙事重心,而小说中的个人自由时间一般会被小说家们看成是落后的,自然成了批判的对象而加以舍弃。
实际上,小说如何塑形个人自由时间,小说家的创作观念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小说人物的时间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9)李贞玉:《晚清革命书写中的烈女想象》,《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正因为如此,一百年来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对个人自由时间的塑形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可谓众说纷纭。从“小说革命”的新“国民”,“人的文学”的新“人”,经过左翼文学的“革命者”、延安文学的“工农兵”、十七年文学的“人民”、文革文学的“三突出”式的“革命英雄”,到新时期的“知青”“土匪”及“新写实”小说的“小市民”……人物主体形象走马灯似的转换,人的个人自由时间的塑形意义也迥然有别。
晚清写情小说备受冷落。其原因在于晚清“新小说”被作为建构新国家的重要工具,小说抨击“官场”,宣传新思想,以至于“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10)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5页。。因为在亟需重建历史的晚清,书写爱情等个人私下生活的时间是落后的。为了彰显杂志的时代进步性,《新小说》《小说林》《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小说期刊所刊载的小说几乎都与社会的进步相关涉,为了突出小说人物的进步性,人物的个人公共时间被放大书写,个人自由时间则被“压缩”,甚至放弃。如“晚清革命小说主要把个人参与革命政治活动的时间作为建构进步历史的主要力量加以叙述”(11)赵斌:《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的个人公共时间叙事》,《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以突出他们参与、建造历史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晚清小说具有现代特征的人物不多,而人只有在现代历史时间里才可能谈及个人的公共时间与自由时间。
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成了时代主题,“个性解放”下的小说人物书写为个人自由时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为个人自由时间具有反抗力量,离家出走、自由恋爱等个人自由时间具有了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当然,在“人学”兴起的时代,对恋爱等自由时间塑形也会有所抵制,时人熊熊说:“为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神圣斗争……我们不应自私,更不应把这神圣的责任为恋爱之魔所击碎!”(12)熊熊:《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中国青年》第66期,1925年2月14日。人的恋爱生活时间是把双刃剑,有时候会对革命有消解作用。当恋爱与革命发生冲突时,恋爱必须让位于革命,因为革命更需要个人公共时间。正如恽代英所说:“今日的世界……还有功夫讲什么恋爱?……在要吃饭的世界里,要恋爱纯洁,一大半是梦想罢!”(13)恽代英:《青年的恋爱问题》,《学生杂志》第11卷第1号,1924年1月5日。由此可知,恋爱等个人自由时间在进步人士看来是落后的。
五四之后,“人性论”“阶级论”逐渐形成对峙。“人性论”下的小说对恋爱等个人自由时间的书写不遗余力,“阶级论”下的小说却要尽力挖掘个人参与集体(阶级)的公共时间的意义,以至于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梁实秋等自由主义者与左翼革命阵营发生多次论争。梁实秋把“人性”看成“恋爱的力量,义务的观念,理想的失望,命运的压迫,虚伪的厌恶,生活的赞美”(14)梁实秋:《文艺批评论·绪论》,《文艺批评论》,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页。,其目的是“企求身心的愉快”。(15)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梁实秋的“人性论”虽不否定“义务观念”下的个人公共时间的集体意义,却过分强调了个人自由时间的“愉快”意义,这与阶级革命对个人公共时间意义的挖掘背道而驰,其被左翼革命派批驳则是必然的。到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张阶级的人性,试图综合“阶级”与“人性”,否定抽象的人性,书写“工农兵”参与革命的个人公共时间的阶级意义,形成“人民文学”的历史建构。这样,五四“人的文学”传统“都将扫清,而‘人的自觉’‘人的文学’的旧口号也将全部被‘人民的自觉’‘人民的文学’的新口号所代替”(16)周扬:《“五四”文学革命杂记》,《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83页。。此时的“人民”存在于阶级革命中,是个集体概念,“人民文学”下的“人民”存在于集体时间之中,“人民”的个人自由时间不太容易“溢出”。当《我们夫妇之间》等少数小说的叙事描写伸向了人的个人自由时间,虽然小说不像“解放区的小说”“读起来很枯燥,没趣味,没‘人情味’”(17)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5卷1期,1951年10月26日。,但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自然受到了很多批判。当时的“人民文学”“人情味太少”,是“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作品上的阶级论”(18)巴人:《巴人杂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26页。的结果。这种政治意识下的“人民文学”派“反对那种目光只在个人的生活琐事旁边打转,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成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人情味”(19)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汇报》1960年2月10日。。于是,“个人的生活琐事”等自由时间被从小说中剥离出来。“三突出”“革命样板戏”的文艺创作应运而生,从而“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命题”。(20)文化部批判组:《评“三突出”》,《人民日报》1977年5月18日。文革文学竭尽所能挖掘正面英雄人物的个人公共时间,尽力摒除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即使写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也让它具有个人公共时间的积极意义。如电影《艳阳天》,在原小说中老贫农马老四为了养好合作社里的牲口,自己吃野菜,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喂集体的小牲口。拍摄电影时,为了突出萧长春的“高、大、全”形象,这个细节情节被改成:萧长春“吃野菜,省下来的半袋小米送给马老四喂牲口”(21)《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革命文艺工作者畅谈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体会》,《人民日报》1974年7月29日。。按照“三突出”的艺术标准,英雄的日常的个人自由时间也具有了革命进步性。可见,从左翼到文革,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很难得到大量书写。
到了新时期,五四“人的文学”的传统得到了部分恢复,但人物的恋爱等自由生活时间却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尤其是新写实小说,它试图将“某种庸俗琐碎的时间意识发挥到极致,生活特地以庸常的形式出现”,小说不仅仅以个人庸常的自由时间展示生活,还为这种个人庸常的自由时间叙事“正名”,意在“对英雄时间的消解”,也是“对50-70年代文学中时间观念的一种反拨”。(22)孙鹏程、马大康:《关于当代文学庸常化的美学思考》,《扬子江评论》1999年第5期。小说通过对人物个人自由生活时间的正面描写,一种可能被认为是虚假的个人公共时间意识得到了消解,目的是恢复人物个人自由时间的塑形意义。
二、个人自由时间的落后性塑形
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具有落后性,源于个人生命中惰性的一面。在晚清、五四小说中,成长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会按照道德和现代性两个标准来审视人物的这种落后性。
晚清小说有不少进步人物,小说中的“新女性”比比皆是。但小说对新女性的个人自由时间塑形会受制于道德判断,其很难呈现五四小说的启蒙意义。晚清小说对处于恋爱等自由时间中的男女会以礼教设防,要“始而相识,继以礼交,后以情合”(23)是龙:《自由女之新婚谈》,《申报》1912年9月19日。。“自由结婚”本来是男女走进个人的自由时间的,但是“两人虽订定了终身,同在一处,却断没有丝毫苟且的事体”。(24)仙源苍园:《家庭现形记》,上海:文振学社,1907年,第34页。个人很难突破传统的伦理道德的限制。小说《新石头记》中的新人物贾宝玉来到上海,当他听说黛玉坠入腐化生活时间里,完全接受不了这种变化:“上海粉头中最有名气的‘四大金刚’,头一个竟是林黛玉,宝玉猛然听了,犹如天雷击顶一般,又是气忿,又是疑心:‘气忿的是林黛玉冰清玉洁的一个人,为甚做起这个勾当来?’”(25)吴趼人:《新石头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页。传统道德审判了个人自由生活时间。
曾朴的《孽海花》本来是按照“历史小说”来构思,然而,历史时间与人物的“琐闻逸事”的自由时间出现了错位。小说的原意是通过对男女情欲等庸常的自由生活时间塑形来影射、解释政治历史时间的变数,“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在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26)曾朴:《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孽海花》(修改本),上海:真善美书店,1928年,第1-2页。但是,作者习惯于传统叙述模式,把德宗和太后失和的政治历史叙述引向了男女婚恋庸常生活时间中,并做了道德判断。如庄仑樵兵败发配,堕落到娶妾、女色、诗酒等腐化生活时间里;祝宝廷囿于船上妓女的圈套,自请去职,在腐化生活时间里堕落;傅彩云借着“自由”名词堕落于姘居孙三、勾搭向菊、权肉交易、婚外恋、偷情等私生活时间里,有冲破封建伦理藩篱的时间意义,但对其道德审判会消解个人自由时间的意义。另外,李定夷的《霣玉怨》、詹公的《自由误》、瘦鹃的《押邪鉴》、花奴的《钓上鱼儿》、剑秋的《女总会》、秋梦的《车夫语》、恨人的《意外缘》等写人物私生活的小说都有一定的道德谴责。更为重要的是,囿于道德的限制,小说人物会拒绝进入正常的个人感情生活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晚清小说现代化的步伐。如《泥中玉》的主人公“冷观先生”对着女学生装的女郎爱慕有加,后知女子有夫,却大惊失色,不敢与女郎共同走进甜蜜的个人爱情生活时间里。(27)治世之逸:《泥中玉》,见《新聊斋》,上海:上海改良小说社,1909年,第68页。人物的落后性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性审视个人自由时间与道德审判不一样,道德审判比较传统,现代性审视是按照是否符合现代历史发展的眼光而做出的理性判断。如小说《未来教育史》(28)悔学子:《未来教育史》,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7页。的主人公萍生是个进步人物,有教育救国的抱负,却又挣脱不了生活中的儿女情长的枷锁,因为儿女情长等自由生活时间会阻止人物的进步。小说家为了突出人物进步性,会有意增加小说人物的公共时间的篇幅,以压缩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玉梨魂》改编为《雪鸿泪史》即为明显例证。《玉梨魂》本是“革命+恋爱”小说的滥觞,但人物的恋爱自由时间几乎覆盖全篇,人物的革命生活时间很少;而在《雪鸿泪史》中,人物的革命生活时间与恋爱自由时间基本持平。《雪鸿泪史》有14章,从己酉年梦霞离家写起,到庚戌年离家东渡结束,文本中恋爱时间与革命时间此消彼长,不像《玉梨魂》中的革命时间在结尾处才短暂出现,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雪鸿泪史》前半部分主要写革命时间的发生:梦霞与石痴的交往与志趣相投,石痴东渡时,其革命理想影响了梦霞;梦霞与梨影结识,梨影屡劝梦霞东渡,革命时间与恋爱时间相互交织。接着,革命时间与恋爱时间发生冲突:梦霞、梨影难舍难分的儿女情长与革命的召唤纠缠不清,但革命时间已经有了优势,因为,“男儿以报国为职志,家且不足恋,何有于区区儿女之情而不能自克?”最后,梨影、筠倩相继死去,进一步激发革命时间的出现。那么为什么做这样的改编呢?徐枕亚在《自序》中说:“近小说潮流,风靡宇内,言情之书,作者伙矣。或艳或哀,各极其致,以余书参观之,果有一毫相似否?”(29)吴组缃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集·第8卷·小说卷六),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598页。刻意将革命时间的进步性与恋爱时间的落后性予以鲜明对比。另外,在《上海游骖录》《巾帼阳秋》等小说中,某些革命党新人抱着“旋乾转坤之烈士”的远大理想,却在日常生活时间里打麻将、逛妓院、花天酒地,无所担当。人物在个人自由时间中腐化堕落,其落后性显而易见。
五四小说人物的自由生活时间也具有落后性。《海滨故人》的五个女学生把个人自由时间消耗在公园里。她们“在公园里吃过晚饭,便在社稷坛散步,她们谈到暑假分别时曾叮嘱到月望时,两地看月传心曲,谁想不到三个月,依旧同地赏月了!”露沙和宗莹、云青、玲玉“总是四个人拉着手,在芳草地上,轻歌快谈。说到快意时,便哈天扑地地狂笑,说到凄楚时便长吁短叹,其实都脱不了孩子气”(30)庐隐:《海滨故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60-64页。。她们虽是五四新式人物,却在悠闲的自由时间颓废了。小说《伤逝》中子君也满足于安宁和幸福的生活,在饲养油鸡、喂阿随等日常自由时间中堕落。张闻天在小说《恋爱了》(31)张闻天:《恋爱了》,《小说月报》第16卷第5号,1925年5月10日。中不再坚持自由恋爱的“个性解放”的新思想,而是用嘲讽的笔法,把沉醉于恋爱、失恋等个人自由时间中的男女学生进行不无辛辣的讽刺。胡适也在《一个问题》(32)胡适:《一个问题》,《每周评论》第33期,1919年8月3日。中发出一个疑问:“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小说对自我成长的重新思考,显示了人物对处于碌碌无为的自由时间之中的焦灼,为人物的重新行动提供了思想动力。陈衡哲小说《洛绮思的问题》(33)陈衡哲:《洛绮思的问题》,《小说月报》第15卷第10号,1924年10月10日。的主人公是留美女博士洛绮思,她认为,家庭是事业的对立面,一个人如果沉迷于操持家务和生儿育女等自由时间,会对她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追求事业的成功,她放弃了恋爱、婚姻和家庭。沉樱的小说《妻》也写了一个“我”与妻由恋爱而同居的故事,妻有“从事于文学的野心”,但是,怀孕却使妻陷入绝望,为了追求自由与理想,为了避免“一个美丽的梦境破灭”(34)小铃:《妻》,《小说月报》第20卷第9期,1929年9月10日。,她决定采取打胎这种过激行为来反抗个人自由生活时间的堕落性。可见,五四时期的新女性拒绝回归家庭,害怕淹没于世俗生活时间中而有损于人的进步性。
三、个人自由时间的进步性塑形
相对于个人自由时间的落后性塑形,其进步性塑形可能还丰富一些,因为在历史转折时期,人的个性解放成为历史进步的一个尺度,而个性解放就是要放大人的自由。刘半农说:“王尔德所著各书,能于‘爱情真谛’之中,辟一‘永远甜蜜’的新世界。左喇所著各书,能以‘悲天悯人’之念,辟一‘忠厚良善’之新世界。”(35)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第3卷5号,1917年7月1日。想怎样反映社会生活,想怎样写人物,著者对个人自由生活时间的思想态度很关键,因为,个人自由时间有落后/进步“两副面孔”。
上文说到,人沉迷于恋爱等自由时间之中会堕落。但是,1902年蔡元培在原配夫人病故后,与志同道合的黄世振女士举行了新式婚礼,这种个人自由时间塑形却很有意义。蔡元培在惊世骇俗的征婚(“男子不娶妾”“夫妇不合时,可以解约”等)、求婚、婚礼等世俗时间里加入了拜孔子、演说等具有新式思想的活动,开启了晚清自由结婚的先例(36)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54页。,具有进步的时间意义。更有意思的是,小说《孽海花》没有把傅彩云塑造成一个虚无党的革命者,也没有把傅彩云放在革命公共时间展现人物的历史进步性,而是把傅彩云放在“风花雪月”的自由浪漫的时间中,“藉此混淆了国家大事与风花雪月,将公众与私人的道德范畴融入一问题重重的新空间”,并且“通过一个从良妓女的风流韵事,折射中国国运之盛衰起伏”,“傅彩云的浪漫冒险嘲弄了传统孔孟之道从修身到平天下一以贯之的逻辑,将诸恶之首的‘淫’变成了救赎民族伤痛的灵丹妙药”。(37)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3-41页。可见,妓女的个人私生活时间也具有一定的历史驱动力。因为“爱情与感情主题的重要意义也日益增长”,《孽海花》《恨海》《九尾龟》等写情小说也能够“表现出敏感的个人的命运与无情的社会压迫力量之间的冲突”。(38)M·D·维林吉诺娃:《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伍小平译,见王继权、周榕芳编:《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小说》,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0页。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傅彩云用她的“淫”作为反抗的武器,《上海游骖录》中的人物则用“鸦片”、用“毒”作为反抗的武器。及源说:“正惟政府要禁,我偏要吃,以示反对之意,不然我早戒了。况且我的吸烟与大众不同,我是自己有节制的。”(39)吴趼人:《上海游骖录》,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7页。人物显然为自己堕落到个人腐化时间里做辩解,但人物的反抗确是真的,其进步性也是有的。
学者周乐诗说,晚清“小说常常以放荡和泼辣来表现女性的这种‘新’对传统道德的破坏”。(40)周乐诗:《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这样,人物个人腐化时间成了展现人物进步的一种手段,新人物在日常生活时间中的戴眼镜、穿皮鞋等新潮打扮以及对日常的态度也就具有了社会进步性。在小说《侠义佳人》中,女学生柳飞琼有“一肚子的新名词,满腔的自由血”,与楚孟实“结为密友,常常一同逛花园,坐马车,吃番菜,看夜戏……”痴迷于恋爱生活时间之中,结婚也“依了新法……只买一个上好钻石戒指”。婚后方知上当受骗,后求救于“晓光会”,才得以离婚,正如柳飞琼所说:“我有我的自由权。”(41)复旦大学中文系:《女子权·侠义佳人·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08-411页。可见,在柳飞琼恋爱、结婚、离婚等自由时间里彰显了清末民初青年学生的进步性——思想解放。小说《二十世纪之新审判》中的主人公慧姑自认为是一个小家碧玉,受父母疼爱,“凡有所求,靡不如志,以故虽青闺深锁,不事女红,视针蒲如仇讐,悦简编以遣兴”(42)水心:《二十世纪之新审判》,《小说月报》第4卷第5期,1911年6月21日。。慧姑又是一个新女性,而一寸芳心恒倾欧化,于“男女平权”“自由结婚”诸学说,尤心领而神会。小说写得很含糊,慧姑“不事女红,视针蒲如仇讐”是她极力抗拒进入庸常生活时间里,但这种新思想是来自父母的“娇生惯养”还是“泰西之学”,不是特别明确。另外,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韦士的《采桑子》、李涵秋的《蝴蝶相思记》、商铭的《我之家庭》等小说都记述了一个人物挣扎于恋爱、婚姻、家庭等自由时间里以示反传统的故事。如小说《我之家庭》的主人公王泽民被女学生邵李梨演说缠足之害所打动,接着相识相爱,毕业后在张园举行文明婚礼,一时观者如堵。(43)商铭:《我之家庭》,《小说丛报》第7期,1917年7月10日。“有情人终成眷属”是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大团圆”结局,而这篇小说却通过书写恋爱、婚姻、家庭等自由时间表现出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婚姻的渴望和追求。一般来说,我们会将民初言情小说的“感伤”,“解释为取‘悦’读者的商业手段,也可以视为作者有意震撼人心,促使读者社会问题的方法”。(44)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9页。从这一层面来看,民初言情小说所展现人的自由时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到了五四时期,小说家对个人自由时间的书写更加多样化。在一些小说创作中,小说家“热烈地赞美与肯定‘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45)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一方面他们展现人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又挖掘人的自由生活时间中的自然原欲。五四新文学宣扬人的“个性主义”,其深层文化内质和人性取向到底是什么?蒋承勇认为,“首先是‘原欲’,其次是‘人智’”,而且“对禁欲型文化的攻击,最好的途径就是充分肯定和大力张扬人的自然原欲,因此,无论中外,人的解放也总是从自然本能的解放开始的”。(46)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在这种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小说自然把人物的自由生活时间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且突出个人自由时间的反抗意义。小说家从人的自然本性的层面肯定人,把人的自由生活作为艺术表现对象。如《春天》中的霄音在日常生活中不安分,在给昔日的恋人写信时被丈夫撞见,让她不知所措。小说通过对人物日常的婚外恋生活时间的展现,目的是展现新女性已经意识到自我的存在;《爱山庐梦影》中的女孩从城里回来,她进入了烫发、涂着脂粉、穿上高跟皮鞋等新的自由生活时间里;《疯了的诗人》中的旧式的夫妻觉生、双成夫妇不顾世俗眼光,把旧式生活转变成新的自由生活:“书房里,后园里,不用说时刻见他们双双影子……河边田野也常常见他们搀着手走过,有时他们跳跃着跑,像一对十来岁小孩子一样神气……”(47)凌叔华:《花之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觉生、双成夫妻进入一种自由的生活时间,终于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找到了彼此的快乐和幸福。另外,《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春痕》等小说也是通过描写人物追逐自由时间来反抗封建礼教,其中,小说集《卷葹》“确实能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初期的五四时代的青年女性心理与勇猛的冲决旧礼教屏藩的精神”(48)钱杏邨:《关于沅君创作的考察》,《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上海书店,1933年,第128-130页。,确实是有现代性意义的。
陈独秀曾经用“兽性主义”来孕育一代新人。(49)陈独秀:《基督教与中国人》,《独秀文存》3卷2册,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页。与之相似,五四时期的“私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南迁》《秋柳》等也用“兽欲”来展现人的“灵肉冲突”。小说主人公都是耽于色欲、追求性解放,游荡于腐化时间之中,常常“沉沦”于酒馆妓院之中,效仿魏晋名士放浪形骸、借酒浇愁、狎妓……小说通过对自我放纵的时间塑形,表达了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如《秋柳》中的主人公于质夫“无处可以发泄”,去找妓女海棠。于质夫个人“的自由都不愿被道德来束缚”,是人的腐化生活时间对封建专制的一种抗拒,也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露骨的直率”,使封建道学家们感到了“作假的困难”。(50)郭沫若:《论郁达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17页。在此,个人自由时间的反抗性被推向了极致。
四、个人自由时间的异化塑形
郁达夫的小说主人公在个人自由时间之中“沉沦”以示反传统,个人“腐化”时间具有个性解放的进步性。但事物都有两面性,小说人物的私生活时间如果超出了限度,反而会适得其反,被异化而失去本来的时间意义。同样是个人欲望的自由时间塑形,张资平的小说主人公追求自由的性关系,三角恋爱、四角恋爱、乱伦、婚外情泛滥成灾,这就超出了度,从而备受批判。所以,晚清、五四小说有不少借助个性解放之名行腐化之实。正如何震所说:“新党之好淫者,必借婚姻自由为名而纵其淫欲;女子稍受敎育者,亦揭‘自由’二字以为标,视旁淫诸事不复引为可羞。……中国二百兆女子,使人人均为卖淫妇也。”(51)志达(何震):《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1907年8月10日。评论不无道理。
小说的现代转型时期,小说家“对于全盘的社会现象不注意,他们最感兴味的还是恋爱,而且个人主义的享乐的倾向也很显然”(52)茅盾:《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9页。。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的“新”往往用性自由、性放荡做注脚。《文明小史》中的新女性广东阿二“读过一年外国书……改变了脾气”,借助“外国婚姻自由”行“轧姘头、吊膀子”等堕落行为。(53)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处在腐化时间中的“新女性”没有多少进步性,并且,人物脱离了正常的时间轨道。《上海游骖录》中的屠牗民的女友是一个女学生,她和屠牗民毫无顾忌地当街调笑,开口就骂、顺手就打。牗民涨红了脸,他说:“我们中国人的程度低到极点了,怪不得孔子当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依着文明国之规矩和他结交,认他做一个女朋友,不料他倒干预我的自由起来了。”(54)我佛山人(吴趼人):《上海游骖录》,《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27页。小说中的新女性男性化有个性解放的意义,但也扭曲了个人正常的生活时间。同时,屠牗民也在外偷腥,借“自由”之名行腐化之实。屠牗民等“新人”掉进了腐化时间之中,“自由恋爱”也随之异化了。清末小说中的一些新女性“打扮新潮,言谈中充满新名词、新思想,但作风腐败、品行猥琐”(55)周乐诗:《晚清小说中的“新女性”》,《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人物在腐化的个人自由时间中堕落。
更为荒唐的是小说《女娲石》,小说中的春融党“不忌酒色,不惜身体,专要一般国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设有百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一般癫狂学生,腐败官场,无不消魂摄魄,乐为之死”,个人处在腐化的自由时间里“娱乐至死”。小说《未来世界》的新女性赵素华也是在伦敦、巴黎、长崎、东京“放诞惯了”,后来与黄陆生自由恋爱,结婚后才知上当受骗。由此赵素华滑向异化时间里“另结新欢”,她还为自己辩解:“我在外面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查问……你也没有诘问的权利……我自有我的自由权。”当黄陆生要拉她回家,练过体操的赵素华“左手带住了黄陆生的右腕,右手将他当胸一推……仰面一跤跌到在地”(56)春颿:《未来世界》,《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拾),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58、491页。。女性男性化的赵素华在留学、游历、恋爱、结婚、婚外恋等非正常的时间中堕落。无独有偶,《梼杌萃编》中自由女性玉妞是一个钦差的千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她个人私生活混乱:“叫全禹闻就陪他在那里住。全禹闻始而不敢,那姑娘说:‘你要不答应我,我回去叫你不得了!’……全禹闻又何肯推辞……这晚住在餐馆里,居然行了个自由结婚的大礼。”(57)钱锡宝:《梼杌萃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放荡的自由生活时间异化了。小说《新党升官发财记》中的维新人物也是个个生活腐化,把花酒当成日常生活,这些所谓新人物在腐化个人自由时间里扭曲了灵魂,并不能在历史中成长。小说《碎簪记》有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方今时移俗易,长妇姹女,皆竟侈邪,心醉自由之风,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亦犹男子借爱国主义而谋利禄。”(58)苏曼殊:《碎簪记》,《苏曼殊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可见,有些晚清小说中的新人物的堕落实际上多于反抗。
相对于晚清小说,五四小说中的个人自由时间的异化塑形也很常见。小说《茫茫夜》中的于质夫悲愁难遣,于是病态地性发泄。他像饿犬一样在街上找女人,最后用卖香烟的妇女的旧针和手帕“狠命把针子向脸上刺了一针”,以此寻求快意。这个处在畸形生活时间里的人物令人不寒而栗。小说《酒后》也写了日常生活时间中的一次唐突的心理越轨:宴会之后的朋友子仪醉卧沙发上,然而,妻子采苕却不断盯着沙发上的子仪看,甚至提出吻子仪的荒唐要求。五四时期,随着“个性解放”大胆演绎,小说对“婚外恋”等异化的自由生活时间塑形更加卖力。本雅明说:“女同性恋是现代性的女英雄。”(59)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68页。五四小说女同性恋少见,“婚外恋”却以反封建口号为自我掩护出现“井喷”态势,《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与梓青是一例。另外,《洛绮思的问题》的主人公洛绮思无性之爱也很特别,洛绮思说:“结婚的一件事情,终究是很平常的,人人做得到,唯有那真挚高尚的友谊,却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啊!”并且,“各个女子的思想和性情,是不能一样的”。(60)陈衡哲:《洛绮思的问题》,见《小雨点》,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104、109页。新女性处于异化的自由生活时间里,确实富有个性。更畸形的是,“五四后,男学生都想交结一个女朋友,那(哪)怕那个男生家中已有妻儿,也非交一个女朋友不可”,因为,“贞操既属封建,应该打倒,男女同学随意乱来,班上女同学,多大肚罗汉现身,也无人以为耻”(61)苏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第45页。。处在个人异化的生活时间里,“并不像先驱者所设想的那样由情感的解放、爆发来促进理性的解放,确认新时代的理性精神,反而逐渐远离理性的母体而趋向情绪化”(62)张宝明、张光芒:《百年“五四”: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对话》,《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1期。。这种五四情绪更多的是非理性成分居多,脱离了正常的生活时间轨道。
五、结 论
小说现代性的本质是小说的时间意义,其时间叙事的重心在于小说家如何处置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史里,不同时期小说家们对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的塑形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即使是同一个时期的小说家们,他们对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的塑形也不太一样。在晚清、五四小说中,现代转型时期的小说家对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赋予多种意义的“塑形”,编码、生产出“落后”“进步”“异化”等多种时间美学意义。但是,晚清、五四之后,小说家努力挖掘时间的进步性,小说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越来越被看成落后的、非革命性的,自然成了批判的对象而加以舍弃。这种个人自由时间的“窄化”叙事到了十七年小说、文革小说达到了极致,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小说。在这些小说中,为了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形象,林道静、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主要英雄人物的个人自由时间很难被纳入到革命的叙事中,其个人自由时间的“窄化”叙事是必然的。当然,个人自由时间塑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值得在文学研究中展开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