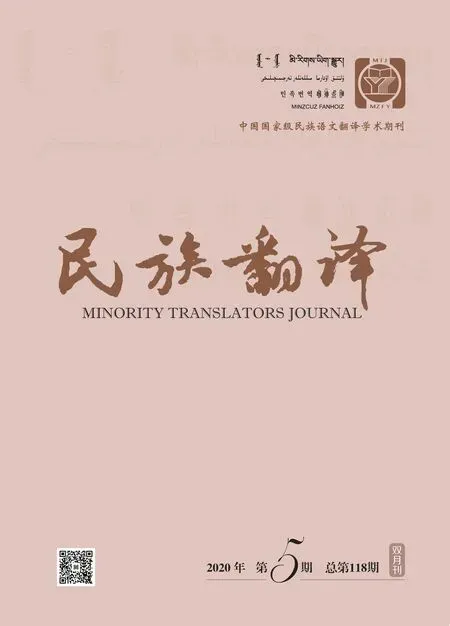《论语》在韩国的译介状况与典籍外译策略探析*
⊙ 白 璐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论语》作为儒学的代表性著作,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在海外的译介是中国文明与中国形象对外呈现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表现。韩国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4世纪,“韩国儒学”作为带有韩国文化特色的儒学思想,是东亚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韩国的《论语》翻译史称得上是海外儒学典籍翻译的优秀典型,韩国也可以说是海外儒学普及最成功的地区。他们不仅翻译了儒学典籍,还深入分析并接受了儒学,使得儒学思想深入到了韩国人的文化和生活中,创新发展了“韩国儒学”并向海外传播。本文旨在梳理《论语》在韩国的译介过程,分析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韩国对《论语》翻译和接受的基本脉络,对比分析各个时期《论语》译本的特点,理清影响各时期译本的诸多因素,分析韩国儒学典籍的译介方式,找出我国典籍外译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典籍外译策略。
一、《论语》在韩国的译介过程
(一)《论语》译介的汉字谚解期①(公元前3世纪至15世纪)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长达两千余年之久,译介史也达五百余年。中国人大批移居朝鲜半岛始于秦初,儒学典籍传入朝鲜半岛的时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年左右,即春秋战国末期和秦朝初期[1]。朝鲜半岛在拥有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之前,历史文化的记录和传播一直依赖于汉字。因此在儒学典籍传入朝鲜半岛以后的一千多年里,《论语》主要以汉文形式被传播和学习。历史上虽然也有利用“吏读”和“口诀”等汉字借字标记法对《论语》进行谚解的记录,如《三国史记·列传》中记载新罗学者薛聪以“吏读”的形式对儒学典籍进行解读,又如朝鲜后期郑元容编撰的《文献撮要》中记载高丽末期学者郑梦周和权近以“口诀”的形式对儒学典籍加以注解[2]189,但吏读和口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译介,只是借用汉字标注汉文中没有的助词和语尾,便于本国人的阅读和理解。
(二)《论语》译介的汉朝混用谚解期(15世纪至19世纪末)
训民正音创制以后,朝鲜半岛的儒学典籍翻译工作逐步展开。15世纪到19世纪末,朝鲜半岛的儒学典籍翻译基本是国家组织下的翻译。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儒学典籍翻译工作在朝鲜世宗时期(1397—1450)展开,集贤殿学者们奉王命翻译儒学典籍,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发行,但可以说此时期的成果奠定了《论语》韩译的基础。朝鲜成宗时期(1457—1494年),以儒教性理学为重要政治理念的士林派掌握了中央政治的主导权。自此,儒学典籍翻译迎来了新的局面。为了广泛传播儒教性理学理念,士林派学者倾尽心血翻译和传播儒学典籍。朝鲜半岛最初的《论语》翻译成果是朝鲜朱子学代表人物李滉的《论语释义》②。1576年儒学家李珥奉宣祖之命翻译四书,最终以《四书栗谷谚解》为名于1749年出版,《论语》译文收录于其中。1590年校正厅发行《论语谚解》[2]190。这三本《论语》译著影响了朝鲜半岛儒学典籍翻译长达300余年,也是朝鲜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儒学译著。此时期的翻译也称为“谚解”,所有汉文译著都是在原文之后附上谚解文,原文的每个汉字后面用训民正音注音,并加上标示助词和语尾的“悬吐”,便于本国人阅读。
此时期的翻译有如下特点。第一,彰显了典籍权威主义。《论语》谚解书籍主要是士大夫之间传播和学习儒学典籍的工具,并没有做到民间普及,其翻译目的也不在于大众普及化。第二,在儒学核心词的翻译上基本采取了不译的原则。仅在原文后加上了训民正音注音,并没有用朝鲜语固有词翻译出来,如“仁,孝,弟,谨,信”等词。此不译原则也可以窥视到朝鲜时期重视典籍权威性的一面。与《论语》谚解书在相近时期出版发行的《小学谚解》使用了大量的朝鲜语固有词,其大众普及性明显要比《论语》谚解书籍高得多。这说明当时朝鲜士大夫将《论语》视为不可亵渎的神圣经典,翻译时十分慎重,如若使用朝鲜语固有词,多少都会对原文含义有所损害,也易出现误译,为了最大程度保持原文的“圣意”,学者们不得不采取消极翻译原则。
(三)《论语》译介的近代化(1900年至1945年)
从短暂的大韩帝国到长达35年的日本统治时期,朝鲜半岛儒学典籍翻译进入了近代化发展时期。此时期出版发行的《论语》译著比朝鲜时期多,但和后期《论语》译著的大量涌现相比,译著数量并没有很大的增长趋势。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译著有三部。一是1909年发表的《少年论语》,二是1922年儒教经典讲究所出版发行的《谚译论语》,三是1932年文言社出版发行的《言解论语》。
《少年论语》是朝鲜半岛第一本近代综合杂志《少年》在1909年第7-10期中连载收录的《论语》翻译。此杂志在创刊的第一年,所有刊登的文章和翻译都出自创刊人崔南善之手,《少年论语》的译者也即崔南善。崔南善出生于1890年,儿时在私塾学习汉字和汉文,自学了训民正音。1902年进入京城学堂学习日语,1904年赴日本东京留学3个月后归国。1906年再次赴日,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地理历史,1907年退学。1908年归国创立新文馆,1909年创刊《少年》并担任青年学友会的创立委员。1919年作为民族代表48人之一起草《独立宣言》,参与“三一”运动。从崔南善翻译《少年论语》的前后经历来看,翻译《论语》对于自小接受私塾教育的他并不困难,作为当时支持独立的进步青年,崔南善通过翻译《论语》表达了他对青年读者寄予的期望[3]138。
《少年论语》属于《论语》的选译本,只翻译了“学而篇”的6个章节,“为政篇”的12个章节和“八佾篇”的1个章节。从翻译内容来看,主要选取了孔子对弟子说的话,而弟子及其他人的话则被排除在外,这可以看出崔南善顺应时代的需要,选译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需要的内容[3]139。韩国典籍翻译学界普遍把崔南善的《少年论语》奉为韩国典籍翻译近代化的开始,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第一,脱离了典籍权威主义。《少年论语》摒弃了原文中晦涩难懂的汉字词,用最通俗的语言翻译了原文,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懂经典内容,从中领悟人生哲理。第二,结合句意和文章脉络,使用了多种翻译方法。虽说当时的韩国知识分子熟知汉字,精通汉文,但汉文毕竟是符合汉语结构和语境的表述方式,翻译成和汉语结构完全不同的朝鲜语就需要下很大功夫推敲翻译方法。崔南善在这一点可谓开创了韩国近代典籍翻译的先河。
《谚译论语》和《言解论语》的最大特征是详细。正文部分包括原文、字解、训读和意解。原文部分添加了训民正音注音和助词、语尾的“悬吐”标记。“字解”是逐字对原文进行解释,“训读”是翻译部分,“意解”则把原文中蕴含的深层意义和背景做了详细叙述。从翻译意图来看,这两本译著在韩国被评价为日据时期增强殖民统治的工具,当时的日本利用韩国人熟知的儒教理念加强殖民统治;从翻译内容来看,《谚译论语》和《言解论语》的近代性特点不足。这两本书的训读部分和朝鲜时期出版发行的《论语》谚解书并无太大差别。字解和意解的内容仅仅是对朱熹《论语集注》内容的概括,很多表达方式照搬了《论语集注》的原文。
此时期的翻译有如下特点。第一,翻译的内容更加详细,具有大众性。与朝鲜时期针对士大夫阶层翻译的《论语》相比,此时期的《论语》翻译面向的是更广的读者群,目的不是宣扬典籍的权威性,而是让广大群众普遍了解儒学典籍的内容;第二,翻译目标语的近代性突出。代表性译著就是《少年论语》,此书使用了大量的朝鲜语固有词,在普及儒学典籍内容上有重大意义。
(四)《论语》译介的蓬勃发展期(1946年至1990年)


成百晓1982年毕业于高丽大学汉文教育系,现任韩国古典翻译院名誉汉学教授、成均馆大学兼职教授、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海东经史研究所所长。他翻译的《论语集注》(1990)可谓是至今韩国读者最多的儒学典籍译著,这本书作为韩国大学学习汉文的教材被广泛使用。从翻译内容上来看,《论语集注》(1990)是朱熹《论语集注》的译书,译文简单易懂,注解详细;从翻译方法来看,采取了逐字翻译,详细解释了每个汉字和整句话的意义,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汉文学习教材。
除以上译著之外,这一时期的《论语》韩译本还有:表文台的《论语》(1965),车柱环的《论语》(1969),朴一峰的《论语》(1973),桂明源的《论语》(1975),都珖淳的《(新译)论语》(1977),李明奎的《趣味阅读论语的方法》(1983),安炳周的《论语》(1984),李民树的《论语解说》(1985),张基谨的《论语新译》(1985),金钟武的《(释纷订误)论语新解》(1989),金敬琢的《论语中庸大学》(1989),等等[3]158。
(五)《论语》译介的多元发展期(1991年至今)
笔者在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上搜索1991年至今以“论语”为题的书籍,搜索结果998条,仅2019年就有23部《论语》译著发行。类别涵盖大学教材、儿童读物、儒学研究书籍、漫画、随笔等,译本形式和风格有全译本、变译本、叙事性译本、文学性译本、趣味性译本等等。由此可见,进入90年代,韩国译者对儒学典籍的认识已基本脱离了固定思维,不再将《论语》作为晦涩难懂的汉文书籍来处理,而是作为韩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进行解读。
多元化时期的《论语》译介有如下特点:第一,译文简单易懂,贴近生活,译本以韩语译文为主,原文作为附录或脚注收录;第二,译者不再局限于学者和研究人员,非专业人士也参与到了《论语》的翻译中去,扩大了儒学典籍的译者层和读者层;第三,译文添加了译者的见解等原文中没有的内容,丰富了《论语》译本的内容;第四,过去的重要译本纷纷修订重版,顺应新时代读者要求,改进翻译方法,突出译文的重要性,力求译文的独立性。例如,成百晓的《论语集注》(1990)以《最新版论语集注》(2017)为名再版,李家源的《论语新译》(1956)以《论语》(1994)为名再版,车柱环的《论语》(1969)以《新译论语》(1994)为名再版。
二、《论语》在韩国的译介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结合布雷多克的传播学七要素模式,可以总结出《论语》在韩国传播发展中的译介主体、译介形式、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情景、译介效果、译介受众七个方面的特点。
(一)译介主体
韩国《论语》的译介主体经历了从士大夫到汉学家到多层次译者的转变。朝鲜时期是《论语》韩译的初级阶段,译介主体是以儒教性理学为政治理念的士林派,其中李滉和李珥最为著名。日据时期《论语》韩译的译介主体则转换为进步人士或亲日派人士,其中崔南善最为著名。独立后到1980年代《论语》韩译的译介主体以汉学家、东洋哲学家为主,其中李乙浩和成百晓最为著名。1990年代至今《论语》韩译的译介主体扩展到了非专业人士,译介主体范围最广阔,标志着《论语》韩译深入到了韩国人的生活中。
(二)译介形式
韩国《论语》的译介形式经历了从典籍到专著到教材到多元化形式的转变。朝鲜时期的《论语》韩译是针对士大夫阶级的,具有明显的典籍权威性。进入20世纪后,译本形式逐渐向专著转换,学术性特点较强。1980年代后译介形式增加了教材这一重要类别,并在大学中广泛推广。1990年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论语》在韩国的译介形式呈现多元化,有专著、教材、随笔、儿童读物、音像制品、视频课堂等等。
(三)译介内容
韩国《论语》的译介内容经历了从全译到节译到增译的转变。朝鲜时期为了彰显典籍权威性,均采取全译。进入20世纪,选择性的节译逐渐增多,例如,儿童读物基本采取节译形式,选取论语中教育意义强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添加译者见解的增译也越来越多,译者把《论语》的内容与自己的见解结合起来,以随笔或散文的形式出版。
(四)译介途径
韩国《论语》的译介途径经历了从官方出版到多元化出版的转变。朝鲜时期的《论语》译本主要由官方组织翻译并出版,目的是作为士大夫阶层的读物或教材。日据时期的出版也主要由日本殖民政府组织翻译并出版,目的是为了加强殖民统治。到了现阶段的多元发展时期,出版途径早已脱离官方限制,以盈利为主的私人出版社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论语》韩译本的出版发行队伍中来。
(五)译介情景
译介情景也是译介背景,韩国《论语》的译介情景经历了封建社会、殖民地时期、学术复兴期和文化交流全球化时期。在各个时期,《论语》译本分别作为封建统治工具、殖民统治工具、学术复兴标志、文化交流的工具发挥着作用。
(六)译介效果
《论语》在韩国的译介效果和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受容状况息息相关。“译作在目的语国传播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文化接受国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以及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等。当译作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接受国所倡导和追求的价值观相近或相同时,该译作就更容易得到接受和传播。”[5]从这一点来看,《论语》韩译本在韩国的译介效果是极佳的。韩国和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文化、思想和制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论语》韩译本真正出现之前,儒家思想就已深入到朝鲜半岛。韩译本出现之后,其受容的积极效果则更为显著。
(七)译介受众
《论语》韩译本的译介受众经历了士大夫阶层到普通民众再到全体公民的转变。朝鲜时期的译本面向的是士大夫阶层,其出版目的是彰显典籍的权威性,让士大夫阶层更好地学习《论语》,以巩固统治阶层的地位。日据时期的译本面向的是普通民众,其出版目的有两个:独立民主人士翻译《论语》是为了唤醒青年志士;日本政府监控下的《论语》译本是为了加强殖民统治。韩国独立后到80年代,《论语》译本面向的也是普通民众,不过更有针对性,由于此时期译本主要是学术性著作,因此受众局限于研究人员和相关专业的学生。90年代之后的《论语》韩译本面向的是全体韩国公民,翻译呈现多元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其译介受众不分男女老少。
三、对我国儒学典籍外译的启示
(一)《论语》在韩国的译介状况引发的思考
从《论语》在韩国译介的状况来看,以下两点值得深入思考。
第一,中国译者缺席《论语》韩译译介过程。
韩国《论语》的译介以本国的翻译力量为主。从《论语》的韩译之初,主要依靠的就是目的语国的翻译力量。虽然中国译者过去没有参与《论语》的韩语译介,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译者应该缺席典籍韩译的译介过程。现存《论语》韩译本存在很多问题,正如韩国哲学家成泰镛所指出,“纵观现有的典籍韩译书籍,韩国的东洋古典翻译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可以说典籍韩译没有真正迈出第一步。译文不仅仅是存在不顺畅的问题,很多重要内容都多少存在误译现象。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对外国典籍的单方面翻译。”[4]328可以说,正是因为单方面的翻译,也即源语国家译者的缺席,造成了以《论语》为代表的典籍韩译本的误译频出。
第二,中国文化典籍韩语译介研究的边缘化。
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始于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翻译的《明心宝鉴》,笔者认为这仅仅标志着中国典籍在西方世界译介的开始。典籍外译的“外”字代表的应该是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地区和国家。单从这一点看,朝鲜朱子学代表人物李滉翻译的《论语释义》和1576年儒学家李珥奉宣祖之命翻译的《四书栗谷谚解》都要早于高母的《明心宝鉴》。以上事实反映了国内典籍翻译学界对韩语译本的不重视。
国内对典籍外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译、法译、俄译和日译上,对韩译的研究非常少。从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这一现象是十分不合理的。朝鲜半岛作为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主要地区之一,不仅接受着中国典籍的影响,还作为桥梁将无数典籍传到了日本。可以说朝鲜半岛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桥梁。欧洲从17、18世纪才开始流行中国文化,翻译中国典籍,而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典籍就传入了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国家从公元4世纪左右就对中国典籍展开了广泛的传播和研究。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朝鲜半岛的学者就利用汉字借字标记法对中国典籍进行了初步翻译。这一系列的研究动态和丰厚的翻译成果理应引起国内翻译学者的重视。笔者相信,通过对典籍韩译的研究,参考儒学典籍在韩国的受容状况,可以探索出中国典籍对外传播的方法和路径。
(二)典籍外译对外传播策略
参考《论语》在韩国的译介状况和引发的思考,可以对中国典籍外译应采取的传播策略总结如下。
首先,加强力度培养目的语翻译人才的同时,鼓励中国学者与目的语国家译者合作,共同开展典籍外译工作。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译现象,保证译本的质量。从影响《论语》韩译本翻译质量的因素来看,主要为词汇误译、句子误译、文化误译、漏译、过度添译等五种类型。[6]61误译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历史残留问题,也可以称之为历史误译的石化现象。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译者的缺席,合格的中国译者不仅可以纠正语言上的误译,更能纠正文化上的误读,可以更为准确地传递中国信息和中国文化。
其次,调查研究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需求,明确翻译内容和翻译目的。不能盲目地翻译和传播中国典籍,要先了解目的语读者的需求,研究目的语国家读者的接受程度,将目的语国家需求量较大的典籍译介出去。从《论语》在韩国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此典籍在韩国的受众面较广,接受度较高,从简单易懂的儿童读物到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都能看到对《论语》的解读。那么从中国视角或中韩比较视角出发,由中国译者参与翻译出版的相关典籍译本也会有一定的市场。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考虑对象国的受众程度,这样才能更好地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文化。
再次,开展多层次、多维度的典籍外译工作。尽量不要限制典籍外译的读者层,而要把读者层定位在不分男女老少的所有群体,因此需要调查研究目的语国家各个层次读者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翻译工作,用文学随笔、漫画、小说等多种体裁译介中国典籍,让各层次的读者可以广泛接受。用贴近对象国的方式译介中国典籍,用浅显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从而讲好中国故事。
最后,在政策上加大中国典籍外译的资助力度,让更多的学者和译者参与进去,开展国际合作,出版更多高质量的译本,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以上三点单凭某位译者或学者的一己之力是很难实现的,在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关的典籍外译政策,加大力度资助外译项目也是树立国家形象的关键。
四、结语
针对儒学典籍的韩译本,国内翻译学界应从译介过程、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等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研究,从中探究中国典籍外译的路径和策略。中国是一个重视交流的国家,典籍外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交流永远都是双向的,只有在充分的文化交流中开展翻译工作,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注 释:
①朝鲜半岛将汉文典籍翻译成自己民族语言的过程及其译本称为谚解。
②《论语释义》的初版具体发行年代不明,韩国学界普遍推测认为是1557年,再版年代是16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