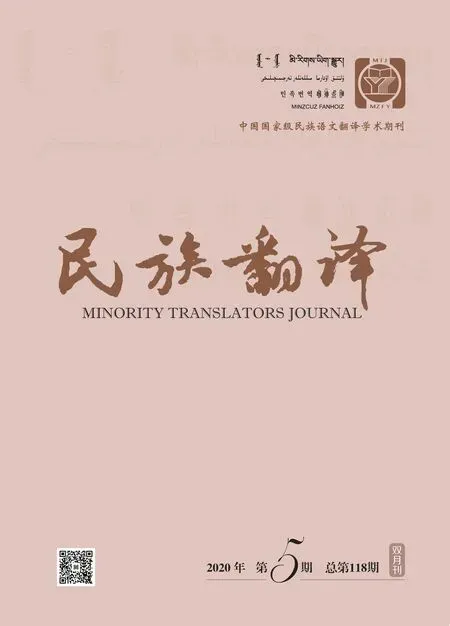从汉语词语翻译的角度看《西游记》的维吾尔语译本*
⊙ 努尔艾力·库尔班 阿尔帕提古丽
(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甘肃 兰州 730030)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也是我国最著名的神魔小说。目前,关于《西游记》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及翻译,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如,唐红在《〈西游记〉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西游记〉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传播状况及其对民族文化交流的启示》两篇文章中,分别从《西游记》在新疆地区传播的历史、传播途径以及接受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1-2]在《西游记》的翻译研究方面,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硕士学位论文中论及较多,如布海丽且姆罕·麦提斯迪克的《〈西游记〉中神魔名称及其维译研究》、贾义龙的《浅析维译版〈西游记〉中佛教词汇的翻译》、努日曼古丽·买买提江的《〈西游记〉维译本人物名称翻译研究》、邹艾璇的《〈西游记〉中佛教称谓语及其维译研究》、谢瑾的《论〈西游记〉回目中专有名词的维译研究》和严治平的《〈西游记〉维译本中妖怪名称的翻译分析》等。
《西游记》作为一部典型的中华古典文学名著,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我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维译版的《西游记》能让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族人民了解中华优秀文化及其博大精深,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从而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长久治安。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西游记》维吾尔语节译本在新疆地区广泛传播;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游记》维吾尔语全译本得到了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人民的青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传播过程中,《西游记》对维吾尔族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西游记》已经超出了一部文学经典的范畴,它已经成为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成为构建新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媒介。从这个角度看,对《西游记》的汉维翻译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翻译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促进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深度交流。本文将从汉语词语翻译的确切性、简洁性和生动性等几个方面对《西游记》的维译本进行描写性探究,借此为《西游记》的维吾尔语译介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一、从词语翻译的确切性角度看《西游记》的维译本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词语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会直接影响到译本质量。所以,在翻译工作中比较有经验的译者,往往把最多的时间放在琢磨推敲词语最确切的意义上。翻译像《西游记》这类包含丰富文化内涵的古典名著更是如此。因为《西游记》具有浓厚的方言色彩,反映的是明代中后期的语言特征,同时还包含了大量的诗词韵文。
词语翻译的确切性包括词义的轻重、范围、褒贬,词语的语体色彩、宗教色彩、文化内涵、政治含义,词语搭配以及同义词、近义词的选择等内容。如果译者对词义的理解不够深刻或者把握不够准确的话,会直接影响翻译的确切性。比如:
例1:
原文:自此,石猿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遂称美猴王。[3]3

例2:
原文:哪吒喝道:“泼妖猴!岂不认得我?”[3]39
译文:häy soltäk maymun,meni tonumaywatamsän?—didi naja warqirap.[4]71
如果我们直接阅读译文的话,不会感觉存在任何问题。但仔细比较这两种文本会发现,译者还是出现了一些错误。如:例1中的“隐”“遂”“美”这三个字。在原文中,“石猿”登上了王位之后,把“石”字给“隐”了、去掉了。这是因为出于一种尊重,表明“石猿”的机智。在译文中,译者尽管把“隐”字译成“tašliwitip”,意为“去掉、扔掉”,准确无误,但翻译“遂”字的时候译成了“bara-bara”,可以理解为汉语中的“逐渐地、慢慢地”。在原文中的“遂”字本来有“于是、就”之意,故原文的意思应该是“于是被称之为‘美猴王’”,所以译者在这里应该译成和“于是”相对应的维吾尔语“šuniŋ biän”,会更确切一些。译者在“美”字的翻译上也有失妥当。在原文中的“美”字指“石猿”的外貌,意为英俊潇洒。而译文中的“hörcamal”虽然有“美、漂亮”之意,但多用来形容女性的外貌,基本不会用于形容男性的外貌上。故译者如果把“美”字译成“uz”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翻译原文的话,可译为“šundin kiyin,taš maymun büyük padišahliq täxtidä olturdi,hämdä《taš》digän sözni tašliwätti.šuniŋ biän uz maymun šah däp ataldi”。这个翻译不仅比原来的译文显得更确切一些,而且还能呈现出原著的语体色彩。
例2“泼妖猴”中的“泼”字之翻译值得商榷。众所周知,《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外号很多,例如“猢狲”“猴头”“猴精”“泼猴”等。凡是上天诸神被孙悟空气着了,都骂他“泼猴”。这是因为孙悟空的泼性十足,撒泼使赖是他的一贯作风。在原文中,哪吒奉玉帝钦差捉拿“泼妖猴”,而在这里的“泼”正是“泼皮无赖、不讲道理”的意思。而译文中,“泼”字被译成了“soltäk”,意为“智力低下的、不懂事儿的”,一般用来责骂别人,具有蔑视、贬低人的成分。所以笔者认为,译者在这里把“泼妖猴”中“泼”翻译成“soltäk”不准确,译者如果把它翻译成“wu bišäm maymun”(意为:你这刁顽、泼辣的猴子)或者“wu kökärmä maymun”(意为:你这倔强、放刁撒泼的猴子)的话,比“soltäk”显得更确切一些。因为当时的场景是玉皇大帝派哪吒到花果山找孙悟空问罪,同时又呼其为“妖猴”,在这里哪吒不只是责骂孙悟空,语气中还表现出了对孙悟空的所作所为极其不满的态度。所以,翻译成“wu bišäm maymun”或者“wu kökärmä maymun”比“soltäk”的语气更强烈、更富有表现力,而且还能够呈现出原著的感情色彩。
如果严格按照翻译的确切性要求来看《西游记》的维译本,类似于以上案例中出现的问题还比较多。译者对一些词语的理解不是很到位,会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质量。如:
例3:
原文: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3]42

例4:
原文:却说那山叫平顶山,那洞叫做莲花洞。洞里两妖:一唤金角大王,一唤银角大王。[3]321

例4中,译者把“却说”翻译成“älqissä”,即跟“却说”一样的旧小说的发语词与小说语体很契合。但翻译“大王”一词的时候,译者把它翻译成了“palwan”(意为侠、勇士、大力士)。无论从“大王”的字面意义还是这两个角色的身份来看,翻译成“palwan”跟原文的内容都不太契合。首先,从“大王”的字面意义来看,汉语中的“大王”是官名,对王的尊称。“大王”在表示官名或王名的时候,在维吾尔语中相对应的翻译有“padišah,xan”(意为皇帝、汗)。汉语中的“大王”是古代对国君、诸侯王的尊称,没有排他性,可以与其他“大王”并存。而“皇帝”拥有绝对王权,不承认世上任何其他皇帝,具有排他性。当一方臣服于另一方时,就得改称“君侯、公等”。而维吾尔语中表示“大王、皇帝”的名词“padišah、xan”也有区别,即“padišah”跟汉语中的“大王”一样没有排他性,可以有很多个“padišah”,而“xan”(汗)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具有排他性,拥有绝对王权。不过,汉语中的“大王”除了以上意义之外,在旧小说中还表示对国王或强盗首领的称呼,对土匪头子的俗称,在这个时候,“大”字也读di。其次,在《西游记》中“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原本是给太上老君看银炉的两位童子,观世音菩萨为考验唐僧师徒取经的决心,向太上老君借来丹房童子,化为妖魔。他们下界以后,住在平顶山莲花洞中,给唐僧师徒四人的取经之路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因为他们所在的“平顶山莲花洞”不是“国家”,因此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山大王”,即那些土匪的首领。通过“大王”的字面意义和人物形象的一系列分析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在维吾尔语中跟“大王”的意思相对应的词,即“ataman”(意为首领、头子)或“xoca”(意为王、领主)。由于“xoca”另有宗教意义,即“和卓”,故排除该词,用“ataman”一词较为恰当。最后,我们根据整个原句的逻辑关系,按照维吾尔语的语法表述和逻辑顺序,可将此句翻译成“älqissä,bu tapiŋdiŋän tei däp atilatti,tadiki nelupärarida ikki alwasti bolup,biriniŋ ismi altun müŋgüzlük ataman,yänä biriniŋ ismi kümümüŋgüzlük ataman idi”,(意为:却说,这座山叫平顶山,这座山的洞叫做莲花洞。洞里有两妖:一唤金角大王,一唤银角大王)这样比原来的译文显得更加明了。
可见,词语翻译的确切性在翻译活动中非常重要。因为严复提出的三个翻译的标准(即信、达、雅)中,实现“信”和“达”的关键是译者一定要正确理解将要翻译的每一个词语,并把翻译后的每一个词连贯地在译入语中表达出来。如果译者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不仅是原著的艺术价值受到损失,更是译者的失败,译著的失败。所以译者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避免词语翻译的不确切现象。
二、从词语翻译的简洁性角度看《西游记》的维译本
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考虑词语翻译的确切性,而且还需考虑翻译的简洁性。翻译的简洁性一般指在保留原文内容完整意义的前提下,使译文言简意赅。译者在翻译时尽量使用简单、通俗易懂的句子,避免译文中出现晦涩的语言。这样能保证译文读者能够懂得原文的意思和思想,免得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琢磨一些词语隐藏的含义。除此之外,词语翻译的简洁性还包括在译文中,译者尽量去掉或避免使用可有可无的词、不言自明的词以及空泛虚夸的词等。译者如果对词语翻译的简洁性不够重视,在译文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复杂长句和晦涩语言的情况;但过于简洁,也会造成原文文化信息的缺失。如:
例1:
原文:三藏谢了恩,收了文牒。又奏道:“贫僧一来倒换文牒,二来与陛下寄有家书。”[3]280
例2:
原文:又命四大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高座七宝灵台,调设各班坐位,安排龙肝凤髓,玉液蟠桃。[3]38



三、从词语翻译的生动性角度看《西游记》的维译本
在翻译实践中,我们除了考虑词语翻译的确切性和简洁性问题之外,还需要考虑词语翻译是否生动、形象的问题。词语翻译的生动性主要指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译者除了译出词语的基本含义外,还要译出其分量、感情色彩、使用场合及其所包含的特殊气氛等。尽管翻译语言受到原文表达的限制,但因为在语言中大量存有同一词汇有不同表达的现象,所以词语翻译在选择词汇时,同样有着是否生动、形象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游记》的维译本,我们会发现译者有时候翻译得非常恰当,能够把原文的意思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而有时候翻译欠佳,就呈现不出原文艺术特征。比如:
例1:
原文:菩萨道:你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亦尻![3]82
例2:
原文:那八戒与沙僧闻得此言,就如鬼门关上放回来的一般,即忙牵马挑担,鼠窜而行。[3]162


《西游记》作为我国经典的小说之一,其所包含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间相互交流的手段,更是促进两种文化相互交流或者两种文化相互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手段。由于汉语和维吾尔语属于不同的两种语系,这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和表达形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比较大。所以在翻译像《西游记》这样的文学经典的过程中,译者不但要考虑该作品的语言特征以及文化内容,更要考虑应该怎样把原作的原貌让译文读者读懂、看懂。在这个过程中,承载文化要素的一些词语给译者增加了难度和障碍。当今,尽管学界给《西游记》的维吾尔语译本评价比较高,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见不到系统、全面地对《西游记》维吾尔语译本进行的译介研究。故本文以《西游记》的维吾尔语译本为个案,从汉语词语翻译的几个方面入手,为更好地开展多民族文学互译工作迈出了虽不完美但却切切实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