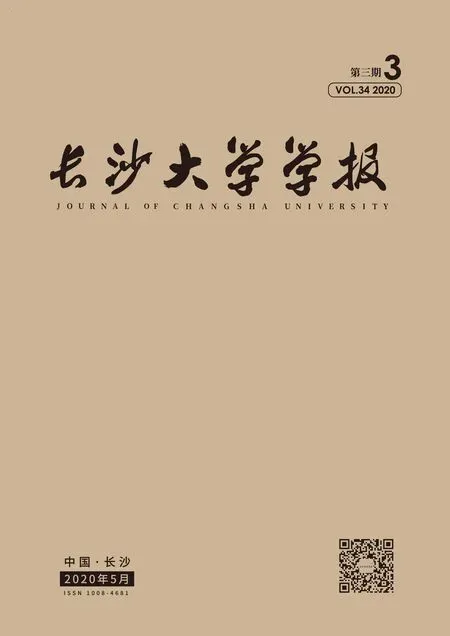狷狂稚子与超灵之子
——现代生态视阈下李贽与爱默生的诗学精神比较
杜 璇
(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目前,学界没有关于李贽与爱默生的对比研究,乍看起来,这两位作家处于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两人似乎不具有可比性。但仔细研究两位作家的作品,探究两者的诗学精神和审美思想,会发现他们的自然观、个性观、平等观会出现一些“遥契”,很值得细致比较。因此,本文拟对两位作家诗学精神的异同加以比较,力图追根溯源,挖掘出异同的深层原因。
一 自然观的异同
不同国度、不同年代、不同文化氛围的作家的审美精神有时会隐形于文心相通之处,比如李贽与爱默生都喜欢居住在大自然中,都主张回归自然、顺应自然,构建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精神家园,以获得灵魂的洗涤、情操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华。
(一)向往自然:“童心说”与“超灵说”
李贽和爱默生热爱自然的特点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因为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都把自然当成精神寄托和信念支柱。李贽经常在感受自然生命的气息之时,享受自然给他带来的启发。他虽然谙熟并掌握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但他没有照搬照抄,他将佛教、道教和自己的理解融会贯通,建构出独具特色的 “自然真空”理论。他认为只有经过自然的洗礼,人们才能拥有一颗未受功名财富等外界因素干扰的、毫无造作的真心,才能拥有表达个人真实感受、真实愿望的本心以及抒写真实意见、真实建议的诚心。他在《童心说》中这样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纯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也。若失却真心,便失却童心;失却童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92只有经过自然的浸染,人们返璞归真,才能脱去任何伪装,摒弃任何的矫揉造作和谋权算计,方能培育出简单淳朴、表里如一的性格特征。
以我之见,李贽毕生追求三个维度,第一是自然界之真,第二是艺术之美,第三是人格之实,这三个维度在他性格中的体现就是蔑视一切权贵的狷狂性格。他认为,基于功利性目标教育的道学只能怂恿和蛊惑众人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这种彻底的虚伪虚假的教育只能使人的童心丧失殆尽,从而使人失去了人之为善的内在根据。李贽大力提倡的远离功名樊笼和世俗干扰、简化人际关系、回归童心是对社会现实的反驳,这给当下视功名利禄为自身生命意义、视官位权威为人生终极目标、视金钱财富为人生终极价值诉求的人们以很深的启发,而他这种任真放旷、率性冲澹、清贫高洁、孑然一世的自然人格也滋润着中国传统文化。
19世纪初的美国,虽然国土幅员辽阔、资源比较丰富、工农商业日益发达,但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教育理念、自然观念等方面,人们一直受着欧洲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基督教大肆鼓吹人的原罪意识、人性本恶等,实质上束缚了人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所谓原罪原本是引导人类向善以洗涤身上罪恶的一种理论,却逐渐沦落为教会敛财的手段和获得特权的工具。后来在工业化大潮的席卷下,在追求高额利润、唯利是图的商人的推动下,实用主义与工业理性成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这些社会思潮激发爱默生构建新的思想理论,他提出人性本善的思想,认为人生来为善且应一心向善,争斗、暴动、动乱、重财则是迷障、蒙蔽人本真的恶魔,要唤醒内心被蒙蔽的美德和善意就必须让心灵回归到人类生命的初始状态,因为个体只在未受外界诱惑和干扰的初始阶段即婴儿阶段,才能保持卓越的道德状态。在《论自助》中,爱默生认为:“婴幼儿时期我们不会遵从任何人,大自然会满足人们的崇高要求,即对美的追求,只有那种从内到外都协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他能始终保持儿童式的天真,哪怕在他成年和老年。他与天地的交流成了他每日食量的一部分。”[2]16
在《再见》《杜鹃花》等诗中,爱默生呼吁人们要隐匿藏身到作为人的精神港湾的大自然中。他认为,人们在漫长的白昼下,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中眺望遥远的地平线,在画眉鸟、杜鹃花、柔软的沙地、潺潺的小溪等组成的绿色生态空间中漫步,能回归到生命的本初,获得生命之素朴、内心之静谧、精神之充实。
爱默生在《论自然》《神学院演讲》等著作中认为,有种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的能量充斥于宇宙之间、天地万物之内,世界万物都是它的显现,这个物体他称之为“超灵”(oversoul)。这也是宇宙的本源, “超灵”的功能是指引人们向善。自然是这种超灵的显现,无处不在的神存在于自然世界中,具有终极的精神价值。上帝是有坚定意志的创造者,能为自然提供运作准则、价值预设和运转规律。上帝也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精神存在,不管是庞然大物,还是微小颗粒,都是上帝巨大价值的体现,而且从外到内都散发出崇高典雅的神圣性。
爱默生用总体(unity)表达这种至高无上的观念,他号召人们返回自然并沉醉在自然的怀抱中以便人和上帝合一;人们可通过运用自己的直觉、想象、冥想和上帝尽情沟通交流,以获得上帝的启示以及感受到宇宙的奥义,由此获得更芬芳甜美、更神秘隐秘、更让人钦佩的道德美好和心灵公正,从而重新获得升华了的精神的神圣体验:自然是人心灵的镜像,自然是终极美的显现、道德的体现、真理的投影和智慧的隐射。
爱默生的自然观和李贽的观念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提出自然状态说,即人类社会应该效仿自然界的自然状态,人们应该远离喧嚣社会,回归宁静的自然世界;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灵魂才能得以净化,邪恶能够自动被过滤和被删除,从而自然能阻止人类作恶多端,甚至可以代替法律。如此,人和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等各种不平等关系也将被和平友善、和谐相处所代替。
(二)“天人合一”与“人是万物的主宰”
虽然两人都崇尚自然,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他们的理念有着明显的不同。
李贽把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大济苍生作为自己人生的至高理想。当他准备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学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时,黑暗污秽却将他这样的正直之士排挤、陷害,他自我言说的权利遭到剥夺,挽救苍生的人生梦想也随之夭折。在饱尝仕途坎坷的摧残和折磨后,他退隐官场并把山水田园作为宣泄官场种种失意和苦闷的归所,在田园风光的浸染中舔舐着自己破碎的心灵,寻找自己的归属感,所以他提倡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寻求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境界。他在表现人和自然的关系时大多持有的是平和空明、虚静从容之心,所蕴含的是冲淡超脱、玄远幽深之情,所展示的是在明丽怡静的大自然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情趣和内心体验,所追求的是物我交融、冲淡虚静、空灵淡远之境。李贽诗中的自然是美丽姣好的,人生的状态是悠闲自得、舒适惬意的,并由此展现出一幅幅天人合一的景观。
爱默生主张人是自然的最大管家,自然和人类的关系是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他在美国浪漫主义的宣言书——《论自然》中这样表示:“野兽、动物、种子、火把、岩石等都是为人类服务的,田野是他的地板、他的工场、他的花园、他的床铺。而人接二连三产生战无不胜的思想——征服一切,直到世界最终变成一个人意识的实践场地。”[3]6
爱默生的著作充分说明自然作为奴仆是要为人类服务和工作的,如大风播撒种子和蒸发海水,季风把水蒸气吹向田野,雨水灌溉了植物、植物养育动物等等。日夜不停工作的大自然的生态系统要完全顺从和听命于人的命令和调配, 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甚至要通过提高技术来更好地开发和攫取自然,以便自然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人类要借助自己的智慧,不再乞求风向帮助他的航行;为了减少摩擦,人类用铁轨铺路,在上面设置能容纳满满一车人以及容纳牲畜和货物的车厢。”[3]18他抬高人的力量,认为世界是微不足道的,人才是掌握一切自然规律的主宰者,每个美国人都要相信自己的价值。他也推崇独立自由精神以及最大力量地开采自然资源。他的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思维方式遭到批评家们的诟病,他们认为这是非生态的,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两人对自然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中美经济政治局势、历史文化背景、审美思维方式的不同密切相关。李贽深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浸染。在华夏农业文明中,自给自足、稳定的生产结构孕育了国人温柔敦厚、平和泰然的品格,造就了国人偏向欣赏温柔如玉、质朴淡然的作品的审美趣味。郭沫若曾对东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做过对比研究:东方人于文学喜欢抒情的东西,喜欢沉潜而有内涵的东西,但要不伤于凝重;那感觉是要类似玉石般玲珑温润,类似绿茶般于清甜中带点涩味,一切都要有沉潜的美而不尚外表的华丽;喜欢灰青、喜欢忧郁,不是那种过于宏伟,压迫得令人害怕的[4]。笔者认为,郭先生对我国古典诗歌的“中和之美”“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把握得很到位。中国古代诗人认为诗歌是寄托情感的工具,诗人应该采取一种以虚待物的静观态度,抑制主观意念、节制主观情感;要融情于物,要完全融入到自然中去,对山水田园的描写也要完全物化,达到“空灵”的审美境界,所以李贽的作品通常以含蓄委婉的情感寄情于风花雪月、微风细雨、梅竹松石、鸣啼鸟虫等具象当中。
爱默生征服自然的思想与本国的地理环境有关,美国濒临海洋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美国人征服自然的历史文化传统;还与美国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关。爱默生生于1803年,卒于1882年,他在世时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人们利用先进发达的科技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使人滋生一种能够主宰天地万物的错觉。当然,那时的人类对自己改造自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尚未明显察觉。
二 个性观的异同
(一)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
在中国封建社会,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尤其是在程朱理学所谓“天理”的压制下,人们的个性得不到自由充分的发展。封建伦理秩序中的家庭中心主义观念已经内化到国民个体的无意识中,国民在个性释放、配偶选择、爱情追求等行动上都必须尊重并严格服从以家庭血缘体系为核心的价值标准,所以,国民对个性释放的渴望和对自由恋爱的憧憬早已被以血缘情感伦理为特色的宗法家族文化所冲淡、遮蔽和掩盖。以个性释放和情感解放来反抗和解构封建伦理本位文化是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因此,李贽要求个体摆脱一切封建道德等外部的束缚而为自身代言和立法。李贽深刻认识到专制制度对人身心的毒害,他想打破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所以把宣扬个体本位思想和提倡个体无拘无束的追求作为创作方向。李贽肯定个人谋求私利,他这样表达:“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己也。”[5]38他主张每个人不能盲目地以他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有独立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要以实现自己的利益为最终目标。由此他呼吁人们要抱有一颗未被社会世俗观念污染和遮蔽的、源于自然本性的最真实的本心,以解放人们思想,摆脱长期压迫人们的封建主义专制。
萌生于对英国殖民专制政治体制的反省和解构,并通过对美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考察,爱默生形成了以追求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为内涵的诗歌创作,且以饱满的激情回应了国家独立后社会的时代脉搏。他把矛头指向清教禁欲制度。殖民时期的英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后来的清教教义对美国人性的钳制和压抑是多角度的,因此,要使得美国人的人性从传统理念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以个性释放的原则对国民意识进行改造和重塑是必不可缺的。所以,爱默生继承和改造了基督教对人的神性诉求,推崇个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相信个人的无限潜能。在《不朽》中,他指出:“个性就是一个人的全部价值所在,自力更生,依靠自己,人的地位、神圣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支持,而不需要天赋和外部的力量的,最终实现个性的最终解放和自由。”[6]130
爱默生对传统政治文化秩序浸染下的种种国民劣根性进行深刻的审视和猛烈的抨击。在现代文化人格的烛照下,他塑造出很多有情感欲求和叛逆性格的、体现自由意志的个性形象,他诗歌和散文中的傲立于宇宙间、充满个性精神和情感欲望的大写的人的形象极其闪亮动人,他的充满个性解放、情感自由的诗歌精神契合了美国大众日渐强烈的个性意识。
在人性观上,两者都认为人在天地间是最有灵性和智识的,他们充分肯定个人自由和主体价值,认为天下万物之所以各不相同就是因为每件事物都有各自的特色,每个人在性格性情、才能爱好、心理欲求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所以要尊重个人差异。另一方面,他们对弄虚作假、口是心非、僵化僵硬的经书义理和趋炎附势的官场风气深恶痛绝,认为这些是对人本真状态的抑制、对人性的异化、对人格的钳制。所以,他们都提倡洁身自好,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和心灵自由。
(二)今生的私利、享乐和来世的回报
在人生观方面,两人对世俗污浊的趋炎附势深恶痛绝,他们都认为人在天地万物中是最有灵性的。但两人又有很大的差别,李贽注重今生、追求现世的享乐,而爱默生相信人具有神性、相信来世、相信生命的永恒。
李贽与传统的“发乎情、止于礼”的做法背道而驰,认为人不需要过多考虑礼义,而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情感走向,大胆追求并享受现实的快乐,且强调以人的自然而然的真情实感来理解和维护人伦道德。他大大赞赏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蔡文卓,呼吁世人以她为榜样,要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追求现世的快乐。
以农业为本的封建社会极大地排斥了商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治国策略,商人的价值长期遭到贬低,商人的地位也非常低下,其权利和利益长期被他人侵害。而李贽将私利合情合理化,在鼓励人们追求个性的同时允许个人追求现实的私利,满足了广大市民对经济利益的迫切需求。
爱默生一直致力于美国宗教世俗化以突破欧洲清教徒的束缚, 他被誉为美国宗教的预言家和先知。他认为理想的人是自立的人且不在乎私利、充分相信自己。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本能、直觉、欲望和理性理智,有获得知识的能力,有独特的个体价值。他信仰的不是具体的、有形的神,而是非人格的、无形的神。他指出,当人的身心得以解放,并保持高度的道德情操和积极昂扬的个性,就能有个充满幸福的永恒来世。“上帝不是别的,就是灵魂的名字,那灵魂处于万物的中心,而我们存在就是他的证明。 因此成为上帝,上帝的不朽、上帝的威严也就随着正义进入这个人的身体。”[7]102
爱默生肯定人们生活的激情,并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主张用坚韧不拔、激进昂扬的精神和活力探索与挖掘人的认知力、感悟力、理解力。爱默生经常描绘肉体和灵魂全部解放后,具有神性的“我”无拘无束地感受自然神在体内流动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感一直会保持到美好的来世。
关于此种差异,西方社会主义学家马克思·韦伯有充分的解释,他指出:“西方的宗教,从犹太教到新教都是一种神中心式的宗教。这种神中心主义式的宗教认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是宇宙的主宰,世界是他创造的。东方宗教则不同,它的教义中的最高一点是一个神圣的宇宙秩序,人是这秩序的一部分。因此,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得到拯救并非是上帝的恩宠,而是人融入这个神圣的宇宙秩序之中的结果。前者是行动之神,后者是秩序之神。”[8]178
三 平等观的相似及原因
李贽站在平民的立场,以平等的视角审视劳动者,经常为下层民众鞠一把同情的泪水。在生活中他经常和下层民众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和沟通,能体会、领悟和觉察下层人民的情感。他深切体会到平民生存的困难和生活的艰辛,对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给予真切关注,对弱势平民给予人文关怀,尤其关注被强势权力话语排斥和压制的底层民众个性的发挥,因此他对统治者进行告诫劝导,促使其实施仁政。他既有很高的历史使命感和文化优越感,又怀有人文情怀能融入布衣阶层。
李贽在《道古录》等著作中指出,无论是凡人还是圣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之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即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9]1他突出平等的理念,告诫人们不要高估圣人的力量和榜样, 也不要低估凡人的思想和潜能,尧舜与常人并无二致,圣人与凡人毫无差异。
李贽批判道家男尊女卑的不合理的思想观念,认为知识的深浅程度和阅历的多寡息息相关,和性格没有任何关系。他具有前瞻性地提倡男女平等:“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10]3他认为男女在智力能力上、恋爱婚姻上是完全平等的。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男女平等的先哲,他尊重女性的主体意识,鼓励女性大胆追求和充分享受爱情和婚姻的自主权,他很想使女性从封建婚姻的桎梏中彻底摆脱出来。
爱默生非常痛恨金钱万能的社会,对官僚们无休止的丑行进行无情的揭示和鞭挞。他认为国家元首、总统和平民没有任何区别;他心系平民,融入平民生活,不遗余力地描写他们充满矛盾和困惑的生存苦难,歌唱底层劳动人民的尊严,主张他们对暴虐者不逆来顺受、不卑恭屈节,更不俯首听命。他认为应运用新的价值理念铸造出新的文化人格,才可能使底层平民获得反抗力量抗衡异化制度;应借用进步的话语清除各种顽固成见,传授民众争取摆脱个体困境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方法,从而繁荣整个民族精神。
爱默生认为,平民经常是贵族历次发起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但又是美国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平民首当其冲地成为爱默生这个先贤需要拯救的群体。诗人从文化反思、艺术创作等自身实践考察得出结论:若想把平民培养成具有民主意识的道德标本,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反思、质疑和抛弃上层贵族阶级的传统做法,转而挖掘普通劳动者的精神优越性和崇高行为。所以平民是爱默生作品的民主价值的承担者和民主理念的践行者,因而对平民的肯定和歌颂也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内容。
笔者认为,造成李贽与爱默生在平等观上具有相似之处的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李贽与爱默生的平等观都是建立在民主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两人都在平民大众的立场上痛斥权贵们的暴戾统治,并启发民众追求人格独立、地位平等。第二,李贽和爱默生的平等思想都是产生在社会变革、新思想萌芽的背景之下。李贽生活的年代正处在商品经济发展、重农思想需要变革的关键时期,爱默生所处的时代也是社会制度和时代思想都处于变革的时代。美国在思想文化上深受欧洲影响,而获得思想独立和建立代表美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体系就成为爱默生的重要追求。第三,李贽、爱默生两人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家中的环境、对劳动人民的认知、对底层生活的体验和感触等有很大的关系。李贽虽然出生在商人之家,但到他父亲那代已经家道中落。爱默生一生生活清贫,从小父亲去世,母亲独自照顾和抚养五个儿子,家庭拮据。后来又帮破产的哥哥还贷,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之后他又经历了爱妻和弟弟们相继去世的巨大悲恸,更加体会到底层人民的艰辛和不易。
四 世界起源观的相异
在世界起源观上,李贽是朴素唯物主义者。他否定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理能生气”的哲学理论基础,他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则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明矣。而又谓一能生二,理能生气,太极能生两仪,何欤?夫厥初生人,惟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初无所谓一与理也,而何太极之有?以今观之,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10]56他否定了先有所谓的“一”“理”“太极”的存在,指出人们的心理认知、思想情感和道德情操等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
而爱默生是个坚定的宗教信仰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世界的起源全部是精神,世界的本源也是思想和意志。他说: “世界和人的身体一样,都是来源于精神,世界是上帝在潜意识中的一个投影。那种向我表明上帝就在我心中的宗教,使我心灵上的力量顿然增长,那种对我来说上帝是我之外的宗教给我的,则使我痛苦不堪。”[11]39哪怕恶劣的外部环境给他内心带来许多失落和沮丧,爱默生在诗中仍然苦苦寻觅着拥有怡然澄澈境界的上帝。
“中华古典诗词章句中,常将复杂的情感浓缩于意象之中。”[12]李贽以自然中的意象描写抒发人生意趣,追求人性在自然中的回归,爱默生也生动刻画了自己憧憬的人性舒展和自由的状态。对于自然,李贽的诗文展现出人和自然是朋友关系,人是自然的欣赏者,应追求人与自然的充分融合,而爱默生则主张人是自然的主宰者、探索者、挖掘者,自然为人服务;对于个性,李贽提倡人应该保持儿童的稚性,而爱默生认为人具有神性,人神合一。在世界观方面,李贽推崇物质起源说,是唯物主义者,爱默生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的审美观念和哲学理念影响至今,激发后人的想象力,拓展了后人的诗学经验,为人们对他们的诗学想象提供了多维度的诗情空间。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