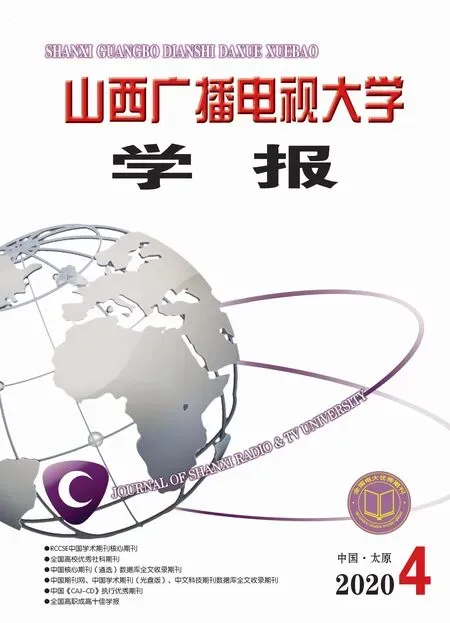有 趣 的 配 角
——简·奥斯丁笔下的中老年妇女形象解析
□董 娜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简·奥斯丁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杰出的女性作家,20岁左右开始创作,短短的一生留下了六部不朽之作:《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诺桑觉寺》《爱玛》和《劝导》。这六部作品中,简·奥斯丁的小说都以描写年轻女性恋爱和婚姻为主线,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年轻女主角,这些光彩照人的年轻女主角数百年来一直被读者津津乐道,并且成为学界的主要研究和评论对象。既然被评论界公认为塑造人物的行家里手,简·奥斯丁小说的精彩之处必然离不开配角的增光添彩。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陪衬在这些年轻的女主人公周围的一些中老年妇女配角同样灵动逼真、不可替代,描写到位且真实再现了当时英国女性在人到中年、老年时期的生活状态,这些女配角或愚蠢、或饶舌八卦,深具角色魅力,她们在承担帮助主角推进和成长的任务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自己的鲜明个性,成功为小说的艺术性增色添彩。人格健全且理智的配角往往承载了作者的理想型人格,虽然是正面形象却难以出彩,往往显得无聊、无趣,难具备戏剧冲突性,反而没有张力。因此,简·奥斯丁作品中的那些有趣的配角便多出现在这些或多或少有性格缺陷的中老年妇女之中。
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蠢笨主妇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仍是父权社会,在那个时代,男性以绝对权威成为了社会各个领域的主导者,男女之间的不平等问题非常突出。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被认为不能独立思考,只有娴淑、听话和逆来顺受的女性才被推崇,而择个好夫婿,有个稳定的婚姻保障才算得上是被人艳羡的女人。理查森曾经说过“为了改善人类的社会组织,男人既要作立法者,天赋的理智就要多一些,我们必须把这作为考虑问题的总的基础”。[1]所以简·奥斯丁笔下出现的大多数家庭主妇都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她们习惯于家庭琐事,不关心周遭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显得无知而蠢笨。
(一)《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太太
班纳特太太是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母亲,在小说《傲慢与偏见》的第一章,简·奥斯丁就对班纳特太太的人品和性格给出了简短而精妙判断:
“太太的脑子是很容易加以分析的。她是个智力贫乏、不学无术、喜怒无常的女人,只要碰到不称心的事情,她就会问候她的老朋友‘衰弱的神经’。她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她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听新闻。”[2]
这样的描述显然离我们内心理想型的母亲形象相去甚远,既然智力缺乏,是不可能指望这位主妇有什么独立思考能力的,她成天琢磨怎么给女儿找个乘龙快婿,既没有头脑更没有才能,最乐于打探小道消息并散播出去,且经常无病呻吟,对于子女的教育自然也谈不上正确的引导。这位蠢笨的主妇对于女主人公伊丽莎白的成长毫无益处,但于读者而言,却是位有趣的人物,为小说的喜剧效果增色不少。因为班纳特太太愚蠢而不自知却又是个活跃的人物,所以但凡她出现的场景都充满了喜剧色彩。她在社交场合总是很活跃,滔滔不绝,她庸俗且不得体的话语时常让有理智的几个女儿感到尴尬与难堪。班纳特太太和丈夫在兴趣和性格上毫无共同之处,班纳特先生年轻时因一时贪恋其美貌而草率地与其结为夫妻,婚后便发现了妻子糟糕的智力和庸俗的内在,班纳特先生对其失望却也只是选择了容忍,他已然不指望和妻子心灵相通,只是把她当作日常生活中讥诮取乐的对象罢了。就像简·奥斯丁所描述的:班纳特太太的“神经质”和“笨头笨脑”倒成了她丈夫的幸运,“不然他就无法享受那异乎寻常的家庭乐趣了”[2]。然而如此糟糕的夫妻关系班纳特太太却依然不明就里,二三十年的相处经验,竟然还是捉摸不透丈夫的性格,丈夫的嘲讽、揶揄和奚落,也不会让她感觉有可悲之处,她只认为是丈夫性情古怪,根本不去、当然也不具备智商去改善夫妻关系。
作为家庭主妇的班纳特太太的首要大事就是帮女儿们嫁个好人家,五个女儿都还待字闺中,形势严峻。当班纳特太太得知临近的内瑟菲尔德庄园是被一位有钱的单身汉查尔斯·宾利租去之后,她立刻意识到她五个女儿中的一个女儿将很有可能变成这位富有的单身汉的太太,她为此而兴奋,觉得这是女儿们的福分。显然只要“富有”即可满足班纳特太太“良婿”的标准,“她只认得钱和钱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根本不知道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感情上或心智上)也需要照顾”[3]。所以她不能体谅为什么二女儿伊丽莎白拒绝了拥有财产的柯林斯的求婚,伊丽莎白美丽、聪慧,且非常有见识,她不愿意因为财产而答应“蠢材”柯林斯的求婚,她正面的道德观从来不因母亲而改变。
由于班纳特太太的智力缺乏,她对女儿疏于管教,尤其是小女儿莉迪亚,生性冲动、放浪形骸、不知检点,当莉迪亚去驻梅里顿的民兵团和青年军官厮混时,班纳特太太非但对莉迪亚的轻狂没有制止,反而觉得女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她的共鸣,让她想起来自己的少女情怀。母亲作为子女成长的监督者和教育者,理应对子女的冒失和轻率加以惩戒和引导,以防引起更加严重的后果。果不其然,班纳特太太的愚蠢和纵容,致使莉迪亚更加胆大妄为,竟和军官威克姆私奔,给全家带来奇耻大辱。即便如此,班纳特太太仍然不觉得自己失职,她怨天尤人地把周遭所有的人都责怪了一遍,甚至认为根本原因是“应该搬家”,她从来看不到事情的最根本原因,总是在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边缘处找原因。因为从来不会独立思考,所以班纳特太太只要看到好结果就满意了,哪怕过程糟糕透顶,她不去思考为什么有了她满意的结果,也不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经过达西先生的努力和付出,最终促使莉迪亚和威克姆正式结婚,使其家庭免于蒙羞。即便如此,这终究不是一门光彩的婚事,可班纳特太太完全不在乎,她没有为小女儿的行为不端有所汗颜,反而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乐在其中,竟还想着怎么为莉迪亚准备嫁妆,甚至向左右邻舍炫耀,告诉大家小女儿的婚讯,着实是愚蠢又好笑。
(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伯特伦夫人
伯特伦夫人是小说女主人公范妮的二姨妈,因为嫁得好,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简·奥斯丁是这样描述这位夫人的:
“对于两个女儿的教育,伯特伦夫人更是不闻不问。她没有工夫关心这些事情。她整天穿得整整齐齐地坐在沙发上,做些冗长的针线活,既没用处又不漂亮,对孩子还没有对哈巴狗关心,只要不给她带来不便,她就由着她们,大事听托马斯爵士的,小事听她姐姐的。”[4]
显然,这位夫人既不聪明也不用心,对子女也没有起到教育和引导。她性格温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丈夫管教孩子,且家里又有家庭教师和保姆,慵懒是她最大的特点,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该操心、该尽责的事情也从来不用心。伯特伦夫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其余的事情似乎都和她无关,她生育了子女却从来没管教过他们,完全交给自己的姐姐去管,她“甚至都不愿牺牲一点个人利益,感受一下做母亲的喜悦”[4]。这位脑子空荡荡的伯特伦夫人温柔顺从、毫无主见,凡事都要请教自己的丈夫,完全不会思考,甚至连自己闲暇时光应该和谁消磨都要丈夫来确定人选。身为有名望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女主人,既不教养儿女,也不打理家事,她就像长在了沙发上,不是打瞌睡,就是做一些丝毫用不到的、莫名其妙的针线活。
女主人公范妮因家境贫寒且子女太多的缘故,被生母送到二姨妈家抚养。多年来,善良的范妮一直悉心陪伴和照料着伯特伦夫人,而伯特伦夫人却从没关心过可怜的范妮,她从来没有思考过,可怜弱小的范妮寄人篱下,多么艰难,多么需要呵护和关心。伯特伦夫人占用了范妮所有的私人时间,似乎范妮是她的私人物品,看起来范妮就像是个仆人。伯特伦夫人自己忍受不了太阳,却让范妮在太阳底下剪玫瑰。范妮第一次正式参加舞会时,伯特伦夫人也是自己先穿戴打扮好才想起让女仆去给范妮帮忙,她习惯了范妮陪伴其左右,她把这个外甥女当成陪伴自己解闷的工具,不认为她也有自己的需求和感情。当范妮想回家去看望自己的家人时,她竟认为:“范妮离开父母都那么久了,实在没必要去看他们,而自己却那么需要她”[4],其冷漠自私可见一斑。当得知有钱人青睐于范妮时,她觉得自己脸上有光彩,觉得“每一位年轻女子都应该接受这样无可指摘的对象来求婚”。
伯特伦夫人因为毫无头脑,便无力去分辨子女的行为是否不端。大儿子在家排演一些有伤风化的戏剧时,她没有任何不赞成。伯特伦夫人对子女一味地放纵,自己的两个女儿成年后去参加社交她也不陪同。两个女儿因为缺少管教,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道德观念淡薄,难以抵制外界诱惑:大女儿水性杨花,私奔遭到遗弃;二女儿也是放荡不羁,秉性恶劣。当丈夫托马斯爵士要出门远行时,作为妻子,伯特伦夫人没有担心丈夫的安危,却更担心自己应付不了家中的事物。她只顾享受丈夫带来的安逸生活,却对丈夫没有妻子应尽的关心。
伯特伦夫人被读者认为是“文学作品中刻画得最精彩的傻瓜之一”,简·奥斯丁以她过人的描写手法,成功塑造了这么一位愚蠢、慵懒的有趣妇人。
二、饶舌的单身中老年妇女
简·奥斯丁笔下还存在着一群年轻时在婚姻市场失败的单身女性,她们孤老贫困,却也能在窘困中找些乐趣,成为饶舌的主要群体。
(一)《爱玛》中的贝茨小姐
贝茨小姐是简·奥斯丁笔下老处女的代表人物,贝茨小姐是海伯里这个村子已过世的牧师的女儿,出生时家境尚可,后来败落,在适婚的年龄因没能及时为自己谋得一个好郎君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导致其只能与年迈的老母亲寄居在一个生意人的小房子里,收入微薄,勉强度日,时常受到爱玛父女和南特利先生的接济。
贝茨夫人是出了名的饶舌,总是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在韦斯顿先生举办的舞会上,简·奥斯丁对贝茨小姐的饶舌有一段精妙的描述,只听见:
“你们真是太好了!根本没有雨。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倒不在乎。鞋子厚得很。简说——哇!”…… “哇!真是灯火辉煌啊!太好啦!我敢说,设计得好棒。应有尽有,真想不到。灯光这么亮。简,简,你看——你以前看见过吗?哦!韦斯顿先生,你一定是搞到了阿拉丁的神灯……一切都这么棒!”[5]
这一段饶舌根本没有人有能力去打断,连想出风头的埃尔顿太太都没机会张嘴了,所有人的话都被贝茨小姐夸张的絮叨淹没了。贝茨小姐的厉害之处在于,她的饶舌根本不需要别人去回应,完全是她自己的独角戏,简·奥斯丁用了两页的篇幅来描述贝茨夫人的絮叨,生动展现了这个滑稽却无害的单身老妇女形象。
贝茨小姐虽然无趣且不讨人喜欢,可是她是个善良且宽容的人。爱玛在勃克次山出游中因为嫌弃贝茨夫人的饶舌而出言讥讽,被南特利先生事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爱玛懊悔至极,便登门拜访贝茨小姐,贝茨小姐并不因当众受辱而记恨爱玛,她真诚地谅解了爱玛。
(二)《理智与情感》中的斯蒂尔小姐
斯蒂尔小姐是年近三十还待字闺中的老处女,严格意义上来讲,在现如今的社会,斯蒂尔小姐的年龄不算老,可是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她却已经沦为他人的笑柄。所以,斯蒂尔小姐总乐于去寻找一个比她更不幸的人来进行嘲讽,才可以让自己稍加慰藉。因此斯蒂尔小姐乐于饶舌八卦,四处打探消息,甚至窥人隐私。因为生活困顿,总是说些肉麻话来夸赞别人,斯蒂尔小姐甚至滑稽到以别人的取笑来安慰自己,别人拿戴维斯博士开她玩笑,斯蒂尔小姐的反应是:
装出认真的样子,求丹宁斯太太替她辟谣,而丹宁斯太太完全理解她的意图。当时向她保证说,她当然不会辟谣。斯蒂尔小姐听了心里简直乐开了花。[6]
简·奥斯丁仅用寥寥数语,斯蒂尔小姐的可怜且可悲的小丑形象便跃然纸上。
三、结语
简·奥斯丁妙笔生花,其作品给了所有女性一个舞台,她们各自展示自己的文学艺术魅力,其中也包括这些有趣的配角,这些形态各异的中老年妇女也是简·奥斯丁艺术长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以及社会的本质。简·奥斯丁真实再现了这些活生生的实例,更无情地鞭挞当时社会的黑暗面,同时使其作品更具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