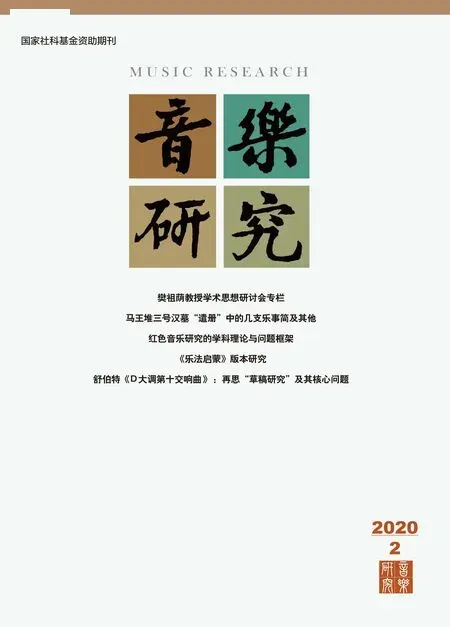红色音乐研究的学科理论与问题框架
——音乐学术研究的反思与探讨(四)
文◎李诗原
红色音乐乃20 世纪中国音乐文化的半壁江山。但在音乐学术得以极大发展的近30 年中,红色音乐却因“告别革命”①“告别革命”是20 世纪90 年代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种学术思潮:既有基于“革命叙事”的史学范式(paradigm)已式微,故需寻求新的范式。以笔者之观察,此论在中国出现,与土耳其裔美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30—2017)《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文相关。德里克在文中说:“库恩的范式概念,概括地说,乃是指导一个科学家共同体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解释模式。在某一时期总有一种主导范式;虽然它可能会受到质疑,但只要它能成功地解释它所旨在解释的现象,其主导地位就不会动摇。随着与范式解释相冲突的证据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无法将该范式视为理所当然,并转而着手寻求能更好地解释论据的新范式,这时范式危机便爆发了。”参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 年“春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版,第138 页。正是在对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1922—1996)“范式”理论的理解和反思中,德里克阐述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和“革命之后的史学”。和“重写音乐史”②“重写音乐史”则是20 世纪90 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学术思潮,其源头大概可追溯至1988年戴鹏海《两点质疑——致成于乐先生》(《人民音乐》1988 年第11 期)。但在笔者看来,“重写音乐史”的呼声与“重写文学史”相关(参见陈聆群《从“重写文学史”到“重写音乐史”》,《黄钟》2002 年第 2 期),而与上述“告别革命”和“革命之后的史学”关系并不大,其动因更主要来自史料的新发现和对既有史料的新认识。但也不难发现,在持续30年的“重写音乐史”呼声中,也不乏“告别革命”的诉求,且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告别革命”尚有某些间接的关联。,而被学术界“边缘化”了。“告别革命”,不过是少数音乐史学家的一厢情愿,在笔者看来,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在新的历史语境和学术视野下,如何建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的“革命叙事”,并使红色音乐研究真正成为一种综合性、交叉性的“文化研究”,进而在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历史视野下,使红色音乐获得新的历史坐标和价值评估?还有,如何使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学在“告别革命”与“重拾革命”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并获得新的学术起点和价值认同?
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确保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得以持续和深入的理论前提。当然,开展红色音乐文化研究并将其作为“重写音乐史”的一个契机,不应只是“弘扬革命文化传统、传递红色文化基因”的驱动,而更应成为音乐史学界自我反思和寻找突破的一种自觉意识。好在“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版》2016 年5 月19 日,第2 版。的原则,可作为开展百年红色音乐文化研究的根本遵循。
一、反思:问题、症结、既有研究及其缺失
纵观百年中国音乐,恐怕谁也不会否认曾有这样一种文化类型:它力图阐述和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诠释和维护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塑造和构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身份,展现和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集聚力量……这个文化类型就是红色音乐。如果将百年中国音乐分为“学院派音乐·专业音乐”“军旅音乐·革命音乐”“流行音乐·大众音乐”“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四个文化类型,那么红色音乐即“军旅音乐·革命音乐”的主体,并成为红色中国重要的“文化标识”(cultural identity)之一。
坦率地说,用“红色音乐”或“革命音乐”这类词汇,在今天似乎显得有点“突兀”,但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词来替代,故只能说是姑且用之。但好在这些词不是虚构的,而是饱有事实支持,且足以证明这个音乐文化类型的客观存在,并昭示出其规模、效应。这里仅摆出两个事实。
(1)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后累计不少于一亿民众,在接受红色音乐“救亡”教育的同时,也得到了音乐的“启蒙”和“娱乐”。④仅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建革命根据地及隶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25 个省级苏维埃政权为例。作为由中共建立的“割据区”,盛期曾拥有近3000万人口,即便是人口稀薄的陕甘宁苏区,也有90 万人口。故累计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时期,革命音乐受众达一万万人(只会多而不会少,且不含国统区、沦陷区民众),占四万万同胞的四分之一。(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数以百计后来在地方工作的杰出音乐家,⑤例如,著名音乐家贺绿汀(1903—1999)即如此,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广州起义,后到海陆丰地区参加革命斗争,作有《暴动歌》(1927);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作有《游击队歌》(1937),后在新四军盐城总部鲁艺分院、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执教;解放战争时期曾在解放区工作。都曾在人民军队或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解放区中,完成了其最早的音乐启蒙,或完成后来作为一个专业音乐家的准备,或积累了其事业的基础。
这两个事实就足以证实红色音乐的规模和效应,而无须说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海量”的革命歌谣,和平建设时期那些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无须说革命歌曲、军旅歌曲在整个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体量及其比重。总之,它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音乐文化类型,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音乐文化类型,故而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音乐文化类型。
然而,在近30 年关于“重写音乐史”的讨论中,红色音乐文化却被“边缘化”了,因为从一些查缺补漏的呼吁看,红色音乐(尤其是20 世纪上半叶的革命音乐)尚不属于补充之列,倒是把那些曾被“边缘化”的音乐家(如江文也、黎锦晖、刘雪庵、陈歌辛、吴伯超、陈洪和王洛宾等)和一些“音乐史的边角”⑥如梁茂春《音乐史的边角——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的一个视角》一著中提及的音乐事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 年版。给予重视。这无疑是必要的,无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历史人物重新定位,还是将一些从“边角”视角发现的新史料写进音乐史,都应是“重写音乐史”的重要举措。但百年红色音乐文化也应得到充分的补充,因为百年红色音乐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人物和事象,不仅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而且对整个中国音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近30 年“重新音乐史”的声浪中,补充红色音乐内容的提议却难以得见。相反,在个别史学家看来,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就应是一部“学院派”音乐史,或是一部描述“学院派”音乐与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的音乐史,而不应杂以“革命派”(救亡派)音乐,更不应有“学院派”与“革命派”的二元对立,甚至将载有红色音乐内容且按中国革命史编撰的音乐史斥为“中共音乐史”⑦“中共音乐史”这个说法,来自中国香港学者刘靖之博士的《中国新音乐史论》一著,台湾出版社(台北)1998 年版。。在“重写音乐史”的语境中,对红色音乐及相关现象无不表露出一种鄙夷的口气。
“重写音乐史”无疑是必须的。清除特定历史时期某些思潮(如“庸俗历史观”和“庸俗社会学”)的负面影响有必要,但“重写”并非剔除红色音乐,而恰恰要正视红色音乐的客观存在和庞大体量,进而加大红色音乐的分量,并在一种新的历史语境中,使之与专业音乐、传统音乐、大众音乐一起,构成一部多元、多线条、多视角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音乐史不能脱离大历史,音乐也不可能没有特定的历史语境。
再看红色音乐研究。红色音乐研究,可追溯至20 世纪30 年代中前期,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等报刊及《革命歌谣集》的出版物,对中央苏区革命歌谣运动的报道和评论,至今已有近90 年的历史积淀。这近90 年的学术史,可分为四个时期。
1. 新民主主义时期(1949 年以前)。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20 世纪30 年代中前期关于红军及其革命根据地(苏区)革命歌谣运动,“左翼”音乐运动的报道和评述;全面抗战后对“左翼”音乐家聂耳的评价,⑧例如冼星海《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新华日报》(武汉)1938 年7 月17 日。以及对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及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包括延安音乐)的评述和探讨,⑨例如冼星海《边区的音乐运动——一月八日在“文协”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冼星海全集》(第一卷),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85—94 页。对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音乐和解放区音乐的观测和评论。这些都见诸苏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音乐报刊及国统区部分进步报刊。关于歌剧《白毛女》的评论是此时期的重要内容。⑩参见1945 年7 月17 日至8 月2 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首先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音乐文献的整理,先后出版了多本革命老区的革命歌谣集,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抗日战争歌曲选集》《解放战争时期歌曲选 集》⑪解放军歌曲选集编辑部编《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1957 年版;解放军歌曲编辑部编《解放战争时期歌曲选集》,音乐出版社1959 年版。。其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音乐和音乐家研究得以起步,⑫1950 年《人民音乐》(一卷2 期)上刊载的《冼星海年谱纪略》和《冼星海作品简目》是为开端;次年的孙慎《聂耳年谱初稿》(《人民音乐》1951 年第5 期)当属聂耳研究的开始。20 世纪50 年代末启动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编写,也极大地推动了红色音乐研究,并逐渐使“革命音乐”成为一个与“学院派音乐”相对应的音乐史学范畴。20 世纪70 年代中前期,《战地新歌》也发掘、改编了一批革命历史歌曲。
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9—2012)。首先是聂耳、冼星海的研究,至1985 年(聂耳逝世50 周年,冼星海逝世40 周年)达到高潮,出版《论聂冼》⑬中国聂耳、冼星海学会编《论聂冼》(内部印刷),1985 年。,并启动《聂耳全集》《冼星海全集》的编辑出版工程。其次是伴随着红色文化史料整理工作的展开,一大批红色音乐史料也得以辑录。主要有20 世纪80 年代《延安文艺丛书》⑭《延安文艺丛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4—1988 年陆续出版。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⑮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下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共4 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共2 册),解放军出版社1986、1987、1988 年版。的出版;20 世纪90 年代,全国各省市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整理出版了一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文化史料,⑯如《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印刷),1995 年;《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印刷),1996 年;《闽浙赣湘鄂苏区革命文化纪事·人物录》(内部印刷),1997 年;《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右江战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红三军在沿河》(内部印刷),1987 年;《湘鄂西湖南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内部印刷),1992 年;《湘鄂川黔革命文化史料汇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 年版;《鄂豫皖苏区革命文化史略》(内部印刷),1996 年;《鄂豫皖苏区革命文化史略(初稿)》(内部资料),1995 年;《皖西风云录——皖西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选编》(内部印刷),1994 年;《鄂豫皖红军歌曲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6 年版;《壮歌行》(内部印 刷),1992 年;《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中国工农红军在云南革命文化史料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年版;《赣粵边三年游击战争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印刷),1998 年版等。其中也不乏革命音乐史料。再者,苏区音乐、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解放区音乐、早期工农革命音乐、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和东北抗联音乐,也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热点,并推出了大批学术成果⑰如汪毓和《聂耳评传》,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年版;《聂耳音乐作品》,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陈志昂《抗战音乐史》,黄河出版社2005 年版;胡建军、邓伟民、傅利民《江西苏区音乐文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年版;吕品、张雪艳《延安音乐史》,太白出版社2012 年版等。,还出现了一批以“苏区音乐”“红色歌谣”“抗日救亡歌曲”“秧歌剧”“新歌剧”为关键词的博士、硕士论文和一般学术论文。⑱其中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孟远《歌剧〈白毛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5 年),桑俊《红安革命歌谣研究》(武汉大学2008 年),陈宗花《1937—1949 年:解放区音乐民族化思潮研究》(东南大学2009 年),谷鹏 《〈白毛女〉的传播研究》(苏州大学2009 年),王冬《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秧歌剧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10 年),王丽虹《延安鲁艺音乐教育中的政治因素》(福建师范大学2010 年),陈杰《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河南大学2019 年),等等。与此同时,解放军音乐研究得以启动,并推出一批研究成果⑲李双江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经典文献库》(共6 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2011 年版;李诗原编著《军歌史话》,解放军出版社2009 年版。。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以来)。延安音乐、抗战音乐、晋察冀音乐、东北革命音乐、抗联音乐和志愿军音乐研究都有重要成果。“中国梦·强军梦”“一带一路”“抒情新时代”主题音乐创作及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受到关注。
纵观近90 年的红色音乐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尚有许多不足。
第一,史料失信。首先是原始资料缺失,因为在既有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中,一些早期革命歌曲的词曲都被进行了“修复式”整理,故掩盖了其基于民歌式口头传播的原貌。其次是作为重要史料的口述史(革命回忆录)存在不准确、不客观的描述,以致部分“事实”存在讹误和偏差。再就是一些地方纪念馆和文史工作者,为夸大革命文艺在本地区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对部分音乐史料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诠释。伴随着红色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这一现象越发严重。
第二,评价失衡。在“弘扬革命文化传统、传递红色文化基因”的语境中,红色音乐的艺术水平、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被不切实际地抬高。尤其高估了革命战争年代音乐作品的艺术水平,并力图以艺术成就(艺术性)作为其价值判断依据。但这种艺术上的高估,不仅苍白无力,还会影响到对红色音乐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乃至历史作用的认识和把握。与之相反,在“告别革命”和某些“重写音乐史”的语境中,其艺术水平、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则被贬抑,甚至对那些“红色经典”的艺术价值也视而不见,并将其艺术经验一概视为“公式化”艺术表达而放逐。
第三,研究失范。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固化,非但不能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红色音乐视为历史“上下文”中的一个“互文本”,进而将其还原到中国革命史和军事斗争语境中,进行一种综合式、交叉式的“话语分析”⑳这里的“话语分析”,即“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的全面、综合和交叉性研究”,参见腾守尧《“话语”与“文本”》,载《美学与艺术研究》(第一集),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 年版,第46 页。这种“话语分析”是相对于“文本分析”而言,即“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且仅限于其思想主题提炼和音乐形态分析,未能展露出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无疑,上述“失信”“失衡”“失范”的症结,就在于学科理论和问题框架的缺失。
至于说自有“告别革命”和“重写音乐史”呼声的近30 年,红色音乐研究虽不乏体量,但相比之下也显得捉襟见肘。像既有研究一样,也只有聂耳和冼星海的音乐、抗日救亡歌咏歌曲、延安秧歌剧、歌剧《白毛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受到学术界关注,而大革命时期的工农革命音乐、北伐军音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及其根据地音乐、我党抗日武装及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人民解放军及解放区音乐,还有新中国的解放军音乐,各历史时期的“主旋律”音乐,都未能完全进入学术视野。其中一些研究似乎成为革命老区和军队学术机构、党史爱好者的专利。还应看到的是,近90 年的红色音乐研究,大多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驱动,而未成为一种学术的自觉意识,进而受到正常、平等的关注。尤其在中国音乐学术领域极大扩展的最近30 年间,许多学术资源被充分挖掘,甚至是被过度开采。一座寺庙或道观的音乐,一个乐种或一个剧种,尚能让那么多博士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们为之倾注毕生精力,但如此大体量和比重的红色音乐,却未能充分赢得学术界的垂青。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红色音乐研究成果的劣势也显而易见,其成果数量总体偏少,且与红色音乐的体量不相匹配,其学术水平总体偏低,研究方法尚显陈旧。总之,在近30 年中国音乐学术中,红色音乐研究的份额并不大,即使在被个别音乐史学家指为“中共音乐史”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中,红色音乐的分量也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21]汪毓和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三次修订版),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年版。全书372 页,关于红色音乐的内容占111 页,不足三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专业性音乐学术活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表现出对红色音乐的漠视:轻则避而远之,重则嗤之以鼻;一些研究红色音乐的学者也多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甚至还担心被指为“投机”。综上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红色音乐在近30 年的中国音乐学术界被“边缘化”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边缘化”现象?笔者认为,这无疑与前面所说的“告别革命”和“重写音乐史”中的某些观点相关。但与既有的某些音乐史学观念和音乐价值观也不无关系,比如,音乐史本来就是专业音乐史的史学观念,再比如,红色音乐就是一个简单的歌曲、无艺术性可言的音乐价值观。红色音乐是百年中国音乐发展进程中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类型,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如何将红色音乐拉回到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的视野?笔者认为,在坚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的原则下,须秉持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深入探讨红色音乐文化研究的学科理论和问题框架。这无疑是红色音乐研究的重要前提。
二、军事政治学视野下的学科理论与方法
何以构建红色音乐研究的学科理论?这就是将红色音乐视为一种战时文化和军事文化形式,在“军事政治学”的视野下,使其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如文化传播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形态学等)的理论和方法。这里的“军事政治学”,姑且理解为作战双方为取得军事斗争胜利,对内、对敌、对外开展政治工作(政治斗争)的理论、方法和价值体系。“军事政治学”旨在为解决军事斗争中的敌我二元对立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方案,并且秉持“一切为打赢”的实用理性及其价值取向。所谓“战时文化”,既泛指战争状态下的文化,又特指旨在服务战争并因战争而显露出某些实用理性原则(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重内容 轻形式等)的文化。因此,作为审美文化的战时文化(如音乐),或显露出战争对它的影响和制约,或旨在表现战争并为战争服务。所谓“军事文化”,即与军事斗争直接相关的文化,或服务于军事斗争的文化,或在军队中生成的文化,受军事斗争的影响和制约。
红色音乐,作为旨在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音乐文化,作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音乐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战时文化和军事文化,或是一种具有战时文化和军事文化特征的音乐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音乐,当属战时文化和军事文化。和平年代的红色音乐(解放军音乐,革命历史题材音乐,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音乐,新时代“中国梦”“强军梦”“一带一路”“抒情新时代”主题音乐等),仍属战时文化和军事文化形式,或战时文化、军事文化的延伸和发展。解放军音乐服务于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其军事文化属性和战时文化特征毋庸置疑。革命历史题材音乐,或直接表现军事斗争,或以军事斗争为背景,作为军事文化形式亦不容争辩。至于说貌似与战争或军事斗争不相关的“主旋律”音乐和其他政治主题音乐,无疑也是为一场场“战争”和“斗争”服务的(如当下《挺住,武汉》《天使的身影》等许多传递“正能量”的歌曲,就是为“战疫情”的“人民战争”服务的),其中蕴含着治国理政价值取向的“战争文化心理”也显而易见,因此,“主旋律”音乐和其他政治主题音乐,依然被打上了战时文化或军事文化的烙印。一言蔽之,红色音乐本质上属战时文化和军事文化,故在军事政治学视野下对其开展一种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究都有可能。其可能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红色音乐置于军事斗争语境,探讨其战时文化特征和军事文化属性,评估战争态势、作战样式对音乐体裁形式、语言风格及思想主题、价值取向的影响和制约,描述战时音乐在军事斗争语境中的反应和变化,并基于“己方”“敌方”“外围”分野的作战思维及敌我力量划分和角逐,认识和把握音乐的助战功能、治国理政功能及其实用理性,并在“一切为打赢”的实用理性精神驱使下完成其文化价值 判断。
第二,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红色音乐还原到革命历史和军事斗争语境中进行综合式、交叉式的“文化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其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的嬗变,建立中国革命“大历史”和红色音乐“小历史”的关系,重新审视“告别革命”和“重拾革命”并建构二者间的新型关系。
第三,在比较音乐学视野下,将红色音乐视为一种在特定地域形成的音乐文化,既将其置于特定战区(如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又将其置于特定战区所对应的文化色彩区,进而建立军事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关系,探寻其战区风格、地域风格及二者间的“重合”和“疏离”,并进行不同战区乃至不同战斗序列音乐的比较。与此同时,探寻实用理性对红色音乐体裁形式、语言风格的规定性。
第四,在音乐社会学和传播学语境中,解释红色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对民众的影响。探讨军民融合的社会组织结构与红色音乐发展状况的关系;认识红色音乐在开展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中的不可替代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探寻红色音乐的独特传播方式,尤其是军事斗争形式,如武装割据、战略转移、挺进敌后、防御作战、军事统战、战略决战等,这些对音乐传播的影响及音乐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探讨战争状态下音乐在传播中的变异、出入和 讹误。
应当承认,上述这些可能性,主要是就革命战争年代红色音乐的研究而言的。但之于和平建设年代的红色音乐研究,其思维和部分方法也是有效的。尤其是认识和把握红色音乐及其传播,所反映出的对己方、对敌方、对外围的指向性、针对性及“一切为打赢”的实用理性,对于和平建设时期红色音乐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军事政治学统摄下的理论构建,关键在于回到特定的军事斗争语境,并在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评估中体现军事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和价值取向。
第一,从军事文化“姓军为战”的本质属性出发,在敌我二元对立中,探讨音乐之于己方、敌方、外围的效用。对己方而言,利用音乐鼓舞军民士气,开展社会动员,诠释军令政令,协调军民关系、维护军民团结,以巩固和提高己方战斗力。对敌方而言,利用音乐争取舆论、捍卫法理,发动政治攻势、攻心而策反、瓦解敌军,对敌后方进行情绪影响和心理干预,以消解和降低敌战斗力及潜在战斗力。 对外围而言,利用音乐协调外部关系,赢得外界支持,以增强己方战斗力,阻滞敌战斗力的增加,团结友军盟军建立统一战线,旨在为军事斗争提供有利战场环境和强大战力支援。显然,认识这种助战功能及派生出来的助政功能,无疑是评价红色音乐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基点。和平建设年代的红色音乐,依然是在敌我的二元对立中发挥其效用的,同样也呈现出对己方、对敌方、对外围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其效用亦为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评估的基点。
第二,从战时文化或军事文化与生俱来的实用理性着眼,探讨红色音乐中那种“一切为打赢”的“军事政治策略”,以及诠释和维护中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追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塑造和建构中共及所领导的军队、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身份的“军事文化谋略”。更为重要的是,应使不假音乐外在形式美感与内在结构逻辑,评价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成为一种可能。
第三,从战时文化或军事文化与军事斗争的关系出发,探讨作战样式、战争态势对红色音乐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探讨不同战区(或不同战斗序列)音乐因战略方针、作战原则、作战对象、作战地区和宣传策略的不同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比如,红军音乐的产生及传播,就与红军的“武装割据”和“战略转移”两种基本作战样式相关。
总之,军事政治学统摄下的红色音乐研究,即将音乐置于军事斗争语境,在敌我二元对立思维和“一切为打赢”实用理性精神的驱使下,探讨其战时文化特征和军事文化属性,并评估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在既有红色音乐研究中,许多与事实相悖的结论,都因为脱离军事斗争语境而得出。例如,将红军音乐与根据地音乐分为两个领域的研究,就忽视了土地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高度“军民融合”的事实,而未能建立“红色及其革命根据地”或“根据地及其红军”的整体思维。
三、问题框架及研究选项的设定
红色音乐研究的问题框架,即所谓基本问题和选项。这主要包括:红色音乐作为一个文化类型的基本特征,与其他音乐文化类型的关联和区别;红色音乐的审美原则;红色音乐创作及红色音乐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国家文化身份和文化形象构建中扮演的角色。
其问题框架具体在于四个方面。
第一,红色音乐与其他类型音乐文化的关系问题。任何文化都不是单一的文化类型,文化与文化之间也只有“边缘”而无“边界”。红色音乐与百年中国的其他音乐文化类型关系密切。尽管这种关系尚未销蚀它与其他文化类型的“边界”,但红色音乐在文化“边缘”所形成的“对话”也不可小视。这首先是与专业音乐之间的对话。自全面抗战始,大批专业音乐家进入革命阵营,故红色音乐逐渐与专业音乐相关联,并在体裁形式、语言风格上与专业音乐比肩。和平年代的红色音乐(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音乐)更显现出专业音乐的维度。与传统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不仅是早期革命音乐(如红军及其根据地音乐)对民间音乐的直接利用,还在于红色音乐为满足民众审美情趣而选择了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音乐。红色音乐与大众音乐的关联也毋庸置疑。中央苏区一首《可怜的白军》(仿“可怜秋香调”)就体现出这种关联;“左翼”音乐嫁接于电影也是这种关联的见证;改革开放时期,流行音乐则再度成为发展红色音乐的文化资源。
第二,红色音乐的审美原则问题。红色音乐的审美原则无疑是所谓“三化”,其内在逻辑则是由“革命化”而“群众化”,再由“群众化”而“民族化”。这种内在逻辑早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时期就已显露出来。当时的红色歌谣,正因为选择了民间歌谣而为红军及根据地民众所喜闻乐见,进而在取悦军民的同时,也完成了鼓舞军心士气和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最终满足了革命的要求,完成了其政治使命。在远离战争硝烟的红色音乐中,虽然民族化和大众化也被时代性和专业性所“冲淡”,但作为“红色”的“革命化”仍是其坚实的底色。
第三,红色音乐的艺术哲学问题。这里“艺术哲学”即红色音乐(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即“红色经典”)创演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套路”。这首先是曾一度登峰造极后又被批判的“主题先行”和“三突出”;还有个性遮蔽下的“集体抒情”和淡化性别特征,旨在回避爱情的“同志关系”与“革命夫妻”及“脸谱化”表达模式下的敌我二元对立,表现革命胜利的“大团圆”结局。此外,还有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旨在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党指挥枪等)的主题,作为正剧的“正大气象”和作为革命英雄主义的“悲剧”和“崇高”,以及“解放全人类”和“最后解放自己”的远大理想和牺牲精神。上述这些无疑都属于红色音乐的“艺术哲学”。
第四,红色音乐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形象问题。红色音乐的文化功能即显性的助战、助政功能——充当催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形成“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弘扬“主旋律”的重要形式,传递“正能量”的重要载体;其隐性的功能即作为一个历史文本,诠释和维护了革命、建设、改革、追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而红色音乐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所建立的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
问题框架的设定和基本问题或选项的逐渐增元和不断调整,无疑也是有效避免红色音乐研究“泛化”“僵化”和“平面化”的方略,而对于上述红色音乐审美原则、艺术哲学和文化功能的认识和把握及价值判断,也是红色音乐研究的重要选项。
四、探讨: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
红色音乐的历史评价和文化价值,乃红色音乐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要确立一种音乐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首先就应认同这种音乐赖以存在的文化前提,认同这种音乐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确立革命音乐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就需确立“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革命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确立,不仅仅是一种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个阶级、某个政党既得利益的价值判断,还需要获得一种人文主义价值体系的支撑。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政治制度取代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暴力行动,从主观上是否真的具有特定历史条件下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从客观上是否真的改善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生存状态,进而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无疑是判断革命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和关键。这就意味着,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仅仅来自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 目标,还取决于这种人文关怀的最终实现。
这种人文关怀作为人文主义精神及其价值认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文化或文明的自然法则,就是人在顺应自然或与自然搏斗中,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不懈努力和终极价值追求。由此可见,这种自然法则,就来自人与生俱来的那种不断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优化意识。这种“优化”即“文化”;或者说“文化”即一种承载着优化意识的意识形态。[22]关于这一观点,参见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人总在不遗余力地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优化意识,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就此意义而言,革命像人类任何改善自身生存状态的行为一样,从理论上说,也应是一种在优化意识作用下推动社会发展和变革的行为,只不过它采取了暴力的方式,或“突变”的方式。很显然,那些推进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改善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从本质上说都体现出了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统一,进而就充分呈现出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旨在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相反,那些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有碍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革命,从本质上说则是一种不利于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行为,既没有体现出人文关怀,又缺乏其历史主义精神。
总之,如果革命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那么革命音乐就具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而既具有基于特定阶级和政党性质、宗旨、任务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又具有基于人文关怀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例如,《国际歌》作为一首革命歌曲,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既来自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先进性,又来自它为“全世界受苦的人”谋利益的人文关怀。这种判断的背后,是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认同机制。
如果说文化的存在方式即“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优化”,那么人文主义精神及其价值认同,就是文化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取向所在。一种文化(包括审美文化)是否具有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就要看这种文化是否具有一种旨在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意识。当然,作为一种人文主义视野中的价值认同机制,还必须受到历史主义的框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的维度,都不可能是一种超历史的存在,而人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故文化及其旨在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意识,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或结晶,也必须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一种文化而言,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确立,都需要“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认同机制。脱离历史语境,甚至完全无视历史制约的存在,孤立地探讨文化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是没有意义的,也是徒劳和无益的,必将陷入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反之,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究某种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而缺乏人文视野,也必然是一种封闭和狭隘的价值判断,最终也必将陷入一种庸俗历史学和庸俗的社会学。[23]参见陆贵山《文艺的人文精神和文艺的历史精神》,《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1 年第3 期。
确立革命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既需要人文视野,又需要历史框范。如果说一场革命被证明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变革,那么一切服务于革命的文化形式都具有基于革命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哪怕这种文化在形式上并不完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和此前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都呈现出这种文化价值观。这就意味着,革命音乐作为一种革命文化形式,既具有基于革命力量之先进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还体现出了革命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而生发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作为一种基于人文精神的意义和价值,无疑也是一种最为可靠、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体现出人文关怀的革命,作为一种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行动,作为一种暴力行为,必有流血牺牲,故必然要牺牲一些局部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但这种牺牲,对于革命者而言,就是革命的代价;对于革命的对象而言,则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替代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必然,或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亦为落后阶级和社会制度所应付出的代价。故那种对先进阶级的革命及革命战争的反思,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反思,其本身是一种脱离特定历史语境的反思,或者说是一种超阶级、超社会的历史反思。这种历史反思貌似充满人文关怀,但实质上恰恰放逐了一种更宏大、更长远的人文关怀。这种超历史、超社会的历史反思,无疑是评价革命文化(乃至一切文化)之意义和价值所应反思和摈弃的。脱离特定历史语境、放逐更深意义和更长远目标的人文关怀和战争伦理,难以构成否定革命文化或战争文化的理论前提。这即所谓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认同机制。
1921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为目标、旨在改善广大中国劳苦大众生存状态的社会变革。故这场革命是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更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这种合理性、合法性乃至人文关怀,无论是从主观上看,还是从客观上看,一开始就得以显现出来。它蕴含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土地革命纲领之中,因为打破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中国这个农业社会大多数人所追求的梦想,这就是其合理性、合法性及人文关怀所在。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才脱颖而出。但在革命之初,甚至在革命之中,这种合理性、合法性和人文关怀并不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以致出现了不革命的,甚至出现了反革命的。然而,经过一百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后,尤其在“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中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即将实现之时,这种革命的合理性、合法性和文人关怀,就被更清晰地体现出来了。例如,红军音乐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种从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土地革命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歌谣,无论是基于土地革命的,还是基于抗日救国的;也无论是一种具有不可替代助战功能的军事文化形式,还是一种诠释和维护土地革命及其军事斗争合法性、合理性和人文精神的革命文化,一种塑造和构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红军作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身份的革命文化,都体现出了基于“革命”的人文关怀,故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毋庸置疑。因为红军音乐作为一种服务于土地革命战争的音乐文化,正是体现出那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旨在不断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意识。这种优化意识正是其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所在。因此,这种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甚至也是可以脱离其艺术及其审美价值而独立存在的。这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形式或文艺形式,其意义和价值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承载了那种旨在改善人的生存状态的主观愿望,哪怕在客观上看这种愿望难以实现,而主要不在于其艺术的形式美感和结构逻辑。当然,一种具有艺术及其审美价值的文艺形式,可能更便于承载这种人文精神,或者说让受众更能感受和理解这种人文精神。
总之,这种人文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认同机制,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但却是一种更具终极意义的实用理性。这种具有超越性和终极性的实用理性,正是我们评价包括红军音乐在内的一切红色音乐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终极标准。这种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价值认同机制,也是“重写音乐史”的关键。
——评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