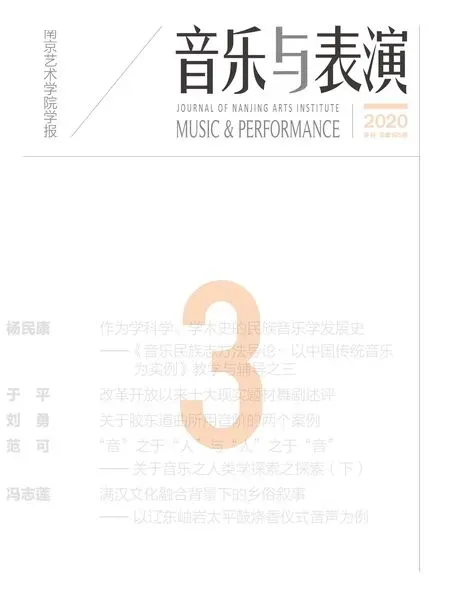纵横丝绸之路 通观东方音乐①
——重读《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兼论东方音乐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吕 畅(四川音乐学院,成都 610000)
谁曾想到,琵琶这样一件在中国流行千年不衰,于唐人诗词里便已司空见惯的乐器,在漫长的历史书写中连身世渊源都不曾被厘清。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1]65所谓“新发见”,既指新材料,也指新方法。当然,二者很难拆分,更多的时候是运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进入21世纪以后,一批从国外留学深造归来的音乐学者将许多中国音乐史中纠缠不清、似是而非的课题,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之中,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赵维平教授发表于《中国音乐学》2003年第4期上的《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一文,运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本史料、考古实物、传世古物的翔实解析,对琵琶从印度及西亚流入我国新疆,进而到达日本的流传之路进行实证性考察,一举廓清了音乐史学界长期以来模糊不清的阮咸(秦汉子、秦琵琶)、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各自的历史渊源。
经过十五年后重读,笔者认为,《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的意义远不限于对琵琶乐器史的开拓性贡献,至少还在三个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第一,为采用国际视角对丝绸之路音乐史进行研究,提供了范本;第二,为文献与文物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提供了新思路与新实践;第三,对中国东方音乐研究的学科建设在新世纪打开新局面起到奠基作用。
以下拟从这三个方面,分别阐述该文的学术贡献与历史意义。
一、国际视野下的丝绸之路音乐史研究
中国本土包括乐器在内的原发性器物,有其命名规则,即均以单个汉字命名。如今日所说的“衣裳”“跋涉”等,在先秦时期分别为“衣”与“裳”,“跋”与“涉”,内涵迥异,不可混淆。见诸于各种史籍中的周代“八音”乐器,也都如此,例如:琴、筝、瑟、笛、筑、鼓,等等。
而以两个以及两个以上多个汉字命名的乐器多由域外引进,并集中出现于张骞通西域以后,筚篥、箜篌、琵琶等便属此类。东汉末年刘熙所撰《释名》最早提到:“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2]113。因此,厘清这类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乐器的来龙去脉,必须逆流而上,回顾其发源之地。
据笔者所见,最早有意识地运用中国以外考古发现,对阮咸、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的关系与渊源进行考察的著述为日本学者林谦三出版于1962年的《东亚乐器考》[3]。
在该书第三章“弦乐器”中的“阮咸与五弦阮”“琵琶的定弦规则及其变迁”“五弦与搊琵琶的异同”三节中,分别对三件乐器的部分形制进行了考察。在“阮咸与五弦阮”中,林谦三曾专门考察了斯坦因在高昌故地阿斯坦那(Astana)发现的绢本画残片、东京艺术大学所藏白玉弹琴妇女像、正仓院藏金银平纹琴面画、洛阳西郊唐墓螺钿镜四种发现于中国境外的与阮咸相关的乐器图像的区别。“琵琶的定弦规则及其变迁”中,对伊朗四弦四柱琵琶、唐传日本四弦琵琶的定弦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五弦与搊琵琶的异同”中通过对古印度阿摩罗福地浮雕、正仓院藏五弦琵琶的比较,推断出在龟兹地区,印度传来的本为指弹的五弦琵琶受到来自波斯的四弦琵琶拨弹奏法的影响,改作拨弹。[3]245-293
《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是对三种琵琶形制渊源关系的探讨,显然较之《东亚乐器考》又大大前进了一步。首先,论证四弦曲项琵琶在汉代经由波斯传入中国新疆地区,解答了《通典·乐四》中,“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自胡中,俗传是汉制”[4]338的疑问。其次,论证了五弦琵琶与公元2世纪印度琵琶一脉相承的关系及其借助佛教经由龟兹传入的历程。再次,成功论证了阮咸的产生过程。提出在弦鼗与阮咸之间,有过一个秦汉子,或称作秦琵琶的过渡阶段的观点,即弦鼗经过模仿两晋时期大量进入中原的四弦曲项琵琶,最终形成秦琵琶,从而解答了阮咸在南北朝时期突然出现之谜。
《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之所以能够廓清千年以来不曾阐述清晰的丝绸之路琵琶流变史,主要的原因就是将历史考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亚洲。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前人研究中错误的由来:
对琵琶的历史考源仅从我国境内这一段史料来进行推论是难以达到完整而准确的答案的。因为它是一件孕育、发展、成熟、展衍于整个丝绸之路上的乐器,去头截尾、腰断的论述是难以厘清其历史脉络的,因而出现谬误也是在所难免的。[5]47
可以说,《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中,横贯整个丝绸之路的详密考证,对三种琵琶的形制渊源,成功地展开跨越国界的追索,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其他乐器流变提供了范本,是丝绸之路音乐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二、二重证据法的新实践
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给清华大学学生印发的《古史新证》中讲道: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6]2
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史学中最受瞩目的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强调文献史料与考古发现史料结合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自此之后的近一百年,借助地下考古发现论证古史,成为推动20世纪史学进步的重要方法论。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新视角与新史料的不断拓展,二重证据法的局限性逐步浮于水面。据笔者总结,学术界对二重证据法的反思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依赖有文字的考古实物,忽视无文字考古材料所包含的信息。第二,重视埋葬品研究,忽视传世品的史料价值。第三,重视文本史料与考古实物的互证,忽视考古发现与传世品之间,以及考古发现之间的互证。
《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所呈现出的广博与灵活,为二重证据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实践。这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境内外包括古代文本、雕塑、绘画在内的多种史料选择上的拓展,以及处理上的运用自如,更重要的是实践了以时间维度辩证地下考古发现与传世古物所包含信息之间关系的成功范例。下面具体举例说明。
史料选择上的拓展与运用:
论证四弦曲项琵琶由来问题,最重要关隘是要论证《通典》中所说的“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是否可信。为了考察四弦曲项琵琶自汉代进入中国的历程,《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自新疆出发,逆流而上,通过追溯6至7世纪波斯萨桑王朝Barbat琴、3世纪下半叶至6世纪龟兹古都壁画、1世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犍陀罗浮雕艺术、1世纪前后古希腊Barbiton琴,论证了四弦琵琶进入中国前的状态及进入中国的时间。在没有其他类型出土实物的情况下,画像与浮雕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弥足珍贵。
王国维先生原创的二重证据法由于对不带有文字的考古史料和地上考古史料的忽视,而体现出的局限性,早已被学术界认清并突破。但是,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采用多重材料辩证分析的案例,仍然很少。作为一个史学研究传统极为悠久的国家,我国学界对个别领域文本史料的解读已近乎极致,若要继续尝试依靠极为有限的文本史料的分析来进一步探索琵琶流传史的真相十分困难。因此,任何拓展史料范围的工作,其积极意义远超出所解决的具体问题。
再看从时间维度辩证考古发现与传世古物之间关系的应用范例。
位于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中所收藏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唯一传世的唐代五弦琵琶。《通典》“历代沿革”与“龟兹乐”两节中提到在5世纪北魏宣武帝时期,由吕光击破龟兹而得来的五弦琵琶已经十分流行。
《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从《通典》中这两段文献出发,进行了三点考证。首先,通过考察龟兹地区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壁画,证实了3世纪后期至5世纪时五弦琵琶在龟兹地区随佛教艺术盛行而繁荣的局面,找到了中原地区五弦琵琶直接源头,与《通典》中的记载形成前后对接。其次,从龟兹出发上溯到印度,以佛教艺术为线索,以印度甲古他博物馆所藏公元170年阿玛拉为缇石雕中的五弦琵琶乐伎,考察了五弦琵琶在印度的源头,与龟兹壁画形成对接。再次,从日本史料《续日本纪》中对遣唐使藤原贞敏在唐朝学习琵琶,并于回国后为仁明天皇演奏的记载,说明在9世纪琵琶已经成为日本上层社会中极为流行的乐器。自此,正仓院中的传世珍品,借助考古史料找到了源头。五弦琵琶这件盛行于唐代,但是自宋代就已销声匿迹的乐器,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脉络终于清晰可见。
依据文献寻找传世品的来历,有其天然的缺陷,即不能精确地证明文献中的材料与眼前实物的关系,特别是像五弦琵琶这类已经早已不流行的器物。从这个角度看,以考古实物作为补充证据,优势十分明显。《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中对正仓院所藏唐传阮也做了与五弦琵琶相似的源流梳理,但是对五弦琵琶的论证更为典型,在此不做赘述。
总之,利用多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史料进行学术研究的先例早已有之,但是就中国音乐史学界而言,达到《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水准的研究还不多见。
三、东方音乐学科的新起点
中国近代的东方音乐研究最早发端于王光祈先生留德时期完成的比较音乐学著作《东方民族之音乐》《东西乐制之研究》。而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入高等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则源于上海音乐学院沈知白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的呼吁及身体力行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至60年代,以亚非拉地区的音乐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东方音乐学科渐具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由于沈知白先生的首倡,上海音乐学院逐渐成为国内东方音乐研究中心。“文革”结束后,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首届东方音乐学术研讨会重启东方音乐研究热潮。90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招收东方音乐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1999年,饶文心教授作为国内第一个东方音乐专业博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导师为沈知白先生弟子赵佳梓教授。1999年,赵维平负笈东瀛十载后返回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并于2000年开设东方音乐概论课程。至此,东方音乐学科在上海音乐学院完成了从沈知白到赵佳梓,再到赵维平的学术接力。
然而,纵观国际学术界,21世纪以前,我国的东方音乐研究完全不能与中华民族在古代东亚地区以及今日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力比肩。1987年,参加过在中国召开的首届东方音乐学会的日本学者岸边成雄指出:“在大会中所读到二十八篇论文多数以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主要对象,这是不得已的。”[7]34究其原因,他认为是由于研究资料的匮乏,以及“中国派往亚洲、非洲,进行传统音乐调查研究的人还极少。”[7]34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音乐学界重启东方音乐研究时的真实情况。虽然不能说中国传统音乐不属于东方音乐研究的范畴,但是东方音乐的学科属性显然主要应当是着眼于音乐文化在以亚洲为中心的整个东方范畴的流动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以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兴起,不少学者走出国门,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的传统音乐进行实地考察,发表了一系列属于东方音乐研究范畴的成果。随着东方音乐专业在音乐院校的设置,学术梯队开始逐步形成。但是,在规模与影响上仍然十分有限,真正着眼于从“东方”这一特定范围进行研究的较少,特别是与邻国日本相对比就更为明显。
据岸边成雄归纳,日本东方音乐研究在近代经历了三个时期:1936年以前,以田边尚雄为代表的时期;自1936年日本东方音乐学会成立到1955年左右,以林谦三、拢辽一与岸边成雄为中心的时期;1955年以后,小泉文夫留学印度开始的时期。[8]82相信对于中国音乐学人而言,不必罗列上述人物的研究成果,即可知两国在东方音乐研究领域的巨大差距。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奋起直追的我国东方音乐研究很大程度上也与受到日本学界刺激有关。
直到进入21世纪,东方音乐学科在中国才真正迎来了繁荣的时期。从学术团队上看,上海音乐学院每年都有东方音乐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入校或毕业,随之而来的是一批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和有志于从事东方音乐研究的学者。其他音乐院校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专业中也有不少致力于东方音乐研究的师生。宁波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相继召开东方音乐研究高端学术会议。2018年,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东方音乐研究院成立,《东方音乐》多媒体丛书进入实质编纂阶段。从学术成果上看,应有勤、韩宝强、赵维平、饶文心、喻辉等学者的研究已处在十分前沿的位置,可以说不输于早期的日本东方音乐学界。
那么,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对于中国人的东方音乐研究而言,在缤纷复杂的东方音乐门类中,应当以哪一种课题为中心?
笔者认为,基于数千年来,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对周边文明起到的巨大的吸收与辐射作用,中国的东方音乐研究的重心必然集中于中国与亚洲各国,尤其是东亚诸国的音乐交流方面。这不仅出于研究本身的便利,而且关乎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一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和融合曾对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生态产生重大影响,是古代“东方”的主体。前辈学者涉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著述,如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等,已经有意识地从这一角度进行过探讨。
厘清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不仅对解决中国古代音乐史中的许多难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有助于古代曾受到中国影响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等国音乐史的书写。这既有助于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提高中国音乐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地位,也对整理古老的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对于东方音乐学科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琵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交流最为开放的唐代盛极一时的乐器,日本和朝鲜的琵琶也在这一阶段经由中国传入,至今仍是传统音乐的重要乐器。对于东亚地区,琵琶的影响远远超出音乐文化的范畴,产生了无数精美绝伦的诗作、壁画、雕塑。贯通丝绸之路,探索琵琶在东亚地区流变历程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作为丝绸之路中段的中国在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上起到的作用。
综上所述,这篇18000余字的长文对琵琶在亚洲的历史源流的论证,超越了前人(特别是日本学者)在琵琶源流历史研究方面的已有成就,取得了琵琶历史源流研究这一广受东亚学者瞩目的课题的突破性成果,标志着中国学者的东方音乐研究走向成熟,是中国东方音乐研究的新起点。
结 语
现在再次回到《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该文之后,赵维平的两部专著可以视作《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的后续。《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东流日本的研究》(2004)从音乐体裁、乐器、乐谱、音乐制度方面论述了中日音乐交流的历史。《中国与东亚音乐的历史的研究》(2012)将历史上中国与同处东亚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的音乐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将中国音乐文化定义为“自我完善” 型,将日本音乐文化定义为“以自我文化视角解释外来艺术”型,将朝鲜和越南定位为“全面接受中国文化”型,对于透过中国看东亚文化形成,具有很高的启发意义。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音乐学界渐渐将目光再次凝聚于丝绸之路,这一领域的研究早已突破中国音乐史、东方音乐的范畴。但是即便如此,《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所提供的研究方法与学术成果仍然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