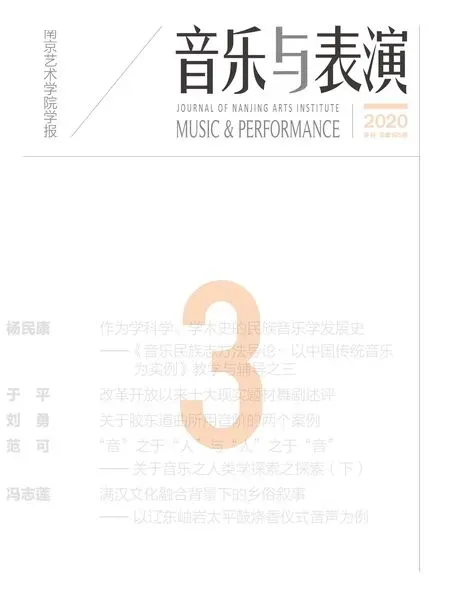“末泥”演剧形态考①
——以宋金元戏曲文物为例
楚二强(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中国古典戏曲由萌芽发展到最终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宋元戏曲史》中所言:“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1]。在此,王先生准确道出了中国戏曲的遥远源头。然而,直到元代,它才逐渐摆脱以往的混沌状态,并将包括巫、优表演在内的各种伎艺融为一体,最终造就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座高峰——元杂剧的到来。隋树森也在其《元曲选外编》前言中说:“根据极不完备的统计,在元代不到一百年的时期中,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就有一百余人,见于书面记载的杂剧名目也有六七百种。”[2]在有元不足百年间,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先后形成了几大演剧中心,据元人夏庭芝《青楼集》所记,可知在当时社会,已出现众多搬演杂剧的男、女艺人,他们以己所擅,将这“前无古人”式的伎艺搬演于氍毹,从而在中国戏曲上史上留下了惊鸿之一瞥,由此可见,这门艺术演出之盛。
众所周知,元杂剧繁盛局面的到来得益于前一个时期的表演艺术——宋金杂剧的滋养,它为元杂剧的发生、繁盛做了准备。可以说,二者具有深远的联系。对于宋金杂剧具体演出形态的考察,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史料记载为基础,以“文本内证”为主。然而,随着近年来大量戏曲文物的陆续发掘、出土,为这宋金元时期杂剧演出状态提供了便利。它不仅还原了宋金杂剧的演出形态,为研究提供了形象直观的佐证;而且,亦证明了宋金杂剧色发展到元代戏曲脚色,其具体职能于剧中地位的变化,尤其是元杂剧中担任主唱的末泥,由宋金杂剧中的作为配角,一跃而为元杂剧中主角。笔者以为,通过对比两个阶段的文物可探寻“末泥”转变的蛛丝马迹,他之所以在元杂剧中充当主唱地位的状况的发生并非偶然,实际上早在宋金杂剧繁演时期,已开始酝酿。基于此,笔者首先探讨宋金杂剧色之职司及末泥的演出形态。
一、宋金杂剧色之职司
关于宋金杂剧演员、表演形态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代文人笔记小说中。以《梦粱录》与《都城纪胜》的记载为例:
在《梦粱录》“娱乐”条记:“且谓杂剧中末泥为长,每一场四人或五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3]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亦载:“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4]
可见,两部书的记录基本相似,都指出宋金杂剧的五个演“杂剧色”及具体职司。两处记载之所以称呼末泥、引戏、副净、副末为杂剧之“色”,是因其还不能指代具体戏曲脚色行当。元鹏飞认为,这样的称呼验证了“杂剧色”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一个名词而单独存在。[5]笔者认为,从历时性发展角度来看,对这一称呼的体认,于中国戏曲而言,恰恰说明了宋金杂剧、杂剧色在元杂剧形成前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态而存在。而纵观目前学界对其所做研究,就其演出形态,目前已形成普遍共识,认为可大致分两段,在其上演时,“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两段。”这一说法也为方家学者广征博引。
而其五个杂剧色的具体演出形式为何,研究者多从以上所列宋代文献史料中寻求论据,其中征引最为普遍的即为皇宫庆典仪式上的宋杂剧演出。由《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第四盏“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打和”可知,杂剧色已配合参军色的指挥,在演出过程中,进行“打和”。而另一部笔记《武林旧事》卷一“圣节”条“天基圣节排当乐次”中,“第五盏”“第四盏”“第六盏”等的记载可知,参与其中的杂剧色共有十五人,黄竹三先生在其所编《中国戏曲文物通论》中认为:“将这15人分成三组,每组五人,正好为一组完整的杂剧脚色。”[6]关于这种推论,如若将其与《武林旧事》“乾淳教坊乐部”条所记“杂剧色”比对,很显然,在其下所记载五个部门:“德寿宫”“衙前”“前教坊”“前钧容直”“和顾”,其人数由两人至三十人不等,而未出现十五人的队伍。然而,在同条“杂剧三甲”中所记“盖门庆进香”“内中祗应”“潘浪贤”三甲中,分别有五人的记载,因而,不难看出这种推测具有合理之处,同时也不排除参与“天基圣节排当乐次”的杂剧色为“杂剧三甲”的可能。
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得知在皇宫庆典仪式时,这些杂剧色的具体职司,尤其是在“杂剧三甲”中虽也记载具体杂剧色,但对其演出状态还未涉及。虽然在文字记载中,我们已知这些杂剧色所担任的具体职司,而且在宋金杂剧中副净、副末为主要表演者,除进行插科打诨等滑稽表演外,亦有偏重于歌舞、故事表演等综合性较强的形式。[7]22-29但其他杂剧色于具体表演中实际演出为何,尤其是“末泥”所从事的“主张”到底为何?笔者以为在现有资料不能明晰的情况下,大量戏曲文物的存在,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宋金杂剧砖雕之末泥
宋金杂剧作为曾经盛极一时的艺术表演形式,随着元杂剧、明清传奇的兴继,而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并不能否认它对于中国古典戏曲的开创之功,一个最为重要的显征就是宋金杂剧“末泥”色对元杂剧“正末”的影响。以往的论述大多认同宋金末泥色对元杂剧正末的影响,宋金杂剧色对中国戏曲行当的重要影响,在此不赘述。
在元杂剧中,担任主唱,作为剧中主角的往往是正末,并于剧中一唱到底。而宋金杂剧“末泥”,或宋金杂剧色的具体演出如何,则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以上《梦梁录》《都城纪胜》中出现的五个杂剧色为宋金杂剧中的角色,景李虎在其《宋金杂剧概论》中则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认为,“末泥”“引戏”为一类;“副净”“副末”“装孤”为一类。并对五个杂剧色的具体职能进行了分析:“副净色‘发乔’,即刁滑、古怪、乖戾;副末色‘打诨’,表演中多滑稽的语言和动作,逗人发笑;装孤色就是假扮官吏。”[7]82“末泥”则为演出的主要负责人,“引戏”在演出中从事介绍剧情,指挥调度,并列举具体文物中的形象加以佐证。笔者认为这些分析与宋金杂剧色实际演出中相符,然而,通过罗列宋金戏曲文物中的杂剧形象,引起笔者的质疑:宋金杂剧色中末泥是否仅“主张”,五个杂剧色是否逢演皆具?由车文明先生主编《中国戏曲文物志 四》中宋金时期杂剧盛演的两个地区山西与河南目前出土的宋金杂剧文物来看。
在现存山西宋金杂剧文物方面,有关宋金末泥色的实物以砖雕居多,有四处:
(1)山西省稷山县马村段氏五号金墓杂剧砖雕,共两排,后一排为乐师,正作吹乐状。前一排为四名杂剧色,其中从左至右第二人为末泥色,戴朝天脚幞头,短袄长裤,系带,右手执一木杖,举于胸前,无引戏。
(2)山西省稷山县化肥厂金墓杂剧砖雕,在其南壁有杂剧人物四,第二人戴尖耳翘脚幞头,穿圆领长袍,腰系博带,左手握右手于胸前者为末泥色,无引戏。
(3)山西省稷山县化峪镇三号金墓杂剧砖雕,南壁镶嵌杂剧砖雕五块,为浮雕形式。一砖一人,其中自左向右,第四人为末泥色,戴无脚幞头,穿圆领长袍,双手执一竿,五人中亦无引戏者。
(4)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宋金墓杂剧砖雕,杂剧砖雕五块,其中杂剧演员三人。从左向右第二人为何色不详,第四人为末泥,也是戴幞头,方领窄袖长袍,左手执一杆杖,有引戏。
河南所存宋金杂剧文物砖雕方面,则多达九处:
(1)河南省荥阳市东槐存朱氏墓石棺北宋杂剧线刻,线刻展示出来的场面为四位杂剧演员正在表演,左起第一人为末泥色,头戴东坡巾,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执棍杖,左手向前指。无引戏色。
(2)河南省禹州市白沙镇北宋墓杂剧砖雕,砖雕四块,左起第一人戴花脚幞头,穿直裰者为末泥。无引戏色。
(3)河南偃师市李村酒流沟水库北宋墓杂剧砖雕,六块砖雕中,三块砖雕上刻有五个宋金杂剧色,依次为引戏、末泥、装孤(末泥、装孤为刻于一块)、副净、副末(副净、副末刻于一块)。末泥为左起第二人,装束与前基本相同,右手持官印,左手指对面一人,正在说话。
(4)河南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杂剧砖雕,绘有五人,左起第一人为末泥,与其他不同的是其所戴为东坡巾,耳后插翎毛,左手执顶部涂有赭黄色骨朵子。
(5)河南省温县博物馆藏宋金杂剧砖雕之一,砖雕五块,一砖一人,五人分别对应宋金五个杂剧色,左起第一人戴介帻,双手执一短棒,“似为末泥色”。
(6)河南省温县博物馆藏宋杂剧砖雕之二,砖雕两人,其中双手执棍杖者为末泥色,无引色。
(7)河南省温县西关宋墓杂剧散乐砖雕,五块砖雕,对应宋金五个杂剧色,左起第一人为末泥色,其头戴软巾,右手执一棒槌左手二指伸入口中打口哨,作跳跃之势。
(8)河南省义马市金墓杂剧砖雕,四块砖雕中,右起第一人为末泥色,双手执竿。无引戏色。
(9)河南省洛阳市关林宋墓杂剧砖雕,共三幅杂剧图五人,对应宋金杂剧五色。其中,左起第一幅图绘有杂剧色二,左一人右手捧印匣,左手指右侧人者为末泥色。
由以上出土杂剧砖雕来看,在具体杂剧演出过程中,在宋金杂剧中五个杂剧色地位不一。在“末泥”“副末”“副净”“引戏”“装孤”中,副末与副净为宋金杂剧主角,是杂剧活动的主要表演者,并于表演过程中进行“插科打诨”表演,且于演出中处于主导地位,二者缺一不可,而其他杂剧色均为其服务,配合其演出,因而处于次要地位。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这些文物亦能看出,在宋金杂剧演出中,杂剧五色并非均为杂剧演出的必备要素,也即某些杂剧色甚至可以省略不设。例如,司职“分付”的引戏色,在上述杂剧文物中,有七处杂剧砖雕未设引戏色,引戏未出现的同时,又往往有末泥色的出现。那么,当“引戏”色不再登场时,其所担任的职能,笔者以为当由末泥色承担,这主要源于末泥“为长”的地位。首先,“副末”“副净”主要是参与杂剧表演,无法执行“分付”职司,否则将会影响杂剧演出的正常进行;其次,“装孤”色有时只是在剧情需要时才会添加,故而在宋金笔记小说中往往出现“或添一人‘装孤’”的描述。当然,除装孤色外,有时在杂剧中也会出现装旦色。因此,既然以上三个杂剧色因为演出需要皆无法兼代“引戏”色“分付”职能,那么执行这一杂剧色职能的就只有“末泥”了,故末泥色在演出过程中除了做好分内事外,还要兼职执行“分付”。因为引戏色在表演中的功能与末泥色较为相似。
关于末泥色因何能兼职引戏职能,如果仅靠文献记载为依据,利用“文本内证”法推测,似乎无法推知这一结论。而从以上所列众杂剧色形象,为我们认识末泥提供了方便,笔者将对此做一简要阐述。首先,上述所列末泥形象,其手中持木制类砌末出现时,在杂剧表演中,引戏似乎都不存在;其次,长期以来,已有学者认同引戏源于参军色的事实。黎国韬认为:“引舞即参军色,参军色生出引戏系共识。”[8]胡忌在其《宋金杂剧考》中也赞同此观点:“明白了‘引戏’(参军色)和‘舞头’的意义以后,就可推知‘引戏’和‘戏头’是从大乐(舞蹈)中模仿而得的产物了。”与墓葬中出土的末泥手持棍棒类砌末相同的是,宋金杂剧参军色在表演时往往会持竹竿子作为道具进行勾队表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载:“第四盏,如上仪。舞毕,发谭子。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和……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宰臣酒,独打方响……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9]在此表演中,参军色总是手持竹竿子,故而在宋金杂剧中无论是认为引戏来源于参军色,还是引戏就是参军色,则二者有一共同特征,引戏继承了参军色念诵伎艺,手持竹竿。最后,从后世文献中,对于末泥的描述来看,其也具有唱念表演,学界经常引用的两个例子,一为《水浒全传》八十二回咏末色:“裹结络球头帽子,着筏役叠胜罗衫。最先来提掇甚分明。念几段杂文章真罕有。说的是敲金击玉叙家风,唱的是风花雪月梨园乐。”廖奔先生认为:“所咏或即末泥。则末泥在剧首上场,有念有唱”[10]。另一则为明代汤式《笔花集》“新建勾栏教坊宣赞”散曲中记载:“【二煞】捷剧每善滑稽能戏设,引戏每叶宫商解礼仪,妆孤的貌堂堂雄赳赳口吐虹霓气。付末色说前朝论后代、演长篇歌短句、江河口颊随机变,付净色腆嚣庞、张怪脸发乔科冷诨、立木形骸与世违。要挆每未东风先报花消息,妆旦色舞态袅三眠杨柳,末泥色歌喉撒一串珍珠。”[11]以上两例均指出末泥的具备唱念技艺。
因此,作为宋金杂剧演出中的执事人员,而非具体参与演出的脚色,在杂剧扮演过程中,末泥既然与引戏具有类似功能,末泥也就可能代替引戏职司,这也就是上述所列文物中为什么当末泥出现时引戏未出现,末泥为什么手执棍棒类、竹竿类道具的原因。
三、元杂剧戏曲文物之正末
元杂剧作为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不仅体现在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作家,产生众多优秀的杂剧作品,更表现为有元一代,它作为“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国维先生曾在其《宋元戏曲史》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2]王国维对于元剧给予了高度评价。
元杂剧根据其主唱脚色的不同,可分为末本戏与旦本戏两大类。对于末本戏中主唱脚色正末,有时又可省称作“末泥”,简称为“末”。在元代夏庭芝《青楼集》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皆有相关表述,在此不赘。与宋金杂剧中“末泥”相比,元杂剧中末泥的具体演出形态,似乎从文本来看,仅能知其作为剧中主唱,通过唱辞介绍剧情,并推动故事情节发展。而如若从现存元杂剧文物入手,似乎更能见其生动的演出场景,此处试以目前现存的两处元杂剧文物以例: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元代戏曲壁画与山西省新绛县寨里村元墓杂剧砖雕。
山西洪洞广胜寺水神庙壁画,该画绘于元泰定元年(1324),帐额书“尧都见爱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 泰定元年四月日”。此话交代了杂剧演员中都秀于此演戏的情景。画中演员、司乐等共计十一人,演员、司乐分两排,前排五人为演员,居中一人,手持笏板,脚穿乌靴,仅仅露出脚尖者,容貌清秀,应为杂剧主唱兼主要演员中都秀。周贻白先生也推测居中之人,“这也许就是帐额所题的主要演员‘忠都秀’吧!”[13]从其名字来看,其中带一“秀”字,符合元杂剧中女性演员称呼,在《青楼集》中,名字中带“秀”字者多达几十人,故中都秀在《青楼集》中虽未见载,但仍可知其该戏班中的主要演员,且为女性;其次,从其容貌特征来看,微髭,双耳缀以金环,脚甚小,故其当属女性无疑。关于其所演剧目名称虽至今未知,但从其戴展脚幞头,穿圆领大袖红袍,手持朝笏,综合其他演员手持之物及其装扮可推知,其所演当为末本戏,作为女演员的中都秀在剧中所扮人物应为男性官员,并作为剧中“正末”(末泥)形象而存在,故在绘画中人物所占位置亦十分讲究,中都秀作为主要演员,居中站立面向观众。与之几乎同一时代的另一元杂剧文物“山西省新绛县寨里村元墓杂剧砖雕”[14]34也反映了这一情形,该墓于1963年发现,建于元至大四年(1311)二月。墓内存砖雕五块,每块一人。自左向右,第三人穿戴与“忠都秀”无异,并双手执笏,故其所演也应为末本类戏。与宋金杂剧砖雕所展现出不同的是,此元墓杂剧砖雕中虽然也有副净、副末,但其在演出中位置已退居其次,反之,末泥后来者居上,在元杂剧演出中占据主要地位,“自左至右似为装旦、装孤、末泥、副净、副末,末泥居中,反映了元杂剧末泥主演的演出体制。”[14]34-35
这与洪洞水神庙元杂剧壁画所展示出来的情形相一致,反映了我国戏曲脚色的发展与演化,也反映了宋金杂剧中末泥与元杂剧末泥演出之差异。随着戏曲艺术的逐渐成熟,末泥职能与剧中地位亦随之发展,由不参与杂剧搬演转变为剧中主角。且其人物性别亦相对宽泛,在元代女性亦可扮演“末泥”在剧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反映了脚色制的发展,也反映出元杂剧艺术的繁荣景象。
可见,就宋金杂剧而论,在其具体演出过程中,五个杂剧色并非均需参与其中,有时只需末泥、副末、副净即可开始一场宋金杂剧的搬演。同时,在演出过程中,末泥有时除司职“主张”外,从其手持砌末来看,有时也会直接参与杂剧演出,甚至出现末泥承担引戏色“分付”的职能;就元杂剧言之,由山西省新绛县寨里村元墓杂剧砖雕中,所存杂剧演员五人来看,结合宋代笔记小说中所载五个杂剧色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元杂剧在演员组成体制上,深受宋金杂剧五个杂剧色的班社组织形式的影响。
综上,如前文所述,洪洞广胜寺水神庙戏曲壁画中的大都散乐人忠都秀所演为末本戏,那么,由壁画中前排参与演出的五人来看,其受宋金杂剧“五人制”的班社组织的影响更加形象直观。并且除人员数量上受其影响外,在元杂剧演出中,其主唱脚色正末手持砌末这一标识来看,也与宋金杂剧文物中末泥色高度相似。因而亦能由此管窥中国戏曲脚色 末泥色的大致演变路径。对此宋金杂剧末泥砖雕与元杂剧末泥形象,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在元杂剧中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末的职能,早在宋金杂剧繁盛时期,已由艺人对司职“主张”的末泥色的演出职能进行了改造:由不参与杂剧演出,处于配角地位向后世戏曲中处于主唱地位过渡性尝试。
总 结
综上,宋金杂剧与元杂剧都具有各自独立的演出体制。结合目前现存戏曲文物能获得二者中演员组织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其中宋金杂剧“末泥”与元杂剧“末泥”,二者显然在演出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元杂剧中居于主唱地位的末泥,实际在宋金杂剧中,已经偶尔会参与到演出过程中。通过对比两种表演体制下的脚色形象表明,在宋金杂剧演出中,已有人对末泥的表演职能进行了尝试,即突破由副净与副末二人占据主导地位的体制,由末泥扮演,扩大其于演出过程中的职司。这种大胆的创新,在元代已得以普遍实行,并最终造就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座高峰的形成。